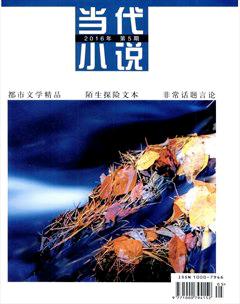菱花
杨志罡
1
我越来越潦倒了,一场大病,不仅害得我丢掉了原来不错的工作,还差不多花光了我的积蓄。我都付不起房租了,可我总得住房,没有办法,我只好从繁华的市中心搬到了偏远的郊区。可即便如此,我也只能租最便宜的那种,一间位于楼房最顶层的铁皮房。我没带什么行李,所有值钱的东西我都卖了,就剩下一把卖不出去的二胡。在我刚搬进铁皮房的第一个晚上,我怎么也免不了伤悲。我一伤悲就拉起了二胡。我拉的是《二泉映月》,这是我惟一会拉的曲子。拉着拉着,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不久,我听到了敲门声。我问是谁?一个娇滴滴的女声回答说是我。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将门打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刚冲过凉头发还湿漉漉的女孩,穿一件粉红色的睡袍,不说话,就笑盈盈地站在门口嗑瓜子。我结巴地问:你是……
我是你隔壁的邻居。女孩一边说,一边示意了一下她自己住处,那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的大单间,远非我的铁皮房可比。
我可以进来听你拉二胡吗?
欢迎。
女孩走进门了,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
嗑瓜子吧。女孩抓起一把瓜子递给我说。
我说我这几天嘴疼,嗑不得瓜子。这是谎话,这一谎话刚一出口我就后悔。我后悔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嗑瓜子,而是因为我将女孩的好意轻易拒绝了。不仅如此,我还像有心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正人君子,故意坐到了床角。因为我撒谎说自己嘴疼的缘故,女孩盯住我的嘴看了半天。我有一些心虚,以为她看出了什么破绽,她却突然以大夫的口气说:你肯定是上火了!
女孩围绕上火的话题扯个没完没了,一边扯一边嗑着瓜子。我的表情慢慢地放松了,装作饶有兴趣地听她闲扯,其实是在借机欣赏她的脸。我想吃瓜子,不是女孩手里的瓜子,而是她的脸,她的脸也是一颗瓜子,一颗最大最大的瓜子。我开始流口水,如果女孩一直不停地闲扯,我想我早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还是听你拉二胡吧,我就想听听你拉二胡。
女孩像猜到了我心思似的,突然就停止了闲扯,于是,《二泉映月》又从我的手指间流出来了。
你怎么老是拉这个曲子?换个新鲜的吧。
我脸红了,可也只能厚着脸皮说,我就会这个曲子。
女孩像有些不相信地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你怎么就会这个曲子呢?
因为我太笨了,别的曲子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可是这个曲子你却拉得棒极了。
因为这个曲子简单些,连一个瞎子都会拉。
我胡扯一气,自然,我说的瞎子就是阿炳。话一出口,我就在内心赶紧请求着阿炳的原谅。事实上,阿炳是我最尊敬的人物之一。
可以教一教我吗?说话的时候,美女笑出了两个迷人的酒窝。
我把二胡搁到美女手里,教导她该怎样怎样。看她不得要领,我干脆手把手教她。女孩的手柔软而又光滑,让我一握住就不肯放了,而她本人好像也不介意我这样,当然,要想把二胡学会,让师傅碰一碰手,那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我没心思教二胡了到最后,我的脑袋都搁到了女孩的香肩上。她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明白了什么。
你坏!你坏!
女孩皱了皱眉头,做出一个挖我眼睛的手势,可是最终并没有将我的眼睛挖出来,只不过轻轻刮了刮我鼻子而已。我试着用手去摸女孩的瓜子脸,女孩也不躲闪,相反像是在期待我这样做似的,静静地一动不动,只有她的小嘴在微微地张合。没容我退缩,女孩立刻就将她鲜红的小嘴堵了上来,跟着又用两条柔薏似的手臂紧紧箍住了我……
接下来的细节我无须述说太多,我只是惊讶,自己大病初愈的身体怎么简直就是一种兽性的疯狂,在它的冲击下,所有的事物,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难免毁灭。我心甘情愿接受毁灭,有毁灭才有新生,才有今后美好生活的开始。我要说一切都是无比美好,在我大病初愈过后,在我刚刚搬进廉价铁皮房的第一天,这美好的开始令我对未来重新生发了奢望。
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在缠绵的梦乡被一阵走调的音乐惊醒过来,这是情人拉的二胡。我悄无声息地爬了起来,紧紧将她搂抱在怀里。我还要亲吻她,可是这一次,她将脸避开了。我想,她一定是怪我还没有刷牙吧?
接着我就问她名字。真是疏忽,我跟她都发展到了这一步,却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告诉我她名叫菱花。我问是菱角的菱吗?这名字真好!她说名字好有什么用?名字好也不能卖钱。好在我有身体可以卖钱。对了,你快些给我钱吧,我马上要去上班了。
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迟疑地问:钱?你是叫我给你钱吗?
你当然得给我钱!菱花明明是在诘问我,声音却依然是娇滴滴的,如果是在几分钟前,我会把这娇滴滴的声音当做音乐来欣赏,可现在不行了,现在我的肚子里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我知道不给钱是不行的,不给钱我就是强奸了,只要她说我是强奸,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洗刷不清,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请她开个价。她一开价就是三百块,还说是看在邻居的份上优惠的。我讨价还价,最后,她降到了两百。两百就两百吧。我叹息一声,从钱包里取出了两百块钱给她。现在,我的钱已所剩无几了。
菱花给了我一个飞吻,拜拜。我才不跟她拜拜呢,我黑着脸,也不看她一眼。菱花走出门外又转身对我说,你真可爱,太可爱了。我一听见这话就打了自己两耳光。我可爱吗?我可恨得要死,还有我的二胡也可恨得要死。我抓起二胡想把它砸烂,可我的手悬在空中砸不下去——我舍不得砸了,一把二胡,也是两百块钱呢。
2
一连好几天我都不再拉二胡了,我害怕菱花,害怕她再来骚扰我。我甚至不开灯,不开灯表示我不在铁皮房里面,自然,菱花就没办法来骚扰我了。也许菱花根本用不着来骚扰我,因为她总是能够逮到猎物,而且都是心甘情愿的那种。铁皮房有一面是混凝土结构,隔壁就是菱花的房间。很多时候,都会传来一阵有节奏的响动。偶尔,隔壁是沉寂的,那是因为菱花要在工厂里加夜班。这时候,我本来应该很高兴,可是我却高兴不起来。没有那种有节奏的响动来催眠,我睡不着了。
我讨厌菱花,可我又总在回味。我明白自己的人格出了毛病,可是,我没钱去给自己买药,而且即便有钱,我也不知道到底该吃哪种药才好。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能够挽救我,那就是二胡,可我迟迟不愿跟它重归于好。
我已经有一个多礼拜没有拉二胡了,一个多礼拜,我的人格越来越扭曲。我喜欢回味和她共度的夜晚,可我却讨厌她本人,每次碰到她,我都要故意黑着脸。菱花不跟我黑脸,她总是嬉笑着跟我打招呼,还给我飞吻。有一次她还问我,怎么好久没听你拉二胡了?见我不吭声,她又加了一句,好想再听你拉二胡哟。回到铁皮房,我对着二胡注视了很久,因为长久没人理睬它,二胡的表面都蒙上了灰尘,这使得它像一个没精打采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我注视了它一会儿,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抱起了它,又小心翼翼地擦去了蒙在它表面的灰尘。于是,二胡在我手里重新恢复了光泽。慢慢地,《二泉映月》又从我的手指间流出来了。乍一听见那旋律,我的人格就高尚了起来,这时候,所有的屈辱,都算不得什么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敲门声。我猜想肯定是菱花来骚扰我,一问,果然如此。我没有理她,继续拉我的二胡,不过我的心情已遭到了破坏。菱花好像故意要跟我捣蛋似的,将我的房门敲个不停,敲得墙壁、窗户和天花板都震动起来。我猛地将门打开,大吼一句:你有完没完?声音大得几乎要将我自己的耳膜震破。菱花故意显出一副受惊了的样子,可很快又嬉皮笑脸地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干吗对我这么凶?瞧我对你多好,专门给你买来了新鲜荔枝,你快尝尝吧。菱花说着就从我的腋窝下挤了进来,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床上。如果我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我完全可以将她轰出去。可不知怎的,我的心肠就是硬不起来。不过,我的面孔仍然是板着的。菱花剥了一颗荔枝送到我的嘴边。尝尝吧,味道可美呢。菱花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我说。我回了一句,少来这一套!话音刚落,荔枝就从我的牙缝里硬塞进来了。我本应该吐出来才对,可我没有吐,我把它在口中含了半天,最后居然嚼动起来。看到如此滑稽的情景,菱花笑了,她赶紧又剥了一个荔枝要送到我嘴里,我白了她一眼说,我自己又不是没手,还要你剥?现在,我开始自己伸手剥荔枝了,送上门的荔枝,不吃白不吃。吃了菱花又能把我怎样?我已打定主意,不管菱花施展什么伎俩,我反正不再同她上床就得了。
荔枝吃到最后,菱花拿起我的二胡说,怎么样?再教我拉一拉二胡吧。吃了人家的口软,尽管我知道菱花并不是真心要学二胡,可我也不好意思说出拒绝的话。没等我吭声,菱花早已拿起二胡,让它发出了狐狸一样的怪叫。我赶紧教训她说,你哪里是在拉二胡?简直是成心弄坏它!菱花就笑着说,你心疼是吧?那就教我呀,教会了我就不会弄坏你的二胡了。菱花话说到这个地步,我只好指点了她一下。她拉了拉,毫无进展,就一屁股坐到我腿上来了。
不行,你还得手把手教我。她嗲声嗲气地说。
我怎么啦?居然没有把菱花推开,我在一瞬间变得像木偶人一样,大脑一片空白。等到我惊醒过来,几根贱骨头都好像让菱花坐软了,怎么也使不上劲。谢天谢地,她只是把我的大腿也当做了一把座椅吧?这座椅不仅坐着舒服,而且方便我手把手地教她拉二胡。因为两人的身体贴在一起,手都是一个方向的,所以教起来也特别顺手,半个小时下来,菱花居然能拉出一段完整的《二泉映月》出来了。我忍不住称赞她说:你这个人还挺聪明的嘛。看得出来,菱花听到我的赞美很开心,可她很快又摇头了:我聪明什么?聪明就不会这样过活了。
多亏菱花提醒,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趁我这会儿还没有犯糊涂,我赶紧收神敛志,站起了身子。自然,菱花没办法赖在我身上了。
时候不早了,你快回去休息吧。
你要睡觉了是不是?菱花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说,那好,我们睡觉吧。我赶紧说你饶了我吧,我很穷,我真的很穷,你看,我连租房子都只能租最差劲的。
菱花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又扫了一眼房子,说,也许你的确不是很有钱吧。这样好了,你出一百五,这样的便宜去哪找啊?
菱花说着又开始脱胸衫,我赶紧又替她拉下。我说我跟你磕头好不好?说着我真的要弯下腿了。菱花叹口气,说一百吧。我就将门拉开了。菱花明白没戏了,摇摇头,啐了我一口说,你是个大笨蛋,天底下最笨最笨的大笨蛋!
这个晚上到了下半夜的时候,从隔壁传来地动山摇的响动。我明白菱花终于有了猎物,而且她故意制造比以往更大的响动,以此来打击我的神经。我一把抓过二胡,立刻,我又心平气和起来。我慢慢地拉起了二胡,拉起了永远不变的《二泉映月》,那悠扬的旋律,使得我隔壁的响动像是突然静下来一样。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二泉映月》,我知道这曲调绝对地不合时宜,可是没办法,我只会拉《二泉映月》,而且,只要我心安理得,我又何必在乎太多?
3
和二胡相伴的人,日子始终难熬。从前是阿炳,现在是我。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能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这种生活永远就像梦幻虚无缥缈。我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弱者,就畏惧在战场上跟人拼杀,尽管拼杀是我惟一的出路,我却只能退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蜷缩。我的形象越来越猥琐,也越来越害怕将自己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大部分的时间我都躲在铁皮房里,一把二胡,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没完没了地拉着二胡,拉着我惟一会拉的《二泉映月》,我恍惚觉得,自己已经超凡脱俗去到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那世界什么都是现成的,因而所有的人们都能和平相处。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我乐意沉醉其中。然而我始终还是一个人,是人就得用食物填饱自己的肚子,即便是最差劲的食物也得用钱买来才行。我的钱包一天天地干瘪,一想到这点我就心烦意乱。我尽量不去想这些,一心一意在二胡里面沉醉,在《二泉映月》里面沉醉,可是有人打扰我来了。我以为又是菱花,听着无休无止的敲门声,我比上次更加怒气冲天,嘴里骂着最肮脏的字眼,猛地将房门拉开了。可事实上,来的并不是菱花,而是一身肥肉的女房东。房东上门没可能有好事,她是来收取房租的。我没钱交房租,只能赔着笑脸跟房东说好话,求她尽量宽限几天。可是宽限又能如何?我依然没钱交房租。终于,房东要将我扫地出门了。扫地出门就扫地出门吧,大不了就是像乞丐一样睡大街,我所尊敬的阿炳不也睡过大街吗?而我作为阿炳的传人,睡一睡大街又有何不可?
然而我最终并未睡大街,因为有人拔刀相助来了。这拔刀的人就是菱花。拔刀是个比喻,她事实上并没有拔刀,而是从她自己的钱包拿出钱来替我将房租垫付了。事情还真有些碰巧,在房东正将我朝门外推搡的时候,菱花回来了,她本可以径直进她自己的房子,可她像是喜欢看热闹似的,偏偏要询问情由。我以为她会趁机将我奚落一番,正要落荒而逃,她却一把拉住我胳膊说,不就两百块钱吗?我替你出好了。
我回头看了菱花一眼,她说话的口气是极为认真的,一点不像是在开玩笑。很快,钱就从她手里拿出来了,也没有经过我的手,直接就到了房东的手里。房东自然是见钱眼开,钱一到手,就不再为难我了,可她肯定有些纳闷。不光是房东,我也有些纳闷,不久前还狠狠宰过我一次,怎么现在就成了一个助人为乐的侠女呢?难道她别有企图?可是对于我这样一个穷光蛋,她又能图到什么呢?还好,我刚开始有一些小人的想法,立刻就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不管怎样,菱花的行为都是值得赞扬的。我想对菱花说几句感谢的话,说些什么呢?好像说什么都是虚伪的,事实上,最能表达我谢意的就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都噙出了泪花。一个男人,居然在女孩子面前落泪,这太丢人了。我拼命克制自己,不让泪水再朝外流,可越是克制,眼睛就越是不争气。不过,菱花并没有认真看我一眼。
谢谢你,菱花,钱我会还给你的。
我终于说出了一句感谢的话,自然,在这之前,我将自己眼睛里的泪水也擦去了。
菱花打开她自己的房门,半个身子已迈了进去。她依然不看我一眼,用一种满不在乎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可不敢指望,像你这样天天赖在床上睡大觉,拿什么钱还我啊?你干脆去死得了。说完,菱花就把门嘭地关上了。我的脸刹那间火辣辣地烧了起来,菱花的话,无疑是给了我一记狠狠的耳光。我该怎样做?惟一的出路,就是拿起自己的武器,冲上战场去厮杀。我真的这样做了,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走出了铁皮房,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四处奔走,寻找着一个可能突然降临的机遇。虽然到了半夜我也没有寻找到它,可是我的内心却开始充实起来——被慢慢鼓胀起来的自信充实着。
我每天回到铁皮房的时间越来越晚,只有可怜的几个小时用来睡眠。自然,二胡也越来越被我疏远了。事实上,我是很需要二胡的安慰的,因为我每天从外面归来,都是遍体鳞伤。我知道二胡能够倾听我的诉说,能够为我抚平身上的创痕,可如果我求助于它,就只能证明我是一个弱者。我不能做一个弱者,如果是那样,就像菱花所说的,干脆去死得了。死固然不是一件难事,一死百了,轻松之极,只是,我欠下菱花的人情,又该如何偿还呢?我必须偿还菱花的人情,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欠过任何人的人情。出于维持自己做人的原则,我必须成为一个强者。我知道强者不是一下子就坚强起来的,我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又一次又一次地爬起。我已经跌倒了无数次,总有一天,我会牢牢地站住不再轻易跌倒的。这是命运的必然规律,明白这规律,我还有什么理由丧气呢?我不需要二胡的安慰,并不等于我完全不理睬它。我时不时还会抱起它,替它擦去表面的灰尘。我会当它是一个有嘴巴有耳朵的生灵跟它说话,是那种很轻松又很幽默的玩笑话,谁都不必放到心里去。我还会拉它,拉我惟一会拉的《二泉映月》,只不过,我不是为了拉给自己听,而纯粹是为了让二胡本身运动运动,或者说,给我所置身的环境增添一些活力。我即兴而拉,随心而止。连我自己也能够感觉到,我创造的是《二泉映月》本身之外的意境。
我时不时会碰到菱花,自从替我付了房租后,她一直对我不理不睬。她还能怎样呢?一个做她这种生意的人,只可能对着猎物才有笑脸。她没可能再将我当做猎物了,作为猎物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有钱。那天她说出那样的话,肯定认为我已不可救药。很多次我跟她打招呼,她都板着面孔从鼻子里哼一声,甚至不屑看我一眼。可是后来……后来她的表情慢慢地温柔了,那是因为,她明显感觉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这时候,她开始用眼睛看我了,可也仅仅是看一眼而已。尽管如此,我也像得到了巨大的鼓励,并在心里暗暗给自己加油。
4
我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做成了一单业务,赚了一笔不小的钱,这才是一个真正美好的开始,这美好的开始证明我并不天生就是一个弱者。当然,要想证明自己是个强者,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还钱给菱花。都到晚上九点钟了,菱花还没有回来,我猜想她今晚肯定又在加班。我反正睡不着觉,就边拉二胡边等她。快十一点钟的时候,菱花回来了,听她踩楼梯的脚步声,我就知道她很疲倦。她才到门口我就过去跟她笑着打招呼,她没有笑,却冲我点了点头,并用满是疑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菱花,我把钱还给你吧,我现在有钱了。
说话的时候,我将早就准备好的钱拿了出来,递向菱花手里。菱花接过钱,有些不相信似的问,你真的有钱了?
我点点头,为了让菱花真的相信我,我干脆将自己赚到的一大沓钞票全都亮了出来。我有意将它们在空中甩了甩,让它们发着窸窣的响声,那其实也是音乐呢,一种让人无比心动的音乐。一刹那,菱花的眼睛亮了,不是羡慕和贪婪,单纯就是惊喜。
哇,这么多!我还真没看错你!说时,菱花还用她的小手在我的肩上捶了一拳。
没看错我?我想起了菱花那天替我付房租时说的话,就故意说一句,我现在不必去死了吧?说时我还有意吐一吐舌头,做一个吊死鬼的模样。
菱花怔了怔,笑着说,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啊?其实我是故意激励你的。你还真没让我失望,我就知道,你这个人肯定是能有所作为的。男人嘛,就得做顶天立地的那种……喂,趁你现在有了钱,请我吃一顿夜宵好不好?
没问题,去什么地方,随你挑好了。我挺直腰板,大大咧咧地说。
真的?那我可要狠狠宰你一次哟。
不宰白不宰,你就狠狠地宰吧。
我哈哈大笑,内心早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说完,我就一把拉住菱花的胳膊,要朝楼下走。菱花忙说等一等,让我先冲一个凉吧。我想到底是女孩子,事情想的比男人周全些。
菱花进自己的房间冲凉去了,关上房门前,菱花还给我一个飞吻,那飞吻令我心里面热乎乎的。不知不觉,我就有了视菱花为红颜知己的意思。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菱花冲好凉出来了,完全是一个全新的菱花,一个我过去从未见识过的菱花,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漂亮。
你发什么呆啊?不认识我了是不是?
看见我痴痴呆呆一个劲地盯着她,菱花扑哧一笑,没好气地用手指头在我的额上戳了一下。
下了楼,七转八转的,我被菱花拉进了一家大排档。
怎么来这种地方?你不是要狠狠宰我吗?不行,我们还是换一个好点的地方吧。
我拉起菱花就要朝外面走,菱花哪里由我?她像灵敏的兔子将自己挣脱出来,笑吟吟地说,我哪里忍心宰你?你的钱也不是那样轻松挣来的,再说这地方也不错啊。能够到这种地方来吃夜宵,我已经非常满足了,真的。
我最终还是被菱花强行按在椅子上坐下了。现在不像是我在请她,反倒是她在请我了。是她在为我端茶递水,又问我喜欢吃一些什么样的菜。菜都端上来的时候,我问菱花喝什么饮料?菱花说喝饮料不带劲,我们喝酒好了。我喜欢喝红酒,你给我拿一瓶红酒吧。
我猜想菱花很能喝酒,女人不喝则已,一喝是少有男人敌得过的,这几乎是我们生活中的惯例,不过我已经做好了舍命陪君子的准备。
其实你大可不必做那个。我说。
菱花明白那个的意思。
不做那个做什么?凭我在工厂上班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还不够我女儿一个月的药费开支呢。
我没想到菱花居然已有了一个女儿,这么说,她早已经结婚了。
你很惊讶是不是?我十七岁结婚,我的女儿今年已经五岁了。给你看看我女儿的照片吧,瞧她像不像跟我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菱花说着就从随身携带的一个手提包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小女孩,的确跟她长得很相像。
看上去很可爱!什么病?
白血病。
菱花的口气有些轻描淡写,我的心却猛地抽搐了一下。
这种病从前是绝症,可现在好像能治了……
菱花点点头:医生也说能治,不过要花很多钱,所以我才要加倍努力。
你丈夫呢?你丈夫他在干什么?
我丈夫?别提他了,他在监狱里蹲着呢。其实,他也是为了给女儿治病才去抢别人钱的,结果钱没抢到,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哎呀,我这是怎么了?说这些多没意思啊。我们喝酒吧,喝个一醉方休……
我无话可说,所能做的,只能是喝酒。我也很想一醉方休,可我知道,我必须拿出男子汉的责任感来。我最后保持了克制,没有将自己灌醉,可是菱花却醉了,在这个时候,醉对于她来说,的确是最好的解脱。
我扶着烂醉如泥的菱花回去。她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整个身体都压在我的身上,好几次连我也要摔倒了。看看不是办法,我只好让菱花趴在我的背上背着她走。因为害怕自己会滑下去,菱花一路都用她两条柔薏似的手臂紧紧箍着我的脖子,这令我呼吸倍感艰难。走在平路上还可以支撑,最要命的是爬楼,我的整个人都让汗水淋湿了。有那么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自己就是她的爱人一样,这念头刚刚升起,立刻就受到了良心的谴责:阿明啊阿明,你都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最后还是将菱花背回到了她自己的宿舍,把她放到了床上,她似乎已经睡着了,可在我刚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却说了声别走。我回过头,发现她眼睛依然是闭着的,她是在跟我说话吗?或许,她这会儿已到了梦中,是在跟梦中人说话吧?可不管怎样,我的脚步都迈不动了。
别走……
菱花的声音有些颤抖,手在空中抓来抓去,最后,她把我的手抓住了,紧紧地抱在怀里。我由她抱着,因为我发现,在她抱着我手的时候,她的脸色平和了许多。
我想,菱花是把我当成了她女儿吧?她是害怕女儿会突然去到另一个世界吗?我不能待下去了。我小心地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起身离去。已经走到门口,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取出了自己刚刚赚到的那沓钞票,分了一半,放在菱花的枕头旁边,然后,我无比留恋地看了她一眼。
第二天我就搬家了,我搬到了一个环境单纯的新居。空闲的时候,我依然喜欢拉二胡,拉着拉着,我就会在心里念叨一个名字:菱花。
责任编辑:李 菡
——二胡曲“二泉映月”演释[1]的多元化与一元化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