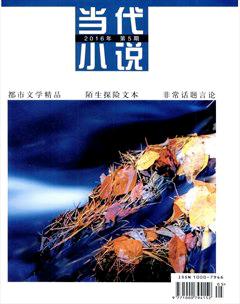飞翔
周齐林
1
“娘快不行了,你赶紧回来!”福喜挂断电话,妻子的这句话便一直在他脑海里盘旋着,挥之不去。福喜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把娘接出来看看这外面的世界,娘就病倒了。厂里一连几个月没什么订单,福喜很容易就请到了半个月的假。
“醒醒,快醒醒,到了,赶紧下车,下车!”福喜一个颤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两眼茫然地往车窗外看了一眼,见暮色渐浓。福喜提起行李,匆匆离座,一团模糊的口水印在窗玻璃上,女售票员一脸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福喜下了大巴,坐上中巴,几经辗转,回到家已是黄昏。房屋紧闭,屋内开着灯。福喜急切地敲门,门开了,露出福喜他老婆一张憔悴的脸。福喜刚放稳行李,女儿雯雯就跨步走到他面前,一脸神秘地说,爸爸,奶奶生吃鸟。福喜没吭声,他急步走到暗房,苍白的灯光下,福喜看见母亲像一块失去水分的豆腐块干瘪瘪地躺在床上,闭着眼,有气无力。福喜噗通一声跪在床边,两只粗糙的手轻轻抚摸着母亲的额头,喊了声,娘!福喜他娘像是从深远的睡梦中醒过来,见跪在床边的是儿子,眼底放出一丝光芒,却又昙花一现般迅速黯淡下去。福喜他娘蠕动着嘴唇,眼角溢出一滴眼泪。
福喜陪娘说了会话,见娘重新入眠,便出了房门,来到屋外。此刻晚霞满天,只见几只寒鸦在屋外的梧桐树上左右上下纷飞着,不时发出悲戚的咿呀声,闻之令人颤抖。在半空中盘旋良久的乌鸦,最终落在院落旁枝繁叶茂的橙子树上。看着隐匿于橙子树叶丛中躁动不已的乌鸦,福喜他女儿雯雯迅速从屋内扛出那根五米长的长竿,瑟缩着脚步,小心翼翼地走到枝繁叶茂的橙子树前,而后猛地朝寒鸦集中的方向戳去。一根根羽毛在半空中摇晃着,被戳中的鸦群离弦的箭一般,逃离开来,发出阵阵呀呀的悲鸣声。受惊的乌鸦在半空中盘旋了一阵,复又在不远处的屋顶上落了下来。雯雯手持着长竿,站立于橙子树旁,和几只乌鸦远远地对峙着,她不时从地上拾起石块,狠狠地投掷过去,石块落在屋顶的瓦片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抑或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忧伤的弧线。
在长久的对峙里,寒鸦终于败下阵来,逃离了雯雯的视线。雯雯把长竿放回原处,朝门口站着的福喜一笑。
福喜驻足良久,回到房间,此刻灯光顿时变得柔和起来,福喜想起三个月前,回到家里,母亲两条腿的膝关节肿得变了形,十个指头蜷曲着,像生锈的弓箭,无法复原。他躺在床上,见母亲撑起身子,从床上爬起来,而后全身摇晃着下了床,仿佛随时就要坠落在地一般。母亲扶着墙壁,缓缓移动着,骨头缝里的疼痛时刻撕扯着她的脸,表情显得十分痛苦和怪异。
冷月悬空,月光透过窗格子斜射进来,落在床单上,像凝结了的一层霜。福喜半跪在床边,握着母亲微凉的手,微颔首,看见床下的便盒里有一摊半凝固的鲜血,暗红无比。福喜下意识地回头,看见不远处那间原本潮湿阴凉的暗屋此刻深陷在无边的黑暗里。穿过漆黑的夜色,福喜依稀看见那具棺木的轮廓,那是十年前母亲就为自己预先准备好的。
午夜,福喜被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叫喊声惊醒,他一跃而起,是母亲疼痛的呼喊声。福喜一个箭步冲到了母亲的床前,紧跟在后的妻子早已赶在他前面,娴熟地给母亲半褪下裤子,而后把清洗干净的便盒准确地放在了母亲屁股下面。福喜站在一旁,十几秒钟后,他看见母亲微蹙的眉头微微舒展,那张瘦削无比的脸却愈加苍白起来。妻子把便盒缓缓端出,昏黄的灯光下,福喜看见一摊鲜红的血在便盒里缓缓涌动着。福喜一脸焦急地看着脸色煞白的母亲,神色慌张。正当福喜手足无措时,福喜他妻子提着一只鸟笼出现在他面前,一只披着鲜红翅膀的鸟儿在笼子里跳跃着。妻子把鸟掳住,抓出笼子,在灯光的照射下,福喜看见那是一只披着鲜红羽毛的鸟儿,长着一只细长的嘴。鸟儿扑腾着双翅,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下。福喜看见母亲适才煞白的脸此刻露出一丝红,黯淡的眼底放出一丝光来。福喜见妻子把鸟儿抓到母亲跟前,母亲一把把鸟儿抓在手里,鸟儿扑腾着翅膀,转瞬却安静下来,像是被彻底驯服了一般。妻子一把把福喜拉到门外,而后轻轻地把门半掩着,福喜站在门外,只听见屋内母亲微弱的喘息声。透过门的缝隙,福喜看见母亲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鸟,把它吞入口中,鲜血顿时流了一地,鸟的羽毛纷繁掉落在地。母亲吃鸟的模样让福喜感到十分震惊。
雯雯揉着惺忪的睡眼站在门前,她摸着门闩,在确认无误后,那颗焦躁无比的心才放松了许多。福喜看着女儿疲惫恐慌的神情,脑海里就浮现出娘在半空中飞翔的情景。
很快,门外的福喜听到的是一阵鸟的悲鸣声,几分钟后,他就看见母亲撞击着房门,半悬在空中飞了出来。爸,你快看,奶奶飞起来了。女儿雯雯尖叫着,两只满是虚汗的小手紧紧拽着他。福喜看见母亲飞翔在三米高的半空中,整个身子紧贴着天花板,灰旧的灰尘掉落在地,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福喜看着母亲围绕着整个屋子横冲直撞着,像是在四处寻找出口。此刻,门闩被一把沉沉的铁锁给锁住了。福喜欲前去开门,却一把被妻子给紧紧拉住了。再等会儿,再飞两圈,娘就会下来了。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妻子似乎早已预料。福喜看着母亲在半空中飞翔着,两只瘦长的腿蜷曲在一起,活像一只鸟。两圈后,福喜和妻子惊讶地看见母亲没有停止飞翔,反而拍打着翅膀,速度愈来愈快起来。福喜抬头,只见徘徊在大门口的母亲突然急速飞翔,一下子撞击在几米远处那块硕大的玻璃上,沉闷的撞击声回荡在整个房间。福喜见几丝鲜血迅速从母亲的额头流了下来。这次撞击之后,福喜娘一下子从三米高的空中降到地上,即将掉落在地时,却又扑腾着翅膀飞了起来。福喜看见娘又扑腾着翅膀飞到了三米之高的地方,喘息片刻之后,她又箭一般迅速朝大门口撞去。福喜见状,想去打开大门,却被妻子硬生生地给拽住了。福喜使劲一推,一把把妻子推倒在地,打开大门的一刹那,一阵剧烈的响声在他耳边响起,紧接着一阵大风吹乱了福喜的发梢。福喜迅速闪开,转瞬,他看见娘飞了出去。娘在大门口盘旋着,依旧是在三米高的半空中。盘旋了几圈,福喜看见娘朝村头缓缓飞去。福喜紧跟着,适才他摔倒在地的妻子也紧紧尾随着。然而刚飞出门几米之遥,福喜就看见娘重重地摔了下来。福喜看见娘在急速地降落中有气无力地扑腾着翅膀,像是一具骨架掉落在地,发出喀嚓喀嚓的破裂声。福喜把瘦弱的娘紧紧抱在怀里,就像年幼时他摔倒在地,娘一脸担心地把他紧抱在怀一般。洁白的月光下,福喜看见娘的额头流出几丝鲜血,几处旧伤掩映在头发之间,清晰可辨。
福喜重新把娘抱在床上,一番折腾之后,他看着娘一脸安静地睡去。福喜蹲在门槛前抽着闷烟,月光如水,映着他惆怅的模样。抽了几口烟,福喜忽又猛地摁灭,他转身进屋,一口气把屋里所有的门都统统打开。妻子听见甩门声,闻声而出,一脸忐忑地看着福喜,不敢出声。福喜想着娘额上的伤疤身子上的伤痕,心就感到一阵莫名的疼痛。看着福喜冲着自己发脾气,福喜他妻子倚靠在床前,眼角溢出一滴泪来。
福喜不担心娘飞走,他现在就盼着病重之中的娘能再次飞翔起来。次日,福喜把在县城当医生的小红请了回来。小红是他姑姑的小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多年。看着鲜红的血浆透过血管缓缓流入娘体内,娘发白的嘴唇仿佛也开始变得红了起来,福喜那颗焦灼的心略略缓释下来。
2
鸟笼空荡荡的,黄昏时分,福喜买了一条双喜烟来到村头老王家。老王是方圆十里出了名的猎人,这辈子是靠山吃饭的人。福喜等老王吃完饭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暗黄的灯光下,他看见老王娴熟地往腰间跨上一个老酒壶,老酒壶随着步履的晃荡发出哐当的响声。福喜紧跟在老王身后,两人朝牛头山走去。
牛头山位于五里之外,因形似牛头而得名,老王常年游走在山里,靠打猎为生,通常是晚上启程,次日晨曦时分归来,打来的猎物一部分在墟上卖掉,剩下的就留着自己吃。村里猎人众多,惟老王技艺出众。老王不仅技艺出众,而且颇有作为一个猎人的德品。老王不贪,适可而止。村里的其他猎人,有因狩猎而丧命者,亦有因打猎而缺胳膊少腿者,独老王毫发无损,乐在其中。
牛头山山势险峻,福喜年幼时经常随老王前来。福喜和老王一前一后,抵达到山顶已是深夜。山间树木苍翠,溪流在暗夜中缓缓流淌,发出淙淙之声。福喜紧跟着老王,山势险峻,他不敢轻易乱动。在半山腰,只见老王猫着身子,在林间左右穿梭,几番围追堵截之下,随着一声枪响,一只肥硕的野兔落入囊中,再往山上行走攀爬,老王又捕获了两只羽翼鲜艳丰满的野鸡。无论是野兔还是野鸡,老王皆无伤及要害部位,一枪下来,大都命中在大腿略上的部位。
山顶幽静无比,被一层微凉的空气笼罩着,皓月当空,苍白的月光透过树的缝隙飘落而下。福喜卸下老王捕来的猎物,只见老王从随身携带的旧背包里抓出几把大米,置放于百步之遥的巨石上。石头沾染着一丝阴气,光滑而又潮湿,几团青苔附着于边缘。转瞬之间,一股浓浓的香味透过清冽的空气,传到福喜的鼻尖。几分钟之后,福喜就隐约感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醉意。那股香味像是在陈年老酒之中浸泡染多日一般,浑身散发着一股酒味,却又带着一丝莫名的香味。
布置完引料,老王席地而坐,嘴叼着烟杆,烟火在幽暗的林间明灭不定。突然间,福喜觉得幽静无比,他自己那颗焦灼无比的心此刻也跟着安静了许多。当老王把烟杆重新放进包里,福喜就听见百步之遥的半空中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声。福喜抬头,看见几只扇动着鲜红羽翼的鸟儿出现在他面前。起先是一只,紧接着又飞来七八只,在半空中盘旋着,形成一个圆圈状。福喜屏气敛息地观望着。盘旋良久,只见一只鸟儿落在石头上,机警地朝四周张望了几眼,在石头上轻啄了几下,又停止下来。福喜微转身,看见老王嘴角溢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很快,几只鸟儿也跟着盘旋而下,落在石间。福喜见状,一脸欣喜。老王紧绷着脸,神情肃穆地凝视着。纷纷而下的几只落在石头上,踩着轻盈的步履,在石间走了几步,却又纷纷拍翅而起。福喜见状,迅速看了老王一眼。老王像是预料到什么,立刻举起手中的猎枪,迅速朝前方疾驰几步,而后停步,朝半空中连续开了几枪。只听见砰砰的几声巨响,适才在空中盘旋的几只鸟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惊吓,慌不择路,迅速箭一般朝前方的丛林中飞驰而去。老王又连续开了几枪,转身又朝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瞄准着射出一枪,只见一张巨网从半空中落了下来,适才飞驰的几只鸟瞬时扑腾着翅膀落入网中。另外几只没落网的在半空中咿呀着,盘旋良久才离去。
一夜无眠,福喜抱着捕来的两只鸟匆匆赶到家中,见娘还未睡醒,妻子和女儿还酣睡着。此刻,天边的那轮火球刚露出一丝火星。在时间的酝酿下,那丝丝火星逐渐蔓延开来,铺成一条长长的朝霞。福喜走到床边,静静地看着娘,娘的双唇依然是苍白,毫无血色。他蹲下,摸了摸娘的手,手上满是皱纹,疼痛已让她的手蜷曲着,不能伸直。福喜转身离开房间,在门槛上蹲了下来,默默地抽着烟。等他抽完烟,再转身,妻子正倚靠在房门口,凝望着他。
3
福喜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娘重新飞翔的那一刻。一整天,娘却悄无声息,从上午到黄昏,她只喝了几口水,还有一小半碗粥。福喜看着娘浑浊的眼,很不是滋味,心底像是被什么东西在叮咬一般,直感到疼。
一直熬到深夜,福喜才疲惫地睡去。一连多日,福喜他娘悄无声息,像一块失去水分的豆腐平躺在床。几日后的深夜,电闪雷鸣,转瞬天空便下起了暴风骤雨。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雨雾之中,闪电如锋利的刀剑般劈开漆黑的夜晚,出现一丝光亮,转瞬整个村庄又淹没在无边的黑暗里。福喜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心里满是担心。他轻推开娘的房门,见娘正睡着。福喜在一阵担心中缓缓入睡,他梦见娘在瓢泼大雨之中飞了起来,羽翼被雨水淋湿,单薄的身子被斜风细雨吹打得四处摇摆。一道明亮的闪电劈在她身上,很快她就跌落在地。
福喜在一阵尖叫声中惊醒过来,他睁开眼,看见窗外骤雨停歇,皓月高悬,雨水在月光的映射下发出苍白的亮光。福喜把大门打开,一阵清冽的风吹来,他全身忍不住蜷缩了一下。只听见屋内两声鸟的悲鸣声,再进屋,只见几片鲜红的羽毛在半空中飞舞着。
福喜看见娘在房门口盘旋了一阵,便从大门口轻盈地飞了出去。隐约中,福喜看见娘眼里闪着一丝血丝。
整个村庄静悄悄的,所有人都酣睡着。洁白的月光照在大地上,映射出一缕缕白。福喜和妻子一路小跑着,紧跟着半空中的娘。正当福喜担心着娘究竟要飞往何处,难以再寻觅时,福喜却看见娘一个趔趄,从三米高的空中重重地掉落下来。娘掉落在百米之遥的水田里。福喜和妻子一路奔跑过去,半途中却又见娘挣扎着飞了起来。福喜他娘轻拍着双翼,越飞越高。福喜转身,立刻吩咐女儿回去把家里的长竿拿过来。福喜他女儿飞奔而去,把一根笔直细长的竿子递到福喜手中。福喜挥舞着手中细长的竿子,紧跟着娘,一边抬头朝半空张望,一边注意着脚下泥泞的路。
福喜跟着娘围绕着整个村庄绕了一圈又一圈,他的步履愈来愈快,跌倒了又爬起来。福喜见娘像是着迷了一般,在清凉的夜空,一圈又一圈围绕着巴掌大的村庄寂静地盘旋着。福喜最终忍不住了,他挥舞着手中的长竿,想把娘引出巴掌大的村庄。福喜调转方向,往村口的方向奔去。他一边跑一边回头,见娘依旧盘旋在半空中,缓缓绕着村庄飞翔着。福喜一脸焦急地停下脚步。福喜娘最终盘旋着落在了空置多年的老屋上。福喜望着这栋破败多年的老屋,脑海里就浮现出幼时那些欢快的日子。福喜娘栖在老屋良久,忽又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福喜扯破嗓子,大声叫了句,娘!转身便挥舞着长竿往前飞奔起来。福喜再次回头,欣喜地看见娘朝他飞了过来。福喜愈跑愈快,很快他就跑出了村庄,来到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马路上。这条宽敞的柏油马路,福喜太熟悉了。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扛着蛇皮袋出门远行,娘就是在这里目送着他一步步走远。现在,他看见娘飞了过来,在他的头顶盘旋着。福喜见状,又挥舞着手中的长竿在月光里飞速奔跑起来,他担心娘看不见他的身影。细长的长竿是他们彼此的参照物。福喜越跑越快,把妻子和女儿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微凉的风里,他感觉自己几乎飞了起来。他微微转身回望,看见妻子和女儿变成了豆大的身影。恍惚中,他像是听到了她们呼唤的声音。福喜顾忌不了那么多了,他想着把娘引出大山。他这样想着,心里一阵欣喜,心仿佛也跟着飞了起来。福喜再次回头,却发现娘慢了下来,扇动的双翼显得有气无力。福喜又使劲朝半空中挥舞着手中的长竿,大声呼喊着娘。在福喜的声声呼喊之下,他看见娘重新朝他这边飞过来。但这种情况持续了没多久,福喜看见娘掉转头往回飞。福喜见了,心底一阵焦急。他举着手中的长竿,跑到娘的最前头,竿的顶端几乎能触到娘飞动的身体了。他用长竿轻轻碰了碰娘,大声叫喊着娘调转方向,别往回走。这一触碰,福喜他娘像是受到刺激一般,盘旋了一阵,飞到了高空。福喜看见娘缓缓往村里飞去。他有些绝望地仰望着天际,却只能一步步跟着。回去的路上,福喜他娘飞得愈来愈慢起来,她在半空中慢慢盘旋着,一点点从半空中落下来,即将跌落在地时,忽又挣扎着飞了上去。福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像是预感到什么,他又往村口的方向使劲奔跑起来,一边挥舞着长竿,一边朝娘大声呼喊着。像是受尽颠簸,福喜他娘最终重重地跌落在村口的那块水田里。福喜看见娘慢慢跌落下来,几步之外的他迅速跑了过去,一把接住了她。他们紧抱着,跌倒在冰凉的稻田里。福喜紧抱着娘,只见娘的脸色愈加煞白,浑身颤抖着,身上的衣服早已被田地中淤积的雨水湿透。福喜脱下自己的外套,一脸悲戚地把娘抱在怀里。
次日黄昏,福喜娘没了鼻息。福喜跪在床边,娘瘦弱的手被他紧握着,手温却渐渐冷了下来。那一晚,福喜在睡梦中隐隐抽泣着,像一个受伤的孩子,睡梦中,福喜梦见娘重新飞了起来,娘轻盈地在天空中飞翔着,羽翼微微扇动,耳边夜风阵阵,他骑在娘丰满的羽翼上,朝村庄外的世界飞去。
娘去世的那一晚,整个屋子顿时人影憧憧起来。披麻戴孝,村里人都准备着把福喜他娘葬在村后的那座牛头山上。他坚持着要火葬。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最后,福喜和几个亲戚差点掐着脖子打闹起来。要是今天不拉去火葬,我就撞死在这里。福喜边说边当着众人的面朝路边的一块巨石撞去,巨石露出尖尖的一角,在福喜的头部即将碰到那刀尖般的锋利时,众人迅速把他拉住了。众亲戚无奈地耷拉下了头。福喜说,你们都别拦着我,等火葬完了,我要带着娘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从火葬场抱着娘的骨灰盒回来,福喜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神情肃穆,骨灰盒始终被他抱在身边,无论去哪里,他都带着,寸步不离。晚上睡觉时,福喜把骨灰盒放在床上,他久久凝视着,娘的面容浮现在他脑海里。现在,娘变成了一把灰,静静地躺在这个冰凉的铁盒子里。窗外,夜色深沉。福喜跪在床上,紧抱着骨灰盒,叫了声娘。福喜揭开骨灰盒,看见灰白的骨灰,那是娘。福喜又低沉地喊了一声,娘,我想你了,眼里顿时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福喜他老婆一脸凄然地看着他,也跟着落下泪来。
4
休整了几天,福喜就上路了。骨灰盒紧紧地包裹着,最里面一层是一块黑布,最外面一层则裹着一块普通的白布。天微亮,福喜就起身了,他把骨灰盒跨在肩上,护在前胸,生怕它丢失一般。福喜他老婆带着女儿一直把他送上车,一直目送着大巴车远远穿过山峦,远远离去,才返身回去。
山路颠簸,福喜一路把骨灰盒捧在怀里,不让它受到丝毫震动。汽车经过牛头山脚时,一群扇动着鲜红的羽翼的鸟儿盘旋在半空中,有一只转瞬便拍打着翅膀降落到了车顶,有几只则尾随在车的周围。福喜看着那几只鸟,忽然意识到什么,把骨灰盒抱得更紧了。那几只鸟像嗅到了什么气息,一直尾随着。当道路逐渐顺畅,汽车顿时飞驰起来,那几只鸟的影子愈来愈模糊。福喜朝车窗外张望着,那个忐忑的心舒展了一些。
下了车,福喜把骨灰盒放进了大行李箱里。厂是小厂。进厂门口时,保安盯着他的行李箱看,福喜像是预感到什么,迅速递给保安一根烟。保安老王一脸关心地叫福喜节哀。
福喜把骨灰盒放在紧挨自己床铺的床头柜里,出去买了一把新锁换上。白天,福喜总会提前几分钟下班,趁没人时打开抽屉好好看娘一眼。晚上睡觉时,想着娘就躺在自己身旁,福喜空荡荡的心就仿佛被填满了一般,倍感踏实。
这个周末,订单少,厂里又是双休,福喜准备带娘出去走一走。他洗了个头,然后带着娘出门了。下班很久了,厂门口就坐着保安老王和老李。在工厂干了五六年,福喜和他们都比较熟。福喜带着娘走到厂门口,却被保安老王拦住了。平常福喜跟他们都嘻嘻哈哈的,经常开玩笑讲黄色段子,这次却眼神异样,动起了真格。老王问他包裹里装着的是什么。福喜没吭声,抱着怀里的骨灰盒,直往门外走。保安老王见状,身强力壮的他一下子把福喜拉了回来。福喜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他站稳身子,首先抱稳了躺在怀里的娘。这一闹,保安亭里的几个保安都急匆匆走了出来。福喜迅速被带进保安室,几个保安气势汹汹地看着他。
把包裹打开,我们要检查。这是厂里的规定。福喜沉默不语,他紧抱着娘,死死地盯着保安老王和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