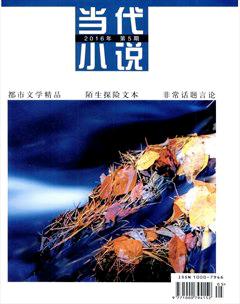去往海的另一边
莫飞
时间已过正午,天气酷热。路面汇聚着直射的光线及海面反射的光线,蒸腾的暑气,把人眼前的砂石路面扭曲变形。
女孩一手提着一个蓝底小雏菊图案的布包,一手拉起孔雀花纹的波西米亚长裙的裙摆,露出了左膝盖。
“我说过,不要做那么危险的事。”男孩比女孩高出一个头,背着蓝色的双肩包,用手揽过女孩的肩头。
“不危险,只是擦破了点皮。”女孩只是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口,然后把裙摆放了下去。
两个人走在桥下的阴影里,一堆腐烂的西瓜皮散发着发酵的气味,苍蝇在上面围着。行驶过桥的卡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声,有那么几个瞬间,他们彼此以为噪音阻断了对方的声音,互看了一眼,才发现彼此都沉默着。
下午的阳光趴在路边屋子的一排彩钢瓦上,一阵阵的热浪,像点燃的透明烟雾,让人觉得路面起伏不定。刚才,女孩跨到高于路面的海塘堤坝上,感觉走得很稳的样子,身体没有丝毫的摇摆,就跌落下来,几乎是坐在地上。男孩还来不及去扶,她却以极快的速度站了起来。
男孩要察看她的伤口,她满不在乎地挥挥手。
“我们喝点冰的,我的肚子好像要着火了。”路边的小酒馆,外面拉了藏青色的帆布棚子,下面支了几张矮桌矮凳。女孩把包放在桌子上,摘下帽子,刘海湿成一片,粘在额头。她把藤编的草帽盖到包上,一根细藤编织成的蝴蝶坠在帽檐的边缘,蝴蝶的正中央缝着一颗水滴状的粉色水晶,此刻正反射着太阳的光。这是妈妈,喜欢在她的衣帽上留下的无聊痕迹。她撇了撇嘴,似乎为这个时候想到妈妈而心生闷气。
“啤酒吗?喝了上车会好睡点。”男孩把双肩包卸下,拉了一张方头矮凳。凳子的腿不齐整,坐着有些不平稳,他拉动凳子,希望是不平整的地面造成的摇晃。
“我不想喝酒,冰橙汁就可以。”女孩看了眼屋里,感觉门帘里有双眼睛注视着他们,却没有打算出来接受热浪烘烤。一定有台电风扇吹着那些人的后背,凉凉的。女孩想着摸了一下擦破的膝盖,有一丝丝疼痛,可她并不想表现出来。
“再要点东西吃,会饿。”男孩说。
“不会饿。”女孩说。
“就要一盘子花生,卤鸡翅,切一份红肠。”男孩说。
女孩抬头看了眼男孩,没再坚持,点了下头说:“花生和卤鸡翅就够了,我真吃不下。”
男孩扭过头朝着帘子喊,“来一瓶啤酒,一杯橙汁。”
女孩把帽子上的粉色水晶迅速揪下,握在手心,以极快的速度向外扔去。水晶就是一个光点,空中一闪,就消失在沙石路边几棵无精打采的狗尾巴草中间。
帘子被一只手掀开,一个女人走出来,穿着白色的高跟凉鞋,声音清脆地走到桌边。女孩瞟见她丰满的身材裹在一件黑色丝质连衣裙里,长度刚刚到大腿。
“没有橙汁,只有冰镇西瓜。”女人把一瓶冒着冷气的啤酒放到桌上。她的声音和动作干脆利落,从她走出来到放完啤酒,这一系列动作像在进行一项优雅的运动。
“西瓜要吗?”男孩问女孩。
女孩摇了摇头。
“那再来盘花生,卤鸡翅。”男孩说。
“你在看人家屁股。”女孩并没有看男孩,她低着头,脚底下有一条水泥裂缝,从脚底延伸到桌腿下。
“有什么好看的。”男孩收回了目光。
“可你就是盯着人家看了。”女孩不依不饶。
“你不知道。”男孩将脑袋凑近女孩的耳朵,“这里的服务员除了端茶上菜,还要陪人家喝酒,还要……”男孩朝女孩使了个眼色,又朝门帘内瞅瞅。
女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男孩。
“真的,不骗你,到了傍晚,附近工地上的工人下工,这些小饭馆里的女人全跷起二郞腿坐在外面,涂脂抹粉,招揽生意。”男孩言之凿凿。
“你来过?”女孩淡淡的眉毛凝在一起。
“我哪来过,听朋友说的。”男孩赶紧申辩。
“那你的朋友肯定来过,你的朋友都不是好人。”女孩把眉毛打开,嘴巴微微翘起。
女孩还在学校的时候,她和男孩出去约会。热闹的夜市上,男孩遇到他的朋友在吃宵夜,一个朋友拍着男孩的肩膀说,忘了带钱,先借些钱。男孩转身望望女孩。女孩从包里掏出钱,替他们付了吃烧烤喝啤酒的钱。
这些钱,男孩从来没提起,他的朋友会还。
“我跟他们一样都不是好人。”男孩一脚蹬在桌脚上,桌子发出难听的叫声。
女孩把头转向海的方向。海面像个巨大的盛满光线的容器,泼洒着,晃动着。她闭上眼睛,想像了一下海对面的城市。上初中时,她就收听过海那边的电台,一名叫阿染的女人在深夜播一档《半夜心香》的栏目。她躲在被窝里听别人的心事,陪别人流泪,听一些伤感的英文歌曲,也给阿染写过信,却从未寄出去。
女孩收回目光,偷偷瞧了一眼男孩。男孩紧盯着地面,一动不动。他感觉到女孩在看他,抬起目光。女孩来不及躲避,朝他勉强挤出个笑容,男孩也朝她笑笑。
这样,两人算是冰释前嫌了。
女人托着盘子出来,一瓶啤酒,一个玻璃杯,一碟花生。她看了一眼男孩和女孩,又进去拎了一台电风扇,打开。热风呼呼地吹,女孩的头发被吹得凌乱无措。
“太吵了,你把电风扇关了。”女孩说。
“吹一吹,你的头发都粘在一块儿了。”男孩说。
“我觉得吵死人了,你就不能关一下吗?”女孩站了起来,走出遮阳棚,阳光立刻让她变得耀眼起来。
“还是进来喝一杯啤酒。”男孩冲着站在外面的女孩喊着,电风扇继续咯吱咯吱转。
“这么冰?”女孩着实受不了外面的太阳,一屁股又坐下去,猛喝了一口酒。
“冰的喝着舒服。”男孩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我觉得寒气直往肚子里钻。”女孩摸了下肚子。
“可你头上还冒着汗……你是心里不舒服吧。”男孩心里也不舒服,自从一个多小时前,她给她爸打了电话,他就一直不舒服,浑身是刺。
“没有。”女孩咕咚咕咚喝光了,“那么你就舒服吗?”
“我们可以不提吗?”男孩只好举手投降。
“可以。”女孩说。
“那么,你跟你爸怎么说的。”男孩一直不敢问。
“还能怎么说,就说,我跟你去私奔了。”女孩没好气,好像这个决定是他逼她做的。
可究竟这个决定是谁做的?她搞不清楚,好像这一切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对,自然而然。
“那我们不谈这个,还是喝点酒。”男孩说。
“可我真不想喝,喝了头晕脑涨,说不一定,一会儿上车还会吐。”女孩说。
“那我们进去看看,说不定冰柜里还有别的喝的,有酸奶就更好了。”
男孩站了起来,女孩也跟着站了起来。
女孩突然想到,好像这样便是自然而然。
他们俩一前一后掀开门帘。
除了穿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两人在门口坐着,一台电风扇在背后吹着。相对于穿黑色裙子的女人,另一个丰满得多,或者说肥胖。她坐在那里,垂着双下巴,打量着女孩孔雀图案的波西米亚裙。
想到闷热的屋里有这样两个女人,一直盯着他们在说话,女孩突然觉得不自在。她的脚背一凉,一粒瓜子皮吐在上面。她一把抓住男孩子的手,嫌恶地皱皱眉头,绕开两个女人去保鲜柜那里看饮料。两条明显的水迹从底部渗出来,有丝凉意。女孩看了眼还停留在脚上的瓜子壳,用另一只脚轻轻蹭掉。
除了酒,雪碧,可乐,没有酸奶,半个西瓜覆着保鲜膜。女孩盯着西瓜上一颗颗黑色的籽,她觉得很扎眼,像在眼前飞舞的苍蝇。
屋子里放了三张圆桌,有一个窄小的窗户,室外的强光勉强挤了些进来。真难想像,这间屋子现在笼罩在青天白日下,阳光在闪耀。
“你们还要点什么?”女人问。
“点的卤鸡翅没上呢。”男孩说,“还有其他喝的吗?”
“哦,我忘了跟你们说,卤鸡翅没有,我们店到了晚上才供应鸡肉之类,老板这会儿还在市场挑鸡呢。”女人说,“喝的还有椰汁,西瓜我可以给你们榨汁,十块钱一杯。”
“要不喝一杯吧?”男孩问女孩。
女人给她榨了杯西瓜汁。她在外面都能听得到屋里机器发出的轰鸣声。
西瓜汁装在大口径的玻璃杯里,吸管歪斜着,白色的沫子沿着杯壁绕了圈。女孩想那些黑色的西瓜籽此刻都成了细沫混合在汁水里,她知道此刻自己尽胡思乱想来着。她捏着吸管动了一下,碰到杯底的冰块。
男孩看女孩怏怏不快的样子,心里有些难受。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还爱不爱她,或者一开始是佯装着爱,到后来,特别是受到女孩的妈妈反对后,他对她反倒爱得更强烈了,时刻希望和她在一起。女孩为了他,才上到高二,便没了心思上学。她在家里,妈妈不让她出门见他。她撕了两床被单,一头绑在床脚上,一头从三楼丢下来。他看得心惊胆跳,怕女孩摔下来。女孩的妈妈后来发现了,追到了他们,给了两人各一记耳光。男孩捂住脸,火辣辣地疼。
一辆摩托车突突地开来,驾驶员戴着头盔,露出晒得很黑的鼻梁和一双眼睛。女孩盯着车子由远及近,看到车子朝他们驶来,没有一点减速的迹象。她有点害怕地抓住自己的裙子。
摩托车驶了上来,停在他们身边,一大股机油味。车子后座分别挂着两个大铁筐子,装了几只鸡。鸡从颠簸中清醒过来,纷纷挤着惊惶的脑袋东瞅西瞅,不时发出咕咕的声音。
像一场戏开演了。这屋子里的两个女人,手脚麻利地抬了一个白色的铅皮盆子出来,“咣”一声,扔在地上;一直静悄悄在旁边的煤炉,被火钳子捅了几下,呼呼地冒出火焰来,一壶满满的水坐上去;两把刀,几个碗,屋内屋外来回的脚步声。摩托车驾驶员从骚乱的铁筐里揪出一只鸡,三下五除二,除掉脖子上的毛。黑裙子的女人搬来了长条凳,凳子下搁了只白瓷碗。男人一手拿刀,一手将鸡按在凳子上,抬起左脚压住翅膀,抻长鸡脖子,手起刀落。鸡血起先是滴滴答答,后来汇成一股注到碗里,泛起一圈白沫子。鸡无力地在渐渐放松警惕的控制中挣扎了一下,几滴血滴到了水泥地面,像画了几朵红梅。男人又给鸡脖子补了一刀,血流得更畅了,鸡停止了挣扎。
男孩和女孩目不转睛地看着男人杀完一只鸡,将明晃晃的菜刀在鸡毛上正反擦拭一下,将鸡丢在地上。鸡翅膀偶尔还在抽动。两个女服务员将鸡扔进盆中,从煤炉上坐的热水直接浇下去,一股子鸡毛的腥味飘散开来。
“闻着想吐。”女孩站起来,走出棚子,做着眺望海的样子。
男孩没动,盯着女孩的背影。女孩蹲下,裙摆在地上被风吹起,她的手在草丛里扒拉。
“快进来吧,太烫。”男孩喊。
女孩满头大汗地进来,“我喝不下,咱们走吧!”
男孩看了下手机说:“还早,车子还要过一个小时才到。”
“可我想走了。”女孩把目光瞟向了手起刀落的男人。
“来喝杯啤酒,一会儿车上好睡一些。”男孩把女孩杯里的西瓜汁泼在地上,给她倒上啤酒。
女孩喝了一口,她皱了皱眉头,“怪味。”
“没有啊。”男孩拿过去喝了一口。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男孩压低了声音,他试图安慰女孩,转移注意力。“你知道吗,几年前,在造这跨海大桥的时候,涨大潮,好多工人都被卷走,怎么都找不到。”
“怎么也找不到?”
“找不到。”
“为什么会找不到?”
“海太大了。”
“那他们去了哪里?”
“谁知道呢,反正就是不见了。”
“不可能找不到啊,被鱼吃了?”
“或许吧。”
男孩对女孩这种无休止的追问和想像有点不耐烦,虽然他还是耐着性子。
“叫服务员再拿个杯子来好吧,我们再叫一瓶。”男孩说,“喝了酒,一会儿在车上就可以睡着,醒来,就在海的对岸了。”
“那是因为剩下的西瓜汁和啤酒搅和在一起了。服务员,再拿个杯子来。”
“我不想喝酒。”
“就喝一杯。”
“我为什么要睡着,我想清醒着。”女孩咬了一下自己薄薄的下嘴唇,“我想醒着,一直醒着,不想睡着。”
“那也要休息。”
“那我也要睁着眼睛休息,我不要睡觉,不要闭着眼睛,不要,不要。”
“好,好,但你别激动。”男孩摆着手。
“我没有激动,”女孩说,“我很镇静。”她转过头去看蹲在地上的女服务员正在给鸡褪毛,另一个用一把黑色的剪刀,剪开肚子。她扭开了头。
一个小时后,男孩和女孩拦下了即将驶上跨海大桥的大巴。他们坐在最靠后的位置。女孩头晕,一直想哭。
女孩好像睡着了,还有点抽噎。
男孩睡不着,他闭着眼睛,把下巴贴近女孩的头部,紧紧抱住她的身体。他发现女孩的一只手放在裙兜里,紧紧地攥着什么东西。
三天后,饭馆的一个服务员在桌子上发现一张客人留下的报纸。她仔细看了看。
看过报纸的人对不看报纸的人说,“你记得前两天两个年轻人吗?”
“那个穿波西米亚大裙摆的女孩?”
“对,她被海浪卷进海里了。”
“天哪,真的?”
“女方的妈妈反对,他们打算私奔,被发现了。”
一下午,两个服务员坐在门帘背后,盯着帆布棚下,男孩和女孩坐过的凳子和桌子。
责任编辑:李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