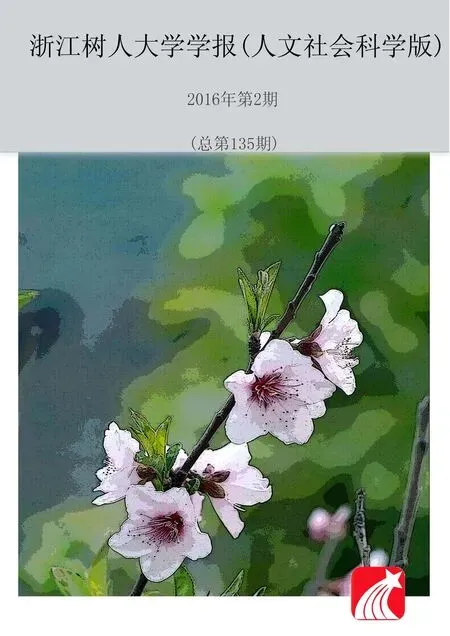《感应类从志》与《博物志》关系考
张乡里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感应类从志》与《博物志》关系考
张乡里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感应类从志》的作者问题存有争议,《说郛》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均定作者为张华;而天一阁钞本前有陈星南题词,认为其作者可能是狐刚子,且书名应为《感应类从谱》;《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题作者为张华是依托。结合古人对待图书的随意著录甚至删改以至变更书名,以及《博物志》一书在后世遭删改、部分与地理相关的内容被摘录并被名为《张华博物记》《张华博物地名记》等情况来看,《感应类从志》可能是从《博物志》中摘录出来的有关物类相感的内容。从具体内容来看,《感应类从志》与《博物志》有较多相近甚至雷同的说法,所以《感应类从志》应该是《博物志》的一部分。
关键词:《感应类从志》;《博物志》;物类相感
明代陶宗仪所编《说郛》卷二十四著录有晋张华的《感应类从志》一书,录有20条文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亦有《感应类从志》一书,其文字与《说郛》本有些不同。
《感应类从志》一书,因学者对其关注较少,故疑问也较多。如作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在杂家类存目丛书中著录《感应类从志》一卷,提要云:“《感应类从志》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旧本题晋张华撰。隋唐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所不载,诸家书目亦不著录。书中语多俚陋,且皆妖妄魇制之法,其为依托无疑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3页。认为题张华为作者是依托,否定了张华是《感应类从志》的作者之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著录《感应类从志》时所添扉页,定此书作者为张华,而影印天一阁钞本前有陈星南的题词云:“考《存目提要》有不知何人所作,托名张华云云。按《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有狐刚子《感应类从谱》一卷,盖即此书妄改,题作者为张华,且易谱为志。”*张华:《感应类从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据明代范氏天一阁钞本影印,第707页。认为《感应类从志》的作者应该是狐刚子,且《感应类从志》一书应该为《感应类从谱》,也认为《感应类从志》一书不是张华的作品。日本学者山田庆儿也曾撰文谈到:“在《物类相感志》之前还是要先说说被视为具有谱系性联系的两部著作。无论是张华(?)写的《感应类从志》还是李淳风(?)写的《感应经》,其内容都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从各种古籍那里抄录了自然的感应现象,并没有像葛洪那样严格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实践信念,只不过是咒术的现象和物类相感现象拼凑在一起,简单地用气加以说明。《物类相感志》则严密地排除了上述两者,彻底地记叙了事物的现象。但据说《感应类从志》也是赞宁的作品,但是它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实在是不可思议。”*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77页。从中能感觉到山田庆儿对于《物类相感志》作者的迷惑:说是张华,但打了问号;说是赞宁,却又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感应类从志》是否是张华的作品呢?作为博物学著作,它被认为是赞宁的《物类相感志》等一系列书的源头,那么它与《博物志》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一、《博物志》的阙佚及《博物地名记》的出现
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华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7页。这说明除了一些独立成篇的小文章外,张华的著作流传于世的就只有《博物志》一书。而现在所能见到的张华的作品,除了单篇文章、《博物志》外,还有《感应类从志》《博物地名记》两书。其中《博物地名记》见于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经王谟考证应该是《博物志》的一部分。
因为天灾人祸等原因,古书亡佚较多,同时,古人对于书籍的态度又远没有今人严谨,所以在传抄、辑录古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遗漏、删改等情况。比如《说郛》和《类说》在著录前人作品时,很多都是经过一番汰捡的,有些类似今天的读书笔记,仅仅是将感兴趣的内容记下来。如《类说》辑录的《穆天子传》《洞冥记》《列仙传》等,均是摘录,而且文字与原文差别较大,《类说》卷二十一《汉武帝故事》中的“罢遣方士”条,与今本文字就不同;甚至有的名字都发生了变化,如《赵飞燕外传》,在《类说》中题为《赵后外传》。《说郛》也如此,其卷一经子法语部分所录的《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等,均为摘录,仅著录一些关键的字词,无著录全文者,如《庄子·逍遥游》仅录“逍遥、北冥、海运、水击、扶摇、野马、坳堂……”等。在《说郛》中,同一本书有重复著录的情况,如《述异记》在卷四和卷二十均有著录;同一作品以不同书名出现的情况也很多,如《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一书,卷四著录为《洞冥记》,卷十五为《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可见,《说郛》在著录作品时,对其书名也较为随意。再如卷七十一载有扬雄《法言》一书的部分内容,但其书名为《扬子》;卷七十二有颜回的《颜子》五卷,著录了23条文字,除其中3条源自《中庸》《易·系辞下》及《礼记》外,其余内容均为从《论语》中选录的有关颜回的文字。这种随意改变书名的情况在各类书籍中都很常见,如晋人张勃的地理书《吴录》(其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将佚文收集在一起,重新命名为张勃《吴地记》,于是在《唐志》中就出现了张勃《吴地记》一卷,而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又将其著录为张勃《吴地理志》。这种不严谨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又因为增删和随意著录,后人无法考证某一部书的原貌;任意改名往往又使得一部书以不同的名字出现,这些都导致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与人们对它们的误解。《博物志》一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关于《博物志》一书的阙佚,前人有很多记载和论述。早在王嘉的《拾遗记》中就记:
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剪,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王嘉:《拾遗记》,萧绮录,齐治平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0-211页。
但后人往往因为《拾遗记》是“杜撰无稽”的小说家言,且与《博物志》中所记的“武帝泰始中武库火”事相冲突而否定其真实性。但王嘉与张华时代相去不远,此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故后世学者多从此说。从后世的文献记载中,也可以看到《博物志》被删改的记载。在《魏书》卷八十一、《北史》卷四十二有《常景传》,载北魏常景曾经“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62页。,故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据此说:“考《北史·常景传》有删正《博物志》语,是世所传本,已非张氏之旧,段公路《北户录》及《文选》注所引各条,多出今本之外,疑据景未删之旧笈也。”*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页。可见丁氏认为今十卷本乃常景所删之本,诸书所引而今本脱载者乃常氏所刊落。
在各本《博物志》的序跋中也可以看到对其曾被增删的肯定,甚至后世的编者也在进行增删工作,如唐琳在《刻快阁本博物志序》中说:“今读其书,虽多奇闻异事,而简略不成大观,岂书传既久,残缺处多耶?”王谟《刻汉魏丛书本跋》云:“是则此十卷即武帝所删定也。自后行世,惟此十卷。其轶犹时时散见他书……殆即本卷所删。”《稗海本广宁郎极序》云:“其卷帙不全者,复证之《津逮》本中而补其一二云。”钱熙祚《刻博物志跋》云:“予既主叶本,杂采宋以前诸书,补正其脱误,并辑逸文,附箸卷末。”*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0-152页;第155页。前两者都肯定《博物志》有残缺或曾遭删减,后两者则明言据前人著作对《博物志》进行了增补。而今天通行本所辑录佚文有212条,亦可见出其阙失之多。
对这些阙失部分的内容,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如黄丕烈在《刻连江叶氏本博物志序跋》中说:
若夫《通考》所云:“《博物》四百,本非有成书。”而刘昭《郡国志》注、小司马《索隐》、李崇贤《文选》注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多出今本外。《隋志》云:“《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又云:“《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云:“《杂记》十一卷,张华撰。”然则所引或出二书欤?*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3页。
将后人书中所引的《博物志》佚文,视为《张公杂记》或《杂记》的内容。对于这些佚文的归属,后人有较为详细的辨定。如王谟在《汉唐地理书钞》中,收录有《张华博物地名记》一书,其中共收集60条文字,据王谟所言,是从《郡国志》注、《后汉书》注、裴骃《史记》注、杜氏《通典》注中收集而来的。王谟将收集的资料与《博物志》一书进行比较后,发现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雷同的,又根据《水经注》所引《博物志》文与刘昭注《郡国志》引《博物记》文合,宣称“则此《博物记》之即为张华《博物志》审矣。”*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9页。而在通行本《博物志》的后记中,范宁先生也针对《博物志》与《博物记》进行了辨析,得出了“足证《博物志》、《博物记》实为一书,毫无疑义。分为二书,其说妄矣”*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4页。的结论,并在佚文中也收录了刘昭注所引的《博物记》一书,共二十五条,其中二十二条与《汉唐地理书钞》所录的内容相同或相近(只是文字上有些不同),另三条则因为与地理知识无关,没有被王谟所辑录。
但王谟在辑录这些内容时也将其名称改了,因为他所采集的都是与地理有关的知识,所以在目录中将其标题写为《张华博物地名记》,而在正文中该书的标题又被写作《张华博物记》,在文中“永安有吕甥邑也”条下,有注云:“《路史·国名纪》引此作《博物古今地名记》。”*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6页。这些不同的名称及上述各书所著录文字的不同,都说明古人在著录前人作品时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导致了对一部作品的任意拆分、组装,甚至通过重新命名而制造出了一本“新书”。《感应类从志》,就是这一情形的产物。
二、《感应类从志》与《博物志》内容的比较
在《说郛》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均著录有《感应类从志》一书,只是文字有些许不同,有的是增加了一些编者的校注,如第二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下面增加了“此疑有阙文”;有的则可能是传抄时的讹误,如第三条中将《说郛》本的“榆木化灰”,写作“时木花灰”;第六条中将《说郛》本中的“此二句目验也”,改为“此二句自验也”。所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杂家类的《感应类从志》一书,应该是从《说郛》本来的。
从《说郛》所著录的《感应类从志》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张华的作品,而且很可能是《博物志》的一部分。原文如下:
芦灰投地,苍云自灭。《史记》有苍云围轸,轸楚之分野,是不善之征。楚太史唐勒夜以葭灰遗于地,乃更灭,拂之,其苍云为之半减。人遗灰,乃尽去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围”作“圃”,“轸轸”为“轸”。)
萌芽生,角音振;蚕丝也,商弦绝。绝紧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商弦绝。绝紧也。”作“商元绝。绝紧也。此疑有阙文。”)
积灰知风,悬炭识雨。以榆木化灰聚置幽室中,天若大风则灰皆飞扬也;以秤土、炭二物使轻重等,悬室中,天时雨则炭重,晴则炭轻。孙化侯云:“以此验二至不雨之时,夏至一阴生即灰重,冬至一阳生则炭轻,二气变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榆”作“时”,“化”作“花”,“晴则碳轻”作“天晴则碳轻”。)
僵蚕拭唇,马不咬人;狼皮在槽,马不食谷。以僵蚕拭马唇内外,即不咬人,亦不吃草;取桑作末涂口,即不吃草也。以鼠狼皮挂马槽上,或云置谷上,马不咬谷也。
胡桃之券,令鸡夜鸣;甑瓦之契,投枭自止。以胡桃树东南枝劈之书券字讫,遶之于鸡栖下,则夜鸣不止;以故甑书契字置于墙上,忽闻枭鸣,取以投之,即不敢更鸣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遶”作“还”,“忽闻枭鸣”作“忽闻枭”。)
口诵仪方,登山不见虎;心念仪方,入泽不逢蛇。此二句目验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目”作“自”。)
藉草三垂,魑魅收迹;金乘一振,游光敛色。夜卧以所眠上抽草一茎出,长三寸许,魑魅不敢来魇人。田野中见游光者,火也。其名曰燐,鬼火也。或人死血久积地为野火、游□。然不常,或出或没,来逼人,夺人精气,以鞍两相叩作声,火即灭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作“叁”,“或人死血久积地为野火、游”后加一“光”字,“夺人精气”为“夺人气精”。)
货宅之财,不买生口;估乘之物,不以聘妇。卖宅之财,不买生口、奴婢及生物,并不利于人;卖驴马之财,不聘妇,令家耗耄,妇至不安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贷”作“卖”,“妇至不安也”无“至”字。)
牛马度阑,出手即售;衣服运井,入市争酬。欲卖牛马驴畜,宿以木阑障之,明乃度,过令寡妇击其尾,作十字,则其物易售也。欲出卖衣服,运遶观井三匝,将入市争酬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牛马度阑”作“牛马广栏”,“十”作“拾”,“欲出卖衣服”作“欲出买衣服”,“遶”作“达”,“观”作“睹”。)
月布在户,妇人留连;守宫涂臂,自有文章。取妇人月水布,烧作灰。妇人来,即取少许置门阃门限,妇人即留连不能去。五月五日,取蝇虎虫以刺血竭养筐筐中,以朱砂和牛脂食之,令其腹赤乃止。阴干百日。末少许涂人臂,即有文章,揩拭不去。男女阴合,归即灭。此东方朔法,汉武帝以验宫人,故曰守宫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月布在户”,作“布在户”,“守宫涂臂”作“守宫人涂背”,“门阃”作“门间”,“五月五日”作“伍月伍日”,“竭”作“蝎”,“筐筐”作“箇雨”,“令其腹赤乃止”另起一行,且无“令”字;“末少许”作“来少许”,“阴合”作“合阴”。)
高悬大镜,坐见四邻;迴风之草,目睹四户。以大镜长竿上悬之向下,便照耀四邻,当镜下以盆水,坐见四邻出入也;取迴风草插头上,令人顾见四户之事,迴风即从风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目睹四户”作“目睹四石”,“迴风”作“回风”,“顾见”作“顾风”。)
群毛止风,孤槌息涝。取黑犬皮并毛、白鹞左翼翦烧之,扬鹞即风生,扬犬即风止也。三寡妇、七孤儿各令持研米槌,孤儿仰天号,寡妇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验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取黑犬皮”前有“即雨也”,“向地哭”作“向地泣”。)
井衣独运,逃亡自归;甑缕缝裳,竖奴无去。取逃人衣裳井中垂运之,则逃人自思归也。以甑带麻作线,左系之,缝奴婢衣脊,缝一尺六寸,即无逃走之心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甑缕缝裳”作“甑缕缝衣”,“以甑带麻作线”作“以甑带缕麻作线”,“衣脊”无“脊”字。)
木瓜翻鱼,秦椒伏雀。以木瓜灰和麦饭、糠及米投水中,鱼乃食之,鱼皆翻目矣。或罔罩杀之,其鱼皆不堪食也。秦椒为末,和稻饭,雀食之而伏地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投水中”作“投之水中”,“矣”作“溪”,“罔”作“网”,“秦椒为末”无“末”字。)
橘见尸实繁,榴得骸叶茂。橘见死尸即多子;石榴一名茶林,以骸骨埋于树根下绕之,其树滋茂而叶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叶多”作“著多”。)
刀汤不纰于练,阴水可以延绫。凡练绢帛,以刀画釜中作“白”字或作“十”字,名曰刀汤。其练物不纰疎,既练生作熟讫,即内井中,悬之不至水,经宿然后出之,名曰阴水。故考切尽此为贵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为贵”作“道贵”。)
龟骸环床,子孙聪明;狗肝泥灶,妇妾孝顺。取龟左骸骨,环而带之,子孙聪明智慧,以狗肝和净土泥灶,令妇妾载顺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床”作“裳”,“左”作“在”,“载”作“孝”。)


居三徙,鬼逐人;邻三犬,家必破。家三移徙,耗鬼逐人。三犬为穴,刦神也,言此常侵耗人家不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家三移徙”作“三家移徙”,“刦”作“势”,“常”作“张”。)*陶宗仪:《说郛》,中国书店1986年版,据涵芬楼1927年版影印,卷二十四,第18-21页。
这些内容涉及的都是物与物之间相互感应、影响的情况。
感应之说在中国人的思维领域中非常重要。《庄子·渔夫篇》云:“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27页。《吕氏春秋·有始览》明确记:“类固相招,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陈奇猷先生注云:“盖事物之同一属性者谓之类,《有始》‘以观其类’是也,则类即有同一属性之意。‘类固相招’犹言同一属性者固相召致。”*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页。《淮南子·览冥训》记:“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辨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蚕饵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50-451页。《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亦云:“气同则会,声比则应……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物故以类相召也……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阴阳之气,因可以类相益损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天地之阳气起,而人之阳气亦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8-360页。《春秋元命苞》记:“猛虎啸而谷风起,类相动也。”*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页。这种物类相感的理论在后世也非常流行,王充在《论衡》中有《变虚篇》,辨析天象影响人间之说;有《感虚篇》,辨析人事影响天象之说;有《变动篇》,辨析人君以政动天之说。
感应之说不仅仅限于天人之间,物类之间亦有。后世赞宁的《物类相感志》所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山田庆儿根据赞宁的《物类相感志》推论:“其物类相感现象的大部分可以说是从繁杂的日常观察即生活智慧或生活的技术等知识出发而获得的。其中也有物理现象(例如夏月热汤入井成冰),而大多属于化学现象。除了中和、发酵外,还有金属(例如‘津液可溶水银,末茶可结水银’)、肥料(例如‘枇杷不宜粪’)、药物和毒物(例如‘松毛可杀米虫’)、烹饪(例如‘薄荷去鱼腥’)以及其他知识。有关动物的知识也不少,有动物的习性(例如‘鹤知子午’)、季节与动物的关系(例如‘芒种日螳螂一齐出’)、朴素的生物发生论(例如‘麦得湿气则为蛾’),也有迷信的成分(例如燕子戊日不归家)。要对杂多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分类和整理是相当困难的。”*山田庆儿:《〈物类相感志〉的产生及其思考方法》,《哲学研究》1990年第4期,第71-78页。可见古人的物类相感,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现在民间仍有较多这类说法,如小孩子不能吃鱼子,因为“吃鱼子,不识数”;中月不能理发,因为“中月剃头,死舅舅”;女孩子不能吃猪脚,因为吃猪脚会导致恋爱时第三者插足;吃饭时不能移动位置,否则结婚时会下雨,等等。这些说法在民间广为传播,被作为约定俗成的因果关系所接受,并被一代一代传承,正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的:
凡物有相感者,出于自然,非人智虑所及,皆因其旧俗而习知之。今唐、邓间多大柿,其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榅桲亦可。则红熟烂如泥而可食。土人谓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淮南人藏盐酒蟹,凡一器数十蟹,以皂荚半挺置其中,则可藏经岁不沙。至于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类,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气粉犀,此二物,则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罂,形制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圣俞以为碧玉。在颍州时,尝以示僚属。坐有兵马钤辖邓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识之曰:“此宝器也,谓之翡翠。”云:“禁中宝物皆藏宜圣库,库中有翡翠盏一只,所以识也。”其后,予偶以金环于罂腹信手磨之,金屑纷纷而落,如砚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诸药中犀最难捣,必先镑屑,乃入众药中捣之,众药筛罗已尽,而犀屑独存。余偶见一医僧元达者,解犀为小块子,方一寸半许,以极薄纸裹置于怀中近肉,以人气蒸之,候气薰蒸浃洽,乘热投臼中急捣,应手如粉。因知人气之能粉犀也,然今医工皆莫有知者。*欧阳修:《归田录》,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34页。
所以古人所说的各种事物间的化学变化、物理变化等等相感现象,都是沿袭旧说,并不是人们通过实践和论证所得出的理性结论,即便有些是从实践中来的,其原因也是不明确的。
在《博物志》中,卷四《物理》部分的内容全部属于物类相感之说,《感应类从志》极有可能是从《物理》篇中佚失的内容,其中很多记载和《博物志》所记很相似,而有的文字则大体相同。如“芦灰投地,苍云自灭”条,与《博物志·物理》篇所记的“凡月晕,随灰画之,随所画而阙”*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的记载,是很近似的,都是记运用灰烬来影响天上的天象;再如“萌芽生,角音振,蚕丝也,商弦绝”条,与《博物志·物理》篇中“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而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蚕弭丝而商弦绝”*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中的后一句说的是一件事情,即蚕新吐丝的时候,弹奏商音的琴弦就会断。再如《感应类从志》中记:“藉草三垂,魑魅收迹;金乘一振,游光敛色。夜卧以所眠上抽草一茎出,长三寸许,魑魅不敢来魇人。田野中见游光者,火也。其名曰燐,鬼火也。或死人血久积地为野火、游。然不常,或出或没,来逼人,夺人精气,以鞍两相叩作声,火即灭也。”这一记载和《博物志》中的一些内容也是很相近的,如《博物志》中两则关于梦的记述:“人藉带眠者,则梦蛇。”“鸟衔人之发,梦飞。”*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这与此处的“藉草三垂,魑魅收迹”是一类的,都是关于人睡眠时做梦的问题,只不过前两者是告诉人们做某一种梦的缘由,而此处是防范做噩梦的方法,但都是巫术性质的;后面关于游光的记载与《博物志·杂说上》中所记也有相同之处,《杂说上》中云:“斗战死亡之处,其人马血积年化为燐。燐著地及草木如露,略不可见。行人或有触者,著人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愈甚有细咤声如炒豆,唯静住良久乃灭。后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差。”*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6页。这两处所记都是关于燐火,也就是民间所谓的“鬼火”,都认为燐火是人死后的血积年所化,时出时没,对人有害。只是表述稍有不同,而且前者给出了应对的办法,后者没有。
再如《感应类从志》中云:“月布在户,妇人留连;守宫涂臂,自有文章。取妇人月水布,烧作灰。妇人来,即取少许置门阃门限,妇人即留连不能去。五月五日取蝇虎虫以刺血竭养筐筐中,以朱砂和牛脂食之,令其腹赤乃止。阴干百日。末少许涂人臂,即有文章,揩拭不去,男女阴合,归即灭。此东方朔法,汉武帝以验宫人,故曰守宫也。”而《博物志》佚文中辑有褚人获《坚瓠集》引:“月布在户,妇人留连。注谓‘以月布埋户限下,妇女入户则自淹留不去。’”《博物志》卷四戏术部分有:“蜥蜴或名蝘蜒。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年不灭。唯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传》云:‘东方朔语汉武帝,试之有验。’”*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第51页。这些记载仅是文字上的不同,其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关于妇女月水布的记载,《感应类从志》有:“蛙布在厕,妇不妒;草发在灶,妇安夫。以妇月水布裹蝦蟆于厕前一尺,入地五寸许,即令妇人不妒忌;又埋妇发于灶前,令妇人常安夫家。又取他人发埋灶前,令人不怒恒喜。”前一条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引《博物志》大致相同。《本草纲目》所引《博物志》佚文为:“取妇人月水布,裹蝦蟆,于厕前一尺入地埋之,令妇不妒。”*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同样被《本草纲目》所引的一条文字,“以狗肝和土泥灶,令妇女孝顺。”*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1页。在《感应类从志》中也有相近的文字:“龟骸环床,子孙聪明;狗肝泥灶,妇妾孝顺。取龟骸骨环而带之,子孙聪明智慧;以狗肝和净土泥灶,令妇妾载顺也。”这些记述也都是非常接近的。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感应类从志》与张华的《博物志》有较多的雷同、近似之处,它被著录为张华的作品是有根据的。再联系《博物志》一书在流传过程中被删减、被重新编辑甚至有对其内容分类摘录并重新命名的情况以及《说郛》在著录作品时的不严谨态度,随意著录作品内容、甚至改名的情况来看,《感应类从志》应该是从《博物志》中摘录出来的内容,是《博物志》一书的一部分,它为研究《博物志》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
(责任编辑金菊爱)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n Ying Lei Cong Zhi and Bo Wu Zhi
ZHANG Xiangli
(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choolof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25,China)
Abstract:There exists dispute on the author of Gan Ying Lei Cong Zhi. Both Shuo Fu and Series of Si Ku Quan Shu Title Collection consider the author to be Zhang Hua, although the Tianyi Pavilion transcript has Chen Xingnan’s inscription and believes the author may be Hu Gangzi and the name of the book should be Gan Ying Lei Cong Pu.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also believes the author not be to Zhang Hua.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people in the old times randomly falsified book and changed titles, and the contents related to geography in Bo Wu Zhi was extracted to be Zhang Hua Bo Wu Ji, it is possible that Gan Ying Lei Cong Zhi was an excerpt from Bo Wu Zhi. From the specific contents, the two have similar or even identical argument and text. Thus Gan Ying Lei Cong Zhi should be part of Bo Wu Zhi.
Key words:Gan Ying Lei Cong Zhi; Bo Wu Zhi; mutual sense of species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张乡里,女,安徽宿州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DOI:10.3969/j.issn.1671-2714.2016.0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