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補遺
趙 貞
(作者單位: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補遺
趙 貞
2008年,筆者曾撰《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研究》一文,對公元10世紀時期敦煌文獻中所見的曹元忠鳥形押、曹延禄鳥形押、尚書鳥形押、長千鳥形押和雜寫鳥形押記作了詳細梳理,指出鳥形押的作用和意義並不限於節度使簽名的一種形象圖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統治敦煌的一種强化手段,也是曹氏歸義軍政權的一種標誌性符號*趙貞《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研究》,《敦煌學輯刊》2008年第2期,10—28頁;《鳥形押: 歸義軍曹氏統治敦煌的標誌》,《尋根》2008年第3期,33—39頁。。不過,由於管見所及,視野所限,致使在鳥形押材料的梳理中多有疏漏。近年來,隨著《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和《敦煌秘笈》的相繼公佈,又有數件鳥形押的文書面世。有鑒於此,筆者在前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敦煌文獻中的鳥形簽署和畫押進行補遺,力求對曹氏歸義軍鳥形押的梳理趨於完整。
一 曹元忠鳥形押
在敦煌歸義軍的歷史上,曹元忠是執掌歸義軍時間最長的節度使(944—974年)*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3—122頁。。在擔任歸義軍節度使的30年中,他先後使用過三種形制的鳥形押,這在 P.3257、P.2641、P.4992、P.3160、S.3728、P.3272、P.3111、P.3897、P.3975、S.5571、S.5590 等寫卷中有明確反映。除此之外,還有P.2482P《榮保慶等名單》、S.8426《歸義軍酒破歷》、S.8516B《廣順二年(952)使帖牓衙門應管内員寮軍將□□百姓等》、S.8516A《廣順三年(953)敕歸義軍節度使牓》、BD16479《繼遷葬親狀並判》和Дх.4749《建隆三年(962)歸義軍節度使帖》六件文書,亦有曹元忠鳥形押使用的痕跡。
(一) P.2482P《榮保慶等名單》

(二) S.8426《歸義軍酒破歷》
此件揭自Ch.00103,已殘成10片,内容俱爲歸義軍衙内官酒支出破用歷。在這些官酒消費賬目中,提到了願富、赤書宰相、蟲兒、南山宰相、張定奴、程押牙、王留住、閻都知、石定子、義成、瓜州張都衙、賈僧政、李憨兒等人*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83—84頁。,也提到了賽神、祭拜、鎮壓、送路、藏鉤、算羊、刈麥等活動。值得注意者,《破歷》對於每筆酒的支用去向及數量都有詳細的記録,有時每筆消費記録後還有草書的鳥形押,體現出歸義軍對官酒支出賬目的監督和審核。比如,較典型者有:

(三) S.8516B《廣順二年(952)使帖牓衙門應管内員寮軍將□□百姓等》
此件已裂成八個殘片,經綴合後,B1+B2爲一片,B3+B4+B5爲一片,B6+B7+B8爲一片。從紙質、字體、内容看,當係同一文書*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96頁。。但拼接後的三片文書仍不連續,中間亦有殘缺。其文字如下:
使 帖牓衙門應管内員寮軍將□□百姓等。


諸處攞拽□□官來者,一生百姓亦乃貶流會稽,的無容捨。仍仰准法指揮,不得有違□□者。
廣順二年□□(月)五日帖。

此件的性質爲“帖”,首、尾兩行“使”字較大,尾題年份上鈐有朱色“沙州節度使印”(首行亦鈐有一方朱印)。“帖文内容爲差發正散行人秋收事,官人不奉條流者,貶流會稽(歸義軍東部邊鎮)。據年代知署押發帖者爲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96頁。
(四) S.8516A《廣順三年(953)敕歸義軍節度使牓》
此件亦割裂爲數十殘片,經拼接、綴合後,除尾部兩行已殘外,内容尚算完整。具體文字如下:
敕歸義軍節度使 牓。
應管内三軍百姓等。右奉處分。蓋聞□封建邑,先看土地山川阡陌堪居,遂乃置城立社。況河西境部舊日總有人民,因爲土蕃吞侵,便有多(?)投□廢。伏自 大王治世,方便再置安城,自把已來,例皆快活。唯殘新鄉要鎮,未及安置軍人。今歲初春,乃遣少多人口耕種,一熟早得二載喉糧,柴在門頭,便是貧兒活處。仍仰鄉城百姓審細思量,空莫執愚,耽貧過世。丈夫湯突到處,逢財怕事不(?)行,甚處得物。自今出牓曉示,樂去者牓尾標名,所有欠負諸家債物,官中並賜恩澤,填還不交。汝等身上懸欠便可者,聞早去得安排次弟及時,初春趁得種田,便見秋時倍熟,一年得利,久後無愁。坐得三歲二年總□□□□□仍仰□□□□□□□□。
廣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牓。
此件第二行“應管内三軍百姓等”鈐有朱印三方,尾署紀年處亦鈐朱印四方,紙縫各有一方朱印,共三方,印文爲“沙州節度使印”*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95頁。,據此可知本件爲沙州歸義軍官文書之一,其性質是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簽發的“牓”,核心内容是爲配合新鄉鎮的設置,鼓勵管内三軍百姓前往新鄉開墾耕種,以便充實新鄉鎮的財賦和軍防。牓文提到,百姓樂去新鄉者,官方不僅給予恩澤賞賜,甚至還免除“所有欠負諸家債物”。牓文後有小字題名:“新鄉口承人押牙多祐兒、兵馬使景悉乞訥、李佛奴、於羅悉雞、趙員定、大雲寺僧保性、平康武揭橋兄弟二人。新城口承人押牙王盈進、玉關宋流住。”*《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12卷,151頁。應是樂於遷往新鄉的僧俗百姓名録。
(五) BD16479《繼遷葬親狀並判》
此件被裁成A、B兩片,爲同一内容,其中B片在上,A片在下,中間尚有殘缺,不能直接綴合,存文字7行,其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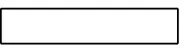
□繼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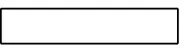
不幸薄福,禍尅慈親,葬日時臨,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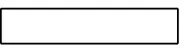
聞,伏乞
4 台□特賜贈濟 光揚,伏聽 處分。
5 丙辰年五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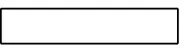
□支布壹尺,紙叁帖,酒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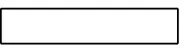
狀文中,繼遷因爲慈親亡故,葬期臨近,故向使主申請,請求特賜助葬物品。第6、7行是使主的批示,即賜布一尺,紙三帖(150張),酒三甕,及音聲人若干。P.4640《歸義軍布紙破用歷》載,己未年(899)八月十六日,奉判支與兵馬使劉英傑助葬粗布壹疋。庚申年(900)八月廿七日,支與押衙張忠賢助葬粗紙壹束,又支與押衙閻奉國助葬粗紙伍帖*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254、264頁。。又P.2629《歸義軍酒破歷》載,乾德二年(964)八月九日,衙内設甘州回鶻使酒壹甕,劉保通妻助葬酒壹甕*《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275頁。。這些破歷表明,歸義軍時期沙州的喪葬活動中需要支用相當數量的布匹、紙張和酒。這些喪事用品既然從歸義軍衙内領取,説明亡者應是歸義軍管内官員及其親屬,由此可知BD16479中的“繼遷”也應是歸義軍節度使屬官。本件中的鳥形押,其形制又見於P.3160《辛亥年(951)押衙知内宅司宋遷嗣檉破用歷狀並判憑》。據此,可推知本件中的“丙辰年”爲後周顯德三年(956)。
(六) Дх.4749《建隆三年(962)歸義軍節度使帖》
此件首部殘缺,尾部完整,存文字4行,每行後半部分已缺,其文如下:

此件文書中,第四行“使”字較大,係沙州節度使、歸義軍節度使的標識,這爲判斷文書的性質提供了依據。現知敦煌文獻中同類性質的文書有三件。其一是S.1604《天復二年(902)沙州節度使張承奉帖》。此帖鈐有“沙州節度使印”三方,首行、尾部各題有“使”字,且字體較大,墨蹟較濃*郝春文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第7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319—321頁。。第二件是S.4453《宋淳化二年(991)十一月八日歸義軍節度使帖》。此件鈐有“歸義軍節度使之印”,首、尾之“使”亦大字書寫,筆墨濃重,且尾部“使”字後有曹延禄鳥形押*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4輯,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年,306頁;趙貞《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研究》,10—28頁。。第三件是S.8516B《廣順二年(952)使帖牓衙門應管内員寮軍將□□百姓等》。前已提及,此件首、尾“使”字書寫稍大,且鈐有朱色“沙州節度使印”。因此,根據以上三件文書的信息,可將Дх.4749號文書的性質定爲歸義軍節度使帖,其首部雖然已殘,但可推知首行應有大寫的“使”字,且鈐有“歸義軍節度使之印”。又本件中的鳥形押,又見於P.3272、P.3111、P.3897、P.3975、S.5571、S.5590等卷中,爲曹元忠使用的鳥形押之一。綜合這些信息,可將Дх.4749定名爲《建隆三年(962)歸義軍節度使帖》。
二 曹延禄鳥形押
曹延禄是歸義軍曹氏時期的第六位節度使(公元977—1002年)*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24—127頁。,在執掌歸義軍的15年中,他根據“延”之俗體“”創製出側身左轉、展翅飛翔的鳥形押形象,這在P.2737、P.3835、P.3878、P.4525、S.2474、S.4453等寫卷中有生動反映。此外,敦煌文獻中還有S.8673、S.9455、S.8666、S.6998B、羽35等文書,均曾作爲曹延禄簽署而使用的鳥形押。如S.8673《丁丑年(977)八月都頭知作坊使鄧守興狀及判憑》載:

□
頭知作坊使鄧守興。
□
3 肆拾隻。未蒙 判憑,伏請 處分。
□
。
這裏“丁丑”,榮新江據鳥形押形制,推定爲公元977年*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109頁。,甚是。“作坊使”指歸義軍手工業的管理機構——作坊司的長官,通常由都頭充任,鄧守興即以都頭的身份兼知作坊司事務。據馮培紅研究,作坊司的職責是爲歸義軍官府製造各種手工業品,包括製造扇子、紙張、金銀器、佛軸、弓箭及煎膠等物品。有時作坊司還是服務於軍需的特殊産業部門,製造各種軍器*馮培紅《敦煌歸義軍職官制度——唐五代藩鎮官制個案研究》,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115頁。。作爲作坊司長官,鄧守興肩負著對當司製造的物品、器具和物資進行管理的職責。職是之故,對於都頭索流住和押衙閻瘦子的弓箭支給,鄧守興要如實向使主報告,請求節度使的“判憑”或“處分”。又S.9455《丁丑年(977)九月都頭知作坊使鄧守興狀及判憑》載:

□
憑十二(?)
□
2 都頭知作坊使鄧守興。
。

以上有關作坊使的3件公文書表明,曹延禄在執掌歸義軍節度使的當年和翌年(977—978),已頻繁使用鳥形押的圖案來代替節度長官的簽署。S.2474《己卯年(979)十一月駝官鄧富通狀及判》載:
1 己卯年十一月二日駝官鄧富通羣入算後駱駝破籍。
3 伏請 處分。
4 己卯年十一月二日駝官鄧富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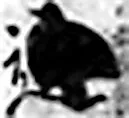
需要説明的是,S.2474還有庚辰年(980)駝官張憨兒上狀三通,分别彙報當年八月、九月駱駝死亡及皮肉處理事宜,請求節度使核實處分*《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4卷,86頁;《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601頁。。同類性質的文書還見於P.2737《駝官馬善昌狀並判》中。該卷記載了癸巳年(993)四至九月馬善昌的4次上狀及節度長官的批文。作爲管理駱駝事務的專職官員,馬善昌彙報了“换于闐去達坦”(韃靼)及出使西州時駱駝的使用情況,還兩次提到駱駝病死後“皮付内庫”*《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602頁。。此外,S.6998和日本杏雨書屋所藏羽35號文書中,還有乙未至丙申年(995—996)駝官馬善昌、李粉堆的上狀及判憑八通,先後8次向使主報告“羣上”、“槽上”駱駝病死及“皮付内庫”的詳情。這些狀文在短時間内即得到了使主的批覆。當然,在“爲憑某日”的判憑中,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代表使主個人簽名的鳥形押,其形制與S.2474完全相同。
再看馬匹的管理,在同期有關馬匹使用、破損、死亡及皮肉處理的官文書中,同樣能夠看到鳥形押的使用。S.6998B《乙未年(995)十二月至丙申年(996)二月歸義軍知馬官陰章兒狀及判憑》載:
2 判憑,伏請 處分。
3 乙未年十二月 日知馬官陰章兒。
這裏“知馬官”即歸義軍管理牧馬業的官員,負責馬匹的算會、調撥、使用、支給,以及損耗、死亡馬匹的核查、處理等事務。尤其是“槽上”或“羣上”馬匹若有損耗或死亡,知馬官都要及時、如實地向節度使彙報,請求批示。狀文中,陰章兒作爲知馬官,正在履行此職。實際上,相同性質的狀文,本卷還有7通,均是有關馬匹病死,“皮付内庫”的情況説明。其中知馬官陰章兒,還見於日本杏雨書屋藏羽35《丙申年(996)四至八月知馬官陰章兒狀及判》中:
6 判憑,伏請 處分。
7 丙申年四月 日知馬官陰章兒。
本卷文書中,陰章兒先後8次上狀,向節度使彙報槽上、羣上、僕射宅、王粉堆、泊再定等羣馬匹支用、病死及“皮付内庫”、“皮肉付藥酒社”、“皮肉付于闐使”之事*武田科學振興財團編集《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はまや印刷株式會社,2009年,236—237頁。,使主審核後,做出了“爲憑某日”的判署,從中不難看出歸義軍對馬匹管理的重視。
以上有關駝官、知馬官的上狀及判文,不約而同地傳輸出這樣的信息: 首先,無論駱駝還是馬匹,歸義軍支用的牲畜都是大駝、大騍駝和大馬。根據P.2484《戊辰年(968)羣牧駝馬牛羊見行籍》中大馬、三歲馬、二歲馬、當年馬駒、大駝、三歲駝、二歲駝、當年駝兒的分類,可知大馬和大駝即四歲以上的公馬和公駝,大騍馬和大騍駝則指四歲以上的母馬和母駝。從敦煌、吐魯番和于闐發現的中古契約文書來看,絲綢之路上有關馬、驢、駝、牛等牲畜的經濟活動(如買賣、雇傭、租賃、博换等),通常多在四歲以上的大牲畜中進行*詳見拙稿《杏雨書屋藏羽34號〈羣牧見行籍〉研究》,待刊。。無論是軍事出征和驛站交通,或是商旅運輸和農耕生産,還是提供肉食來源及皮毛手工原料,大牲畜在富國强兵、溝通内外及社會生産生活中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加大了大牲畜損耗、傷病和死亡的頻率。
其次,歸義軍對“槽上”、“羣上”牲畜的管理非常重視,不僅對駝馬的牧羊、徵調和支用有明確規定,而且對於駱駝、馬匹的死亡也有具體的處理方式。换言之,如果駝馬在提供畜力中死亡,那麽領養者或徵用者應將皮肉剥離帶回,交付“内庫”、“藥酒社”或有關官員(如張弘定、于闐使),作爲核實、檢驗牲畜死亡的憑據。吐魯番所出《唐神龍元年(705)西州兵曹處分死馬案卷》中,一旦長行馬“急黄致死”,即令馬子(馬夫)“自剥皮肉收掌”,“具録申州”。其中馬肉“任自出賣得直”,可允許就近出售。有時考慮到“其肉不能勝致”,或者“醜蛹不堪收什”*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250、257、259頁。,只能棄擲不收,唯有將馬皮帶回,輸納州府。吐魯番所出《唐總章二年(669)至咸亨元年(670)西州長行坊死馬價及皮價帳》*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372—375頁。提供了較爲典型的案例:

收,剥皮將來納庫訖。
五月廿九從伊州使回磧内死,皮肉棄不收,剥印將來,檢明毁訖。
□
,後征未納。
不難看出,長行坊馬匹死亡後,通常有“皮肉不收,剥印將來”、“肉棄不收,剥皮將來納庫”和“肉賣得銅錢,送司倉,皮納庫”三種處理方式。《唐六典·諸牧監》載:“凡馬、牛皮、脯及筋、角之屬,皆納於有司。”*李林甫著,陳仲安點校《唐六典》卷一七《諸牧監》,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488頁。可知駝、馬、牛等牲畜皮肉都是官方重要物資。以此參照,歸義軍駝馬死後“皮付内庫”的規定,顯然是因襲唐代畜牧管理舉措的生動反映。
三 餘 論
作爲替代曹氏歸義軍節度使簽署的一種形象圖案,鳥形押的性質或與中古社會流行的“花押”書式相近。史載,唐人韋陟“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宛若五朵雲彩,時人頗多羡慕,讚譽爲“郇公五雲體”*《新唐書》卷一二二《韋陟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4353頁。。在宋人看來,韋陟的“五雲體”就是通常所説的“花押”。周密《癸辛雜識》稱:“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韋陟五朵雲是也。”*周密撰,吴企命點校《癸辛雜識》,北京: 中華書局,1988年,102—103頁。説明“花押”其實就是將名字“稍花之”,最有效的方法是“草書其名”,既便於書記,也難於模仿。高承《事物紀原》稱:“古者書名,改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仿。《唐書》曰: 韋郇公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浸相緣,率以爲常,復有不取其名出於機巧心法者。此押字之初,疑自韋陟始也。”*高承撰,李果訂,金圓、徐沛藻點校《事物紀原》卷二《花押》,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67頁。這種草書名字的“花押”一旦出現,很快在中古社會流行*清代學者趙翼認爲,中古時期帝王詔敕已有“花押”現象,但所押者多爲“諾”、“依”、“可”諸字,“而非自花其名也”。一直到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制”。至於士大夫的“花押”,自六朝至唐宋則較爲常見。參見《陔餘叢考》卷三三《花押》,上海: 商務印書館,1957年,697— 698頁。。歐陽修《集古録》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説明五代時“花押”作爲簽署的象徵已在帝王將相中廣爲使用。葉夢得《石林燕語》載:
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畫,左引腳,中爲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匾,而收横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敕》,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去,旁别作一圈,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敕。*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石林燕語》卷四,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57—58頁。
此處“花書”,一名“花押”、“畫押”,其根本特徵是“草書其名”,乃至唐誥書名中“未見一楷字”。若以荆公王安石而論,所押“石”字亦是草書寫成,有時隨意走筆竟被識爲“歹”字,因而荆公力圖修正,但似有矯枉過正之嫌。這則故事表明,宋時押字即以代名,“不復書名也”*趙翼《陔餘叢考》卷三三《花押》,第697—698頁。,此種現象甚爲常見。宋人黄伯思《東觀餘論》曾説:“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顧炎武撰,黄汝成集釋《日知録集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602頁。可見,無論官方表章還是民間書尺牘,“花押”的使用確實非常廣泛。
以上論述表明,唐宋是“花押”、“押字”使用頗爲流行的時期,尤其是隨著商品經濟和契劵關係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花押”和簽署符號出現於社會經濟文書中*仁井田陞《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復刻版,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24—84頁。。以鳥形押而論,其實正是曹氏歸義軍創製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花押”圖案。通過這種鳥形押的簽署,凸顯曹氏的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押蕃落等權力,從而在沙州的治理與經營中打上曹氏歸義軍的深刻烙印。比如曹元忠鳥形押,其原型是“元”字,即仿照“元”字化裁、擴展而用四筆寫成。“一筆之點化作鳥首,二筆之横化作鳥翼,三筆之撇化作鳥身,四筆之右彎化作鳥足與樹枝,四筆組合成爲立鳥之形。”*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294頁。至於曹延禄鳥形押,李正宇指出是依據“延”之俗字“”化裁而成。其“”圖案化作鳥形,“辶”則保留字體筆畫,係圖案與字體之合成*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294頁。。黄征認爲,此種形制的鳥形押,根據結構分析應是“辶”内著“鳥”或“隹”、“翟”之類的字形。“辶”内著“鳥”,相似者有“邊”字;如果是“辶”内著“隹”(“隹”亦鳥也),則爲“進”字;如果是“翟”,則有可能是翟姓某人的姓名合文*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292頁。。無論是哪種字形的草書,顯然都屬於“押字即以代名”的範例,因而比較符合唐宋“花押”構造的基本特徵。
鳥形押的簽署,筆者曾指出應與10世紀敦煌地區流行的飛鳥獻瑞現象有關。或可參照的是,昭宗乾寧二年(895),割據越州自立爲帝的董昌,就很好地利用了“鳥獸”的祥瑞意義。《新唐書·董昌傳》載:
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秘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吴、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册’,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新唐書》卷二二五下《逆臣下·董昌傳》,6467— 6468頁。
關於董昌稱帝之事,《新五代史·錢鏐世家》載:“妖人應智王温、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囊時謡言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以示昌,昌大悦,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兵爲兩軍,中軍衣黄,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錢鏐》,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837—838頁。羅平鳥由於“四目而三足”,形象上與普通鳥類完全不同,且出自《越中秘記》,因而更增加了它的神異色彩。此鳥見於吴越地區,且能主宰吉凶福禍,因此在吴越之地被奉爲神鳥。蓋由於此,董昌自立稱帝,自然而然地與“羅平鳥”聯繫起來,不僅國號爲“羅平”,而且署名“文與鳥類”,似乎也打上了鳥形押的印記。這種建國稱帝的神異色彩,很容易與稍晚時候“白衣天子”張承奉建立金山國時的白雀獻瑞景象聯繫起來。頗有意思的是,董昌的軍隊,改編爲“歸義”,不經意間亦與沙州歸義軍巧合*余欣《符瑞與地方政權的合法性建構: 歸義軍時期敦煌瑞應考》,《中華文史論叢》2010年第4期,374—375頁。。聯繫曹議金時的《白鷹呈祥詩二首》(S.1655),不難看出,曹氏歸義軍的鳥形押創製,可能與董昌稱帝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借助祥瑞神鳥的象徵性庇護,完成對敦煌長久統治的願望。
法國學者艾麗白指出,鳥形押的使用最勤的是“那些與歸義軍節度使最高權力機構往來的物資供應報告中”*艾麗白《敦煌漢文寫本中的鳥形押》,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室編《敦煌譯叢》,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204頁。。進一步來説,鳥形押大多出現於歸義軍節度使對衙内諸司(宴設司、内宅司、柴場司、酒司、軍資庫司、羊司、作坊司),駝官、知馬官有關財賦、物資和牲畜管理的勾稽與審核中,這在以“爲憑”爲標誌的諸司上狀及“判憑”中有明確體現(P.2641、P.2737、P.3160、P.3272、P.3878、S.3728、S.5571、S.5590、S.2474、S.6998B、S.8666、S.8673、S.9455、羽35等)。這些關乎歸義軍財賦、物資和牲畜管理的狀文及判憑並不始於曹氏,早在張淮深執掌歸義軍時期(867—890)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判憑”文書,這在光啓三年(887)張淮深簽署與批示的一系列牒狀中有明確反映。

光啓三年(887)張淮深處分牒狀表*表格參考資料有: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12卷,56頁;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67頁;《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622頁;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189—190頁;《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66—167頁。
上表中,P.3569V中張淮深的批示值得注意。“付陰季豐算過”,即指派陰季豐對官酒的支出與破用情況進行“算會”和審核。同卷《押衙陰季豐牒》稱:“右奉判令算會,官酒户馬三娘、龍糞(粉)堆,從三月廿二日於官倉請酒本貳拾馱,又四月九日請酒本粟壹拾伍馱,兩件共請粟叁拾伍馱。准粟數合納酒捌拾柒甕半,諸處供給使客及設會賽神,一一逐件算會如後。”*《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622頁。牒文中,陰季豐以押衙的身份對酒本、酒賬和酒歷進行勾稽和核算,實際上扮演了“勾官”的角色。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指出,勾檢制是行政管理制度的核心,以勾檢制爲核心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形成唐前期文治武功卓著、經濟繁榮、文物昌盛的重要條件。敦煌吐魯番所出的官文書中,某日受某日行判、録事勾檢稽失、録事參軍勾訖,這三者構成對每個官府都適用的勾檢制*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0頁。。但歸義軍時期,諸如押衙陰季豐之類執行“算會”職責的勾官並不多見。更多的情況是節度使直接對財政和物資賬目的勾稽和審核,這在張淮深、曹元忠、曹延禄時期,都呈現出財務管理中的共通性特徵。换個角度來看,使主對財賦和物資用度的勾稽,以及對牲畜支給及死亡後皮肉處理方式的核查,體現出歸義軍節度使所具有的“觀察處置支度營田押蕃落等使”*歸義軍節度使中,張議潮、索勳、曹元忠官銜均有“支度營田”。P.3556(10)《張氏墓誌銘並序》:“伯祖皇諱議潮,河西十一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右神武統軍兼御史大夫伊西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保。”莫高窟98窟甬道北壁供養人第三身題名:“敕歸義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支度營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守定遠將軍上柱國钜鹿郡索諱勳一心供養。”S.518《曹某建窟簷記》:“維大漢天福拾肆年歲次丙午八月丁丑朔廿二日戊戌,敕河西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支度營田押蕃落等使,光禄大夫特進檢校太傅,食邑壹阡户食實封三伯(佰)户,譙郡開國侯曹某之世再建窟簷記。”、“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等使”的性質*歸義軍節度使官銜通常附有“管内營田”。S.P.9、P.4514《曹元忠造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弟子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開國侯曹元忠雕此印板。”莫高窟第431窟窟簷題樑:“維大宋太平興國伍年歲次庚辰二月甲辰朔廿二日乙丑,敕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管内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譙郡開國公食邑一阡伍佰户食實封七佰户曹延禄之世創建此窟簷紀。”。無論是“支度營田”或是“管内營田”,都説明使主也是管内最高的財政長官,因而在那些有關物資供應和駝馬支用情況的牒狀中,使主在三日之内的批示——“判憑”無疑也體現了較高效率的財務勾檢。另一方面,光啓三年酒司曹文晟的牒狀及判憑,就性質而言,同樣是財務支出情況的報告,並請求使主的勾稽與審核。無論行文、格式還是批示,都可在10世紀後期的“判憑”文書中找到對應,從中不難看出歸義軍曹氏對於張氏制度的因襲與拓展。唯一不同者,使主的押署,從張淮深的親筆簽名,到曹元忠、曹延禄的鳥形押,正好佐證了我們對歸義軍曹氏鳥形押的認識,即鳥形押的作用和意義並不限於節度使簽名的一種形象圖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統治敦煌的一種强化手段,也是曹氏歸義軍政權的一種標誌性符號*趙貞《歸義軍曹氏時期的鳥形押研究》,10—28頁;《鳥形押: 歸義軍曹氏統治敦煌的標誌》,33—39頁。。

敦煌文獻所見曹延禄判憑表*表格參考資料有: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3輯,601— 602、605— 608頁;榮新江編著《英國圖書館藏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録(S.6981—13624)》,61、107、109、127頁;《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12卷,38—39、182、187、241頁;池田温《李盛鐸舊藏歸義軍後期社會經濟文書簡介》,《吴其昱先生八秩華誕敦煌學特刊》,臺北: 文津出版社,1999年,29—56頁;《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影片册一,236—239頁。

(續表)

(續表)
(作者單位: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