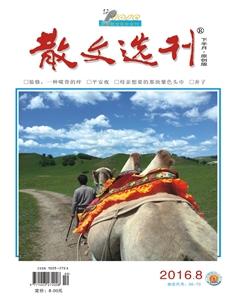母亲的顶针
傅柏林
母亲的顶针是黄铜的,由于常年使用,顶针光滑得就像一枚闪闪发光的金戒指。
顶针,是母亲做针线活的好帮手。有了它,母亲的针线活做得既快又好,把旧衣变新衣,大衣改小衣,尤其是绣花、裁剪,无论是什么样式的布料,只要她看上一两遍,就能做得像模像样,而且手工精细绝伦。母亲常常用些布头线脑,为我们兄妹仨缝制各式各样的衣衫。每当看着我们兄妹仨穿上合身的新衣服,母亲脸上就乐开了花。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的这一门手艺的确让我们原来紧巴巴的生活滋润了不少。
要说针线活,做鞋最苦最累。那年月,由于父亲每月只有72元收入,工资不高,没钱买鞋,我们兄妹仨穿的棉鞋、布鞋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那时做鞋底的原料是穿破的旧衣服。母亲把旧衣服剪成布片子,将布片子摊在饭桌上,刷一层糨糊粘一层布片,结结实实地糊上许多层,晾干后揭下来,再摞在一起,然后依照我们兄妹仨脚的大小剪裁鞋底,厚度足有一扁指宽。纳鞋底时,母亲要用锥子使劲将鞋底扎透,再凭手指上的顶针将粗钢针从鞋底上顶过去,实在顶不出来的时候,就用钳子往外拔。为了结实,每穿过一针,母亲都要用手把粗线绳拽住狠狠勒紧,一双鞋底纳下来,手指节都会勒出血来。天长日久,母亲那双白嫩、细滑的巧手,渐渐变得粗糙弯曲。
1984年的冬天,我从中越边防哨所到昆明军区出差,首长为了表彰我在边防前沿阵地上的突出战绩,破例给我放了五天假,让我回家与父母家人团聚。在我临去部队的前夜,深夜醒来,只见母亲为我收拾行李,缝补衣裳。灯光下,我静静地看着母亲偷偷落泪。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当时在阵地防御战中边防战士流血牺牲时有发生,母亲在为儿子的生命安危担惊受怕。此后,在边防前线,在猫耳洞,在八里河东山的冬秋寒夜里执勤巡逻、站岗放哨,每当我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背心,抚摸那缝得细密的针脚,仿佛感受到母亲那千缕柔情、万般慈祥的母爱,心里便涌起一股暖暖的激流。
如今,当我读到唐代诗人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就想起32年前的那个不眠之夜。
责任编辑: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