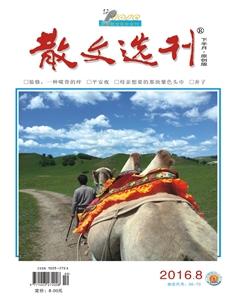装修,一种噬骨的痒
吴曦
无孔不入的粉尘,在我拥有的地盘上,肆无忌惮地张扬。一刻不停的吱吱切割声,让这讨厌的家伙更加飞扬跋扈。
我冒着黑发变白发的危险,乐此不疲地在粉尘的相拥相亲中来回穿梭,听从装修师傅的指令与调遣,把瓷砖搬到盆里浸水。盆里冒出气泡,如同儿时吹的肥皂泡。还有吱吱的响声,告诉你瓷砖的质量指数。师傅脚下的水泥渣,需要扫帚效劳,出面邀请无疑仍然是我。
除了鞍前马后为师傅效力外,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监工。这是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师傅明白东家在场的意义;东家清楚自己不在场可能造成的后果。曾经请两个装修队实地考察:丈量,画图,测算。最终报给我的造价永远超过我的预期。只好返回老路,按传统的运作模式,化整为零,根据土木水电铁五大类不同材料,请不同的师傅施工。
自主设计,选材料,看质量,定价格,货比三家,价砍百家,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亲力亲为。
倘若装修师傅心里不爽,要刁难你,说你买的材料造型差,品相差;这不行,那不行。言下之意,只能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退货就是换货。
乖乖,到了这节骨眼上,师傅的话一句千钧如同圣旨。
总在一个时间点上被敲门声惊醒。
清晨五点,这对很多早起和有晨练习惯的人来说,不算早。但对于我这样习惯晚睡晚起的人,算是太早了。我一般在早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起床。五点,正是熟梦酣甜的时候。
很重的敲门声伴着东家名字的叫唤声,让人听出声音里的急切与快意。一旦惊醒,我便一刻也不敢怠慢,边穿衣服边大声回应,表明自己已经起床并速来开门。从酣梦中带来的那些哈欠,早已吓得无影无踪,只能空张嘴不敢出声音。要知道,这是关系到一天的装修进度呀。
我的装修在夏天,这是最理想的季节——雨水少、日照长、干燥快。挑工每天赶在太阳出山之前,完成一天所需要的定量——沙石土、水泥砖,按各自比例,挑到装修师傅指定的地点,然后赶到另一家或者另一个工地继续干活。他们每天都是掐着时间辗转,也不容易,为着养家糊口。
对于我来说,他们到不到场,关系到这一天的装修是否打水漂。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没有装修材料,装修师傅就有了转移“战场”的足够理由。他们和挑工一样,玩的也是“连环套”。
不知从何时起,装修市场变得如此陌生与纠结,如同耍猴儿变戏法一样。
挑工的工钱是这样算的:沙石土水泥砖,按每层定价,不同材料不同价。比如沙一担一层多少钱,砖按块算,水泥按包算。户外十级台阶算一层,平地十米算一层。我家只有三层,结果算作六层。因为材料卸在离家门口十米远还加二十级台阶的地方。
我有点茫然,这是哪门子的数学?比陈景润的“哥得巴赫猜想”还玄乎。
挑工说,都这么算的,这是市场行情。
行情?如今行情也真多,什么事都可以扯上边。
好吧,既然是市场行情,就别怪人家挑工,那就随行就市吧。
想想挑工也不容易。每天光着油黑发亮的膀子,肩上压着沉沉的担子,一头搭着一条毛巾。烈日在身上洒一层汗珠,雨一样流到地上。操起毛巾不停地擦汗,又不停地流汗,那毛巾简直可以拧出水来了。被汗水濡湿的脚板,在层层台阶上留下宽大厚实的脚印。脚印在我家的楼梯和屋外的台阶上,重重叠叠,就像趴着一只只巨无霸草虫。挑工一日三餐的体能积蓄,就为着这肩上和脚下的功夫了。
这挑工是从乡下来的农民工,五十多岁了,瘦瘦的身子露着骨节,像是被挤干了水分,没有多余的东西一样。太重的担子压在他的肩上,你会担心他的身子骨,什么时候突然哗啦一声散了架。
每回我都劝他悠着来,量力而行少挑点。饭要慢慢吃,钱也要慢慢赚。他说不碍事,瘦骨伶仃顶千斤,趁现在还不算老多赚点钱。
他家离我家不远,下一道坡,穿一条巷就到了。
他有一男三女。大儿子开“地老鼠”载客,俩女儿上学,老幺在家。我每回给他的点心他都舍不得吃,趁歇息的间隙急急送给家中的幺妹。我说,还是自己吃吧,免得把自己累垮了。他笑笑,多喝点水就不饿了。于是,我每回就多给他一份点心。他不置可否。汗水从额上流下来,那张蒙着粉尘和粘着沙土的脸变得四分五裂,很像京剧脸谱,又像一副假面具。我想,他一生的乐趣,似乎都在这个家上,都在儿女们的身上了。
装修师傅也是乡下进城的农民工,比挑工几乎小一半岁数。原本个头就瘦小,理了个几乎露青皮的平头,更显稚气十足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手下却跟着一大帮人,不是亲戚朋友,就是同乡本村,甚至还有为谋生投奔他的非亲非故异乡人,其中还有两位都老大不小算得上是他的叔伯辈了。
砌墙的时候,一帮人马悉数到位,按照他的指令摆开阵势,每人各占一个位置,一刀泥浆一块砖,手起刀落,一上一下很有规律和节奏。除了砖刀与砖的撞击声外,便是一阵沙沙作响,如同放大无数倍的蚕食桑叶的声音。
分散与聚合,是他们的作业方式。除了砌墙体、倒平台需“大兵团”作战外,其余多半是分散在各家各工地小股作业。
顶层墙体拿下来后,装修师傅找我结账。我说,不是定好完工后再结么?顶多也是过半后的事。装修师傅说,那是指小股作业。一大帮人马不及时结算,到时理不清。
原来如此。怪不得“大兵团”作战,风卷残云,三下五除二,急速又麻利,很是干脆。小股作业,就不一样了,实行的是“拉锯战术”,你急他不急,来一天歇两天,你催他,他便摆出歇工的种种理由,从不提在另一家干活的事儿。说,我们也想早点竣工,好接新活儿干。其实,他们早就一口气答应了五六家。然后,就开始南征北战,四处打游击,东干两天西做三日,既占有了市场份额,又不得罪这些东家。皆大欢喜,何乐不为?
他们既玩“连环套”,又玩“空手套”。
装修师傅将一张比火柴盒大点的纸片给我,上头挤挤挨挨地堆着豆芽菜一样的数字。我带着疑问加设问的口气,有这么多么?装修师傅说,没骗你,就是这么多。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卷尺,把墙体重新量了一遍,边量边让我看数字。对吧?你帮过我的忙,我怎么敢骗你?
我有片刻的脑“休克”,然后快速地在记忆库中搜索。
哦,是你。你是阿齐的那个侄儿?
对啊。
阿齐是我的邻居,我们邻里历来相处得很好,有事都会相互帮着。这回装修房子,是阿齐帮我联系的师傅,但他没说就是他侄儿,我也从没见过这个侄儿,只是通过两次电话,压根儿就没想到就是这位装修师傅。
装修师傅说,我会记住你的好,但不是现在。现在一大帮人的工钱没办法折扣。装修由我做主,会给你便宜。他态度相当诚恳,稚气的脸十分可爱。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稍稍有些狼狈,好像我早有预谋一样,算计好这个时候用手上的砝码同他进行一场交易。
他果真没有食言,我的装修自始至终由这位小个子师傅“主政”。打下手的小工,有时一个,有时两个。他的一个哥哥则始终跟着他。
他哥的身体比他壮实,海拔也比他高很多,他把他哥使唤得团团转。高兴的时候哥哥长哥哥短;不高兴的时候,只要他哥有一点点闪失,就被骂得狗血喷头。
他哥也真是,都老大不小了,也跟了他好几年,手艺一点都没长进,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呀。一次,他叫哥粉刷卫生间的一根下水道的塑料管子。整整折腾了一天,水泥洒落一地,把个塑料管子抹得如同烟囱。小个子师傅气不打一处来,冲进卫生间,抢过泥勺摔在地上,还把他哥推了个仰八叉。指着他哥的鼻子骂道,你给我出去,出去!我不要你这样的徒弟。
第二天,他哥果真没来了,换了个新徒弟。我埋怨地说,毕竟是你哥,怎么能这样对他?
他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这是工场呀,是干活的地方,没什么亲情可言。要是都碍着面子,手下十来号人怎么捯饬?又怎么服人?我被一通话呛得哑口无言。
我终于明白,大凡能震人的人,总有他过人之处。
那天,要上一条长三米、重一百多斤的钢条当挑梁,叫了五六个师傅来帮忙。结果好一阵折腾没整出一点名堂来。正在忙着贴瓷砖的矮个子师傅,急得眼睛快喷出火花来。他飞身跃上脚架,肩膀顶起钢条,大喝一声,上!钢条稳稳当当落在墙两头。
房子如人的脸,上了年纪脸皮就松弛了,皱纹也出来了,眼袋耷拉了。这次想动个大手术,把该拉的皮拉了,该整的地方整了,该垫高的地方垫高了。所以此次装修就叫作内部结构大整容。按我心仪已久的简欧风格,进行五官全挪位。动刀动枪、敲敲打打、拆东墙补西壁就在所难免了。这样一来,房子就像刚经历过一场激烈鏖战的战场。
粉尘弥漫如同滚滚硝烟;残壁断垣有如坍塌的城垛;破砖碎石,活像被炸成四分五裂的死难者的尸身;那些丢弃在建筑垃圾上的坛坛罐罐,好比战败者的头盔;地上的一两根木棍还有酒瓶,一如断树残枝;破碎的瓷砖,恰似古代战衣上的甲片,随着主人的丢盔弃甲而撒落一地。还有惊慌失措的壁虎,正落荒而逃;蟑螂到处爬来爬去;一群浩浩荡荡的蚂蚁抬着一只死蟑螂,像在游街示众……
每天我有两次打扫战场,收拾残局。一次是中午,是在师傅回去吃午饭的时间。这次的收拾并不太费劲,只是稍作整理和归拢,整出一块让师傅下午能够施展手脚的地盘。第二次是傍晚收工。这是大清理,是把一天中的建筑垃圾彻底清出门外,好让挑工一大早就有活干。我常常是吃完晚饭就动手,一直干到深更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挑工的叫唤声中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烧水,泡茶。把茶放在避开粉尘又显眼的地方,再摆上几包香烟。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师傅使唤和差遣了。
师傅有好几拨,差遣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泥工,他常常会叫你拉住卷尺一头丈量尺寸,或者叫你把瓷砖搬到盆里浸泡。要是瓷砖不够了,你就得火烧火燎地赶到瓷砖店,又屁颠屁颠地赶回来,生怕误了活儿。又比如电工,零件最小,又使唤最多。一个插座,一只开关,甚至一颗螺丝钉,都要你去跑。
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师傅一动嘴,东家跑断腿。
房子装修是个小工程,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粗略算来,至少有十类以上的工种,十拨以上的装修人马。有人结合民间五行特性,捣整出十个字,来概括装修的大体内容:金木水火土,电梯刷吊挑。
二十年前,我盖房连装修,除水电外,顶多就两拨人马,无非土加木,所以过去把盖房子叫“大兴土木”。如今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像在表演分身术:门窗都用铝合金或者不锈钢(金);木头只用在家具上(木);水塔、热水器、太阳能、空气能……水的家族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先进(水);灶也和土分家了,用组合式厨灶(火);瓷砖、石板材、金刚板取代了水泥地面(土);冰箱、空调、电视、电脑、电饭煲、微波炉……五花八门的家电变过去的单一线路为家庭电网(电);楼梯的扶手,换上更为美观雅致的新型材质(梯);墙壁粉刷无需泥工代劳,自有专业人马(刷);做吊顶另有其人(吊);挑工必不可少(挑)。十项工种十拨人马,我要轮流面对,接受他们的善意,友好,苛刻,挑剔,甚至于刁难。
师傅列了个清单让我购买缺了的材料。我要是为难,说,不知道哪家好,也不晓得看货色。师傅就会略作迟疑说,哦,是这样啊?那我中午上工时顺便帮你捎带一下。说得不经意,也很轻描淡写,像是一种无法推辞的责无旁贷。这种事,其实很正常。要不是几乎每个师傅都如出一辙,像是一种模本的翻版,我也不会去“偷翻”底牌。
如果东家自己去买材料,师傅连问都没问,也会从货色和品牌中看出端倪来,知道货出哪家店铺。实在无法辨识,他才以一种十分关切的语调问东家,而后避开东家,给店老板打个电话,说是自己推荐的。店老板就会记下这一单,累积一段时间后,就会叫师傅来店铺领取回扣。说来,师傅也不容易,都是为了生活,尤其是那些农民工。
那个矮个子装修师傅,进城七八年了,还没有立足之地,租在离县城二里地的郊外一户也是农民的家中,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因为没有户口,三个子女上学都要高价。收入比别人少,付出却比别人多。师傅吃不吃回扣,其实这事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师傅与店家的双赢,并不建立在我的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对于店家,是利润的累积;对于师傅,是搂草打兔子——捎带;对于我,毫毛未损。装修房子本来是件惬意的事,可在我这里,则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好不容易挨到尾声,几拨装修师傅同时都不来了。说是有个楼盘交房,装修的日子都定了,帮东家讨个好彩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装修市场的行规,或者叫潜规则——斩头留尾吃中间。结账的时候,挑工拿了一张小纸片给我,像是从孩子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头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像虫子一样爬。好多字不是短斤少两,就是缺胳膊断腿。比如“水泥”写成“小尼”;“砖”字成了“专”;“层”字里的“云”少了一横……不过,我倒是看明白了。我把我记的账单拿出来对照,感觉数字有出入,便说,好像不是这个数。他吓了一跳,紧张得额头都冒出汗来了,说,我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还算了好几遍,怎么会错呢?
那天他到我家结账是在晚上,灯光下的汗珠晶亮又饱满。看他那紧张样,我连忙说,钱少算了。他缓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多算。又有点纳闷,也不会少算呀?我把两张清单一项一项对照,一项一项念给他听。念到总金额时,发现他那张清单的钱少了。
不等我发问,他连忙解释,是这样,我扣掉一份点心钱了。
我实在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好。叽叽歪歪了一阵,最后冒出一句,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不成我多给你一份点心,是为了赚你一份点心钱?
他见我生气,有点不好意思,像做错了事的孩子,手足无措,一只手使劲地摩挲着短而稀疏的头发,语无伦次地说,已经有一份了……我只是想……不是这意思……千万别误会……吃人家的东西总要付钱的。
我不再多作解释,话说得很干脆,你要是把我当邻居,就把那份钱退回去。下个月我房后的拨岸和沟也要动工,还是你来做活。要不,我就另请他人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吓到了。唯恐我有活不叫他干。农民工最怕的是没事儿做干闲着,有劲没地方使;最盼的是天天有活干,即使忙得累趴了,心里也快活。他到我家干活,鼻子挨着嘴巴,效率老高,一天能干出一天半的活。
好吧好吧,就听你的吧。他的额上仍然在冒汗。他用力抹了一把,脸上湿湿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抑或是鼻涕?
和矮个子装修师傅结账就简单多了。他说,我就不写清单了,要是信不过,你自己算一遍。总共两万块,你就给我一万五吧,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不让。
我傻眼了。愕然了。没见过如此干脆的人,还带着一点点霸气。
我说了,凡是能服人的人,肯定都有两下子。
这满脸稚气的小不点,凭什么后头会跟着一大帮年纪比他大得多的泥工师傅?
这世界,凡是存在的,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