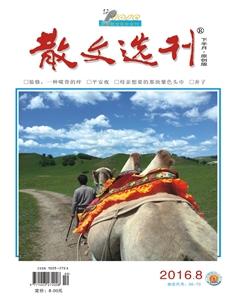平安夜
刘荒田
一
纸杯里的咖啡没加糖,越喝苦味越浓。10分钟前,我走进新开张的“汉堡王”,见识“麦当奴的老冤家”的新气象。这位于“地王之王”的庞大店面,多年来开的是麦当奴,不久前才因租约到期被取代。刚才我进来,排在长队里,一排收款机在柜台上侍候。轮到我了,收款员是靓丽的墨西哥裔女孩,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她告诉我,买汉堡包薯条之类要等叫号,咖啡却由她负责供应,快得很。说罢,走向背后的大型咖啡机,磨磨蹭蹭好几分钟,还是摆不平,咖啡终于出来了,却一滴慢似一滴,有如今晨小雨后的檐霤,我猜她按了浓缩意大利咖啡“厄可斯皮拉索”的键。好在,我不但不“赶”,还正好有时间根据笑容的真诚度与口音为她设计了身世:第二代移民,父母分别是旧金山旅馆的清洁工和搬运工,她在州立大学上一年级,趁假期来赚买第六代苹果手机的钱。店新开,新手来不及训练,便出这等低级错误。我站在一旁静候,倒是小妞儿急得脸成了桃子。咖啡递来,我接过,道谢。她说:“久等了,抱歉。”收款2.25元。我暗里叽咕,星巴克咖啡店的咖啡才2.10元,那才叫正宗哥伦比亚风味。
把喧闹的餐厅扫视一遍,靠里的桌子都满了,近门口处一张形如酒吧的高桌空着,因为当风的缘故,我面对大门而坐。和我同座的是比我年轻10多岁,但比我老气横秋的黑人大叔,他以老牛嚼嫩草的悠然吃特大汉堡包。我独沽咖啡一味,或者说,为取得落座于此的资格而喝。我和芳邻的视线一致,对着五步开外的人行道。但小有不同,他注意的是本店一位派出的黑人小姐,她身穿浅蓝色制服,腰背颇为粗阔,一如流水中的礁石,给川流不息的行人予以美好的拦截,递出一个个迷尔小包,里面盛着量少而实惠的爆米花。这可是极管用的广告,我目睹人流中的若干支流,就是在吃了爆米花以后改道,“流”进店里的。这“中流砥柱”虽胖,但因年轻而妩媚,怪不得胖大叔面带微笑紧盯不舍呢。
我较为超脱,因为老的缘故,看的是大街上人的潮水。马上想起20多年前,也是今天,我在离这里七八个街区的“马丹巷”上班,也是这个时刻,我趁休班来这一带看人潮,看累了,坐在联合广场的石阶上读木心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其中有句:“我漫游各国,所遇者尽是些天然练达的人,了无愧怍,足有城府,红尘不看自破,再也勿会出现半丝赧颜半缕羞色了,心灵是涂蜡的,心灵是蜡做的……”于是竭力思索,那一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不错,所有物品的价格提高了,在“金发女郎比萨店”,从前,不必顾“体面”的年轻浪子买下一块当街大嚼,以解决午餐只花一块钱,如今,连“每天特价”、以拍斯脱酱拌鸡肉当馅料的比萨,一块连税金要四块多。其他方面呢?明显的区别似乎不多。这就是和平的可爱之处——社会整体位移,“年份”的站台过去一个又一个,稳妥,安宁,教人浑然不觉。
二
喝完咖啡,把纸杯放进垃圾箱。从爆米花女郎旁边经过,马上沉没在人海里。此刻旧金山城内,任是哪个地方,论人的密度,论色彩的浩瀚,都比不上这里——跑华街和市场街的结合部。一来,这儿是缆车总站,登上具有170多年历史,以地下钢缆牵引的交通工具,无疑是外地游客的必选,排队登车的人绕了几重密圈。二来,旁边就是地铁和市内电车、巴士的中转站。电动扶梯上密匝匝的是回家的人。三来,这是宣传家和音乐人的必争之地,朗诵的高声,试图掩盖黑人小乐队的小鼓和吉他;救世军劝捐的铃铛,夹在因太杂乱反而显得无关紧要的市声里。卖“超级普雷结”的摊贩,和档前扛着“拯救人类”大牌子、晃来晃去的理想主义者相安无事。
怎么说,这也是我在旧金山湾畔的旅游名城度过的第35个平安夜。若是看热闹,一如乘缆车,如果赶时间,我不像来自全球的游客那样在总站排进长队,而是往北步行一两个街区,从尾部跳上车。我大致判断得出,会聚于此的人海,支流来自何处。看购物袋的标记,知道兴奋得颊如桃花的姑娘们,刚刚从“梅西百货”的试衣间待过,手里提的是自己中意以及自以为亲人也喜欢的衣物;带LV标记购物袋里一盒盒的是什么?该是最新潮的手袋,妩媚的“玛丽BB”,端庄的“凤凰PM”,瑰奇的“奇蒙特”——但不可一概而论,得看请“流向”,同是“家里衣橱永远缺一件最中意的”女士,如果从市场街南侧踏着斑马线过来,源头便是“老海军”和“诺斯特朗”。手拿带《星球大战·原力觉醒》中的武器——光剑和激光重炮的孩子,来自一个街区以外的“迪士尼”。骑在爸爸的阔肩上,手拿五彩气球的孩子,那气球是联合广场旁边的大叔吹的。大叔旁边是临时搭建的溜冰场,场内播放的圣诞音乐节奏特别欢快,使得人海上空有如风筝的气球,招摇时带上节拍。戴虎头帽的西班牙裔小男孩,在妈妈推的婴儿车上,睡相无比安详,从广场方向飘来的三支小号的竞奏,奈何他不得。今天,专卖虎头帽的小摊,赶猴年的时髦,制作了一系列“猴头帽”,档主是中年女同胞,今天喜气洋洋,15年前我知道她起家时摊子的位置——海悦旅馆斜对面的十字路口旁边。
我在这一带走了这么多年,随便拣哪一处,都说得出一个半个故事。比如,市德顿街面对联合广咖啡店的“寇尔·汉恩”名牌专卖店,从前是专卖意大利名牌如巴尔蒂尼和菲拉格慕的“彭密”鞋铺,它的经理卡尔,男同性恋者,20年前在“马车”餐馆的酒吧内,意外撞到旧情人,绝望地吼叫一声,扑上前去要同他拼命,因为后者使其得了致命的艾滋病。从前,法兰科斯大旅馆的看门人——黑人拉里,因替全世界无数政要开过门而成本市名人,他在门口接待客人凡40年,从瘦皮猴的青年站到大腹便便的60岁,此公和我有数面之雅,我路过旅馆门前时和他握手,开几句玩笑。他早已退休。再往上追溯,午间以铁链关闭,阻止车辆进入,以便在里头开露天餐厅的“马丹”巷,如今遍布珠宝店、发廊和办公楼,上世纪初叶,却是鼎鼎有名的红灯区,每个星期发生一宗以上的凶杀案,起因要么是黑帮争地盘,要么是喝醉,要么是争风吃醋。
有把握对周遭说出许多“从前如何”,即所谓沧桑感,教人“心安”,也就是家的感觉。但有一样,是从前没有的,那就是正在紧张施工中的地铁。它从市场街沿市德顿街向北,通向唐人街,地下工程已接近完成,市德顿街一段,过去被往下掘好几十英尺以便开巨无霸掘进机建隧道和建车站,现在重新覆盖,铺上人工草坪,大人小孩躺着,坐着,听小乐队奏爵士乐。我走累了,在草地上曲肱而枕,试图躺出情调来,却差点把捉迷藏的孩子绊倒了。连忙爬起,继续在人潮的裹挟下走路,走路。
三
我在这一带游走,乃刻意为之,蹈袭的是“细雨骑驴出剑门”的古典招式,试图从“老金山”的身份倒逼,重新体味“新”,一如缆车站和广场石阶上眼神又好奇又迷茫的外地游客。我设想自己一个星期前才通过移民海关,还在等候绿卡,头一遭来此处,是谓“开洋荤”。
而新,即“未曾涉足”。这一带,我在上班的年代,虽走过数千乃至上万次,但并非每一处都登堂入室。今天专拣没进过的地方,为的是用洗手间。这次才注意到,联合广场居然没有公共厕所,以为街旁的白色平顶房是,门外却不见“三急”长龙,原来是旅游局的业务处。走过缆车叮叮当当地驶过的大街,进圣法兰大旅馆,在走廊浏览过百年以来的黑白照,却找不到男洗手间,女的则有两间。并不“内急”,所以没向大堂里坐镇的经理询问,20分钟以后走出。下一目标仍是旅馆,从“大使”的后门进去,行李员笑脸迎上,我问洗手间在哪里,他指了指过道尽头。自此,发现一个新花样——门推不开,用电子钥匙才能开。我抚头笑起来,“非顾客”借用洗手间,一直是闹市商家的头疼问题。行人密集,人家进来解决私人问题,拒绝显小家子气,也为自家的客人造成不方便;因此,许多店家在门口贴告示:“洗手间只供本店顾客使用”。然而开旅馆,怎能逐个检查进进出出的人呢?凭卡进洗手间,就阴险而体面地摆平难题。怪不得行李员对我笑得那么灿烂,他未始不含恶作剧的意图。最后,在一家小旅馆,坐了一阵,才尾随一带电子匙的顾客进了洗手间。
我自问,设若是光会好奇地张望的新乡里,能做到吗?答案自然是“不”。
真正使我实现心理“返新”的还是缆车。1992年,即在旧金山生活了12年的中年,我写了一首《夜过跑华街》的新诗:“跳下缆车/走向市场街/一个街区/十重关隘——”
四
暮色沉沉而降。我游走一圈后,回到缆车终点站。司机把缆车停进大转盘,跳下车,和售票员一起,用手推缆车转180度,换一个方向,摇了摇铃,开走了。一带顿时寂寥起来。宣教者的麦克风和黑人乐队的铜管都已停下,救世军募捐者的手摇铃还在响,但变成催归了。是啊,平安夜,一如中国人的除夕,任你身处何处,多么忙碌,都要回家。
风起了,纸片翻飞。寒冷从颈部侵入,我裹紧夹克。所谓天时之利,因“冷”为最。试想想,大街上要没有教人跺脚不迭的严寒,不晓得团圆的可贵的年轻人愿意赶回家吗?家里的窗子,要没有被大风不客气地猛敲,如何反衬出屋子里融融的暖意?是时候了,客厅或起居室那一株散发树脂香的或塑料做的圣诞树,树下横七竖八地堆着贴上受礼者名字的礼物盒,即将被受礼者逐一打开,随即,狂喜的孩子呼叫、蹦跳,亲人热烈地拥抱,互道感谢,配偶作深情的拥吻。一年难得使用一次的壁炉(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壁炉常常被禁用,违例者要吃告票),今天师出有名地烧旺,木柴噼啪作响,火花应和着开香槟酒的嘭嘭声。谁在唱歌:“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眠——”先是低沉的,柔如第一片雪花着地,然后,一个又一个加入,汇成洪流。我刚才所见的人海,幻化为歌的海。
我也回家了。两个外孙女的脸,被壁炉的火光映成灿烂的桃花,她们盼望了好久的圣诞老公公,要从烟囱里下来了。22年前的今夜,10时多,我下班,顺路送一位同事回家,他是年过半百的捷克移民。一路看不到行人,灯光璀璨而孤独,音乐隐约可闻。他凄然叹气,说起老家的圣诞节。我无所感,因为我和这个节日无缘。然而此刻,我终于获得虔诚基督徒一样的情怀,热烈地赞美:“啊,平安夜的平安!”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绘画:孙鸣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