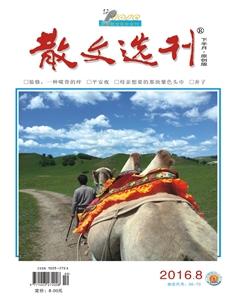缝纫机边的母亲
许晓青
我不知道老家那台缝纫机是不是比我年长,反正从我有记忆起,西窗下就有它。
闲时,缝纫机总是被一块藏蓝色土布从头到脚罩着,即使罩着布,姆妈也不允许我在缝纫机上放碗、茶杯,更不能写字、画画、做东西。等要派用场了,姆妈掀开罩布,解开绑在车头的布绳,揭去裹着的塑料膜,露出它零件复杂的机头,黑色的画着金色蝴蝶和鲜花的机膛,浅黄色的木台板,棕红色的铁架。机头最上面盖一块棕色呢布,呢布按照突起的零件的样子剪出窟窿,因为窟窿的大小、形状和零件严丝合缝,所以盖在上面不用担心被碰掉。姆妈说,买这台缝纫机用了二百多块钱,相当于她不吃不喝干一年的收入。
我们家的缝纫机,吃的是社办厂里领来的布料,下出来的是一只只手套。布料有粗棉布的和劳动布的。粗棉布虽厚却软,就是缝起来会有毛丝飞出来,在空气中载沉载浮,姿态优美却会让人鼻尖发痒。有时我在旁边看,两只闲着的手就在空中晃来晃去像赶蚊子似的赶毛丝。缝劳动布手套就没这个麻烦了,可是劳动布太结实,老会别断针,一包针要五分钱,所以姆妈还是喜欢领废花布料。领来的布料一捆一捆堆在家里,像农家的柴火,真让人担心我们家的“鸡”能不能吃完这些“口粮”。白天,姆妈要上班。总是在吃过晚饭后,爸爸把布展开来,折呀剪呀,裁成一块块小方块,再把一叠布按前次剩下的手套的轮廓线剪下来。这当儿,姆妈把缝纫机上上下下擦拭个遍,再用油葫芦给各处零件喂机油,把皮带上到上下两个轮子上,收紧。再调机针的松紧度,调得紧,针脚密,速度慢,废线;调得宽,针脚疏,速度快,省线,就是容易脱线,得调到一个合适的能通过验收的阀值上。等爸爸剪好一叠布料,缝纫机也已经像一匹吃饱喝足、养足精神、上好鞍子的马了。
“哒哒哒哒”——姆妈迅速从旁边的凳子捞起两片布料,对好正反面,两两重叠,送到车针下,扳下“鸭舌板”,踩动轮子,扶正布料,布料自己就往针下送。一眨眼,“鸭舌板”后面就生出一只手套。一会儿工夫,一只只连着的手套像一长串咬尾的鱼一样挂到缝纫机下。在一旁的爸爸就剪下这串手套。如果爸爸不在,到手套在地上堆成一座小山时,姆妈才会停下“哒哒”声,起身剪下这一长串手套,把它们挪到一边,又继续响起欢快的“哒哒”声。我和哥哥学习的时候,姆妈不允许我们管手套的事,而我们听惯了“哒哒”声,能安之若素地看书做作业。
“哒哒哒哒”——针尖起起落落像马在草原上撒欢。从手腕处起跑,一路绕过五指山,从手腕另一边退出,又跑进另一只手套的手腕处,开始翻越新的五指山……进去和出来之间“哒哒”声不会打一点疙瘩。
“哒哒哒哒”——“马蹄声”隔几幢屋都能听见。有时,“哒哒哒”的声音停下来,姆妈起来喝口茶,或者伸伸懒腰,用拳头捶打肩头或者抡着胳膊走几圈。那个时候我以为姆妈在缝纫机上踩几个钟头,和我坐在桌前看一会儿书,写一会儿字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以为姆妈比我们有耐心,所以能几个钟头坐在缝纫机前。
手套缝好了是要翻过来的,手腕处开口大,容易翻,到五个指头处就不容易翻过来了,得用棒头把缩在里面的指尖顶出来。有些夜晚,我一觉醒来,灯还亮着,爸爸和姆妈默默地翻着手套。
做好的手套用剪下来的废布条扎成一打一打的,又堆得像柴火堆。我们家的缝纫机,几天工夫就能吃完一个“柴火堆”,又生下一个“柴火堆”。爸爸把新生的“柴火堆”送到社办厂,回来的时候,就会有给我和哥哥的铅笔、橡皮和本子了,就会有交学费的钱了,就会有订杂志的钱了,就会有买荤菜给我们打牙祭的钱了。
做一只手套能赚1分钱,这个收入在当时大概是很高的。周围的农家很羡慕我家有缝纫机,他们家没有,所以他们的孩子每天放学后要割兔草、羊草。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家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姆妈工作了前半生的社办厂倒闭了,爸爸所在的供销社受个体经济的冲击,收入少得可怜,还常常几个月、半年不发工资,社办厂也停止了加工手套的业务,而我和哥哥又在镇里、城里读书,开销增加。姆妈白天在附近的单位和私人厂做临时工,晚上揽一些要用缝纫机的活:缝窗帘、蚊帐、鞋垫、工作服、简单的衣服。
姆妈没正经学过裁缝,做衣服全靠自己摸索,她先给家里人缝衣服。在她过去的同事圈里,流传着从上海传来的服装裁剪纸样,她把它们描在报纸上,再按尺寸、比例收放,然后把修改过的样子剪下来放在布上,再照着轮廓线剪布料,最后缝起来。用这种方法,姆妈缝出中山装、列宁装和时新的小翻领、方领、铜盘领等等式样的衣裳。看上去,也和专业裁缝做得差不多。
这个时候,缝纫机倒跑得不像原先缝手套时那样欢畅了。肩与袖笼长短不一致,领子开得太大了,没有粘衬衣服挺不起来……姆妈常常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嘀咕,缝了拆,拆了缝,裁好了的布料片在缝纫机上放上一星期、半个月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她忘了算上左右门襟要叠合部分的尺寸,就剪下了布料,重新裁吧,布料又不够。姆妈干脆在左、右门襟上又接了一道边,美其名曰“新款时装”。因为边接得平整,看上去倒也别有风味,像后来流行的夹克衫。
又有一次,“哒哒”声骤然变得沉闷,随之响起一声尖叫,车针踩到姆妈的手指上了!姆妈叫我抬起“鸭舌头”,可我怕针动起来会让姆妈更疼。姆妈骂了我,一咬牙,自己抬起“鸭舌头”,又抽出手指。我飞跑着去写字台的抽屉里找红药水瓶和棉花。姆妈按着手指,可血还是溢出来,滴到地上。姆妈说:“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那个时候,姆妈才四十几岁。
在“哒哒哒哒”的机声中,我和哥哥都念完了书,参加了工作。爸爸退休回城里老家时,那台缝纫机留在了爸爸的一个农民朋友家里,因为姆妈的身体已经再也不允许她踩缝纫机了。
不久,我的踩了大半辈子缝纫机的姆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夜半,我恍惚间看到姆妈伏在缝纫机上的背影:不抬头地看着针尖,两手的食指和中指拈住上下布料使它们对齐,又轻轻按住布片使针跑得不致太快而使针脚过疏。有时手指拈动布料使线脚转折或慢慢圆转。有时右手拿过镊子,夹住布料,使它在针旁几毫米的地方折成几层,针迅速踏上叠成几层的布,像马飞驰上小丘,又快速下来,一个皱裥就出现了。姆妈看也不看,伸出左手捞过布料,右手拨一下堆积在台面上的缝好了的布片……
那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的“哒哒哒哒”声,此刻又响在我耳边。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