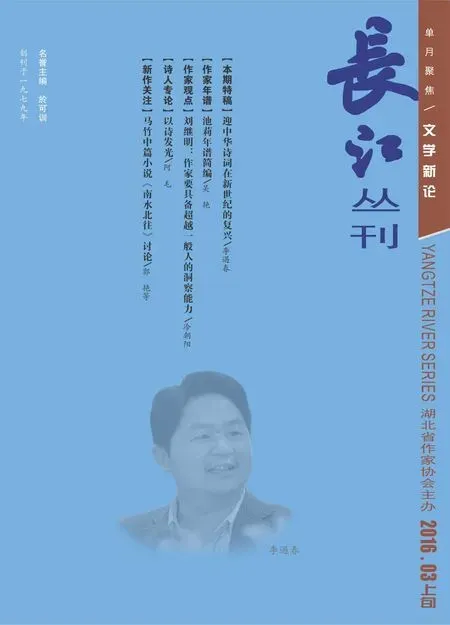“孤独症”及其疗法——阿毛诗歌的一种读法
■陈 亮
“孤独症”及其疗法——阿毛诗歌的一种读法
■陈亮
在一篇散文中,阿毛这样自陈:“诗歌实在是一门最孤独的艺术。”(《在文字中奔跑》)她有一首诗就叫《孤独症》。阿毛还有一首诗,名字叫《病因》。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来,《孤独症》与《病因》是两首恰恰可以构成互文的诗。《病因》的结尾写道:“为了被医治,我不间断地/发狂,写诗。”诗歌既是“孤独的艺术”,是“孤独症”,又具有“医治”功能。也就是说,在阿毛那里,诗是孤独症的症状,也是孤独症的疗法。
把诗形容为孤独的产物,这是老生常谈。同样,人们常常会说诗是爱的产物,是痛苦的产物。这没有错,却不值得多谈。孤独与诗,更像是一种普遍意义甚至是本质意义上的联系。把孤独与某个诗人的写作单独放在一起谈,似乎容易大而无当。然而,在阿毛的诗歌中,我们很难不去注意到孤独的存在。孤独是她写作的开始,是她写作的场景,也是她写作的对象。孤独是她诗歌展开的根基,也是她美学生长的根基。由此,孤独逐渐成为她写作的一个独特气质。从孤独出发,审视阿毛的诗歌,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一
孤独时,一个人会面对与自我的关系。
阿毛曾引用一句诗来说明自己写作的开始:“我们在某个人死去时开始写作。”(《在文字中奔跑》)她说,是父亲的死亡让她开始了写作。死亡是他人离开自己,把自己置于孤独的境地。死亡也是自己离开世界,把自己置于孤独的境地。死亡是人人逃离不了的命运,是人在时间轴上的终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就是一种在时间中的孤独。死亡不仅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也是等待实施的律令,是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提醒着人们,孤独是必然的命运。从死亡开始的写作,也就是从孤独开始的写作。
阿毛有一首散文诗《夏娃的自述:我是第一个》。其中反复说“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看到我自己的,第一个听到我自己的,闻到我自己的,品到我自己的,触到我自己的;作为第一个女人的夏娃,也是第一个碰到“他”(亚当)的。有意思的是,阿毛还有一首诗叫《我是这最末一个》:
我是这最末一个,留着黑发与披肩。
我是这最末一个,用笔写信,画眼泪。
并且看见一粒种子如何长成全新的爱。
我是这最末一个,像从没看见那样惊讶
和专注。
你和你的幻想一直忧伤。
我是这最末一个欣赏者,因为我是最初那一个
纵容蓝色的缎带飘成大海,纵容笔下的文字
预示你全部的成长。
既是“第一个”,也是“最末一个”,这其实就是说,“我”是那唯一一个(唯一一个,就是孤独)。在孤独中,人与自己相处。如果说在人群中人总是会关注别人的话,独处的时候则更多会关注自己,会去探寻自己,认识自己,会去问“我是谁”。在群体中,人更会体现出集体的类的属性,而在独处时,人通过认识自己的不同来认识自己的存在。“我”既是第一个认识“我”自己的人——在其他人之前真正理解自己,也是最末一个认识“我”自己的人——在其他人之后又一次审视自己。无论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都是对“我”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的确认。
阿毛有一首诗叫《一间自己的屋子》,其中写道:
一间自己的屋子,心灵的居所
和镜中的自己谈起
所有季节最美的事
窥镜自语,这是独处时典型的场景。在自己的屋子里,一次次地看见自己,一次次地听见自己,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第一次听见自己。这首诗显然是由伍尔夫的名篇、女性主义的经典文献《一间自己的屋子》而来的。在传统社会,女性并非没有自己的屋子。比如在中国古代,男人的屋子是书房,女人的屋子是闺房。但闺房并非是女性独立的屋子,而是在男性监管下的住所。闺房的主要作用是束缚,——关住女性,防止女性出嫁前与别的男人来往,——而并非给女人自由。当女性一旦出嫁,就连闺房也没有了。甚至于,闺房还是男性欲望窥探的对象。因此闺房只是“他者”的房间,而不是女性自己的房间。当女性要求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时,她要求的是一个可以掌控、自由活动的场域。作为女性诗人,当阿毛在这样“一间自己的屋子”,在一个人的孤独中观照自己的时候,她必然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既而为女性“寻根”,在女性的谱系中确认女性个体的存在。
这正是阿毛的诗中一再出现“夏娃”这个词汇的原因。
她,生来就不同于他。被叫做
夏娃或女娲,一开始
姓名中的偏旁就是性别。
没办法改变的不仅是
身上的那朵深渊。
……
因为,她从来就不是花瓶,
也不是插图,却成为
一首永远读不淡的诗。
一些顺流而下的句子,
这是阿毛的一首长诗《女人辞典》中的句子。这首诗既是一部“女人辞典”(共时意义上的),也是一部“女人史”(历时意义上的)。实际上这部辞典或这部史并不提供答案,整首诗只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女人从何而来?女人是谁?
被看一眼就流泪,
……
那根肋骨,和丢弃她的身体互称为爱人,
从创世纪到现在,和将来。
多么脆弱的爱人,通过性生活,
流汗,治愈感冒和孤独。
……
“妈妈,我不要婚姻。
橄榄花冠,也掩饰不住彼此的杀机。”
这首诗名为《夏娃》。很明显,“夏娃”是女性的代名词。这是一首决绝的诗。“随手卸下的肋骨”,代表了女性被抛弃和被忽视的命运。女性拒绝被赐予的爱和男性主导下的婚姻形式,因为“橄榄花冠,也掩饰不住彼此的杀机”。
阿毛写了不少女性主义色彩浓厚的诗。她并没有投身1980年代那拨女性主义诗歌的热潮。在我看来,这些诗也并非追赶潮流的产物,而是孤独中对自我的审视和体验的产物。女性主义往往体现为对男权话语的拒绝,这种拒斥,和女性主体的建立是一致的。确认自身和拒绝他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女性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表现出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的隔膜,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越将女性区别与于男性,女性的自我就越清晰。
而阿毛诗歌中在孤独中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也并非只表现为女性主义一面,还表现为一种不包含性别因素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自在的精神体验,有一种充盈的精神满足感。
诗正是诗人在午夜吐出的月亮,
……
正是诗人成为了西西弗斯,
成为了午夜的露珠聚成的湖泊,
成为黑暗的深处滚向黎明的石头
这首诗叫《午夜的诗人》。某个层面上,阿毛恰恰可以被称为“午夜的诗人”。午夜是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人最能检视自己内心的时间。“诗正是诗人在午夜吐出的月亮,”我们也可以想到,诗人吐出的月亮又把诗人照亮。诗还可以是诗人的镜子,她照出的面容就在其中。她照镜就是在写诗,她读自己的诗就像是在照镜。这是种“自我阅读”或者“阅读自我”,诗人有理由说:“我一直是自己的最佳读者”(《自我阅读》)。
在午夜(或许不是午夜)的精神漫游中,诗人感叹:
理想被日常生活羁绊
磁带上的歌曲被怀念倒放
我要穿过
雨天的瀑布幕墙和它的玻璃窗
经历各种各样危险的奇遇
到达群山之上、彩虹之上
这首诗叫《不及物》。所谓“不及物”,正是与外部的现实世界隔离,远离物,抵达内心深处。内心的丰富并不逊色于现实世界,诗人可以在精神的漫游中“到达群山之上、彩虹之上”。
午夜是尘世黑暗的时间。选择午夜,还意味着逃避尘世。前面说到,阿毛把自己的写作称为由死亡开始的写作。如果持一种浪漫的观点来看待死亡,死亡就是辞别喧嚣的尘世,抵达孤独而宁静的另一个世界。这不正是可以寂然凝虑、开始写作的场域么?因此在一首名为《墓志铭》的诗中,阿毛写道:
我不离开了
就在这树下长眠——
听风声、雨声、读书声
续写被人间折断
的半句诗
被人间折断的写作,在绝对的孤独中终于可以重新开始,续写完成。
二
孤独时,一个人会面对与语言的关系。
在《献诗》中,阿毛这样写道:
这首诗给夜半的私语,
给私语中不断出现的前世今生。
给所有秘密,无音区,
和手指无法弹奏的区域。
给眼泪,它晶莹剔透,
却仍是话语抵达不到的地方。
给灯下写字的人,
他半生的光阴都在纸上。
这首诗被置于诗集《变奏》的卷首。我认为这是阿毛很重要的一首诗。这首诗呈现出了阿毛诗歌的一个基本情景:夜半,灯下写字;呈现出了阿毛诗歌的发声姿态:私语,献诗。而且,这首诗在追问诗歌(语言)与生命的关系,诗歌(语言)对于生命的意义。“手指无法弹奏的区域”和“话语抵达不到的地方”,也就是现实世界的边沿。“光阴都在纸上”,纸上的光阴是时间之外的时间;“灯下写字的人”,写字即是构建新的世界。写诗就是在营造一个超越(不是脱离)现实空间的诗意空间,用尘世的杂草编织语言的花冠。让杂草成为花冠,这是由现实到语言的变形记。如前文所说的《孤独症》与《病因》的互文一样,阿毛有一首诗《题献》,可以与《献诗》相对应,其中写道:“倘若定要留下印笺,/就在用心写成的书上,//于卷首或卷尾的/空白处婆娑://你我虚度的一生,被文字纪念。”这是要用文字让“虚度”的一生充实起来,让一生在“纪念”中被赋形。
追问诗歌(语言)对于生命的意义,这在阿毛的诗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她1990年代初写的《敲碎岩石》中,有这样的句子:
语言的光穿过诗歌
诗歌穿过我们的内心
……
我们自己点燃自己
照耀自己
我们大彻大悟
诗歌的灯在高处闪烁
……
诗歌依然不会让我们
无所不能,但我们
仍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敲碎岩石,让它成为星星
敲碎自己,成为通往高处的路
诗歌不会让我们无所不能,却会引导我们走向高处。诗人诚然在现实中可能是无用的,却可以在语言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诗人是他语言世界的造物主和主宰者。
阿毛还有一首诗,诗题就叫《居住在文字里》。居住在文字里,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或者说,当人处在孤独中时,他与外部的世界有了一定距离,他读书写字,语言就可能是他的全部现实。孤独的人依赖语言,需要以语言来确立自身的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诗人想象和虚构的以文字建造的诗意空间,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处,他要用语言的莲瓣重塑一个肉身,——有别于尘世烟火塑造的肉身。如同阿毛在诗中所说:“我在纸上。”
在《肋骨》一诗中诗人说:“写作,放逐了原罪,解放了她自己,/而束缚了一些词。”由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首写女性的诗。在西方宗教的说法里,女性天然被视为“肋骨”,是男人的衍生品,又因为教唆男人吃智慧果而带有原罪。而写作,正是女性对现实命运反抗的一种方式。或者说,针对男权秩序女性可以进行语言反抗。藉由写作,女性放逐原罪,解放自己。“束缚了一些词”带有一定的反思意味,即在写作中,女性重新确立语言秩序,词语(作为对现实的指称)在女性话语里各归其位。
《鹅毛笔》一诗是对写作的隐喻。
写下的字,
不认眼睛,
不认横陈的肉体和世俗之气;
一如鸟认它洁净的巢,不认他人的金窝。
“看啦,它那么小,却飞得那么高。”
一如这些字,渺小却可以不朽。
鸟的巢洁净且高,这就是语言之家。鸟努力往上飞,要回到巢中,就仿佛诗歌要回到语言之家。诗人的笔就仿佛传说中的金手指,笔尖触碰纸张就如金手指触碰石头,努力让那些平庸的成为珍贵的和不朽的。
在《唱法》中,诗人则说要用手指加入万物的合唱,让纸上的文字成为黑色的钻石。
轻柔的晨光,和不轻易
看见的雨雾
隔着一阵风,两阵风,三阵风……
沐浴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
和树上数只婉转的尤物。
先是用目光,然后用手指,
我也加入这合唱。
它们唱的是:绿色的树上,结着金色的果子。
我唱的是:白色的纸上,长着黑色的钻石。
无论是用语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是让渺小的文字“不朽”,成为黑色的钻石,都体现出诗人所认为的语言对于现实的超越。正如她在散文《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的那样:“写作远远不是愉悦,而是如何超越。”诗歌是对现实的重新述说,这种述说不是重复,而是将生活诗意化,将生活纳入到语言的家园中。藉此,现实生活在语言中安顿。语言中的生活比现实中的生活更长久,这就像纸上的黑色钻石能够不朽。诗人要做的,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打造钻石,将其置于纸上。
值得注意的是,阿毛有许多以诗论诗的作品。这是诗人在孤独中与语言为伴,朝夕相处,对语言的体悟与认知。
比如这首《玻璃器皿》:
它的美是必须空着,
必须干净而脆弱。
……
你们用它盛空气或糖果,
我用它盛眼泪或火。
玻璃器皿是一件工艺品,也可以把这件美丽的玻璃器皿视作一首美丽的诗。这首诗既是在议论工艺品,也是在议论诗。诗的美也“必须空着”,“干净而脆弱”,如果诗是一件容器,它可以用来“盛眼泪或火”。这大概是阿毛眼中某一类完美的诗的形态。
诗用来“盛眼泪或火”,这在《终于》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终于劝住纸上滴水的针
终于……稳住针脚
终于用纸包住了火
终于……又一次被了结
终于拥有一副失声的歌喉
终于……成为石头
诗就是“包住了火”的纸,诗要有缜密的“针脚”,诗最终要歌唱出来,成为石头。
在《宽容》中诗人这样阐释诗歌中“词的暴力”。
所以我理解词的暴力,
也从不在句中杀死那些坚硬的词。
它们自有魅力把握语调与节奏,
像在风暴中行走,
这样的时光毕竟美妙而稀少。
我只需记下它,
不必说出,也不必拒绝它的流传。
所谓词的暴力,也就是说词不一定温文尔雅,可以更直白一些,更放肆一些。以暴力的词记录偏执的事物与激情,这也是一种美。
在《春天的禁忌》中,诗人说她“不写花”,“尤其不写那种太好看的花”。
我不写它,是担心,美一经笔尖流传,
就成为庸俗的时尚。我甚至不愿说出它的名字,
我是担心,过分的惊呼会毁灭美。
这是对那种一拥而上赞美春天、赞美花朵、赞美显而易见的美丽事物的诗歌的反拨。诗歌本来是要呈现美,让美如其所是地在文字中呈现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轻浮的写作中“过分的惊呼”会毁灭美。
《发展史》一诗则直接阐明了诗人对白话的坚持。
所以不研究自白派是口语,还是书语,
只坚持用白话写诗。
这是前途:
你不能认为路窄就不当它是路。
类似这样的论诗的诗,在当下是并不多见的。这除了体现出阿毛学哲学出身的思辨性的思维特征外,还体现了孤独地处在语言之中的诗人对语言的审视和甄选。诗人选择亲近某一类语言,疏远某一类语言,用某一类语言书写自己的存在。诗人自觉地用某些语言建构自己,让自己在纸上成为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三
孤独时,人也会面对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孤独并非是与外部世界的完全隔离。孤独的人只是没有热切地投入世界,没有加入到群体中去。他却依然可能观察着世界,张望着世界,对世界作出判断。实际上,有些人愈是悉心地体察世界,愈会感到孤独。
阿毛的诗歌并非全然是对自我和语言的诉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她写过许多直接与现实相关的诗。尤其是近些年来,她的诗歌呈现出“向外转”的趋向,由关注心灵转变为更多地关注世界。
在《病因》一诗中,诗人这样阐释自己“孤独症”的“病因”:
这些年,兄弟姐妹们
都到了城市,无人
去打理乡村,和破损的风筝。
……
我在没有乡音的
都市,空落落的心里总是疼,眼泪,成为身体的另一种形式。
这些和那些,
一并成了我的心病。
为了被医治,我不间断地
发狂,写诗。
在这里,孤独是因为无法被慰藉的乡愁,是因为传统的乡村被城市化碾压,不复从前的模样。孤独的病因不来自于心灵,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异化。诗人总想要寻找故乡,故乡却一天天变成异乡。所以阿毛会在另一首诗里感叹:“诗歌是难的!……返乡也是难的!”(《田园》)
除了写乡村生活的衰落,阿毛还写了许多城市生活的情景。在《不能不写到》这首诗中,她说不能不写到风,不能不写到花,不能不写到雪,不能不写到月,除此之外,也不能不写到“鼻尖上的黑痣”“断发、老脸和颤抖的双臂”“庸才的琐碎和长寿”,不能不写到“生活的细部”。她的那首曾引起广泛争议的作品《当哥哥有了外遇》,写了一场家庭变故;《爱情教育诗》写了大学中因爱情而发生的一场跳湖事件;《凌晨排队等专家号》写了在医院排队挂号的场景。《红尘三拍》从网络聊天写起,对随时代变迁而变化的人的关系发出喟叹。诗人由网络中的欲望男女想起古时的书生小姐。“我敲木鱼三声/提醒翻后园而入的书生:/一切的香胭脂粉,皆是红尘寂寞,哀怨人声。”木鱼三声比照聊天工具报告好友来到的敲门声,十分巧妙。她还集中写了数首关于节日的诗,如《不下雨的清明》《中秋节变奏诗》《2月14日情人节中国之怪状》《我们的平安夜》。清明、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和情人节、平安夜这些西方节日,本身承担着许多文化意义。而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中,节日的意义已悄然发生变化。这几首诗由中国人过节的世态百相,生动地描绘出这个时代的浮躁。不难看出,在阿毛的笔下,都市喧嚣繁华生活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落寞与孤独。“唯谈论这人间/让人如此疼痛。”(《疼痛》)
阿毛喜欢阳台。在《诗歌在阳台上》一文中,她说:“一间没有阳台的房子不能算是理想的居所。”
《孤独症》这首诗中有一个阳台上的场景:
歌曲哼完了,
频道搜遍了,
书页翻卷了,
床榻睡晕了,
衣衫倦怠,
头发一团糟……
嗨,很久没写惊人的句子。
你发来短信,
我在阳台上剪去多余的花枝,
向外抛。
《孤独症》描绘了一个人处在孤独中的状态。孤独并非隔绝,其中有两处写到了与外界的关联。一是“你发来短信”,二是“我在阳台上剪去多余的花枝,/往外抛。”短信能否安慰人的孤独,诗人没有明说。在阳台上剪去花枝往外抛,写出了一种深深的美丽的寂寞。往外抛花枝,似乎还在隐隐提示,诗中的主人公不仅安享独处的美丽,也在将这一份美丽传递给阳台下的世界,有和外面的世界发生关系的期待。
阳台在阿毛的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火车也是。
阿毛写过大量的与火车相关的诗。《火车站》一诗中她写道:
我喜欢写火车
其实是喜欢途中的摇晃
喜欢陌生的人群流动的风景
喜欢在此处又在彼处
喜欢是自己又是他者
我多么欣喜于
似乎接近却永不到达的远方
阿毛既渴望“一间自己的屋子”,在里面孤独、充实和自在的写作,与自我对话,又渴望不断地出发,一直在路上。如同她在《不断飘落的雪》中写到的:
我能从石头里
唤出一个灵魂来呼应它的纯洁
却无法阻止身体里
不断出发的火车……
对火车的热爱让她宣称:
在一列奔跑的火车上,
写出最好的作品。(《剪辑火车和水波》)
阳台是这样一个场所:它既在屋内,又连接着屋外的世界。你可以在阳台上观察屋外的世界,却不用走到其中去。屋外的人也不会注意到阳台上的人。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己的屋子里张望和窥探世界的地方。火车有与阳台类似的特点。人坐在车里,张望着窗外。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变幻,从眼前闪过。风景中的人也不了然火车里有这样一个张望的人。无论是阳台还是火车,都是把自我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在阳台和火车上,不用放弃自我,投入世界,又能看得见世界,可以冷静地观察世界。因此,在“午夜的诗人”之外,认识到阿毛也是一个“阳台上的诗人”“火车上的诗人”,会对她诗歌的发声姿态、审美倾向有更全面的理解。

《我的时光俪歌》
站在内心的位置去打量世界的时候,诗人的每一次打量都像是第一次看见世界,什么都是新鲜的和陌生的。这个时候,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荒诞性就展露了出来。
子宫一定是一个可爱的迷宫
所以,我们一出生
就爱上捉迷藏,就在寻找隐身术
可又怕不被找到
所以动一下厚窗帘,发一点小嘘声
被找得太久了就干脆蹦出来
吓人一跳——“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这里是哪里?

《个人史》
这首诗叫《这里是人间的哪里》。诗中的“我”本来是在捉迷藏,从隐藏自己的窗帘后跳出,却发现眼前的世界完全是陌生的,像是自己偶然被弃置在这里。这当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却可能是许多人都有过的经验:刹那间不知身在何处,觉得周遭的世界是没有来过的,与之格格不入。看似我们与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亲密无间,实际却有着隔膜。这种隔膜感时不时就会跳出来,让我们禁不住发问:这里是人间的哪里?
阿毛有一首诗叫《个人史》,其中说:“壮丽山河不值一提/波澜文字也不值得记取//你,如被吹拂/定是我体内群山漏出的风。”在另一首《流水账记录群像》中有这样的句子:“我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群体,/最后才是一代人的近处和远方。”纵观阿毛的诗歌,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人史”,同时,她的诗歌又是时代的群像记录。她记录时代的方式是记录个人,以个人史来书写时代志,就像她用个人史来书写女人史。“我”是个体,也是群体,还是“一代人的近处和远方”。由体验自我来体验世界,由观察世界来反观自我,这也是一种孤独中的经验。
在孤独中体验自我、体验语言、体验世界,这是阿毛诗歌的一条线索。如文首所说,诗歌是“孤独症”的症状。《孤独症》的末尾说“我在阳台上剪去多余的花枝,/向外抛”。这向外抛的花枝,未尝不可理解为诗歌。诗人在孤独中培育诗歌,将之抛向世间。
诗歌安慰了孤独,缓解了孤独,是孤独症的一种疗法。但孤独终究是一种不治之症,它是一种本质性的体验,总会在某个时间到来。所以诗人总会有“多余的花枝,向外抛”。这却是期待美的读者乐意看到的。
作者简介:(陈亮,青年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人民铁道报社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