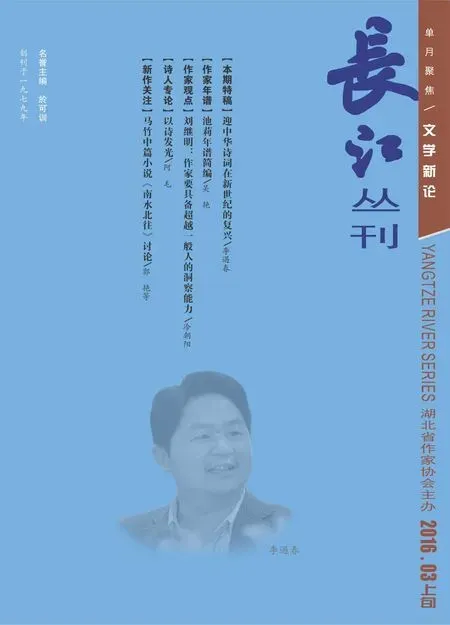“镜中叙述”——阿毛论
■张立群
“镜中叙述”——阿毛论
■张立群
有关诗人评论的写作,历来不外乎整体与局部两种写法,至于如何在其中抽取恰当的线索实现一次独具匠心的“文字构造”,最终总要取决于批评客体的特性进而展现评论主体的把握能力。面对诗人阿毛厚厚的诗稿,作为评论者或许都难免“心生敬畏”:其丰富的内容、艺术的多样以及历史的跨度,很容易使我们在整体描绘中“顾此失彼”——显然,阿毛并不是那种使用几个女性理论术语就可以涵盖的诗人,因而,通过“镜中叙述”为题展开的“阿毛论”,便是在尊重阿毛创作客观实际的前提下,期待介入其独特一面,进而深入阿毛的诗歌世界。
一、镜中的“故事”
正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写道:“由于强调了艺术观念在理智中的位置,艺术家们便习惯于认为艺术作品是一面旋转着的镜子,它反映了艺术家心灵的某些方面。偶尔这种强调甚至导致这样的看法,认为艺术是一种表现形式或交流的形式。”[1]翻开诗合集《旋转的镜面》,我惊讶于阿毛在1995年就有题名为《镜与灯》的作品——
你着了迷/镜中的这朵花/出自谁人之手?/这是上帝赋予我们唯一的通行证/是我们最珍视的宝贝/岁月将这张脸变得分明/将往事变得越来越模糊/烛光摇曳回忆刚刚开始/而镜是一片怀旧的巨光/令我通体透明
阿毛以问句的方式开头,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错觉”,“这朵花”究竟作何理解?是作为女性诗人的阿毛本人吗?而接下来上帝赋予的“唯一的通行证”和“最珍视的宝贝”,又使我们重新猜测“这朵花”也许是一个故事或是爱情本身。但在烛光摇曳的瞬间,我们又看到那怀旧的记忆,这使“镜与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间隔”,一切归根结底都来自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并在灯光下的镜中摇曳生姿。而诗作结尾处的“我们只能留下一点/烛光一样易于熄灭的精神/一如镜面上易于飘散的水汽”,蕴含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情绪,也确然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所谓“故事”的本身。
阅读阿毛那些有关“镜子”意象的诗,不难发现:“镜子”在其诗歌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并在“而立之年”带来怎样的精神感悟。“什么都走了,退到了镜子的背面/像亲人退到碑下,爱退避到心里/身体里没有水,像玻璃杯里没有空气/所有的生命都成为化石//三十岁的时候,我就梦见头发白了/是一点点的白,却不是象征/沧桑和资历的银白/镜子总是在诉说一点点的变化与疼痛”,在《镜中的生活》中,阿毛将沧桑的经历化作生命的“有形之物”和此刻的诗行,早生的“白发”以及容颜的“变化”,还有“忧郁的眼”和“镜前的词”,“一面镜子坦言无数的生活/那镜中的人一直是这样悲伤/故事曾和花朵一起开。但从未开出/一段舒心的童话//孤寂的人,用左手安慰右手/右手安慰心,心安慰眼睛/像丝绸安慰皮肤。但是任何安慰/也无法抚平岁月这张满是皱纹的脸”,这是属于阿毛的表达方式。她将自己的生活和心灵嵌入到“镜子”之中,并在镜面旋转的过程中折射出诗的存在方式。作为一直想“为镜子找一些完美的形象”(《午夜的诗人》)的诗人,阿毛如此在意如何通过一面“镜子”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许,在宁静的午夜,在朦胧的灯光下,“镜子”会赋予阿毛别样的感受:她可以向“镜子”诉说自己的一切,而“镜子”只是聆听,还有什么比这种表述方式更能呈现内心的世界呢?
无论忧伤,还是幸福,阿毛都通过镜面翻转出自己的心灵之作。如果诗人同样是一位艺术家,那么,“艺术家的世界不是事实的或法则的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他完全是由幻想组成的,而他感兴趣的世界是由梦想的东西构成的一个世界。”[2]或许更适合阿毛的镜中“故事”。这时,“镜子”已成为其传达诗歌的一道介质,它闪耀、透明、纯净,但无论怎样,“镜子”都始终对应着阿毛的精神世界,正如“精神的镜像正是其自身,心灵之镜事实上是‘镜子的镜子’”[3]。
二、自我的“影像”
在《由词跑向诗》中,阿毛曾写道:“诗歌是什么东西?/是妄想病人的呓语,/是自恋者的镜子”。诗人是如此地看待自己钟爱的创作,这种略带嘲讽的口气,或许会使我们对其诗在一定程度上打点折扣,然而,这是诗人式的夫子自道,而别人实际上很难完全理解其中的真意甚或焦虑。但无论怎样,“自恋者的镜子”都是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说法——阿毛在镜前的“自恋”,表明她的诗要写给自己。为此,我们不妨看看她在《热爱书中的女人》中的一段文字:“传说中的女人是一段段美丽的飘拂,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而书中的女人则是具体的文字。那文字是她们的躯体。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她们的灵魂。我们阅读的眼睛,通过这些文字,感知到她们丰腴的肌肤与真诚的歌声。因为这,她们真实又美丽。我们通过这种接触,恍恍惚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飘落在书中的文字里。事实上,那些与书为伴的女人,时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为书中的女人。她在阅读中与书里的女人相互重叠。喃喃自语或沉默不语地同那些通过文字说话、叹息的女人谈心。”[4]诗人是“自恋”的,也是高度自我的,为此,她最终选择“镜子”作为“影像”,进而投射到创作之上,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从物理学的角度可知,日常生活镜子中的影像属于虚像,它反映着主体的形象却无法成为灵魂的“聚焦”。不过,如果从“我就这样把梦变成了诗,却没法把诗变成生活。这是我作为诗人的一种安慰,也是我作为诗人的一种缺憾。这同时是大多数诗人的安慰与缺憾”[5]的角度,看待诗歌与生活的关系,阿毛无疑在两者之间找到了可以聚焦的“关节点”。作为一位具有丰富阅读知识、“热爱书中的女人”的女诗人,阿毛写作就其自身而言,或许期待的正是“一种更深的接触是融入。是女性通过创作,把自己的灵魂融入文字中。写作的女人成为书中的女人,然后给另一些阅读者去触摸去感叹。”[6]“黑夜”中用灵魂在镜前写作的阿毛,其实是需要读解的。正如她在《以前和现在》中写道“以前我走的路,都很平坦/以前我走的路,都在生活的外面……人们看我一脸痛苦/其实,我那时多么幸福”;“现在我走的路,都很坎坷/现在我走的路,都在生活的里面……人们看我一脸幸福/其实,我现在多么痛苦”。是的,年轮的增长会使一切都逐渐褪去光泽。在翻转镜面的过程中,“自我”同样也经历了“历史化”的过程。
“我在镜前看着身上的黑色披肩/它使我优雅、高贵/还有一丝现实的温暖/这些足以与幸福混为一谈”,在名为《雪在哪里不哭》的诗中,阿毛打扮后的形象曾获得了自我安慰,然而,这一切最终都离不开文字的形象化与物质化。“哦,写作!因为写作,所以我有理由不说话,我有理由一个人坐在没人看见的角落。你们看我很安静,其实我的脑子在文字中狂奔。”[7]阿毛通过文字、诗歌连结自我与镜像之间的关系,但显然,“镜像”可以在对应主体的过程中成为“他者”,而“他者”也同样可以解构主体。这样,在我们阅读其早期之作《洪水将至》中“我心疼这个夜晚/灵与肉的战争/硝烟四起/柔情的绝望因你而生/爱人/我手执铜镜/照耀你的每一次呼吸”,便不难看到:所谓“镜中”的另一道风景早已生成。
三、爱情的描摹
或许,很多人认识阿毛是通过那首颇有争议的诗《当哥哥有了外遇》。阿毛在诗的结尾曾以“我并不想当一个道德的裁判/只想当一个杀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事实上,细读阿毛的作品,这样的故事便显得不再陌生。在写于1997年的《外遇》中,阿毛曾有“我的镜子照见了一切”;“我心疼你,也和镜子一样缄默/抬头品味遭遇一次灾难的意义/而一面最后的镜子,还是/变幻的世界”。是因为切肤般的体验而痛苦不堪甚至嫉恶如仇吗?我想:阿毛诗作的此类情感最终都可以归结或者说只能归结到“爱情的描摹”之上。
许多场景在阿毛的笔下曾反复出现,这同样也体现了阿毛诗歌是旋转镜面的特质。“在行走的镜子前瞥见/一朵局促不安的花/对一个可怜的躯体/完成了匆忙的抚摸/在没有追上风之前/我们无法遇到一个结局/也无法回到一个起源”,同样在写于1997年的《风,它的身姿》中,阿毛至少重复了“镜子”、“花朵”两个意象。在“行走的镜子”前,阿毛是如此地注重“我们”之间的“过程性”,以至于将其置于钟爱的镜子前。显然,诗人是如此注重爱情的体验,这一点其实与其一贯认为的——在“爱”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好地沉醉。当然恰当的忧郁和痛苦是难免的。一个写作的人有必要让她的作品散发出令人沉醉的忧伤而又美丽的个体气息。”[8]——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感性契合。
爱情无疑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诗人会丧失灵感、容颜苍老。诗人阿毛当然知道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她曾写过《我们不能靠爱情活着》这样的作品。但镜中的描摹或许又与此有很大的不同,“获得玫瑰并不就是赢得了爱情/正如夏天并不意味心中温暖/我想说的生活,总在你们看不见的另一端”(《镜中的生活》)。阿毛的“镜中之爱”讲求诗意的深度,这使其诗歌在阅读过程中具有较为特殊的文字体验。也许,那些有关阅读、看电影甚至是其他创作的经历,决定了阿毛也常常将自己幻化为书中的人物——“作为一个阅读同时又是写作者的女人,更是无法停止热爱那些书中的女人的。”[9]
在散文《我们的灵魂就是爱》中,阿毛曾结合叶芝的名诗《当你老了》以及对其终身恋人毛特·岗的故事,谈及自己的爱情认识以及诗中的爱情,“二十岁以前的我因为年轻对人事对爱情没有深刻的认识,常常会在多愁的黄昏梦想拥有这样一份诗人的爱情。当然,我的这份幻想是难以成真的。我的周围没有这样的诗人,当然也就没有这样一份诗人的爱情。倒是我自己常常在诗歌里倾诉这种爱。于是那在想象中飘扬而在现实中却从未出现的爱人一次又一次地走入我的诗中,成了我诗中的爱人与灵魂,与我的梦相亲相爱。”[10]阿毛是向往爱情也是懂得如何在诗中表现爱情的,这或许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心灵镜像”。同样地,正因为懂得,阿毛才会写出镜中爱情的“深度”——

《旋转的镜面》
这当然不是速度的问题/雨已经很小了/远处青苔暗哑/而爱人歌声嘹亮//
我在听,但不是听/过道上的水滴/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点点点点/成线,成针/成不容置疑的镜面//
这当然不是雨滴落下的速度/是想你的深度/和针扎入肉体的疼痛
——《深度》
以雨滴落下的方式,写出“想你的深度”和深入身体的“疼痛”,这当然不是速度的问题,而是持续的力度。“爱人歌声嘹亮”,是一道布景,被水滴照映,但却可以一样深入爱人的灵魂。上述内容使爱情成为一种过程的考量,而在镜中描摹的过程中,又一个主题势必呈现于阿毛的创作之中。
四、时间、记忆及其他
将时间作为诗歌重要素材之一,对于女诗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结合文学演变的历史,“挑战时间”至少构成了现代甚或后现代创作的重要标志。所幸的是,阿毛对于时间的专注在于一种过程的体验与记录,在于文字物化时时间的流逝。“此刻的我在写作中。文字在我的右手中不断流在洁白的纸上。时间却在我的左手腕上流失,并不为我停留片刻。它绝对无视内心的声音。但我们仍然努力在时间的波浪中跳跃出好看的花朵与姿势。”[11]在短诗《时间》中——
我们曾经多么幸福啊!文字/用它的魔力虚构了我们的生活/还有那个女人的美丽,在诗里
与其另一段诗行——
不能说话,只能默默地写字/在许许多多的形容词后面/时间悄悄收回它的馈赠
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时间”与“文字”、“爱情”、“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毫无疑问,时间会“收回我的心和温丽的容颜/在一首诗里,一句话里,/甚至一个词里”,但时间无法收回它缔造或曰生成的文字与形式,这一点,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或许尤为重要。
在《记忆的形式》中,阿毛不无深情地写道:“一直以来,记忆,和想象一样,是一切艺术最重要的源泉和组成部分。人类一直过着有记忆的生活,就如同我们一直过着有想象的生活一样。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记忆的生活是没有的。记忆一直以我们所见或未见到形式活着。像鲜花开在空气和阳光下,开在爱人的花瓶中,也开在看不见的尘埃里。我们拥有记忆,就如同我们拥有生命”[12]。谈及记忆,无疑是对应着过去和时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是我们的生命中最温柔的抒情部分”,既是诗人创作的源泉,同时,也是诗人重温已逝时间的载体。“琐事淹没了我的一生/我能送给你的唯一奢侈品/就是回忆/这些往事,这些花瓣/我用忧伤的手指一层层剥开它们”,在《镜子的眼睛》中,阿毛将“镜子的眼睛”作为潜在的视角,而镜中的记忆是如此的唯美、纯情,以至于在阅读、感悟中让人怦然心动。将这些描述结合以上关于“记忆”的部分,我们仿佛看到了阿毛沉浸于过去“景深”时陶醉的神情。
除时间、回忆之外,阿毛诗歌中偏爱的词还有“睡眠”——“睡眠是我在诗歌中爱用的一个词。它在诗歌中最有力部分的频繁出现增添了我诗歌中叹息与赞美的休憩部分的弹性与魅力。它不仅具有温柔、迷茫、沉入、香醉的质地,更是诗歌中最尖锐的伤口与消魂激情的均衡器。它们因为睡眠在其中特有含义的出现,而保持了最适当的节奏与最自然的呼吸”[13],阿毛关于“创作中的睡眠”的说法,不由得让人想起《镜子的眼睛》中如下的诗行——
在一面神奇的镜子前与你相逢
我回忆的不再是一个纸人
在风中行走,告诉你
这个被回忆的睡眠浸泡的人
在风中爱上了一个人的声音
或许,阿毛的爱情、记忆在时间的河流中都属于过去时的,而除了阿毛本人,没有人能从镜中看到这样的风景,进而以诗的方式,缓释内心的焦虑。
至此,在阿毛的“镜中”,我们至少看到了如上几种叙述。结合近年来阿毛的创作,比如:那些关于“春天”意象的诗,我们大致可以感受阿毛的世界正向更为广阔的空间敞开。然而,“在场”是“忧伤”的——“我坐着不动,像个思想者/只是我不再思想,我只是忧伤”(《在场的忧伤》)。阿毛诗质的渐次透明取决其心灵之镜的变动状态,但“镜面”是“旋转”的,这就结果而言,使阿毛的诗具有更多的折射与抵达空间。至于本文在侧重阿毛诗歌“镜中叙述”基础上,探寻阿毛诗歌世界的空间与意义也正在于此!
注释:
[1][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页。
[2][3][英]R.G.柯林武德:《精神镜像或知识地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2、4页。
[4][6][9]阿毛:《热爱书中的女人》,阿毛:《旋转的镜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99页。
[5][10]阿毛:《我们的灵魂就是爱》,阿毛:《旋转的镜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109、108—109页。
[7]阿毛:《跋:在文字中奔跑》,阿毛:《旋转的镜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278页。
[8][11][13]阿毛:《语言的时间》,阿毛:《旋转的镜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172、162、168页。
[12]阿毛:《记忆的形式》,阿毛:《旋转的镜面》,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年版,134页。
作者简介:(张立群,辽宁沈阳人,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