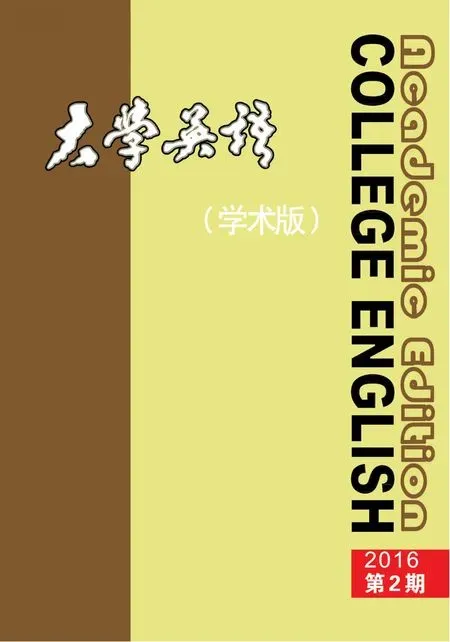失真的英雄主义
——再论“拜伦式英雄”
陈晓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失真的英雄主义
——再论“拜伦式英雄”
陈晓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作为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拜伦的诗歌气势磅礴,包罗万象,抒情与讽刺运用自如。他四处游历的经历和传奇般的人生故事更使他声名远播。他笔下那些热情洋溢,追求自由的男主人公们仿佛是他自己的缩影,常常与这些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同时出现的还有众多女性形象,然而拜伦透过男性视角主观地将这些女性刻画为男性审美理想的载体。女性压抑的自我和话语权、作为男性的无私奉献者,与“拜伦式英雄”所呈现的个人主义、追求正义、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本文将通过女性批评的角度对比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和拜伦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希望能更深刻地理解“拜伦式英雄”的创作动机以及还原其背后真实的女性形象。
拜伦式英雄;女性主义;女性形象
引言
拜伦生于贵族家庭,但是他的童年生活却并不幸福。拜伦的父亲为了母亲的财富而与其结婚,待钱财挥霍一空后便抛弃了她,致使拜伦的母亲精神压抑,性格暴躁,年幼的拜伦便成为这一恶行的受害者。另外,天生的残疾使他的性情更加孤僻,渴望母爱的同时对女性也萌生了一定的负面情绪。十七岁时,拜伦前往剑桥求学,随后游历了欧洲多个国家,最终死于希腊的独立战争中。短暂的一生中,拜伦像一个英雄一样为了自由、独立和平等而战斗,从他的诗歌中可见一斑,那些激昂的文字,或惊心动魄,或鞭辟入里,都富有极其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长诗中的男主人公是热情且意志坚定,勇敢而又孤独的反抗者,如《东方故事诗》(1813-1815)、《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09-1817)以及讽刺史诗《堂璜》(1818-1823)等。与之相反的是,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或软弱无能,或被赋予了奴性,一些角色虽不乏个性,但仍然是父权社会下男性的附庸。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因为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阅读模式,使我们能够从又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文本,还为我们提供了哲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本文采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观,从生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差别出发,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审美感受理解和分析拜伦的诗歌作品,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拜伦式英雄”以及其背后的女性们原本的形象。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拜伦的诗歌作品以及“拜伦式英雄”的发展过程;其次分别对典型的拜伦式英雄的特征和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总结归纳两种形象特点与可能的起源。
1.拜伦的诗歌特色与“拜伦式英雄”
拜伦的父亲在与拜伦的母亲凯瑟林·戈登结婚前曾有过一次婚姻,且育有一女,即拜伦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拜伦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将妻子的财产挥霍一空后逃往国外,最终死于异乡。十岁时,拜伦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和庄园,但郁郁寡欢的童年,父母的婚变和自身的残疾在拜伦的心中种下了一颗阴郁的种子。幸而拜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3岁时在哈罗中学读书,1805年在剑桥大学求学。他的第一本诗集《懒散的时刻》,出版于1807年,但并未受到好评。性情敏感冲动的拜伦以一首讽刺诗作为回击。可见拜伦的自尊心极强,又有郁郁不得志的反抗和叛逆精神,以及讽刺诗人的胆识和才能。随后拜伦周游欧洲多国,如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拓宽了眼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和背景。拜伦还曾游览过一些东部国家,这一经历还为他的诗歌增添了些许异域风情。但从整体而言,他的作品多以讽刺和抒情为主。他所处的社会并没有给他足够的包容和温情,而是用有色眼光看待和指摘他的所作所为,因此不难理解他的诗中常出现的讽刺性诗句和抒发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心声。
拜伦不仅被称作杰出的诗人,也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不停地投入到反抗的队伍中,为英国的“卢德运动”中破坏机器的工人和他们受到的严酷镇压而辩护;反对英国政府对爱尔兰人民的控制和压迫;作为反对“神圣同盟”的领导,抵抗欧洲的封建统治,支持各国的革命和独立运动;参与意大利的独立解放组织“烧炭党”反抗奥地利统治;后又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贡献了自己全部的财产和年轻的生命。他的诗剧《该隐》中反抗上帝的该隐和路西弗、《曼福雷德》中既不祈求上帝也不像魔鬼屈服的曼弗雷德、长诗《青铜时代》的主题中,都清晰地体现了拜伦的立场:反对压迫和奴役,追求正义和自由。他所推崇的英雄主义还包含理想化的、审美的以及人道主义的因素,拜伦也正是以他这种理想的审美的英雄观来抨击和对抗英国乃至欧洲的贵族专制制度和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这一理念反映到其诗歌创作,便形成了具有独特反叛性格的一系列“拜伦式英雄”。“拜伦式英雄”是革命者,是勇于打破旧秩序的斗士,也是彷徨忧郁的自我主义者。然而,一个个体并不能独立存在于社会中,这些英雄式人物在与社会现实作斗争的同时,自己也身处于现实的复杂人际中。拜伦在诗中对具有美丽外表和品德的女性不吝赞美和柔情,而不符合此类审美标准的女性多屈从于男性的统治,处于拜伦式英雄原本致力于反对和抵抗的那种地位。
2.典型的“拜伦式英雄”与女性形象
2.1 英雄形象特征
2.1.1 浪漫英雄—爱与理性的化身
最早的拜伦式英雄的雏形出现在《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中,长诗的主人公年轻的贵族哈罗德对上流社会的虚伪浮华感到厌弃,于是坚决地离开了英国前往国外旅行。航船离开英国的海岸不久,哈罗德唱了一首歌曲《去国行》来抒发离家的心情。“别了,别了!故国的海岸……海上的红日径自西斜,我的船扬帆直追;向太阳、向你暂时告别,我的故乡呵,再会!” “船儿呵,全靠你,疾驶如飞,横跨那涛涛海浪;任凭你送我到天南地北,只莫回我的故乡。”(拜伦 2011)两段诗中主人公对故乡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哈罗德潇洒离去但又热爱故土,想要“暂别”,但又命令船儿“莫回”,这种犹豫的心情正如一个满怀抱负而无法施展的游子。哈罗德的对家乡的大海、土地都满怀爱恋,但前方未知的未来也让他充满期许,因此他勇敢地踏上征程,颇有骑士的风范。拥有独立思想的哈罗德反对暴政、渴望自由,没有随波逐流,但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与忧郁。哈罗德之所以怀有如此深刻的“厌世的忧郁”,反映了工业命革后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激烈变化,原有的秩序、道德、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均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曼弗雷德》的中的英雄形象曼弗雷德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古老城堡中,性格阴郁的曼弗雷德与继妹安斯塔蒂相恋后又十分懊悔,于是杀了自己的妹妹。极度痛苦的曼弗雷德向安斯蒂塔的灵魂祈求宽恕,但始终无法得到内心的平静。他既不屈服于神明,也不相信邪恶的力量,他的心才是自己的恶与痛苦的根源。这些浪漫的英雄对自然和生活充满热情,也有一颗萌生爱情的心,碍于社会道德的限制,他们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2.1.2 正义英雄—反抗压迫的革命斗士
在剑桥大学学习时期,拜伦受到法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无时无刻不在追求自由,为自由而抗争。欧洲此起彼伏的革命和解放战争激发了拜伦的创作。拜伦通过“拜伦式英雄”的形象把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个人主义思潮推向了新阶段。那些孤独的奋斗者们在维护人格独立与尊严的抗争中丰富了“自我”的内涵,张扬了个性,同时也证明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展现出个人对于社会的神圣性。诗人对自由的追求大多以反叛的姿态表现。罗素认为撒旦主义是拜伦遗产的一部分。撒旦在西方宗教和文学史上常作为上帝的对立面出现,它的精神内核就是反叛,反叛上帝、传统、权威和宗教。比如诗剧《该隐》,大胆地将上帝刻画成邪恶的暴君,该隐则是有骨气的反叛者。和湖畔派诗人不同,拜伦没有躲避到大自然中去寻求内心的宁静,他认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会改变我对肆虐暴政的口诛笔伐和愤慨之情”。堂璜就是另一典型的勇猛强壮、无所畏惧的正义英雄形象。拜伦曾指出,他的长诗《堂璜》是对于当下社会现状中的恶行的讽刺,他在诗中写道:“如果可能,我要教石头反抗世上的暴君。”堂璜这一角色最早源于西班牙,一位放荡的花花公子杀人后最终被正法的故事,在拜伦笔下,堂璜是奴隶市场上身为囚徒却依然昂首挺胸的不屈者,是苏丹王宫中不惧女王淫威,面对兰勃洛的专横残暴,挺身而出激战的战士,虽然身处危境几次险丧生命,他仍竭力与环境和社会抗争,不愿做一个被动的任人摆布的角色。坚强不屈的灵魂或常遭迫害和排挤,拜伦选择了反抗,即使代价是付出生命。
2.2 英雄背后的女性形象
西方女性主义作家Sandra M. Gilbert和Susan Gubar的著作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中,研究了19世纪前西方男性文学中常出现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在男性文学作品中,“把女性神话为天使的做法实际上一边将男性的审美理想完全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剥夺了女性形象的鲜活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审美理想的牺牲品”(Gilbert & Gubar 1997),还有一类出现在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妖女或魔女,这些形象体现了男性对不肯服从的女性的厌恶和恐惧。拜伦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实际上都是用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对女性的厌弃和贬抑,以下是对其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概括,分为三类:
2.2.1 软弱无能的奴仆
中国的封建社会主张男尊女卑思想,拜伦当时所处的西方社会也不例外。圣经中,女性来自男性的一根肋骨,是属于男性且依靠男性而得以存在的。在拜伦的作品中,男主人公在爱情中的地位常常高于女性,女性似乎成了爱情的“奴隶”。比如拜伦描绘了多次堂璜与情人之间的分离,堂璜总能全身而退,可是对于女性来说,后果总是毁灭性的。她们承担了爱情中的负担和罪责,却仍旧心甘情愿,像是完全被爱情俘虏的飞蛾一般,乐于为她们的男性统治者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拜伦在《十四行诗:咏锡雍》中,赋予男性形象以“不可征服的灵魂之永恒精神”(Eternal Spirit of the Chainless Mind),在另一首名为《我给你的项链》(The Chain I Gave)中拜伦笔下的无名的情人或妻子则有一颗“欺诈的心灵”。“它们(项链-Chain)的责任尽到了,——可惜,没能教会你尽你的责任”(拜伦 2011:58),男性英雄形象注定要做一个自由的灵魂,而其背后的女性应当戴好自己的锁链,男性的Chainless mind和要求女性带上的Chain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旦“家中的天使”没能达到男性的期待,即谦卑、柔弱又驯顺,随时准备为男性而献身,便会跌入妖妇的行列。软弱无能仿佛成为了女性的标签:拜伦用“小姐办事情不靠侍女可不成”形容海蒂,“这黑眼的奴隶”描绘英勇的葛娜拉,然而她们的所作所为却证明了她们并不是没有头脑,时刻依靠他人的弱者。拜伦希望女人能够满足男性的欲望,但又惧怕女人有独到的思想意识,超出他们的掌控能力,于是过度地贬低和批判女性;同时,诗人有赞赏和渴望真爱,向往忠诚,女性可以无私地牺牲一切,因此诗人对女人的矛盾心理下的女性形象并不够真实。
2.2.2 红颜祸水
拜伦在诗中经常对妇女的美丽容貌和姿态表达赞美,人们耳熟能详的《她走来,风姿优美》、《雅典的女郎》、或是《堂璜》中的海蒂、抑或是《海盗》中的葛娜拉,美不胜收。令人奇怪的是她们的爱情却像潘多拉的魔盒一般带来不幸或灾祸。堂璜在船只失事后漂流到海岸边,被美丽的希腊少女海蒂救助,相爱后结为夫妇。少女的父亲归来,反对他们的结合,并将堂璜关押运送出海“此时此刻,做梦也想不到祸患,突如其来,被捉到海上远行,受了伤,还不让动弹,连栓带捆,都只为爱河起浪,少女怀春……” 失去爱人的海蒂坚决地与父亲对抗,“她付出生命,抵偿她轻率的过错,谁犯着过错,都得把孽债偿还”(拜伦 2011:297)。拜伦对海蒂的态度很明显,认为海蒂的爱情如同潘多拉的好奇心,是错误和悲剧的源头,害得堂璜受伤离去,最后自己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作者似乎意在告诫人们,女性必须严格控制自己的情感,才能对男性世界不构成任何威胁,维持社会的安定平和(阚鸿鹰、李福祥 2006)。可是这真的是海蒂的过错吗?她拯救了堂璜的性命,在父亲面前勇敢地保护他,不屈不挠,为了爱情矢志不渝,本应是以英雄的形象呈现出来而不是别人的灾难的替罪羊。如果说非要为这些灾祸寻找来源的话,海蒂的父亲可以算作一个源头。他本身是海上的劫掠者,抢劫钱财,伤人性命,见到堂璜后的第一反应便是暴怒,不了解任何实情的情况下大打出手,反对女儿的婚姻,最后造成了两败俱伤的结局,实则是父权制社会下对女性歪曲和压抑产生的悲剧。再如《海盗》的女主人公葛娜拉这一形象,在熙德王爷眼里她不止是宠妃,更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葛娜拉后来倾心于救过她性命的康拉德,为了拯救恩人康拉德不惜冒险杀了熙德王爷,为两人的未来做准备。掌握了主动权的葛娜拉却被康拉德称作“杀人的凶手”,受到冷言冷语的嘲讽,最终迫使葛娜拉恢复了屈服于男性统治的地位,而此时康拉德才“原谅”了她,终于葛娜拉沦陷在他的绝对男权至上的伦理中(白英丽 2008)。这一段描写清晰地表现了男性统治社会中对女性的期待,女性话语权被压抑,在社会中属于从属地位,僭越了本来的身份地位便是不符合天使般女性形象的恶行。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我更是无法被接受的,是潜在的危险信号。拜伦式英雄追求人格独立、自由的思想,对女性的态度却是意图强加一只锁链来将其束缚。
2.2.3 虚情假意的荡妇
与英雄式的忠诚和坚毅的品格不同,女性是因其虚伪、轻浮和善变而被厌弃的存在。拜伦对女性的轻视和戒备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谁会相信妻子或情妇,虚情假意的伤感?两眼方才还滂沱如注,又嫣然笑对新欢。我不为眼前的危难而忧伤,也不为旧情悲伤;伤心的倒是:世上没一样,值得我珠泪轻抛”(拜伦 1993)。《堂璜》中与年轻的堂璜发生秘密恋爱关系的贵妇茱莉亚,宣称自己和堂璜之间是柏拉图式的爱情,但实际沉浸在对性欲的追求中;明知这种行为是被宗教和社会所不齿的,却仍欺骗丈夫掩盖自己的罪行。拜伦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的嘲讽从他的讽刺笔调中流露了出来。类似的还有虚伪的艾德琳夫人,表面上看起来和丈夫是恩爱的一对,但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温暖热情的外表下是冷若冰霜的心。她们都是男性文学作品中的妖妇或恶女形象,体现了男性对不肯服从的女性的厌恶和恐惧。而这些“荡妇”形象的背景多为上流社会,一场不幸的婚姻以及严酷的社会道德的禁锢。她们拥有自己的欲望,面对不幸的婚姻没有选择继续压抑自己,因而成就了与拜伦式英雄对立的反面形象。在传统的话语中,是没有女性声音的。虽然诗中出现了女性的独白,但很可能是为了迎合男权话语而创造的,因为诗人刻意回避了男性寻欢作乐的责任,贬低了女性的人性本能和欲望。女性在社会中的失语,正如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少女翡绿眉拉,被国王铁卢强暴后割掉了舌头,化身为燕子泣诉,表明了女性在西方历史中的话语权缺失。在传统的男性文学对女性的刻画中,女性不是天使便是妖妇,女性的存在和思想历来鲜有理论和术语来描述,传统的理论话语更是浸透着对女性的歪曲,因为她们既无名又无言(黄苹 2007),因此波伏娃才有那句名言:“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即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的主观话语中被塑造出的失真形象。
3.两种形象反差溯源
诗人对于软弱无能,依附于男性的行为感到十分厌恶,也对狡诈虚伪的女性嗤之以鼻,这些“厌女情节”很大程度上和个人经历有关。从拜伦本人身上可以发现拜伦式英雄的影子,而这些反面的女性形象或许也可以看作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影射。拜伦其父抛弃其母后,浪迹于欧洲大陆,而拜伦游历欧洲以及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人公漫游各国等场景,似乎是对其父亲行为的追随和效仿。在一个父权社会中,即使父亲的身份缺失,仍旧在拜伦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母亲的精神不正常,苛责和惩罚,或许使他对父亲的错误做法产生了一定的赞同,导致了拜伦式英雄不仅是忧郁勇敢的战士,也是内心包含撒旦式反叛心理的矛盾英雄。
拜伦和女性的关系也一直不顺遂,童年时期母亲的暴躁,少年时期对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的痛苦的不伦爱恋,到成年后妻子的无理和不解,以及众多风流韵事,使他难以体会到女性的关怀和爱。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一个请求,就是在给我的任何信中都不要再提到女人,即使是对这种性别的存在的一种暗示也不要有,我甚至不愿再谈到一个女性的词……”(张建理、施晓伟 1991)。再加上当时社会中女性地位低下,男权思想是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由此诗人常常在作品中夸张和扭曲女性的形象,从而衬托出拜伦式英雄的高大和正义。
4.结束语
拜伦传奇般的经历使他得以洞察妇女的苦难,对女性受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性的歧视有一定理解和同情,但母爱的缺失以及多次感情上的失意,令渴望得到女性精神慰籍的拜伦对女性抱有很深的偏见,失望中的拜伦将愤慨和不满倾注于笔端,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嘲讽和贬低时常出现。可见,拜伦在本质上仍然是父权意识形态的继承者,拜伦式英雄这一典型的文学形象是拜伦所处的时代以及拜伦个人生活经历的产物。两种形象相比较后,可以看出英雄背后的女性并非妖妇或悍妇的形象,有的女性甚至还有一些英雄气质。拜伦的个人经历致使其将女性形象扭曲,经过男性视角加工改变后以文学形象呈现出来,或许这样更能够衬托出男性英雄形象的高大伟岸,但从女性的角度看,这一描述有些矛盾,欠缺了真实性。
Gilbert, S.M.& S. Gubar.1997.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拜伦.1993.唐磺[M].查良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拜伦.2011.拜伦诗选[M].杨豫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白英丽.2008.拜伦的英雄伦理观透析[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
阚鸿鹰、李福祥.2006.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
黄苹.2007. 女性主义文学观的美学解读[MA].曲阜师范大学.
张建理、施晓伟.1991.拜伦,地狱的布道者—拜伦书信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