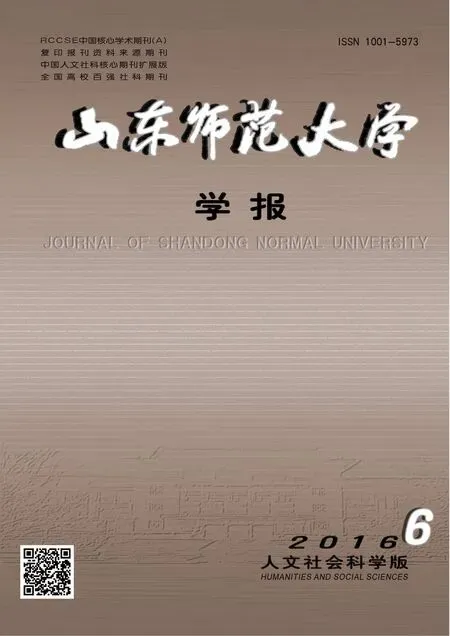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之流脉*①
辜也平
(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
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之流脉*①
辜也平
(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中,除梁启超、胡适、朱东润等人的有关理论主张受到足够重视外,还有朱湘、许寿裳、郑天挺、孙毓棠、戴镏龄、沈嵩华等一大批人的理论探讨未得到应有关注。正是这几代学人从不同侧面进行的思考与探讨,才汇聚成从作家到学者,从零星到系统,从历史到文学,从比较东西方传记差异到提倡传记文学,从探讨创作手法思考到理论的建构之流脉。而由“新史学”出发一路走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虽未出现热烈繁荣的局面,未出现震撼文坛学界的宏篇巨著,但他们的努力所彰显的探索精神,由相互碰撞所形成的思维成果,都已经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记文学理论积淀,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系统梳理这一发展脉络,总结其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思维成果,无疑对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
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理论建构;发展流脉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02
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的过往视界中,关于传记写作,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著名作家学者的有关理论主张受到充分的关注,但除此之外其他人的理论探讨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实际上,创作的转型发端于观念的变革,而写作的实践也促进、启迪和丰富理论的建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上述著名作家外,其他学者对现代传记文学理论也从不同侧面进行过比较深入的探讨。因此,系统梳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理论建构的发展脉络,总结那一时期关于传记文学理论的思维成果,对于传记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
一、史前的资源与域外的视角
一种观念的提出,或一种理论的建构往往都和固有的相关积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有的积淀或影响新的理论观念的生成,成为新的建构的基石,或成为对应、甚至对立的一方,启迪和促进新的理论观念的萌生。因此,考察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就有必要系统考察这一建构所对应、所参照或所依据的传统理论资源。
从表面上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生成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传记文学理论观念的启迪,但从更深处考察其史前资源,中国古代相关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典籍中,很早就有有关“传”或“传记”一词的记载或解释,当然最初的含义与现代传记的观念略有不同:
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无所不究。*②《汉书·刘歆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7页。
丘明……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③《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这里的“传”或“传记”,承担的是对于“经”的阐释功能,接近《尔雅注疏》释为“传也,博识经意,传示后人也”。*《十三经注疏·尔雅》。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刘勰则进一步辨析:
发口为言,属笔曰翰,常道曰经,述经曰传。*《文心雕龙·总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655页。
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文心雕龙·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26页。
正因为承担“释经”、“训释”的功能,所以刘勰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文心雕龙·史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84页。
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传”虽然仍属意于“解经”“释纪”,但已有“列事”、“录人臣之行状”*《史通·内篇·列传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2页。之解释。至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则专列《传记》一篇,并辨析道:“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於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文史通义·传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48页。至此,“传记”之含义与现代传记文学之“传记”已几无差别矣。
现代梁启超、胡适、朱东润等均文史兼治,故取法《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典籍,或以它们为新传记、传记文学提倡之参照也在必然之中。梁启超在谈及中国古代史学之发展时就专门谈到:“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4、25页。五四之后,一般的作家、批评家都不愿意轻言与传统的关系,作为曾经喜欢标新立异的思想者,作为站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的文化巨人,梁启超的描述客观地揭示了无可避讳的承传事实,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表明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精神。
胡适非常推崇章学诚的“学问与见解”,曾颇费心思地编撰过一部“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序》,《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2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页。的八万多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他写于1914年的《藏晖室札记》关于东西方传记比较的札记虽然很有标榜西方传记之意,但其标榜本身也是建立在与东方传记的详细比较当中,如非谙悉中国传统传记及其理论,崇尚实证的他也一定不会轻下断言。许寿裳《谈传记文学》*许寿裳:《谈传记文学》,《读书通讯》1940年第3期。中关于“传记文学的种类”、“传记文学的发展趋向”的立论,依据的基本是《论语》《庄子》《史记》《大戴记》《晏子春秋》等中国古代相关的写作实践,言及“传记文学的效用”时,则直接引用刘知几《史通》中关于“三传并作,史道勃兴”*《史通通释·内篇·人物第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38页。的表述。孙毓棠的《论新传记》更是明确指出:
西洋传记文学本有传统,基于一种个人主义和英雄崇拜的心理。自普鲁它克(Plutarch)的英雄传传世以后,几乎代代不乏名传记家。但是我们中国传记文学的传统,并不是见得弱于他们。自从太史公撰史记以列传为式之后,历代正史都拿列传作基石。汉末魏晋时因为时势造成了英雄烈士的心理,起始重视个人,一时碑版及传记之风大盛(如《曹瞒传》、《英雄记》、《谢玄别传》、《汝南先贤传》等可惜都已见不到完壁)。这两种体制一直流传后世。六朝唐宋的小说每喜以传记为体,都是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明清文人脱离了小说碑志,为写传而写传的很不在少数。有清以来年谱之学较宋明两代尤为发达,虽是受编年史体例之影响,但以个人事迹编年,也是传记学上的一大进步。所以我们传记文学的传统,并不亚于西洋。*孙毓棠:《论新传记》,《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1页。
至于朱东润,他从1930年代进入大学任职,从事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史的教学与研究,而之后的十几年里,又先后完成《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史记考索》《后汉书考索》以及《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等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可见,传统的史前资源对于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理论建构的影响虽然不甚彰显,但无疑是存在的。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的另一重要参照是外国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传记文学转型期中,首先跨越传统,在理论探索中引入域外视角的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是先进行传记写作、后展开理论探讨的,但在写作传记时他就已经有“仿西人传记之体”*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页。的自觉。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以人物为本位”、“人的专史”、“专传”等现代传记命题的重要理论参照,也是域外的传记理论与实践。如在谈及《史记》的特殊价值时,梁启超说:
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故其书厕诸世界著作之林,其价值乃颇类布尔达克之《英雄传》,其年代略相先后(布尔达克后司马迁约二百年),其文章之佳妙同,其影响所被之广且远亦略同也。后人或能讥弹迁书,然迁书固已皋牢百代,二千年来所谓正史者,莫能越其范围。岂后人创作力不逮古耶?抑迁自有其不朽者存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6页。
在考察传记与历史之关系时,他又谈到:
在现代欧美史学界,历史与传记分科。所有好的历史,都是把人的动作藏在事里头,书中为一人作专传的很少。但是传记体仍不失为历史中很重要的部分。一人的专传,如《林肯传》、《格兰斯顿传》,文章都很美丽,读起来异常动人。多人的列传,如布达鲁奇的《英雄传》,专门记载希腊的伟人豪杰,在欧洲史上有不朽的价值。所以传记体以人为主,不特中国很重视,各国亦不看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9页。
胡适在1910~1917年赴美留学期间接触到西方传记作品和理论,并于1914年写下了比较东西方传记,后来题为“传记文学”札记。这一札记受西方传记的影响显而易见,而且正是从这一时期起,胡适对传记的兴趣已经从一般的写作尝试逐渐转向理论的思考。
紧接着的是梁遇春、郁达夫等人的介绍。梁遇春在他的《新传记文学谭》中介绍了施特拉齐(Lytton Strachey)、莫洛亚(André Maurois)和卢德伟格(Emil Ludwig)这三位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郁达夫在《传记文学》《什么是传记文学?》等短短的几千字中谈到的国外传记作家作品,包括了从“Xenophon的《梭格拉底回忆记》”到“南欧的传记文学作者Giovanni Papini”的《基督传》等20余种。朱东润1939年以后开始切实提倡和研究传记文学,除了西方传记作品,他还认真研读了提阿梵特斯(Theophrastus)的《人格论》(Then Characters)和莫洛亚的《传记综论》等理论著作。*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序》,《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3页。后来在《传叙文学与人格》中,他还专门谈到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在“传叙文学”上的“重大的影响”。*朱东润:《传叙文学与人格》,《文史杂志》1941年第1期。林国光的长文《论传记》中,还专列一节,分析从旧约圣经中的传记故事到李顿·施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的作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洋传记的演进”,并在文末特意声明,其论文“多引哥伦比亚大学涅焚斯(A.Nevins),萧德威(J.T.Sho well)二教授著作”*林国光:《论传记》,《学术季刊》1942年第1期。。而像湘渔(吴景崧)的《新史学与传记文学》、孙毓棠的《论新传记》*湘渔:《新史学与传记文学》,《中国建设》第1卷合订本,1948年;孙毓棠:《论新传记》,《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等文中,被当成理论圭臬的也基本上是西方现代传记观念。
另外,在卢骚的《忏悔录》,尼采、歌德、托尔斯泰等人的自传,以及斯特拉屈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卢德威克的《俾斯麦传》、莫洛亚的《拜伦传》《雪莱传》等外国传记名作被介绍和翻译到中国的同时,相关的理论批评也开始被直接翻译到中国。1930年,巴金翻译出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其中一并翻译了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丹麦的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所写的《英文本序》。在此前后,勃兰兑斯关于传记文学的一些理论表述已经为中国作家所借用,如郭沫若声称自己写作“自传”“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也不是想学Goethe和Tolstoy要描写甚么天才”,*郭沫若:《〈我的童年〉前言》,《郭沫若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页。他所说的关于西方自传的这两种主要类型,在勃兰兑斯所写的《英文本序》中已经有类似的表述:
以前的伟人的自传大抵不出下面的三种类型:“我以前如此深入迷途;如今我又找到了正路”(圣奥古斯丁);“我从前是这么坏,然而谁敢以为他自己要比我好一点?”(卢骚);“这是一个天才因良好的环境慢慢地自内部发展的道路”(歌德)。在这些自我表现的形式中,作者总以自己为主。
十九世纪名人的自传又多半不出下面的两种类型:“我是这样地多才,这样地吸引人,我赢得人家如此的赞赏与爱慕!”(约翰娜·露易丝·海伯格的《回忆中的一生》)或者“我是才华横溢,值得人爱,然而人们却不欣赏我;看我经过了何等艰苦的奋斗才赢得今日的声誉。”(安徒生的《我一生的故事》)在这两类生活记录中,作者主要想的是他的同时代的人怎样看待他,怎样说起他……*[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我的自传〉英文本序》,《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从勃兰兑斯对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的评价,可以看出其对最佳传主的看法。他认为,“许多的男男女女并不曾经历一个伟大的生活也成就了伟大的一生事业。许多人的生活虽然是无大意义、平平常常,然而他们却引人入胜。至于克鲁泡特金的一生则兼有伟大与引人入胜二者”。在他看来,传主生平“引人入胜”,才能使传记作品“蕴藏着构成事变丛生的生活的一切要素——牧歌与悲剧,戏剧与传奇”。而在写作上,勃兰兑斯则强调“生花妙笔”和“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的成份”。*[丹麦]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我的自传〉英文本序》,《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勃兰兑斯的许多观点自然被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的探索者所接受。后来,湘渔在谈及如何处理传主人格刻画与展现传主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时,也直接引用了勃兰兑斯对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的评价:
在他底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底心理,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底心理,他述叙同时人底故事,实较叙述自己底故事的心更切。因此他底生活记录里面,便包含着当时的俄国底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动(工)运动底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底世界中时,我们又看见外的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见巴金译克鲁泡特金底自传)*湘渔:《新史学与传记文学》,《中国建设》第1卷合订本,1948年5月。
1938年,广州宇宙风出版社出版由陶亢德编辑的《自传之一章》,附录全文收入由豈哉翻译,日本现代知名作家、批评家鹤见祐辅撰写的长文《传记的意义》。鹤见祐辅认为传记的意义在于可以给阅读者两个方面的收获,“其一得到感化,即受到人生的教训,另一是获取知识”。关于前者,鹤见祐辅认为:“传记的真实目的,不在记述政治家武将的成功谈,而在于描写人类处广泛的环境之间,磨其心志展开何种人格的经过。所以,近代的传记,其寻求对象有舍政治家武将而向文艺家,思想家,画家、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探险家,社会运动家之势;这是人智之进步,同时也由于人类兴味已舍政治军事而向更通俗的生活部门”;至于后者,鹤见祐辅认为:“历史学的难解,因其只是简单记述的书籍。既无插话亦无富于人情味的故事之史的记录,因为不能动人,即难唤起感兴,而不能唤起感兴的记录,要能记忆自然困难”;“所以我人为了取得一般的教养而思大略习取专门以外的知识,莫如阅读各部门学问技艺之特出人才的传记”。
鹤见祐辅的文章给人理论意义上的启迪还在于其区别对待的传记文体观。他认为,“传记者,一方面是科学,他方面又必须是文学”。但科学与文学毕竟属性不同,它们之间有许多难以兼容的特征和要求,所以鹤见祐辅传记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传记作家可以(也应该)有所侧重,即“我人必得更进而概观近代史传的倾向,知道选择传记的一种标准”:
以科学为主者,是以材料为中心的传记,即世之所谓“正传”者是。正传也者,即凭其人之所有或其子孙所保管的材料,精确地作限于史实的蒐集,这在作为后世的史料固为有益的文献,但作为一般人之读物却不相宜。
至于以文学为主的传记,则将此类史料充分咀嚼,巧妙安排,而将那人物活写于纸上。这种才是人人可读的传记。
当然,鹤见祐辅属意的是第二种,在欧美已经成为“最近重要读物的一部门”的“新史传”,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传记文学”。因此,这一长文在传记文学方面也给人以多方面的独特启示。如他强调,“为新史传的中心者,是人格的发展纪录”,“这在以个人人格为中心处,与历史截然不同。历史是社会与民众的生活纪录,而传记却是个人生活之足迹;故往时以传记为历史家的余业,最近则新史传成了小说家的工作”;因为“小说的目的与传记的目标在某一点上彼此一致,即人格的发展是也,而非简单之外面的记述”。
和一味强调传记的客观纪实的传统观念不同,鹤见祐辅还特别强调和充分肯定传记作家主观价值判断对于作品意义生成的影响,“也就是说,传记作家在客观的记录之外,必得加上主观的批判,除此即得难得人物之记录。浅言之,传记作家自身非有一种哲学乃至理想不可,也就是非由一种精神的尺度来说明其人物的性行言动不可”。在鹤见祐辅看来,传记的“最要部分,是在作家的价值判断;他的价值判断可以引动读者。《勃鲁太克英雄传》之博得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爱读,即在于他所具有的庄严之价值判断能荡动我人心胸:此亦即勃鲁太克之所以占有独步古今的地位”。*上述相关引文均见鹤见祐辅:《传记的意义》,豈哉译,陶亢德:《自传之一章》,广州:宇宙风社出版,1938年。
1941年,《西洋文学》第5期还刊载了张芝联翻译的西方现代著名传记理论家莫洛亚的《现代传记》。该文译自莫洛亚被称为“现代传记的理论基础”的《传记面面观》(Aspects of Biography)的第一章。莫洛亚用列敦·斯屈齐(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皇传》等为例,分析、总结了现代传记“勇敢的追求真实”、“注意人格的复杂”以及“比较近乎人情”等三个特征。莫洛亚理论的翻译介绍,直接影响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传记理论探讨与研究。
1948年,汤钟琰在其《论传记文学》*汤钟琰:《论传记文学》,《东方杂志》1948年第8号。中,已不再一味崇尚西方传记和“新传记”,而是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布鲁达克以来西方那些显赫一时的传记作者及其作品。他认为布鲁达克的“名著《罗马英雄传》亦仅系史书只以文字瑰丽,始为后代文士所推崇”。鲍斯威尔的《约翰生博士传》“也应该算是最伟大的传记之一,这本书的特色是一破过往的传统,没有把约翰生写成一个完人。……但是,鲍斯威尔仍然有很多令我们不能满意的地方。《约翰生博士传》还只是事实的记载(虽然没有隐瞒没有过分的偏袒),而缺乏心理状态的叙述。我们虽说可以看得出约翰生的好的与坏的表面,但是不能看到他内心的生活。用一个比较空洞的比喻,鲍斯威尔之作还只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他比较赞赏斯特瑞基的新传记,引用并肯定其《维多利亚王朝名人传》序文中的观点:
写一部完美的传记也许与过一个完美的生命同样地难得。要保持一种恰当的简洁——就是说要把一切重沓浮滥的材料完全删掉,而又没有删却一点重要的材料——这无疑问地是传记家第一个任务。至于第二个任务,就是传记家要保持他精神上的自由。他的任务不在恭维人家而在把种种有关的事实,依照他所能了解的揭露出来,既不偏袒,也不带别的用意……(从范存忠译——原注)
他还发现斯特瑞基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研究依利莎白,所以整本《依利莎白女王传》中“几乎有一半的篇幅都侧重在女王心理的描写”。同时,他还引用卢特威奇《耶稣传》序言的文字,认为这“也是新传记运动中一篇重要的文献”。
这本书写的是“耶稣”这个人,没有一个字提“基督”这个神。……我的目的不在注解大家明白的教义,而在写出这位先知的内心生活……我一点都不想摇撼在基督意义之下生存的,人们对于基督神性所有的信仰,我的目的反倒是想给那些以为耶稣的人格是造作起来的人知道,耶稣实在只是一个合乎人性的“人”……(从孙洵候译《人之子》,商务——原注)
另外,针对有人批评莫洛亚的传记作品“太不忠实于史实”,汤钟琰认为“这并不是公允的批评”,因为“莫洛亚的大部分著作并没有过分歪曲史实,他只是在史实的范围以内,过多地侧重于心理的描写而已”。*汤钟琰:《论传记文学》,《东方杂志》1948年第8号。
所以说,外国传记文学理论观念的介绍和翻译,不仅拓宽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家的新视野,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传记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参照。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参照已经从梁启超、胡适的一味推崇变为一种理性接受,进而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合理建构之中。
二、始于新史学的思考与倡导
一般认为,1914年胡适在题为《传记文学》的札记中率先提出“传记文学”的概念。但据卞兆明《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一文考证,“写于1914年9月23日的《藏晖室札记》卷一七第一条原本没有标题。而现在看到的‘传记文学’这一分条题目是胡适的朋友章希吕在1934在1月5日至7月7日这段时间内抄写整理这则札记时给加上去的”;他认为,“胡适在1914年并没有使用‘传记文学’一词,9月23日的札记谈论的也只是‘传记’而不是‘传记文学’,直到1930年胡适在《〈书舶庸谭〉序》中才正式开始使用‘传记文学’名称”。*卞兆明:《胡适最早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的时间定位》,《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从这一角度看,在1930年代之前的中国尚无人进行自觉的传记文学的提倡,胡适、梁启超等人的理论探讨也还仅是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中进行。
从表面上看,胡适在1914年就有过关于东西方传记差异的思考,而梁启超是在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才提出“人的专史” 的概念,进而对传记写作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但是,胡适关于东西方传记不同特点的思考仍然是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中进行,而在他之前,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已经在学界广为传播。所以,在考察中国传记理论转型时,首先应关注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开始大量写作传记的。1901年10月李鸿章去世,11月梁启超即完成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李鸿章的传记。同年,梁启超还写作了他的另一重要传记《南海康先生传》,并完成其史学论文《中国史叙论》。1902年,他所完成的中外名人传记则包括了《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加利爱国者噶苏氏传》《张博望班定远合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等。此时的梁启超已经“颇有志于史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9页。因此又写出重要的史学论文《新史学》一篇。
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提出了迥异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他认为新史学和旧史学不同在于旧史学仅仅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新史学“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参照“西人”世界史分期方法,把中国史分为秦之前的“上世史”, 秦统一至清代乾隆的“中世史”以及乾隆末年之后的“近世史”,以打破传统的“以一朝为一史”的史学观念。他还分别把“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时期的中国依次称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12页。在《新史学》中,梁启超表明了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新史学历史观,并且主张治史应多采西学新说、新法。如关于史之编撰,他认为:
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后之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9页。
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梁启超新的世界性眼光。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35~114页。中,梁启超提出“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这为之后专门提出“人的专史”奠定了基础。在论及个人与时代之关系、回答“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时,梁启超提出了“历史的人格者”的命题: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领,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
梁启超认为,“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为现代传记写作把握历史人物与时代之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8~30页。中,梁启超就“人的专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人的专史”“即旧史的传记体、年谱体,专以一个人为主。例如《孔子传》《玄奘传》《曾国藩年谱》等”。正史就是以人为主的历史,其缺点在于“几乎变成专门表彰一个人的工具”,“多注重彰善惩恶,差不多变成为修身教科书,失了历史性质”;但梁启超认为“历史与旁的科学不同,是专门记载人类的活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伟大活动可以使历史起很大变化”,所以“一个人的性格、兴趣及其作事的步骤,皆与全部历史有关”,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线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梁启超的立论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的,但从人物与环境的角度看,关于个人与历史这方面主张却有其合理性。
梁启超专门考察和辨析了不同类型的“人的专史”,列传、年谱、专传、合传、人表的不同特点。他认为:“凡是一部正史,将每时代著名人物罗列许多人,每人给他作一篇传,所以叫做列传”;“专传以一部书记载一个人的事迹,列传以一部书记载许多人的事迹;专传一篇即是全书,列传一篇不过全书中很小的一部分”。可见梁启超所说的列传,基本上就是传统所说的“史传”,而专传则大致为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或传记文学作品。因此,他对于专传特点的辨析特别有助于现代传记的文体特征的把握。他认为理想的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而列传虽也以一个人为中心,“但有关系的事实很难全纳在列传中”,“得把与旁人有关系的事实分割在旁人的传中讲”。 专传与年谱的区别则在于“年谱很呆板,一人的事迹全以发生的先后为叙,不能提前抑后,许多批评的议论亦难插入。一件事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更不能尽量纳在年谱中。若做专传,不必依年代的先后,可全以轻重为标准,改换异常自由。内容所包亦比年谱丰富,无论直接间接,无论议论叙事,都可网罗无剩”。梁启超认为“专传在人物的专史里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37~56页。
在传主的选择方面,梁启超认为“应该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约有七种,即“思想及行为的关系方面很多,可以作时代或学问中心的”;“一件事情或一生性格有奇特处,可以影响当时与后来,或影响不大而值得表彰的”;“在旧史中没有记载,或有记载而太过简略的”;“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的;“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的;“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的;“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而“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的则有两种:“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
至于如何作传,梁启超一些比较具体的论述对传记文学写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
为一个人作传,先要看为甚么给他做,他值得作传的价值在那几点。想清楚后,再行动笔。若其人方面很少,可只就他的一方面极力描写。
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大事看环境、社会、风俗、时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语行动乃至小端末节,概不放松。*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89~121页。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缘由也和梁启超提倡人的专史很有些相似,他也是在进行一定的传记写作后开始其理论思考的。胡适1904年到上海求学后在中国公学校刊《竞业旬报》发表过《姚烈士传》《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中国女杰王昭君传》等作品。从题目上看,“第一伟人”、“第一女杰”等的立传角度明显受了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等作品的启发。实际上,胡适与梁启超的“历史”渊源还不止这些,在后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胡适曾谈到这一传记的作者、传主的儿子张孝若是生活在“新史学”的时代,并且借此对“新史学”时代的特征进行过比较简练的概括:
他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05页。
1910年赴美留学之后,胡适广泛接触西方传记作品和理论,才于1914年写下了被题为《传记文学》的札记。札记从理论上比较分析了中西传记的“差异”,认为“东方无长篇自传”;中国的传记“静而不动”,即“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而西方传记“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且“琐事多而详,读之如亲见其人,亲聆其谈论”,等等。*胡适:《传记文学》,《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00~201页。这一札记虽然仅是提纲,而且未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概念,但已经显示胡适对于传记这一文体的理论自觉,而且基本体现了他的传记文学观念。
胡适在1929年年底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仍然未正式提出“传记文学”的名称,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已经表明,此时他关于传记的理论思考已经是在文学的范畴内进行。在胡适看来,中国传记写作不受重视的原因在于“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此文中,他把有别于传统史传的传记称为“新体传记”。*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202、204页。1930年,胡适在《〈书舶庸谭〉序》(1930)中开始使用“传记文学”名称。此后,在《〈四十自述〉自序》(1933)、《中国的传记文学——在北京大学史学会的讲演提纲》(1935)等文中就一直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从总体上看,中国传记或传记文学的不发达的原因是胡适进行理论探讨的出发点和基本着眼点,他的许多论述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胡适虽然已经常采用“传记文学”的概念,但其理论思考却并不完全囿于文学的范畴,历史和文学在胡适讨论传记或传记文学时常常是含混的,这也正是作为转型时期中国传记文学提倡者特殊的理论特征。
就在胡适的传记理论思考从历史范畴逐渐向文学范畴转换的过程中,梁遇春率先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1929年5月,梁遇春在《新传记文学谭》一文中介绍了西方传记文学的新进展,认为德国的卢德伟格(Emil Ludwig)、法国的莫洛亚(André Maurois)和英国施特拉齐(Lytton Strachey)“不约而同地在最近几年里努力创造了一种新传记文学”。他不仅总结了这种新的传记文学的特点,而且着重介绍了施特拉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人物》(Eminent Vietorians)、《维多利亚皇后》(Queen Victoyia)等著名传记作品。他认为:
他们三位都是用写小说的笔法来做传记,先把关于主要人物的一切事实放在作者脑里熔化一番,然后用小说家的态度将这个人物渲染得同小说里的英雄一样,复活在读者的面前,但他们并没有扯过一个谎,说过一句没根据的话。他们又利用戏剧的艺术,将主人翁一生的事实编成像一本戏,悲欢离合,波起浪涌,写得可歌可泣,全脱了从前起居注式传记的干燥同无聊。*梁遇春:《新传记文学谭》,《新月》1929年第3号。
可见,梁遇春已意识到用小说和戏剧笔法写成的传记文学作品同传统史传的区别。
三、观念转换与实践方法的探讨
1929年梁启超病逝后,梁遇春、胡适开始启用“传记文学”名称,这标志着有关传记的讨论由历史范畴进入文学的范畴。而除了梁遇春、胡适,在1930年代努力提倡传记文学,并始终坚持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理论倡导的是郁达夫。郁达夫在1930年代初写了《传记文学》(1933)、《所谓自传也者》(1934)、《什么是传记文学》(1935)等几篇提倡传记文学的文章,在理论上表现了与传统、同时也和时人截然不同的见解。
郁达夫认为中国缺少的是“文学的传记作家”,缺少“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环境,描写得极微尽致的”英国鲍思威儿Bosell的《约翰生传》,“以飘逸的笔致,清新的文体,旁敲侧击,来把一个人的一生,极有趣味地叙写出来的”英国Lytton Strachey的《维多利亚女皇传》,以及法国Maurois的《雪莱传》、《皮贡司非而特公传》、德国的爱米儿·露特唯希,若意大利的乔泛尼·巴披尼等“生龙活虎似”的作品。*郁达夫:《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01~202页。他认为中国急需“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应是怎样呢?郁达夫认为:
新的传记,是在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
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
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第6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283~286页。
郁达夫认为,传记文学不应仅记传主的美点而应传述包括缺点在内的整个人,不应仅是传主外部生活的纪录而同时应写出其内心的变革,不应仅写传主的公生活而还应写其私生活;传记文学的要点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而在于艺术的创造。这些观点充分昭示了郁达夫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的坚定立场。
几乎和郁达夫同时,茅盾也写了同题的《传记文学》。茅盾也认为“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他觉得“虽然在古代典籍中间,我们有着不少人物传记,但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目的只是在于供史事参考,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文学。历代文集中的传记,以颂赞死人为目的,千篇一律,更说不上文学价值”。而五四文学革命之后,“小说,诗歌,戏剧已很明显地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而改变形式,占了现在创作中的主要领域”,但“在现代西洋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传记文学”,中国“却依然缺乏”。究其原因,茅盾更主要是从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角度加以解释的。他说:
传记文学的发展,在西洋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换句话说,描写人物生平的文学,是到了近代个人主义思想充分发展以后,才特别繁荣滋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物中,人物传记往往占最大的销数,这只是因为描写个性发展,事业成功的文学容易受中产阶级读者欢迎的缘故。可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主义的幻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英雄或法西斯蒂领袖;同样地在封建家族思想灭落,集团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国,也不会有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产生。即使有所谓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茅盾:《传记文学》,《文学》1933年第5号。
虽然茅盾不像郁达夫那样具体谈论传记文学应有的特点,但他说到的“描写个性发展”、“个人主义的幻想”以及“用文学描写”等,都表明了他把传记文学的“文学价值”和一般人物传记的“史事参考”区别开来的努力。
阿英在1935年也写过一篇《传记文学论》,但他所谈的却是“传记文学”里“别创的一种新格”——“小说似的近乎虚构的故事”,如中国古代的《聂隐娘》《郭橐驼》和《瞽琵琶传》。阿英认为,这类作品“并不是全没有根据,而驰骋着作者自己想象的部分,究竟是很多的”,作者所以“要写作这一类的传记”,“自然是有所寄托,而又不能直截的正面的写,遂采取了如此的表现法”。因此,阿英认为这类作品“同样的是有着文学的和社会史的意义”,而且“比那些歌功颂德,自捧自唱的‘传记文学’,价值要高得多的”。*阿英:《传记文学论》,原载《文艺画报》1935年第3期,此据《阿英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阿英所谈的,实际上已是纯属艺术虚构,但采用了传记形式表现的传记体小说。这种传记小说,与用历史或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具体人物为传主的传记文学相去甚远。
由于梁启超、胡适到郁达夫、茅盾等的提倡,传记文学在1930年代也就有了相对繁荣的景象。可能受郁达夫、茅盾前一年文章的直接影响,上海第一出版社在1934年6月到11月推出了包括庐隐、沈从文、张资平和巴金等的“自传丛书”。1934年,上海文艺书局出版由新绿社选编的传记选集《名家传记》。同年底,郁达夫自传开始在《人间世》连载。进入1935年之后,《我的母亲》(盛成)、《林语堂自传》(林语堂)、《一个女兵的自传》(谢冰莹)、《钦文自传》(许钦文)、《悲剧生涯》(白薇)、《经历》(邹韬奋)、《实庵自传》(陈独秀)、《李宗仁将军传》(赵轶琳)等相继推出。1938年,广州宇宙风出版社也出版由陶亢德编辑的自传选集《自传之一章》。
在1930年代的传记文学创作热潮中,除了胡适与郁达夫,郭沫若、巴金等一些传记(特别是自传)的作者,其他作者虽然没发表过专门的文章,但他们在序跋之中也都表达过对于传记文学写作的见解。而潘光旦在为顾一樵《我的父亲》所作代序中则明确表示,年谱、列传并不配称传记文学。他说:
中国以前只有传记,并没有传记文学;也可以说只有传记意味的文学,而并没有传记。配称传记文学的笔墨实在不多见。真正好的传记也找不到几篇,更找不到几本。年谱,重片段的事实,而不重文,列传的文字,重简练的笔墨,而不重事;二者又都谈不上“亲切”两字。“亲切”便是“文情并茂”的“情”。要文,情,事三者都顾到了,才配叫做传记文学。*潘光旦:《一篇传记文的欣赏(代序)》,顾一樵:《我的父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1页。
他肯定和赞赏注重家世与里居环境的叙述:
一人的生平,所占的时间见得到的,不过数十寒暑,而见不到的,必十百倍于此。换言之,一人的生平,一部分是早在祖宗的行为与性格里表现出来过的,我们后来加以分析与描写,诚能于其先世人物,先事了解,我们便不难收事半功倍的效力。同时一人成年后的功业所开辟的环境,是极容易见到的,而其幼年的环境,朝斯夕斯所接触的事物,虽往往与后来的造诣有极大的因缘关系,却极容易受忽略,事过境迁之后,也极不容易得到翔实的记载。*潘光旦:《一篇传记文的欣赏(代序)》,顾一樵:《我的父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页。
至于邵洵美为《庐隐自传》所作的代序,表面是评价介绍庐隐本人,实际上涉及的则是传主的选择,为传的态度、方法以至文趣等方面的问题:
像庐隐这么一个作家,当然最适宜于写自传了。第一她因为对自己特别感到兴趣,于是会细心地去观察自己而立下几乎是大公无私的评语。第二她有充足的脑力去记忆或是追想她的过去。第三她有勇敢去颂扬自己的长处及指斥自己的弱点。第四她有那种痴戆或是天真去为人家抱不平及暴露人世间的丑恶。第五她有忍耐同时又有深刻的观察力去侦视这人生的曲折。第六她有复杂的经验可以使自传不枯燥。第七她有生动的笔法可以使一切个人的事情使别人感到兴味。第八也是最难得的,便是她是一个“自由人”,她不用在文章里代什么人说话或是为什么人辩护及遮蔽。*邵洵美:《庐隐的故事》(代序),《庐隐自传》,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第7页。
而在《名家传记》书前,甚至还刊有长达万言的《怎样写传记》(佚名)*据该书“例言”称:“传记作法问题,本拟辟专篇以论之,适值某报附刊发表《怎样写传记》一文,征引广博,要言不烦,询其可否转载,竟然见诺,同人感其美意,聊誌数语,以表谢忱。”。该文包括“传记与传记文学”、“传记的一般作法”、“传记的种类与形式”、“传记文学之贫困”和“关于自传的作品”等五个部分。
“传记与传记文学”主要辨析如《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游侠列传》《李斯传》《李广传》《李陵传》《祢衡传》等传统 “传”或“列传”与现代传记文学的不同“含义”,认为上述的一些所谓“传”或“列传”,“大都只是些历史的记录,是属于历史而不属于传记。传记是文学上的一个独立的部门。传记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历史的资料看待,但决不就是历史”。而传统的“行述”,和现代的“自传”也截然不同。在这一部分,作者还首次追溯了传记一词在欧洲希腊语的解释和用法:
传记,相当于希腊的bios一词,义为生平或生活(life),故凡有关于一个人的生平的某些作品,便都以传记称之。英国人根据此希腊语,造一新字曰:biography,最初用此字者,是十七世纪的诗人屈里顿(John Drydon,1631-1700),那时他正要论述布鲁塔奇的《英雄传》(Plutarch’s“Lives”),故需用这一新字。在这以前,英国字典中尚无“传记”一词;或者换句话说,便是传记一词的定义,在此时才确立了起来。一直到有一为名叫鲍斯威尔(Boswell)的,把约翰生博士(Dr.Samuel Johnson)的生活史编成一部作品的时候,才出现了第一部真正的传记。
“传记的一般作法”强调四点,即:“(一)要写真传神,(二)要刻画时代,(三)要用文学技巧,(四)要有系统程序。”其所说的“要用文学技巧”是“须用灵活的笔致,清新的风格,细腻的描写手腕,旁敲侧击的文字技巧”。其在“要有系统程序”中则还谈到:“要注意怎样从所传者的各个时期中摄取真实而且精当的材料,尤其是富有特色和新的趣味的材料,还要注意怎样避免着事实之单纯的罗列,而努力于作者主观的抒发。”
在“传记的种类与形式”中,作者则根据不同的标准列举了三种不同的分类法:
有些人以被传者的在社会上的成就分为:(一)革命家,(二)思想家,(三)艺术家,(四)科学家等传记。例如《列宁传》,《墨索里尼传》,属于革命家的类型;《马克斯传》,《克鲁泡特金传》,属于思想家的类型;《贝多芬传》,《歌德传》,关于艺术家的类型;《达尔文传》,《牛顿传》,属于科学家的类型。
有些人以传记写作的风格,分为:(一)以批评研究为传记中心者,叫做评传;(二)以历史为中心者,叫做史传;(三)以心理分析为中心者,叫做心理传记;(四)以日常谈话为中心者,叫做鲍斯威尔式(Boswellian)的传记;(五)以年代的记录为传记者,叫做年谱;(六)以介绍的形式写传记者,叫做介绍文。
又有人以作传者的地位分为:(一)自传,(二)他传。普通所谓传记,大抵是指由别人写的传,由作家写自己的传,即称之曰自传。
“传记文学之贫困”主要谈原因,而且基本上引用胡适和茅盾的观点。“关于自传的作品”则关注到当时已经出版的一些自传作品,但同时也指出“在自传之中,固然写不出Everything,却是应该说出Something,总不应该写了一个Nothing。”
虽然《怎样写传记》中的一些理论观念的表述不尽严密,而且目前还无法确认其作者,但该文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上的贡献却应充分的肯定。因为该文第一次追溯了西方关于传记一词的解释和用法,第一次关注到不同标准中传记文学的不同分类,同时还具备把传统传记与现代的传记文学区别开来的自觉意识。
四、学者的介入与理论的建构
进入1940年代,中国传记文学的理论建构进入全面展开的时期。其标志是,不仅仅作家,包括许寿裳、林国光、朱东润、郑天挺、许君远、孙毓棠、戴镏龄、寒曦、湘渔、汤钟琰和沈嵩华等一批学者先后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传记文学的相关立论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首先是许寿裳。许寿裳开始传记文学研究,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但从时间上看,许寿裳的传记文学研究和教学明显比上述这些学者们早。他于1940年发表的《谈传记文学》(《读书通讯》第3期)在时间上刚好是这一传记文学理论研究阶段的引领之作。而他1940年在华西协合大学讲授《传记研究》的专题课,比朱东润1947年在无锡国专开设《传记文学》课程,在时间上也早了好几年。所以完全可以说,许寿裳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深入展开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
《谈传记文学》一文就传记文学的种类、效用和发展的趋向发表了看法。许寿裳认为:“传记文学的种类很多,可是大别起来不外两种:(一)自传。(二)他传。”他特别强调自传的长处在于“能够自语经历,感想以及治学方法,把自己的真性情和活面目都表现出来,使读者觉得亲切有味,好像当面聆教”*许寿裳:《谈传记文学》,《读书通讯》1940年第3期。。
关于传记的“效用”,许寿裳遗稿《传记研究杂稿》中开列的有修养人格、增加作事经验、把握历史主眼、发扬民族主义等几个方面。在《谈传记文学》一文中则简化为:一、修养人格;二、发扬民族主义;三、拿着历史主眼。这些有的是沿用前人的观点,有的也带有许寿裳基于时代的思考。如所谓“增加作事经验”沿袭的则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说法。“把握历史主眼”沿用的是梁启超对于综合性传记的看法,即认为“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标准,可以把所有的要点,看得清清楚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但“修养人格”,指的则是从每一时代寻出代表人物,“将种种有关之事变归纳于其身,其幼少时代之修养如何?所受时势环境之影响如何?所贡献于当世,遗留于后代者如何?其平常起居状况琐屑言行如何?一一描出,俾留一详确之面影以传于世”,*许寿裳:《传记研究杂稿》,黄英哲等:《许寿裳遗稿》(第2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94页。而“发扬民族主义”在“遗稿”的表述是“显扬祖德,巩固国本,使民无攜志”*许寿裳:《传记研究杂稿》,黄英哲等:《许寿裳遗稿》(第2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696页。。
关于传记文学的发展趋向,许寿裳认为:“上古时代,史传和神话传说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然不免带有神话传说性质,而神话传说之中也往往含有史实。”“孔子以后,历史和神话分途了。司马迁以后,正史和小说分途了。魏晋以后,别传繁兴了,杂传也多了,正史变为官书,列传的体例越严,而内容越薄,文学趣味反而低减了。”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谈传记文学,自然当以西人的传记性质为标准,也就是上文说过的综合性的传记,对于能够发动社会事变的主要人物,使之各留一个较详确的面影以传于后”*许寿裳:《谈传记文学》,《读书通讯》1940年第3期。。
1940年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的重镇是朱东润。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传记文学研究之后,朱东润撰写和发表了《传叙文学与人格》(1941)、《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1941)、《传叙文学与史传之别》(1941)以及《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等著述。这些加上其《〈张居正大传〉序》(1943)等,可以看出1940年代的朱东润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观念。
和胡适、郁达夫等人一样,朱东润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中外传记理论的吸收、借鉴的基础上的。但朱东润和众多提倡者的不同在于,他学习借鉴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创作,但决不机械地加以照搬与模仿。首先在关于“传记文学”名称的使用问题上,朱东润力排众议,主张废“传记文学”之名而用“传叙文学”,他认为中国依传统的看法,“传是传,记是记,并合在一个名称之下,不能不算是观念的混淆”;而采用“西洋文学”的看法,“传记”实际上又包含了“biography(传记)”和“autobiography(自传)”二类,如仅称“传记”则是“以偏概全”。而在中国传统中,“叙是一种自传或传人的著述”,所以,为“求名称的确当起见”,应该用“传叙文学”取代流行的“传记文学”。*朱东润:《关于传叙文学的几个名词》,《星期评论》第15期,1941年。
在对传记文学命名进行理论思辨的同时,朱东润从一开始也关注到传记文学的基本属性问题,并且始终强调传记文学的史学、文学双重属性。他认为“传叙文学是文学,然而同时也是史;这是史和文学中间的产物”。然而朱东润论述传记文学属性的意义并不在于其结论,而在于其论述过程中辨析文学与历史不同属性的理论启示。他认为:“传叙文学是史,但是和一般史学有一个重大的差异。一般史学底主要对象是事,而传叙文学底主要对象是人。”*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一绪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从梁启超提出的人的“专传”到朱东润的“对象从事到人”,表明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探讨的深入。人的“专传”虽然有别于传统的史传,但仍然是在史学的范畴中立论,而“对象从事到人”实际上已是文学的理论自觉。
既然认为“从事到人”是传统史传与现代传记文学的根本区别,在关于传记文学的论述中,如何写“人”也就成为朱东润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强调“传叙文学应当着重人格的叙述”,而且“传叙文学家认识人格不是成格而是变格”*朱东润上述关于传主人格的主张的引文,见其长篇专论《传叙文学与人格》,《文史杂志》1941年第1期。。
当然,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朱东润虽然意识到传记文学必须是独立于历史著作之外的文体,但在对这一文体进行深入思考时仍然很难突破史传的影响,仍然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如他把西方传记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进而具体描写传主生活的鲍斯威尔型;“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繁琐的考订”的斯特拉哲型;一切都“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繁重作品型。*朱东润这些论述见《〈张居正大传〉序》,《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但他认为,在现代传记文学刚刚兴起的中国,所需要的是第三种。他强调史学方法的运用,强调史料的辨伪考据,要求做到严谨有据。对历史真实的过度关注,一定程度上使得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探讨忽视了对艺术真实的思考。*关于许寿裳与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阐述可参见笔者专文《许寿裳与现代传记文学》(《上海鲁迅研究》2013年春之卷)、《论朱东润传记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差不多和朱东润同时进行传记或传记文学理论探讨的还有郑天挺、林国光、许君远和孙毓棠。郑天挺于1942年10月为光明电台文哲讲座所写的广播稿《中国的传记文》*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国文月刊》1942年第23期。,虽然是从史学的角度立论,但其中关于传统史传完美叙事的“条件”、“禁忌”以及对“后来传记所以不好的原因”的总结,对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启示。
他认为,写出优秀传记的前提“条件”是“求真”、“尚简”和“用晦”。求真指“尽量征求异说,尽量採摭史料”,但“绝不麻胡,绝不苟且,对于一切一切的事件都要辨别它的真伪”;尚简指“提倡简要,反对文字的烦富”,期望“文约而事丰”;用晦则“因为他们尚简,所以有许多事迹他们不明显的直说,而用旁的方法委宛的点出来,烘托出来。或者是只说大的方面,重要的方面,而将小的轻的不说,使读者自己去体会”。
而写作优秀传记的“禁忌”是“诡异”、“虚美”和“曲隐”。 所谓诡异指“神圣不经之谈,离奇诡异之说”;虚美指“对于一个人的过分称赞,或者一件事的过分夸张”;曲隐则是“只叙述其善而曲隐其恶”。至于“后来传记所以不好的原因”,郑天挺认为主要受文字、技巧、观念、史料以及主观等方面的影响。所谓“主观”,他指的是:“写传记的人最容易用自己主观来写旁人的言行。……他们往往忘了所写的人的个性,忘了所写的人的学识才情同环境,只凭自己的主观。”
林国光的长文《论传记》分“传记与文学及历史的关系”、“西洋传记的演进”和“传记的定义及其分类”三个部分论述了传记的相关理论问题。由于作者主要的理论参照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涅焚斯(Allan Nevins)和萧德威(J.T.Sho well)的著作,所以其论述基本是历史学的视角。他认为:
传记的编纂是一种艺术,一种人对人的了解与分析,其撰作有如现代人像画,不过是一个人的生平言行思想,用最优美的文字表现出来。……但是传记究竟还不是纯粹的文艺作品,不像史诗,更不像历史小说,不能单靠丰富的想象力,驰骛空中,即景会心而杜撰。其实传记作家的搜罗材料,考订调核,排比分析,批评估计等等,惨心经营,有如一般史家修史,所以传记与其属“文”,不如属“史”。*林国光:《论传记》,《学术季刊》1942年第1期。
所以作者坚持认为,“传记是史学的一种,至少也可以算是个人的历史”。但即使是在史学的范畴中讨论,林国光不少观点对于传记文学理论的建构还是有特殊的启示。他强调传记必须写人,“必须能够充分表现传主性格,恍然如生;对其生平行动经历的叙述,必须巨细无遗,细心公正;必须指出传主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也肯定传记作者的主体性意义,认为“传记每每因其略带主观私见,人物有声有色,活跃于纸,远非史书其他形式所可比”。他还比较准确地概括介绍和肯定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李顿·施特拉其(Lytton Strachey)编撰传记的方法,并指出一些拙劣模仿者的致命弱点。
关于传记属“文”属“史”问题,著名报人和翻译家许君远的观点则与朱东润比较接近。他在《论传记文学》一文中则比较客观地比较了传记与文学及历史的关系,认为传记文学的“性质介乎历史与小说之间,写传记的手法也和写历史写小说为近”。据此,许君远认为评传年谱“对某一个英雄或大哲作一个编年史式的介绍,只要有生卒年月事业或著作,材料便已完备,再用不着什么谨严的布置和细微的描写”,所以“严格说来”这两种应该归在“史”的方面。他还指出中国“自传”不够发达的原因,并且批评胡适的《四十自述》也仍然没畅所欲言:
“自传”素为中国文人所不取,这原因大部是他们不肯说实话,小部是他们顾虑太多;还有一点便是中国学者缺乏写传记文学的风气,如果真的有人(尤其是往古时代)自撰一篇自述,不免被目为“其人怪诞不经”,便会以“小说家言”而遭摒斥。近人有的在试作这一番工作了,不过仍然不能畅所欲言,譬如胡适之写《四十自述》,对于恋爱只字不提,便是一个例子。*许君远:《论传记文学》,《东方杂志》1943年第3号。
对于传记文学的发展前景,许君远可能受到英国著名传记理论家尼科尔森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无可怀疑地传记文学是在向着一条崭新的路线上走:离历史的边缘更远,距小说的核心愈近;同时全是日常生活,不使被传者迷失本性”*尼科尔森在关于传记的科学性和文学性问题的论述中说过:传记创作中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必将分道扬镳”,“科学性的传记将趋于专门化和技术化”,文学性的传记则“步入想象的天地,离开科学的闹市,走向虚构和幻想的广阔原野”(参见尼科尔森著,刘可译:《现代英国传记》,《传记文学》1985年第3期)。。
同样从事史学研究,但曾列名于新月诗派的孙毓棠,在194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传记与文学》。其中的《论新传记》一文主要论述撰写新传记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孙毓棠仍然坚持传记的史学属性,但他所说的“新传记”实际指的却是“英国斯特莱基(Strachey)首创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写传记”,这种传记“不仅负记载史实或集录信札,记及个人逸事的责任,而且重在性格与心理的分析解释”;“不仅是枯干的记事,而且重在文笔的动人”。因此,孙毓棠所说的撰写新传记“六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项,大部分都和传记的文学叙事有关。他认为,撰写新传记,第一“必需忠于史”,第二“需着重心理的分析”,第三“当以描写性格为中心的任务”,第四“必需照到主人翁所生的社会及其时代”,第五“当注重文笔”,第六“某种幻想有时又是可以被容纳的”。
在上述主张中,最能体现孙毓棠开放的传记观的是第五、第六点。在谈及第五点“新传记当注重文笔”时,孙毓棠认为:
传记如果以记实为目的,当然可以不注重文笔,这类的传记著作世界上很多。但是理想的新传记不只是一种史学的著作,它同时还应该是一种文学的著作;应该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给科学披上文学彩衣的艺术品。雪莱(Shelley)的传记也很有几本,但读谋汝洼的爱丽儿(Ariel)一书的人,观其文笔之生动,叙述之有趣,对于雪莱性格描写之清晰亲切,实可令人神往。我们也知道这部书中有很多地方不忠于史,作者也未曾拿他当一本历史书写,可是这本书在文学上讲,确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从史学上讲,也不是一部完全要不得的书。……谋汝洼曾讲,写传记和别的文学创作一样,也是一种精神的产物(Andre Maurois:“Aspects of Biography”——原著),其实历史的著作以及一切旁的科学的研究与著作,又何尝不都是如此呢?在人的创作欲上讲,写一本小说和科学上求一种发明本是一样的。*孙毓棠:《论新传记》,《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7页。
正是在强调传记的“文笔”、“文学的著作”、“艺术品”和“神的产物”的基础上,孙毓棠在最后正面肯定了艺术虚构在传记写作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在传记写作中“往往因史料缺乏之故,自然会露出许多空隙来”,“为了文章起见,某种幻想有时又是可以被容纳的”。他说:“这样参进去的幻想是合理的,不致大错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幻想叫作“合乎逻辑”的幻想。在传记之中参入这种合乎逻辑的幻想,总比说汉高祖腿上一定有七十二个黑点子的话显得还更合理更可靠些。”*孙毓棠:《论新传记》,《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8页。
在《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一文中,孙毓棠还就传记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所谓‘个人事迹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一样,是不容易也可以说是根本不能够得到的。”所以他主张:“传记家……应该只求以现存的关于此个人的记录为材料,以探讨其性格与精神。为将此性格与精神描写出,解释给一般读者知道,他不得不主观地剪裁材料,合理地以推测或合乎逻辑的幻想来弥补知识之空隙。”*孙毓棠:《传记的真实性和方法》,《传记与文学》,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第25页。
进入1940年代后期,有关传记和传记文学的讨论继续向纵深发展。1947年7月,戴镏龄发表《谈西洋传记》*戴镏龄:《谈西洋传记》,《人物杂志》1947年第7期。,介绍外国传记发展情况及相关传记文学理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传记这个名词英文里是Biography,1660年才在英国开始用,不过它在欧洲是起源很早的一种文学,散见于希腊罗马的著述里。即是在古代希伯来的民族的文学里,它也占有重要地位。”可见,戴镏龄是在文学的范畴里讨论传记的。他明确提出传记作品的三个要素:
第一,它是一种记载。
第二,它是关于个人的记载。
第三,它是用画术手腕写成的。
所以,他认为传记“所记载的是个人的事实,所注意的是个人内在的性情,气质,言行的动机和心理上种种微妙变化”。传记家搜齐传主的“全部事实,按年月日排起,本身还不是传记,不过是供写传记者的一部资料。……传记家须从浩瀚的材料里节取精彩紧要的部分,然后加以严密的锤炼和完整的组织,用优美的文辞做经,丰富的想象做纬,使最后的成品是经过匠心制造的一件艺术成品”。
从西方传记发展的角度看,戴镏龄特别强调“自由的心灵”在传记写作中的重要性。所以,他特别推崇史特拉屈(Lyttonstpachay),认为他“回到了以前欧洲的传记界的良好作风——对于人重行用自由的心灵作精微的心理分析”,他代读者“打倒偶像,消除他们精神上的压迫,恢复他们心灵的自由”。戴镏龄最后认为现代传记的发展趋向是:“用自由的心灵去探索人性,力求忠于事实”;“英雄崇拜的语气,颂扬劝惩的意念绝不能再欺骗作者和读者”;“保持一种适宜的简短,用最经济的篇幅,表达最繁复的人生”;“叙述紧张生动,前后起伏照应一脉相通,结构巧妙而谨严,读来津津有味,就赛如小说”,等等。可见,戴镏龄的论述始终是围绕传记的文学属性展开的。
戴镏龄发表《谈西洋传记》之后的第二年,寒曦也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现代传记的特征》*寒曦:《现代传记的特征》,《人物杂志》1948年第2期。一文,试图总结从史屈拉琪的《维多利亚名人传》开始的现代传记“共具”的特征。寒曦认为,现代传记的第一个特征是“绝对尊重事实”,“现代传记作者很少为了道德的成见,或尊重世俗的传统,而去隐瞒或歪曲事实”;第二个特征是“认识人性的复杂”, 现代传记作者“努力从各方面,各种矛盾的琐碎事实,试去表现一个复杂的活的真人物”; 第三个特征是“具有艺术的技巧”,“现代传记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本艺术的作品。现代传记家把诗歌小说图画戏剧,甚至电影的技巧都用之于传记的写作”。 寒曦最后表示,“在讣文一类文字非常流行,传记文学不够维多利亚时代水准的中国”,他希望前面总结的“这几点是可为我们借镜”。
与寒曦发表《现代传记的特征》的同时,湘渔(吴景崧)则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了题为《新史学与传记文学》*湘渔:《新史学与传记文学》,《中国建设》第1卷合订本,1948年。。在这近两万字的长文中,作者力图廓清的是新史学与传记文学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传记就其主要的性格讲,是历史的一个支庶,是文学的一个部门”,而在古代,传记和历史“是形迹不大容易区分的混合物”,如史诗“是古代作家对于英雄的歌颂,一种多少带些史迹的历史”,但史诗在歌颂英雄时也“无形中替那位主角,作了一个小传”。接着,作者依次辨析新史家和旧史家、历史家与传记家、传记家与小说家的不同。他认为历史家所写的“是这一人在历史戏剧中所演角色的动作”,而传记家所写的则是“那人的人格的形成”;传记家不同于小说家之点在于“小说家的主角,不必社会上实有其人,而传记家的主角,必然是社会中某一特有的人,而其言论行动,尤必须根据那一特有人的言论行动,符合于那一特有人的言论行动”。因此,湘渔特别强调:“传记家的最终目的,是在寻取真实,这正如科学家一样,而不仅是完成了某种审美的任务。”另外,他的文章还谈及传记的分类和资料的使用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汤钟琰的《论传记文学》对西方传记文学理论除了批判性接受之外,该文另一理论亮点是对于传记与传记文学的辨析。汤钟琰认为“传记原属历史的范畴”,后来“之所以把传记归之于文学”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古代历史与文学原无明显分野,写得好的文章一概名之曰文学,不独历史不独传记而已”。“第二是大部分的传记,多系出自文士的手笔。中国历代史官,均以文人充任,历史的研究并非他们的拿手(自然更谈不上史观);其所以连正史亦多以传记出之者,因为传记中易于插入主观的想象与描写,换言之,也就较为接近文学的创作”。“第三是自从新传记家如斯屈瑞基(Lytton Strachey)、卢特威奇(Emile Ludwig)等出现以后,……在传记中史实的叙述并不算十分重要,占首要地位的乃是个性的分析与描写。传记主角在某一个时候做了一桩什么事,这是历史家的笔法。但是,他为什么要做,在做这桩事的过程之中他所起的心理变化如何,这却需要文学家艺术的手腕。为了在心理上予以细腻的描写,传记家有时甚至不得不借重主观的想象。这就接近文学的创作了。”*汤钟琰:《论传记文学》,《东方杂志》1948年第8号。
最后,作为“大学丛书之二”,教育图书出版社于1947年出版了沈嵩华编著的《传记学概论》。这是一部全面吸纳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郑天挺等人的研究成果的系统著作,共含“传记之概念”、“传记之种类”、“传记之作法”和“中国之传记学”四章,主要从史学角度展开论述,但也兼及文学。但诚如编著者在《序》中所说:“在过去,关于传记的理论,虽有散篇的论述,但是有系统的著作,一直到现在,还未曾见,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界和文学界的一大缺陷。”*沈嵩华:《〈传记学概论〉序》,福州:教育图书出版社,1947年。所以,这一著作的出版无疑有一定的意义。而谈及“传记”一词的解释时,沈嵩华在追溯中外观念演变、论述个人与历史、英雄与历史等关系之后,引用克罗齐“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阐述了传记的“现代性”意义:
“真正的历史可说都是现代史,现代性,这一点,实是一切称为历史者的主要特征”,这是意大利史家克罗斯(B Croce)的名论。近来美国史家赫萧(Hcaens haw)也有“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话。这意思应用于历史中的伟人传记,更见其确切。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历史人物都是现代的人物,这种人物的事业是流传不朽的,言行足垂模范监戒,其人格历万古而常新的。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与现代生活有密切关系,尤其在当时有关民族兴衰的伟人,他们的言论思想事业人格,在现代民族生存上还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们的重要造就,永远保留着在其今日民族生活之中。(伟大的科学家与英雄,其精神且存在今日全世界人的生活中。)就“现代性”一点上说,传记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可以略窥见一斑了。*沈嵩华:《传记学概论》,福州:教育图书出版社,1947年,第4页。
总而言之,从20世纪初以来,上述作家、学者、批评家从不同的方面为传记文学的理论建构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晚年的梁启超潜心新学说、提倡新史学而属意“人的专史”,探索“专传”的书写,虽少了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激情,却多了学理思考的自觉。胡适的提倡和鼓吹以及对东西方传记特点的思考有开拓之功,郁达夫则以“文学”自觉从理论和创作展开切实工作。朱东润的探索深入而自成体系,充分体现其理论特征的《张居正大传》也以厚重的特色而别具一格。之后,学有专攻的许寿裳、郑天挺、孙毓棠、戴镏龄等人分别从历史或文学的不同角度,对传记和传记文学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充分体现出从作家到学者,从零星到系统,从历史到文学,从比较东西方传记差异到提倡传记文学,从探讨创作手法的思考到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流脉。而由“新史学”出发并一路走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建构虽未出现热烈繁荣的局面,出现震撼文坛学界的宏篇巨著,但他们的努力所彰显的探索精神,由相互碰撞所形成的思维成果,都已经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传记文学理论积淀,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
责任编辑:李宗刚
On the Development Stream of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Gu Yep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The theories and views in the researches on modern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MCBL) raised and advocated by Liang Qichao, Hushi and Zhu Dongrun have been more studied than those by Zhu Xiang, Xu Shoushang, Zheng Tianting, Sun Yutang, Dai Liuling, Shen Songhua and others, but the latter have not been paid due attention to. Since the scholars across generations approached MCBL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chools of theories have converged into a development stream made from writers to scholars, from fragments to systems, from history to literature, from differences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iography to the advocacy of biographic literature, from the discussions of creation devices to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CBL that arose from “new historiography”, though no prosperous scenes have emerged and no grand theories have been produced, the explorative spirit and speculative outcomes have, however,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ies of MCBL featured by the Chinese imprints and have always affected greatly its practice of cre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categorize the development stream and summarize the thought outcomes of MCBL of this historic period.
modern China,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theory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tream
2016-08-29
辜也平(1955— ),男,福建永春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06BZW055)的结项成果之一。
I207.5
A
1001-5973(2016)06-0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