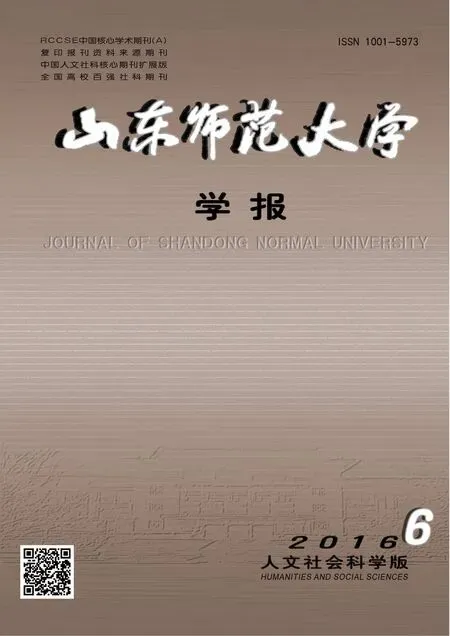河患、信仰与社会: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的历史考察*①
胡梦飞
(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252059 )
河患、信仰与社会: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的历史考察*①
胡梦飞
(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252059 )
漳河是流经华北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民间对漳河神的崇祀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水灾频发,对沿岸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危害;而漳河每次漫溢之后,所遗留下来的淤泥又使得当地农田成为丰腴之地,故沿岸民众既希望能够避其害,又盼望能够得其利。这种复杂的情绪和感情共同导致了河神信仰的盛行。河神信仰在保有祈雨、治水等传统职能的同时,其职能亦有所拓展。由信仰而衍生出来的庙会和祭祀活动在凝聚人心、社会教化、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河神信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成为“河流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典范。
清代;漳河下游地区;河患;河神信仰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11
中国是一个河流密布的国家,自古以来,河神信仰就极为发达。远古时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加上人们受其本身认知能力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限制,对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及现象怀有恐惧与敬畏意识,由此产生“万物有灵”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为自然崇拜,这其中就包括对山川、河流的崇拜。在各种河流崇拜中,莫过于对黄河河神的崇拜。广义上的河神泛指各种河流之神,黄河、运河、淮河、卫河等俱包括在内;狭义的河神则专指黄河河神。河神信仰则是指官方和民间对河神的观念和态度、相应的仪式制度、行为习惯和社会风俗以及崇祀活动等。河神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黄河的影响力及其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有关黄河河神信仰的研究,学界取得了大量成果,漳河、卫河等中小河流,由于其影响力远不及黄河,故相关成果尚不太多。本文以流经华北平原的海河支流漳河为视角,选择其河流下游地区为重点考察区域,在论述河神庙宇分布情况的同时,重在探讨河神信仰盛行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一、河川有灵:河神庙宇的地域分布
漳河,中国华北地区海河水系的南运河支流。上游由两河合一,一为清漳河,一为浊漳河,均发源于山西长治。其中清漳河发源于山西省和顺县境内,至涉县污犊村入河北省。由于流经地区多变质岩,泥沙含量不多,河水清澈,故名;浊漳河发源于山西省襄垣县,流经下马塔后进入河北省,流经地区多黄土丘陵,河水混浊,故名。两漳河在涉县合漳村汇合后称为漳河。下游作为界河,划分河北与河南两省边界,至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境内合流卫河,称漳卫河、卫运河。漳河流经三省四市21县市区,长约412公里,干流长179公里,流域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本文所指的漳河下游主要指漳河平原段,即现今涉县合漳村至馆陶徐万仓一线,地域范围主要包括现今漳河流经的涉县、磁县、临漳、大名、馆陶等地以及历史上受漳河河道变迁影响的曲周、成安、肥乡、邱县等地区。
漳河历史上的改道路径大致有三:其一是漳河北源与滏阳河合流,史称“北道”,大体自临漳,经广平至邱县,出威县西北,过新河县一线。其二是漳河南行与卫河合流,史称“南道”,故道大体自临漳、魏县、经大名、至馆陶一线,并在馆陶县以上入卫。其三是介于北道、南道之间的“中道”,大体自临漳,经肥乡、广平东北流,至冀县与滹沱河合流,再北流河间等地直达天津入海。从时间上看,走南道时间最长,从公元 1368~1942 年的 575 年间,有347年走南道。明初,漳河主要分两股,行中路和南路。中路自临漳、成安东北流,经肥乡、曲周而下,直达天津入海。南路由临漳东至成安注于魏县,再经元城 (今河北大名县境)之西店村(今大名县西北西店村)达馆陶入卫河。漳河起初中、 南两路并行,其后逐渐以南流为主*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永乐九年(1411年),漳河在张固村决口,与滏阳河合流,主行北路。*(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七《河渠志五·漳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0页。为接济运河水源,元代曾使漳河支流引入卫河以减其势,到了永乐年间已经堙塞,但是旧迹依然存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御史林廷举奏请引漳水由馆陶入卫河。*(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七《河渠志五·漳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1页。于是在广平大留村“发丁夫凿通,置闸”,自此“漳河水减,免居民患,而卫河水增,便漕”,自此“漳水遂通于卫”。*(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七《河渠志五·漳河》,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1页。此次漳卫合流是通过疏通永乐年间已经阻塞的旧河道,这便是明代“引漳入卫”的开始。正德初年,漳水“徙于元城之阎家渡入卫河,又十余年自魏县双井村入卫河。”*《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嘉靖初年,漳水“自回龙村入卫后,复自内黄县石村入卫河。”*(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镜纂:《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漳水入卫的地点不同,同时也证明了漳河“易迁徙”的特点。但到万历二年(1574年),“漳河北溢由魏县、成安、肥乡入曲周县之滏阳河,而馆陶之流绝。”*(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镜纂:《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万历初年,漳河又北徙入滏阳河,不再入卫。由此可见,明代漳河和卫河时分时合,北流的时间远多于南流。
清朝初年,政治局面尚未稳定,因此也无法修整运河。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漳水至广平县平固店直注邱县分为两道,“一从县西迳直隶广宗县下达于滹沱河,一从县东迳直隶清河县北支青县入于运河。”*(清)张度、邓希曾修,朱镜纂:《乾隆临清州志》卷二《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9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漳水再次入卫,此时自万历二年(1574年)漳水不再入卫已过去124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卫水微弱,粮运涩滞,乃堰漳河分溉民田之水,入卫济运。”*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0页。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卫河微弱,惟恃漳为灌输,由馆陶分流济运。”*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5页。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漳河“仍由馆陶入卫济运。”*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5页。从以上可以直接看出引漳入卫的目的是济运。康熙年间,因卫河水流微弱致使漕运难以进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济宁道张伯行建议 “引漳入运”,以补卫河水不足。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漳水“入邱之上流尽塞而全漳入于馆陶,自此漳、卫汇流,舟行顺利无胶涩虞”*赵尔巽:《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七《河渠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5页。,从而实现了“全漳入卫”。嗣后,漳河虽变迁不定,但一直在南道。1942年,漳河在河北省馆陶县徐万仓入卫至今,形成了现在漳、卫河合流的态势。
有关漳河神的崇拜由来已久。古都邺城在今临漳县境内,是 “河伯娶亲”和“西门豹治邺”故事的发生地。战国时期,魏国漳河年年泛滥,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的不幸。当地流行着一种恶俗:居民们每年都要向漳河神——河伯奉献一位年轻的女孩,给河伯当老婆,期望法力无边的河伯息雷霆之怒,不要用洪水残害人民。后来,漳河边来了一位贤明的地方官西门豹,他了解了河伯娶亲的真相后,就设计把那批鱼肉百姓的乡绅、里正统统扔到河里,并带领当地居民兴修水利,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王迎喜:《安阳通史》(原始社会-1949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6页河北沙河市境内有“漳河神坛碑”。碑文记载河南修武县人张导,字景明,东汉建安三年(198年)为钜鹿太守。时漳河泛滥,民不能耕,导按地图原其逆顺,揆其表里,修防排通,以正水路。水患既绝,人寿年丰。黎民于铜马祠侧建漳河神坛碑,以志其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4页。可见,清代漳河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盛行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嘉庆《涉县志》记载涉县漳河神庙:“在南关,始建无考,乾隆元年重修,以六月二十四日祭。别有庙在原曲村,明万历间建,任令澄清记。”*(清)戚学标纂修:《嘉庆〈涉县志〉》卷三《政典祀典》,《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40页。咸丰《大名府志》记载大名府河神庙在府治南关陲高岸上,即艾家口,咸丰元年,道、府、县捐资重修,漳、卫龙神合祀。*(清)朱煐等纂修:《咸丰〈大名府志〉》卷六《秩祀》,《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5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魏县漳神庙在县城东郭外。*(清)朱煐等纂修:《咸丰〈大名府志〉》卷六《秩祀》,《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5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光绪《临漳县志》记载临漳县漳河神庙:“在南关外,同治七年,直线骆文光重修,旧地五亩,知县陈大玠新充西太平村河地一顷八十亩,又附县四关厢官地四十七亩三分三毫以供香火。”*(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二《建置·祠祀》,《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清人王履泰《畿辅安澜志》记载成安县漳河神庙:“在县城外东南河滨,顺治十一年,知县张一霆建,康熙十一年重建。”*(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8页。曲周县漳、滏二神祠:“在曲周县东东桥南河畔。”*(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8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8页。民国《肥乡县志》记载肥乡县漳河庙:“在城北堤上,耆善修庙三楹,知县王建中增修墙壁。”*张仁侃等修,李国铎等纂:《民国〈肥乡县志〉》卷十八《坛祠》,《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2页。雍正《馆陶县志》记载馆陶漳神庙:“在城西南四十里,雍正四年,奉旨敕封为惠济漳河之神,知县赵知希设立牌位,悬挂匾额,每年春秋致祭,行礼如制。”*(清)赵知希纂修:《雍正〈馆陶县志〉》卷八《祀典志·祠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90页。民国《邱县志》记载邱县漳河神庙:“在北极庙后,康熙四十五年,知县杨兆亿鼎建。”*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十三《地理志·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
关于漳河神的人物原型,说法不一。通观相关史料,主要有张果老、女娃、汜水孙孝廉三种说法。山西沁县漳源村漳河神庙,又称通玄先生庙,供奉的是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长治发鸠山灵湫庙供奉的漳河神则为女娃。发鸠山位于长治市长子县城西30公里处的玉峡乡。也名“西山”,海拔1646.8米,相传为精卫填海的故事发生地。据《山海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谈。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女娃死后,被百姓奉为漳河神,并在发鸠山上修建了灵湫庙。对联上写着:女娃理水,经南纬北,神泉汇集高灵渊。漳源泻碧,西流东注,灌溉上党万顷田。*《漳泽水库志》编纂委员会:《漳泽水库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漳源村和发鸠山都位于漳河上游,庙宇建立年代较为久远,承载着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民众多对其进行演绎和改造,故充满浓厚的神话和传说色彩。而临漳县漳河神庙建立时间相对较晚,故其人格神的形象更为突出。临漳知县骆文光在《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中对临漳县漳河神庙中所供漳河之神做了记载:“世传乾隆间,有汜水孙孝廉,北上渡河,没于漳水,遂为兹川之神。”*(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59页。
二、利害相关:河神信仰盛行的原因
南宋初年,黄河夺淮入海以后,在华北平原留下了高出地面的黄河故道,加之漳河含沙量大,将淀泊淤成平陆,河水盛涨,泄水受阻,至使漳河经常泛滥成灾而不可制约。漳河历代迁徙无常,明清时期, 有史料可考的河流改道就达近80次, 平均6-7年就会发生一次变迁。*石超艺:《明清时期漳河平原段的河道变迁及其与“引漳济运”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清顺治九年(1652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242年间,漳河泛滥成灾40次,平均约6年一次。人们称之为“桀骜不训的漳河”。以水患最为严重的临漳县为例,明代临漳县之漳河或入滏河,或入卫河,而无衡定。漳水屡临城下,为害更甚。此时漳河经彰德府北、临漳城南(落村、岗陵城)流人魏县界,分为二股:一股经馆陶,注入卫运河,另一股在魏县大名之间,与西南流来的汲水合流。明洪武十八年,漳水冲毁县城(今杜村乡小庄);洪武二十七年,移县治于理王村(今临漳)。永乐九年,在西南张固村河口(今杜村乡西营西南约三里处),漳滏合流;十三年,漳滏并泛。洪熙元年,漳河决三冢村等堤(宣德八年,复筑此堤)。正德元年,漳滏泛溢,决杜村西南堤。隆庆二十五年秋,漳河北徙;三十年,漳河又西徙。英宗时,漳河已通卫。后来漳水复入新滏河。自此,漳河入卫之道渐渐湮没。*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漳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6页。
清代,漳河迁决频繁,为害不息。顺治五年,漳河发二次,环城数十里,城门淹没五尺;九年,漳河又发,水与城门齐,淹田11万亩;十一年,大水冲入西门,环城皆水,房屋尽毁;十三年,雨水连绵,漳河泛滥,城中搭浮桥往来。康熙七年,漳河泛溢,冲田2700亩;五十九年,漳河自距城三里的坊表村西,再次南迁,向东流经杜成营北、羊羔北、成安县徐村南、说法台(今成安南)南,至馆陶入卫河;六十一年七月初三日,漳河暴发,水泛溢,城中可行舟。雍正元年,漳河徙城北,二年、三年,漳河屡徙;八年,漳河屡临城下,又再次迁到城南;分二股,一股沿康熙五十九年河道而下,另一股自三冢村经武学、赵坦寨、王明寨、岗陵城、七里营、西羊羔南、五岔口北,至成安町上村,于馆陶李鸭窝,注入卫运河。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次入城;四十六年,漳河决小柏鹤村;五十四年,漳河自铜雀台南分支,经韩陵山南与洹水同入运河;五十八年,漳河大徙,复归故道(雍正年问);五十九年,漳河决三台,向东南迁,至胡家口入洹水。道光三年,漳河决商家村,经大楼王西、沙河岸南,于胡家口流至内黄庆丰庄入卫河。十四年,漳河决三宗庙;二十三年,漳河决段汪村,三十年,再决三宗庙,流经杜村庄南、曹村庄北、孙陶庄西南、教书屯东北,于胡家口入安阳界。咸丰元年、二年,漳河两次决口三宗庙东流。光绪十二年,漳河决二分庄,十八年,漳河东流决于辛庄;光绪二十一年,漳河再决二分庄,经张小庄南,后佛屯北,砚瓦台南,从老庄南,都村北,入魏县界。*河北省临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漳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6页。
自万历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漳河以“北流”为主,流经邱县境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漳水骤至馆陶与卫河会。此后,北流渐微。虽然起初南、北、中三路并行,但此后逐渐转为以南流为主,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全漳入卫。民国《邱县志》记载漳河:“自万历四年,出御河(即卫河)入滏阳,遂为曲梁东关巨浸。虽泛滥无常,旋而归壑。迄康熙三十一年,遂出滏阳东泛,全漳尽徙邱境。”漳河故道主要有两条:“一自直隶曲周村,北经邱县西门外,西北至宋八疃,入直隶曲周界;一自曲周县南堤村,经邱东门外盛水湾,即黄河故道,北至柳疃,入直隶清河界。”漳河的流经,亦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水患。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漳水大溢,啮城门尽颓,麦田漂没,岁大饥。”*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0页。次年秋,“漳水复溢,平地水深丈许,陆地行舟。”*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0页。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六月十三日,“漳水自成安县决口,直奔邱城,水环城北下,西北五十余村,田禾庐舍,漂没无算。”*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0页。次年六月初三日,“漳水自决口大至,故道湮淤,全河注邱,西北田庐,漂没殆尽,只禾无存,人民逃散。”*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0页。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漳水盛发,绕城,漂没房舍,没尽秋禾。”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五月,“漳河泛溢,盛永等五营尽被水患。”*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1页。次年,漳水再次决堤,“胜永等五营平地水深数尺,田庐漂没,禾稼无存。”*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九《大事志·灾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61页。
漳、卫二河在馆陶县(县治在今冠县北馆陶镇)境内合流,同样是水患极为严重的地区。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在其《闸河日记》中记载:“壬辰(道光十二年)春,予北上,迂道存翰风于馆陶署。翰风言境内漳神庙,乃直隶、河南、山东三省轮奉旨致祭之大祠。今年庙断不可守,吾子当有法止其冲塌,已具舆马,请前往相度之。庙去城三十里,予至庙,询住持,云:‘漳去庙前旧有二百丈,今山门前仅容一车,大约入夏必圮矣。’予见直庙门二十余 丈外,河心有砖墩,周围四五十丈,乃本庙戏台被冲入水,已三十年。”馆陶漳河神庙位于城南四十里漳河岸边,因常年为漳水所冲击,以至面临倾圮的危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漳河水灾的严重性。*谭其骧:《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4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47页。
“灾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并通过社会实践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汪汉忠:《从水旱灾害对苏北区域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看水利的作用》,《江苏水利》2003年第3期。频繁发生的水灾无疑是导致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借助神灵之力镇摄、平息水患,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成为沿岸地区官民信仰河神的根本目的。临漳知县骆文光在其《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中云:“漳河,冀豫间一巨浸也,溯其源来自太行山右,汇清、浊二流,东至旧闸口。闸以上,山石夹护,虽湍流迅激,不能为害。自雀台以下一带,平原旷野,夏月水势涨发,汹涌异常。往往淹及田畴,甚且为城郭、村墟之患。而临之民处漳下游,耕凿为业者,独能当横流而不惊,集中泽而无虞,非有神明为之呵护乎 ? ……能捍大灾、御大患,是即有功德于民者,固宜列入祀典也。”*(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59页。
频发的水灾不是导致河神信仰盛行的唯一原因,人们在受其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其利。雍正《馆陶县志》记载:“漳河南徙于康熙四十二年、五十年、六十一年间为灾为甚,怀襄之势居然水国矣。今则其势少驯,每逢天雨连绵,矣间有泛滥之忧,但漳水性浑浊,与黄河无异,随挖随淤,且其中冲溜无定,难施疏凿之功,至设立闸座启闭,恐一淤又复他道矣。且漳水南徙,民忧漳水之淹,而亦甚德漳水之淤。盖漳水所过薄地,尽膏其为利,亦复甚普也。”*(清)赵知希纂修:《雍正〈馆陶县志〉》卷八《地理志·山川》,《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8页。漳河在临漳的利和害,历史上评论不一。古人褒者,说漳河为“富漳”,斥者则称其为“浪漳”。历史上改道之害繁多,数百年中,受其害者不仅有县城,而且有数百个村庄。光绪《临漳县志》载有杜念祖的《漳干行》,就具体叙述了漳河之害:“滔滔漳流不计年,形势变更几万千。春日清波鱼可数,入夏万顷尽茫然。浊浪无边平地涌,禾没奚从辨陌阡。水耕火耨前功弃,家家向隅呼苍天。水退潮平波犹怒,数里折湾直奔注。地裂岸崩不须臾,沃壤尽作冯夷路。”*(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诗》,《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05页。然而在同一县志中,同是身居漳河边的吕游(烟寨人)与李泽兰(常家屯人),则言漳水之利。因杜念祖是被洪水冲淹之村,而烟寨与常家屯,则是漫水淤泥之村,故评论不一也。西门豹治邺时,投巫开渠,利用漳水溉田,以利民生,未言及河害之大。周、秦时代,漳河经邺城北,注入黄河故道。当其暴涨时,临漳是漫溢之区,故既可开渠,又受淤泥之惠。西门豹、史起治邺,政清物阜,为邺城之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二贤令之功与漳水之利昭然。由于民殷物阜、经济优裕,随着发展,邺地由军事重地,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朝发祥地在商丘,而曾多次迁居。其中有河直甲居相,相址,在今孙陶镇。古人在游牧时期,逐水草而居。转为农耕,则是选择肥沃之地域定居。河宜甲居相,则因相地肥沃,适合耕牧之故。商代,漳河流经九侯城(今邺镇附近)北、今临漳北、成安南,至肥乡注入黄河故道,临漳正是漫溢之区。顺治时,知县万廷仕《修建漳河神祠碑记》中记载此地是大河以北之膏壤,民殷土沃。*(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37页。雍正时,陈大玠《福惠渠记》中亦言:“邑城自旧县移建于兹,几四百年矣。漳水忽北忽南绕四围,退则泥淤积岁月而成膏壤。”*(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46页。民国时期,漳河两岸在未筑堤之前,每有漫溢,翌年二麦(大麦,小麦)必然丰收。但秋季常有水灾,轻重不一,故两岸居民,喜种高粱,不惶水淹,以防歉收。纵论漳河,以往言害者多,而忘其利,更忽略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影响。
三、乡土神灵:河神信仰的功能及影响
利用祈祷和祭祀河神平息水患、祈求降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看来,这也是河神最为基本的职能。受史料的限制,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较少,但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漳河河神作为沿岸官民心目中的乡土神灵,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地方保护神的角色。同治八年(1870年),敕加河南临漳县漳河神“昭惠”封号。*(清)昆冈:《清定大清会典事例》,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第10955页。光绪《临漳县志》记载了加封漳河神的原因:“同治二年,山东会匪自范、观扰至临境,及渡漳,人马淹没过半,势以孱削。同治七年正月,捻匪北窜,扰及临境,从九王毓莹等率乡勇迎敌阵亡,同时死者男女共四百余人,及匪渡漳,覆溺贼骑无数,几断流。抚部院李具题八年六月初二日,奉旨敕加河神‘昭惠’封号,并颁赐‘双源汇泽’匾额。”知县骆文光《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对此记载更为详细:“同治二年秋,山左会匪由范、观等县进窜临境,蚁聚者三四千人,比渡河,覆溺无算。(同治)七年正月,(骆)文光宰是邑,皖捻北窜,时正水浅可涉,先二日上游忽暗涨,溺毙者几至断流。二月杪,贼又回窜,官军、民团拒至河干,忽水复漫溢,歼毙以千计。嗣积雨连绵,流势倏分数道,向东北奔注,一似蹑迹追踪 ,驱令入海隅。俾戎事得以合团成捷,神之灵佑昭著,不特临境蒙其庥,即豫疆亦因之巩固。军事竣,文光禀陈、李抚帅,蒙奏准敕加昭惠封号,颁给‘双源汇泽’匾额。呜呼!圣世崇德报功,祀汉祭淮,列在巨典,神之功配四渎得荷,褒荣尤足,传之史笔,炳曜鸿文,而为临民所永仰也!”*(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59页。
崇祀河神在凝聚人心、社会教化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沟通国家和民众的桥梁,地方官员把修建庙宇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内容。临漳知县万廷仕《修建漳河神祠碑记》云:“今年春,余承乏兹土,莅治甫阅月,邑人有南郭庙事之举,立碑致享,问序于余。余以受命漳邑,则漳神之妥侑与社稷等分不容辞,又惧荒略不克,道扬其盛。窃念漳之为利,亿万斯年,民殷土沃,生生有庸,邀神之惠,匪朝伊夕;其频岁以来,荡析离居,罔有定止,岂神之怒。此一方抑或守土者不修政事,不蠲祀享,致神之恫,以贻毒百姓。”身为临漳知县的万廷仕在《碑记》中认为修建神灵庙宇是地方官员的份内之事,为的是能够保佑当地“民殷土沃”,而如果守土者“不修政事,不蠲祀享”,就会招致神灵的愤怒,给百姓带来危害,以致“荡析离居,罔有定止。”*(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上》,《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37页。
漳河与沿岸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河神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共同修建庙宇、祭祀神灵等活动,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强化地域认同、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目的。骆文光《重修临漳县漳河神庙碑记》载:“逮庚午秋,工告成,邑民来与会者不下二万众,文光因倡议,以每年九月九日兴会半月,五年缮整庙宇一次,其一切献牲、演剧、修葺之需,均按沿河四十庄派费,载在规约。庶几岁修有例,而庙貌常新,勉厥同人缵承无舛。至管键庙门,向由住持僧职掌,尤虑玩忽从事,或致庭除芜秽,今议仿西史大夫祠,亦设义学于庙之东厢,取赡书院地租,延师授读。选邑中端谨士,昕夕在庙,兼察住持勤惰。凡此,皆所以崇神烈,隆祀典,而令邑之黎元蒸蒸向化,知乐利所由来也。”*(清)周秉彝修,周寿年、李燿中纂:《光绪〈临漳县志〉》卷十四《艺文·记下》,《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5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459页。为此,还专门制定了《漳河神庙秋报会规约》:“每年九月九日庙会,派城乡绅士四人,本城四街殷实铺家四人并库吏、钱粮房、漕粮房、银炉四人,共十二人为会首,总理一切;每保派首户二人,每营派首户一人,分四路挨日赴庙献供行礼,会首接待茶饭”。“漳河神为一邑保障,万民蒙福,各保各营遇丰年愿扮杂剧来献者,听;所派香资不准摊及小户,至每保、每营派定首户,不亲赴庙行礼,即以不敬论,罚钱十千文。东南乡漳河两岸过水之地,既蒙神佑,每逢麦收,一顷以上之户,每亩捐麦一升,先由督催于九月会中报明地数,注入捐簿,至次年五月,如数催收交仓,四路督催亦准预会。……漳河变迁靡常,设遇漳水改流,有穷民淹没田庐、被灾较重者,酌提谷麦若干石,代神赈济;功德无量,赫赫在上,监观不爽,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该首等能多尽一分心力,即多获一分善报,试看吞公项、霸祠产、吃庙地者,其人果何如哉,可不勉欤!”*(清)骆文光:《同治〈河南省临漳县志略备考〉》,《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0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69-72页。《规约》对庙会的经费来源及组织、运作做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可见当地官民对漳河神庙会的重视程度。除临漳县外,邱县、肥乡等地亦有祭祀漳河神的庙会。邱县漳神庙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知县杨兆亿所建,每年六月十日当地都会举行漳河神庙会,演剧祭赛漳河神。*薛儒华修,赵又杨纂:《民国〈邱县志〉》卷十三《风俗志·岁时礼节》,《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6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肥乡漳神庙在城北堤上,每年六月二十四日这一天,当地亦有庙会。*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646页。
河神庙宇还成为当地著名的文化景观。成安县清风观约建于1930年左右,县志记述其沿革规模,清晰易懂,全文摘录如下:“清风观在邑城东南隅,隔堤有高地一区,古漳神庙在焉。前邑侯高公景祺,资其地凿井种树,标为农事试验场者也。惜不久庙遂倾圯,近邑绅赵召南王绍平请人,以保存古迹之心,怀恢复名胜之志,醵金修葺,以关圣吕祖与漳神,合记一堂,名之日清风观。虽规模隘小,不能与平津各大公园并衡,然每当城关集会期间,亦仕女遨游之佳境也。”*成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安县文史资料》(第1辑),1989年,第43-44页。
四、结语
河神信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与官方治河活动密不可分,也与沿岸民生息息相关。从相关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漳河下游频发的水灾是导致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人们希冀从漳河漫溢中得到利益,这一点原因同样不容忽视。河神庙宇不仅为官方所敕封,也成为地方官员和民众祭祀河神、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场所。
与黄河、运河不同,漳河作为一条区域性河流,虽然在清代有过敕封,但远没有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白大王等黄、运河神有名,故其官方史料中记载相对较少。相比江南、珠江三角洲以及运河沿岸等地区,漳河下游地区地处华北平原一隅,较少被学界所关注。地方性和世俗性是漳河下游地区河神信仰最为显著的特征。
随着近年来“水利共同体”、“河流共同体”等概念的提出,对河神信仰这一社会生态命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河流是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有水和水的载体,还有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它们可以统称为河流共同体。”*张纯成:《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8页。“人类与河流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河流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雷毅:《河流的价值与伦理》,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在传统伦理学那里,人是河流的主人,河流是人的奴隶,人与河流之间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河流伦理的构建,使人从河流的征服者转变成河流共同体的普通一员,和其他成员相比,人没有什么高贵特别之处,有的只是平等和普通。这不仅意味着人类应该尊重包括人在内的河流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也意味着人类没有任何特权凌驾于河流共同体其他成员之上。”*张纯成:《现代黄河文明及其生态补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8页。
“河流的生命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活动,应遵循发现、尊重和顺应河流自身规律的法则。”*李宗新、李贵宝:《水文化大众读本》,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第149页。古人对河神的敬畏和信仰,正是河流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沿岸地区河神信仰的考察,在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也为我们处理人地关系、探讨区域社会生态和民众心理提供了重要视角。
责任编辑:时晓红
Floods, Religion and Society: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igion of River God at the Lower Reaches of Zhang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Hu Mengfei
(Institute of Canal Studi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Zhang River is an important river flowing through North China, and the worship of the God of Zhang River is a tradition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lower reaches of Zhang River flooded frequently in the Qing Dynasty, bringing serious harm to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living along the both banks; and after each overflow of Zhang River, the sludge remained made the local farmland rich and fertile, so the people living along the banks wanted to avoid its harm, and hoped to get its benefit. This complicated emotion and feeling together l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religion of river god. The religion retained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praying for rain and controlling wa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anded its functions. Temple festivals and sacrificial rites, which were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unifying public feelings, educating the society, and maintaining the local social orders and so on. The religion of river god wa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model of the theory of “river community”.
the Qing Dynasty; the lower reaches of Zhang River; floods; religion of river god
2016-11-06
胡梦飞(1985— ),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博士。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民间信仰研究”(16DLSJ07)、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金龙四大王信仰研究”(321051519)的阶段性成果。
K24
A
1001-5973(2016)06-012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