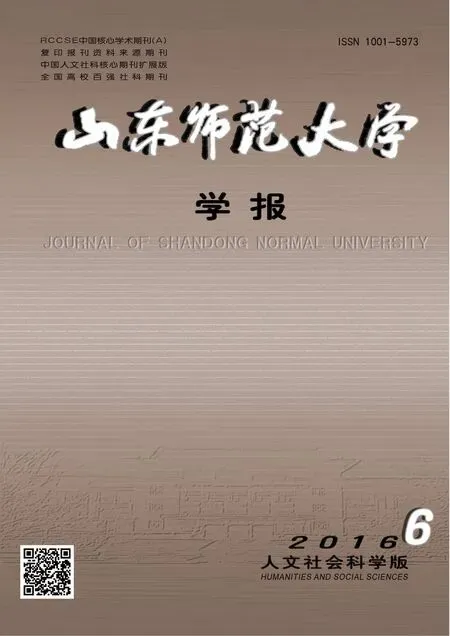生成整体论视角下词义组合同化的认知分析*
施晓风
(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3;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100 )
生成整体论视角下词义组合同化的认知分析*
施晓风
(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3;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250100 )
对由于组合同化而造成的词义感染的研究,是根据词所在的语言单位或语言环境来考察词义衍生途径的新方法,突破了在单个词义系统内部孤立地研究词义演变的传统。词义感染与词义引申的主要区别在于词义的共时演变与历时演变的不同,而其产生的原因是受到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影响,词义在与之关系更近的小语境中,受到相邻义位的同化而产生了感染义。词义感染与缩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二者都是基于整体论的视角,但不同的是词义感染是词与词之间词义内部互动进而造成语义同化与形式脱落,而缩略不存在词义内部的同化,仅是用省略的词形来表示整体义。前辈学者提出判定词义感染的历史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结合中古词汇“赴救”、“赏募”和“典藏”三个例词,我们从生成整体论视角提出另一种基于常规关系的习用组合原则。
生成整体论;组合同化;词义感染;词义引申;缩略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发现“词义感染”(也叫“词义沾染”)是古汉语词义衍生的一种特殊途径,并明确把“沾染义”作为词义的一种,如杨琳(2015)提出:“一个词所具有的意义从发生学的角度可分为四种类型,即本义,引申义,寄生义,沾染义。”*①杨琳:《论相邻引申》,《古汉语研究》2015年第4期。在把组合与聚合关系对词义的不同影响区分开之后,围绕因组合而发生的词义同化问题的争议,一方面集中在合理化例证上,另一方面集中在与词义引申的区别上;此外,有些学者还注意到词义感染与缩略在形式上的相似性,如伍铁平(1984)、俞理明(2005)、唐子恒(2006)、董志翘(2009)等,但均没有展开深入讨论。本文试图在生成整体论的视角下对组合同化所面临的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探讨,揭示词义组合同化的本质。
一、词义感染与词义引申的区别
所谓“词义感染”,也称“词义组合同化”,是指在古汉语中,两个意义不同的词经常连用,其中一个词可能受另一个的影响而具有另一个词所表示的意义。比如“夏屋”表示大屋,经常使用,战国以后“夏”受“屋”的感染而产生了大屋义。由于“魏阙”常用的缘故,战国以后“魏”受“阙”的感染也用来指观阙。由于“眷顾”经常使用,所以汉代以后“眷”受“顾”的感染产生了回视义。*②邓明:《古汉语词义感染例析》,《语文研究》1997年第1期。其实,词义感染(semantic contagion)不只在汉语中存在,它也是其他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两种或几种互相接触的语言之间也可能会发生。*③伍铁平:《词义的感染》,《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早在1933年,布龙菲尔德就在法语里发现了词义感染现象。*④[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2页。
(一)词义感染的例证引发的质疑
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词义感染的现象,有的明确提出词义感染或类似的概念,有的则只分析了例证,现择举如下:
伍铁平(1984):“然”因“然而”组合而感染转折连词的用法。
孙雍长(1985)(称为词义渗透):“字”因“文字”而生修饰义;“以”因“所以”组合而生“所”的指代义;“且”因“且夫”组合而生“夫”的指代义。*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中国语文》1985年第3期。
柳士镇(1992):“等”因“何等”连用而丧失实义,同“何”结合作疑问代词,表“什么”。*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
朱庆之(1992)(称为词义沾染):“如”因“何如/如何”组合而感染“何”义。*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205页。
高守纲(1994):“漪”因“涟漪”组合而感染微波义;“觉”因“睡觉”组合而感染睡眠义。*高守纲:《古代汉语词义通论》,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张显成(1995):“产”因“产生”组合而感染“生、活、鲜”等义。*张显成:《“产”有“生、活、鲜”义——浅谈词义的“感染”》,《文史知识》1995年第2期。
张博(1999):“箕”因“箕踞”组合而感染踞义;“胼”因“胼胝”而感染老茧义; “揖”因“揖让”感染推让义;“盗”因“盗贼”感染劫杀义;“贼”因“盗贼”感染私窃义;“暴”因“暴炙”感染火烤义;“炙”因“暴炙”感染日晒义。*张博:《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
邓明(2001):“糟”因“糟粕”感染酒滓义;“弹”因“弹丸”感染弹丸义;“安”因“安置”感染安放、放置义;“颜”因“颜色”感染色彩义;“涕”因“涕泗、涕洟”感染鼻涕义。*邓明:《古汉语词义感染补证》,《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2期。
苏宝荣(2006)(称为语义偏移):“畏”因“敬畏”而产生敬服义;“寒”因“贫寒”而产生贫义。*苏宝荣:《“隐喻类比”与“近义偏移”——谈汉语多义词形成的两种主要途径》,《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
席嘉(2006):“要”因“若要”而感染假设连词用法;“然”因“虽然或然虽”而生让步连词用法;“还”因“若还”而生假设连词用法。*席嘉:《与“组合同化”相关的几个连词演化的考察》,《语言研究》2006年第3期。
董志翘(2009):“如是”因“如是不久”而生不久义。*董志翘:《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胡敕瑞(2010):“塘”因“池塘”而生池义;“所”因“尔所”而生指示代词用法。*胡敕瑞:《组合、聚合关系与词义的衍生及阐释》,《汉语史学报》第十辑。
袁嘉(2012):“犹”因“犹如”而生连词“如”的用法;“为”因“因为”而生表因为的连词用法。*袁嘉:《语法意义的感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
杨琳(2015)(称为沾染):“侃”因“侃侃而谈、侃侃言说”而生言说义。*杨琳:《论相邻引申》,《古汉语研究》2015年第4期。
学者们提出的例证有的受到了质疑。比如,李宗江(1999)认为邓明所释由于“吉祥”的频繁使用,“祥”受“吉”的感染而具有了吉利义,是不可信的,其实“祥”本义“预兆”,包括吉和凶,后只表“吉兆”,是词义缩小。*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第21页。徐之明(2001)也对张博的很多例证提出怀疑,认为“蚕”表侵蚀义只是“出于修辞需要的临时性用法”,“习”早在“学习”组合之前就已具“学”义,“削”表弱也产生于“削弱”组合之前,此外,“审”因“审问”感染审问、询问义,“道”因“知道”感染知义,“息”因“消息”感染消义也都值得怀疑。*徐之明:《“组合同化”说献疑──与张博同志商榷》,《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董志翘(2009)对朱庆之的很多例证表示不认同,认为“念”因“爱念”感染爱、怜义,“照”因“照明”感染清楚、明白、知晓义,“哀”因“悲哀”感染动听义,“方”因“方便”感染方法、谋略义,以及“呼”因“呼请”感染请、谓义等皆将引申义误认为是感染义,所说的词义沾染其实是同义复用。*董志翘:《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俞理明(2005)指出:“‘感染’说立足于共时的基础,从意义的关联来说,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对于一种历时的变化来说,这种解释没有分清因果或源流,也未能恰当地描述变化的过程和动因,存在明显的不足。”*俞理明:《汉语缩略研究——缩略:语言符号的再符号化》,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298页。贝罗贝(2008)和董志翘(2009)也都曾指出,“(词义沾染)确实可解释一些不是‘引申’和‘假借’可以说明的词义衍生现象”,但词义沾染缺少对文献的广泛调查,及对词义系统本身的深入考察和梳理,因此要“首先关注演变的内在力量,而慎言外部力量的沾染或类推”。*贝罗贝:《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沈阳、冯胜利:《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页。
(二)从产生原因看词义感染与词义引申的区别
对组合同化所造成词义感染现象产生原因的解释,前辈学者有的认为是由于语义的类推机制,如罗积勇(1989)认为“毗邻相因义的产生也是基于一种语义上的类推”,而关于类推的原因,他认为是思维定势造成的,不能简单地用语义亲密度来解释。*罗积勇:《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与罗积勇的观点不同,张博(1999)认为语义类推的深层原因是受到同义并列组合的影响,因为“同义连用在古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占有“强势地位”。胡敕瑞(2010)也持此观点。邓明(2006)认为词义感染产生的原因是词义或语法关系的模糊,词义隐遁或语法功能的弱化。*邓明:《古汉语词义感染综论》,《语文研究》2006年第2期。伍铁平(1984)认为这是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用一个词表示原来用一个词组才能表示的意义,这正是词义感染现象用得越来越多的内部原因。唐子恒(2006)也持经济性原则这一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我们认为还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1.词义感染受到汉语双音化的影响
经研究发现,词义感染发生的时间与汉语复音化的时间基本吻合,尤其多见于双音节词大量产生的中古时期前后。朱庆之(1992)曾认为词义沾染是“中古汉语词义演变的一个主要方式”*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96页。。先秦时,单音节词的引申多依赖于大语境,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事物不断增多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大语境)下,单音节词基于自身词义系统内部与语境的切合点而发生词义的引申。在双音节词应运而生的过程中,原来独立运用的单音节词除了大语境,还受到与之关系更为紧密的小语境(即词所在的句法结构形式)的制约,受小语境的影响,与跟它搭配组成句法结构的词产生义位上的互动关系,进而发生词义的感染。就像胡敕瑞(2010)所说,造成词义衍生的因素有很多,除了词义内部的引申,还应考虑到语境和结构关系的影响。*胡敕瑞:《组合、聚合关系与词义的衍生及阐释》,王云路:《汉语史学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0辑。杨琳(2015)则指出:“沾染义与引申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基于词的既有意义派生出来的,而前者则是受词的组合体的沾染而产生的,其形成与词的既有意义无直接关系。”*杨琳:《论相邻引申》,《古汉语研究》2015年第4期。
2.词义组合同化是一种词义的共时演变
高名凯(1995)指出:“我们既要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观察语言,也要从语言在历史某一时期中的相对的静止状态来观察语言的系统。”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中的个别现象的演变,语义在言语中的变化称为“共时性的语义变化”,这种变化是一种临时的“创新”,具有一定的主观因素。*高名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5页。张志毅(2005)认为:“义位受到聚合和组合纵横坐标的多项多种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差异性的制约”,“共时性变化(synchronic changes)一般是言语的组合的语流义变,其结果多是义位变体的产生或义素的消失,这属于线性变化模型内”*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5、263页。组合关系,是动态语义组合,是指在语流中各个语义成分通过前后连接而形成的关系,韩礼德称之为“搭配”。波尔希的句法场理论也是建立在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基础上,指出一些词经常和另一些词连用,词与词之间就会发生经常性的语义关联。*陈建生:《词汇范畴理论探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6期。在线性义场中产生的新义位,多数是伙伴间的语义感染。*倪波、顾柏林:《俄语语义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
传统语言文字往往更重视从历时的角度沿着词义本身引申发展的途径进行研究,而往往忽视共时层面所形成的组合关系的影响。词义的组合同化不同于词义的历时演变,它更倾向于横向组合关系中词义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人们如何利用动态言语环境和认知信息来补充语义。*徐盛桓:《认知语用学研究论纲》,《外语教学》2007年第 3期。所以说,它是词义演变的一种特殊途径,是一种词义偏移。这种偏移的词义其实是语用推理的结果,也被称为“言语义”或“用法义”*赵克勤:《古代汉语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72页。,与词义的纵向引申有本质的不同。制约词义偏离的语境因素,最直接的就是相邻词语的搭配关系,汉语史上的词类活用就是典型的共时语言现象。词义感染同样也受到语境的制约和影响,发生浮动变异,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的感染义或活用义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使用,即成为该词的一种固定用法,而有的则没有最终固定下来。
词义感染与词义引申之所以相混,是因为二者都是应语境需要或受语境影响而滋生出新义位。不同的是,引申之后的新义位在与别的词组合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但感染由于受到组合体整体语义的强势影响,所以被同化的词,能单独表感染义,却不能自由地与其他词组合,其组合形式受到原组合体的制约。
二、词义感染与缩略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一)词义感染与缩略形式上的混同
词义感染与缩略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伍铁平(1984)在分析词义感染的常见组合时指出,除了在“形+名”组合中名词容易获得意义外,“名词+介词+名词”的组合也可能紧缩为“介词十名词”,并获得原来由整个词组表达的意义,并指出这种词义感染与词义紧缩和略语形式相似。*伍铁平:《词义的感染》,《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董志翘(2009)在举汉译佛典中“如是不久”的组合使“如是”沾染“不久”之义时,对“到底是‘如是’发生类化,还是‘如是不久’的缩略形式”这个问题也存有疑惑。*董志翘:《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首先,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来看,二者确有其相似性。词义感染是以双音节组合(也有多音节的情况)中的一个词单独运用表示与另一词相同的意思为标准的,如果着眼于被省略的那个词,词义感染伴随的状态很像是缩略。而缩略是从一个词语中选用部分形式来表示这个词语的整体意义,形式上二者都发生了词形的省略。
其次,从生成整体论来看,二者都着眼于整体语义观。生成整体论是认知语用学研究的一种当代形态*吴炳章:《生成整体论:语用学研究的新范式》,《外语学刊》2008年第3期。,从认知视角进行语用研究,会比较注意从话语的整体去把握话语的信息,将语言的意义和人的涉身经验联系在一起,不管是时间上前后相继,还是空间上彼此相接,亦或是顺序、序列上彼此接续的两个相邻的对象,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整体性感知效应都将其表征为一个整体。词义感染与缩略都是基于整体语义感知所发生的形义变化。生成整体论的语言观将交际的意向性、语言的互动性和意义的生成性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认为只有在语言单位的整体功能和目标下才能准确揭示其构成要素的性质。*吴炳章:《常规关系和语言使用——徐盛桓基于常规关系的语用学理论概述》,束定芳:《语言研究的语用和认知视角——贺徐盛桓先生70华诞》,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7页。这就较好地解释了感染义的生成与缩略形式产生的理论依据,二者都可看作是在生成整体论下的语用变化,因此也容易发生混淆。古汉语存在着普遍的省略现象,尤其是先秦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一句话完整意思的表达更依赖于语义整体性或句法场,是缺省思维的表现。英语在书信落款处通常只写“Yours”,意思却涵盖了“Yours Friend”,而用“Oh,My”代表“Oh,My God”,用“morning”代表“Good morning”也都体现了这种缺省思维,可以理解为语义场中成分之间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简略表达。说话者给出一个刺激,使得说话者和听话者双方都清楚交际者意欲通过这一刺激向听话者表明的一组假设,这就是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所说的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 Cognition.Oxford:Blackwell,1995,p63.
(二)词义感染与缩略的区别
俞理明(2005)指出:“感染”与“凝缩”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感染”只适用于双音节词语(不包括双音的单纯词)向单音节的变化,而“凝缩”没有这个限制。*俞理明:《汉语缩略研究——缩略:语言符号的再符号化》,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297页。但他认为,词义组合感染是在两个词汇单位融合为一个更大的词汇单位之后,抽取其中部分形式来表示全体意义,变化的不是词义,而是词语的形式,这就与缩略形式相混了。
词义感染与缩略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语义上,发生词义感染的那个词所感染的是双音节组合中另一个词的意义,当它单独使用时,表示的是另一个词的意思。而缩略发生后剩下的词形所表示的是缩略之前整体的意义,如“警”表示的是“警察”的意思,所以缩略的词义没变,只是词语的形式简化了。词义组合感染除了表面上词形的省略,最主要的是词语内部意义也有转变的过程。在强势语义的影响下,弱势语义虚化或磨损,进而被掩盖,具有强势语义的成分把表弱势语义的成分同化,两者表同一义,这在词形上出现了缀余现象,由于经济性原则,形式上就要发生省略或脱落,而脱落掉的恰恰是原来表强势语义的那个成分。
以往学者们所举的例词很多都应该是缩略,而非词义感染,如伍铁平(1984)所说的“terminal”表终点站*伍铁平:《词义的感染》,《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其实不是感染,而是terminal station的缩略,蔡镜浩(1990)所释“缘”表示为什么,凭什么*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5页。,也是“缘何”的缩略。唐子恒(2006)提出“粉”因“粉红”而生粉红义,“符”因“符合”而生符合义,是词形内部的横向合并*唐子恒:《词素间意义的横向合并》,《山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其实也是缩略。
词义感染与缩略都可以看作是词义的共时变化,不同的是缩略更容易成为历时演变的前奏,如“机”表“飞机”义,即来源于共时缩略的整体义,后固化为“机”的引申义,就进入了历时演变的通道,英语的gold演变出“金牌”义,也是由gold medal缩略促成的。*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30页。这大概是由于这种整体义与原有词义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相比组合关系下的并列、偏正或承接等关系,包蕴关系显得更为紧密和容易被联想。
三、词义组合同化的判定原则及认知分析
为了正确判定词义感染现象,避免与词义引申相混同,徐之明(2000)和董志翘(2009)都指出判断词义组合同化应遵循的原则。首先是历史性原则,是指被同化词新义位的产生必须晚于相关组合的存在时间,比如“念”表“爱、怜”早于“爱念”组合而生,就是自身词义引申的结果,那么“爱念”一词就没有发生词义感染,而仅仅是同义复用。*董志翘:《词义沾染,还是同义复用?——以汉译佛典中词汇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这一原则可以从时间上根本性地区分词义引申与词义感染,实为前提条件。其次是社会性原则,即促使被同化词新义位产生的组合形式要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徐之明:《试论词义“组合同化”应遵循的原则——兼与张博同志商榷》,《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高频使用是为了区别于个别性的临时用法,然而对使用频率的考量却似乎并不明确。我们认为高频使用的原则并不是必然的,有些组合使用频率并不高,使用范围也不够广,但由于是具有一定社会认知度的习用组合或常规搭配,同样也发生了词义感染,比如下面所举“赴救”、“赏募”和“典藏”三例。
(一)赴救
“赴救”本是表承接关系的连动词组,意为“前往救援”,始见于东汉,如:
(2)即时遣使,至彼军中,白其王言:“我曹比国,用作恶为?所索河水,今以相与,我当以女为汝夫人,国有特物,更相贡赠,急难危崄,共相赴救。”(北魏慧觉等《贤愚经·盖事因缘品第三十四》)
此二例中,“赴救”作为及物的连动词组,宾语均承前省略,原因大概是“赴”当赶赴、前往讲,本应跟表处所的宾语,而“救”的对象应为具体的人或事,二者所应及的宾语不同,故“赴救”连用,宾语往往省略。比“赴救”连用表“前往救援”义稍晚,在中古时期,“赴”有了单用表“救”的意思,如:
(3)指水不能赴其渴,望冶不能止其寒。(南朝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下》)
(4)君居家,遇人无亲疏,豁如也。乐赴人之急。(宋曾巩《抚州金溪县主簿徐洪墓志铭》)
(5)平生热肠坦腹,善赴人缓急。(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一)
例句中“赴”的宾语不是处所,而是“渴”或“急”等事,据此判断其义为“救”,宾语对动词义起了限定作用,故没有像“赴救”连动一样省略宾语。《说文·走部》:“赴,趋也。”本义是趋走、前往的意思,此外还有“到达”、“投身”等引申义项,而表“救”义,显然并非“赴”自身词义引申的结果,而很有可能是在与“救”组合连用的过程中感染而生的。在“赴”单用表“救”义之前,从东汉始见到唐以前“赴救”的用例并不多,那么“赴”是如何在较少组合用例的情况下感染到“救”义的呢?
将英语电影纳入高中英语教学中,并不是一件新鲜的尝试。一门新语言的学习,语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的高中英语教学中,大多数的学校并没有聘请外教或者赴外学习的能力,因此将英语电影引进教学课堂,使学生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感受英语的知识和国外风貌,是当前经常采取的教学方式。例如,电影《泰坦尼克号》上映期间,全国各地的高中院校纷纷组织学生进行观影,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习英语的语感。然而,随着现代技术的提升,高中英语学习不能满足于电影这种单方面接受的视频教学,而可以进一步尝试互动视频、微视频等学习技巧,让学生借助直播软件直接与外国友人进行对话,从而更好地感受英语的语感与魅力。
“赴”在春秋时期常常不带宾语,或者后加介词词组,由此看来,“赴”最初可能是个不及物动词。如:
(6)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来赴吊如同盟,礼也。(《左传·文公三年》)
(7)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左传·隐公三年》)
“赴”在《左传》的20个用例中,后不加宾语的句子有7例,后加介词词组的有11例,而带宾语的只有2例。如:
(8)二十五年,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9)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从战国时期到西汉,“赴”带宾语的情况才越来越多,宾语有具体的处所,也有较为抽象的所在。如:
(10)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荀子·议兵》)
(11)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赏不足以劝;盗跖犯刑赴难,罚不足以禁。”(《韩非子·忠孝》)
(12)故百人之必死也,贤于万人之必北也,况以三军之众,赴水火而不还踵乎!(《淮南子·兵略训》)
到东汉时“赴救”组合的使用,使“赴”重新处于无宾语状态,与“救”在语法位置上的邻近关系,映射到词义上,“赴”很快就感染而有了“救”的意思。在“赴”的意思无限靠近“救”而远离“前往”的过程中,在句中假如需要,“前往”义就选择由别的词来承担,如:
(13)七年闰月,魏大将军曹爽、夏侯玄等向汉中,镇北大将军王平拒兴势围,大将军费祎督诸军往赴救,魏军退。(《三国志·蜀书三》)
句中“往赴救”,显然“赴救”的结合更为紧密,应读为“往/赴救”,而非“往赴/救”。在《北齐书·本纪》中还有“来赴救”的表达形式,如“七月壬午,行台侯景、司徒高昂围西魏,将独孤信于金墉,西魏帝及周文并来赴救。”更显示出“赴救”组合的整体性,由此可见,随着“赴”义的演变,“赴救”由连动组合逐渐变成了同义并列。
(二)赏募
“募”本表“募集、招求”,为了以防募集不到,便要施以好处,于是和“赏”搭配组成连动结构。“赏”是手段,“募”是目的,“赏募”即表“悬赏招募”,始见于六朝时期,用例亦不为多。如:
(14)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觽。(《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15)岂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三国志·魏书十四》)
颜洽茂认为“募”在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了“悬赏搜捕”义,如《六度集经》卷一:“贪王募之,黄金千斤,钱千万。……收泪而曰:‘吾闻新王募吾甚重,子取吾首,可获重赏。’”进而又有“奖赏”义,如《贤愚经》卷六:“往从乞眼,庶必得之,若得其眼,兵众可息,此事苟办,当重募汝。”*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经词汇研究》,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1、286页。《旧杂譬喻经》:“时国王夫人有疾,夜梦见孔雀王,寤则白王:‘王当重募求之。’”那么,“募”表“奖赏”义是为何而生呢?
“赏募”组合是一种相邻性常规表达。从认知注意力和视角来看,虽然“募”是目的,但“赏募”的语义重心却是“赏”,人们更在意的是“赏”。因为领了赏,被招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在此“招募”义成了一种隐性表达。在这样的常规关系下,当“募”单用的时候,依然能表达“赏”的意思。所以在经过与“赏”连用之后,“赏募”先经过缩略,由“募”单用表“悬赏搜捕”,很快又仅表“奖赏”义,即发生词义的感染。这个过程与“募”自身词义发展演变的途径并不相符,应该是受到“赏募”组合中“赏”的强势影响。随着“募”词义的演变,“赏募”也由连动组合变成了同义并列,“赏募”只表“奖赏”而没有了“招募”的意思,如:
(16)是时猎师剥师子皮,持至于家,以奉国王提毗,求索赏募。(《贤愚经·坚誓师子品第五十四》)
(三)典藏
“典藏”是一个现代汉语常用词,而《现代汉语词典》一直到第5版才收进此词,释为“(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图书、文物等)”。在这个双音节词中,“藏”表“收藏”是常用义,那么,“典”的意思是什么?“百度百科”解释“典藏”:本义指将重要的文献、典籍收存起来,后引申为对重要、珍贵事物的收藏,泛指用于值得收藏的经典的珍藏品。对现代社会中“典藏”的用法,这样的解释也不为过。但实际上,把“典”的意思理解为“重要文献、典籍”、“珍贵事物”或“经典”等义,恐怕有失偏颇,而且“典藏”的结构关系也无从解释。
“典藏”最早的用例出现在汉译佛经中,通过CBETA电子佛典检索显示共有179例,其中绝大部分是“典藏者”、“典藏臣”或“典藏吏”的形式,意为“掌管仓库的人员或官吏”。较早的用例有:
(17)化王于时遥知彼意,勅典藏臣:“取我先祖大弓弩来。”授与彼王,王不能胜。化王还取,以指张弓。(《撰集百缘经·罽宾宁王缘》)
(18)时,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复出与大王用之。(《杂阿含经》)
(19)如是布施,经数时中,诸藏之物,三分已二。时典藏吏,往白其父:“摩诃阇迦樊,自布施来,藏物三分,已施其二。诸王信使,当有往返,愿熟思惟,后勿见责。”(《贤愚经·大施抒海品第三十五》)
在中土文献中,自古以来“典藏”的用例并不多见。最早的用例见于唐代《法苑珠林》和《群书治要》等书中,但也是以“典藏臣”的组合出现,共6例。自宋以降,用例也不过六七十个。在“典藏臣/吏”中,“典”的意思是“掌管、主管”,“典”的这一义项产生的时间很早,如《书·尧典》:“命汝典乐。”《论衡·命禄》:“或时下愚而千金,顽鲁而典城。”《三国志·吴书十七》:“专典机密”等,又如:典御(掌管统治);典诠(主持选拔);典守(主管、保管看守);典领(统领统治)等,其中“典”都表“掌管”。
“典藏吏”表“掌管仓库的官吏”,而掌管仓库的官吏本职工作就是替国王收藏重要而珍贵的东西,加上“典”的掌管义较抽象,假如不与“吏/臣”等搭配使用表“掌管……的官吏”,其自身意思就无以附着,所以译经中“典藏”通常只表“收藏”,“典”表掌管的意思逐渐弱化消失。如:
(20)长者即请千辟支佛,饭食供养。彼残千人,复诣其家,亦求供养。长者复问其藏监曰:“卿所典藏,谷食多少?更有千人,亦欲设供,足能办不?”(《贤愚经·散檀宁品第二十九》)
例句中,“典藏”在“所”的后面,表动词“收藏”。也有单用“典”表收藏的情况。如:
(21)其藏监言:“所典谷食,想必足矣,若欲设供,宜可时请。”(《贤愚经·散檀宁品第二十九》)
再看下面两例:
(22)于是轮宝,当在王前虚空中住,其轮去地七多罗树;象宝、神珠、玉女、典兵、典藏宝,次第来至。时盖事王七宝具足,典四天下,一切众生,蒙王恩德,所欲自恣,王悉教令修行十善,寿终之后,皆得生天。(《贤愚经·盖事因缘品第三十四》)
(23)立誓适竟,大国之中所有宫殿,园林浴池,悉来就王。金轮、象马、玉女、神珠、典藏、典兵,悉亦应集,君四天下,为转轮王。(《贤愚经·顶生王品第五十七》)
例(22)中,“典兵”为“典兵宝”的省略,义为“带兵的将军”,“典藏宝”义为“主管府库的官员”,至例(23)中省为“典藏”。由“典兵宝”到“典兵”、“典藏宝”到“典藏”的省略,应该是受到作品刻意追求句式整齐的影响,其余列举之物都是双音节,“典兵宝”和“典藏宝”也只能被缩略为双音节的“典兵”和“典藏”,这种单纯形式上的省略并没有影响“典”的意思。然而,在现代汉语中“典藏”的意思却是承接着“典”感染而生“收藏”义之后,二者同义并列而得以使用的,与上面两例情况不同。所以,把“典藏”一词中的“典”理解为“重要的文献典籍”、“珍贵事物”或“经典”等义,肯定是错误的。
上述发生词义感染的三个组合形式,虽然没有经过高频使用,而且这些组合形式结合并不紧密,但却不能因此说它们是临时性的组合。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构建词义系统,常规关系就是基于人们的常规经验所建立起来的事物间的一种自然关系,以知识形态或社会意识的形态固定下来,被认定为一种较为经常性、规约性的联系,并可为言语所利用而推导出隐性表述的内容。基于能建立起一定关系的两实体倾向于被识解为一个整体这一认知心理,人们在感知事物并进行识解时,会因为其中一个实体的出现,通过通感、通知而领悟出另一个。*徐盛桓:《认知语用学研究论纲》,《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赴救”连用,在人们的心目中便形成了一种常规关系:凡需救必紧急,所以要尽快赶赴现场,“赴”是过程,“救”是目的,“赴救”形成了一个语义整体。“赴救”的语义重心在“救”,而在“救”字被隐去的情况下,其意思依然能通过缺省推理补出来,可见“赴”表“往救”是建立在常规关系基础上的组合生义。“赏募”的情况也是如此,“赴救”和“赏募”都是表语义重心的词反而成为了隐性表述。“典藏”的情况略有不同,“掌管收藏”在长期搭配过程中也形成了相邻性常规关系,其语义重心是“藏”,“掌管”义由于其抽象性而被弱化隐去,最终表收藏成了典藏的显性义,以至“典”单用也感染此义。“典藏”因其特有的文言色彩,又区别于一般收藏而多了几分郑重和珍视,在现代社会中常常被用来表示一些贵重物品的珍藏。然而“典”单用表“收藏”义,却最终没有摆脱对语境的强烈依赖而独立出来,也就没有成为“典”的固定义项。“赴”表往救和“募”表奖赏也都具有中古汉语的时代性,之后,其含义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赴救”与“赏募”的组合形式现代汉语亦已不用。由此可见,语义特征的突出和隐退都是靠语境关系和人们的认知心理来进行选择的,暗含(潜在)性和临时性都是语境意义反常性的表现,是一种共时义变。由此我们提出,组合同化除了历史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之外,还应考虑到常规关系影响下的习用组合原则。
四、结论
语言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体与部分及部分与部分之间不仅有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而且有相互影响、相互调整的互动关系,结构成分的意义和功能正是在这种依存和互动关系的作用下得到实现的。*任鹰:《动词词义在结构中的游移与实现——兼议动宾结构的语义关系问题》,《中国语文》2007年第5期。早在清代王念孙提出“同义相因”说时就主张从词与词的互动关系中去探求词义的发展和演变。认知是全方位的丰富而复杂的系统,在考察一个新词义产生的途径时,除了内部引申理据和外部大语境之外,也要关注组合搭配关系的小语境,所有与新词义有形式上联系的因素,都不排除会对其形成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词组不管凝不凝固成复合词,它都形成一个语义整体,词组和复合词都不能阻止词义的发展,整个复合词和词内部的词素意义,或者词组内部各词的意义都仍然会处于运动变化的状态中,词素与词素之间或词与词之间在意义上互相影响、制约,就有可能发生组合同化。由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词义组合同化与词义引申的区别。从原因来看,词义组合同化受到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影响,受到所在句法结构的小语境影响。
2.词义组合同化是一种共时语义演变。从感染义的固化与否,还可看出词义感染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是所有的共时语义变化都能进入历时演变的通道,被感染词的新义位不一定流传至今,也不一定被词典所收录。
3.通过与缩略形式的比较,我们发现,词义感染是语义组合同化与形式省略的结果,其语义内部深层次的互动过程是缩略所没有的。
4.从“赴救”等三例可以看出,组合同化除了历史性和社会性原则之外,还可以从习用搭配角度进行判断和验证。感染义的生成是在整体化语言观下,词与词在一个语言表达式中,通过语义互动造成的语义改变。
爱切生(Jean Aitchison,1990)在谈到词语中的语音脱落问题时曾指出,“同化和省略现象是全球性的”*[英]简·爱切生:《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徐家祯译,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同化和省略往往也是相伴而生的。词义引申是在形式未变的基础上语义的演变,缩略是形式的简化,但未衍生新义。与它们不同的是,词义感染基于同化与省略,语义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
责任编辑:孙昕光
A Cognitive Study of Combined Assimilation of Wor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Holistic Theory
Shi Xiaof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lu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3;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The study of the infection of word meaning caused by combined assimilation is a way to investigate the derivation of word meaning in terms of linguistic unit or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the word. The study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word meaning in a single word meaning system.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eaning infection and meaning extension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ynchronic evolution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word meaning. And the reason of its formation is the influence of the double syllables of Chinese vocabulary, and the meaning of a word in a relatively small context is assimilated by the adjacent meaning, thus resulting in meaning infection. Meaning infection is similar to abbreviations in the form of expression. They are bo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olistic theory. The difference is that the infection of word meaning is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which results in the semantic assimilation and the loss of form, while abbreviations have no internal assimilation, only using elliptic forms to represent the whole meaning. The senior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historical principle and social principle to determine word meaning infection. We take “fujiu”, “shangmu” and “diancang” as three case words, and propose the conventional combination principle based on the norm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tive holistic theory.
generative holistic theory;combined assimilation; infection of word meaning; extension of word meaning;abbreviation
2016-10-05
施晓风(1978— ),女,山东莱州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H139
A
1001-5973(2016)06-01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