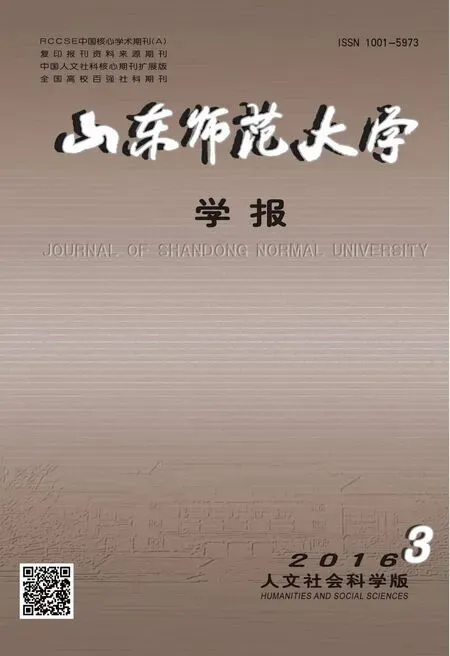现实主义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左派民族文学论中的功能*
李大可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现实主义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左派民族文学论中的功能*
李大可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现实主义论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进步文学阵营的主导话语理论,是民族文学论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与民众文学论、第三世界文学论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学论。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论具有构建民族文学论的民众性、脱冷战意识形态性及《创作与批评》阵营身份三个主要功能。1980年代,民族文学论走向分化和激进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成为激进民族文学论者之现实主义论的重要参照。
现实主义;民族文学;民众文学;冷战意识形态;《创作与批评》阵营身份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3.005
一、民族文学论的复杂语义网络
左派民族文学论仅是韩国1970年代的文学话语,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同的文学话语?它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怎样?对此,不同韩国文学史的叙述方式有明显差异。在某些文学史家笔下,它被视为七八十年代的代表性文学话语,被赋予了绝对的文学史叙述优先权乃至唯一特权。这方面的例子可举出权宁珉的《韩国现代文学史1945-1990》。该文学史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合述为“产业化过程与文学的社会扩张”,下分相当于概述、文学批评、诗歌、小说和戏剧的四个小节。其中相当于文学批评部分的第二小节(“民族文学的论理及实践”)及其下属的四个分节(“民族文学再认识”,“民族文学论的论理”,“民族文学论与民众论”,“民族文学论的成果及局限”)都以“民族文学(论)”为核心词构成标题,而且未加“进步”或者“左派”这样的限定词,从而一方面在章节目录上(在具体的论述中实际也是如此)使左派民族文学论呈现为该时期唯一的文学话语。*[韩]权宁珉:《韩国现代文学史1945-1990》,首尔:民音社,1995年,第217-231页。另一方面,在更注重完整描绘文学史版图(用李东夏的话说是“制作批评业绩的明细表”*[韩]金允植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现代文学社,2002年,第532页。)的文学史家笔下,它仅被叙述为该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学阵营之一即《创作与批评》阵营(乃至白乐晴个人)的文学话语。这方面的例子可举出金允植等34人编著的《韩国现代文学史》,其中的1970年代文学批评部分(“扩大与深化的戏剧性时代”)由李东夏执笔,下分无标题的七小节,内容分别为概论、承前启后的老一代批评大家、70年代批评主力之《创作与批评》阵营、70年代批评主力之《文学与知性》阵营、文学史家、独立批评家以及结语部分。虽然将“创批”阵营(即《创作与批评》阵营)与“文知”阵营(即《文学与知性》阵营)并举,但李东夏仍认为白乐晴(扩大至《创作与批评》杂志)一直独占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坛的理念先锋”*[韩]金允植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现代文学社,2002年,第536页。位置。1980年代部分由高炯镇执笔,下分无标题的六小节,论述的中心文学话语是民众文学论。虽然该部分模糊地将民众文学论定位为“新的‘民族文学论’”*[韩]金允植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现代文学社,2002年,第603页。,但强调其对白乐晴之民族文学论的扬弃。不过,对民族文学论在韩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何种地位这一问题,上述两种文学史的观点是大致相同的,权宁珉显然赋予了民族文学论以绝对优先的文学史地位,而李东夏也认为“创批”阵营以旗帜鲜明的民族文学论、民众文学论以及第三世界文学论开启了韩国文学史的新篇章。*[韩]金允植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现代文学社,2002年,第535页。
被视为左派民族文学论之理论奠基作的《为了民族文学概念的确立》,其最初发表时的标题是“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为什么是“新展开”呢?从个人方面说,白乐晴的首篇评论《创作与批评的新姿态》(发表于1966年冬《创作与批评》创刊号)与其发表于1969年的《市民文学论》一道被视为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起点。*[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03页。“新展开”意味着作者在此基础上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之第一部分“文学的‘国籍’意味着什么?”中提到的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话语已迎来春天,政府为此投入巨额财政预算,而曾经被攻击、警戒的民族文学论也已成为流行话语;二是作为与“世界文学”处于相对关系中的概念,“民族文学”最近呈现出了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色彩;三是要像警戒民族文学否定论那样警戒没有坚实基础的民族文学论。*[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23-124页。1970年代初,为了在文学领域配合朴正熙政权的“韩国式民主主义”,官方团体“韩国文人协会”在其机关杂志《月刊文学》推出了“民族文学论”特辑,主张继承1920年代保守、复古的国民文学论。参见[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52页。上述三点内容实际上已部分地勾勒、暗示出了民族文学论的复杂历史-现实语义网络,那就是光复后至分裂前(史称“解放空间”)的左派(林和)主导的“文盟”的民族文学论,*崔元植采纳的是三种民族文学论说,增加了“文总”的两种民族文学论,即“青文协”(金东里)的正宗文学论(纯文学民族文学论)和“文笔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倾向的民族文学论。此外,他还高度评价了1950年代郑泰镕的民族文学论,称之为在世界矛盾中认识分裂现实的最初火种;重视1960年代白铁的民族文学论,认为它虽然较郑泰镕的民族文学论退步了,但相对而言却是通往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最直接的桥梁。参见[韩]崔元植:《民族文学论的反省与展望》,[韩]金史仁、姜亨哲编:《民族民众文学论的论争焦点及展望》,首尔:翠林,1989年,第18-26页。当下现实中的官方民族主义话语,*[韩]金一荣:《朴正熙时代与民族主义的四种面孔》,《韩国政治外交论丛》第28集1号,第225页。以及实际上附和了官方民族主义的各色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民族文学论。实际上,从光复时期再上溯,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卡普文学对立的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的民族文学论——“国民文学论”*崔元植指出了国民文学论的复古主义性质,但仍认为它是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最早前身([韩]崔元植:《民族文学论的反省与展望》,[韩]金史仁、姜亨哲编,《民族民众文学论的论争焦点及展望》,首尔:翠林,1989年,第17页)。相反,任轩永认为,民族文学是普罗文学的大前提,被视为阶级文学的卡普文学首先是民族文学,而处于卡普文学对立面的所谓民族文学(即国民文学论),其本质是间接呼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意识形态的“反民族文学”(参见[韩]任轩永:《民族文学之路》,《艺术界》1970年冬季号,第51页。转引自[韩]高明哲(音译):《超克1970年代维新体制的民族文学论》,首尔:宝库社,第68页)。。正因为“民族主义”、“民族文学(论)”概念的历史沉积和现实脉络如此复杂、混乱,色彩混浊、暧昧,一些学者和批评家才有意回避使用“民族文学论”这一概念来概括20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进步文学运动,而倾向于使用体制更为透明、色彩更加纯粹的“民众文学论”这一概念,*[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或者在“民族文学论”前面加上限定词,如“进步的”。本文之所以使用“左派民族文学论”这种指称方式,正是参考了后一种做法。
那么,明知“民族文学”概念如此混沌,却一定要选择使用这一概念,其理由何在呢?崔元植认为,1970年代围绕民族文学论出现面目各异(官方的或非官方的,赞成的或反对的)的大量论说,表明了民族文学论的“历史当为性”,认为它是自4·19革命开始在韩国社会中显著发力的民族主义动力在韩国文学中的集中反映。*[韩]崔元植:《民族文学论的反省与展望》,[韩]金史仁、姜亨哲编:《民族民众文学论的论争焦点及展望》,首尔:翠林,1989年,第13页。在该文中,崔元植还提到了最早尝试整理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几篇文章:[韩]具仲书的《70年代批评文学的现况》(《创作与批评》1976年春季号),[韩]崔元植的《我国现阶段的批评》(《创作与批评》1979年春季号)和《70年代批评的前进方向》(《创作与批评》1979年冬季号)。用白乐晴的表述来说,这种“历史当为性”是由作为国民国家的本民族的危机现实所决定的,即正如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激发了呼应朝鲜民族·民众之反殖民、反封建要求的民族文学一样,光复后的国土分裂、南北内战以及南韩国内民族的同质性和主体性正在经历的不亚于此前任何时代的严峻考验也要求人们在以下两条道路中做出选择:要么将先人在日本占领期开启的民族文学传统推向成熟,要么在赋予“民族文学”这一理念以真实内容从而使之获得存在之合法性的历史条件——换言之,在现实中仍存在以“民族文学”这一区别性概念来指称一个民族的主体性的、人道性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文学之必要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过早地”宣告这一传统的破产。答案显然是前者。*[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25、137页。
既然如此,如何与官方的(伪)民族文化论以及复古主义的或国粹主义的(伪)民族文学论相区别地构建“真正的”民族文学论这一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在白乐晴对民族文学概念的阐述中有以下两个最具概括力的规定性:一是“历史性”;二是“民众性”。所谓“历史性”,一方面指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相应的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会被否定或者被上位概念吸收;另一方面,所谓特定的历史条件,既具有呈现为多种具体现实面目的可能性,又具有不变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危机处境,即“民族的主体性生存以及大多数民族成员的福祉面临严重威胁”的危机处境。白乐晴认为,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这种危机意识的产物,它要反映这种福祉被破坏的现实,捍卫民族的主体性生存权利。*[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25、131页。由此可见,“历史性”这一规定性的第一个方面已经不再将“民族文学”视为某种恒久不变的东西,从而将“民族文学”与视“民族”有某种恒久不变之属性的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的民族文学观区别开来了,而其第二个方面则与推行牺牲民族主体权利以及大多数民族成员之福祉的发展路线的官方民族主义形成区分。所谓“民众性”,一方面与“历史性”中的“大多数民族成员的福祉”相关联,要求“反映”这种福祉被破坏的现实;另一方面,还要将“民众意识”牵引向“市民意识”,以担当起清算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重任;而这两个方面都应通过既与民族语(体现出民族主体性)又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语相一致(民众性)的韩国语写作这第三个方面来完成。*[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1-132页,第129-130页。上述三个方面,至少前两个方面是确切具有与官方民族主义相区别之功能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符合上述条件的文学,就可以纳入白乐晴定义的民族文学范围,且这些条件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内容方面的要求,只有语言要求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形式方面,而美学范式方面的要求则根本没有正面提出,白乐晴仅在探讨民族文学的先进性时提到了民族文学有望“继承在20世纪西方文学中几乎中断了的19世纪现实主义大家们的传统”*[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6页。。那么,现实主义论是为何、如何成为左派民族文学论之必要骨干成分的呢?
二、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论及其功能
可以说,民族文学问题和现实主义问题都是在1970年代初期凸显出来的。*白乐晴认为,直至1970年代最后几年,对分断问题的认识才在韩国社会的相当一部人头脑中扎下了根,民族文学论才正式形成。参见[韩]白乐晴:《站在民族文学的新关口》,[韩]白乐晴、廉武雄编:《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第9页。从源头上看,它是1960年代“纯粹—参与文学论争”中调动、积聚起来的理论能量的扩张,也是那时产生的问题意识的深化、细化和精准化。*有的学者将纯粹-参与文学论争称为“现实主义论的入口”。参见[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79页。相对而言,现实主义被聚焦和问题化的时间更早,虽然一般认为它是通过1970年第4期《思想界》推出的以“4·19革命与韩国文学”为主题的座谈文章为标志正式拉开帷幕的,*柳文善认为,具仲书在此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及他此后发表的《韩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金龙洛认为该文是1970年代最早系统阐明现实主义见解的文章。参见[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22页)宣告了现实主义将成为韩国文学最正确、最富有指导性的主流文学方法(参见[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84页)。白乐晴的《关于现实主义》也认为是1970年代初的现实主义论争促成了1974年廉武雄的《现实主义论》等总结性文章的出现,在此基础上,1970年代中期以后,对现实主义问题的主体性理解又进一步被设定为民族文学论的重要目标之一(参见[韩]白乐晴:《关于现实主义》,[韩]金润洙、白乐晴、廉武雄编:《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2年,第315页)。但在1960年代中后期,“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就已开始走出边缘地带,包括白乐晴本人在内的批评家们一再从现实主义角度思考韩国文学(如白乐晴的《韩国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展望》,《东亚日报》1967年8月12日),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关心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也被大量翻译出版。*[韩]吴昶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讨论与外国文学专业批评家的象征权力》,[韩]文学与批评研究会编:《韩国文学权力的谱系》,首尔:韩国出版营销研究所,2004年,第105-108页。
1966年《创作与批评》创刊后的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白乐晴的关心点是构建韩国的市民文学,他对现实主义问题的思考也是与这一关心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市民文学论》显示出,白乐晴有意在市民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之间建立同位性“连带”关系。通过追溯法国启蒙文学(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德国古典主义文学(歌德、席勒)和市民文学(荷尔德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司汤达、巴尔扎克)、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D.H.劳伦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白乐晴探讨了市民意识的深化过程以及现实主义与市民文学的关系,提出了“市民文学的传统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以及后来的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否说明市民文学对现实主义的需求具有某种必然性?”*[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72页。的问题,并给出了“市民意识的具体表现要求写实性”*[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73页。这一肯定性的回答。具体来说,他认为:
因为理想的市民文学是全体市民共有的文学,而健全社会的市民极为关心社会现实,所以,理所当然,那种尽量采用当代的题材,尽量采用千万人觉得自然的技法——那当然是一种技法,也就是说,事实上不是照自然原样,而是一种艺术惯例——描绘出来的文学才够格。此外,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学的形成是一项持续的事业,要求对既存现实进行不断批判,而现实主义就具有这种特点,这一点也很重要。*[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72页。
这也就是说,不仅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最契合市民们具体了解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具有直面现实并不断加以批判之特点的现实主义精神也与在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学建设中需要持续保持的批判精神或者说先进的市民意识相一致。这是因为,“作为真正的市民文学之原理的理性并非固定不变的合理性,而是意味着对现存合理性的不断挑战”。*[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78页。
“市民文学论”在1970年代初曾被“民族文学论”扬弃,但作为其核心概念的“市民意识”及其现实主义美学取向并未被抛弃,而是被吸收进了后者。前文注释已提及,按白乐晴的陈述,1970年代中期以后,对现实主义问题的主体性理解被设定为民族文学论的重要目标之一。白乐晴本人曾通过《第三世界与民众文学》*[韩]白乐晴:《第三世界与民众文学,》[韩]白乐晴:《探求人的解放之路》,首尔:诗人社,1979年。对现实主义进入民族文学论后的新发展进行了总结,其他学者有的将现实主义论视为民族文学论的方法论,*[韩]权宁珉:《韩国现代文学史1945-1990》,首尔:民音社,1995年,第222页。有的则超越了这种定位,看到了它作为民族文学论“问题框架”的功能,*[韩]高明哲:《超克1970年代维新体制的民族文学论》,首尔:宝库社,第81页。或者构建象征权力的功能*[韩]吴昶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讨论与外国文学专业批评家的象征权力》,[韩]文学与批评研究会编:《韩国文学权力的谱系》,首尔:韩国出版营销研究所,2004年,第124页。。本文主要在后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探讨现实主义论在构建民族文学论“正体性”(即身份、特性、identity)方面的几个主要功能。*虽然有学者认为白乐晴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同时也是韩国的现实主义理论构架)至1980年代才正式形成([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89页),但鉴于1980年代的进步文学话语已由民族文学论主导转向由激进的民族文学论主导,本文集中在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名下探讨其现实主义论,只是考察范围不限于民族文学论阵营在1970年代发表的文章,也包含了该阵营在1980年代乃至其后发表的相关文字。
第一个是构建民族文学论的“民众性”这一正体性的功能。1972年,廉武雄在《月刊中央》第3期发表了《在黑暗中前进的民族文学》,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必须与民主和民众概念相结合”的主张,有学者将此视为民众概念在民族文学论中的正式登场。*[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87页。从白乐晴的民族文学定义看,捍卫“大多数民族成员的福祉”是构成民族文学正体性的主要规定特征之一,“民族文学必须是民众性的”,而民众文学论也被部分学者以及白乐晴本人视为民族文学论的有机成分。*[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0页。其实,自市民文学论阶段起,白乐晴就已将民众性阐释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属性。前面已经引用过,在《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中,白乐晴阐述说,市民文学之所以需要现实主义,是因为理想的市民文学是“市民共有”的文学,而现实主义正是能通过“采用千万人觉得自然的技法”而使全体市民得以共享文学的创作方法。在此前白乐晴的《韩国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展望》一文中,现实主义文学还被表述为能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文学。
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在于,它旨在使作品的实感不仅仅局限于作家个人或几个特殊读者的实感,而是成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的所有人的实感,使个人关心的问题成为与之一起生存的所有人都关心的共同问题,而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也被每个个人视为自己的问题。为实现这一根本意图可采取多种方法,但应特别看重的,当然是选取当代现实为素材并追求写实性的描写方法。*[韩]白乐晴:《韩国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展望》,《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239页(原载《东亚日报》1967年8月12日)。
上述引文将“全体社会成员性”视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最根本属性,将选择当代题材和写实手法作为由这一根本意图派生出的第二级别的问题。比起《市民文学论》中“采用千万人觉得自然的技法”那种模糊阐述,这种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阐释的独特理解更接近于白乐晴后来的民族文学阐述(即“大多数民族成员的福祉”)。由这一细微的演进轨迹,可以看出与市民文学论一体的现实主义论为何会被成功吸收进后来的民族文学论。但上述两段引文显示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此处讨论的是民族文学论及其现实主义论中的民众性问题,那么这两段引文中分别使用的“全体市民”和“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所有人”与民族文学定义中的“大多数民族成员”所指称的是同一“民众”群体吗?
表面看来,“全体市民”、“同一时代、同一社会的所有人”、“大多数民族成员”这三种指称既有全称与特称的区别,又有“市民”与“成员”乃至“人”的规定性质的区别,很难说指称的是同一人群。但总体把握市民文学论、民族文学论和现实主义论就会发现,我们据以概括出“民众性”的这三种指称,实际上最终都要通过“市民意识”这个概念才能获得确切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它们彼此间的上述差异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进一步加以说明的话,首先,在白乐晴关于现实主义(包括西方和本国的作品)的论述中,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是充分反映出作家高度自觉的市民意识的作品,而与这些作品形成对照的失败之作,则是作家小市民意识作用的结果。其次,在白乐晴关于民族文学的论述中,“市民意识”仍是核心评价尺度(至少是之一)。在《韩国文学与市民意识》(晚于《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3个月发表,但被编入白乐晴首部文学评论集时,被归入以市民文学论为主题的第一部分)中,有这样的论述:“当‘民族文学’概念与真正的市民革命、民族革命的要求不一致时,就会堕落为小市民的另一种文学表现”,“错误的民族文学论会成为小市民意识、殖民地意识的表现”*[韩]白乐晴:《韩国文学与市民意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79页(原载《读书新闻》1974年10月6日)。,其中隐含的仍是贯穿全文的“市民意识”(尽管有时它也会以 “市民意识、民众意识”或“市民文学、民众文学”并举的暧昧形式出现)这一标尺。在《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中,民族文学本质的获得也是与“促使民众意识发展成堪当这种历史使命的市民意识的事业”*[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2页。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无论“民众”在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述和现实主义论述中以何种具体指称出现,是“全体市民”,“同时代、同一社会的所有人”,“大多数民族成员”,或者干脆就是“民众”,其“民众性”的实质都是市民性,它植根于“市民意识”这一市民文学论的核心概念。可以说,在民族文学论中,民众论是价值论与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发展观的复合体,其中的“民众”是价值论,而“市民意识”则是历史发展观。借用1980年代激进民族文学论代表之一曹贞焕的观点来说,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正是民众立场与市民革命之客观性的辩证结合。*[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81页。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崔元植认为在《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中尚部分存留的市民文学论要素在1975年发表的《现阶段的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1975年春季号)中就已经得到了清算*[韩]崔元植:《民族文学论的反省与展望》,[韩]金史仁、姜亨哲:《民族民众文学论的论争焦点及展望》,首尔:翠林,1989年,第31页。金龙洛也认为白乐晴已通过《民族文学理念的新展开》(1974)、《现阶段的民族文学》(1975)、《人的解放与民族文化运动》(1978)以及《第三世界与民族文学》(1979)等论述成功地在其民族文学论中以“民众”概念取代了“市民”概念。[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06页。,但1980年代崛起的新一代民众文学论(即激进民族文学论)者仍将民族文学论视为超克的对象*[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47-148页。,当时及后来的部分批评家和学者也倾向于将二者明确区分为“民族文学论”与“民众的民族文学论”(或者干脆是“民众文学论”)。本文之所以仍将“民众性”视为民族文学论的正体性特征之一,是因为笔者认为,尽管“市民”和“民众”指称的对象可能并不完全重合,甚至完全没有交集,但在否定、批判独裁政治和维新体制,维护被统治者权益这一大方向上,二者具有一致性。更进一步,在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二者都具有人民性。
民族文学论之民众论中所包含的民生价值取向以及民族国家主权独立价值取向具有抵抗官方唯发展论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殖民地化经济现实的功能,民族文学论之现实主义论的民众取向呼应着民众论的民生价值取向,与民众论协同共建民族文学论的“民众性”这一身份特征。在白乐晴那里,对“民众性”的坚持不仅基于民众价值论、民主政治立场以及超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间主义”这一伦理价值观,还在于它是“文学先进性”的保障。白乐晴认为,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流脉已经丧失了与大众的联系(因而也就丧失了其先进性),而韩国作家以及应与之建立连带感的第三世界作家*若要完整地讨论现实主义论与民族文学论的民众性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讨论民族文学论的第三世界文学论与现实主义论以及民众文学论的关系。金钟哲认为,现实主义论的民众立场因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引入而得到了强化,从而得以超越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局限。(参见[韩]金钟哲:《第三世界文学与现实主义》,[韩]金润洙、白乐晴、廉武雄编:《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Ⅰ》,第302页)限于篇幅,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此问题。却仍具有这种与民众的血肉关联,这是这些作家的幸运。虽然白乐晴的这种民众—现实主义文学先进性的论述存在较明显的逻辑跳跃,由价值论、认识论转向功能论的路径没有被明晰构建出来,但由“文学先进性”这一参数的追加,仍可进一步看到民众论在民族文学论中被赋予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是构建民族文学论的脱冷战意识形态这一正体性的功能。现实主义概念在韩国历史脉络中形成的过程,渗入了复杂的意识形态要素,烙上了抹不掉的意识形态印迹,或者用崔元植的话说,充满了“意识形态记忆”*[韩]崔元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会通》,柳钟镐等:《现代韩国文学100年》,首尔:民音社,第632页。。殖民地时代的阶级文学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卡普文学 )*辛斗远认为,193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论取得了值得瞩目的主体性发展,而解放后朝鲜文学家同盟的左派民族文学论也已提出民族文学论的几乎所有“原型性”规范。[韩]辛斗远:《民族文学论的历史展开》,[韩]民族文学史研究所编:《新民族文学史讲座2》,首尔:创作与批评社,第439、441页。和解放空间时期左派的民族文学论,都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作为自己的核心方法论*[韩]崔元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会通》,柳钟镐等:《现代韩国文学100年》,首尔:民音社,第622页。,而1950年代朝鲜战争后,官方和亲官方文化势力则对现实主义极度压制。现实主义文学穿越韩国现代文学史时被刻上的这些意识形态印迹,一方面使它获得了先在的反官方文化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又决定了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不是直接借助于那些意识形态印迹,而是试图剥离它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防备政治迫害的策略性考虑,即在独裁体制下,要与刻印在该概念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历史痕迹可能招致的毁灭性危险作斗争*[韩]吴昶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讨论与外国文学专业批评家的象征权力》,[韩]文学与批评研究会编:《韩国文学权力的谱系》,首尔:韩国出版营销研究所,2004年,第111页。,而且也是出于探索同时超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之路的创新、求索的意志。*姜亨哲认为,在白乐晴的文学论对民众文学的哲学性思考中含有这样的前提:在谋求真正的人类进步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失败了。参见[韩]姜亨哲:《第三世界文学与现实主义》,[韩]金史仁、姜亨哲编:《民族民众文学论的论争焦点及展望》,首尔:翠林,1989年,第226页。
首先,现实主义文学被称为“归队兵”*[韩]吴昶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实主义讨论与外国文学专业批评家的象征权力》,[韩]文学与批评研究会编:《韩国文学权力的谱系》,首尔:韩国出版营销研究所,2004年,第111页。。由于195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成为边缘和禁忌,因此,使被禁闭、受惩戒的士兵归队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去官方意识形态的抵抗性,被视为追求自由的解放行为以及4·19革命的产物。在前文提及的1970年《思想界》推出的以“4·19革命与韩国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上,作基调发言的金允植将“现实主义”称为“自由”的“文学称谓”,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能够得到原则性保障的社会”中,现实主义才有可能达成,而现实主义是韩国文学找到前进方向的唯一出路。*[韩]金允植:《4·19与韩国文学 》,《思想界》1970年第4期,第299页。通过将现实主义纳入4·19革命脉络,*具仲书在“4·19革命与韩国文学”座谈会后发表的《韩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认为4·19革命促使韩国社会的市民意识和历史意识走向了成熟,促进了现实主义倾向。参见《创作与批评》1970夏季号,第349页。并建立“现实主义=自由”这一关联性,金允植不仅使现实主义文学在韩国文学史上获得了浪漫主义文学曾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的革命意义,有效地否定了1950年代以后的文化专制,而且使现实主义成为检验现实政治民主程度的标尺,从而使之在新的层面上获得了抵抗官方意识形态压制的政治意义。
其次,将现实主义置于4·19革命的脉络中,也具有对它进行再历史化或新历史化的功效,可以覆盖或淡化以往的社会主义印记,使之在当下的存在合法化。一方面,由于大力借助于非社会主义圈的西方话语,这种合法性又被进一步强化了(实际上,再历史化或新历史化本身也是借助于西方话语完成的)。与金允植相似,在《市民文学论》中,白乐晴也将“真正的市民意识”视为“爱”和“自由”的同义词*[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90页。,将它阐释为柏拉图式“理性”以及作为理性之推动力的“爱”的历史化*[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82页。,认为它具有持续的革命性(即先进性)。另一方面,其现实主义主张的阐述也大力借助西方尤其是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巴尔扎克等)和现实主义文学话语(托尔斯泰、恩格斯、A.豪泽尔、L.戈德曼、G.卢卡奇、L.威廉姆斯等)。金炳杰也声明:“我们所主张的现实主义是各位不必过虑的批判现实主义。”*[韩]金炳杰:《为何要曲解现实主义》,[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431页。而任轩永则辩解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美学,非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现实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代言人”,并将对暴力、异化、经济矛盾的揭发称为“人本主义的本土化”行为*[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54页。原载《朝鲜日报》1978年9月23日。,力求在本土文学传统中找到“民族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韩]任轩永:《韩国文学的任务:民族现实主义之路》, [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389页、第406-408页 。
使现实主义归队,这在韩国的政治语境中构成对反共意识形态的抵抗和消解;而扩大到世界资本主义链条来看,它又具有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诉求。不过,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所针对的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中具有特殊性:一是独裁政府的专制形式所具有的封建性;二是民族分裂所具有的前现代性。就第一点而言,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具有以市民革命克服专制形式之封建性的民主现代性诉求;就第二点而言,民族文学论是以统一论为大框架的,现实主义论处于这一大框架之中,以民族统一为其市民革命的现代性目标。因此,在这两点上,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都具有难以撇清的关系。从市民文学论开始,白乐晴就试图通过区分“资产阶级(bourgeois)”与“市民(citoyen)”这两个概念来解决此问题,试图寻找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市民意识、市民精神及其动能的另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并由此找到超克资本主义的非社会主义路径。遗憾的是,这是一个过于艰巨的任务。其一,尽管可以强调“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不同功能,但正如后来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历史中的实体,二者具有一体性,都是新的剥削行为的实施主体,勉强可视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其二,要寻找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市民意识、市民精神及其动能的另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这不仅需要非凡的思想力,需要历史(国际环境、社会结构、主体力量以及其他势能的聚合)内含着这种可能性,而且还需要成功模式的引导。而在当时,并没有这种可参照的成功模式。因此,市民文学论所提出的超克“资产阶级”的“市民”概念,便只能停留在“等待我们去争取并创造的未知、未完的人类形象”*[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65页。这种模糊程度上。在市民文学论向民族文学论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民众”概念被日益凸显出来。但这个概念仍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既未辨明其与作为剥削主体的资产阶级-市民概念的关系,也未说明它如何有助于“市民”概念与“资产阶级”概念的剥离。因此,仍未真正跳出市民革命的思路,或者说,虽然放弃了这一思路,但尚未形成新的成熟的思路。至1978年发表《人的解放与民族文化运动》,白乐晴不再将“民众”、“民众意识”纳入“市民”、“市民意识”、“市民革命”及“市民文学”这些理念框架中进行思考,而是提出了对“民众”概念加以“科学”定义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此工作只进展到了将之规定为历史性(“在给定的时空中” )、总括性概念的有限程度。*[韩]白乐晴:《人的解放与民族文化运动》,《创作与批评》1978年冬季号,第16-17页。在1979年发表的《谁是民众》(收入白乐晴:《探寻人类解放的论理》,首尔:诗人社,1979)中,对“民众”概念进行“科学”定义的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因而难免被批评为“抽象”“模糊”的概念,甚至被进一步批评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不定是受进化论世界观这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极易被掩盖社会结构内部矛盾的统治意识形态吸收”。*[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编:《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49、246页,第248-249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学论所倡导的旨在成为“不是仅仅被动地反映和传播现有的民众意识,在反映的同时,还须发挥艺术作品的能动作用,即促使民众觉悟到捍卫民族生存权利、完成反封建的市民革命这一客观使命并付诸实践”*[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1页。的“民众性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暧昧性也就不可避免了。换言之,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不得不在与“民众”概念之模糊性的纠缠中与之“共舞”,并通过对其进行不断质询来探知可能的前进方向。由于民众概念既是民族文学论之民众论的核心概念,又内嵌于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之中,因此,这种共生和质询既发生在现实主义论与民众论之间,又发生在现实主义论内部。换言之,它既是发生在民族文学论内部的自我搏斗和自我质询,又是发生在现实主义论内部的自我搏斗和自我质询。以这种多层次的自我搏斗和自我质询为前提和基础,民族文学论才能不断辨明自身的民众正体性,其现实主义论才能真正发挥预设的去冷战意识形态功能。
第三个是构建民族文学论之《创作与批评》阵营身份的功能。虽然民族文学论者的实际范围超出了一般所说的《创作与批评》群体,但民族文学论仍主要被认为是以《创作与批评》为基地生长起来的话语,有的学者甚至干脆说民族文学论严格来说是白乐晴个人的作品,是他纯正的爱国热情、卓越的才华以及植根于此的雄心和霸气的产物。*[韩]李东夏:《扩大与深化的戏剧性时代》,[韩]金允植等:《韩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现代文学社,2002年,第536页。毫无疑问,正如金允植将现实主义视为韩国文学找到前进方向的唯一出路的观点所揭示的那样,民族文学论之现实主义论(民众文学论和第三世界文学论当然也是如此)的提出是历史地认识当下现实的结果,是历史进程提供的“天然”文学突破口。尽管其中并非绝无观念性的阐述,但总体上看,它绝非抽象观念的产物。但是,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又是在“纯粹-参与文学论争”的延长线上构建起来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沿承了其对抗模式。具体来说,作为现实主义论之诞生基础的对历史的现实认识,是在与纯文学论阵营以及自由主义文学阵营的对抗中形成并在这种对抗中表达出来的。通过不断更新、完善话语构建,持续发现、培养和推出相应的作家、作品(民众文学、农民文学等),现实主义论逐渐被打造成某种堡垒性的存在。虽然现实主义论者(乃至其对立方)的意志并不在于维持这种对立结构,反在于消除它,但这种意愿在现实中实际上无法实现。由于保守的、守旧的以及自由主义文学阵营否认现实主义论的现实依据、合法性或唯一性,甚至简单、粗暴地将之判定为公式化的东西和追新情结的产物*[韩]金铉:《韩国小说的可能性》,[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339页。,现实主义论也就日益被视为仅具有或主要具有区别意义的身份符号。如此一来,双方既在张力关系中被激发出一定的成长活力,又被迫日渐固化自己的身份特征和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确保自身话语权的同时拓展新的话语空间(例如实现崔元植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会通)便很难了。*白乐晴对自然主义还是包容的。他认为,要成就韩国式的现实主义,就不能轻易抹杀自然主义小说特有的成就,因为这不是单纯的小说技法问题;对于更加切实地探索主体性地接受外来文学之路的工作来说,自然主义文学的科学主义所包含的哪怕是不完全的人类解放精神,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韩]白乐晴:《站在民族文学的新关口》,[韩]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第32页。其结果便是各自固守自己的唯一性。一方坚持说韩国文学所能采用的唯一技法是能够揭露现实主义之虚伪性的批评和象征技法,即“洞察力”和“想象力”*[韩]金铉:《韩国小说的可能性》,[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367页。;而另一方则声称只有现实主义才是真正的美学,是人类艺术所能达到的极致,除此之外的其他美学都是虚伪的*[韩]任轩永,《韩国文学的任务:民族现实主义之路》, [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389页。。白乐晴下了很大气力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理论性探讨,于1980年代前期发表了三篇容量大、辨析深刻、颇具启发性的重要文章:《关于现实主义》(1982)、《关于现代主义》(1984)和《现代主义讨论补缀》(1985)。白乐晴强调区分“近代性”与“近代主义(以及近代化论)”“现代主义”两组概念, 主张对“大体上与中世纪秩序崩溃后人类的全部经验相联系”的“近代性”, 既要看到其创造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压制性的一面,而对试图片面地将“近代性”之发展的一面加以绝对化的“近代主义(和近代化论)”以及“虽然在字面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压制性层面进行反驳,而实际上却与这种压制性是表里关系”的“现代主义”艺术理念,则要全部加以拒斥。*[韩]白乐晴:《现代主义讨论补缀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5年,第475-476页。基于这种区分以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现实性对立,是当今世界文学的主要矛盾”这一基本认识 ,白乐晴一方面主张民族文学论应对西方的非写实主义艺术持更具弹性的姿态*[韩]白乐晴:《关于现实主义》,[韩]金润洙、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2年,第319页。,一方面又表示“坚信不能轻易抛弃‘现实主义’这一名称”*[韩]白乐晴:《关于现代主义》,《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5年,第442页。。为此,甚至创造了“后现代现实主义(post-modern realism)”这一概念来指称“经历了现代主义洗礼的现实主义”。*[韩]白乐晴、[美]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对谈):《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文化运动》,《创作与批评》1990春季号,第285-286页。可以看出,白乐晴的现实主义主张既有经的层面又有权的层面,固守是权而不是经。作为经的开放性与作为权的固守即闭锁性构成了内在的张力关系,二者随着现实的变化不断在冲突中寻找并达成新的平衡。这在外表上便呈现为其现实主义论的不断“变奏”,并因而被困惑不解的批评家们批评为过于具有包容性和圆通性。*黄钟渊在肯定白乐晴之现实主义论的功绩时说:白乐晴的现实主义论对韩国文学免于两种危害做出了很大贡献,一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技法游戏之害,二是受教条的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之害。但他同时又指出,白乐晴所说的现实主义,一方面参照了典型性、客观性、党派性等美学尺度,另一方面,又包含了“文学固有的辩证法”这种一般论性质的假说以及“至公无私”这样的道德标准,因此“过于圆融自在”([韩]黄钟渊、白乐晴(对谈):《韩国文学成就何在》,《创作与批评》2006春季号,第299页)。柳浚弼则将相关批评意见概括为:“人们多次指出,白乐晴的现实主义论已经超出了文学论的范畴,具有明显的指向‘精神’或‘态度’的特点”,并试图以白乐晴现实主义论中的“均衡感”这一用语为轴心,来统合黄钟渊所指出的“过于圆融自在”的诸多方面(参见柳浚弼:《白乐晴现实主义论的问题及现实意义》,《创作与批评》2010年秋季号,第373-380页及注释28)。笔者认为,这种“指向‘精神’或‘态度’的特点” ,正暗示出白乐晴之现实主义论的经的层面。正因为有这个经的层面的存在,白乐晴的现实主义论才在固守的同时,显现出“过于圆融自在”的开放性。对此,白乐晴回答说,他并非卢卡奇那样的现实主义论者,现实主义之于他不过是个抓手而已。换言之,对他来说,“现实主义”并非严密的分析性概念,而是一个像“民族文学”那样的论争性概念。*[韩]黄钟渊、白乐晴(对谈):《韩国文学成就何在》,《创作与批评》2006春季号,第299-300页。白乐晴时隔多年之后的这番话可谓道破天机,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现实主义论提供了解开疑团和困惑的关键钥匙。白乐晴的上述发言显然更强调了其现实主义论的权的一面,而权的主要目的,一是指向独裁政权的社会批判,二是构建民族文学论的《创作与批评》身份,其中后者针对的应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现实性对立”这一“当今世界文学的主要矛盾”在韩国文学中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是这一主要矛盾的韩国式境遇。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性对立”的存在,尽管其他民族文学论者(如崔元植)也曾试图使民族文学论在方法论上获得某种程度的弹性,但从整体上看,白乐晴本人及其主导的民族文学论自始至终都固守着现实主义美学价值,甚至民族文学论向女性话语、生态话语等方向的拓展都未能改变这一固守。
围绕现实主义问题,1970年代共发生了两次大的论争,以1970年和1978年这两个时间点为焦点画出的震幅椭圆中,又交叉着许多不同震源的小规模论辩。通过这些论争,现实主义美学观念深入文坛,确立了其权威性地位。这种权威性虽然在接下来的1980年代受到来自激进民族文学论者的挑战,但直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初才遭遇到真正的危机。虽然用“现实主义 VS 现代主义”这种对立模式来概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文学史难免有将复杂的文学事实简单化的危险,但这一对立模式对认识现实主义话语和现代主义话语在彼此对立中相互塑造和强化的悖论性关系却十分有效,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在构建和维护自身身份的过程中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以及具有何种正面和负面的意义。
三、1980年代的现实主义论及其功能
如果1970年代的文学话语对立可简要概括为左、右阵营之对立的话,1980年代最触目的便是左派阵营内部的话语分裂。白乐晴充分认识到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论在理论建构方面的薄弱性,期待在新的十年里,在加强民族文学论各分支间对话的同时,进一步深化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韩]白乐晴:《关于现实主义》,[韩]金润洙、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2年,第317-318页。《创作与批评》于1980年夏季号集中推出了三篇重要的现实主义论文(林哲规的《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潘星完的《德国市民文学的可能性及局限——卢卡奇与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论争》,李东烈的《文学的社会指向性》),开启了《创作与批评》阵营1980年代现实主义话语建构的帷幕。但不幸的是,由于期刊旋即被禁,且时间长达8年(其间虽然于1985年尝试以不定期刊物的形式发行了一期,但因此导致出版社执照被吊销,直至1987年才通过抗争发行了《创批1987》,次年即1988年得以正式复刊)之久,因此,民族文学论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失去了自己的大本营,只能通过出版图书的方式发出声音,或转战其他友情刊物,理论发展因而大受阻滞,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受到极大削弱。加之民族文学论自身已具备一定的体系性,虽仍有待修正、坚实和完备,但内部构架已相对稳定,理论机制也已相对成熟,依照自身的逻辑发展难以迅速与急遽变化的时代对接,因此,尽管白乐晴本人尽力追随时代步伐,民族文学论自身应对现实的有效性也并未完全丧失,但仍失去了韩国文坛话语的先锋性和领袖地位。1980年代的激进民族文学论话语对文学之社会功能的强调,对国家统一的强调,以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倡导,都可视为在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延长线上的新发展,但在倡导民众文学主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大众化方面,却实现了实质性突破。二者的殊途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现实变化的原因。以光州事件为标志的政治斗争的激化,未能与同窗、同事、同志们一起牺牲在斗争现场或者未能给他们提供有效帮助的沉重负罪感,民众力量的崛起*许多韩国学者都认为1980年5月的光州民众抗争是1950年之后韩国社会运动的分水岭,在促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市民性民主化运动”向1980年代“真正的民众运动”跨越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的思考由对部分的、现象性的社会矛盾进行孤立的批判,前进到了对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进行展望的新阶段([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70-171页)。金明仁明确道出了“真正的民众运动”的结构成分:“自由主义民主化运动的力量在1980年法西斯镇压下受挫后,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等生产劳动大众以及采纳了其世界观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手中。” [韩]金明仁:《从市民文学论到民族解放文学论》(原载《思想文艺运动》1990春季号,第202页),转引自[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64-165页。,民间艺术文化的进一步繁盛,优秀工人和农民作品的涌现(诗歌、小说、经历自述、报告文学、现场手记)的出现,MOOK运动(如《实践文学》《我们时代的文学》《文学的时代》等),同人杂志运动(如首尔的《诗与经济》、光州的《五月诗》、大田的《人生的文学》、大邱·青州的《分裂的时代》),地方文学运动(如釜山的“5·7文学会”、光州的“光州民族文学协会”、大邱的“大邱·庆北民族文学会”、大田的“忠南民族文学会”、青州的“忠北民族文学会”等),文学体裁的扩大,社会结构论争等,*始于1980年代中期,大致可分为强调阶级矛盾的“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和强调民族矛盾的“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论”两大主张,重要论争文献收入朴炫埰、曹喜昖合编的《韩国社会结构论争》1-4卷(首尔:竹山,1989-1992年)。[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71页。这些都是1970年代所不具备的。它们既是1980年代文学运动的内容和成果,又是激进民族文学话语得以产生的现实物质基础。《创作与批评》的停刊使左派文学话语阵营一时间失去了纵向秩序,转入多元化、平面化的百家争鸣状态。这固然可被视为此前遭压抑的新生左派力量之思想能量的解放,但视之为进步文学阵营的崛起也许更为恰当。“民众的民族文学论”、“民主主义民族文学论”、“民族解放文学论”、“劳动解放文学论”,等等,这些不同名称的进步文学话语也被统称为“激进的民族文学论”,其问题意识和理论主张中既有对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继承,又有断裂、超越和创新。*近年来,有韩国青年学者从文艺民主、颠覆文坛话语霸权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评价1980年代新兴的进步文学运动。笔者部分赞同其见解,但不主张强调《创作与批评》的被禁与新兴进步文学运动之繁盛二者间的因果联系,认为这既有可能造成对全斗焕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行径的混乱认识,又会遮蔽新兴进步文学运动崛起的其他现实要因(李大可、[韩]全炯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80年代韩国的译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第58-59页)。白乐晴在谈到1980年代的同人杂志、合作诗集以及MOOK运动的繁荣情况时说:这表明民族文学已经深深扎根,不依赖于一两个杂志的存亡([韩]白乐晴:《站在民族文学的新关口》,[韩]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第47页),笔者赞同白乐晴的这种见解。
第一个变化是民众文学论突破了民族文学论框架,由其要素和分支扩大为包括性的上位概念,而“民族”则退居下位,由“民族的民众”刷新为“民众的民族”,现实主义论成为民众文学论的下位概念,被表述为“民众的现实主义”,知识分子世界观改造、民众典型以及民众文学主体是其主要的理论支点。前文已经论述过,由于民族文学论的核心概念“民族文学”在能指层面上与官方的民族主义话语以及守旧的民族文学话语存在共名现象,为了与之区别,白乐晴除了对自己的民族文学概念进行基本阐述外,还构建了民众文学论、现实主义论以及第三世界文学论这三个下位话语,以彰显、强化自身的正体性。这个过程是个不断吸纳、完善的系统构建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民众文学话语被吸收进民族文学论中,相关论者也被纳入民族文学论阵营。但到了1980年代,某些曾被纳入民族文学论阵营的民众文学话语被单独拣选了出来,纳入了新的思想脉络,或被作为新思想脉络的起点。最典型的事例是诗人金芝河的名文《讽刺还是自杀》(载《诗人》1970年第7期)被标举为民众文学论的镐矢,成为1980年代新的话语风暴的最切近的传统。*[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50页。实际掀起这场话语风暴的则是金明仁的长篇评论《知识分子文学的危机与新民族文学构想》(载《文学艺术运动》1987年第1期)。*在此前一年,蔡光锡发表了《从小市民的民族文学迈向民众的民族文学》,有学者认为,该文使民族文学论与激进的民族文学论之间的对立“呼名化”了([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93页)。不过,一般认为,激进的民族文学论之产生巨大的影响是自金明仁的该评论始。该文高调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以及民众文学主体的问题,并详细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在世界观问题上,1970年代的现实主义论者就反对仅将现实主义视为文学思潮或文学技法,强调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和世界观问题。白乐晴通过讨论为什么其他作家采用了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样的题材和自然主义技法,却未能继承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这一问题,将世界观、人生观要素提到了现实主义的核心位置, 并提出了克服小市民意识的问题。*[韩]白乐晴:《市民文学论》,《创作与批评》1969年夏季号,第473页。1970年代晚期,廉武雄更是明确提出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作家有多少才能或者写作技巧如何,而在于站在谁的立场上、为了什么而使用才能”*[韩]廉武雄:《小说的最近倾向及展望》,《创作与批评》1978春季号,第318页。的主张。金明仁继承了前一时代的上述问题意识,在《知识分子文学的危机与新民族文学构想》中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但他不是主张将小市民意识提升至市民意识,而是主张将小市民意识提升至“生产大众的世界观”。而改变世界观的途径之一,金明仁认为,就是到劳动现场,与工人、农民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一方面接受工人、农民的影响,一方面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以便使他们成为民众文学的写作主体。
虽然在白乐晴1970年代的论述中也提到了对民间文学进行文学史挖掘的问题,但民族文学论的民众文学论主要是为民众代言的文学论,主张平民文学中的平民意识需要被提升至市民意识。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主要关注的则是西方文学体裁范畴内的小说和诗歌,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文学的民众性,一方面对经典文学表现出宽容态度,认为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不同领域的同志关系,只要作家是站在民众立场上,即使其现实主义作品一时难以被民众理解和接受,作家及其作品也仍会受到民众的喜爱(如金洙瑛)*[韩]白乐晴:《文学的与人的》,《创作与批评》1973夏季号,第455-457页。,显然民众文学论更看重的是作家的民众立场问题。应该说,白乐晴的主张具有务实性,符合政治联盟的实际运作原理,尤其是他根据参加变革运动的实际经验提出的作家与民众的关系是不同领域的同志关系这一见解,实际上提出了首先将民众视为同志还是视为受众的问题,为重新思考一直困扰左翼文学的作家(乃至知识分子整体)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但是,在1980年代民众运动高涨,并出现了优秀的工人、农民作者以及大量的“亚文学”形式(经历自述、报告文学、现场手记等)的新现实条件下*柳文善特别强调这一现实变化是激进的民族文学论诞生的根本现实依据,并将1984年6月14日“民众文化活动协会”的成立视为这种变化的象征。[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93页。,激进的民族文学论者对民众之需要文学的程度和迫切性都有了不同看法,文人文学(专门文学)获得真正民众性的可能性受到怀疑乃至否定,“大众主体文学论”(代表人物是金明仁和蔡光锡)被视为“民众的民族文学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力推崇、发掘和培养工人、农民作者也被视为建设民众的民族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金度渊等人提出了“扩大体裁”的主张。可以说,在激进的民族文学论所提出的“作为运动的文学”(以及在此延长线上的“现场性”)、“集体创作”、“扩大体裁”、“民众创作主体”以及“文学的大众化”等主张中,“扩大体裁”堪称关键举措。这是因为,工人、农民所创作的诗歌和小说符合文人审美水准的很少,而且“现场性”这一要求也极大制约了对体裁的选择。不过,虽然表面看来,“扩大体裁”是对既有的文学定义和文学秩序提出了挑战,但实际上,它恰恰是以对既有的文学定义和文学秩序的认可为前提的。比如说诗歌、小说等传统体裁在某种情况下会妨碍文学成为运动的文学和认识的文学,不适合用来做“谋求大众性的主要战术单位”,因而需要通过边缘体裁进行各种形式实验,或者创造全新的体裁(民间故事传说、趣话、俗语、谜语、歌词改编、谶语、板报诗、板报小说等反映民众感情、体现民众美感的民众次元的体裁),以开辟获得广泛大众性的道路。*[韩]金度渊:《为了体裁的扩大》, [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99-130页。这实际上意味着承认诗歌和小说有自己特定的文体约束或者说文体自律性,意味着对民众次元的体裁的采用主要是基于对特定现实语境的战术考虑,因而并不具有普遍的文学范式意义。
1989年,金明仁和蔡光锡先后明确提出了“民众的现实主义”概念,将塑造普通工人典型作为该概念的规定内涵之一,进一步完备了“民众的民族文学论”的理论框架。
第二个变化是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话语成为民众文学论者构建理论体系时的重要研究对象和参照系,论者不忌讳凸显自身的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在1970年的座谈会上,自称属于4·19一代的金铉认为,当下的韩国不存在西方式的市民阶层,也不存在市民社会风俗,因此,也就不存在与市民社会相匹配的现实主义,存在的只能是观念的现实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金炳翼虽然认为当时韩国的现实主义论不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也未支持、鼓动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但仍指出了其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矛盾、描写平民生活等方面的共同点。*[韩]金炳翼:《现实主义技法及精神》,[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441-443页。金东里也以1960年代后期以后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批评家大多(约80%)看重否定现实、主张平民意识、革新和弘扬社会正义的作品为由,将之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或进步主义的写实主义”。*[韩]金东里:《韩国文学思想的特质及背景》,[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462页。上述贴标签式的言论都遭到了廉武雄等民族文学论阵营评论家们的反驳。
然而,与试图同时超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者相比,1980年代的激进民族文学论者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寻求解决方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作为需规避的棍子和帽子,而是作为规范和法则被树立为正面标尺。“民众的民族文学论”主倡者蔡光锡和金明仁先后提出了“民众的现实主义”概念,按照金明仁的阐释,“民众的现实主义叙写工人阶级主导的革命实践及革命展望,塑造普通工人典型,就此而言,它超越了批判现实主义,但尚未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韩]金明仁:《现实主义再认识(1)》(原载《文学艺术运动》1989年第3期),转引自[韩]金龙洛:《民族文学论争史研究》,首尔:实践文学社,1997年,第189页。,“可以说是在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扬弃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保留这二者之间产生的过渡性的或妥协性的用语”*[韩]金明仁:《为了实践的现实主义》,《实践文学》1993年第3期,第248页。。曹贞焕主导的“民主主义民族文学论”及“劳动解放文学论”也提出了“工人阶级的现实主义方法”及“工人阶级党性”的概念。*[韩]林洪培:《现阶段工人阶级现实主义的论争焦点及展望》,《实践文学》1990年第6期,第257-273页。此外,该时期(1980年代下半期至1990年代上半期)出版、发表了很多译介、研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书籍和文章,也有一批相关主题的学位论文出现。这些文化现象,都可视为激进民族文学论之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冲击波的产物。
第三个变化是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有学者将1980年代的进步文学话语梳理为白乐晴的民族文学论(现实主义),金明仁等的民众的民族文学论(民众的现实主义),《劳动解放文学》的劳动解放文学论(工人阶级现实主义),“工人文化艺术运动联合”的劳动解放文艺论(党派的现实主义),《绿豆花》的民族解放文学论(民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文学与社会》团体(参见[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95页)。按照这种梳理,最后的《文学与社会》团体并没有单独提出自己的文学论和方法论主张。为了讨论方便,笔者依据其重要成员成民烨的核心文学主张,暂且称之为“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及其现实主义论的加入。1970年代的韩国文坛呈现为《创作与批评》和《文学与知性》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的格局。两大期刊被迫停刊后,原属《文学与知性》阵营的几位年轻评论家(成民烨、郑科理、洪贞善)创立了MOOK《文学与社会》,标举民众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一定的左派倾向。不过,该群体虽然在倡导现实批判精神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面与1970年代的民族文学论有某种一致性,在主张以民众文学论超克民族文学论方面与激进民族文学论有一定共同性,但在强调文学之“文学性”方面却沿承了《文学与知性》阵营的自由主义立场。
具体来说,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拒绝被视为纯文学论者那样的文学主义者。他们不仅一般性地认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认为由于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已在某种程度上展开并导致了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激化这一客观条件,以及由4·19革命和6·3抗争促成的民众意识的成长这一主体条件,使民众文学获得了摆脱卡普文学和解放初期的民族文学之命运——因观念性地、抽象地认识现实,最终只能是一场未获广泛大众呼应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封闭性运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宣告民众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批评白乐晴的市民文学论未能在小市民意识泛滥的表象下看到民众意识的成长*[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46-149页。,认同经济学者朴玄埰将工人视为当代民众的基本成分,将农民、小生产者、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视为民众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他们的这些主张与激进民族文学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看待文学与民众运动之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们与后者产生了原则性分歧。激进民族文学论者认为,民众文学从属于民众运动,更确切地说,从属于民众运动的民众文化运动,主张民众文学首先要服从民众运动的规律,而不是现实主义的规律。而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则认为,民众文学与民众运动是平等的,二者都受现实规定,而不是文学受民众运动规定,故而反对追求现场性的“作为运动的文学”,并将之判定为非文学的标语口号,提出了文学性与运动性相统一的课题。*[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75-176页。显然,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的上述主张是存在思考盲点的。其问题在于,它将民众运动排除在了规定文学的“现实”之外,忽略了民众运动固然受现实规定,但它本身也是一种现实,是影响文学的现实的一个方面。换言之,“民众文学受现实规定”这个判断成立,但是,“民众文学受不包括民众运动在内的现实规定”这个判断显然无法成立。出现这种逻辑错误的原因在于,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只看到了民众运动的意识形态性一面,却忽略了其更重要的现实属性。
虽然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并不反对甚至支持将标语口号作为运动宣传形式,但由于严格区分所谓标语口号式作品与真正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已经与自己提出的将民众文学视为“战略性的、相对的概念”*[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45页。这一充满智慧的弹性见解发生了冲突。作为“战略性的、相对的概念”之民众文学必然是从属于民众运动的,必然是向着“现场性”和“运动性”无限敞开的。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自我矛盾,应与其现实主义论对民族文学论的偏离分不开。前文曾论及,经过1970年代围绕现实主义的持续论争和探讨后,现实主义话语在韩国文坛确立了牢固的权威性,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超出民族文学论框架之外的独立地位。*1980年代,韩国学者开始从现实主义视角重新考察和撰写韩国文学史。[韩]柳文善:《南韩现实主义论的展开过程》,《实践文学》1990年第9期,第294页。现实主义论从属于民族文学论,意味着它与民族文学论所主张的实践性、行动性和运动性*白永瑞曾论及恢复《创作与批评》的运动性的问题。在其撰写的《以恢复运动性来实现自我革新的创批》一文中,有三处文字有助于我们理解《创作与批评》的“运动性”:A.“这里所说的运动性意味着由既要摆脱日常生活的惰性,又要回到日常生活现场并扎根于其中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所产生的运动特性,也即力量。” B.“但是我们所说的运动性的恢复并不局限于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那样的制度外的斗争方式。经过自我更新的进步力量要使制度内外的活动配合进行。”C.“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今年起,《创作与批评》会更加贴近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尖锐批评并揭示对策,全力做一个论争性写作的模范。我切实感到,这正是结合了文学想象力、现场实践经验和人文·社会科学认识的《创作与批评》与众不同的长项,而且它也因此就有了与之相称的必须做表率的义务。”(参见《创作与批评》,2006年春季号,第3-4页)。笔者认为,A引文是针对当下的新现实(即“日常生活”)而对昔日《创作与批评》 的“运动性”概念所进行的调整,B引文和C引文才是对作为《创作与批评》传统的“运动性”概念的阐释。是不相排斥的,而脱离民族文学论框架的现实主义论,则意味着游离实践性、行动性和运动性的可能。激进民族文学论者蔡光锡将“民众运动的规律”与“现实主义的规律”对立起来,正反向印证了这种游离的存在。白乐晴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学与行动”的问题,认为“在今天的民族危机中,要搞民众文学的理由,不是为了仅仅被动地反映和传播现有的民众意识,而是在反映的同时,还须发挥艺术作品的能动作用,即促使民众觉悟到捍卫民族生存权利、完成反封建的市民革命这一客观使命并将之付诸实践”*[韩]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的概念》,《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Ⅰ》,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78年,第131页。。在某些行文中,他甚至直接使用了诸如“忠实地服务于分断的克服”、“用民众意识武装起来的庭院剧和庭院舞”这样的表述。*[韩]白乐晴:《站在民族文学的新关口》,[韩]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第26、48页。前文引用过的金铉之所以指责民族文学论者将是否具有煽动民众的意向视为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标尺,其所针对的也正是民族文学论之现实主义论的这种行动指向*[韩]金铉:《韩国小说的可能性》,[韩]洪申善:《我国文学论争史》,首尔:语文阁,1985年,第339页。,而金钟哲之所以说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有别于西方的现实主义传统,应该也是着眼于此。可以说,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首要关心并提出的不是现实主义文学自身规律的问题,而是改造社会的变革实践问题。在民族文学论那里,现实主义的功能在于构建和凸显民众性、脱意识形态性以及《创作与批评》身份等,但并未被赋予保障民族文学之“文学性”的功能,它保障的是对小市民意识的克服。就此而言,在实践性、行动性和运动性方面,民族文学论是向着激进民族文学论敞开的,或者换言之,激进民族文学论所倡导的“作为运动的文学”,是处在1970年代民族文学论的行动论和运动论的延长线上的。*白乐晴在分析1970年代的分断题材作品时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比起概念化地呼喊统一、慨叹分断的诗歌或小说来,那种正直、深刻地描述了分断时代之人生的作品,即使没有在字面上描绘国土分断或思想对立,作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其中蕴聚更切实的克服分断的意志(参见[韩]白乐晴:《站在民族文学的新关口》,[韩]白乐晴、廉武雄:《现阶段的韩国文学Ⅱ》,首尔:创作与批评社,1983年,第23页)。由此看来,在白乐晴那里,现实主义的运动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像1980年代的激进民族文学论所主张的那样直接服务于变革运动的“现场性”。尽管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也认可文学的社会功能,也认为现实主义论对探讨民众文学的艺术原理和形式法则来说必不可少,*[韩]成民烨:《民众文学的原理》,[韩]成民烨:《民众文学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4年,第158页。但由于对他们而言,这种功能只能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即以文学不丧失其相对独立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否则就丧失了被称为文学的资格,因此,其现实主义论严格来说并不处于民族文学论之现实主义论的延长线上,而是处于游离出民族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之延长线上。*笔者认为,就成民烨来讲,其现实主义论中还隐蔽着对当时中国文学话语环境的敏锐知觉和洞察这一背景,也有来自现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资源。对激进民族文学论的激烈批判之所以主要不是来自受到激进民族文学论挑战的民族文学论阵营,而是来自与激进的民族文学论同属于1980年代的民众文学论这一大阵营的文学本位的民众文学论者,其原因大概正在于上述谱系关系。现实主义论被用于强调文学的自律性或文学性,这表明依托1970年代的左派民族文学论树立起权威地位的现实主义论已向偏离乃至背离、对抗其原有的行动性、运动性指向的方向分化。
责任编辑:孙昕光
Function of Realist Theory in the Discourse of Left National Literature of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70’s to the 1980’s
Li Dak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s the leading and predominant theory of the Left Literary Camp in South Korea during the 1970’s to the 1980’s, realism was one of the three basic theories of national literature,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literary theory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s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literary theory. Realism of the 1970’s bore the following attributes, namely the popular character to construct the People’s Literature, the character to transcend the Cold War ideology, and that to construct the Changbi identity. And the Left national literary theory of the 1980’s headed for differenti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and Socialist realist theory beca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realist theory of the radical national literary discourse.
realism theory;national literature;the People’s literature; Cold War ideology; Changbi identity
2016-03-26
李大可(1966—),女,山东微山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I109.5
A
1001-5973(2016)03-00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