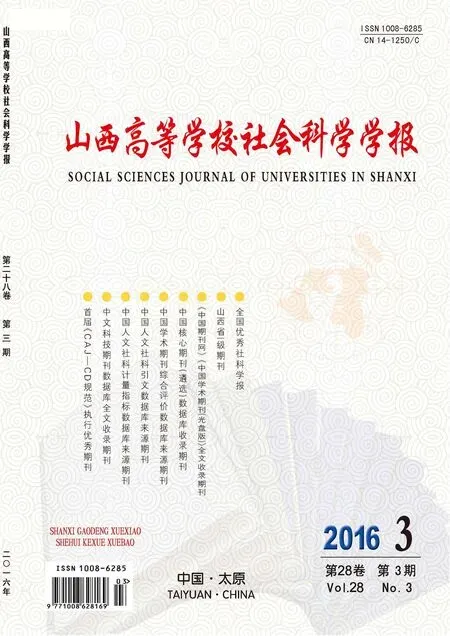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究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熊亚文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究
——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熊亚文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尽管《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但却刻意回避了为受贿罪设置独立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议题,并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司法适用难题。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应以贪污、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适当兼顾经济发展变化和反腐政策需求,并以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为参考而做出。基于此,应当分别构建“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在维持现有入罪数额标准不变之基础上,以一定经济指数为参照,合理、科学确立适当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量刑动态数额标准。
[关键词]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刑法修正案(九)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3.015
201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九》)对贪污受贿犯罪做出了重大修改,确立了“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但是,此次立法修正不仅刻意回避了构建独立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等重要议题,而且还留下诸多需要继续讨论的司法适用问题。本文以《修九》为背景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立法与司法完善有所裨益。
一、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立法修正及其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有两大特点:一是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二是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以刚性的具体数额为核心标准。尽管这样规定是根据当时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和司法机关的要求作出的,但随着近2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贪污腐败现象的恶化,这种以具体数额为定罪量刑核心标准的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有效惩治贪腐犯罪的现实需要。有关贪污受贿犯罪的司法实践与立法现状早已相差甚远。其一,贪污受贿犯罪的实际数额起点被大幅提高,司法机关“抓大放小”现象普遍;其二,巨额(10万元以上)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区间相同,量刑结果不具有合理性差异;其三,贪污受贿犯罪的非数额情节依附于犯罪数额,没有充分发挥量刑调节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存在两大固有缺陷。一方面,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使数额在定罪量刑标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唯数额论”。数额并不能完全体现贪污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无法全面评价和反映贪污受贿行为的不法和罪责,这是刚性数额标准本身固有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存在严重的滞后性,无法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地区经济差异的基本国情,不仅会导致刑事立法和司法的机械性、僵化性,不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还会变相加重对行为人施加的刑罚量,从而导致刑罚过剩,有损刑法公正、谦抑的基本精神。
鉴于此,《修九》第四十四条将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对犯贪污罪(受贿罪同等处之——笔者注)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由此,《修九》删去了1997年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之规定,原则设置了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并对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保留适用死刑。
不可否认,本次立法修正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刚性具体数额标准修改为弹性的“数额+情节”模式,使其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贪污受贿犯罪的不法与罪责,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性。但与此同时,《修九》不仅刻意回避了为受贿罪设置独立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议题,而且其确立的概括数额标准及其他情节标准,必然会使司法机关面临如何确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如何把握其他情节事实的内涵外延以及如何处理数额与情节在适用上的冲突和协调等司法适用难题。
首先,“贪污罪与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表征、侵犯的法益、犯罪成本等都不相同,适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不够科学和合理,对其定罪量刑标准应当予以分立。”[1]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然而,《修九》对此却刻意予以回避,未对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做出修改。将贪污罪和受贿罪适用同一定罪量刑标准,无法体现二者罪质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刑法评价的不全面、不充分,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其次,尽管《修九》确立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三个量刑档次的概括数额标准体系,但却未对是否调整定罪数额标准、如何拉开不同法定刑档次所对应的量刑数额标准做出明确答复,而是将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交由“两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由此引发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如何确定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激烈争论。特别是对于定罪数额标准,由于关系到贪污受贿的罪与非罪问题,争论最为激烈。主流观点认为,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应提高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标准,宜以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主要基准,并在参酌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CPI)、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基础上,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数额(起刑点)设置为3万元[2]。反对观点则认为,基于民意的表达、犯罪预防的基本原理、中央惩治腐败的基本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及世界各国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路径等有关的理论,贪污贿赂犯罪的起点数额不能提高[3]。其中,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基于打击贪腐犯罪“零容忍”的政策考量,应维持现有的5000元入罪标准,在此基础上拉开不同法定刑档次所对应的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4]。各家观点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使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确立曾一度陷入困境。
最后,尽管《修九》赋予贪污受贿犯罪其他情节独立的定罪量刑功能,并确立了“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四个量刑档次的其他情节标准体系,但却并未明确其他情节的具体内容,以及各个具体情节在定罪量刑中的权重大小。这就必将导致司法机关的实践中在适用其他情节定罪量刑时无所适从,从而无法准确、全面地根据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刑罚裁量活动。此外,《修九》除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外,基本回避了在数额与其他情节并存的情形下,如何处理数额与其他情节的关系问题[5]。如果贪污受贿犯罪“数额较大且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且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巨大且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或者其他“数额”与“其他情节”任意组合并存的情形,司法机关应该如何考量并适用“数额+情节”的二元标准进行刑罚裁量,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总之,《修九》仍然未能从根本上化解1997年刑法规定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存在的固有缺陷,也没有分别制定出充分反映贪污罪和受贿罪法益侵害本质的定罪量刑标准,《修九》自身确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样遗留诸多需要继续探讨的具体适用问题。
二、构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刑法基点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应以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在此基础上适当兼顾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以及反腐政策的需求,并积极借鉴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而做出。
(一)以贪污、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
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而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要求,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大小时,既要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为基础,又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把握行为和行为人各个方面因素所体现的危害性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值得强调的是,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指导定罪量刑等司法活动,还能指导具体罪名法定刑设置等立法活动。因此,在立法上为具体罪名配置相应法定刑时,也应当考虑该具体犯罪侵害法益的内容及其背后所体现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由于侵害法益的内容不同,因而行为性质、不法内涵及程度均不同,其法定刑配置也应当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有时还不仅仅是刑罚量上的区别,而是刑罚性质以及刑罚量的评价标准的区别。
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内容可以决定刑罚的性质及刑罚量的评价标准——对于侵害生命健康法益的犯罪,其刑罚性质应是自由刑和生命刑而非财产刑,其刑罚量的评价标准应是行为动机、手段、结果等犯罪情节而非数额;对于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其刑罚性质应是自由刑和财产刑,其刑罚量的评价标准应以数额为主、以其他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情节为辅……总之,具体犯罪侵害法益的内容,决定相应刑罚的性质及刑罚量的评价标准,这是刑法立法为具体犯罪设置法定刑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因此,构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明确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保护法益,进而根据二者保护法益的内容来确定相应刑罚量的评价标准,如此方能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兼顾经济发展变化和反腐政策需求
贪污受贿犯罪是典型的数额犯,数额犯的数额大小是衡量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核心考量因素。受经济发展变化影响,相同数额在不同时期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存在差别。因为数额以货币额为计量单位,而货币额与价值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货币的币值是不断变化的,同一货币额在不同时间会代表不同价值量。我国从1997年至今的经济发展变化,尤其是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已将法律规定的具体数额标准无形改变,其结果,或者在同一个量刑幅度内加重处罚(隐性的刑罚过剩),或者上升至上一档法定刑幅度内加重处罚(显性的刑罚过剩)。这种因评价标准固化而导致的立法严重滞后,已经对贪污受贿犯罪,尤其是犯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案件,造成显著的刑罚过剩现象。我们应当意识到,要想保持同等水平的惩罚意义和教育意义,定罪量刑数额应当随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而不是用十几年前的标准处罚今天的犯罪行为,如此才真正符合现代法治的“责罚相当”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构建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必须将经济发展变化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以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和适正性。
而变频调速的特性以及无可比拟的节能功效在机械调速领域脱颖而出。因此,怎样更好地把变频调速技术引入并应用到起重机械行业中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领域[1]。本文所研究的变频工况下的起重机械起升机构动力学仿真与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仅根据经济发展变化一味提升贪污受贿犯罪的入罪标准,还需要处理好其与当前中央打击腐败犯罪“零容忍”政策之间的关系,对二者适当兼顾、平衡。尽管贪污受贿犯罪的“入罪标准不可能与党纪、政纪处罚标准完全一样。对腐败的‘零容忍’不应被理解为腐败行为一律入罪、入刑”[6]。但是,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打击腐败犯罪,政府和社会对贪腐犯罪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反腐败“零容忍”政策集中反映了官方和民间从严惩治腐败犯罪的态度。在此国情和政策背景下,冒然提高贪污受贿犯罪的起刑点,显然有悖国家和民众对反腐工作的期待。因此,较为妥当的做法应该是,维持现行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刑点不变,在此基础上拉开其他档次量刑数额标准的幅度,如此便兼顾了经济发展变化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影响,以及反腐“零容忍”政策的需求,也有利于实现此次立法修正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以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为参考
惩治贪污腐败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考察域外有关贪污受贿犯罪的立法实践,有助于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立法的完善及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衔接。尽管由于历史文化、贪腐形势以及立法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域外各国(地区)立法不尽相同,但仍有许多共通性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其一,将贪污罪与受贿罪的处罚严格区分,分别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在刑法分则中,凡是单独定罪的犯罪行为均有其单独的法定刑,只有我国贪污罪和受贿罪共用法定刑,这种立法例世所罕见[7]。综观国际社会的立法通例,均是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分别定罪量刑。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性不同,前者作为财产犯罪,其保护法益主要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危害性主要通过贪污数额得到反映;而后者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其危害性大小往往不仅仅体现于数额多少,还同时体现于对国家机关公正权威的损害。因此,不能对二者适用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否则会导致评价不全面、不充分等问题。
其二,对贪污罪和受贿罪规定罪名体系,形成层次分明、严而不厉的犯罪群。在日本、法国、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刑事立法中,对多发性犯罪设计系列犯罪构成或罪名体系,已经成为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技术[8]。以日本刑法为例,对受贿行为一共规定7个不同罪名,即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这7个罪名以行为的不法程度为基本线索而设定,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受贿犯罪的复杂情况,分别规定了各种不同的与单纯受贿罪在危害上相同但行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受贿罪[9]。应当说,罪名体系立法方法的合理使用,有利于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刑事犯罪群,但同时也需要较高的立法技术。
其三,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以数额为中心,更没有规定具体的入罪、量刑数额标准,而是综合考虑数额、主体、行为方式、后果、违反职务等诸多因素来配置刑罚。对于受贿罪,域外刑法主要根据受贿犯罪的情节轻重进行处罚,立法一般规定具体的不以数额为主要标准的定罪情节。即便有些国家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考虑受贿数额,也只是将其作为加重处罚的因素,而并非像我国刑法一样将其作为起刑数额[10]。例如,德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新加坡、芬兰等国皆将是否违反职务、是否实施违法或不正当行为、是否主动索贿、是否多次(职业性)受贿、是否通过中间人受贿、是否事前通谋受贿、是否数额巨大、是否具有特定身份等,作为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考量因素。对于贪污罪,域外刑法仅重视对贪污行为的定性,而少有规定具体数额标准者。即便有些国家刑法对贪污罪的处罚规定了具体数额,也只是将其作为适用死刑的限制条件,如越南刑法规定贪污财产价值5亿盾以上或者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可以适用死刑,而不是以贪污数额为绝对的入罪、量刑标准。
三、我国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分别构建
无论基于法益侵害本质还是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都应当分别进行。笔者认为,从贪污罪和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出发,应当分别构建“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在维持现有入罪数额标准不变的基础上,以一定经济指数为参照确立适当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动态量刑数额标准。
关于贪污罪的保护法益(客体),理论上的共识是:贪污犯罪不仅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还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是贪污罪区别于其他财产犯罪的最重要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法益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法益之间,应是一种层次递进、由表及里、因果条件关系,而非并列或主次关系。详言之,侵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是贪污行为的第一层不法内涵,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是第二层不法内涵;前者是现象而后者是本质,由第一层次进到第二层次就是透过现象特征看到本质属性;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和条件,正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才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据此,在立法论上,完全可以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作为衡量贪污犯罪法益侵害性的主要标准——贪污行为侵犯公共财物所有权越严重,其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也相应的越严重,进而其整体的法益侵害性就更加严重。由于对公共财物所有权侵犯程度的评价标准,首当其冲的应属“犯罪数额”。所以,犯罪数额应该是立法为贪污罪设置法定刑的主要标准。当然,尽管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法益的现象和原因,但这仅仅表明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必然排斥其他因素独立影响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程度。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他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因素,如贪赃枉法、贪污特定款物、贪污手段恶劣、贪污造成重大损失和不良影响、贪污导致严重后果等行为,也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反映贪污行为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程度,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一并纳入考量。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贪污罪应当确立“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定罪量刑标准。事实上,从《修九》设置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来看,其本质上即已确立了“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定罪量刑标准。尽管《修九》在形式上将“其他情节”与“数额”并重,但实际上,基于贪污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以及司法实践传统,贪污数额终究要成为司法机关判断罪与非罪以及刑罚裁量的主要标准,这一点毋庸置疑。确立“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能为“数额”与“其他情节”并存情形的处理提供方向。即在一般情况下,应以数额标准确定具体法定刑幅度的选择,在此范围内综合考量其他犯罪情节以确定宣告刑;仅在“其他情节”在贪污罪中具有更重要的实质性评价作用时,才例外地以其他情节标准确定具体的法定刑幅度,并在此范围内综合考量犯罪数额以确定宣告刑。
关于贪污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之确定,笔者认为,根据构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刑法基点,应当维持现行刑法规定的5000元起刑点不变,在此基础上拉开其他档次量刑数额标准的幅度,从而形成轻重有别、严而不厉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体系。至于“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则应通过对已生效司法判决的实证分析并参照一定经济指数合理、科学地确定。关于贪污罪定罪量刑其他情节标准之适用,笔者认为,“其他情节”主要包括:贪污手段、次数、财物性质、时间跨度、是否进行非法活动以及因贪污行为造成的损失、影响等。至于“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具体标准,则可通过借鉴现行刑法中采用“概括数额+其他犯罪情节”量刑标准模式的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予以确定。
(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
关于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历来存在起源于罗马法立场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起源于日耳曼法立场的“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纯洁性”之争。从现在的刑事立法来看,一般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即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基础,同时考虑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纯洁性[11]。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使职务行为是正当合法的,贿赂行为也会使国民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纯洁性产生怀疑,从而导致对政府、国家的不信任;更何况,实际上绝大部分贿赂行为或多或少都会对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产生影响。因此,为了保障国民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纯洁性的信赖,以及积极预防贿赂行为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纯洁性的侵犯,刑法有必要对职务行为提供前置性保护,即将一切作为职务行为对价的贿赂行为均规定为犯罪,而不论该贿赂行为是否实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如果贿赂行为已经实际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那么,其便在侵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其他不法内涵。这种法益侵害内容的增加所导致的贿赂行为的违法性提升,必然要反映到受贿罪的法定刑配置上,以此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既然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以及公正性、纯洁性(后者仅作为违法性提升的根据),那么,对受贿犯罪违法性程度的评价,核心标准应在于“职务行为”,而非“贿赂数额”。对于贿赂犯罪而言,“这种腐败所造成的代价并非贿赂本身,而是贿赂导致的低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12],数额不应成为决定贿赂行为危害性程度的唯一变量。“作为一种交易性的犯罪,人们不仅应当关心行贿人为购买公权力花费了多少价格,更应该关心公职人员出卖什么样的公权力,行贿人因此买到了什么。”[13]
据此,笔者认为,对于受贿罪应当确立“以情节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而贿赂数额则成为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对受贿罪原则规定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形,相应规定三档法定刑,并对情节特别严重,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保留适用死刑。关于“情节”的具体评价内容,应当包括贿赂数额(重要但非绝对标准)、是否违反职务、是否主动索贿、是否多次(职业性)受贿、是否具有特定身份、是否将贿赂用于从事非法活动、受贿行为是否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是否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等,并由“两高”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确定。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修九》仍将受贿罪按照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定罪量刑,这种立法惰性忽视了两罪法益侵害内容之本质区别,有待进一步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受贿罪作为一种以“权钱交易”为基本行为类型的犯罪,贿赂数额无疑是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重要参考标准。可以说,贿赂数额与犯罪情节之间是一种表里关系,即贿赂数额越大往往反映出犯罪情节越严重。因此,为延续司法实践的传统,司法解释仍然可以将现行刑法规定的5000元作为受贿罪的入罪数额参考标准,成为受贿罪“情节较重”的参考标准之一。相应地,通过对已生效的司法判决的实证分析并参照一定经济指数,可以合理、科学地确定“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中的数额参考标准。当然,与贪污罪不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意味着,贿赂数额仅仅只是一项重要的而非绝对的参考标准。即便贿赂数额达到“情节严重”的数额参考标准,但如果综合全案事实因素仍属于受贿罪“情节较重”的情形,则应当在“情节较重”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内进行刑罚裁量。
简言之,贪污罪中的贪污数额是绝对标准,而受贿罪中的贿赂数额是仅供参考的相对标准。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1):44.
[2] 赵秉志.完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思考和建议[C]∥赵秉志.刑法论丛:第4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36-37.
[3] 张兆松.再论贪污、受贿罪定罪处罚数额标准的立法完善[C]∥赵秉志.当代刑事法学新思潮: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75.
[4] 王林林.论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研究视角[C]∥赵秉志.刑法论丛:第4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58-59.
[5] 梁根林.贪污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完善[J].中国法律评论,2015(2):165.
[6] 王文华.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修改完善问题研究[C]∥赵秉志.刑法论丛:第4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43.
[7] 高珊琦,曹玉江.对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标准的重新审视[C]∥赵秉志,张军,郎胜.现代刑法学的使命: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761.
[8] 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13.
[9] 李洁.日本受贿罪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J].北方法学,2007(1):158.
[10] 卢勤忠.我国受贿罪刑罚的立法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3):84.
[11]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732.
[12] 苏珊·罗斯·艾克曼.腐败与政府[M].王江,程文浩,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304.
[13] 孙国祥.我国受贿罪的立法完善[J].人民检察,2014(3):54.
A Study on the Standards fo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es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ConsiderationsonthebasisofAmendment(Ⅸ)totheCriminalLaw
XIONG Yawen
(LawSchoolof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
[Abstract]Although in Amendment(Ⅸ) to the Criminal Law,standards for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es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have been established as judging by "amount+seriousness", the key topic about setting up an independent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 for bribery is deliberately ignored, which leaves many problems unresolved in terms of judicial application. In f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ndards for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es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should ful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tent of legal interests against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the appropriate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eeds of anti-corruption policy, and the common experiences of foreign legislation. Based on this, standards by "judging mainly by amount, supplemented by seriousness" and standards by "judging mainly by seriousness" should be constructed separately, while keeping the existing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amount of bribes and taking into reference some economic index, so as to build up a flexible standards of sum for sentencing that can reasonably and scientifically reflect the appropriat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Key words]crime of embezzlement;crime of bribery;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standards;Amendment (Ⅸ) to the Criminal Law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熊亚文(1990-),男,安徽宿松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6)03-0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