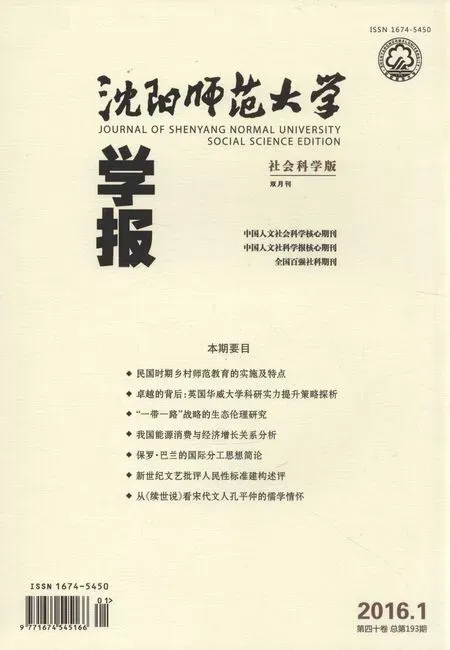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建构述评
姜桂华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文学综论
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建构述评
姜桂华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文艺的人民性,是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在中国流行开来的一个现代文艺观念、文艺价值取向。然而,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言及文学人民性的声音趋弱。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直面文学危机、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声音再次响起,诸多建构主张各有启发意义,各有值得商榷之处。王晓华、陈晓明、孟繁华等先生均在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建构问题上发表观点,为文学人民性标准的进一步建构拓展思路。
新世纪;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
新的时代语境下,文艺人民性标准的提出、讨论,属于老话新说。新建构的文艺人民性标准的内涵、适用范围、它与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文艺人民性话语及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新的文学经验之间的关系等,都需要辨析、界定。新世纪到来的十几年间,重建文艺批评人民性标准的努力已经初见轮廓。概括说来,有五种建构表现值得关注。笔者早期已对民族特性护卫意义上的人民性建构主张和底层关怀意义上的人民性建构主张进行了简要述评,这里将对另外三种于文学人民性建构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进行粗疏评议。
一、公民主权伸张意义上的文学人民性建构
2005年,王晓华发表《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一文。在该不该倡扬文学的人民性这一问题上,他表明了与一些学者大致相同的看法,认为人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建构文学的人民性在现代语境中是合法的、有意义的。但是,在如何理解文学的人民性,怎样才能建构真正的人民性这一问题上,他却表明了与其他文学人民性倡扬者不同的见解。他认为,1949至1976年间的中国文学虽然高喊人民性,却并未真正建构起人民性,相反,以人民的名义造成的悲剧和苦难却令人难忘。今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应该探索建构文学人民性的新思路,而不能延续传统意识形态的旧思路。他不同意将人民等同于底层的观点,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不可能不包括精神劳动,绝大多数精神劳动者不在底层,但不在底层的他们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将他们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岂不是使人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1]相应的,他也反对将人民性等同于阶级性或阶层性,理由在于曾经的阶级意识使斗争逻辑统治了文学艺术家,酿成了不少悲剧,今天的阶层意识容易导致作家在同情中混入优越感、把关怀引向拯救。他认为,要走出文学人民性言说的老路,建构真正的人民文学,应该找到新的话语资源,创造出新的话语体系。卢梭从每个公民个体出发建构的现代人民理论,被他视为可资中国文学界建构文学人民性借鉴的恰当资源。主张应该像卢梭那样,把人民理解为自由、自主、平等的个体(公民)通过契约建立的联合体。个性、主权身份应该是人民内涵的实质,因此,只有以公民为表现的基本单位,以公民性为根本维度的文学才是真正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正如人民性来自于公民性一样,对人民的真正关怀也必须落实为对公民的普遍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居高临下的代言和安慰,而是让所有公民意识到自己的主权者身份,作为主权者站立起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使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不能不表现所有公民的主权者身份。”[1]
应该说,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在言说文学人民性的诸多文章中,王晓华先生的观点确实有其独到之处,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将公民性理念引入文学人民性的讨论,强调个体主权意识、主权身份之于文学、之于人、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彰显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强调文学对作为公民的人的普遍关怀,意在张扬文学领域的平等和民主。力主在文学人民性问题上走出旧思路、旧资源,寻找新思路、新资源,建立新的话语体系,体现了善于反思历史、真正记取历史教训的理性和勇气,也表现了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
越是有独到见解和启发意义的文章越是能激发起阅读者的更高期待,也许正是这一阅读规律导致我们对王晓华先生的文章产生了意犹未尽之感。我们期待作者对以下问题有较明确的认识和论说:1.作者以不认可的口吻指出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主流文学以人民性为唯一维度,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是文学家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表现出尊重艺术规律、反对文学工具论的可贵艺术观。然而,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却也流露出以公民性为唯一维度来要求文学的决绝态度。那么,公民性会不会也有成为话语霸权的危险呢?2.作者不同意把人民的外延缩窄为底层、把人民性定位为底层关怀,不同意将小资文学、校园文学、白领文学等排除在人民文学之外,然而却并未对这些文学作品在内涵上如何具有人民性展开深入的论说,而且文章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中国文学缺乏公民性人民性的遗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作者所说的小资文学、校园文学、白领文学等到底具不具有人民性呢?还是说,具不具有人民性并不在于它是白领文学、校园文学、小资文学或者其他什么类型的文学,而是在于它是否呼唤公民意识呢?3.关于“代言”写作,王晓华先生表示了坚决的否认态度,我们认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可否认,强迫命令式代言写作确实存在作家与人民双重压抑的状况,然而,能由此推断出所有代言式写作都处于双重压抑状态下吗?文学史上不存在主动而不是被动受命式的代言写作吗?4.无论是别林斯基还是托尔斯泰,他们对文学的人民性的论说都是内容丰富甚至驳杂的,都有随着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特点,王文将别林斯基的言论归为阶级性的人民性,将托尔斯泰的言论归为全民性的人民性,是否有简化武断之嫌呢?5.强调所有公民在人格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以此为目标。但是,我们要不要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现象呢?面对生活中的不平等、不自由、不自主,文学何为?公民叙事如何表现其人民性?6.既然说公民叙事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已成为基础和底线,为什么只拈出惠特曼、狄德罗、左拉三位作家来说明文学的人民性呢?而且对三位作家作品人民性的阐析也很难让人对文学人民性的内容、形式、实质等形成豁然开朗的领悟。
2006年,王晓华又发表题为《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的文章,进一步申明自己在文学人民性问题上的立场。也许是得益于争论者的提醒,在这篇文章中,王先生明确承认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在文学中失语失踪状态等,是文学人民性重新热说的一个原因。也不像上一篇文章那样只把个体公民主权视为人民性内涵的全部,而是将人民性界定为有着复杂关系的整体性与个体性两个维度。虽然他还是批评俄国以及中国的文学人民性的提倡者都过于强调整体性、共性,而忽视个体性,但是他毕竟也不主张只重视个体性、完全忽视整体性的人民性。尤其是在现阶段的中国,他认为,同时建构宏大的人民叙事和个体性的公民叙事,才是文学的正确方向。这篇文章表明,王晓华先生的文学人民性建构主张思考得更全面、表述得更辩证了。我们能够领会王先生的深意:每个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的获得与全体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获得都极为重要,而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保障,将文学的人民性定位在公民权利伸张的意义上,正是对文学现实性、人文性强调的一种表现。
然而,我们还是不免有一些疑问要就教于王晓华先生。1.关于写底层。王先生似乎特别忌讳“写底层”之类的说法,因为在他看来,似乎一写底层就意味着写作者对被写者的俯视,即便表面上的仰视也免不了骨子里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免不了自上而下的拯救心态和拯救情节设置,免不了写者与被写者之间代言与被代言的双重压抑,免不了把底层写成“无个性的群集”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一写底层就一定会出现这些免不了呢?为什么写什么就注定了文学有或者无人民性呢?为什么不从具体分析作品的内容、形式、情感倾向等出发坚定文学的人民性呢?谁说俯视、仰视地写就一定写不出人民性呢?不需要看俯视、仰视什么吗?俯视该俯视的、仰视该仰视的,为什么不能写出人民性呢?以底层为对象的文学,如果真的写了“无个性的群集”,作品就一定缺乏公民主权意识吗?文学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揭示无个性、无主权意识的现状而表达呼唤个性、主权意识和主权现实的深意呢?作家的公民意识、作品的公民意识并不因作品中人物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有无而有无,这不应该是最浅显的文学常识吗?我们说,人民并不等于底层,但人民中肯定有底层存在,因此文学中出现写底层的作品就既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写底层并不一定是真正关怀底层,也不一定具有人民性。同样,写底层也并不就意味着背离人民性,一切都需要具体分析。2.关于中国文学界人民性理念的判断。王晓华先生既说:“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那部分中国文学家们仍仅仅把人民性理解为整体性或‘绝大多数民众’。这使得当下的人民性吁求仍未抵达人民性的本质。在包括我在内的汉语学者将权利主体概念引入中国文学之后,大多数提倡人民性的中国文学家还在延续上述传统。”[2]又说:“在目前展开的有关文学人民性的论争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批评家都同时强调群体利益和个体公民的价值和尊严。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人民性和中国文学的人民性都在发展中。”[2]显然存在矛盾,到底哪一种说法符合王先生的本意呢?在他那里,前一种说法是事实,后一种说法是客气呢?还是后一种说法是事实,前一种说法是偏激呢?3.关于宏大叙事与公民叙事。文章对二者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二者的区别是在篇幅规模的一长篇巨制一短小微观呢,还是在内容的一写社会整体一写公民个体呢,抑或是在时间轴上一与现代化过程相应一与现代化完成态相应呢?个体性的公民叙事到底是内在于宏大的人民叙事之中呢,还是与之并列?公民叙事是只指个体性的细小叙事呢,还是也包括宏大叙事?4.关于中国文学的走向。虽然我们认为文学发展的原因是多样的,文学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文学的走向不是任何人能够预设的。但是,我们还是同意王晓华先生文学是“观念引导的事业,对于人民性的不同理解通向不同的文学实践”[2]的说法,我们也同意对俄国民粹派及中国1949年至1976年间文学人民性观念的反思。但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文学就真的像王先生不断言说的那样,能够毋庸置疑地成为我们建构文学人民性的路标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批判过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抽象性、空洞性和虚幻性,在建构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重温那些真知灼见,以使我们的建构既面对中国问题又向世界开放,既汲取历史教训吸纳历史经验也具有鲜明的当代性。
二、“后人民性”现象的指认
2005年,陈晓明发表《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一文,提出了“后人民性”一词。这个词是他对鬼子、东西、荆歌、熊正良等“晚生代”作家一个时期以来小说创作倾向的一种指认。意思是说,这些作家虽然表现出反映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倾向,与前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期间所说的文学的人民性——对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站在人民立场上表达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从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和相似。但是,他们的作品与曾经的人民性作品相比,“多了一些别的意味”,他们对人民性的强调,“并不能在政治思想意识方面深化下去,而是变成了一种美学表现策略,或者说转化为一种美学表现的策略。反过来,美学上的表现也使‘人民性’的现实本质发生实际的变异”。在他们,“人民性不再是自觉建构的意识形态,而是文学性创新压力下寻求自我突破的一种现实捷径”。也就是说,书写底层苦难、人民疾苦,在“晚生代”作家们那里只是一种借助、一种“脱身术”,而这种脱身术“由于其魔术般的精巧,既非真正地进入历史,也无力把历史从文本中解放出来”[3]。因此,陈晓明在文章结尾处表达了对“更深刻的批判性或更具有修辞性的反讽”的期待。
显然,“后人民性”只是陈晓明对晚生代作家创作倾向的概括,这种指认中既有他对创作现象的理解,也流露着遗憾和不认可,因此,我们不能将“后人民性”理解为他对中国文学出路和方向的正面主张。
陈晓明对“晚生代”作家创作状态的分析、创作倾向实质的揭示是深刻的,令人信服的。然而,由于“本文并不想全面论述‘人民性’概念在新的历史情势下的变化”[3],我们无从得知他对文学人民性问题的一般观点。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对时代、美学等都比较热衷于从现代、后现代分野的角度进行理解和把握的陈晓明先生看来,处于新的时代语境中的中国,还要不要、能不能建构文学的人民性?“只有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取得胜利这一历史意义上,人民性才可能产生或得到认可”[3]。这种说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时期文学人民性的时代特点,还是说文学的人民性只能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时代相伴而生?像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现实、与现实主义、与现代性、与人道主义等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这样的问题,当今中国文学的主流刊物所认同的美学原则或曰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的问题等,陈先生在文中都有所提及,但又都未做全面阐述,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如何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希望看到像陈晓明先生这样的在中国文学研究界一向居于前沿位置的学者对相关问题发表明确观点。
三、“新人民性文学”的发掘
2007年,孟繁华发表《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一文,认为,无论是19世纪俄国文学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概念,都与民粹主义思想有程度不同的关联,而在新世纪以来的一些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中,他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况。他用“新人民性文学”指称这种创作现象,并明确表示了倡扬之意。他对自己所说的“新人民性文学”有清晰的表述:“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存在的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文学’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新人民性文学’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4]
分析孟繁华先生所说的“新人民性文学”,我们可以意会,它不仅体现在价值取向上的新:超越民粹主义思想的既批判社会又批判底层民众身上的民族劣根性,更体现在书写内容上的新:反映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商业霸权主义、消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文化逻辑、跨国资本等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极度不平衡。而且可以说,正是因为书写内容的新,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值取向的新。因为作家们或在豁人耳目的不平衡中、或在看似平静实则发人深思的生活真相中,一方面看到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看到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4]。
与文学人民性的其他倡导者不同,孟繁华既不是把“新人民性文学”作为解救文学危机的唯一出路提出来的,也不是认为文坛缺乏人民性文学因而才呼唤它的。他是在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在指认、肯定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时提出“新人民性文学”的,是认为它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经验之一种时对它进行分析阐释的。因此,孟繁华的“新人民性文学”主张就避免了一些绝对、偏激、空疏等问题。
但是,“新人民性文学”主张也留下了有待进一步阐释的空间。1.除了孟先生评论过的北北、曹征路、吴君、马秋芬、李铁、刁斗等人的作品外,“底层写作”的作品还有很多,那么,“新人民性文学”与“底层写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2.既批判社会又批判人物身上的劣根性,是针对“新人民性文学”整体倾向而言,还是认为任何一部“新人民性文学”作品都应该如此体现价值立场?3.“新人民性文学”如何达到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的平衡?在艺术性上,“新人民性文学”有哪些表现和高度?面对“非文学性冲动”等指责,“新人民性文学”主张如何应对?其实,这些问题是所有文学人民性提倡者共同面对和应该认真回答的。相信,随着创作的发展,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对文学人民性问题的认识会更加透彻,而理论认识的透彻又会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取得新的进展。
[1]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J].文艺争鸣,2005(2):10-13.
[2]王晓华.人民性的两个维度与文学的方向——与方维保、张丽军先生商榷[J].文艺争鸣,2006(1):23-30.
[3]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J].文学评论,2005(2):112-120.
[4]孟繁华.新人民性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的一个视角[N].文艺报,2007-12-15(4).
Construction of Affinity-to-the-People Standard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Jiang Guihu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Liaoning110034)
Affinity to the people,a modern literary concep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became popular after Mao Zedong published“Speech at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in 1942.However,in the Chinese literary world,affinity to the people was seldom talked about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e late 1990’s.People began to face the crisis of literature and rebuil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standards of affinity to the people more than 10 years after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Many of these construction claims hav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meanwhile need further discussion.The current research makes a comment o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claim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andards of literary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develop ideas for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s of literary affinity to the people.
the new era;literary criticism;the standard of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206.7
A
1674-5450(2016)01-0098-04
【责任编辑 杨抱朴】
2015-09-03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1BZW008)
姜桂华,女,河北平泉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