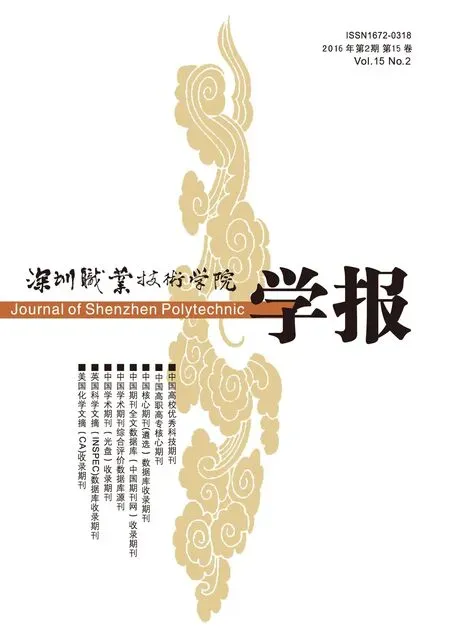听之道
——默温诗歌与中国文化因缘*
肖小军(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听之道
——默温诗歌与中国文化因缘*
肖小军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默温是美国当代杰出诗人、“深层意象”派重要代表,他的诗学精神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学界与批评界一直忽略或尚未认识到中国文化在默温创作中的影响,实际上,诗人致力毕生的听道诗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启迪。在默温的个人诗学中,听是诗歌既要表现的形式又是要表现的主题,同时,听道还反映了他的生命观和生态观。
关键词:听;道家;诗歌形式;生命观;生态观
美国前桂冠诗人(2010-2011)、国会图书馆诗歌顾问威廉·斯坦利·默温(William Stanley Merwin 1927-)自承,如同时代其他一些诗人那样,他的诗歌创作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本人不识汉字,对中国文化典籍及诗歌的接触是通过英译进行的,他认为这些译文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堪比《圣经》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他说,
“我们对当今整体的中国诗歌译文负欠,我们深受这些译文对我们诗歌的持续影响,对这一种总是难以捉摸的艺术,这些都是我们最乐于负担的债务之一……这种债,至少在种类上说,可以比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的翻译者所负欠的一样……它已经扩充了我们语言的范畴与能力,扩充了我们自己艺术及感性的范畴与能力。到了现在,我们甚至难以相像,没有这种影响美国诗歌会是什么样子,这影响已经成为美国诗歌传统本身的一部分了。”[1]21-22
而钟玲则质疑中国文化影响在默温创作中的存在。“在默文(即默温,笔者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实在是搜索不到什么中国诗学的论述方式。”[1]21同样,关于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影响这方面的国内研究专家赵毅衡、朱徽在其各自专著《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2]与《中美诗缘》[3]中也几乎只字不提默温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任何关系。在美国国内,默温已是学界与批评界关注的重点对象,相关研究成果也甚为硕丰,对其诗歌成就、基本诗学思想和艺术特性的评价似乎已成盖棺定论之势。包括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阿尔提瑞(Charles Altieri)、莫尔斯华斯(Charles Molesworth)、斯科尔斯(Robert Scholes)等一线批评家在内的大多学者将默温与“末世论”(Apocalypse)、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语言实验、神话与宗教等联系在一起[4],而对默温自己所坦承的其个人创作中中国文化影响的存在而表现为集体失语。因此,我们不禁要问,默温是否真的如他本人说的那样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如果是,其影响为何,又何在?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关注的是:默温诗歌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是如何融入其个人诗学主张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诗人的诗歌和诗论文本中寻找。
事实上,与其他一些诗坛好友诸如罗伯特·勃莱(Robert Bly 1926-)、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 1927-1980)、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 1905-1982)、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等人相比,默温的创作实践除《寄语白居易》(“A Message to Po Chu-I”)、《致苏东坡》(“A Letter to Su T’ung Po”)、《吉丁虫》(“The Rose Beetle”)等屈指可数的几首诗歌外指涉中国文化的作品少之又少。但是,诗人的中国影响并不是通过文字的简单能指来体现,而是消融在其诗歌的肌理与气质之中。默温毕生致力建构的听道诗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文化影响所致。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其听道一直以来竟被学界与批评界集体所忽视。它不仅关涉诗人与中国文化的因缘关系,而是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理解默温的文学意义。
1 听道之中西文化差异
在人体各种感官机能中,听觉与视觉总是相提并论。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曾说:“我们的眼睛看见对称,耳朵听见和谐。”[5]黑格尔以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但是,中西传统文化在对待视听的方式上则态度不一,西方厚此薄彼,重视觉而否听觉,而中国则二者兼顾,在某些方面甚至更重视听觉的作用。
根据德国当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的考察[6],西方文化尤其在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等领域于公元前五世纪就确立了视觉的优先地位,赫拉克利特宣称眼睛“较之耳朵是更为精确的见证人。”毕达哥拉斯因其“和谐理论”而被其讥讽为“骗子魁首”。尤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典故表明:视觉是通往现实、真相、真知甚至真理的唯一途径。自此,视觉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谱系的核心。古希腊“那喀索斯与厄科”神话更是强化人们“视觉核心、听觉附庸配角”地位的基本认识。当十八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于1787年提出著名的“圆形监狱”后,视觉的重要性和地位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视觉诚如“圆形监狱”中狱警的那双眼睛,高高在上,监督和把控着一切;而听觉就如同监狱囚室里的囚徒,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处在黑暗而边缘的生存状态。进入二十世纪,当人们开始深入反思感官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关系时,批评家们几乎将全部的注意力投放在视觉上,尼采认为,在明亮而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听觉是可有可无的了,“只有在漫漫的黑夜中,密密的森林中和幽暗的洞穴里,耳朵,这恐惧的器官,才会进化得如此完美,以适应人类产生以来最长的一个时代,即恐怖时代的生活方式的需要:置身于明亮的阳光下,耳朵就不再是那么必须的了。”[7]厄文·斯特劳斯里程碑式的著作《论感官的意义》花了大量的篇幅谈论视觉的意义,而对于听觉则几乎没有触及。知觉现象学创始人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其《眼睛与精神》一书中关注的是可见与不见的关系,认为智慧总是并只是与眼睛作伴。庞蒂的哲学体系中,知觉空间是我们判断世界并为个人行为作出预判的关键。而空间恰恰是我们身体语言中眼睛的涉指范围。韦尔施指出,西方文化就是典型的视觉至上、视觉霸权的视觉主义文化。而当人们对视觉和听觉的理解超出其感性的表面认知,将它们纳入权力、伦理、生态、文化批评的话语体系后,他们发现,视觉至上的西方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前途清晰可鉴:以霸权、权力至上、主体性、富有攻击性为主要特征的视觉主义正将人类带向一条末路。基于这样一种西方文化大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默温为何会悲观地奏唱“末世论”,从他最初的《两面神的面具》(A Mask for Janus 1952)、《跳舞的熊》(The Dancing Bears 1954)、《炉中醉汉》(The Drunk in the Furnace 1960)、《移动的靶子》(The Moving Target 1963)、《虱子》(Lice 1967)到后来的《河流的声音》(The River Sound 1999)和《迁徙》(Migration 2005)等,诗人的语调灰暗而沮丧,俨然末日就将降临。但是,在“末日论”的主旋律中,我们隐隐约约感知到:当诗人眼睛看不到未来,他转向自己的耳朵,他听到了从遥远东方传来希望的声音——它不仅让诗人的作品诗意更加盎然蓬勃,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它弥补了西方文化唯视觉独尊的自然缺陷。
中国传统文化以强调个人的修为为基础从而实现社会的大和与世界的大同。在个人修为上,视听都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而听,因其特殊的功能机制而呈现出接受、被动、温顺、谦和低调、弱者姿态与客体性等特征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儒道释皆以为,人应拒绝外物的干扰和影响,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天地。“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礼记·礼运》)。“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道家思想更是倚重听觉的文化表达。道家先哲无论老子、庄子还是文子都不约而同地将听这种感官方式与作为本体存在的道家之“道”以及道的获得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我们知道,道家之“道”,虚虚实实,空灵飘渺,存在却没有实体,超越人的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感知能力,实际上,它也超越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听觉感受。但是,老子以为,道可以被闻听到。很显然,道家之听是个人的智慧与修为的完美统一,如道一样,听似乎也被赋予了某种神性。道家看来,宇宙间能听到的最大声响是无声之音,“大音希声。”无声之音实际上就是隐存浩瀚洪荒中的自然之道——自然之音,因而,无声之听包含了道的神性、智慧和力量。庄子《齐物论》中的“人籁、地籁和天籁”之分在一定程度上是“大音希声”的注脚和补充,“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而将听与道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是文子:
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尊精积稽,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文子·道德》)
文子的此段论述与庄子“心斋论”中的“耳听、心听、气听”之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文子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论述“听”的价值,它关乎个人“达智”、“成行”和“致功名”,而他更大的突破在于,“听亦有道”:“神听、心听和耳听”——他有了初步的系统化、方法论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尝试。其中的“神听”更是与诗歌美学所注重的“诗性”“灵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道家哲学被认为是诗性哲学的典型表现。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审讯程序中,都注重听的作用。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它描述了中国古代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时观察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五种方法,很显然,此处的听亦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声音之听,而是被赋予某种神性的自然力量。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听觉,它“始终以静、空的时间体验方式(听觉方式,笔者注)将真理的理解置入了超越空间(视觉方式,笔者注)之上的虚无维度,以谦卑的姿态在视觉霸权的压制下顽强进行着天生归属感的寻求。”[8](路文彬 2006:126)而这应该就是吸引默温的文化源头。
2 听、诗歌形式与道
与大多数传统诗人一样,默文有自己成熟而独特的诗学观,但不同的是,他并不以长篇大论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只不过偶尔发表一些美学性质的小品文,可我们仍可以从中管窥其诗学要旨。《论开放形式》(“On Open Form”)是其代表之作,文章篇幅短小,全文不过千余字,但微言宏义,彰显诗人的思想精髓。
默温从诗歌形式切入自己的诗学理想。诗歌传统中,形式与内容是二分的,虽然都存在于诗歌文本这一共同体中,但双方有明显的界限和本质区别。形式是意义以外的东西,包括如节奏、押韵、声音、分行等诸多元素,形式让诗歌发展出多种形体如商籁体、无韵体、俳句、短歌、五言诗、七言诗、自由体等。但默温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诗歌形式也是如此。“被称之为形式的东西就是诗歌与时间有关:诗歌的时间,它写作的时间。”[9]298他解释说,不同时代的诗歌对形式的理解不一样,他以中世纪为例,那时候,诗歌形式是透明的(transparent),也就是说,形式是形式,内容是内容。换言之,当今的诗歌形式与内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体。某种程度上,默温的诗歌形式观与他同时代的投射派核心思想“形式向来不过是内容的延伸”基本一致。我们也可从他形式的价值观中得出同样的判断,他说,“中世纪的诗人需要形式让诗歌从世界分离(separate)出来,而今天的诗人需要形式来帮助诗歌发现(find)世界。”[9]299因此,“诗歌自身可以被视为它的形式。”[9]300
默温如此高调突出形式的作用,我们切不可草率地用“形而上”这一术语来简单化理解。事实上,他的“形式观”有具象式的诠释:“诗歌形式:是听见诗歌如何以语言的方式产生,但语言自身不会形成诗歌。同时,它是证明听见生命如何在时间里发生的方式,但时间不会形成生命。”[9]299几乎所有的批评家在引用并阐释诗人的这段话时将关键词锁定在“语言、生命与时间”上[10]6-10,而忽略了默温最倚重的“形式”——“听”。在默温看来,听是诗歌发生的方式,也是诗歌的形式和要表现的内容。
默温的上述表述的确过于简单,他后来也没进一步地深入,因此被忽略甚至误读也就不难理解。但是将它置入诗人完整的创作背景之下,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其深度咀嚼,透析其义理和意义。
默温个人第二部诗集《跳舞的熊》里收有一首名为《论诗歌的主题》(“On the Subject of Poetry)的短诗,该诗后来又被选入2005年获得国家图书诗歌奖(National Book Award for Poetry)的《迁徙》(Migration)选集中,由此可见它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全诗共五节,每节分五行。诗的标题“On the Subject of Poetry”(论诗歌的主题)就已凸显它的异类性,表面上看,它既不言情也不状物,而是论理言说,典型的学术论文式标题。实质上,本诗所表达的主题的确如标题所示,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诗人采用了诗歌最常见的象征与隐喻手段,以虚实兼论的方式来营造一种独特的情思意蕴,因而,作品既不乏想象奇特、虚构为本、语言和思想上富有跳跃性等方面的诗歌特质,同时,它还很清晰地传达了诗人的学理思想。
我无法理解这个世界,天父。
花园尽头的水池边
有人低头慢行聆听
溪流中机轮旋转,只是
那儿根本没有旋转的机轮。
他坐在三月的尽头,他也坐在
花园的尽头;他双手
插在口袋,并没有
特别的期待,也不
聆听昨日。机轮在旋转。
天父,当我说,这个世界
我不得不提。他既不迈开双脚
也不抬头
他担心惊扰到他听见的声音
就如没有哭喊的疼痛,他听着。
天父,我以为我不会喜欢
他聆听之前总要
准备聆听的样子。这
不平等,天父,正如
机轮旋转的理由,尽管没有机轮
天父,我说起他,因为
他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
在花园的尽头,聆听着
那根本就不存在的机轮旋转,但是,
天父,这就是我无法理解的世界。[11]25-26
从实践到理论,《论诗歌的主题》与《论开放形式》表现得高度一致。《论诗歌的主题》忠实地诠释了诗人的诗学观“诗歌形式:是听见诗歌如何以语言的方式产生”。诗人将所有的笔触都集中在“听(listen, hear)”上,从诗歌的开篇到结束,每诗节都回环往复性地演绎一个基本的事实存在:有人在聆听着机轮旋转(wheel turning),“有人低头慢行聆听/溪流中机轮旋转,只是/那儿根本没有旋转的机轮。”[11]25(第一节)“也不/聆听昨日。机轮在旋转。”(第二节)“他担心惊扰到他听见的声音/就如没有哭喊的疼痛,他听着。”(第三节)“他聆听之前总要/准备聆听的样子。”(第四节)“聆听着/那根本就不存在的机轮旋转。”(第五节)“听”扮演着双重审美角色,一方面,它实施着主体审美行为,另一方面,它是读者的审美对象。在诗人构筑的整个画面世界里,“听”是支撑它的轴心。诗人另一首题名为《诗》(“The Poem”)的短诗似乎也是为诠释诗人的这种理念而创作的。该诗收在《移动的靶子》一书中,全诗短短六行,每三行一诗节。“总是姗姗来迟,/我尽力记住我听到的一切。/光线躲避着我的眼睛。//多少次我听见门锁关门的声音/听见云雀拿走钥匙/将它们挂在天宇。”[11]93依然,诗人将“听”作为该诗存在的核心元素,而结尾两句的奇异想象让作品惊艳绝伦。
《论诗歌的主题》中“听”的对象“并不存在的旋转的机轮”不是一个具有画面感的普通意象,它是本诗的诗眼,已超越了其基本的文字所指功能和一般性的象征含义,它实在而又非在,实实虚虚,恍恍惚惚,非常识和常理可以彻底诠释。那么,如何理解它呢?我们可以从《道德经》中找到帮助:“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表面上看,“机轮”为一简单的个性实物,而实际上,“机轮”是个泛化的模糊体,是听的终极对象,它无所不在,它担承着道家哲学思考中“道”的角色。它在此处是“旋转的机轮”,而在他处可能是“门锁”(“The Poem”),也可能是“麻雀的叫喊”(“In the Night Field”),“刀上流动的光线”、“击打钟鼓的影子”、“与自己聊天的日子”(“The Crossroads of the World Etc”),“盲人们的锤子”(“The Students of Justice”),“面包的心脏”(“Bread”)等等。因此,“旋转的机轮”不是诗人耳听甚至心听的一般物象,而是神听感知的自然之道。默温寄予“听”以中国道家的哲学关怀和智慧,因此,我们就不难体会他为何要将“听”作为自己的诗歌主题——实际上又是诗歌形式和发生的缘由。
3 听与生命观、生态观
唯听而听不是默温的诗学目的,他绝非唯美主义式诗人,他的“末世论”已昭示他的世界情怀,从他《论诗歌的主题》那抑郁的“我无法理解这个世界”顿呼中我们就可以感知一二。他“末世论”的背后隐藏着他对生命和环境的终极关怀,而“听”是传达他生命观和生态观的美学方式。或者说,听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态度。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他为何要将听视为“诗歌发生方式”的同时还将其视为“生命发生的方式”。
前文已有所交代,视听这两种不同的感官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化,前者霸权、主动、自我、富有攻击性等,是西方传统文化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表现,而后者则柔弱、谦卑、低调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默温遵听道显然是西方传统视觉主义的文化觉醒。
牟宗三曾将中西传统哲学的差别简括为“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哲学所关心的其重点在‘自然’。”[12]这样的对比显然相对笼统而且也不客观。在生命与自然的二元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合二为一,而西方则二元对立,人类生命凌驾于环境生态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尊重生命,但人的生命与自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一样同等珍贵,人类的自我生命观在大自然的背景下应该谦卑并主动适应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归一。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谢灵运、白居易、李白、杜甫等为代表所创作的大量山水诗作正是生命与山水相互应和的文学映照。而这些诗歌连同其他一些文化典籍正是默温所言他“负欠中国文化”的根由。
默温的听道本质上是一种生命诗学,而他的生命诗学又是他致力毕生的生态诗学。诗歌《感谢》(“Thanks”)表达诗人生命观中非常重要的感恩情怀。作品以一个“听”字置于篇首,以表明自我生命姿态的谦卑,与此同时,听是我们的个体生命与其他生命建立相互关系的纽带,因为听,个体生命不会孤单,这是诗人为何要向其他一切生命表达感激之情的缘由:
听
当夜幕降临我们说谢谢你
我们停在桥边凭栏鞠躬
我们走出玻璃房
口里含着食物仰望天空
说谢谢你
我们站在水边谢谢它”
……[11]280
诗人将“夜幕、桥栏、天空、水”等都视为给我们恩惠的生命体,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很容易将它们简单地理解为“诗人特权”(poetic license)下所赋予的诗意的生命,实际上,正是这些所谓的“诗意的生命”更能让人觉得自我生命在宏大的宇宙生命体面前倍感渺小,这样更能促使我们正视和珍惜环境。“当动物在我们身边死去/带走我们的情感我们说谢谢你/当森林倒下的速度比我们生命流逝的时间/还要快我们说谢谢你”[11]280我们不能不说,默温的生命观与生态观紧密联结在一块,他用诗歌的方式诠释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伟大智慧。
早在诗人青少年时期,西方日益发展的都市文明与日渐消失的乡土气息让默温失望而担忧。乡土气息是人类生命与自然世界相通相融相互尊重的重要保证,它代表着所有生命存在的自由和各种生命体之间温存的情感。而都市文明的扩张,势必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一些生物的生存危机,更危险的是,都市文明下的生命因情感的缺失而变得冷漠与恐怖。对此,默温忧心忡忡,“那时我有个隐秘的恐惧——一个至今仍时时袭来的恶梦,那就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城市,整个世界都覆盖着水泥、大楼和街道,再也没有乡下。再也没有树木。这种世界似乎并不遥远,虽然我不相信这种世界能存活下去,但我肯定不能活于其中。”[13]174-175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说,“在世界的最后一天/我希望栽种一棵树”[11]282,种树的目的不是为了摘取果实,而是它能作为纯粹的树活着,它自由地吸收阳光和水分。在诗人的世界观中,树是世界的象征物,是人与世界和谐依存的迹象。所以,默温的生命观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爱”,我们除了爱自己的生命,还要爱其他一切生命: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无论是动物的还是植物的,无论是花虫草木还是风沙云石,等等。“听到死亡的消息后/无论我们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我们说谢谢你”。[11]280“我正在破译昆虫的语言/他们是未来的声音。”“我认为那不是要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那是这样一种强烈愿望:去热爱、去尊敬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事物,这些事物似乎比我们所能说、所能形容的更美丽、罕见和重要。”[13]175在《岛上纪念日》(“Anniversary on the Island”)中,默温用听觉的方式解释了他为何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远离自己的故乡大都会纽约来到夏威夷的一个小岛上,他为了“最终躺在我们怀抱里的岛上/聆听着树叶的沙沙声和海岸的呼吸声/不再有岁月/只有一座山以和四周一片汪洋大海”。[11]278值得一提的是,他自来到小岛后,购置了一块土地,栽种几十种濒危植物,此举是为了保护和传承“夏威夷文化和恢复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flora and fauna)”。[10]4
“传承”是默温生命观和生态观中另一个重要理念。传承不囿于本民族文化或同质文化,而是对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传承。在默温已有的诗歌创作成果中有明显中国痕迹的作品屈指可数,其中两首值得关注,从中我们还可看出默温对中国文化的熟知程度。《寄语白居易》(“A Message to Po Chu-I”)一诗于2010年3月发表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该诗是默温以白居易《放旅雁·元和十年冬作》一诗为原型题材而借题发挥,有必要提及的是,白诗在其个人创作中略显平凡,即便我国国内读者也知之甚少。它描述的是诗人本人的一段亲身经历,作者借以抒怀个人郁闷之气。在严寒之日逛街,诗人偶遇一儿童正兜售一只捕获的大雁,这引起了诗人怜悯之心,遂掏钱买下并放飞,并祈祷它不要飞向西北。“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因为那儿正发生战争,战事双方将士都食不裹腹,饥饿难耐,诗人很担心大雁被射下来以充饥之用!白居易借这只南归的大雁来隐喻沉浮于宦海之中的自己。当然,从当代生态批评学的角度来说,白居易买雁放飞的举动是环保意识驱动使然。默温借这样一个题材加以利用显然有其深层用意,一是白居易的放飞大雁举动引起默温生态共鸣;二是与其个人生命诗学思想也基本一致:尊重自然界的每一个生命体的生存权。最重要的是,该诗传达了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传承是生命和生态发展的保证——因为有类似诗人“我”这样的人在传承,白居易的大雁尽管历经千年却依然健在,“我一直想让你知道/那只大雁至今还健在我的身边/你还会认出这老迈的候鸟/它在我这儿已待了好久/眼下并不急于飞离”。[14]诗歌的结尾,诗人不无忧虑,“我无法告诉你/究竟能为那难逃杀害的雁群做些什么/我们正在促使南北极消融/我实在不知道这只大雁/离开了我可飞往何处”。[15]默温一方面是担心他之后无人保护那只大雁,另一方面又希望后人能继续传承下去。另一首与中国文化有直接关系的题为《致苏东坡》(”A Letter to Su T’ung Po”)的短诗于2007年也同样发表于《纽约客》。“几乎千年之后/我问着你提过的/并不断重复的相同问题/仿佛什么也不曾改变”。[15]默温思考着苏东坡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历经千年却依旧“不曾改变”,“每当夜深我坐在/幽静的山谷/我会想起你在河边/水鹰梦中的皎洁月光”[15]。默温虽然未将苏的问题具体化,但我们不难猜出苏东坡那豪迈洒脱的诗意之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以及出自《赤壁赋》的哲性之问“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那么,苏东坡的问题引起默温什么样的思考呢?“我会想起你在河边/水鹰梦中的皎洁月光/我听见你问题后/所带来的宁静/今夜那些问题有多悠久”。默温以他特有的听的方式感受着中国古代诗人关于天地与自我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智慧,人只有将自己定位在苍茫浩瀚的宇宙天地间才能归复宁静,才可诗意地栖居在温暖的大地上。而中国先辈的生命之思正是默温毕生的追求。另外,对诗人来说,这两首短诗的创作与发表时间也能说明问题,正值诗人创作生涯的暮年,因此,他以书信诗歌的方式向中国同行先辈致谢并表达自己的敬意。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在告诉我们,他的诗学理想在某些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域传承。
学界和批评界对默温听道的冷漠或者说有限关注不能归咎于他诗歌的风格使然,也不能问责于学界与批评界审美情趣或方向的选择。在一个以最大程度满足视觉感受的社会与时代,听道的被忽视就显得顺理成章。但是,默温对听道的推崇无论是出于纯文学还是文化建构或人类命运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有益的。就像他之后出现的如沃尔夫冈·韦尔施这样一些杰出的文化学者也开始关注起听的意义来,韦尔施在他的《重构美学》一书中非常乐观地表示,“一个疑虑在游荡:我们迄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6]173
参考文献:
[1] 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 朱徽.中美诗缘[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4] Cary Nelson and Ed Folsom. W. S. Merwin: Essays on the Poetry[M].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5] Taarkiewicz, Wfadysfaw. A History of Six Ideas[M]. Warszawa: Polish Scientific Publishers, 1980:313.
[6]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7] 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漓江出版社,2000.
[8] 路文彬.论中国文化的听觉审美特质[J].中国文化研究,2006(秋):126.
[9] Merwin W S. “On Open Form”, from 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M]. edited by Stephen Berg and Robert Meze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10] Hix H L. Understanding W. S. Merwin[M]. 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11] Merwin W S. Migration: New & Selected Poems[M]. Washington: Copper Canyon Press, 2005.
[12] 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3] 爱德华·何斯奇.“诗歌的艺术——W. S.默温访问记”[J].沈睿,译.诗探索,1994(5).
[14] Merwin W S. “A Message to Po Chu-I”[J]. The New Yorker, March 8, 2010, http://www.newyorker.com/ fiction/poetry/2010/02/08/100308po_poem_merwin (accessed March 2010).
[15] Merwin W S. “A Letter to Su T’ung Po”[J]. The New Yorker, March 5, 2007.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318(2016)02-0033-07
DOI:10.13899/j.cnki.szptxb.2016.02.006
收稿日期:2015-06-06
作者简介:肖小军(1969-),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与诗论的研究。
Poetics of Listening: W. S. Merwin’s Poetry and Its Sources of Chinese Culture
XIAO Xiaojun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5, China)
Abstract:W. S. Merwin is a very great American contemporary poet and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deep imagist. His poetic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the academia and the critics have ignored or failed to realiz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Merwin. Factually, the listening poetics Merwin has striven for has been inspired by Chinese culture, in particular, Taoism. In his personal poetics, listening is both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poetry. Besides, listening poetics shows his life view and ecological view.
Key words:listening; Taoism; form of poetry; life view; ecological view
*项目来源: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美国‘深层意象’派的中国诗缘”(GD12C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