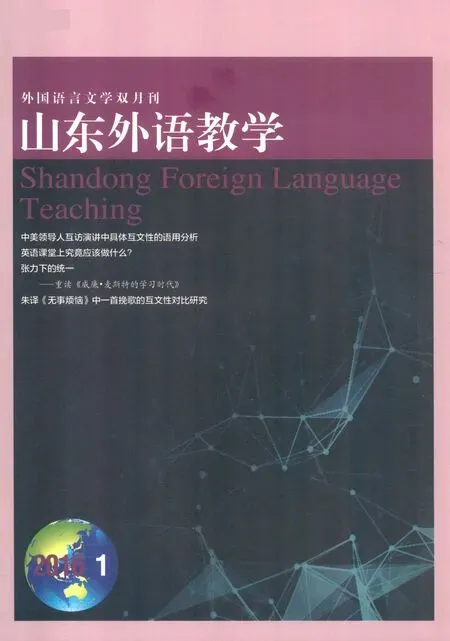张力下的统一——重读《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①
孙胜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 200083)
张力下的统一
——重读《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①
孙胜忠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上海200083)
[摘要]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自问世以来,一方面被奉为原型成长小说,另一方面因其反讽结局和文本中存在的各种张力而遭到论者的诟病。本文拟从小说的结局、德国当时崇尚的“美善合一”的理想和歌德本人“相互联系”的观念等方面探讨小说中反讽结局、感性与理性、现实与观念、行动与思想等张力下的辩证统一性,并结合成长小说的美学原则、当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作家的创作思想进一步探究文本既矛盾又统一背后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歌德;《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成长小说;美善合一;辩证统一
歌德(J. W. Goethe, 1749-1832)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MeistersLehrjahre,1795-1796,以下简称《学习时代》)中充满着各种张力或曰矛盾,它成了这部原型成长小说①遭人诟病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但问题是,文本中的张力是否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是否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是否有艺术上的逻辑性和统一性。透过文本,结合18世纪末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本文试图在诸多矛盾的表象下管窥其内在的统一性。
1.0 从反讽结局中看其辩证统一性
《学习时代》的结局是主人公威廉被象征着社会的塔楼会社所接纳,这一结局引起了与歌德同时代及此后众多作家和学者们的质疑。质疑者认为威廉被塔楼会社收编这种“被动”行为与成熟的特征不符,也与成长小说主人公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意志相背离,因此小说的结局充满着反讽的意味。②
诚然,成长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由天真走向经验和成熟的过程,成长主体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追求自由和独立。但何为“成熟”?成熟与以天真为标记的青春相对,《学习时代》“把青春看作是人生最有意义的部分”,而“作为现代性‘象征形式’的成长小说”正是通过表现“流动性和内心躁动不安(inner restlessness)这个‘年轻人的特征’”来塑造“现代性的具体形象”。因为青春与现代性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即它们都具有“活力”和“不稳定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春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本质’,一个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寻求意义的世界的符号。”年轻人内心的躁动不安和流动性成就了作为现代性象征符号及以年轻人为描摹对象的成长小说,但这些特征同时也与“新时代”的“杂乱无形”(formlessness)及“千变万化”和“飘忽不定”等现代性的特质形成了某种契合。问题在于要成型,青春还必须具备“一个几乎相反的特征”——成熟,因为青春是短暂的,不可能永远延续。如此一来,“活力与限制,躁动不安与‘终结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成长小说的结构将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Moretti,1987:3-6)如此看来,悖论、反讽或曰张力仿佛是成长小说的宿命。
在《学习时代》中,歌德基于“启蒙理性和古典现实主义诗学原则”(韩瑞祥,2010:44)塑造了一个历经人生变故最后“务实地”融入社会的青年形象。毋庸讳言,小说中充满着张力,但作者通过反讽艺术对琐屑生活现实的沉闷和压抑与诗意的浪漫想象之间的矛盾作了戏剧化处理,又借助自我教育(Bildung)③的理念化解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了一种平衡。
小说中那个“令人困惑的结局”表明,这个经典成长小说的源头实际上既表达了创作主体的美好理想和诗意想象又体现了他理性的人生态度,因为在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歌德看来,“幸福是自由的反面,是生成的终结(the end of becoming)。它的出现标志着个体与他所处世界之间张力的结束;进一步蜕变的全部欲望都熄灭了”。(Moretti,1987:23)由此可以推断以歌德为代表的经典成长小说作家们的“成熟”观:成熟就意味着对“限制”——“自由的反面”——的接受,不再奢望变化,停止“生成”,从而化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获得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来自主人公的一种自觉,当社会融合的外在要求被个体内化为自己的价值选择之后,它与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随之消失,在此之下的诸多次要矛盾也似乎顺理成章地得以化解。正如莫雷蒂(Moretti)(1987:24)所言,“经典成长小说的幸福是客观完成的社会化的自觉症状(the subjective symptom):没有理由质疑这种辩证的同质性。” 由此观之,小说貌似矛盾的结局在作家理性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经过反讽艺术的处理却具有了某种辩证统一的意味。
从深层次来看,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结局既反映了市民或中产阶级的困境,也表现出作家为社会融合找到合理化逻辑的努力:“个人的自主性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冲突”似乎在“逃离自由”中得到了化解,即“将‘归属’的欲望置于个人心理自身的内部”。“当社会融合的逻辑已经被内化,变成个人视之为他‘自己’的欲望,事实上是作为他最大的欲望,所有其他的都可以等而次之且可以牺牲——那么社会化就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必要,而是作为一种价值的选择:它已经变成合理的了”。(Moretti,1987:67)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导出经典成长小说的一种内在逻辑:个体要想幸福就得融入社会,而融入社会就必须放弃乃至“逃离”以自主性为标志的自由,而且要把融入社会的社会归属感化为一种自觉,变成个体“合理的”内在需求。这种逻辑表明,经典成长小说中幸福与自由之间的对立是自我化解的,在《学习时代》中,“自由自我‘化解’为幸福:主人公充分体验了他对独特性的渴望,直到厌倦了其无效,他才把它‘换成’一场成功婚姻这个典范的社会化”。(Moretti,1987:115-116)显然,小说的结局是矛盾走向统一的标志,只不过这种统一仍带有反讽的意味。
事实上,在进入塔楼之前,威廉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蜕变,一改此前只关注自己的内在修养,转而开始留心外部情况。小说第七卷第八章结尾处威廉打听自己的财产情况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就在他离开剧院,准备与他人一起从事有意义的活动时,“他打听他的财产情况,这时他才感到奇怪,自己长久对此都不关心了。他不知道,照例所有的人在注意内心修养的时候,总是对外界情形漠不关心。威廉一直是处在这种情况中,他现在才似乎第一次注意到,他为了持续活动,需要外界的辅助手段”。(歌德,1999:471)④这是威廉由内心世界走向外部世界,或者说他注意两个世界结合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从塔楼会社的那些格言来看,歌德对小说的反讽结局及威廉复杂的成长过程了然于心。威廉不甚明了的那些格言在小说中实际上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操控着文本而且使威廉错综复杂的成长过程显得合乎逻辑而真实可信:“文本中正在发生的一切都受塔楼会社格言的引导。从这些格言提供的角度来看,威廉表面上不规则和不合逻辑的错误和困惑的历史呈现的却是阐明和表达他独特个性固有的必然复杂和显然凌乱的过程,以及确实可能会促使那种个性与他有可能参与的外部世界有效接触的过程。”(Beddow,1982:125-126) 因此,无论是从威廉的成长历程还是从歌德对文本的掌控来看,我们都不难发现小说结局反讽表象下的有机统一。
2.0 从“美善合一”看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其实,威廉最后进入塔楼,即融入社会,与他一贯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似乎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当时席勒等德国著名思想家的观点,融入社会意味着顺应社会要求,接触的是粗鄙的生活现实,而艺术应该背对现实,否则就会导致对艺术理想的背离,这里体现的就是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但我们同样可以从这对张力中窥见其内在的统一性。与歌德同时代的德国诗人、哲学家和小说家荷尔德林有言:“没有精神之美的理智,就像做帮手的徒工”;“理性没有精神之美和心灵之美,就像监工。”(荷尔德林,1999:79)这说明理智和理性离不开精神和心灵之美,后者显得必不可少,因为缺乏它的人是乏味的,至少是不完美的。但没有前者,后者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支撑。威廉的成长过程就是“从个人心灵创伤到最终发现坚实基础”的过程,也就是主人公心灵“疗伤的过程”。(Ammerlahn,2006:25)
威廉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以及他最终融入社会的行为恰恰体现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这从塔楼会社的毕业证书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半是“关于培养艺术鉴赏力的”,另一半是“关于生活的”。(P524)这实际上是小说,也是歌德,关于人是否成熟的标准,即人在成长“学徒”期满后,应具备艺术和生活两方面的才能,既要有艺术鉴赏力,又要掌握生活的艺术。
关于怎样的人才能毕业,雅尔诺说的明白:“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只许这样的人毕业,他们感情热烈,明白供认自己为何而生,受到足够的训练,可以相当轻松愉快地去追寻自己的道路。”(P525)换言之,只有那些既有炽热的感情又清醒而理性地认准了人生之路的人才能毕业。这体现了歌德以“完整的人”为核心的辨证成长观:“小说表明人的完整性是某种不可能在宁静中获得的具体教训或洞见的东西。相反,它是个体的人在生活中相伴而在的潜能的聚集,是可能性的一种暗示。”(Swales,1978:70)在他看来,完整的人“不仅要有朝气,有热情,有激情,同时还必须有现实意识,有冷静的头脑,有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而要成为这样一个人,他必须要“接受教育,但接受教育的途经是与社会接触”。(范大灿,2006:392)这种教育有别于学校教育,也不局限于歌德时代所信奉的戏剧教育,而是“自我教育”,即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调适自我最终获得完整的人格。
这种融感性和理性于一体的成长观在当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为18世纪末期,德国崇尚古希腊文明,把古希腊人视为人类的典范。科尔纳(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1756-1831)在写给席勒的信中就曾借用古希腊的教育理想——“身心健全,美善合一”(Kalokagathie)——来描述威廉成长的特点:“在我看来,完整的统一在于再现一个通过内在素质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影响而逐渐形成的美好人性。这一形成(Ausbildung)的目标就是与自由的一种完美的平衡(equilibrium)、和谐。”(Kontje,1993:10-11)科尔纳这里所谓“完整的统一”实际上与歌德“完整的人”的概念是一致的,既可以指主人公身心的完美结合,也可以用于衡量一部经典成长小说,即看这部小说是否再现了主人公实现身心完美结合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美善合一”不仅指个体的人自身的身心健康、和谐,它还指个体与外部世界,即他所处的社会之间的和谐结合。如果说在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前文所述的艺术鉴赏力的提升,即主要体现的是“美”的话,那么,个体与社会的结合,即融入社会,则更多反映的是“善”。融入社会意味着个体不能以“独善其身”为自己的唯一价值追求,而是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要牺牲小我以服务社会,这也正是当时歌德、洪堡和席勒等德国人文学者提出“自我教育”观念的主要动因和目的之一。将个人的理想与社会要求相结合,乃至将社会要求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追求,此乃至善。还必须指出的是,“美善合一”不只是个体身心和谐,也不仅是个体与社会的融合,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威廉先是通过学习戏剧艺术,激发自己的诗意想象,从而克服了琐屑而沉闷的生活现实与浪漫的诗意想象之间的矛盾,获得了身心和谐;后又加入塔楼会社,摆脱了“小我”的羁绊,实现了与生活的融合。这从两个方面逼真地体现了“美善合一”的教育理想。由此不难看出,科尔纳并不认同后文将要提及的席勒对歌德小说中各种矛盾的指责,因为科尔纳的和谐与统一是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而它是辩证的,即它首先是建立在各种矛盾和张力的基础之上,而各种矛盾经由内因和外因之间此消彼长的搏击最终都得以化解。因此,辩证地看,《学习时代》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既充满张力,而这些张力——主人公与社会之间以及文本自身内部存在的张力——最终又自我消解了,它是在矛盾中走向统一与和谐的。但从“美善合一”的角度来看,它首先体现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3.0 从“相互联系”看“思”与“行”之间的辩证统一
威廉进入塔楼会社这一结局似乎暴露了他行动与思想上的脱节,也折射出现实与观念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表象恰恰体现的是威廉的成熟,也再次凸显了歌德辩证统一的思想。巴赫金关于成长小说中“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表明,人在成长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现实与观念、行动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关系,寻找一个平衡点,因为人在进入一个“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时要“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力求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巴赫金,1998:233)这十分切近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学习时代》中所发现的“歌德的诗性想象”,即他突出的“相互联系”(Zusammenhang)的观念。在莫雷蒂看来,这是“经典成长小说的叙事逻辑”:“它告诉我们当个体暂时性(‘整个人生的轨迹’)的内部互联同时意味着对外部的开放,一个与‘俗务’(human things)的外部关系日益宽广和密集的网络时,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他进而指出,“自我发展与融合是互补和会聚的双轨道,位于它们相遇和平衡点上的是对‘成熟’特有意义的完整和双重顿悟。达到这一点时,故事才实现了它的目标并能平静地结束”。(Moretti,1987:18-19)这说明上述矛盾虽然存在,但它们又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之道在于将个体的观念与现实相结合,将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通过二者的结合和实践的检验进一步认识自我。
例如,小说中的塔楼会社致力于人的成长和自我提升,有一系列典礼仪式和戒律,但它并非刻板教条,而是强调积极的人生,主张人要通过自身的观察和实践了解自己,尤其要认识到特定自我的局限所在,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完成自己特有的使命。歌德似乎要通过塔楼会社的宗旨来化解小说及其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与观念、行动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小说主张认识自我和世界实际上是对矛盾双方各自局限性的认识,然后通过二者的结合来加以克服。
众所周知,歌德的小说以想象见长,并突出人的整体性,因此,在《学习时代》中他赋予威廉以艺术家的气质。如果从艺术家成长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话,那么,我们更容易看出上述矛盾之间的统一性:“作为一个‘有思想的诗人’(denkender Dichter),威廉由基本上是自恋式的自我陶醉(narcissistic self-absorption)成熟到自我认知,与此相联系,他在小说中的艺术‘自我教育’在于他不断提升的控制其主观幻想这种潜在危险的能力,以及认识到外部世界的现象和规律重要性的能力,不仅是他的认知能力而且还是他的创造力。”(Ammerlahn,2006:37)这说明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就是其化解主观臆想与客观规律之间矛盾的过程,他在提升自己认知能力和创造力的同时也实现了由自我陶醉到清醒而客观地认识自我的跨越,从而做到了思与行的统一。
威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痴迷,并在此后的成长过程中研究戏剧,参加剧团演出,但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追求戏剧艺术只是手段,最终收获的应该是生活的艺术。歌德认为,主人公的使命“不该是成为一位德国的莎士比亚,而是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董问樵,1999:2)那么,这一“更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歌德本人并未提供答案,实际上,他不愿强化小说的中心思想,厌恶任何“清晰可辨的信息”(clear-cut message)。(Swales,1978:70)威廉的人生目标一开始也是模糊的,甚至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步骤,但歌德显然肯定了这些“错误步骤”的价值,他借用小说中神父的话说,“迷误只有通过迷误行为来医治。”(P525-526)在生活中,威廉逐渐学会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例如,他摆脱了过去的羁绊,不再沉浸在对往昔的记忆中而不能自拔。其明显的进步在于他学会分清想象与现实,艺术与生活,走出哈姆雷特的阴影,敢于直面人生。人只有在实践和行动中才能认识自我,学会生活,这种对生活艺术的强调正是《学习时代》的显著特征。一如生活是复杂而矛盾的,这部成长小说也充满着矛盾与张力,它以现实与观念、行动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呈现出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主人公的人生目标由模糊而逐渐明晰的过程。“伟大的艺术……不仅反映人类现实,而且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关涉原型星群(archetypal constellations)和永恒真理(perennial truths)并展望未来的可能性。”(Ammerlahn,2006:30)歌德的小说正是从粗鄙的现实中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4.0 矛盾与统一的背后
长期以来,对《学习时代》提出的质疑多半因这部小说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而起,那么,是否因为它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就否认它成长小说的原型地位,乃至否认成长小说这一体裁的存在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文学一般反映社会和文化这一本质属性来看,文本中的矛盾不仅不能构成否定成长小说的理由,相反,复杂的矛盾和张力正是反映西方文化和人文心态所必备的艺术手段和文本肌理。
首先,让我们从成长小说的美学原则来审视其辩证统一。成长小说的情节受“分类原则”和“转换原则”两种文本结构原则的支配,只不过在具体的小说中这两个原则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且侧重点不同暗示着不同的“价值选择”,甚至是“对现代性相反的态度”。(Moretti,1987:7)同样与现代性相关,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或象征形式,“成熟”与“青春”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它们几乎“成反比例”——强调前者就意味着贬低后者,反之亦然。但
无论这看起来可能显得多么矛盾,这种象征形式的确能够存在,不是尽管而是由于它的矛盾性质。它能够存在是因为在它内部——在每个单个作品内部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这个体裁的内部——两个原则都同时有效,无论它们的力量是多么不平衡和不均匀。它能够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必须存在。因为在现代性与青春相冲突的评价之间,或者在对立的价值与象征性的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瑕疵——或许也可以说是瑕疵——但它首先是很大一部分现代文化充满悖论的功能原则(functional principle)。(Moretti,1987:9)
尽管成长小说中存在着众多矛盾因素,而且这些价值观多半是“对抗性的”,但“它们对现代西方心态来说都同样重要。我们的世界需要它们的共存,无论有多么困难;因此它也需要一种能够再现、探索和测试那种共存的文化机制。”(Moretti,1987:9)由此可见,成长小说成了表达和再现西方文化和心态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机制。
就《学习时代》而言,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对立和矛盾的价值观不仅构成了它自身的特色,乃至代表着成长小说这一体裁的显著特征,而且成了这种小说存在的理由和表达西方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有效工具。虽然人们对歌德的小说一直争论不断,但鲜有否定其重要性的,至少在德国如此。即便是那些持有异议的论者也只不过是试图以此作为“焦点”来“理解和重新界定德国的小说”。例如,有人将《学习时代》称为德国的“标准小说”(Normal-Roman),而“这个小说‘标准’的主题”就是“描述为了自我教育而走遍世界之旅”。虽然对歌德小说强调个人感到遗憾,但把这归咎于18世纪德国政治现实的“不幸状态”;把威廉在小说结束时的“未成熟”状态归咎于在歌德那个时代尚不存在“德国”(the German state)。(Kontje,1993:19)
成长小说的美学原则业已表明,《学习时代》中的矛盾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而且矛盾的双方还显现出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那么,除此之外,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背后到底还潜伏着其它怎样的创作动因呢?我们不妨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运动以及作家的创作思想对此作进一步追问。
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这一时期整个欧洲阶级矛盾异常激烈,社会处于极度动荡时期,德国也不例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种社会动荡和历史大变革在文学上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的文学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的第一次高峰相对而言),期间,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此起彼伏,先后经历了启蒙运动后期、狂飙突进运动、古典时期乃至浪漫主义,甚至还出现了前后重叠的现象,如启蒙运动后期与狂飙突进运动初期、古典时期后期与浪漫主义并行。⑤而歌德的创作生涯正处于德国这一文学运动相互交错,思潮迭起的时期,他的《学习时代》一方面表明这些文学思潮对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他创作思想和风格的变化。
在青年歌德于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时期发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DieLeidendesjungenWerthers,1774)中,主人公维特由于对爱情的失望,尤其是对社会的绝望,最后选择了自杀这种自绝于社会的极端行为,小说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种过度张扬个性和极端反社会束缚的方式是狂飙突进运动的典型表现,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歌德当时对社会的绝望情绪及其创作思想。后来,歌德根据自己的经历认识到,“如果想象在希望和恐惧的王国里、在受伤的过去或理想化的乌有之乡中狂乱地游荡,那么,它就可能变得很危险。如果它不是牢固地植根于现实,那么,它就可能是致命的”。 (Ammerlahn,2006:36)于是,完成了由狂飙突进向古典时期转变的歌德在审美取向上也发生了变化,此时他的“审美感知是现实的”,因此,在《学习时代》中他反过来“采取启蒙理性的认识模式”,并试图使主人公威廉“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经历中成长为完美的人”,并“主张表达情感和理性的和谐”。(韩瑞祥,2010:45)基于这种创作理念,歌德对主人公的成长路径作了较大的调整,尽管小说中依然存在着人的自然感情、自由发展的愿景和人道主义理想与市民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但小说在肯定个人理想的同时突出表达的却是如何与社会现实达成妥协,从而实现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和谐统一。
但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特质恰恰是引起争议的根源,一方面,小说中不乏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冲突与对立;另一方面,小说又试图化解各种矛盾,为主人公融入社会铺路搭桥。前者引起论者对小说结构及其反讽艺术的质疑,后者令小说背上了造作和主人公消极被动的骂名。其实,如果我们将歌德这部小说的创作置于当时德国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中出现的矛盾以及作者为化解这些矛盾所作的努力。歌德创作《学习时代》时正处于古典时期的高峰,浪漫主义已开始萌芽甚至已蓄势待发,在此氛围中,他认为古典的就是“理性的”、“和谐的”,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现实”,因此,他推崇“实实在在的、人性化的”古典的东西。(韩瑞祥,2010:47)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歌德的审美情趣在古典现实主义底色上的浪漫情调,从而理解其小说基于理性呈现出的矛盾,以及在粗鄙的现实之上披上的浪漫而和谐的外衣。从他此前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截然对立到他试图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寻求妥协的努力中来分析,我们不仅能理解小说中的矛盾现象,而且能看出歌德辩证的成长观。
在1796年7月8日席勒写给歌德的信中,席勒指出威廉成长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从一个空洞和不明的理想步入一个具体、积极的人生,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失理想化的活力。” (Kontje,1993:10)席勒按照自己的美学理论对威廉进行评价,并认为歌德在小说中不愿更清晰地传达他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自我教育的理论。对此,歌德礼貌地拒绝与其合作,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席勒对威廉的评价还是中肯的,这一评价道出了威廉,乃至大多数经典成长小说主人公成长的轨迹——从抽象到具体,从不切实际的幻想到积极地投身社会。例如,威廉在成长过程中离开他的理想之所——剧院,转而加入贵族阶层,投身社会。这是经典成长小说主人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成为“完整的人”,这样的人既有理想又脚踏实地;既有情感又有理智。这种完整的人的概念与荷尔德林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他认为:“从单纯的知解力决得不出明智,从单纯的理性决得不出智慧。”(荷尔德林,1999:79)
实际上,歌德小说中所呈现的矛盾首先是他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困惑,这些矛盾也同样反映在与他同时代的席勒身上。一方面,席勒主张人应该顺应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人是时代的公民,正好像人是国家的公民一样;而且,如果人生活在社会团体之中却与社会团体的风俗习惯格格不入,那是不适宜的,甚至是不允许的”,因此,他认为人在选择工作时有义务满足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贴近现实、顺应社会的要求会导致人远离理想的艺术:“这种理想的艺术必须离开现实,并且必须以足够的勇气超越需要;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想从精神的必然而不想从物质的需要去接受她的规范。”(席勒,2009:3)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就是追求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而歌德的小说恰恰回应了这种追求。其次,歌德小说中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作为演绎自我教育理念的成长小说不可能机械地成为阐释这一理念的范本,它只能艺术地,以审美和思辨的形式来形象地演示它。这样看来,小说中的矛盾就难以避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成长小说“即便在歌德时代,即便是歌德自己的作品,也不乏文学的反讽和对修养理念的怀疑。”(谷裕,2013:19)
注释:
① 学界一般认为歌德的《学习时代》首创了成长小说这一体裁,并且被后来的小说家一再模仿和重塑,故《学习时代》常被论者称之为原型成长小说。
② 关于对《学习时代》结局的质疑,请参阅T. C. Kontje (1993)第10-12页。
③ 关于“自我教育”概念的由来及其内涵,详见孙胜忠(2010)“论成长小说中的‘Bildung’”。
④ 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只标注页码。
⑤ 关于这一时期德国的文学运动,详见余匡复:《德国文学史》(1991)第172-175页。
参考文献
[1] Ammerlahn, H. The Marriage of Artist Novel and Bildungsroman: Goethe’sWilhelmMeister, A paradigm in disguise[J].GermanLifeandLetters, 2006,(1):25-46.
[2] Beddow, M.TheFictionofHumanity:StudiesintheBildungsromanfromWielandtoThomasMan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 Kontje, T. C.TheGermanBildungsroman:HistoryofaNationalGenre[M]. Drawer: Camden House, Inc., 1993.
[4] Moretti, F.TheWayoftheWorld:TheBildungsromaninEuropeanCulture[M]. London: Verso, 1987.
[5] Swales, M.TheGermanBildungsromanfromWielandtoHess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6] 巴赫金. 小说理论 [M]. 白春仁,晓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董问樵. 译序 [A]. 歌德. 威廉·麦斯特 [M]. 董问樵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8] 范大灿. 德国文学史(第二卷)[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 歌德. 威廉·麦斯特 [M]. 董问樵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10] 谷裕. 德国修养小说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1] 韩瑞祥. 审美感知的碰撞——评诺瓦利斯对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反思[J]. 外国文学,2010,(6):44-53.
[12] 荷尔德林. 荷尔德林文集 [M]. 戴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3] 孙胜忠. 论成长小说中的“Bildung”[J]. 外国语,2010,(4):81-87.
[14] 席勒. 审美教育书简 [M]. 张玉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15] 余匡复. 德国文学史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Unity beneath Tensions:WilhelmMeistersLehrjahreReconsidered
SUN Sheng-zho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Since its publication, Goethe’s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archetypal Bildungsroman.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been constantly criticized for its ironical ending and various tensions within the tex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neath the ironical ending and various tensions such as those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actuality and notionality, action and idea, etc. in terms of the novel’s ending, the classical ideal of “Kalokagathie” that Germans advocated at that time and Goethe’s concept of “Zusammenhang”.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deep reasons for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ased on the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Bildungsroma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t the time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novel and Goethe’s writing ideas.
Key words:Goethe;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Bildungsroman; Kalokagathie; dialectical unity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2-2643(2016)01-0068-07
作者简介:孙胜忠(1964-),男,汉族,安徽巢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及西方成长小说。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成长小说流变考”(项目编号:11BWW04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4-23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6-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