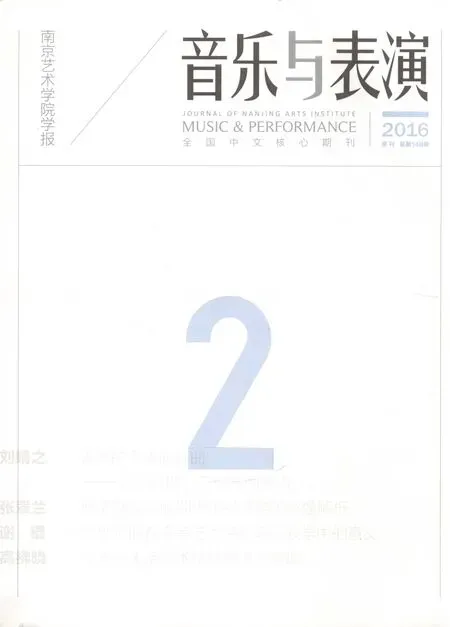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①
周 钟(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①
周 钟(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唐代的船子和尚为了让弟子坚固道心,决然投江而逝,春秋时期的成连先生为了学生体会琴道,入海一去不返。当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作为文化事件被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体现出为守护、传续“道”不惜放身舍命、“剑人合一”的生命美学境界。而舍身传法的行为也有着共同的文化指向,即真理无法言说、绝学无可传授、对道体的领悟无法通过意识思维达成,如果非要言说、传授、领悟,往往只能用生命表达、以绝境示道、在绝处领悟。他们所传、所悟的“道”、真理就是“本来”。舍身传法昭示的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庄严底色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复兴提供了重要启示。
舍身传法;禅宗;琴学;绝学;道;本来
一千多年前,一位叫船子的禅宗和尚为了让弟子夹山消除对所悟之“道”的疑虑,决然投江而逝;两千多年前,一位叫成连的琴师为了让学生伯牙体会“神妙寂寞之情”,独自驾着小舟驶入了茫茫大海。回望历史,这两个舍身传法的文化事件显示出非常相似的意象,暗示了禅与琴的“因缘前定”,而船子与成连那早已模糊的背影依然让人感动与深省。船子为什么要投江?成连为什么要入海?什么法需要以身相传?显然,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的意蕴已不限于禅宗与琴学本身,而是关涉真理的本质、“道”的教育与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等重大问题。
一、舍身传法及其生命美学
首先有必要回顾并分析一下船子传法夹山、成连传法伯牙的过程。
船子和尚(约764-840),名德诚,四川武信(今遂宁)人,得法于药山惟俨禅师,后长期隐居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朱泾一带。他节操高邈、度量不群,泛一小舟,随缘度日,以接四方往来之众,但三十年间一直未遇到可堪传法之人,正是“棹拨清波,金鳞罕遇”[1]115。时夹山法师在道吾和尚的指点下,造访华亭,向船子参学:
船子才见便问:“大德住甚么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师曰:“不似似个甚么?”山曰:“不是目前法。”师曰:“甚处学得来。”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山才上船,师又曰:“道!道!”山拟开口,师又打。山豁然大悟,乃点头三下。[2]537
两人初一见面,船子问了夹山几句,夹山回答的也蛮好,但都是学来的话,并不是自己的真实体悟,因此船子评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意思是貌似明白了道理,其实只是执着于法的口头禅,反成了开悟的障碍。夹山在船子的诘问下愣住了,这时他离开悟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毕竟尚未悟。于是船子让他说话,夹山刚要开口——即用意识思维及佛经上的内容回答,就被船子一桡(船桨)打落水中;夹山刚爬上船时,船子又问,夹山刚要开口,船子又打。这时夹山真正悟了,赶紧点头三下。这里船子所用的方法就是将人逼至绝处,令其“绝圣去虑”——夹山突然被打入水中,人在挣扎时佛经、知识、妄念都顾不上了,如此才有机会顿悟本来面目。
夹山开悟后,船山就传法给他:
师曰:“竿头丝线从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问:“抛纶掷钓,师意如何。”师曰:“丝悬绿水浮定有无之意。”山曰:“语带玄而无路,舌头谈而不谈。”师曰:“钓尽江波,金鳞始遇。”山乃掩耳。师曰:“如是如是。”遂嘱曰:“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没踪迹处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药山,只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后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里钁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山乃辞行。频频回顾。师遂唤:“阇黎!”山乃回首。师竖起桡子曰:“汝将谓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2]537
前几句都是用功方法,夹山懂了。船子和尚高兴道:“钓尽江波,金鳞始遇。”①有关船子传法夹山之因缘,禅林中称为“船子得鳞”。接着用双关语嘱咐其前程,并将他在药山禅师处所得之法传与夹山。于是夹山拜别辞行,但走两步就回头看看,一是难舍恩师,二是对所悟之道还不肯定、还有怀疑。船子和尚看到了,就大声喊他:“和尚!”夹山回过头来。船子说:“你以为还有什么其他的吗?”然后自己倾翻小船、自溺而亡,表示再无余法。元代明本禅师评论整段对偈:“迅机峻令,电走风飞,破执荡情,一发无贷。末后一句,命若悬丝,踏破虚空,有谁敢拟?”[3]船子和尚通过身死之决绝来坚定弟子的信心,而夹山也终成一代禅门宗匠。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感动、震撼的伟大师道。
成连(生卒不详),是春秋时著名琴师,也是伯牙的老师,相传受业于方子春。②《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引梁元帝《纂要》曰:“自伏羲制作之后,有瓠巴、师文、师襄、成连、伯牙、方子春、钟子期,皆善鼓琴。”成连入海可说是伯牙学琴的关键一课:
伯牙……尝学鼓琴于成连先生,三年而成;神妙寂寞之情未能得也。成连曰:“吾虽传曲,未能移人之情。吾师方子春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与子共事之乎?”乃共至东海,上蓬莱山,留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日不返。牙心悲,延颈四望,寂寞无人,徒闻海水汹涌,群鸟悲鸣,仰天叹曰:“先生亦以无师矣,盖将移我情乎?”乃援琴而作水仙之操。[4]7
引文中的“神妙寂寞之情”指的就是琴道,伯牙攻琴三年学成,但只得其技而不得其道。这里,伯牙与夹山有着相似的困境——无法领悟超越言诠、意解的道体(具体所指不同,下文另述)。于是成连假托寻访、求教方子春,带伯牙至东海之滨,欲为其移情。成连的移情之法就是刺船入海旬时(十天)不返。可以想见,这一行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件极危险的事,可说是为了学生将生死置之度外。老师走后多日,被置于绝境的伯牙延望无人,只听见海水汩没漰澌、群鸟悲号之声,终于从心、情与天地、自然的契合、相通与共振中直下体会领悟到了琴学之道、寂妙之情,于是作《水仙操》,妙绝天下,成为了影响千古的琴家。这就是后人所谓的“伯牙海上感沧溟”。而其中的奥妙正是伯牙所叹的“以无师矣”,李贽《焚书·征途与共后语》对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阐析:“唯至于绝海之滨、空洞之野,渺无人迹,而后向之图谱无存,指授无所,硕师无见,凡昔之一切可得而传者今皆不可复得矣,故乃自得之也。”[5]708
可以看出,成连教人方式与后世禅师之手眼颇有相似处,近于禅宗所谓的“善巧方便”,但前者所在的春秋时期佛教尚未传入中土,也就是说,那时的琴学还未受到禅宗的影响,这就非常值得注意、比较与会通。即,禅与琴有着先天的共通处,这是其后来和合、互相影响的前提条件与必然性。而它们的共通处就是用特殊的方法来开示、体悟超越语言、思维界限的道体,船子投江、成连入海正是这种特殊方法的极致表达,并体现出一种让今人仰止的“剑人合一”的生命美学境界。
在船子那里,道就是生命的意义,生命就是道的载体,两者是无二无别的,而悟道、载道、传道就是生命价值的最大体现。从他自己在药山处悟道,到泛舟渡人之载道,再到“始遇金鳞”时传道,一切都那么卓尔不群、任运自在。船子和尚的手眼、做派不是随便来的,更不是一般人能模仿的。③禅宗教法如杀人刀、活人剑,一着不慎可能致人误入歧途或终身不悟,因此须是禅门所谓明眼善知识者方有资格打机锋、行棒喝,这种人不仅自己开悟,更能善辨弟子根器及其可能开悟的时机,非常人可及。他对夹山的问难、狮吼、棒喝基于觉彻心源的智慧,如电闪雷鸣般应机而发,没有一丝做作,只是要把他的迷惑打破,把他的心执震开;他在夹山开悟后的赞许、印可与谆谆嘱咐,则字字诚朴、句句真情,一片师心昭昭然;他在看到夹山还有疑虑而频频回头时,毫不犹豫地跳入滚滚江水,绝无一丝徘徊、瞻前顾后,这是何等大无畏!这是何等洒脱的禅者风范!船子投江是一刹那间的事,但这一刹那却凝聚了他一生的功力,这就是他对无我的本彻体会与对众生的慈悲情怀。相比之下,成连入海则没有那么禅风峻烈,但“善意的谎言”同样展现出其为守护、传留琴道而不惜放身舍命的使命感、责任感与壮丽人格。琴在成连那里不仅是音乐,他传给伯牙的也不仅是技艺,而是“可以与天地参”的琴道。为了伯牙悟道,他为伯牙设计的移情之法可谓用心良苦,他的真实目的从开始一直隐瞒到入海。因为不能说破,一旦说出来,伯牙就会用思维去推想,就可能永远无法真正领悟。成连入海不似船子投江之迅疾,但这种计划好的一往无前、一去不返,更有一层悲壮的色彩。这大约就是为人师者的真义吧!可以说,在师道方面,船子与成连堪称难以超越的典范,这与他们崇高、庄严的生命之美一体不二。
当然,故事还有另一种结尾。南怀瑾先生认为,船子和尚其实死不了,“不知跑到哪里去玩了”;《乐府解题》、《太平御览》等文献则说成连后来返回。这也许是历史的真实,也许是后人的猜测、杜撰或良好祝愿,史书并没有记载他们后来的情况。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舍身传法时的决绝与淡然。
二、文化史视野中的“道”、绝学与“本来”
“道”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尊崇与追求的核心命题,甚至可以说,一切传统学问乃至传统文化的终极归旨就是“道”。而研究道、体悟道、传承道的学问,就称作圣学、大学或绝学。“绝学”一词首见于《老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指古代学问中高精尖的部分,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不同,它强调的是知行合一、与“道”的直接相应,是理论与实践的协调一致、互相印证与完美契合。
绝学的“绝”字,有精微莫测之义,又有无可授之义,即绝学难以用平常语言、行为来传授。绝学的这一特征是“道”不可说的特性决定的,即德里达指出的,言说、书写无法让意义在场,能指与所指是断裂的,因此船子与夹山自始至终也没有说出“道”是什么,成连与伯牙自始至终也没有明示移情的内容。实际上在“道”那里,不仅是语言,意识思维也无法让意义在场,即禅宗所谓“不可以义解,不可以言传,不可以文诠,不可以识度”[3],否则人人都可以开悟,事实上并非如此。那么绝学是如何使人悟道的呢?老子明确指出,需“绝圣弃智”——摒弃成圣成贤的希求心与意识思维;“绝仁弃义”——超越善恶好坏的有对心与对善业功德的贪染心,而臻于至善至仁至义;“绝巧弃利”——打灭对奇巧、捷径、技能的迷恋心与对功利的追逐心。但“此三者以为文,不足”,还要“见素抱朴”——回归本来、“少私寡欲”——消解有“我”之心,才能真正做到“绝学无忧”,[6]273所谓“无忧”就是没有以上种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如实地直面真理。应该讲,以上说法与禅宗是相通的,而这其实就是绝学之“绝”字的第三个含义——即去除、做减法①日本文化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作“残心”。,将自己置于精神上的绝境。
现在回到船子与成连的故事上来,我们会发现这两个舍身传法的文化事件是“道”与绝学的绝佳诠释,即当船子投江与成连入海被置于文化史研究的视野中时,其所呈现出的文化意蕴与思想光辉就远远超出了禅宗与琴学的范畴,而直切中国文化内核,为我们理解真理的本质、绝学的传统——即“道”的教育与传承、中国文化精神等重大问题提供了典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特殊的教育、表达(言说)方式。“道”不可说,但“道”毕竟需要传承。这就意味着虽然真理在根本上是不可言说的,也即言语在示道、传法时是无力的,甚至会造成觉悟的障碍,但又不得不言说,因此就需要特殊的表达或言说方式。这种表达或言说并不是直接告诉弟子道是什么、怎么悟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道”毕竟无可授,“实无一法与人”[1]143;而是引导弟子进入某种情景,促其自己去觉悟。船子和尚对夹山使用的是机锋问难与“一桡打落水中”,前者用种种充满智慧、玄机的诘问(禅宗称之为“直指”)逼迫夹山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即只有理解、没有实悟,诱导其对道体究竟如何产生疑惑与追究,从而转入一种趋向实悟的心灵动势;后者让夹山打灭所有的念头,包括意识分别及种种“我执”,进入一种心性空灵的状态,这时就有可能直切根源、豁然省悟。而成连先生先以“方子春能移人情”之辞,让伯牙产生有所依托的期待感、希望感,然后“刺船而去,旬时不返”,通过自己的消失让伯牙进入一种无所依托、失落、孤寂的状态,这就为伯牙有所感悟创造了条件。从此可以看出,在古人那里教育是活泼泼的,它是一个丰富多元、灵动多变的整体,不仅包含着言传,更有各种超出今人想象的身教,而且经常是直截了当的,不似今学之拖沓繁琐,其终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教人悟道。笔者以为,这种教育、表达方式是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改其生机盎然的密匙所在,它昭告着一种教、学精神的自由与可能性,对今天限于口舌或技术、拘泥于书本与各种符号的僵化教育、程式化表达及工具理性倾向,具有十分宝贵的启示。
第二,以绝境示道、在绝处领悟。绝学之“绝”,在于要在无路处走出一条路,在无门关打破一扇门,而“从门入者,不是家珍”[7]145,这就对老师传法、学生悟道提出了艰巨的挑战。如上所说,这种传、悟只能使用“非常道”、“非常名”,这种“非常”的极致就是用生命来承担——以生命传无可传之法,以生命受无可受之学,这往往就意味着将生命置于绝境,为法忘躯。①从本质上看,“为法忘躯”基于当事人的修养境界。对于老师而言,是其工夫、体认的真实流露,若工夫没到,则谈不上也做不到“忘躯”,纵然“忘躯”也无法可传;对于学生而言,为求道、求法而“忘躯”,才堪为法器,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忘躯”、身心全然放空时,才有可能与“道”相契。或者说,在许多情况下,绝学只有在绝境中方能绝处逢生、传续下去。船子“覆船入水而逝”就是用最决绝、彻底的方法让夹山放下所有疑虑,坚定“道就是如此”的信心;②船子在投江前先以机锋、棒喝令夹山顿悟(但对所悟尚不确信),若无前事,则投江无意义,更无法可传。成连不惜置自己于茫茫大海之险境,就是为了让伯牙“感沧溟”。另一方面,弟子、学生之悟也须在绝处。当夹山被船子打落水中挣扎时,是身处绝境,当他看到船子投江而逝时,是心处绝境,在船子的层层钳锤、身教下,他终于大彻大悟。同样,当伯牙苦等成连十天仍不见其踪影时,伯牙突然意识到自己身处绝境——天地间只有他,他终于感悟了琴学之道、寂妙之情。③弟子求法同样需要舍身的精神,典型的例子如禅宗二祖慧可断臂求法。由上可知,绝学既不易传,更不易得,易传易得的“绝学”是可疑的。船子、成连之苦心自不必说,夹山、伯牙之悟更难能可贵,借用禅宗的话讲,当事人需经历一番“大死大活”,方可焕发出新的生命。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法、悟道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自身,而是关涉“慧命”与文化精神的延续。这可不是无关痛痒的谈玄论道,而是性命攸关的生死拷问,中国文化的精魂就是在这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拷问中传续至今。从此也可说,一部中国文化史(包括宗教、文学、艺术、生存生活方式等)就是生命的历史、灵魂的历史,是无数个体用他们能力所能企及的极限,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写成的一部真实而鲜活的书。
第三,“道”、真理就是“本来”。船子、成连费尽周折向夹山、伯牙传示的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夹山、伯牙所悟的有什么玄机和奥妙?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们用生命守护的、体究的“道”、真理其实就是事物、人心本来的样子,禅宗称之为“本来面目”或“本地风光”。由于在一切事物中“道不可须臾离也”,也即道器不二,所以此事人人本来具足——这是人“悟道”的可能性来源,也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8]651、佛家“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9]272的先决条件,故绝学即“无学”,不假外求。虽然如此,要领悟这无学之学,看见、体会“本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时穷尽一生也难以窥见。明代憨山大师称之为“荆棘丛中下脚易,月明帘下转身难”,看似很简单,但就是做不到。这是因为人心陷溺,我们一般人时时刻刻处于各种烦恼分别中、落在各种虚妄境界里,恰恰忘失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忘失了如何去用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体会事物的本来。换句话说,我们眼中的世界并不是它“自有”的样子,而是被我们的“妄心”加工过的“我”的世界,夹山先前只是解悟而非真悟、伯牙三年未得“神妙寂寞之情”的原因正在于此。而觉悟“本来”的难点也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无法去除“妄心”与“我”,对于夹山与伯牙来说同样如此。所以船子与成连一定不能让他们的弟子、学生去思维、意会“本来”是什么——凡用思虑者就必定不是“本来”了,“本来”在根本上也无法描述、义解;而是使用了上文所述的特殊手段令其“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远离颠倒妄想”,让夹山、伯牙有机会直面本源,顿悟道体。因此夹山落水时所悟的“真如”其实就是一切的本来面目——即世界、心灵“缘起性空”的本质,在禅宗人看来即是宇宙人生之真理、体性;而伯牙“感沧溟”所悟的“神妙寂寞之情”④真,真实不虚之意;如,不变其性之意。“真如”即佛教所说的“万有之本体”,又作如实、法界、法性、实际、实相等。“缘起性空”(相、用的变化无常)与“如如不动”(体、性的恒常不变)为其一体两面。其实就是本心与天地、自然的本真的直接交感、契通,有天人合一的意味。夹山、伯牙所悟的共同点就是“本来如此”,并非“造境”。而就“道”的层次来看,前者要比后者深刻、根本,或者说前者可融摄后者。
彻悟了“本来”,才知所谓悟道、绝学、圣学、大学,毕竟无所得、无可得,因为本来具足,不增不减;所谓传法,也毕竟无所传。怪不得船子和尚曾吟出“满船空载月明归”、“除却蓑衣无可传”[10]的佳句。这不是单纯的咏景,反映的正是船子的修养、工夫境界,同时也是对千百年前船子、成连舍身传法意象的绝佳概括。
“本来”对中国文化意义重大,除佛禅以此为归旨外,无论是原儒的仁学⑤在此意义上,孔子的“思无邪”、“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四端”说等皆是“本来”的表现。、《大学》中的“明明德”、《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朱熹、吕祖谦《近思录》中的“圣人之道如天然”、陆王心学中的“心即理”、“发明本心”、“剥落工夫”、“致良知”、“诚意格物”,还是道家的“法自然”、“清静无为”、“见素抱朴”、“心斋”、“坐忘”,都以之为本体或目的。尽管各家对“本来”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不可否定的是,不理解“本来”,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找到了“本来”,就找到了文化的根、主体、自信与活水源头;忘失了“本来”,文化就会丧失灵魂,变得向外求、逐物,就有可能迷失方向,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嬗变的本质其实就是对“本来”的质疑与疏离,从而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文化殖民。当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学术日益走向僵滞,唐宋之前的宏伟气象及其生机与活力不复存在,各家学统多名存实亡,并对国计民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现在,随着近十年知识界普遍的文化自觉,在21世纪重树中国文化主体性已成为政府、学界、民间的共识,重新回归“本来”、立足“本来”以建构中国未来的文化就自然成为了我们应当重视的课题,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找到自身文化归属、文化身份的必由之路。
第四,无论是船子、成连舍身传法这种特殊的教育、表达方式,还是以绝境示道、在绝处领悟的绝学传统,抑或是夹山、伯牙对“道”、“本来”的追求、体究,都昭示了我们民族一种特有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性,这就是对“道”的尊崇,对守护、传续“道”的使命感,以及将生命历程融入“道”而不惜放身舍命的“剑人合一”的人生境界。这也就是宋儒张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的人生信条的生动体现。同时,历史中无数次的以生命为代价的传法授道,也让中华师道具有西方学统难以比附的庄严底色,让中国传统师生关系具有可以生死相托的强烈的信任感、纽带感与承续感,因为“道”就是他们之间的生命联结,这是最高的见证。但古来圣贤皆寂寞,船子和尚交代夹山时也不过说:“觅取一个半个,接续无令断绝。”可见传续之难。今天,禅与琴再次成为了人们热衷的对象,甚至是一种时尚。与古时不同的是,现在的禅与琴充满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疲软、空洞与消遣意味,人们把在华屋中喝茶品茗、谈笑风生就叫禅了,开馆授业、附庸风雅就叫琴了。再无古人那扑面而来的阳刚气息与追究、守护、承继道体的热情与责任,更无船子、成连那样献身于“道”的丈夫情怀。禅与琴都在,但它们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却不在了。历史发展到今天,又给了我们一次文化复兴的契机,文化复兴是与文化精神的复兴密不可分的。回首往昔,船子、成连依然站在千百年前给予我们弥足珍贵的启示。
余论:别无归处是吾归
船子投江、成连入海,当我们听到他们的故事,我们会想象他们的归宿,会问他们去哪了?船子在《拨棹歌》中回答:“别无归处是吾归。”[10]是的,“别无归处”正是他们壮美生命的归处。这句充满隐喻的诗并不是在诉说死亡,恰恰充满了生机,彰显了生命及其承载的绝学的真义,即“道”不落言筌,人生亦如此。若落在某个“归处”,则说明尚未“到家”。
当船子毫不犹豫地投入江中时,他大约不会想到他与夹山对中国禅宗未来的重要影响;当成连驾着小舟驶向大海时,他大约也不会想到他对伯牙的移情,改变了后来整个的中国琴学。船子与成连是两个幸运的老师,夹山与伯牙是两个幸运的学生。因为他们的相遇,他们一起完成了“道”的接续,也就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的接续。中国文化需要接续下去,但在今天,文化继承者们似乎更有必要先找到它的归处再重新出发。笔者以为,文化的归处就在船子、成连、夹山、伯牙这些古圣先贤当初背着行囊求师问道的出发处。在那里,有一种至真至贵的东西已被遗忘了千年之久。
[1][宋]普济.五灯会元[G]//卍新纂续藏经·第80册.
[2][明]瞿汝稷.指月录·卷十二[G]//卍新纂续藏经·第83册.
[3][元]明本,慈寂.天目中峰和尚广录[G]//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宋]朱长文,林晨.琴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明]李贽.焚书·征途与共后语[G]//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6][春秋]李耳.老子·第十九章[G]//陈志坚.诸子集成·第2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7][宋]重显,克勤.碧岩录·卷一[G]//大正藏·第48册.
[8][战国]孟轲.孟子·告子章句下[G]//陈志坚.诸子集成·第1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9]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一[G].[唐]实叉难陀,译//大正藏·第10册.
[10][唐]德诚.船子和尚拨棹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王晓俊)
J60-02;J608
A
1008-9667(2016)02-0062-05
2015-06-22
周钟(1985- ),江苏连云港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美学。
①本文为江苏省2014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论佛教的音乐美学思想》(项目批准号:KYZZ_0279)阶段性成果。
——释德扬法师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