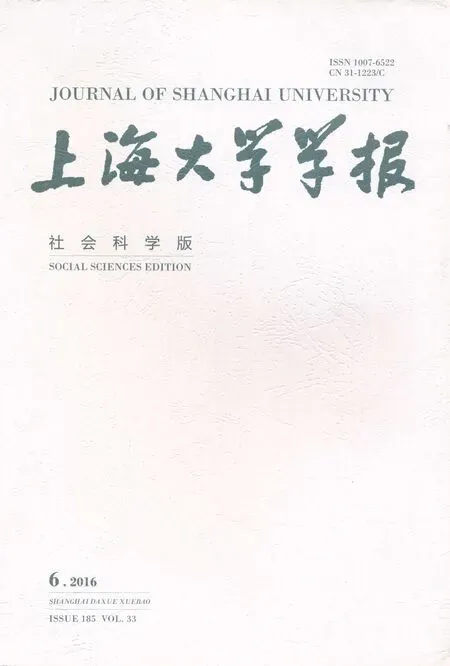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姜 玉 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论盛唐边塞诗对“汉文本”的引用与改写
姜 玉 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从特殊的西北地域文化环境角度来探讨盛唐边塞诗“雄浑”“浑厚”美学风格之形成,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但绝非是唯一的切入点。盛唐边塞诗风格的形成还可以从技术层面上来考察:诗人通过对“汉文本”的引用和改写,突破边塞诗这一诗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局限,从而把其原本处于封闭状态,即受到“边”与“塞”之束缚的诗歌类型,引入到一个以汉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的价值范式之中。盛唐边塞诗的展开空间,是一种与历史贯穿于一体的大文化时空观。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是一种与历史文化紧密相关的创作。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浑”和“厚”的艺术特质也是必然的。
边塞诗;汉文本;引用;改写
在盛唐边塞诗研究中,存在着一个研究者普遍公认的现象,即生活在盛唐的边塞诗人们有一个喜欢借“汉”写“唐”的癖好。程千帆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指出这一史实:“以汉朝明喻或暗喻本朝,就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传统的表现手法,其例举不胜举。当诗人们写边塞诗的时候,也往往是这样做的。全诗或以汉事写唐事,专用汉代原有地名;或正面写唐事,但仍以汉事作比,杂用古今地名。”[1]今天面对这个史实,我们应该追问的是,盛唐边塞诗人为何不直奔主题地去写那些迫在眉睫的战事,反而通过六七百年前的汉来反映当下的唐?促使诗人“以汉喻唐”的内在玄机是什么?
一、从“边”到“塞”:内涵、外延都逼仄的诗体空间
要探讨文学史上的这种创作现象,应该从盛唐边塞诗的诗体自身出发。从概念上看,盛唐边塞诗不是一个笼统而开放的集合,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准则。这种要求和准则简单说就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必须得满足“边”和“塞”之需求。
何谓“边”,何谓“塞”?顾名思义,“边”意指“边远”“边缘”,具体到领土疆域,当然是指远离内地(包括中原和南方)的偏僻且边隅的地理空间,这个地理空间我们通常称之为“边疆”。所谓“塞”,解释为“可作屏障的险要地方”。[2]可见,这个在地理位置上充当着“屏障”的“塞”,比所说的“边”还要“小”。如果说“边”在地理位置上不占优势——远离中心地带,中央政府,可它毕竟还有一定数量的面积作保障,譬如西北边塞就是一个空间相对宽广的概念;而“塞”则不同,它不过是“边”中一个起到阻挡作用的“屏障”,即据守“边”的一个点而已。当“边”和“塞”组合到一起,构成“边塞”时,中心词无疑应该是“塞”。这就说明在盛唐边塞诗中,位于国界边上的“塞”才是统率全局的枢纽之处。这也不难理解,“塞”既是战时士兵们据守的地方,又是非战时期士兵们生活的地方,这一种双重属性就决定了“塞”才是盛唐边塞诗人所关注的重点。
对“边”和“塞”的廓清,意在说明与其他的诗歌创作相比,可供盛唐边塞诗情感挥发、演绎的空间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它一方面要受到远离“中心”且不能逾越的“边塞”的限制,因此诗人在对景物描写、意象塑造乃至于语言的调遣使用上,必须与西北边塞的地理风貌、文化气息相一致;另一方面,诗人们所抒发的感情必须与战事及与战事相关的内容密切相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与战争相关联的诗歌创作模式,盛唐边塞诗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局限,即思想内容的不自由和艺术表达形式的不自由。
当然,彻底自由的诗歌创作并不存在。只要承认诗歌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就必将要受到一系列的限制,但是像盛唐边塞诗这样框定于西北边陲的创作,也并不多见。譬如同时代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也是需要戴着镣铐跳舞,即其所展开的诗情必须得限制在“山”和“水”之间,但该处的“山”与“水”是广义上的“山”与“水”,非但没有受到地域性的限制,相反它还可以是大自然的代称。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就存有用山水代替自然的惯例。从这个角度说,山水诗看上去是不自由的,可这种不自由中又蕴含着最大的自由,整个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星一辰都可以用来寄托诗人的情感。相比之下,盛唐边塞诗则是用“北地的风物,边塞的状况”[3]59歌咏而成的。此处所说的“北地”既指地理空间上的北部边疆,也指诗歌的表现空间;“边塞”也同样如此。这也从另一方面佐证盛唐边塞诗作为一种诗体,它只能调用“北地的风物”来书写和表达发生在“边塞”上的“战事”,而“中原”和“南方”的“风物”被排斥在外。这一种理论上的推想是否与盛唐边塞诗人们的创作相吻合,还需要由具体的诗歌文本加以验证。
盛唐诗人都有写边塞诗的癖好。宗白华曾指出:“盛唐的诗人们——无论著名的作家或未名的作家,对于歌咏民族战争,特别感兴趣,无论哪一个作家,至少也得吟几首出塞诗。”[4]87当然最终以边塞诗屹立于文学史的,则还要首推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等。纵览这些诗人的创作,包括像王维、李白这类虽不以边塞诗见长,可也创作出不少首脍炙人口边塞诗作的诗人,会发现其创作有一个明显的共性:凡是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都是围绕着西北边境上的“战事”展开的,区别仅在于诗人们所描写“战事”的视角,讴歌情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诗人擅长从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地点中发掘诗意,这类诗人往往自身就是西北边塞战场中的一员。他们笔下的诗歌与他们本人关系就是一种亲历的关系。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均属此类。由此也可见,岑参与高适之所以能成为盛唐边塞诗创作中的两面旗帜,写出“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燕歌行》)这类感人至深的诗句,与他们多次亲赴西北边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说岑参与高适喜欢直截了当地描写战争,那么另外的一些诗人则是通过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来烘托战争,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陇西行》,李白的《关山月》等诗都是如此;还有些诗人通过对历史上一些战役遗址的描写,如“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王昌龄:《塞下曲》)来映衬对当下“战事”的看法。显然,无论诗人们的切入点如何,有一点是不变的,都离不开“战事”这条主线,即便是像王昌龄“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从军行·其一》)这类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诗作,也是由“烽火城西百尺楼”这一战争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也就是说,盛唐边塞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但引发盛唐边塞诗创作动机的,都与戍守边疆这一事件本身有关。诚如有研究者在论述到盛唐边塞诗的思想内容时所说:“边塞诗中往往突出地表达唐王朝国内各族人民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兵民众热爱自己国家、民族的精神。”[5]可见,盛唐边塞诗在题旨方面是有所要求的。事实上,盛唐边塞诗不但在内容上需要以“热爱自己国家、民族的精神”为轴线来组织,就是在景物描写、意象塑造上也同样面临着一些具体要求。可以通过下面的具体诗句来讨论该问题: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王昌龄:《从军行》其五);
“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
从表面来看,盛唐边塞诗在景物描写和意象凝造方面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如上述诗歌中所出现的“风”“夜”“石”“日”“红旗”“云”“雨”和“雪”等意象,并非仅仅局限于西北边塞,即使是中部平原、南部地区也有,这一情况是否表明西北边塞虽然地域偏狭,但可供诗人调遣使用,即寄托感情的自然景物并不少?
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西北边塞既没有内陆春暖花开的季节,也没有小桥流水之类的自然景物。这就意味着边塞诗在对自然景物的选择与描写时是存有限制的,即某些景物不可能出现在西北边塞诗中。还不仅如此,即使是对西北边塞已有的景物描写,也是要受到明显地域限制的。如前文中所说到的“风”“夜”“石”“日”“红旗”“云”“雨”“雪”等景物,作为诗歌意象原本具有多义性,像“风”既可以是和煦的春风,又可以是刺骨的寒风,也可以是恬淡的清风;“雨”和“雪”既可以是恶劣、残酷天气的象征,更可以是浪漫、抒情的点缀。然而这些意象一旦在西北边塞诗歌中出现,就只能沿着冷峻、酷寒即“轮台九月风夜吼”“雨雪纷纷连大漠”的方向走了。正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谈到岑参的创作特色时曾说:“岑参若写风定是大风,写雪定是大雪,或是大热大寒。”[6]337冯沅君所说的这种“大风”“大雪”“大热大寒”,就把“小风”“小雪”“小热小寒”排除在外了。西北边塞所固有的地理情况,决定了盛唐边塞诗只能在豪迈、粗犷的价值维度中搭建其审美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此后有研究者概括道:“边塞写景带有鲜明的边地肃杀萧瑟的情调,往往具有苦、寒、险等特色。莽莽瀚海、崔嵬雪山、雄关大漠、陇水关山、飞沙走石、风急天暗等边景为其常见的特色意象。”[7]这一现状就决定了盛唐边塞诗在美学风格上展示出剑走偏锋的瑰丽、奇峭之美,却难以在“浑”和“厚”的美学风格上有所创建。换句话说,它可以拥有一个与地域环境相一致的即以峭峻为特点的诗歌骨架,可要让“骨架”中的肉长得“浑厚”则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种以“浑”和“厚”为特征的审美意境的形成,不但需要审美思想的多样性,同时也需要艺术风格的多样化。而这两点恰恰又是盛唐边塞诗所欠缺的。
总之,由于盛唐边塞诗自身的局限,照其固有逻辑的发展,它必然会走向“狭”而“专”的艺术格局。奇怪的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盛唐边塞诗偏偏又是以开放性的大格局、大气象见长的,文学史上所谓的“盛唐气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盛唐边塞诗的恢宏博大而博得的。换句话说,在古代文学史中,它除了以剑走偏锋之美见长外,也是以“浑”和“厚”而著称的。如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是把盛唐诗歌的“雄浑”之境置于二十四诗品之首的;宋人严羽也是把整个盛唐诗人的创作风格总结成“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8]522他们两位在论述“雄浑”“雄壮”“浑厚”之美学风格时,虽没有直接把盛唐边塞诗推出来,但是现如今对盛唐诗歌有所了解的研究者都知道,最为符合于“雄浑”“雄壮”“浑厚”之条件而又有广泛影响的,无疑应该首推边塞诗。*盛唐诗歌中可以与边塞诗一争高下的,无疑当属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山水诗,这类诗歌的美学特征显然不可以用“雄浑”“雄壮”“浑厚”等词语来概括。这样一来,我们必然会问:盛唐边塞诗身上的这种“浑”和“厚”的艺术特质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盛唐边塞诗诗体自身的局限与实际美学效果之间的矛盾是如何解决的。明白了这一点,其实也就大致明白了整个盛唐诗歌,乃至于古代诗歌的创作理路。
二、“汉文本”的引用:大历史文化观念下的创作策略
与“浑”和“厚”相关联的词语应该是丰富、多样化,而单一化包括内容上的单一和艺术形式上的单一,都是难以达到“浑厚”之要求的。如前文所述,照其所固有的运行逻辑,盛唐边塞诗不管怎么写,在内容上它必然要滑向社会与政治;在艺术表达上要偏向于西北边塞的“荒”和“漠”。前者会导致诗歌内容上的写实,后者会导向艺术风格上的单一。写实与单一,这是中国古代诗歌所一贯崇尚的美学风格吗?
当然不是。对中国古代诗学了解的人知道,古代诗歌从所谓最为写实的《诗经》开始,就是崇尚“虚”而反对“实”的。在中国最早的艺术表达手法赋、比、兴中,除了赋偏向于写实,其他两个都是反对写实的,古人是不赞赏直言其事的。对此,明代诗学家谢榛说得最直截了当:“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以名状……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8]683其意即强调创作的最高技巧就是“含糊”和“难以名状”,反对具体和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最美、最高超的艺术就是要处于“似”与“非似”“像”与“不像”之间。惟有如此,艺术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其所应有的魅力。宗白华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论述:“诗人艺术家往往用象征的(比兴)手法才能传神写照。诗人于此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声调,色彩,景物,奔走笔端,推陈出新,迥异常境。戴叔伦说:‘诗家之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就是说艺术的艺境要和吾人具相当距离,迷离惝恍,构成独立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才能象征那难以言传的深心里的情和境。所以最高的文艺表现,宁空毋实,宁醉毋醒。”[4]168古人这种“宁空毋实,宁醉毋醒”的美学追求,决定了盛唐边塞诗人是绝对不可能就眼前的“边塞”来写“边塞”的,因为这样写难以与现实拉开距离,既达不到“迷离惝恍”的艺术要求,又体现不出“空”和“醉”的艺术特质。
盛唐边塞诗人如何才能在创作中把这种美学追求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最简捷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其创作寻找一个“是”而又“非是”的替代物,或者说象征物也可。
当然,这个“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间”的“替代物”(象征物)需要具备两个条件才行:首先,时间上要与盛唐当下西北边境上所发生的战事拉开一些距离,即能“望”得到,又得与之保持一定时空的距离感。惟有如此,才能把那些迫在眉睫的“战事”给模糊化、破解化,使原本的“实”变成若有若无的“虚”;其次,两个“事件”之间得有一定的可比性,否则这个“替代物”(象征物)也不会成立。纵观中国历史,盛唐之前历代边境上都不乏有战争爆发,然而在综合国力与民众的精神气质上可以与盛唐相媲美的,则当属汉代。尤为重要的是,西汉在与聚居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游牧民族匈奴的长期作战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的优秀将领和英雄人物,同时也流传着许多著名的战役和故事传说等,这一切都为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照文本。果然,盛唐边塞诗人都对这个同样是发生于西北部的汉代战争文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纷纷把其引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如: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如果不了解该诗的写作背景,便会有莫名其妙之感。因为诗歌中的“渠黎”是汉代西域国名;“单于”是西汉匈奴最高首领的名字;“轮台”这个地名在唐代倒是有,问题是驻扎在此地的士兵又是一群“汉兵”。这就不免让人心生疑惑:岑参咏歌的这场“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的战争,与其说是对发生于盛唐西北边塞战争的一种真实写照,不如说是对爆发于汉代大漠边陲的一场历史战役进行追溯更为适合。
如果说这首诗还多少有点令人疑惑的话,高适那首著名的《燕歌行》则无任何悬念了,因为诗歌一开篇就交待了战争发生的时间和交战的双方: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战争爆发的时间是“汉家”,也就是“汉朝”;交战的双方,一方是英勇杀敌的“汉将”——汉代的士兵;另一方是以单于为代表的西汉匈奴大军。显然,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这场以“汉”为背景的战争与盛唐边境上的战事一点关系都没有。然而,诗歌史告诉我们,这首诗,包括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都并非是咏史诗,而是直指当下社会的。前一首是岑参特意为好朋友“封大夫”(封常清)带兵西征而作的一首送别诗;后一首也与友人出塞有关,诚如作者在序言中说:“开元二十六年(738),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9]193该处所说的“征戍之事”是与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即序言中所提到的“御史大夫张公”有关。这个“张公”为了不影响其仕途升迁,非但没把部队大败于契丹之事据实禀报,相反还大肆贿赂朝廷派来调查真相的使者。当高适从“张公”身边归来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忍不住心中的愤慨写下了《燕歌行》,这才有了“因而和焉”之说。
从对以上两首诗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表面上像是描写汉代战争的诗作,其实指向的都是盛唐西北边境上的战争,只不过采用了以“汉”写“唐”的手法而已。这种手法主要还不是一种借古讽今,而将之理解成是对“汉”或者说“汉文本”的一种引用可能更为恰当一些。所谓的“汉文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汉文本”,是指与汉代有关的一切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内容在其他历史时期文本中的再现;狭义的“汉文本”是指“以汉代唐”的历史史实和有关汉代的一些历史、文学典故以及民歌曲调在盛唐边塞诗中的复活与广泛运用,并形成盛唐边塞诗的一个有效构成部分。本文的“汉文本”主要偏重于在后一种意义上的使用。
这样一来,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追问:为何不可以把“汉文本”的使用,理解成是借古讽今?原因如下:首先,所谓的借古讽今,强调的是借评论古代的人和事来评论现实,即重点落在“评论”二字上。其目的是通过对古人和古事的“评论”,来影射当下社会中的“人”和“事”。然而分析一下盛唐边塞诗会发现,那些出现于诗歌文本中的汉代的人和事,非但没有承担任何“评论”之重任,相反它们的亮相是非常自然、流畅的,如同原本就是盛唐中的人与事一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仍以《燕歌行》为例加以论述。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这首诗共有二十八行,但是直到最后一行才提到李将军这个人。具体说,诗人把李将军这个人物引入到诗歌文本中来时,既没有对其身世、功名进行交待,也没有对引入李将军的意义进行评说。总之,没有任何的前兆和过渡,甚至在我们连李将军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诗人强行地引用到了文本中来。
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完成这样一个不会令人觉得唐突的引用?一般说来至少得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李将军必须得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历史名人。的确,该处的李将军确实赫赫有名,《史记》中就有“李将军列传”。第二,李将军在历史中演变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否则对他这个人物的引用就发挥不了作用。这样一来,必然会引申出如下的问题,李将军在诗歌文本中到底隐喻着什么?据《史记·李将军传》记载,他是一位非常体恤、爱护士兵的将军:“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9]195只有当明白了李广将军这个人物符号所承载的意义,是一种“爱兵如命”的精神时,才会懂得“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对应的是“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同时,也才会懂得这些上下诗句之间所产生的那种美学张力。
至此可能会有个有趣的问题浮上来,有关李将军的一切背景知识在诗歌中都是欠缺的,可是诗人与读者之间却呈现出一种心有灵犀的态势,这说明在盛唐诗人和盛唐读者那里,他们头脑中的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互为一体的大文化观念,即从汉到唐以来几百年的政治、历史与文学都是互为贯通的,彼此之间不但可以相互旁证和引用,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相互勾连,互为一体的大文本。正如林庚在谈起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技法时所说,它们“往往不拘于哪个具体战役,哪个时间、地点,而是在广泛的时间、空间上把边塞作为一个整体来歌唱”。[10]65这个“广泛的时间、空间”感的确立非常重要,只有在这样一种大文化时空观念的烛照下,才可以使汉代的士兵、将领、地名和官衔等,不经过任何的过渡和界定就能直接引用到盛唐边塞诗歌中来。
总之,盛唐边塞诗虽然是以盛唐西域战事为抒情依托,但是诗人们的抒情视野则是建立在从汉到唐以来的大文化视野之上的。这一点从盛唐诗歌对“汉文本”其他方面的引用中也能看出来。如果说以“汉”写“唐”是对“汉文本”引用的一种宏观说法,那么还有对“汉文本”的微观引用,试举两例为证。
一是对曲调的引用。盛唐边塞诗中有不少诸如“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李颀《古意》),“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李白:《塞下曲》),“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贯山”(高适:《塞上听吹笛》)这类的诗句,即诗人喜欢借某种曲调来抒发情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中所提到的“曲调”,无论是“出塞曲”还是“折柳曲”,都并非是盛唐时期所独有的曲调,而是能够溯源到汉乐府,并且这些曲调在汉乐府中就是固定情感符号的象征,如“出塞”曲多半对应的是边疆战士的生活;“折柳”曲与征戍之事相关;“借问梅花何处落”中的“梅花”,是指汉乐府横吹曲“梅花落”,这个曲子对应的往往是生死别离之情。盛唐边塞诗人在引用这些曲子抒发情感时,基本延续了该曲调所固有的情感内涵。这说明汉乐府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价值语码,在盛唐边塞诗人这里继续有效并发挥着作用。
二是对汉代历史典故的引用。这在盛唐山水诗中非常多,如“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李颀:《古从军行》)中的“公主琵琶”,以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中的“楼兰”,都属于是汉代的历史典故。从盛唐边塞诗人对这些典故得心应手的运用来看,盛唐时代诗人与读者之间都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汉代的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包括政治文本都是可以直接通达到盛唐边塞诗歌中来的,即这两个大的历史文化时空是融会贯通的。只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盛唐边塞诗人才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把汉代文化中的诸多东西引用到诗歌文本中来。
除了上面所涉及的这几种引用以外,盛唐边塞诗本身其实也就是对汉乐府的一种引用。原因是,盛唐边塞诗人的写作多半是一种乐府旧题式写作,如诗人们广泛采用的《塞上曲》《从军行》《关山月》《燕歌行》等都是对汉乐府体式的袭用。盛唐边塞诗人之所以要从“汉文本”中大量引用资源,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汉代的历史、文化时空引入到盛唐中来,从而在技术层面上破解了盛唐边塞诗过于封闭的表现空间,使之呈现出开放的态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汉”写“唐”的策略,也就是一种把当下的“战事”拉远,使“实”化“虚”的一种技术策略。
或许有人说,这个技术策略的实现是建立在汉代文化与盛唐文化一体化的基础上的,即其前提是,以汉代文化为代表的整个古代文化传统都变成了当下文学所展开的背景与资源。这岂不意味着所有历史阶段中的文学时空都是互为重叠、一体的,如此一来,不也就意味着所有历史阶段中的诗歌创作也都是互为重叠、一体的?具体到盛唐边塞诗,不就意味着盛唐边塞诗是汉代边塞诗的翻版?事实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当下的文学时空在接受以“汉文本”为代表的古代文化传统这个大文本时,也会根据情况需要对其进行改写的,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三、对“汉文本”的改写:盛唐边塞诗的艺术个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盛唐边塞诗的创作就是建立在对“汉文本”引用之基础上的。这或许也是刘经庵在《中国纯文学史》一书中,批评古代作家特别喜欢“模仿古人文体成了千部一腔的老调子”[3]5的原因。刘经庵的批评,有一语道破天机的一面,即由于“引用”作为一种创作手法,被不同时代的诗人们所广泛采用,故而不同时期的诗歌中的确存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然而这绝非表明不同历史时期的诗歌都没有自身的特点,完全可以互相替换与取代。就像盛唐边塞诗的创作,我们可以用以“汉”写“唐”来指称它与“汉文本”特别是汉魏边塞诗之间的关系,但不应忽略的是,盛唐边塞诗具有区别于汉魏边塞诗的个性特征。
汉魏边塞诗的创作状况比较复杂,不同诗人有不同的聚焦点,但总体说来这段历史时期的边塞诗呈现出的一个共同思想倾向是:诗人们通过诗歌文本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多半都是与批判、揭露战争给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有关。如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借助“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的诗句,表达了对秦统治者为了防御异族的入侵而迫使男丁修筑长城的愤慨之情。同时他还用“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的诗句,揭露了巍峨长城实际是用“死人尸骨”堆积起来的丑恶现实。蔡文姬在其著名的以军阀战争为背景的《悲愤诗》中,更是发出了“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的诘问。相比之下,盛唐边塞诗中有时也会穿插上一些质疑战争的诗句,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可一般说来,其总体格调还是昂扬向上的。正如冯沅君、陆侃如在《中国诗史》一书中,谈到他们最为欣赏的盛唐边塞诗人岑参时所说:“他写战争不大诅咒战争的残酷,而常赞颂战争的伟大……然而古乐府中实在诅咒多于赞扬,恰与岑参相反。”[6]362这里谈到的尽管是岑参个人的创作风格,其实放眼望去,与整个盛唐边塞诗的创作状况也是互为一致的。
诗人们不诅咒、排斥战争,而是一方面在诗歌中热情洋溢地勾画出战争的场景,如“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须如猬毛磔”;(李颀:《古意》)一方面又借助于诗歌表达了誓死杀敌的决心与勇气,如“出身仕汉羽林郎,初随骠骑战渔阳。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维:《少年行·其二》)总之,诗歌中充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即便是带有某种批判之情绪的,就如前面提到的《燕歌行》,诗人也只是把批判的触角对准个别的将官,而对战争本身则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价值判断,高适才会在诗歌的结尾发出“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感慨。
诗人们这种乐观、崇高化的审美基调,说明战争在他们的眼中,并非是一件躲避不及的苦差事,相反,他们愿意随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场战争。问题在于,与汉魏边塞诗人相比,盛唐边塞诗人为何会有如此高涨的民族情绪?
事实上,盛唐边塞诗人的这种民族情绪是不那么正常的,因为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盛唐时代却恰恰是边塞上最为相对平静的时刻”。[10]64在这种“最为相对平静的时刻”,盛唐诗人的内心却涌动着赴边塞杀敌的豪情,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而且,这个豪情的背后是对其书生身份的厌弃,如岑参在《银山碛西馆》一诗中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李白也发出了不愿“白发死章句”(《嘲鲁儒》)的心声。就连像王维这样深受佛学、禅宗影响的诗人,也吟出了“忘身辞凤阙,抱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的诗篇。照道理讲,书生与英雄原本是两种不同但可并行不悖的人生定位。诗人的本色就是书生,英雄则应该是武生所承担的角色。盛唐诗人为何纷纷涌现出弃书生而取英雄的想法,借用初唐边塞诗人杨炯的话说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宁可做一个低级军官,也不做一名书生的价值选择,究其原因,或许有多种,诸如盛唐知识分子们的眼界和心胸都普遍地开阔、豪放,这会促使他们不断地拓展、转换其生活疆域。正如研究者说:“唐代知识分子不像两汉儒生那样拘谨褊狭,也不像六朝名士那样狂放怪癖。他们昂扬进取于功业和艺术,而在昂扬进取之中往往有洒脱和从容。……唐士不重礼法,但并不逃名避世,并不远离政治。”[11]这种兼容并蓄的生活态度,决定了他们在从事艺术的同时,也不会排斥政治和功名。除此之外,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当时朝廷针对知识分子所颁布、实施的入幕制度。
古代的知识分子经常在“仕”与“不仕”之间摇摆。不过大致说来,“学而优则仕”还是知识分子们的一个主流选择,尤其是盛唐文人把“仕进”作为“生活的首要目标”。[12]知识分子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常规的办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然而这条路异常坎坷,从岑参所发出的“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与孤独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的哀叹中,不难窥出其中的艰辛。在这样一种现实境遇下,朝廷为读书人另辟出一条“仕进”的渠道,即凭靠着边功就可以实现其建功立业的理想,这怎能不令他们欢欣鼓舞?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高适《塞下曲》中抒发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图画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之感慨了。同时也明白了为何连终生不仕的孟浩然,都鼓动着亲朋好友要“饰装辞故里,谋策赴边庭”。(《送莫甥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
既然赴边杀敌是与“仕”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诗人在赴边的过程中,有时便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不仕”的担忧。这种复杂而幽隐的时代心理,在盛唐边塞诗中有着明显的表现。可以看一首高适的《金城北楼》:
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激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
自称“一生徒羡鱼”的高适,对其想做官的心理从不掩饰,可偏偏他官运不济。早年在长安游历多年,无果;后争取到一个小官,又因故辞掉了。一直到天宝十一载,才等来了机会,经友人推荐,离开长安,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中,担任掌书记一职。这首诗就是写于他奔赴边塞的途中,即路过金城(现在的甘肃兰州)时所作,从中不难读出其复杂的心绪。这首诗的前四句,为我们描画出一幅金城美景。然而面对眼前这幅山傍依着水,月高悬于城头的图景,诗人内心想到的却是“垂竿已羡磻溪老,体道犹思塞上翁”。这两句诗引用了两个典故,即“姜太公钓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传达诗人的内心世界。
在古代文学传统中,凡是与垂钓等相关联的意象,大都是与“钓”皇帝这条大鱼有关。姜太公当年直钩垂钓于渭河,就碰上了赏识他的周文王。无疑,诗人在该处借这一历史典故表达了内心的希冀,希望在这次的赴边中能碰上一位赏识他的君主。当然,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之所以能千古流传,恰恰说明这样的事情并不常发生,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诗人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又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典故,表达了其内心的不安:不知这次奔赴边塞战场的选择,到底是福还是祸?结合该诗的最后两句“为问边庭更何事,至今羌笛怨无穷”来看,诗人对这场发生于边庭战争本身并无太多兴致,否则听到的“羌笛”,断然不该是“怨无穷”。
显然,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出塞不错,但这种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功利心理联系在一起的,即出塞不过是实现其理想抱负的一种手段而已。至此,与汉魏边塞诗的创作主旨就相差甚远了。从艺术自律性的角度而言,盛唐边塞诗人的创作动机似乎不够纯洁,里面充斥着一些政治诉求;可是如果从诗歌的艺术效果来看,又不得不承认,正是激荡在诗人内心深处的这份渴求,才使得盛唐边塞诗多出一种进取的精神和大气磅礴的气势。毫无疑问,盛唐边塞诗在对“汉文本”进行引用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写,即增加了时代所独有的特色,从而使盛唐边塞诗既有与汉魏边塞诗一脉相承的地方,同时也有自身的一些个性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改写不仅仅局限于对内容的改写,在艺术形式上也留有改写的痕迹。
或许是由于时代较早,诗人们的创作观念较为自发的缘故,汉魏边塞诗所展开的艺术时空多半是单维度的时空,如曹植的《白马篇》、蔡文姬的《悲愤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如此。这些诗歌写得真挚感人,但必须得承认,这些诗歌所塑造的艺术空间,包括意象和语言的调遣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特征。这也是这些诗歌为何都带有一定的叙事性的原因。与此相比照,会发现盛唐边塞诗艺术空间的构成要复杂许多,而且就连意象和语言也要色彩斑斓得多。我们的问题是,同样都是以北地的边塞为抒写背景,为何后者就能在艺术形式上展示出更大的魅力?应该说,这主要与盛唐边塞诗人擅长把不同的艺术空间引入到诗歌文本中来有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看一首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这是一首借景抒情的诗,就景而言,无疑描写的是西域八月飘雪的景观。确实,诗歌前两句中的每一个意象,如“北风”“白草”“雪”指向的都是塞北的景物,特别是八月里下大雪更是西北边塞才会有的特殊天气。这就意味着按照正常的逻辑,这首诗歌只能按照北方冬天的逻辑来写,即诗歌中所展开的文学空间对应的只能是北方冬天的时空。总体说来,这首诗也的确是沿着北方冬天的逻辑特征,即“雪”这一意象来展开的,即诗歌由“飞雪”始,到“雪上空留马行处”终。然而,这首诗歌的巧妙之处在于,诗人在遵循北方冬天时空逻辑的同时,又改写了这个时空。
如何改写的?很简单,诗人在保证北方冬天基调的基础上,又把代表春天、代表南方的文学时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穿插到了文学时空中来,从而使原本单维度的文学时空,一下子变成了双维度甚至多维度的文学时空,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表现层次。从这个角度上说,不可低估这种穿插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时空穿插,就像这首诗之所以能从冬天一下子穿插到春天,是因为雪花是白色的,而梨花也是白色的。同时雪花飘落在了树枝上,远远看去也像是梨花。如果缺少了这两个前提条件,时空穿插是不可能实现的。假若缺少了这一环节,整首诗歌从头至尾就只能沿着“冬天”这一个维度来运转。而存在于这一维度中的意象,无论是“雪”“铁衣”“瀚海”“愁云”,还是“胡琴”“琵琶”“羌笛”等,指向的都只能是愁苦和悲哀。这样一来,该首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就被大大地局限住了。而一旦插入进“春风”“梨花”这些与春天相关的意象,这首诗歌就活了,其意境一下子从“愁苦”“悲哀”中逾越了出来。正是因为有了春天这一代表希望的时空的出现,才令诗歌的最后几句“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具有了一抹亮色,给人留下了乐观的遐想。
可以想见,这首诗歌如果缺少了“春天”这一环节,也依旧不失为是一首送别诗,但是其意蕴乃至于感官形式都要逊色许多。显然,这首送别诗被广为传唱的并不是那些和送别有关的诗句,而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并非偶然。这种凭靠季节穿插、引入来丰富、扩大诗歌表现空间的技巧,是盛唐边塞诗人最常用的技巧之一,由于篇幅原因,不多赘述。
综上,盛唐边塞诗之所以能突破其诗体的束缚,让自己在广阔而浑厚的艺术空间中驰骋,凭靠的主要技巧之一就是对文学的历史时空和当下文学时空的巧妙融合,使之形成一种往上追溯可以与汉魏诗歌乃至于整个文化传统互为一体的大文本,往下溯源,又确确实实具有当下社会的特征。如果说汉魏以来的诗歌传统赋予盛唐边塞诗所应有的广度和厚度,那么诗人们所身处的时代则又让他们的诗歌产生了独具一格的魅力。盛唐边塞诗就是在两个相互重叠的时空文本中,寻找到创作的意义的。
[1] 程千帆.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极其类似的问题[M]. 程千帆,张春晓. 程千帆卷.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2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81.
[3] 刘经庵. 中国纯文学史[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4] 宗白华.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胡大浚. 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J].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2):47-55.
[6] 冯沅君,陆侃如. 中国诗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7] 阎福玲. 汉唐边塞诗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14:10.
[8] 陈良运. 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G].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唐诗选:上[G].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93.
[10] 林庚. 唐诗综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5.
[11] 霍松林. 中国诗论史:中册[M]. 合肥:黄山书社,2007:464.
[12] 陈铁民. 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J]. 文学遗产,2002(3):23-38.
(责任编辑:李孝弟)
On the Quotation and Rewriting of “Texts of Han Dynasty” by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ts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JIANG Yu-qin
(TheInstituteofLiterary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vigor and firmness displayed in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can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unique Northwest which is a good, yet not the sole approach. They can also be 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 literary devices. The fortress poets broke the confinements inherent in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tself by quoting and rewriting the texts of Han Dynasty, thus liberating the creation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from the confinement to “frontiers” and “fortresses” and setting fortress poetry in the value paradigm of the whole ancient cultural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the culture of Han Dynasty. That is to say, the folding space displayed in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is a grand cultural temporal-spatial conception integrated with history. In this sense, the creation of frontier fortress poetry in the flourishing period of Tang Dynasty associates closely with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vigor and firmness in the poems are thus inevitable.
the frontier fortress poems; the texts of Han Dynasty; quoting; rewriting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11
2016-04-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15ZDB067)
姜玉琴(1965- ),女,山东济南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
I206.2
A
1007-6522(2016)06-01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