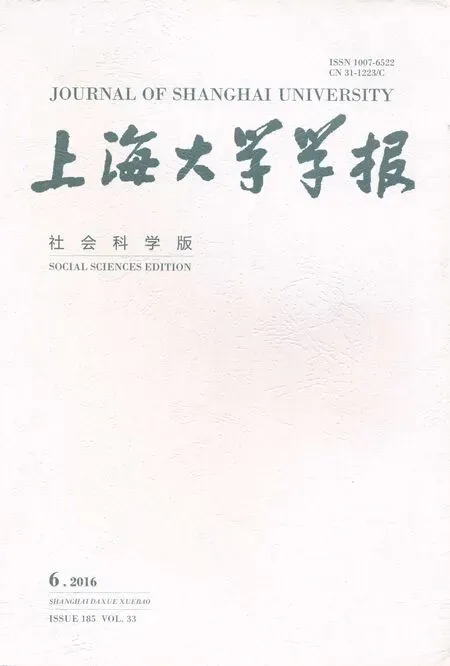目光与世界——《一个勺子》的存在论视觉美学分析
吴 明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目光与世界
——《一个勺子》的存在论视觉美学分析
吴 明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陈建斌的处女作《一个勺子》以鲜明的作者风格,挖掘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主义境遇。借鉴戈夫曼的“区域理论”和海德格尔的“此在世界”概念,探讨这部电影如何通过镜头语言表现目光的位置、方向、移动以及空间、面部的可见/不可见性,展现人物在不同世界中的生存现实。最后,以文化维度和伦理维度,拓宽此在的真实境遇,统携目光、区域、此在、世界的存在论美学。
目光;后台;此在;世界;良知
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几经波折终于上映。这个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现实题材故事,通过粗粝朴拙的影像风格,将人物置于荒诞的存在境遇,逼视真假是非、人心善恶的恒久命题。首次当导演的陈建斌在这部作品中已经显露出颇具个性化的镜头美学风格。本文将探讨这部电影如何通过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的“目光”来处理不同世界中此在的生存论命题。
一、三元区域及其可见/不可见性
电影开场是一个常见的街头群众舞台,但摄影机通过不寻常的视点切换,点明了人物所处的“后台”物理空间,从而奠定了全片的社会空间隐喻命题。影片的第一个镜头表现的是舞台上的表演,但摄影机却并未处在常见的舞台观众视点上,而是始终位于演员背后。台下观众正面朝向电影观众,同时不断有表演者的背影在前景处水平移动。此时,电影观众尚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是剧中人的主观视点,而要到第二个镜头时,电影才对此给予提示。第二个镜头中出现蹲在钢架棚里的拉条子和他背后隔在围栏外的傻子分食物,舞台表演的音乐成为环境背景音。这时,电影观众才领悟到,前一个镜头中所看到的景象是从拉条子和傻子所处的“舞台背后”的位置捕捉到的。这种街头大舞台的常见结构是:在开阔的空间中,以钢架和幕布搭起一面背景墙,前方延伸出舞台,后方则是隐于幕后的钢架围栏等支撑结构——背景墙自然地将原本无所谓前后的空间,划分出台前与幕后两个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对剧场舞台的“前台-后台”区域做过精彩的社会隐喻阐释。他将整个社会看作一个大舞台,人的不同社会身份就是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谓“前台区域”,就是指“作出表演的场所”,表演者通过不断努力表现出渴望被他人(观众)接受的、光鲜体面的形象;而“后台区域”则是与之相对的另一种空间,“在那里显现出被掩盖着的事实”,演员可以放松精神,摆脱角色,同时“能够确认没有一个观众会闯入”。[1]103-109所以,简单来说,“前台”既象征着社会形象的正面价值——繁华和睦;但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正面价值中所蕴含的虚假性——乔装打扮。相比之下,“后台”则代表了某种背阴面——虽朴拙无华、粗陋不堪,但因褪去伪装,所以更接近人的自然与本真状态。《一个勺子》的开场镜头即表现出这种鲜明的对峙与分离:“前台”是浓妆艳抹、敲锣打鼓的热闹世界,被彰显,被关注,被肯定;而拉条子则处在与之相对的“后台”中——被隐藏,被漠视,被否定。
但影片并没有让人物设置陷入肤浅的“贫/富”“正常/疯癫”的二元论结构,而是存在第三元的介入,这可以体现在“后台区域”的空间含混性上。拉条子与傻子虽然都处于与前台相对的一面,但他们之间被一道围栏阻隔,这暗示出此时的拉条子与傻子尚有区别。正如戈夫曼已经意识到“前/后台”二元结构的不足,以“余留区域”来打破僵局。他也将这个区域命名为“外界”,“即除两种已经确定的区域外的所有地方”。[1]128简言之,剧场舞台的“前/后台”虽然形成了某种对峙,但共同被剧场的建筑外墙包围在“内部”,与围墙之外的世界形成相互隔绝的“内/外”结构。戈夫曼将那些处于围墙之外的个体称为“局外人”。“局外人”不属于“前台”或“后台”的任何一方,而是与整个系统格格不入。他既不遵循两者之间必须保持的距离和差异,也无视两者之间达成的默契与约定。影片中的“傻子”就是“局外人”,他从一开始就处于整个舞台围栏的外部,也是片中唯一一个不扮演任何角色,只表露自身原始欲望的存在者。傻子的突然闯入使拉条子和大头哥的区别不再局限于贫富/城乡等社会阶级差异,而是进入到人的生存境遇层面。由此,拉条子的处境成为一种含混游移的“中间态”,他不再仅仅作为“前/后台”二元结构中稳定的一元,而是在与“前台”和“外界”同时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识自身,结构自身,定位自身。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戈夫曼虽然以“区域”概念来统携“前台-后台-外界”的三元结构,但这一概念并不限定在物理空间的层面。戈夫曼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中的“镜头”纳入到“舞台”的范畴,使“后台区域”被定义为“所有当时没被摄像机猎入镜头的地方”。[1]114也就是说,所有“不可见”的私密处所都是“后台”。这样一来,“前/后台”便不再依从空间位置来划分,而是依从“可见/不可见性”来进行判断。所以,当戈夫曼说“在我们社会的每一处,都可以发现划分前台区域与后台区域的界线”[1]118时,这个划分的工具就成了“目光”。
被遮蔽的后台空间只是拉条子“不可见”的一种形式,由逆光所造成的目光之不可及则是电影表现他隐身于世的另一种形式。影片开头傻子第一次在隧道尽头被撂倒之后,镜头又切入街头舞台的场景。但这次机位反转到舞台对面的街道,同时变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画面中不仅收纳了舞台表演和观看群众的背影,而且尽可能容纳了整个喧闹的街市。拉条子与傻子从画面右侧的前景处水平入镜,但由于两人始终处于逆光区,极不容易被观众的视线捕捉到。这就使得拉条子警告傻子“不要再跟”的对话造成了仿佛画外音的效果。观众会依照观影习惯,循光而视,反复在光线充足的远景中搜寻主人公,却只捕获画面上熙来攘往的人群,最终也无法使目光聚焦。这种声画结合方式迫使观众思考影像背后的隐喻意义:很多像拉条子和傻子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身处社会之中,却往往位于“逆光”区域而成为不可见的存在者。这种既存在又被遮蔽的状态,如同他们在镜头中虽有声音,却不可见一样。
可见/不可见性也是贯穿整部电影的社会结构隐喻。如果说大头哥代表冠冕堂皇的前台社会,那么拉条子拜托他为儿子减刑的事就是见不得光的“后台操作”。大头哥不愿意见拉条子,也是“前/后台”之间不可通约的系统规则所决定的——要维持“前台”的可见性,就必须保持“后台”的不可见性。影片中有一段极度荒诞的情节把这种“不可见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拉条子夫妇因为害怕骗子再度上门,又担心傻子万一回来家里没人接应。于是,他们决定把自己完全封锁在家中,以“消失”的方式生活于世。他们紧闭门窗,拉上窗帘,严禁开灯和烧火,想尽一切办法抹除能够体现自身存在的信号,以此保持决然的“后台属性”。在他们看来,只有隐藏其可见性才是确保安全的唯一方式。而一旦暴露于他人的目光之下,就会使他们成为僭越者和众矢之的,遭来横祸。于是,在他们隐遁生活的那几天当中,他们居住的房舍从外表看去平静无比,外人不知道里面还有两个人,而房子内部却正在上演着胶着的剧情。其荒诞性就在于,被外墙和铁门围拢的房舍形成了一个只有后台而无前台的“剧院”——只有演员而没有观众。随时可能到来但其实永远不会到来的“局外人”,成为他们严防死守的假想敌。他们发自内心的紧张和恐惧感,却因为轻信了骗子那句“我会把瘫妈带来”的恐吓,而沦为滑稽的自我表演。
但也正是这种完全的“不可见性”终于使金枝子陷入疯狂,从而打破了这段非人的生活。这源于她本该享有的“可见性”被无情剥夺了。对拉条子来说,“进城”办事是他的前台生活,而“家”则是他用以休息的后台。但金枝子作为一个农村家庭妇女,“家”对她来说不仅是后台,也具有“前台”的意义:她在此施展厨艺,接待客人,这是她的个人价值唯一能有所“展示”和被认可的地方。所以,当这个“可见”空间被完全遮蔽之后,她堕入了彻底的“不可见”,也丧失了作为存在者的全部意义。正是她对“不可见”的歇斯底里的抵抗,迫使拉条子开始逼问自身的存在形态——我是傻子吗?最后,他彻底走向了对“敞开”的执着追求——不畏惧大头哥,不要钱,只想把被遮蔽的事实真相揭示出来。当拉条子不断逼问大头哥的时候,就是彻底撕毁“前/后台”二元结构的时刻,也是他被视为“局外人”的时候。这种对摆脱“不可见性”的强烈欲求,使他最终踏入傻子们的“外界”。
影片首尾隐喻着拉条子整个生存境遇的改变。开场时,他所蹲踞的钢架棚虽然是被遮蔽的后台,但尚且处于舞台的内部空间;但到结尾时,他则身处一片空旷之地,完全袒露自己,与对面走来的表演队伍(前台表演者)绝然逆向而行。《一个勺子》之所以是一部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电影,就是因为它讲述的既不是“后台”如何跻身于“前台”的励志故事,也不是“后台”如何对抗“前台”的政治故事,而是“后台”如何想使被遮蔽的“善”成为“可见”,却最终只能使自己“出局”的荒诞故事。
二、此在的世界与目光的跟随
按照戈夫曼的区域理论,一个人被分为“前台的人”“后台的人”或“局外人”。它是以空间及其可见性为中心,针对观看者,将人的境遇进行切分。这一理论的局限在于,它把“舞台”的结构隐喻当成了“世界”本身,却忽视了“存在者处世”包含着阶级、种族、性别、职业等文化现实的含混性。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探讨。
首先,区域理论忽视了人在现实情境中存在着前台与后台互相介入的可能性。比如,人们常说的“职业病”现象,就是指某人将职业的前台表现习惯性地介入到本该属于后台的生活情境中。这就是把他们原本应该留在工作“前台”的表现,不可克制地带入到生活“后台”中来。同理,“露怯”这种现象则是“于连式”的小人物在面对上流社会时,本应尽力展现其全副武装的“前台”体面,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不愿示人的“后台”身份。所以,一个人的“前台”与“后台”虽然在不同场合下有所侧重,但两者几乎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被完全割裂。
其次,区域理论忽视了在同一情境中,不同存在者可能处于各自不同的“前/后台”境遇。社会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并非平等的存在,低阶层者的“前台”很可能是高阶层者的“后台”。例如,电影《一个勺子》中,“进城找大头哥”对于拉条子来说,是他需要打起精神去面对的“前台”世界;但对于大头哥来说,他的“前台”是作为4S店老板的社会身份,而每次面对拉条子,却是他作为非法中介者的“后台”状态。于是,两人相遇时总是拉条子毕恭毕敬,大头哥极不耐烦,就是因为两者是以各自不同的“前/后台”状态,在同一事件中相碰撞。
最后,区域理论还忽视了“前/后台”的同一性可能。同一性与前文所说的两者间的互相介入不同。“介入”是指“前台”与“后台”在一个人身上的同时并存。但“同一”则是指“前台”与“后台”在一个人身上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由于区域理论建立于“舞台”结构的隐喻之上,那么“观众”的存在——亦即“可见性”与否,则成为判定“前/后台”的根本标准。那么,“没有观众的表演”是否可能?可以说,没有不为了观众而进行的演出。即便是公演前的“彩排”,也有导演等幕后创作人员作为观众存在,同时在演员心中也始终存在着预设观众。所以说,对于真实的剧场演出来说,总是存在着“前/后台”的区分。但在生活中,“独处的表演”却十分常见。“独处的表演”则既是表演者在现实中的“后台”私密时刻,又是他/她在想象中万众瞩目的“前台”时刻。
综上可见,区域理论无法涵盖人在真实境遇中的文化性、多元性、互动性,而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人生的复杂性。对于阐释这种复杂性,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世界”概念更为贴切。
海德格尔将“在世界之中存在”作为“此在”的基本机制。[2]65“此在”与“世界”之间是彼此依托的关系,即“此在”是“在世界之中”的此在,而“世界”则是包含了“此在”的世界。进一步来说,海德格尔的“世界”不只是“此在”的存在空间,更是“此在”的存在方式。他在《论根据的本质》一书中说:“一、世界所指的与其说是存在者本身,还不如说是存在者之存在的一种如何。二、这种如何规定着存在者整体。它根本上乃是作为界限和尺度的任何一种一般如何的可能性。三、这一如何整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先行的。四、这一先行的如何整体本身相关于人之此在。”[3]所谓“如何”,就是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也就是存在者与世界取得内在关联的方式。为了强调这种关联,梅洛-庞蒂用“身体”和“世界之肉”的概念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他认为:“我的身体是可见的和可动的,它属于众事物之列,它是它们中的一个,它被纳入到世界的质地之中,它的内聚力是一个事物的内聚力。但是,既然它在看,它在自己运动,它就让事物环绕在它的周围,它们成了它本身的一个附件或者一种延伸,它们镶嵌在它的肉中,它们构成为它的完满规定的一部分,而世界是由相同于身体的材料构成的。”[4]“世界的肉身性”同时也是“身体的世界性”。因为“身体”的这种能够“让事物环绕在它周围”的“内聚力”,使它以自身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辐射力的“小世界”。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都已经触及“多重世界”的问题,但都碍于维护一个“整一世界”的观念,而止步于此。戈夫曼的“区域理论”则提示我们,世界是可以因存在者与观看者的不同关系而被划分为不同区域的。那么,既然“世界”是关于“存在之如何”的,“世界”也应随不同的存在方式而不同。因此,世界上不会只有一个“世界”,而应该是不同的“此在”有不同的“世界”。每一个“此在”都因包围着它的“存在之如何”而形成一个“小世界”,或曰“此在世界”。最终,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此在世界”(或“肉身世界”)彼此交织、重叠、混杂——而不仅仅是无数个单薄孤立的“存在者”——组成了世界之全部。
在电影《一个勺子》中,“此在之如何”是以人物之间的“跟随”主题来呈现的。影片的基本情节可以概括为:傻子跟着拉条子,拉条子跟着大头哥。不断地跟随与不断地被拒绝,构成了影片中最基本的人物关系,也为最后拉条子与傻子的身份认知合体提供了最直观的联结。“跟随”主题落实到影像上,则主要体现为目光的追随,以及在视线的运动过程中,不同“此在世界”间的碰撞与突破。
影片分别使用不同的拍摄方式来表现两组人物间的“跟随”主题。第一组,傻子跟随拉条子。先用纵深方向的跟拍镜头表现两者的分立,再到水平横移镜头暗示两者的逐渐合一。傻子最初跟随拉条子回家,是一段两人行走于街市上的跟拍长镜头。此段采用明显的手持摄影风格,画面大幅度摇晃。摄影机以傻子的视点,近距离紧跟拉条子,演员背后自肩膀以上的部分几乎以特写的景别出现在画面中。在这段跟拍镜头中,两人始终没有同框出镜,隐喻着在拉条子的自我认知中,此时的自己与傻子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但在后来几次跟随场景中,镜头则逐渐采用侧面平行的第三人称视点,表现拉条子与傻子一前一后在同框画面中水平移动,这暗示了两人后来的认知合体。
在这组“跟随”人物中,拉条子对傻子从排斥到接纳,直至最后的自我认同,实际上是拉条子的“此在世界”如何在与傻子的“此在世界”不断“烦神”的过程中,从“非本真状态”进入“本真状态”。拉条子整个生存境遇的转折,就是他在自证其“此在世界”的过程中,逐渐从“非本真状态”回到“本真状态”。
而迫使其摆脱“常人”状态的直接因素是他遭到另一个“此在世界”的不断拒绝。这就是电影中第二组“跟随”人物——大头哥与拉条子之间的基本关系。在表现这对人物时,影片通过多个“框形”物体区分和剪裁世界,同时强调视线的单向性,以此表现被他者世界拒绝。阿恩海姆在观察“文艺复兴时期祭坛周围的楣梁和壁柱所构成的正面结构”时,发现了“框架与窗口”之间的同一关系:“一幅画的框架被称之为一个窗口。只有透过这个窗口,观赏者才能看到另一个世界。”[5]所以,“框”既是约束视线的苑囿,又是导引视线的通道。大头哥家的门镜显示器就是一个画框,拉条子每次登门,画面上都是他映在显示器上扭曲变形的脸。他与大头嫂的每次对话都被后者粗暴地打断。
这种显示器在视线上是单向度的,即住户可以看见访客,但访客看不见住户,造成双方对话时极不对等的心理位差。这种门镜设备类似于福柯论及的“全景敞视监狱”的电子微缩版。福柯指出,这种建筑空间之所以能实现有效监管,是因为它“通过逆光效果”使视线呈单向性。“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6]所以,对“可见性”的掌控就形成了一种权力。显示器的单向显示功能起到的就是“逆光”效果。它使大头嫂占有“全知视野”,将一切尽收眼底,而且掌控随时切断对讲机的权力;拉条子则是“全盲视野”,他的视野中空洞无物,意识上茫然无知。一方盛气凌人,另一方低声下气,这种不对等的观看关系隐喻着双方社会身份的不对等,或曰“阶级差异”。在存在主义理论背景下,所谓的阶级差异就是“此在世界”之间的差异。每个“此在”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都存在质与量的区别,这种区别使得环绕在每个“此在”周围的“世界”都不同,由此导致每个“此在世界”对其他“此在世界”的影响力(权力)也不同。
当这些占有量不同的“此在世界”彼此相遇时,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欺压或拒斥。拉条子始终被拒之门外,象征着一方“此在世界”对另一方的严苛拒绝。同理可见,拉条子家的窗户也是一个类似于门镜显示器的单向视线框。影片中多次给到“窗户”的特写镜头,夫妻俩透过它监视傻子在院子里的动静。虽然玻璃是双向透明的,但因为傻子从来不会反过来监视他们,所以这里的目光仍是单向的。但与拉条子始终被大头哥拒之门外不同的是,拉条子却从一开始坚决拒绝让傻子进入自己家,到后来慢慢接受他的进入。这也寓示着他的“此在世界”最后会与傻子相容。
除了显示器和窗户,全片另一组意味深长的画框就是大头哥的汽车后视镜和车前挡风玻璃。导演有意识地在这两个画框中,通过视线的改变,完成了对拉条子身份认知的转换。拉条子总共五次上下这辆汽车,从要钱到还钱,再到最后讨说法,镜头进行了不同的处理。前三次他被大头哥以生硬的口吻撵下车,每次都紧跟一个后视镜视点的固定镜头。在后视镜中可以看到,拉条子焦虑、困惑、无助地站在路边,以不甘心的目光追随着旋即开走的汽车。在后视镜的画框中,拉条子的身体迅速缩小,仿佛被大头哥所代表的金钱权力世界无情抛弃。只有第四次下车时,没有后视镜的画框镜头,因为这次是拉条子主动提出下车。
最后一次则与第一次又形成某种对照:拉条子首尾两次都是在人身安全极度危险的状况下,突然出现在大头哥以挡风玻璃为画框的视野正前方。但两次的方向完全相反,第一次是从车下面钻出来,正向示人;最后一次是从车顶上倒挂下来,反向示人。傻子在开场时的第一次露脸也是躺倒在雪地里,反向示人。这都寓示着在大头哥的认知中,拉条子已从正常人变成傻子。而这最后一次上下车的全过程也充分呼应了“跟随”的主题:不同于前三次在后视镜框里被动地缩小,此时的拉条子顽固地维护自己在后视镜(大头哥视野)中的存在。他就像当初的傻子一样,锲而不舍地追车,爬车,停车,进车,再被推出车,撂倒在雪地,被殴打并被称作傻子,直至最终被强行扔下。大头哥对待拉条子的方式,也从一开始依靠语言——喋喋不休地解释和劝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语言而转为身体——暴力肉搏。大头哥的“此在世界”始终没变,但他对待拉条子的方式发生这种改变,即“此在之如何”改变了。这说明拉条子的“此在世界”从常人变为疯癫。
三、不纯粹的此在道德与面部的(不)可见性
赵汀阳曾提出,海德格尔以“此在”为核心的“不纯粹的现象学”恰恰比胡塞尔以“我思”为核心的“纯粹现象学”更接近事实本身。因为“此在直接有着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负荷——从而总能够把我思具体化到在世的境遇里去,本来我思在事实上总是不得不具体化,于是,我们所准备思考的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恰恰不可能是关于我思本身的,而只能是关于存在境况的,因此,纯粹的‘我思’在思考中被不纯的境况消解了”。[7]可以说,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了此在不是孤立存在于世,而是与他人形成“杂然共在”的关系。但海德格尔始终有一种想把本就不纯的此在进行“提纯”的哲学愿望,为此他提出了“常人”概念。所谓“常人”,就是所有此在杂然共处于世的日常生活状态,它对所有此在都实施着一种“真正的独裁”。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杂然共在本身为平均状态而烦忙。平均状态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这种为平均状态之烦又揭开了此在的一种本质性的倾向,我们称之为对一切存在可能性的平整”。[2]156海德格尔想用“常人”勾画出“大众生活”这一最具普遍性的生存论图景,就仿佛电影中俯视全景镜头下的芸芸众生无一例外地过着雷同生活。但正如前文所述,每一个此在都构成一个独特的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都有其内部系统的运作机制。所谓“常人”是通过对此在的“均质化”处理,搭建一套静态的共在模式,它无法应对此在的个体差异,也无法解释某些个体为何会突然脱离常人状态的小概率事件。
要突破此在的均质化假象,首先需要引入社会文化维度。既然此在是一种境遇化的存在,那么要对具体的此在生存进行阐述,就必须深入到它的真实境遇中去。而所谓境遇,就是指包含了历史、地域、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全部文化因素在内的有机社会成分。“海德格尔大抵是从一种超社会(学)的纯哲学本体论层次上来看这一问题的,因为他的所谓存在之本真即是无任何社会情景的天然个人存在,而一当他涉入世界和人类,烦忙和麻烦便预示了他之共在存在的必然沉沦和异化命运,也因之落入非本真存在状态之中。这种理论预制显然是非历史和非文化的。”[8]因此,对《一个勺子》的存在论分析必须把握住“这是发生在中国西北农村与小县城中的故事”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任何对这一事实的忽视与偏离,都容易使分析陷入过度阐释或僵化符号学的泥沼。例如,“羊”的意象在影片中很容易被视为《圣经》中的牺牲隐喻。拉条子从一开场便带着一只小羊羔,它不仅脱离羊群而被养在夫妻二人的卧室里,甚至被穿上衣服悉心照料。由于儿子被囚禁在监狱中,所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小羊羔就好像代替了儿子的地位。而最后,拉条子将小羊羔带到旷野高处去宰杀,导演以颇具仪式化的镜头风格,仿佛暗示着这是一场中国版的“亚伯拉罕献子祭”。
然而,如果将阐释停留在这种宗教激情的崇高时刻,恰恰错失了“杀羊”情节在这部电影中的真正戏剧高潮。因为,在凝重的宰杀仪式之后,镜头直接切入了三哥桌上炖得热气腾腾的羊肉。这是电影中极为成功的黑色幽默:两个农村男人喝着小酒,吃着羊肉,重复着毫无意义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价值信条。拉条子不是亚伯拉罕,而是西北农村的羊倌;他的羊羔没有献给神,而是送给了开杂货铺的三哥;羊羔牺牲的意义丝毫无关宗教信仰的考验,而只在于能炖出一锅鲜美的肉——中国人求人办事必须准备的一份登门礼。以最世俗的口腹之欲来代替血祭上帝的崇高美学,正是这种扎根文化现实的中国式解构,才使《一个勺子》在挖掘中国人存在的荒诞性同时,没有患上西方理论水土不服的症状。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这是一部具有存在主义“色彩”而非存在主义“图解”的电影。
除了确立文化语境,电影还引入伦理维度,展开拉条子的生存境遇。《一个勺子》通过“骗子、傻子、好人”三种道德身份来区分良知对于不同此在的意义。电影巧妙地通过对人物脸部的遮蔽与袒露,完成了对这三种道德形象的镜头表现,同时令人自然地联想到中国民间的话语表述。中国俗语中用“不要脸”来形容道德败坏。日常生活中,人们依靠面容来识别不同的人,所以脸就是最直观可见的身份。同时,在中国文化中,“脸面”也象征着自尊,是人们对自身道德底线的规约与坚守。所以,“脸”也是个人道德的可视化载体,失德也被斥为“丢脸”。在《一个勺子》中,主要人物面部的被暴露/被遮蔽与道德善恶之间形成了有意味的互文:骗子的脸被遮蔽,傻子的脸从被遮蔽到被敞开,拉条子的脸从被敞开到被遮蔽,“良知”的泯灭或显现也蕴藏其间。
根据国家新闻传播广电总局第100号文件的规定:“城市电影院线、电影院、农村电影放映院线和电影队暂停放映有吸毒、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作为主创人员参与制作的电影。”[9]《一个勺子》因饰演大头哥的演员王学兵涉嫌吸毒,被一再延迟上映。王学兵的大部分正面脸部镜头也不得不被剪掉。然而,正是这个出于规范行业作风的政策条款,竟无意中促成了影片中最精彩的镜头表现方式——大头哥作为矛盾冲突的关节人物,频繁出场却始终没有露脸。他大多数戏份是在开车时与拉条子对话,只露侧面与背面。首次出场是镜头跟拍他的脚,在家中通过妻子传话时只有声音。带人贩子来时,虽露脸,却一闪而过且隐于夜色。最后殴打拉条子时,也仍然只有背面全景或脸部以外的身体局部特写。一直被有意规避的面部使这个人物具有了存在意义上的抽象意味。他象征着“常人世界”中持存的、不可见的恶。与之相同,三拨人贩子的脸部也借助夜色、口罩、头盔等物体被有意识地遮蔽,良知的泯灭使他们不配获得一张清晰具体的脸。
傻子的脸从被遮蔽到被敞开,这也是他的命运由安转危的表征。他的脸之前一直被头发、帽子、污垢遮得严严实实,完全无法辨识,除了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是片中唯一多次被特写镜头强调的目光源,耿直雪亮,刺穿蓬乱肮脏的面庞,直抵人心。这道目光连同他每次大声喊出的“妈”,始终坚定果断、确切无疑。在是非摇摆、善恶混淆的世界中,这是唯一可以抓住的确定性。正是这点纯直的确定性,让拉条子和金枝子对他产生了一丝幻觉般的亲情。但等傻子洗完澡,袒露出清晰的面容,又去拍照对这一面容做进一步确定后,他便失去了那道独特的目光,也迅速沦为众人抢夺的财源。因为傻子的生存状态本来就是毫无防备、完全敞开的,对其脸部进行刻意强调,反而是将他强行拉入“常人世界”,破坏了他本真的存在方式。
镜头对拉条子和金枝子的脸则进行了有意识的“袒露”。当拉条子尚未陷入“傻子”的生存境遇时,他和妻子的脸经常以正面固定镜头被端正地呈现在同一画框内,这表明两人共同面对生活困境的态度,也代表他们作为“常人”的道德认知——既有善意又有私心,比如,担心傻子冻死,给他饭吃,但主要是怕他死在自家院里说不清,而且竟然想用他去换回监狱里的儿子。但随着拉条子一步步逼近“傻子”的生存状态,这种对脸部的正面镜头就慢慢消失了。大头哥将印有傻子照片的告示贴在拉条子的脸上——以傻子的脸代替拉条子的脸——预示着两者最后的身份合体。最后,金枝子坚决无情地将拉条子拒之门外,迫其睡在傻子曾经睡过的羊圈里。拉条子自我认知裂变的顶峰时刻,终于在一段浓郁的表现主义梦境中到来。他在梦中与自己逼视——有如伯格曼《野草莓》的经典开头。镜头在两张脸的特写之间快速对切,伴随着剧烈晃动的摄影和带有强烈紧张感的配乐,完美地表现出自我认知焦虑所引起的道德“自弑”与“自赎”。正是由此开始,夫妻再未同时入镜,也不再有两人脸部的正面镜头。直至最后,拉条子的脸重新被太阳帽和雪块遮蔽。
正是由于面部的可见/不可见性与人物的道德水准在电影中存在这种对照性,所以对不同人物脸部遮蔽与裸露的程度差异,则透露出此在道德的不纯粹性,即没有人是纯善或纯恶的。首先,影片没有把傻子视为某种道德至上的存在,对他进行神圣化或浪漫化处理,而是始终不脱离他生存境遇中的社会现实性。而对于傻子这个角色要做到道德隐喻和道德现实之间的平衡并不容易,因为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浓厚的“尚愚”传统。中国道家哲学中有“绝圣弃智”“大智若愚”等智愚辩证观,民间话语中也不乏“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人生信条。而欧洲自中世纪末期开始,“在闹剧和傻剧中,疯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不再是可笑的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10]人们在嘲笑和驱赶愚人的同时,也把他们视为外来世界中被净化过的纯洁灵魂。疯癫因作为“被禁忌的知识”,而具有令人迷恋的魅力。但《一个勺子》中的傻子既非智者也非圣者,他只是一个生理上有缺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者。
正如拉条子每次被人追问傻子到底是什么人时,都只能窘迫而又直白地回答“傻子就是傻子嘛”。这种无可解释,表明傻子作为存在者的无遮蔽性,他仿佛标定了某种无关善恶的“道德零度”。这种非善非恶的状态正是傻子作为道德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构成了他此在世界的道德虚无性。为此,电影有意识地凸显出这个人物身体经验的丰富和语言经验的缺失形成的巨大反差。片中围绕傻子的所有行为,诸如饥饿、被打、吃饭、睡觉、穿鞋、洗澡、理发等,都是对于身体的安顿或处置。拉条子无法通过一再的语言警告让他离开自己,只能通过殴打其身体并大喊“悄悄”(闭嘴),来强行切断他对自己的跟随。而殴打和勒令“悄悄”恰恰也是大头哥最后对待拉条子的方式,因为那时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从语言(理性)上与之进行沟通,只能诉诸身体暴力。可以说,“身体”正是在反语言中心论的意义上——“没有被理性化、同时也并不屈从于话语操纵”[11]——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批判力的现代性概念。作为这种身体性的存在,傻子只对周身世界做出应激性的反应,而不做任何价值判断,这就是他的道德虚无性。拉条子最后自认为傻子,也并非变成至善的圣人,而是被西绪福斯式的命运推入窘境的社会边缘人。
大头哥所代表的“骗子”也并非与拉条子所代表的“好人”形成恶与善的简单二元对立。“骗子”的根本特征不是恶,而是伪,即对真相的遮蔽。而真相恰恰是这部影片中最不可知的部分,它隐藏于无数错综复杂的叙述和表象背后,永远无法被证实。因此,是否能将大头哥等人称为“骗子”也变得十分可疑。影片并未将他们的脸全部遮蔽,例如大头哥和第一个来认领傻子的大旺,他们的脸都在夜色中有过短暂的裸露。大头哥曾苦口婆心地讲述自己如何托人帮拉条子的儿子减刑,这套叙述在减刑结果出来之前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拿钱不办事”的托词,但当减刑结果成为事实以后,反而使人无从判断它的真伪。同样,大旺认领傻子时的激动情绪,虽然很可能是人贩子逢场作戏的表演,但又无法排除找到亲人的可能性。就这样,真相被永远延宕了。
拉条子最后的精神崩溃也主要源于对被隐藏的真相“想不明白”:第一,三拨来认领傻子的人,到底哪个是真的?第二,傻子有什么用,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抢?事实上,片中已借不同人物之口,给出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大头哥告诉拉条子,三拨人都是假的,但他不相信,坚持认为第一个是真的。金枝子转述电视上贩卖人口的新闻说,这些傻子们要么被拉到黑煤窑里去做苦力,要么被杀掉贩卖其器官,要么被打残被迫上街乞讨。这几乎已经很接近傻子被接走后可能遭遇的残酷真相,同时也基本回答了为何一个傻子会成为众人抢夺的资源。但拉条子仍然不相信,以“电视看多了,看傻掉了”强行打断金枝子的猜测。
可见,作为“好人”的拉条子并非纯善、至善的代表,而是交杂着糊涂、懦弱、固执、见识短浅等欠缺性的品质。例如,他在已经意识到被骗的情况下,面对第三拨来者仍不知道要先核实其身份再做答复,这就不是善良,而是愚蠢了。他虽是村里公认的“好人”,但金枝子却用“人好净受欺负”,“人好没好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做不得好人”等一连串地道的中国俗语,质疑这种愚蠢的善。这并非对良知的曲解,反而揭示出良知的另一面——罪责。海德格尔在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此在的欠缺与虚无性视为一种原初的罪责,拉条子在智识上的欠缺就是他作为此在的原初罪责。正是由于他对真相审辨能力的缺失,使他实际上成为骗子们的帮凶,合力将傻子推入命运的深渊。相较于“好人”,片中另一个词“老实人”更适合用来形容拉条子的道德存在。因为他的善只是碍于其怯懦而不敢违犯道德规范的行为,而不是出于理性自觉的道德需要。愚蠢是他良知中的瑕疵,使他作为此在的不纯粹性得以彰显,也使这部电影中的人物没有沦为善恶对立的教条模式。
四、结语
影片结尾,拉条子存在境遇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也最终导致他对世界与自我认知的崩坏。从功利层面来说,拉条子之前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儿子减刑,五万元追回,甩掉傻子,就如中国俗语所说的“傻人有傻福”。但他对真相的探知却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任务,同时他也被村长视为伪装最深的心机精明之人。他再也无从分辨是非对错、善恶智愚。因为生活再也无法被理性和经验所把控,而完全被偶然性和不可知论所左右。
他作为此在的小世界再也无法将他维系在常人世界中,而只能从原本的后台区域越位到外界。于是,他主动戴上傻子的太阳帽,任人扔雪球欺负,彻底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在电影最后的纵深长镜头中,太阳帽形成破碎的有色画框:视野中是被撕裂的世界,代表常人的秧歌队视若无睹地从他身边逆向走过。眼前的世界逐渐被雪糊住,直至一片漆黑。加缪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忽然被剥夺了幻觉与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12]当拉条子的视线完全消失时,他在社会舞台上的自我意识也被彻底摧毁。
[1] [美]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 [德]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上)[M]. 上海:三联书店,1996:174-175.
[4]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眼与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7.
[5]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316.
[6]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25.[7] 赵汀阳. 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269-270.
[8] 万俊人. 现代西方伦理学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99.
[9] 星河.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拳封杀劣迹艺人[J]. 中国广播, 2014(12):87-87.
[10] [法]米歇尔·福柯. 疯癫与文明[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
[11] [美]简·盖洛普. 通过身体思考[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9.
[12] [法]阿尔贝·加缪.加缪文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626.
(责任编辑:李孝弟)
Sight and World: Analysis of Existential Visual Aesthetics inAFool
WU Ming
(SchoolofCommuni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Chen Jianbin’s debutAFoolexplores into the depth of the human existential circumstances in the real world with distinctive auteur styl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rving Goffman’s “region theory” and Martin Heidegger’s “Dasein-World”,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film expresses the position, direction and motion of sight and the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of space and faces through camera languag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existential reality of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worlds. Finally, the paper expands Dasein’s real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ight, regional space, Dasein and existential aesthetics are integrated from the dimension of culture and ethics.
sight; background; Dasein; world; conscience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06
2015-12-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87);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资助(16PJC027)
吴 明(1982- ),女,江苏无锡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J912
A
1007-6522(2016)06-005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