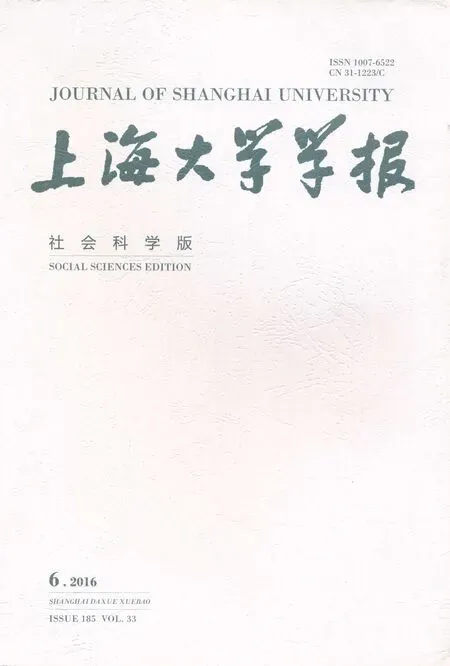再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
谭 君 强
(云南大学 文学院,昆明650091)
再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
谭 君 强
(云南大学 文学院,昆明650091)
诗歌叙事学作为跨文类的叙事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如何既考虑诗歌叙事学与叙事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又将其与后者加以区隔,关涉前者的研究对象,也关涉其研究方法。国外叙事学界的研究较为明确地强调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从西方传统的抒情文学、叙事文学、戏剧文学的文类区分中突出其跨学科性质。从构建诗歌叙事学的理论,形成这一学科分支,并开展有效的实践来看,诗歌叙事学应以抒情诗为主要对象,这样,有利于彰显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展开富于成效的研究;与此同时,在以抒情诗为主的前提下,也可从“诗歌”这一文类角度展开相关的叙事学研究,包括诗歌叙事学研究,探讨在不同文类中的不同表现。
抒情诗;文类;跨文类;诗歌叙事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为叙事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扩大再度开启了大门,叙事学又一次进入研究的繁荣时期。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方法的更新,使一些过去未曾为人们所注意甚或长期被排斥在叙事学研究范围之外的研究对象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对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或诗歌叙事学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自21世纪以来尤为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国内外陆续出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者的兴趣日益浓厚,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可以说,诗歌叙事学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拓展的路上正步步前行。
如何看待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如何界定诗歌叙事学,成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近日,笔者读到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李孝弟的论文《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诗歌叙事学建构的切入点》,对笔者发表在《思想战线》的《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一文中关于诗歌叙事学研究对象的问题提出商榷意见。李孝弟文对《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一文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认为其“观点新颖”,“在诗歌叙事学研究方面的正面性引导和积极性建议居多”。[1]140在此基础上,该文提出对笔者论文最大的不同意见是“在界定研究对象上存在很大分歧”,[1]140认为“将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抒情诗歌,会产生很多歧义与问题”。[1]141其核心意见是:“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所有诗歌,而非仅仅限于抒情诗歌。”[1]143
李孝弟文提出了一些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所提出的不同意见也促使笔者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对学术问题的相互切磋探讨,无疑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机。以下所呈现的便是笔者对李文的不同意见及其他相关理论问题所作的梳理的初步结果,以此求教于学界,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诗歌叙事学的主要对象:抒情诗歌
确实,就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笔者强调的是抒情诗歌,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看待。在笔者2013年以来有关诗歌叙事学研究的论文中,几乎全都涉及抒情诗歌,这从已发表论文的标题可见一斑。除前述《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一文外,其他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论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2014)、《论抒情诗的空间叙事》(2014)、《想象力与抒情诗的空间意象叙事》(2014)、《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2015)、《论抒情诗的叙事动力结构——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例》(2015)、《论抒情诗的叙述交流语境》(2016)、《从互文性看中国古典抒情诗中的“外故事”》(2016)以及即将发表的《叙事学视阈中抒情诗的抒情主体》。
从上述论文可以看出,除《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一文而外,其他所有论文的标题均不离抒情诗,明确地将论述的主要对象指向抒情诗歌。即便未标明“抒情诗”的《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一文,其论述的对象仍然指向抒情诗歌。换句话说,从笔者所进行的诗歌叙事学研究,以及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独特意义的诗歌叙事学理论以及所从事的研究实践来看,其主要的参照、关注、研究与论述对象都是抒情诗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抒情诗歌并以之作为主要对象的基础上,笔者在诗歌叙事学研究中并未“将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抒情诗歌”。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上,笔者秉持的是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封闭的、限制的态度。在以抒情诗为主的基础上,实际上也为其他诗歌保留了空间。笔者提出,除抒情诗歌以外的其他诗歌,如史诗、叙事诗等是否可以列入诗歌叙事学研究中,可视相关情况而定。这就并未对除抒情诗以外的其他诗歌在诗歌叙事学研究中关闭大门。笔者文中的一段话,这里再引述如下:“史诗、叙事诗等,由于其中十分明显地包含着叙事要素,构成为叙事文本,叙事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它们几乎完全适用,对其研究已经成为叙事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在诗歌叙事学研究中,是否将这些同样属于诗歌的史诗、叙事诗等归入诗歌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应该视研究的关注点而定,视其作为诗歌与其他叙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而定。由此看来,诗歌叙事学所要研究的诗歌主要属于抒情诗歌。”[2]120由此可见,诗歌叙事学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局限于抒情诗歌”,而是“主要属于抒情诗歌”。除抒情诗歌以外的史诗、叙事诗等,换言之,也就是叙事类诗歌,既可作叙事学研究(事实上,史诗、叙事诗之类的诗歌在已有的叙事学研究中,不难见到),必要的话,也可作诗歌叙事学研究。如果将形式上符合“诗歌”这一要求视为迪尔凯姆所说的“同一定义”的话,也就是说,将“诗歌”作为最大公约数的话,那么,所有诗歌确实都可归入诗歌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笔者何以要强调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抒情诗歌呢?诗歌叙事学属于跨文类研究,也就是在叙事学的视野下将历来不被视为研究对象的诗歌(这里主要指抒情诗歌)纳入研究的范围。强调诗歌叙事学的主要对象是抒情诗歌首先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知道,在叙事学研究中,抒情诗歌长期以来是被排除在外的。这一状况实际上在托多罗夫于《〈十日谈〉语法》中将对《十日谈》的探讨命名为“叙事学”(narratologie)研究并将叙事学定义为“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3]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叙事学研究很长时间与抒情诗歌无缘的命运。美国学者布赖恩·麦克黑尔也明确提到了这一状况:“当代叙事理论对诗歌几乎完全保持沉默。在许多经典的当代叙事理论论著中,在如你此刻正阅读的专业学术期刊(指《叙事》——引者注)中,在诸如‘国际叙事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上,诗歌都显而易见地几乎未被提及。即便是那些对叙事理论必不可少的诗歌,都被倾向于当作虚构散文处理了。”[4]*麦克黑尔这篇论文的标题直译应为《开始设想关于诗歌中的叙事》(“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Narrative in Poetry”),尚必武与汪筱玲翻译的该篇论文以《关于思考诗歌叙事学的设想》为标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和2010年《叙事》(中国版)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叙事学研究对待抒情诗歌的实际态度。
对于这一叙事学研究尤其是经典叙事学研究中的传统观念,笔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质疑。在笔者2008年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叙事学所研究的,是发生在叙事作品内部的交流,即叙事作品内在的交流。它所对应的,是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向叙述接受者进行讲述、交流的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有些作品中就不一定存在着叙事,即不存在内在的交流,比如抒情诗歌、论说文等,这样的作品就应该排除在叙事作品的范围以外。”[5]从文学分类来说,将抒情诗歌“排除在叙事作品的范围以外”,并无不妥。但在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抒情诗歌并非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状况,只有伴随叙事学研究的发展,尤其是经典叙事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才得以根本改变。在笔者2014年修订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第二版中,笔者删除了上述相关论述,明确地将抒情诗列入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并特别增加了有关诗歌叙事学研究的一节。
关于叙事与抒情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将两者加以区分,但同时也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相互融通。2009年,在笔者发表的《〈堂璜〉:作为叙述者干预的抒情插笔》一文,就充分注意到拜伦的长诗《堂璜》将叙事与抒情两者紧密融合在一起的情况,并明确指出:“将《堂璜》看作为抒情叙事长诗应该更为合理,将它作为充满浓厚抒情成分的叙事虚构作品来探讨也才更符合实际。”[6]*这一看法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在《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上《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一书中,提到了这篇论文,认为“谭君强……对拜伦叙事艺术的研究不可忽略”。该书指出:“谭君强的《〈唐璜〉:作为叙述者干预的抒情插笔》(《云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广泛采用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对《唐璜》中大量的‘抒情插笔’进行了分析,从而认为,《唐璜》既是一部‘诗体长篇小说’,但更是一首充满浓厚抒情成分的‘抒情叙事长诗’,其特点是以‘叙述者干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抒情插笔’”手法——这种手法使得《唐璜》“颠覆了人们所熟悉的诗歌传统,从而在形式上具有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见申丹、王邦维总主编,章燕、赵桂莲主编:《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上《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在《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一文中,这一看法也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要指出的是,无论在诗人的写作中,还是在读者或欣赏者对诗歌的欣赏与解读中,都不会将抒情与叙事完全割裂开来。”[2]121并以大量篇幅展开了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指出:“叙事诗中包含着抒情,或抒情诗中包含着叙事,在诗歌中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二者有时融为一体,难分难舍。”[2]121这种叙事与抒情或抒情与叙事相融汇的情况,在中外许多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在美国学者霍根《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一书中,作者以叙事虚构作品为例,说明了故事情节与情感的内在关系。霍根如是说道:“人类具有一种对情节的激情。从亲密的个人互动到非个人的社交聚会,故事在每个社会、每一时期和每一社会语境中被分享着。这一对情节的激情(passion for plots)与情节的激情(passion of plots),即其中故事所显示的作者和人物感情、由情节而来的激情的方式,以及故事唤起读者或听众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7]在这里,作者将情感(这是促成抒情诗歌形成的重要条件)与故事、情节关联在一起,实际上也表明了在作者的创作与作品的实践中抒情与叙事的密切相关性。这种情况,在叙事虚构作品中是如此,在抒情诗歌中也可发现类似的情况。
二、文类的“四分法”与“三分法”
诗歌叙事学既然是跨文类研究,那就必然与文类划分联系在一起。李孝弟文认为必须将所有诗歌都涵盖在诗歌叙事学研究的范围内,一个重要依据便是:“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教学中,文体四分法,即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已经成为惯常性的共识。”[1]141这一情况,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说明。
我们知道,在文学理论对文类的区分中,中外流行着所谓“四分法”与“三分法”。很明显,李文所指的四分法属于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区分。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中,自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以来,便出现了三分法,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三分法将文学区分为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中国的四分法实际上是自五四以来,借鉴西方的三分法,适当补充而成。这两种不同的划分,各有长短。一部近年由多位学者参与编写的《文学理论》一书认为:“‘四分法’的主要依据是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语言运用和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特征。”“‘三分法’着眼于情感体验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不同,其划分标准具有‘类’的概括性和逻辑性,但忽略了文学作品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特点,诗歌中的抒情诗与叙事诗就被分割开来。”[8]无疑,两类区分方式都有必要引起关注与思考。
“四分法”对文学作品外在的形态关注较多,具有一目了然的特点。外在的语言形态、结构方法,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比如,诗歌有其语言、节律、段位等方面的诸多特征,可以将诗歌与其他文类明确区分开来,并立即引起读者不同的阅读期待和反应。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其《结构主义诗学》中引述了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他的《辞格二集》中的一段论述:如果把一般平平常常的新闻报道体的文字按抒情诗的格式重新排版,四周留出赫然醒目的大片空白,文字虽一字不动,它们对读者产生的效果却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如一段新闻报道体的文字作如下安排:“昨天在七号公路上/一辆汽车以时速一百公里行驶撞上/一颗法国梧桐。/车内四人全部/丧生。”卡勒就此指出:“把上述报道文字写成诗体,读者思想上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期待,这一套程式将决定这段文字该如何阅读,从中应该引出什么样的解释。”[9]由此可见文类体裁所显现出的独特意味,它对于文学研究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然而,在确定诗歌叙事学的主要对象时,不仅要参照文学区分的四分法,也有必要注意三分法。三分法在西方流行超过两千年,自有其生命力和合理之处,值得我们关注。笔者在《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中,概要地回顾了中西文类区分形成的历史过程,同时指出:“在跨文类研究中,首先必须更多注意到不同文类的相异性,从而确定跨文类研究的可行性。”[10]应该说,如果要寻找不同文类的相异性,四分法在形式层面居多。然而,要深入其内在的层面进行分析与探讨,深入文学作品中探究其内涵,其情感来源与表达,叙述主体、抒情主体与文字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等,则参照具有“类”的特征的三分法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将诗歌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界定为抒情诗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考虑到三分法划分中合理一面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诗歌叙事学的理论构建,其作为叙事学一个分支的独特意义才可更为明确地得以彰显。
三、叙事学与诗歌叙事学
不同的理论视角,有其独特的理论内涵和所针对的对象。诗歌叙事学无疑是叙事学这一学科的一个分支,它与叙事学理论的异同何在,它与叙事学研究的对象异同何在?如果两者没有区别,就无需为增添一个新的分支而苦苦挣扎。这就需要摄取各自最为突出的特征进行考量,方可将两者在相互关联的基础上加以区隔。仅以是否属于诗歌为标准来界定诗歌叙事学,显然难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因为这里更多的是对形式层面的关注,而需要关注的主要是其内在的“异”之所在,也才可在这一“异”的基础上看到其相类似之处。普鲁伊在概述霍恩、麦克黑尔、杜布罗等人近年所作的有关诗歌叙事的研究时,强调了他们所从事的并非一般的诗歌研究,而是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他指出,他们的研究已经证明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是可行的,甚至是切实可取的;“抒情诗的‘叙事的/叙事学的阅读’开启了诗歌(the poem)及其不该被忽视或忽略的意义层面的大门”。[11]这里就充分注意到叙事学与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这两者研究的不同取向。
任何种类的文学作品,都是作者透过作品的中介,即叙述者、讲述者或抒情人呈现出来的。但是,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其表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因而,这一表现方式本身便具有重要意义。同为诗歌的抒情诗和史诗、叙事诗,就表现方式而言,是大不相同的,但史诗、叙事诗在表现方式上与小说这类叙事虚构作品则呈现出诸多相似之处。将它们分别置于叙事学和诗歌叙事学的不同理论视野中进行探讨,恰恰可以见出其差异。德国学者霍恩在其《跨文类叙事学的最新发展:诗歌与戏剧中的应用》一文中,特别注明他所说的“诗歌”(poetry)理解为狭义的抒情诗,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传统,“歌德所称的诗歌(poetry)的三个‘自然种类’(‘natural kinds’)是亚里士多德的抒情诗,史诗和戏剧三类”。[12]霍恩在文中指出:“诗歌(理解为狭义的抒情诗)和戏剧(舞台演出剧)都不仅在文本和剧本的总的组织中,尤其是在诗歌的精神心理过程和戏剧表演的对话和行动顺序中,运用叙事结构,而且也在这些过程和顺序的内部,在更低的层次上多种多样地运用叙事结构。”[13]由此,便可十分清楚地看出,小说类的叙事作品中所必然出现的叙事结构,同样也出现在诗歌(抒情诗)与戏剧中,但它们是如何表现的,它们尤其是抒情诗与小说类作品中的叙事结构表现又有何不同,则只有将叙事虚构作品与抒情诗加以区隔,而不是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加以区隔才看得出来。丹麦学者S. Kjekegaad在一篇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抒情诗的论文中,探讨了一类更为独特的抒情诗,即自传性抒情诗。他认为,这类抒情诗对抒情与叙事提出了三个问题:抒情性与叙事性如何相互关联,这一关联如何与诗人的声音相关;这些诗歌在自身处于虚构/非虚构中如何分野;独特的诗的手段如何对诗歌的意义作出贡献。[14]如果将自传性抒情诗与一般的诗歌相比来分析,同样很难看出其内在的独特意义。由此可见,诗歌叙事学以抒情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这类具有独特表现方式的作品作为理论透视的重点,恰恰可以达到探析其独特性的目的,也有助于这一理论分支的建构。
当然,一如笔者所谈到的,“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不同类别的艺术产品,在各显其相互之间差异的同时,在许多方面都拥有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相同、相似的特质。因而,从本质上说,一些涉及对特定文学艺术对象进行研究的理论,往往兼有对其他相关对象进行研究的可能性”。[2]122对诗歌叙事学与叙事学这种具有内在亲缘关系的理论,更应如此。对两者加以区分,目的在于对独特对象的研究与探讨,而不是将两者分隔开来。无论诗歌叙事学是以抒情诗为主还是包括所有诗歌,应该是以有利于对其内在的分析和探讨为原则,尤其是在叙事学的透视下进行分析和探讨为原则。
任何一种文学理论的目的,都在于对丰富的文学实践进行分析和阐释。抒情诗歌历来被视为最无可能进行叙事学研究的文类,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诗歌大国,尤其是抒情诗的大国,笔者致力于诗歌叙事学研究,并将研究对象主要定义为抒情诗歌,除了理论上的取向而外,也包含实践性的考量,也就是希望以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对中国丰富的抒情诗传统进行研究。在笔者有关诗歌叙事学研究的论文中,相当部分是直接以中国古典抒情诗为对象,就是这一考量的具体表现。如果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抒情诗包括中国古典抒情诗都完全可以进行此类研究,那就可为诗歌叙事学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如果连抒情诗都可以进行叙事学研究,原本就在叙事学范围之内的史诗、叙事诗以及其他的诗歌还有什么不能作诗歌叙事学研究的呢?前面曾经提及是否将同属诗歌的史诗、叙事诗等归入诗歌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应视研究的关注点而定,视其作为诗歌与其他叙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而定。在一些特定的关注下所进行的研究,完全可以将诸如叙事诗、史诗等列入诗歌叙事学的范围内。比如,董乃斌在多年的研究中,针对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突出抒情传统,而对叙事传统有所忽略的情况,特别提出,抒情传统“不是唯一的,与之并存同在而又互动互补、相扶相益的,还有一条同样悠久的叙事传统”。[15]他所提出的叙事传统,不只存在于中国小说类的叙事虚构作品中,同样也存在于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的抒情诗歌传统中。比如,他以历来被视为纯粹的抒情作品的古诗十九首为例,“将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相联系,将它们放到中国文学抒情与叙事两大传统发展与消长的平台上来论述”,[16]探讨了这一被视为纯粹抒情诗歌的作品,其中表现出抒情与叙事的相互融合。这样的探讨,自然很适宜在诗歌叙事学的理论视野下来进行,而如果就强调中国文学史中抒情与叙事并重这一理论视角的话,那么,在这一视野下的诗歌叙事学研究,自然应该包括与中国传统抒情诗歌相比数量虽不多,但却同样脍炙人口的叙事诗。
前面也提及笔者对诗歌叙事学的对象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既以抒情诗歌为主(这最能彰显诗歌叙事学突出的理论特色与实践成效),也不排斥其他诗歌,但需要一个加以统摄或加以区别的理论视点。我们不妨在主要展开以对原来不被认可进行叙事学研究的抒情诗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展开对其他诗歌,包括叙事诗等具有强叙事要素的诗歌的研究。而在这样的研究中,其关注点自然与前者有所不同。比如,可以更为关注诸如以诗歌形式展开的叙事与以非诗歌形式的叙事在叙事方式上有何差别,两者在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对读者的影响等方面有何不同,等等,这些都可在联系作品进行探讨的情况下展开,它对于叙事学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都不无贡献。实际上,理论与研究对象的交叉与交集,往往会使理论本身产生必要的适应性的变形与革新,展开这样一种内涵更为广阔的研究,必定对叙事学理论包括诗歌叙事学本身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可促进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也可使诗歌的实践研究获得新的突破,这就能够出现理论与实践双赢的局面。
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是被广为认可的跨文类叙事学研究。而“诗歌叙事学”这一表述或术语,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具有中文语境的用语。目前在国外的叙事学界,尤其是欧美叙事学界并未采用与中文的“诗歌叙事学”相对应的用语。*“诗歌叙事学”,其对应的英译应为“Poetry Narratology”,“Poetic Narratology”甚或“Poem Narratology”。但笔者在互联网上遍查了是否有英文“Poetry Narratology”之类的对应术语,却毫无结果。笔者最近在给德国汉堡大学英文系教授、《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一书作者彼得·霍恩(Peter Hühn)教授的电子邮件中,询问在西方是否有“Poetry Narratology”这一术语以指对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与研究,霍恩教授在2016年4月10日给笔者的邮件中明确地告知,就他所知,并无这样一个术语。笔者同时给美国叙事学界的重要代表、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系教授、《叙事》(Narrative)杂志主编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发邮件,询问是否有这样的相关术语(“Are there any terms like ‘poetry narratology,’ ‘poetic narratology’ or ‘poem narratology’ refer to the research on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lyric poetry?”费伦教授在2016年4月12日的邮件中同样给了否定的回答:“I don't think any single term has emerged to refer to this movement, but phrases like ‘theory of narrative in poetry’ and ‘theorizing narrative poetry’ work.”并认为或许可用诸如“诗歌叙事理论”这样的词语。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英语和欧美叙事学界不使用这一与中文语境完全对应的术语,我们就对使用这一术语表示怀疑。在笔者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诗歌叙事学”这一用语,但在使用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国际叙事学界的情况,了解其不使用这一与中文术语相对应的术语的内在原因。这样,我们才能对中文“诗歌叙事学”这一叙事学分支的基本含义及其主要研究对象有更为明确的认识,也使我们在构建具有中国意义的诗歌叙事学的理论中目标更为明确,在实践分析和研究中更有成效。
李孝弟文引起的笔者的思考,印证了学术研究需要相互切磋,不仅如此,“学术界相互之间的互动——商榷、研讨,甚至哪怕是崇拜和礼节意义上的喝彩,都是前行中孤独者的温暖和动力”。[17]不仅是就诗歌叙事学的这一问题,还是其他的学术问题,都期待能够有进一步的互动。
[1] 李孝弟.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诗歌叙事学建构的切入点[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1):138-145.
[2] 谭君强.论抒情诗的叙事学研究:诗歌叙事学[J].思想战线,2013(4):119-124.
[3] T Todorov.Grammaire du “Décaméron.” [M]. The Hague: Mouton, 1969:10.
[4] B McHale.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Narrative in Poetry [J]. Narrative, 2009(1): 11-27.
[5] 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0.
[6] 谭君强.《堂璜》:作为叙事学干预的抒情插笔[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8-75.
[7] Hogan. Affective Narratology: The Emotional Structure of Stories[M]. Lincolm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11:1.
[8] 本书编写组.文学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186.
[9] 乔纳森·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39-240.
[10] 谭君强.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J].思想战线,2015(5):113-118.
[11] H Plooy. Narratology and the Study of Lyric Poetry[J]. Literator, 2010 (3): 1-15.
[12] D Herman, M Jahn, M Rya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315.
[13] P Hühn. Recent Development in Transgeneric Narratology: Applications to Poetry and Drama[J]. Germanisch-Ronatsschrift, 2013(1): 31-46.
[14] S Kjekegaad. In the Waiting Room: Narrative in the Autobiographical Lyric Poem, Or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Lyric Poetry with Narratology [J]. Narrative, 2014(2): 185-202.
[15] 董乃斌.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J].社会科学,2010(3):169-177.
[16] 董乃斌.古诗十九首与中国文学的抒叙传统[J].北京大学学报,2014(5):53-60.
[17] 王瑛.中国叙事学建构的问题与方法[J].江西社会科学,2016(2):221-226.
(责任编辑:李孝弟)
Revisiting the Narratological Study of Lyrics: Poetry Narratology
TAN Jun-qia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
Poetry narratology as a cross-genre narratological study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cademia. Considering the inherent relevance of poetry narratology to narratology while discerning the former from the later, we should attend to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poetry narratology. Overseas narratological research has a distinct focus on the narratological study of lyrics and protruding its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in distinguishing the literary genres such as lyric literature, narrative literature and drama. Judging from the process of its theory construction, its formation as a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effective practice, poetry narratology should take lyrics as the major objects, which is thus conducive to manifesting its unique theoretic dimension and conducting fruitful research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 Meanwhile, under the premise of lyrics as the focal objects, relevant narratological study can be conducted from the angel of “poetry” genres including the study of poetry narratology, exploring its distinct features in different literal genres.
lyric poetry; genre; cross-genre; poetry narratology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10
2016-03-10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XZW004);云南大学研究生优质课程建设项目(2015)
谭君强(1945- ),男,湖南双峰人。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叙事学、比较文学研究。
I02
A
1007-6522(2016)06-0098-09
——探析文类与社会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