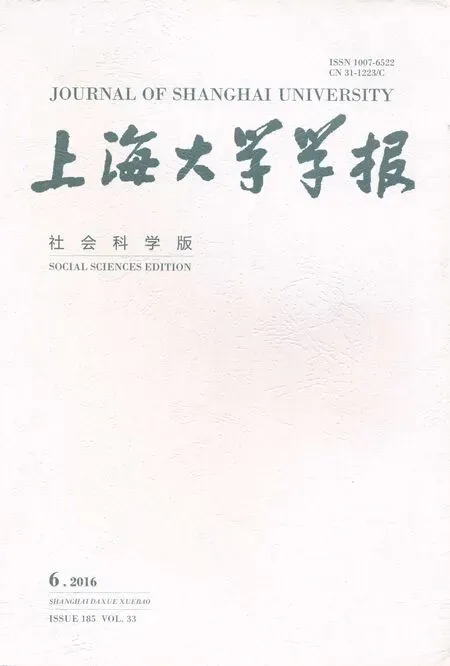仪式与文本: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程 苏 东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仪式与文本:周代官学之“诗礼乐”教与“书教”考异
程 苏 东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诗、书、礼、乐是西周王官教育中最核心的课程体系,也是最早得到王权认可的经典体系。但从《论语》、《礼记》、《国语》等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发现,至晚到春秋后期乃至战国前期,《书》学仍游离于部分贵族教育课程体系之外。这说明,与“诗礼乐”为辟雍、泮宫两级学校普遍教授的政治、社交仪式不同,《书》是天子辟雍中课试贵族子弟的书面“文本”,而在诸侯泮宫中,各国故志、令、世、训典等文献则取代《书》,承担了国家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对于这一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其对早期《书》学功能、传播之影响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西周王官之学的课程设置理念。
仪式;文本;王官学;诗礼乐;《尚书》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礼记·王制》所载乐正掌教贵族子弟的“四术”之一,[1]1342《书》至晚在春秋中期已经与诗、礼、乐并列,成为广受认可的国家经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论郤縠之才云:“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2]327将四学并举,分别以“德”为“礼、乐”之本,以“义”为“诗、书”之本,又以“利”统摄“德义”,从而将“诗、书、礼、乐”四者的核心功能定位为“利”。这种对于“四学”功利性作用的高度看重,虽然与后来的孔孟之道存在极大差异,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赵衰看来,诗、书、礼、乐无疑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经典体系,只有兼备这四种知识者,才是可堪大任的公卿之才。类似的论述还频见于先秦诸子文献中,此不具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战国史料中,有两组文献在论及西周、春秋的经典教育体系时,似乎总是避开《书》而仅言“诗、礼、乐”。一组出自《论语》,代表了孔子对于经典教育的看法,较早受到学者的关注: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529
在关于经典教育先后次序的论述中,孔子仅举诗、礼、乐而未及《书》;在《论语》另外几处关于经典教育的记述中,亦从不言《书》:
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3]1168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1212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3]1213
《论语》中仅见的《诗》、《书》并举之例,出于其弟子的描述: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3]475
显然,《论语》中孔子罕言《书》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蒋善国先生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作出解释:“在《诗》、《书》、《礼》、《乐》中,《诗》、《礼》是主要的,特别是《礼》是个中心环节。《书》本是文献档案,到了战国初年墨子的时候才被重视起来。”[4]且不论其关于《书》与墨学之关系的论述是否可信,就这一问题的解释而言,蒋氏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周人的早期贵族教育与政治实践中,“礼教”居于核心地位,诗、乐都因为附从于“礼”而获得经典地位,这一点,马银琴在论及早期《诗》文本的编辑原则时也提及。*马银琴在《两周诗史》中指出,康王时期《诗》文本的初次编辑,已经“确定了诗文本以仪式乐歌为内容的编写原则。”换言之,在早期《诗》文本的编辑体例中,施用于“礼”(仪式)、“乐”(乐歌)是一首诗歌得以进入《诗》文本的关键要素。参见《两周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而《书》由于不在具有仪节性的“礼教”范围之内,因此相对边缘化,至战国时期才有所转变。就笔者所见,这似乎是目前对于孔子罕言《书》教问题最为中肯的解释。
另一组材料出于《礼记》,目前似乎还未受到学者的关注。先看《礼记·内则》: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衣不帛襦袴,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1]1471*“学书记”,当作“学书计”。(可参卷后《校勘记》,第1472页下栏。)
这则材料详细勾画了一个贵族士人由接受教育到有室、出仕、致事的整个过程,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儒家士人的人生理想。*类似记载又见于《礼记·曲礼上》:“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大夫七十而致事。”可知《内则》篇之说不为无据。(可参《礼记正义》卷1《曲礼上》,《十三经注疏》,第1232页上、中栏。)而笔者关注的重点,乃是篇中从“六年”至弱冠的整个教育过程。关于此篇的成书时间,王锷将篇中部分段落与《仪礼·公食大夫礼》、《礼记·曲礼》、《礼记·少仪》等相关文字对比,认为时代比较接近,又将其与《周礼·天官·食医》、《庖人》、《内饔》等典籍对比,认为后者皆曾参考《内则》,故将此篇的产生时间定于战国中期,兹从其说。[5]198从这一段描述看来,其所学包括数、方名、数日、书、计、幼仪、乐、诗、舞、射、御、礼等,完全涵盖了《周官》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套精密、完备的教育体系中,包括了“诵诗”一科,这又将《周官》“六艺”与《礼记·王制》所载乐正氏掌教的“诗、书、礼、乐”“四术”勾连起来。《内则》篇中先言子弟十岁时“礼帅初,朝夕学幼仪”,复言其二十岁后“始学礼”,而对于乐舞的学习,也从十三岁贯穿至弱冠成年以后,可见,《内则》篇所言“礼”、“乐”,并不仅仅指《周官》所载用以“教万民”的六艺,[1]707同时也应包括层次较高、贵族士子习于大学的礼、乐。换言之,如果周人的教育确实包括类似《周官》“六艺”的初级教育(小学)和比较高级的乐正氏“四术”(大学)两个层次的话,《内则》篇所言的礼、乐,显然正是跨越了这两个层次:幼年时所学“幼仪”属于“小学”,而弱冠后“始学礼”,则属于“大学”。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既然《内则》篇代表了春秋、战国士人所了解的宗周贵族从初级教育到高级教育的全部过程,则在这一过程何以独不言及《书》教呢?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礼记·学记》篇中: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1]1522
该篇据王锷考证,著于战国前期[5]64。此段论述“艺”、“学”之关系,以前者为技术性、实践性的俗务,不可径同于学,与《论语》中“游于艺”、“吾不试,故艺”之“艺”所指相类。[3]443,583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言“大学”之教,而其具体论述的“不能安弦”,明指学乐,“不能安《诗》”、“不能安礼”,明指学诗、礼,三者毕而总结云“不兴其艺,不能乐学”。作者备述大学之教,却还是不及《书》教。
此外,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当孔子论及礼乐之重要性时曾言: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1]1614
诚如前引蒋善国先生之所言,这里明确以“礼”为核心,而以诗、乐为明礼之要津,只有兼习诗、乐,才能真正知礼,礼、诗、乐三者构成“一体两翼”的有机关系,而“《书》教”又不与其列。
再有,在《礼记·孔子闲居》中,子夏论“五至”: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1]1616
由志而为诗,诗兴而成礼,礼以乐为至,乐至于哀而止,志、哀为主体之内在感受,而诗、礼、乐则是三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凡此诸例,皆以诗、礼、乐为一整体而不及《书》。
总之,从上举两组文献看来,至少在春秋、战国士人对西周、春秋经典教育体系的叙述中,与“诗礼乐”三者的有机关系相比,“《书》”常常处于一种游离、模糊的地位。蒋善国先生已经注意到《论语》中存在这一现象,并指出《书》与“诗、礼、乐”之间存在功能性的差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但惜乎其未能联系《礼记》中呈现出的同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对先秦文献中呈现出的“《书》”教与“诗、礼、乐”教在官学制度层面可能存在的差异缺乏关注。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将踵武蒋先生之前式,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辟雍与泮宫的科目异同
我们不妨将先秦文献中论及《书》学的一些资料先作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分析的是《书》教在西周、春秋教育中的地位,因此,凡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学并举的战国材料,都不纳入这里的考查范围,而这样一来,所可据信的材料也就仅剩以下几则:
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王制》)[1]1332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礼记·文王世子》)[1]1404
首先需要明确,这两段材料明确指出其所言系天子之大学,也就是“辟雍”的教育制度,而我们知道,辟雍只是“大学”的最高层次,并不等同于大学。引文中《王制》篇明确指出:“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廱,诸侯曰頖宫。”《大雅·灵台》云:“於论鼓钟,於乐辟廱,鼍鼓逢逢,矇瞍奏公。”[1]525《大雅·文王有声》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1]527皆颂美周王之大学,而《鲁颂·泮水》则云:“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1]611足证辟雍、泮宫之别制。在西周封建制度下,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各级诸侯国,这就意味着除最高学府辟雍以外,还存在数量可观的次级官学机构:泮宫。《王制》篇所载由乐正氏所掌的“四术”、“四教”,以及《文王世子》篇由大乐正、小乐正、大胥、籥师、籥师丞、胥、大师、执礼者、典《书》者共同完成的王官教育,只能代表辟雍的教学体系,其规模恐非一般诸侯国可比拟。因此,我们不能径以《王制》、《文王世子》所载辟雍之教育规格来推演所有大学的实际教学设计,而这一点正是此前多数学者所忽视的。
既然《王制》所载“四术”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官学制度,再回顾前文所引孔子论学、《礼记·内则》论贵族子弟教育、《礼记·学记》论“大学之教”等均仅言诗、礼、乐而不及《书》的现象,我们自然会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我们将包括辟雍和诸侯泮宫在内的官学都视作高级教育机构的话,那么,《书》是否可以视作西周、春秋高级教育体系中的基本科目呢?进一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在西周以至春秋时期,《书》会否只是辟雍教育的基本科目,而非泮宫中常设的科目呢?
笔者认为这一假设是可以成立的。原因有二:
首先,从史料记载来看,《国语·楚语》的一条材料颇足证明,在诸侯国层面的官学教育中,诗、礼、乐乃常设科目,《书》则不与其列:
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6]485
根据《楚语》的上下文可知,本段申叔时所讨论的乃是楚王大子葴的教育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点,这条材料曾被有的学者用以论证楚国以《春秋》设教。事实上,王应麟已经指出:“《春秋》,所谓楚之《梼杌》也”,[7]485这里的《春秋》虽亦有劝善抑恶之义,然而其并非以鲁国史为基础、经过孔子编修的《春秋》则明矣。在这条材料里,申叔时列举了世子所应当接受的各种课程,包括《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凡九种,其中《诗》、礼、乐三科赫然在列,至于《书》则独阙。《楚语》此段所言乃是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期的事情,楚国虽当时已逾制称王,且其偏于南方,在礼乐、制度等很多方面与中原诸侯国均有所不同,但这些差异大多源于楚地旧俗民风的影响,至于大学教育,则非楚地所固有,因此,楚人建立大学,想必仍当以周制为基础。《诗》、《书》、礼、乐,无论是从思想倾向,还是从内容叙述上来讲,都是基本一致的,特别是《诗》与《书》,其所以并称,就在于两者所记述的不少事件可以互证,其彰显先王功德、扬善抑恶的教化功能亦颇为相类。如果周制大学教育与《王制》所载辟雍制度一样,都是“崇四术,立四教”的话,那么申叔时既然保留了周制王官教育中的诗、礼、乐,则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剔去《书》学一科,使王教“四术”不为楚世子所知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诸侯泮宫的教育体系中,常设科目只有诗、礼、乐三种,申叔时为楚世子量体裁衣,在保留这三种传统科目的基础上,为楚世子选择了《春秋》、《世》、《语》、《令》、《故志》、《训典》等楚国历史文献,使之博学而广闻。
其次,《书》与诗、礼、乐三科不同,其特殊的物质载体也决定了它难以成为诸侯泮宫普遍传习的科目。我们知道,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典籍的物质载体及其复制方式始终是影响文献传播之广度与速度的重要因素。我们只要看造纸术改进之后的唐代,《五经定本》犹难传于四方,而印刷术已经非常发达的南宋,各地书院仍颇难配齐一套完整的“九经”,就可以知道书籍载体的物质限制对于学术传播的影响,在早期社会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难以克服的问题。而在西周、春秋时期,主要的书写载体是简牍,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韩宣子至鲁方见《易象》,可知竹书的流传,在春秋时期仍非常有限,在这一背景下,散布于各地的泮宫要想均有一套著于竹简的“统编教材”,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大学教育仍主要以口头传授的方式展开,而其设计的基本科目,自然也必须是适应这种教学方式,甚至是依托于这种教学方式的。以此为标准来看乐正氏所掌“四术”,我们就会发现,礼、乐的传授主要依托于言传身教,此不待言。至于诗,《周礼》载“瞽蒙”掌“讽诵诗”,[1]797《灵台》言“鼍鼓逢逢,矇瞍奏公”,皆以盲者习诗、乐,足证其传习亦可脱离书本。总之,诗、礼、乐三者都不必借助于书本而流传,其传播自然也就比较便利。《书》则不同,笔者以为,《书》的流传必须依托于书本,此有三点为证:
其一,口传之文多为韵文,书传之文则多散文,这是先秦文学的基本常识。就《书》而言,其主体部分都是无韵之散文,显然不利于记诵,亦不便于以口诵方式流传。
其二,看《文王世子》篇对于干、戈、羽、籥、诗、《书》、礼、乐之不同教学地点的记载。“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礼在瞽宗,《书》在上庠”。同样一批学生为何要选择东序、瞽宗、上庠三个不同的教学地点呢?笔者以为,这正是受到了教学内容的限制:干、戈、羽、籥属于舞,其所用的器械较大,因此,习舞的场所应当比较开阔、空旷,这就所谓的“东序”。至于为何诗、礼、乐三科传习皆在瞽宗,唯习《书》需别在上庠呢?笔者以为,这正体现了《书》与诗、礼、乐在传习方式上的差异:瞽宗是一般的教室,设有坐席和琴,诗、礼、乐皆靠口传身授,因此学生随大师、执礼者习之即可。至于学《书》则不同,必须书本,而书本仅存于上庠,故此学《书》必须别至上庠,由“典《书》者”据《书》授之。《书》与诗、礼、乐在传习地点上的差异,正反映了其传习方式的特殊性。《淮南子·泰族训》论及“不学之与学”的重要差异,认为“以弋猎博奕之日诵《诗》读《书》,闻识必博矣。”[8]485这里称“诵”《诗》、“读”《书》,也明确指出《诗》可径诵而《书》则必须据本而“读”。
其三,也是最为确凿的例证,即《诗》、《书》在共经秦火后迥然不同的命运。始皇禁书,最为彻底的就是禁止私藏《诗》、《书》,此秦始皇三十四年诏令之所明也。[9]255然而经历秦火之后,《诗》之三百篇几乎一字不缺,至于《书》则散乱流离,何以两者差异如此之大呢?班固对此曾有过解释:“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0]1708此说符合《诗》的传授方式,确乎可信。至于《书》则不同,据《史记》载: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9]3124
在战国时期常为士人所称引、与《诗》并举的《书》在经历秦火之后竟天下无能治之者,对比《诗》学在齐、鲁、燕、赵乃至楚国各地都各有流传,《书》学的凋零可谓命悬一线。而我们再看这仅存的伏氏《书》学是如何得以流传的,就会对其凋零至此的原因有所理解了: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9]3124
在这段材料中可以发现,影响《书》学之流传与否的关键因素正是物质性的“书”之存佚:焚书之后,伏生有志于学,而其治《书》之第一举措,即在“求其书”,当发现早期所藏壁书仅存二十九篇之后,伏生便以这二十九篇用于传授。在整个《书》学复兴的过程中,“书本”的存亡显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在伏生传授《书》的过程中,书本同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鼌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几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9]2746
从“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可见,晁错从伏生学习《尚书》,主要依托的仍是书本,而伏生口授的义理竟显得或有或无了。总之,从秦火之后《尚书》的传习看来,《书》学的流传首先依托于其书本的流传,而在造纸术尚未出现,书籍传抄、携带、流传极为不便的西周、春秋时代,这类典籍的流传必然是十分缓慢和有限的。因此,考虑到《书》在传习方法上的特殊性,它恐怕难以被确立为天下大学的共修科目。
综合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周代大学包括辟雍和泮宫两个层面,这两类学校虽然同属“大学”,然而在具体设科上则有所不同,辟雍的常设科目包括诗、《书》、礼、乐“四术”,泮宫的常设科目则是诗、礼、乐。受制于《书》“书于竹帛”的特殊传播机制,难以在泮宫中普遍传习,因此,“书教”在早期王官教育文献中常常处于“失语”的地位。
三、《书》教与“诗礼乐”教的功能差异
既然诗、礼、乐已经构成泮宫教育的核心科目,为何在辟雍中还要另外增加一门《书》学呢?换言之,除了辟雍拥有泮宫所不具备的典藏《书》简牍的便利性以外,其使世子、王子、造士等习《书》,是否另有某种特别的用意呢?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仍可参照上文所举《国语·楚语》的材料进行理解。申叔时为楚世子设立的教育体系,在诗、礼、乐三科以外,虽然多达六种,但这六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属于历史文献:《春秋》,上文已言,“楚之《梼杌》也”;《世》,韦昭注云:“先王之世系也”;《令》,韦注:“先王之官法、时令也”;《语》,韦注:“治国之善语”,《尚书·盘庚》尝引“迟任”之言,《左传》中诸侯、行人屡见征引古语,恐怕都属于这类文献,《论语》、《春秋事语》等,也应当是这种“语”类文献的流衍;“故志”,韦注:“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左传》中曾多次征引“志”、“前志”“周志”“军志”,可见这类文献在春秋时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和较高的权威性;“训典”,韦注:“五帝之书”[6]485,《尚书》中有《高宗之训》、《尧典》,《逸周书》中有《度训》、《命训》、《常训》、《时训》、《程典》、《宝典》、《本典》等,皆记述先公先王之故制。总而言之,这些都是记载先王世系、事迹、语录、法令的典籍,而使世子学习这些文献的用意,则在于使之“知废兴者而戒惧焉”。[11]3124关于春秋时期诸侯国用历史文献教育世子,还有一例,见于《国语·晋语七》:
悼公与司马侯升台而望,曰:“乐夫!”对曰:“临下之乐则乐矣,德义之乐则未也。”公曰:“何谓德义?”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大子彪。[6]415
此事发生于晋悼公十二年(前561),早于孔子出生,其所言《春秋》,自非后世所称之鲁《春秋》,而是晋国国史。参照楚、晋两国在诸侯世子教育上的课程设置,回过来再看《书》,我们就会发现,在乐正氏所掌“四术”中,《书》教与诗、礼、乐三教存在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差异:即诗、礼、乐与西周礼乐制度与宫廷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仪式性,而《书》则不具有这种仪式性的功能。
关于诗、礼、乐在周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左传》中的事例可谓俯拾皆是,不必赘述,这里仅举《礼记·仲尼燕居》中所记一例:
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籥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1]1614
两君相见礼中,诗、乐均得到施用,以致孔子认为“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诗、礼、乐丰富的仪式表现力使其获得了充分的沟通功能。
因此,在西周、春秋时代,大学以诗、礼、乐设教,乃是因为这些都是参与贵族社交与政治活动所必需的素养,甚至可以称是一种基本技能,因此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大夫言则赋诗,行则循礼,礼乐不离其身。孔子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900显然,在孔子看来,学《诗》的目的,首先在于能够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熟练地运用它。总之,诗、礼、乐三位一体而与现实社会生活具有密切的关联。
至于《书》则不同,其乃历史故籍之选编,本身并不具有仪式性的实践功能,与诗、礼、乐相比,其施用之场合自有所不同。周代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辨论官材”,官之爵之,对于世子而言,更是为了培养他们将来的执政能力,因此,仅仅掌握一套礼乐仪式显然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了解国家历史、先王得失,而这一切,也就需要一门专讲国家历史的科目,在周天子的辟雍,其所据的教材,当然是记录三代之史的《书》,而在各个诸侯国,学官则可以按照各国自身的藏书情况,选择各自的历史故籍作为教材。*郭永吉先生通过对自汉至隋皇帝、皇太子所习经书的统计发现:“汉、魏时期天子或储君所习经书,除《论》、《孝》外,《尚书》也是必读经典之一。汉昭帝年十三,《论》、《孝》、《书》三经并习;元帝从欧阳地余、孔霸、周堪等人习《尚书》;成帝六岁前,《论》、《书》并习;明帝年十六立为皇太子,即命之习《尚书》;章帝四岁立为皇太子,始治《尚书》,年十岁,又命张酺入授;和帝也是四岁被立为皇太子,初治《尚书》,十岁即位,桓郁复入侍讲;顺帝六岁为皇太子,即受业《尚书》;曹魏齐王芳十三岁时,讲《尚书》毕。而东汉安帝、桓帝、灵帝、曹魏高贵乡公分别于十三、十五、十二、十四岁,由外藩入继大统,均是一即位后,立即派学者入授《尚书》。所以会如此,或许是因为《尚书》所载悉属政治文献,而且大多数都是圣君贤臣的言论,堪当帝王学之名,可提供储君或初嗣大位者将来治国的典范。”可见,统一帝国的君主习《尚书》以知国家政事,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可参《自汉至隋皇帝与皇太子经学教育礼制蠡测》,郭永吉著,台湾清华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这样一来,与诗、礼、乐三科在教学内容上的全国统一性不同,关于历史知识的传授在各国也就显出丰富的差异性,在晋国则是晋国的《春秋》,在楚国则是《春秋》等一系列故籍。《礼记·内则》中称贵族应“博学不教”、“博学无方”,这里笼统所言的“博学”,主要指的大概就是这一类历史文献,而从《国语·楚语》所载楚国大学的课程设置来看,这些历史文献既然包括了训、典,则其有一部分恐怕正是与《书》相重合的。换言之,“《书》”之“名”虽未与诗、礼、乐同列为泮宫之学的基本科目,然其“实”早已在泮宫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国语》所载楚国泮宫的《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晋国泮宫的《春秋》,就其性质与功能而言,正与辟雍中的“书教”相同。这种对于历史文献的高度重视,成为周人政教文化中的重要传统。随着春秋末期礼乐制度的崩解,“诗”逐渐摆脱了依附于“礼乐”的从属性地位,而与“书”组成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涵与义理指向的经典集合,传统的“诗礼乐——书”二分式的经典结构,也逐渐演变为“诗书——礼乐”的二分式结构,并造成战国时期儒门内部关于经典结构的不同看法。由于这一问题所涉颇多,我们将另行撰文讨论,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7:327.
[3]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蒋善国.尚书综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11.
[5] 王锷.《礼记》成书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董增龄.国语正义[M].清光绪章氏训堂刻本.3.
[8]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22.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 王树民.曙庵文史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责任编辑:梁临川)
Rites and Tex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eaching of Poetry,Rites and Music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Official Education of Zhou Dynasty
CHENG Su-do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Poetry, history, rites and music were the most fundamental part of the imperial and official curriculum system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a classic system that was earliest acknowledged by royal administration.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such documents asTheAnalectsofConfucius,BookofRitesandGuoyu,Historywas still wandering outside part of the aristocratic educational curriculum system at least before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or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is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fact that as political and social rites, poetry, rites and music were generally taught by both Piyong (imperial higher education) and Pangong (higher education in vassals’ fiefs) in Western Zhou Dynasty,Historywas the written “text” only for the imperial Piyong curriculum, while in the Pangong curriculum, the documents such as the genres of guzhi (records of ancient history), lin (decrees), shi (records of the activities of ancient kings and princes) and xundian (precepts by kings) in each fief replacedHistorywhile functioning as national historical education.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func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dissemination ofHistoryat its early period, will be conducive to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behind the curriculum design in the imperial and official education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rites; texts; imperial and official education; poetry, rites and music;TheBookofHistory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05
2016-05-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14CZX022)
程苏东(1986- ),男,江苏东台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汉唐经学和先秦两汉文学。
K03
A
1007-6522(2016)06-004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