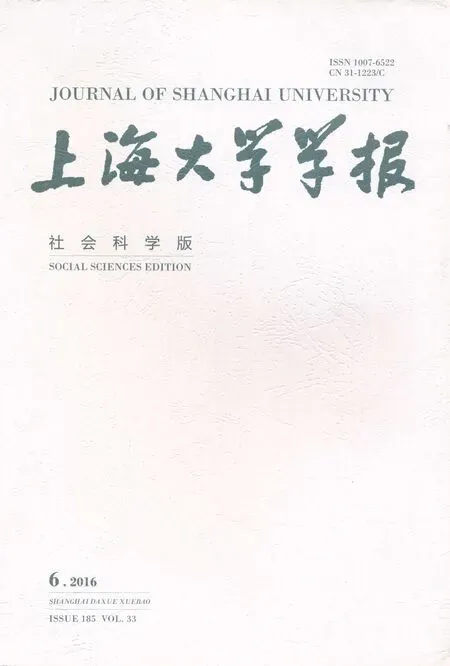英雄与/作为传播
[美国]兰斯·斯特拉特 , 胡 菊 兰 译
(1.福德汉姆大学 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美国纽约 10458;2. 河南大学 外语部,河南开封 475001 )
英雄与/作为传播
[美国]兰斯·斯特拉特1, 胡 菊 兰2译
(1.福德汉姆大学 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美国纽约 10458;2. 河南大学 外语部,河南开封 475001 )
如何理解与阐释英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研究会得出不同结论。从媒介生态学视角看,英雄可以被看作是可写可读的一种文本,可发送可接收的一种信息,可建构也可纪念的一种文化形式,即英雄就是人类传播的一种产物。真实的人仅仅是英雄的原始材料,是通过叙述、文本性、信息传输、人类符号传播和意义生成等方法进行加工的原始材料。在这层意义上,现实中没有英雄,有的只是关于英雄的传播。而且,研究英雄的唯一真实方法,就是研究关于英雄的传播。因为英雄的生成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塑造英雄之传播形式的影响,不同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同类型的英雄。从神话英雄向历史英雄的转变,从历史英雄向名人的转变,都具有戏剧性,而这两次转变都与主要传播模式的变化关系密切:第一次涉及文字革命,第二次则涉及图像革命。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证实,正是由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的改变,导致了传播内容的变化、由传播者形成的关系的变化以及通过传播所创立的文化的变化。因此,诸如书写、印刷和电子传播之类的技术创新,改变了我们谈论英雄、讲述关于英雄的故事和体验英雄的方式,由此也改变了英雄在我们心中的观念。总之,英雄最重要的特征,皆与传播技术具有亲缘关系,而且,英雄概念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转变,是与传播中的创新,诸如书写和印刷的发明、电子媒介的开发等密切相关。
英雄;媒介; 传播;口传英雄;文字英雄;电子英雄
英雄,是我们理想中的自我,是激励我们的自我,是我们立志要做的自我,是我们希望达到的自我。而且,不管英雄是以原型、楷模,还是人体模特的形式出现,我们心中的英雄总是在塑造我们的自我感觉,而且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解读方式。他们教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成为英雄,如何像英雄一样地生活。正如精神分析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解释的那样,由于我们为人类意识的独特天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极度地需要像英雄一样地生活。借助语言和符号的使用所带来的反身法则(self-reflexiveness)之能力,在所有的动物中,我们人类是唯一一种意识到自己终归一死之命运的生物体,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接受这种令人敬畏的常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应对我们自己终归死亡这一想法所唤起的恐惧,保护我们自己,从而对抗面对我们自己终将进入消亡状态时的崩溃感。我们的英雄还教会我们如何无中生有,如何无视和拒绝对死亡的恐惧而生存,如何像英雄一样地活着,并且使我们自己也成为英雄。约瑟夫·坎贝尔解释说,一个人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之行为就是英雄的冒险精神。当我们开始从生到死的英雄之旅时,“我们甚至没有必要独自冒险,因为各个时代的英雄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难解的迷宫已经被彻底地解开了。我们仅仅沿着英雄的足迹前行就足矣”。[1]英雄确实已经为我们标举了行动路线。
英雄的历程不可能在没有先前英雄之足迹遗存的情况下进行,因为,英雄人物表现出的英雄行为需要记叙英雄及其事迹。正如贝克尔所指出的:“文化-英雄们必须拥有适合他们的某种英雄行为体系,在此系统中实现他们的抱负,而且我们把此象征性系统称为‘文化’。”[2]78贝克尔接下来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结构的规则、习俗和观念,此乃英雄主义之载体”。[2]78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文化是英雄的媒介,正如英雄是我们自己心中英雄的自我形象之媒介一样:
事实是,这就是社会,而且一直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系统,一个为行为所制定的地位、作用、习俗与规则之结构,其目的在于为尘世英雄主义提供一种载体。每一个脚本(script)都似乎是独特的,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种不同的英雄系统。因此,人类学家所说的“文化相对论”,在全世界都是真正的英雄-系统(hero-systems)相对论。但是,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是一种尘世装腔作势之豪言壮语的戏剧化;为了展示不同层次的英雄主义,每一种系统都削减英雄的人数:从 “高端”(high)的英雄主义,如丘吉尔、毛泽东或佛陀之类,到“低端”(low)的英雄主义,如矿工、农民、单纯的牧师之类;还有平平常常的每一天,以及引导一个家庭走出饥饿与疾病的粗糙的劳动之手所打造的世俗英雄主义,如此等等。[3]
文化是英雄-系统,而英雄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正如哈伊姆·波托克所讲的那样:“英雄是一个被一批人所接受之价值系统和思想系统的必然伴随物。”[4]英雄充当人类文化的转折点,是集体身份的凝结,是价值、信仰和知识的象征等等。英雄既是心理发展的向导,也是权威和合法性的来源以及社会化的模型等等。他们赋予文化人的面孔和人的声音。但是,英雄不是人,至少在他们是英雄这一范畴内他们不是。例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其经典著作《千面英雄》一书中解释道:
我们并不关心里普·万·温克尔、卡玛-扎曼、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的故事才是我们关心的:而且这些故事在全世界传播得如此广泛——在不同的土地上被赋予不同的英雄形象——以至于这一普遍主题在此地的载体或在彼地的载体,可能是或可能不是曾经基于历史上真正生存过的人这类问题,或许已是次要的了。过分地强调这种历史元素会导致混乱。[5]230-231
对坎贝尔来说,英雄就是一个故事中的叙事元素,一种其意义有待解释的符号。从其他视角看,英雄也可以被看作是既可写也可读的一种文本,既可发送也可接收的一种信息,既可建构也可纪念的一种文化形式。简单地说,英雄就是传播的一种产物。英雄产生于人类传播这一事实不应该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就我们人类喜欢谈话而言,最喜欢聊的话题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对自己理想化的描述。就爱德华·T·霍尔所坚持认为的“文化即传播”而言,[6]贝克尔所说的英雄-系统,以及产生于英雄-系统之中的英雄,也都是传播现象。
传播总是与某种类型的关系相联,而且英雄的人际间关系通常被理解为是分等级的。显然,等级制度在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渊源有自;而且对人类来说,等级制度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在从蚂蚁和蜜蜂到狼和黑猩猩等所有群居物种中,都存在着等级制度,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社会秩序是通过符号的互动性作用来维持的。因此,被理解为一种英雄-系统的文化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英雄政体(heroarchy),因为是英雄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适应社会秩序。但是,此种英雄关系也涉及身份识别,这又超越了等级制度。因此,英雄关系,也可能成为一种平等关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英雄又被看作是下等的。例如:在反英雄中,他们就成了替罪羊和具有讽刺意味的英雄。但是,并非所有的英雄关系都是等级制度的,也并非所有的等级制度关系在特征上都是英雄的。区分英雄关系的是其象征性特征、其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对英雄的崇拜者。
我们甚至可以说,英雄是在旁观者的眼中存在的。每一位英雄都必须是某一个人心中的英雄。奥萨马·本·拉登是一位英雄吗?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和其他“9·11”劫持者是英雄吗?甚至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激怒大多数美国人,但是,难道我们能否认他们实际上也是某些极端分子心中的英雄吗?还有,阿道夫·希特勒曾经一度是数百万人心中的英雄,可悲的是,直到今天某些人仍然认为他是英雄。由此可见,英雄观是相对的,因而也需要用文化相对论和主观性的方法进行审视。这并不是要否定用抽象的方法探讨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制定一些评价标准来探讨英雄的可能性。正如悉尼·胡克所认为的:罕世真英雄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人,无论其改变是好是坏。不过,胡克所说的历史英雄仍然是英雄,因为对诸如胡克这类学者来说他们是英雄,即便这种英雄观是植根于理性而非感情。
英雄不是一个人的存在,但是,英雄却是对人之存在的一种反应,是我们内心所拥有的一个人的形象,是我们赋予一个特定个人或历史人物的意义。就一个虚构人物而言,例如哈姆雷特或超人,就非常容易看出英雄是传播的一种产物。当英雄被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个人时,英雄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可能被混淆。重要的是要理解真实的人仅仅是英雄的原始材料,是通过叙述、文本性、信息传输、人类符号传播和意义生成等方法进行加工的原始材料。在这层意义上,现实中没有英雄,仅仅有关于英雄的传播。而且,唯一研究英雄的真实方法,就是研究关于英雄的传播。我们可以研究关于英雄的传播是如何产生的,英雄人物是如何被塑造的,现实中的个人是如何被呈现的,或者如何把自己作为英雄呈现出来。而且,我们还可以研究崇拜者如何塑造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如此等等。无论如何,如果认为英雄只不过是社会完全凭空捏造之人的建构物,只是一种主观现象,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英雄的生成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塑造英雄之传播形式的影响。
不同的传播模式产生不同类型的英雄。文化英雄是社会、公众或大众传播的结果。一些小说中的英雄可能也会成为文化英雄,但是有代表性的文化英雄被认为是真实的:甚至神话英雄对崇拜他们的人来说也是真实的。文化英雄有别于组织英雄(organizational heroes)(例如公司的创立者、执行总裁等),组织英雄是集体传播的结果。小的群体也可以有他们自己的英雄(如某个群体或社区的领导者),这是基于小型群体的传播。而且,我们的个人英雄(如父母、老师、牧师等等)是人际交流的结果。当要我们说出几个英雄的名字时,我们可能答复一个或者一组这些类型的人物,但是,有益的是要意识到这些是类型非常不同的英雄。文化英雄完全不同于人际交流的英雄,正如拿破仑评论英雄时所言:“仆从目中无英雄。”(No man is a hero to his valet.)没有距离,文化英雄是不存在的。一般情况下,由于时间、空间和社会阶层的原因,一个社会的成员与他们的文化英雄是隔离的,因此了解他们的英雄只有通过故事、图像等等。
在某种程度上,崇拜者感觉他们的文化英雄是遥远的,而且这种距离强化了他们的英雄形象。但是,在距离与存在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受制于有效的传播工具。用霍尔的观点进行推断,文化英雄就是传播的英雄。文化英雄绝非是一种未曾被歌颂的哑然无声之英雄,这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暗指本应该众所周知的英雄却保持默默无闻,尽管这有些不公平。无名英雄可能具有一些被视为英雄的特性,可能是英雄主义的典范,换句话说,可能像一位英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崇拜者,没有人为他或者她唱赞歌,现实中还可能有英雄的存在吗?出于同样的原因,像“被歌颂的英雄”“众所周知的英雄”或“著名的英雄”之类的措辞是冗余的。因为,作为一位文化英雄,当然是出名的,对于一个文化整体的成员而言,也是众所周知的。名气本身已经成为被研究的主体,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传播现象,即当关于一个主体的信息在一群人中广为传播时的存在状态。因此,为了完全理解英雄这一现象,我们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质疑:信息是如何广为传播的?社会通过什么样的工具传播其英雄?英雄事迹如何通过媒介传播?等等。由于正如我们把变化用作媒介,关于英雄的传播也是一样,其结果是,英雄的文化概念也是一样。
布尔斯廷的困惑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是在其著作中明确地论析英雄与媒介之间关系的第一人。他的专著最初命名为《图像:美国梦发生了什么》(TheImage:OrWhatHappenedtotheAmericanDream,1962),后来又更改为《图像:指导美国伪事件》。在这部有影响的著作中,布尔斯廷指出了影响当代美国文化的种种因素,但是,他却特别关注他所说的图像革命,即在图像制作和音像传播中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始于19世纪早期,伴随着摄影技术的出现以及把蒸汽动力运用于印刷技术从而使高速度印刷兴起,到20世纪中期,以电视的广泛推广达到顶点。布尔斯廷认为,一般而言,技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用制作出的体验取代真实体验的能力;他认为,最终,我们会更喜欢以人造的取代现实的,更何况我们已经失去了区别两者的能力。而且,由于我们失去了与真实的联系,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就拥有了过度奢侈的期待。鉴于我们曾经追踪过美国梦,我们现在已经被美国的假象搞得六神无主。我们已经用想象代替了理想。而且,我们已经用虚拟事件取代了真实事件(例如媒介事件),该虚拟事件是为媒介提供内容而制作的虚假事件;正如新闻记者已经从搜集新闻转变成制作新闻,这又导致了对宣传的追踪以及公共关系产业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
布尔斯廷认为,在上述情况出现的同时,我们也已用人为的虚假事件,还有所谓的名人,取代了真实英雄。布尔斯廷对名人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即“因其极高的知名度而出名的人”,[7]57于是,就引出一个由于宣传而产生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英雄以其成就为特征;名人则以其形象或标志为特征。英雄塑造自己;名人则由媒介塑造。英雄是大人物;名人则是享有大名气之人。”[7]61名人“似乎是伟大的,仅仅因为他们是出名的”,然而,按照布尔斯廷的观点,真实英雄“出名,则因为他们是伟大的”。[7]48于是,从布尔斯廷的角度看,伟大是英雄的决定性特性,然而,在传统上,名气与伟大是并肩而行的。图像革命使我们将名气与伟大分离,从而使某些个人的出名与其才能和成就没有丝毫的关联。布尔斯廷认为,这改变了我们对英雄的文化概念的理解: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英雄人物的古老模型被打碎了。一种新型模式已经形成。实际上,我们也确实需要这种模式的形成,这样,适应于市场的人类模型——现代“英雄”——就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批量生产,从而满足市场。现在,通常把一个男人或女人打造成一位具有“全国性广而告之”品牌特性的做法,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一种新类型。现在的新型模式,不是由我们熟悉的道德品质塑造的,甚至也不是由古老的、人们所熟悉的现实塑造的。[7]48-49
尽管名人似乎就像是真英雄一样受人羡慕,但是在布尔斯廷眼中,他们的这种新型模式仍然是一种虚假英雄。“名人崇拜与英雄崇拜不应该被混淆。可是,我们却每天把他们混为一谈,由此,我们正危险地一步步接近于使我们自己失去所有真实英雄的模式。”[7]48名人是虚假偶像,但是对他们抱有崇拜之情的这种过失,并不是说我们正在从善转向恶,而只是说我们在无中生有:
或许,使我们苦恼的与其说是恶(vice),不如说是“无”(nothingness)。我们体验的真空,由于我们为过多使用机械装置进行人为填充而深感焦虑,从而使其在实际上变得更加空虚。值得注意的不仅仅只是我们想象着用如此多的空虚填充体验,而且还有我们想象着赋予体验如此动人的多样化。[7]60
面对这样的空虚,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对伟大的共鸣以及近似于自我崇拜之类的东西。因此,克里斯托弗·拉什把名人评价为一种自恋文化综合征。
布尔斯廷的困惑是:在20世纪晚期控制美国文化的英雄其实不是英雄。他们不是英雄,因为他们不符合传统标准的伟大。但是,就他们是很多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而言,他们又是英雄。考虑到对名人评论的有效性,布尔斯廷的困惑和英雄/名人之二分,使人联想起关于文化与艺术的高/低层次的讨论。布尔斯廷认为,从精英人才的地位,再基于特别的标准(例如伟大),他(和其他人)可以判断哪些英雄配得上英雄这一称号。不过,这样的批判性分析归根结底要走向美学或价值判断。创造一项运动纪录是英雄吗?挣了一大笔钱是一种伟大吗?为慈善机构捐款和支持此类事业是一种英雄主义吗?我们可以不断地谈论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认为最好以不同的方式构建这一问题的原因。我宁愿从一个(相对)客观的、中性的位置开始探讨,尽量判断谁是人们的英雄,什么构成了人们的英雄文化概念,而不愿告诉人们,说他们心中的英雄算不上英雄。我认为,更有效的是把名人看作当代英雄,理解在当今的英雄文化概念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而不是对英雄和名人采用一种二元价值(two-valued),即采用要么英雄要么名人的定位方式(either/or orientation)。这是布尔斯廷本人承认的一点。
我们的时代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显赫。这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这个世纪的特征,正如公元前6世纪希腊神之神性,或者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或骑士以及温文尔雅的情人一样。此显赫不曾驱使英雄主义、圣徒地位或崇高的牺牲完全走出我们的意识。然而,伴随着每一个十年的到来,它却使这些特性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现在,展示所有的伟大的古老形式只在这种新形式的阴影之下存活。这种新型的显赫就是“名人”。[7]57
在此,布尔斯廷含蓄地承认,英雄的文化概念发生变化已非首次。布尔斯廷所维护的传统英雄是历史英雄,而这些历史英雄都曾经是自命不凡的人和篡位者,他们取代了神话英雄。正如坎贝尔所解释的:“每当神话诗被看作传记、历史或科学时,它就被抹煞了。活着的图像仅仅成了一段冷漠的时间或天空的遥远事实。此外,把其演示为科学绝非难事,而且历史神话本身就是荒诞的。”[5]249
从神话英雄向历史英雄的转变,至少像从历史英雄向名人的转变一样具有戏剧性。这两次转变都与主要传播模式中的变化关系密切相关,第一次涉及文字革命,第二次涉及图像革命。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学家,诸如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埃里克·哈夫洛克、哈罗德·英尼斯、沃尔特·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加里·贡佩尔特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等,都已经证实,正是由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方法的改变,导致了传播内容的变化、由传播者形成的关系的变化以及通过传播所创立的文化的变化等等。因此,诸如书写、印刷和电子传播之类的技术创新,改变了我们谈论英雄、讲述关于英雄的故事和体验英雄的方式,由此也改变了英雄在我们心中的概念。传播技术,通过影响我们的思维和将我们组织起来的方式,来对我们施加一种间接影响,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英雄的身上得到体现。显然,除了影响特定文化之英雄概念的媒介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但是我相信,英雄最重要的特征与传播技术之间具有亲缘关系。而且,英雄概念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转变,也曾经与传播中的创新有关系,例如书写和印刷的发明以及电子媒介的开发等等。
从口传英雄到文字英雄
在口传文化中,讲话是传播的主要模式,长时间地保存信息依赖于集体记忆。文化英雄通过口头诗歌和歌唱而出名并被人铭记,荷马史诗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除了人类记忆之外,在口传文化中,没有像书面文件那样有可提供的存储媒介,语言简洁是通常的规则。这就意味着,相对于书面文字文化,口传文化只能传承一定数量的英雄。如果新的英雄被人们接受了,先前的英雄就会被人们忘记,或者其身份特性(identities)会被融合。口传英雄常常会变成复合型人物,很多人的活动会被认为是一位英雄所为。这只能使口传英雄变得高于生活。当然,夸张也起一定的作用,而且不受书面记录所能给予的任何制约,因为有了书面记录才能为英雄的行为提供更加精确的描述。再说,英雄的冒险活动越与众不同,越离奇,其故事就越令人难忘,如此这般,口传文化便愈加青睐离奇的、超自然的英雄。典型的口传英雄故事涉及冒险和旅行经历,正如坎贝尔所解释的,是那些包括辩论、战斗和远征的故事。而且,叙事越具有戏剧性和对抗性,越容易让人记住。结果,口传英雄往往是以其行为和活动而出名的。最终,重要的不是赫拉克勒斯、吉尔伽美什、贝奥武甫或亚瑟王等人的名字;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他们的行动,因为是他们的行动承载着对文化而言具有价值的信息,同时塑造着值得人们模仿的行为。
口传英雄往往是不带个人色彩的、泛型的人物,即类型化人物,因为与个人特质有关联的细节使集体记忆有限的存储容量难以负担,而且它们对于文化的延续也是可有可无的。细节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常常以老生常谈和公式化为特点(例如:聪明的奥德修斯、勇敢的阿基里斯)。口头作品运用一定数量的口传格式,将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首歌。英雄的概念就被包含在这些格式中,而且唱歌者只简单地把具体英雄的名字插入其他格式化的作品中——由此,坎贝尔所说的单一神话就出现了。正如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所加以阐释的:
荷马……按照其塑造的人物名字的韵律价值,把神性、马术、力量甚至金发赋予他们,而不考虑其人物的出生、性格、等级或传奇等等:除非这些东西是所有英雄所共有的。也就是说,除非这些东西是可以互换的。例如:如果作“牧师”与当“国王”或作“骑士”,拥有“清白”或“坚强”,甚或通用词所显示的任何其他品质,具有大约相同的价值,那么出于对韵律(metre)的考虑,就会引导诗人为了某一特定英雄而非另一个英雄,从而强调这诸多品质中的一种。[8]
换句话说,帕里在说韵律是信息。此外,韵律和格式都是助记手段,但是英雄本身也是帮助口传文化成员记住知识的记忆辅助工具。正如沃尔特·昂所提出的:
在其周围信息满天飞的人物,即那些其故事被人们讲述或歌唱的人物,必然成为惹人注目的名人、公众的焦点,体现开放的、大众关心之问题的个人……换句话说,在其周围信息满天飞的人物必定是英雄,在文化上是像奥德修斯、阿基里斯或俄狄浦斯一样“伟大”或“厚重”的人物。另外,文字文化把细节置于手稿之中,但是对于口传文化而言,为了稳固细节飘忽不定的特性,这样的人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样的人物又不可能很多,否则注意力会分散,焦点也会变得模糊不清。于是,就开始了这种人们所熟知的惯例,即把在历史上由各种各样人物完成的行动,归因于有限数量的主要人物(罗马复杂的早期历史可以在特洛伊战争勇士埃涅阿斯的传记中看到,或许也可以看作是罗穆卢斯和雷穆斯的故事);只有在书写和印刷出现之后,在一部现代历史著作或如《芬尼根守灵》(FinnegansWake)之类的小说中,这样多的人物数目才是有可能的。
由此,从某种观点看,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口-耳相传文化(oral-aural culture)中知识储存与传播问题的反映(的确, 在此储存与传播实质上是一回事)。[9]
由于经济的需要,任何一位特定英雄都可能与涉及很多主体的知识有关联,其中包括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地理、宗教、伦理、战争、政治、经济、心理、实际问题(例如:船舶航行、农业、木器等)等等。这也包括对经典传奇本身的歌唱,因为在各种文化形式中,传播的从业人员常常赞美他们自己的活动和职业,不管他们是经典传奇的歌唱者、作者或是媒介娱乐圈人士。不过,由于对经济和所实施的必要之助记功能的需要,口传英雄与其他类英雄不同,他们精通所有行业,而且这也促使他们具有较高的境界。总而言之,口传英雄是属于神话的或者传说的英雄,因为口传文化的传播特征支撑英雄这一概念。
当书写出现时,支撑口传英雄的条件开始削弱,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解释的:
通过文化,一种去神圣化(desacralized)的宗教领域和一种去除神话色彩的神话学产生了,并滋养了西方文化……在此,这不仅仅只是逻各斯神话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图书战胜口头传统的胜利,是文档——尤其是书面文档——战胜其唯一表达工具仍然属于有文字之前的一种口传生活体验的胜利。[10]
书写并非是不假思索地消除口传英雄,而是文字允许个体把自己与其传统分离,以思考的和批评的眼光审视传统,因为一旦写下来我们就可以对文字进行审视,审视,再审视。这样,口述英雄就可能渐渐被削弱,并被取消其合法地位。例如: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书写中就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因为他开始质疑赫拉克勒斯的超人功勋,而且他还质疑了涵盖其后裔15代直至神的希腊宗谱。因此,书面记录一旦被接受为权威,口头记忆就会受到质疑,随后遭到质疑的就是口传英雄。
书写允许比口头传统更多的英雄得到赞颂并被人们记住,而且透明的(sheer)数字本身使个体文化-英雄少一分独特性,多一分人性。伴随着除集体记忆之外的储存信息工具的出现,不再需要厚重的神话和传说人物,令人更为轻松的英雄成了标准。这些新型的文字英雄仍然是非同一般的,但是他们不再是超自然的或超人的,也不再是公式化的。他们是面对现实的人,不是被崇拜的客体,甚至连被羡慕的客体也不是。通过书写工具提高了储存容量,使得每一位英雄的更多信息可以得到保存,这样,英雄就变得具有了个性特征。文字英雄依附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背景,他们的业绩故事也被记录英雄整个生活的传记所取代。性格、美德和内在素质成了历史英雄之新型概念的一部分。当我们从口头文化转移至文字文化时,坎贝尔的英雄之旅也从外在的奥德赛转向了内在的精神之旅。口传英雄必须遭遇并战胜敌对的自然环境,即一种常常用具体的、拟人的词语表达的环境。文字英雄处于自我发现、自我克制和自我实现的旅途之中,于是冲突或多或少在本质上是心理的和精神的。此外,口传英雄的业绩是用插话式的模式表达的,而且作为一系列相对不连贯的冒险,也没有必要确定时间顺序或排除前后的不一致。而书写和印刷则可以展开线性叙事,并且有利于终结性的结尾和一致性,因此历史英雄出现在一个完整的生活故事之中,在该故事中事件是连贯的、有逻辑的(例如:年轻时的勤劳导致中年的成功)。结果是一种复杂但一致的特性描述,从而把英雄的概念塑造成一个独特而又具有同质性的个体或主体,正如布尔斯廷所坚信的,一律以伟大为特征。
印刷机的引进扩展了文字英雄的发展。按照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观点,印刷技术“通过实例,以及圣人和圣洁国王的生活,还有描写普通人追求更具有多样性职业生涯的传记和自传进行教化,使得伟大人物的故事能够得到补充”。[11]229更多的英雄和更多的信息,是与更多专业化英雄的出现有关的,这首先出现于古代文字文化中,后来出现于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文化中。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军事英雄,他们不同于政治英雄,也不同于宗教英雄等等。基本上,每一种职业和每一种业余爱好都有自己的一群英雄。正如口传英雄要有诗人和歌咏者一样,文字英雄要有专门的作家队伍。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的讲演中就表达出这种发展意识:
英雄-众神、先知、诗人、牧师都是属于以前时期的英雄主义形式,他们在遥远的时代出现;其中一些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因而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再展示自己。英雄,像作家一样……都是新时代的产物;只要书写之奇妙艺术,或我们称之为印刷的快捷-书写(Ready-writing)之奇妙艺术继续存在,作为未来所有时代英雄主义的主要形式之一的英雄,就会被人们期待继续存在。英雄,在各个方面,都是一种极其异常的现象。[11]383
显然,作家是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存在的一种英雄,但是书写和印刷导致了很多其他新型英雄的出现,诸如:学者、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音乐家等等。这些新型的文字英雄是以他们的思想、知识和创造成果而出名的。他们的活动仍然存在,但是在此强调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与文学家一样,人类领袖也以其思想而出名,是作为运筹帷幄者,而不是勇士。拿破仑和华盛顿是有名望的,但不是因为他们战斗勇敢,而是因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成就。与奥德修斯不同,哥伦布被人们记住,不是因为他对事件的追求,而是他航海背后的思想。
在口传文化中,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虚构叙事的显著范畴直到印刷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小说和短篇故事中的新型虚构英雄完全不是真实的,不过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的,在一些重要方面类似于历史英雄,由此加强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字英雄概念。
从印刷英雄到电子英雄
印刷革命以活字排版的发展为基础,但是历史学家认为,印刷机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发明,是一种包括排印和雕刻的发明。虽然雕刻比不上肖像绘画能传达那么多数量的视觉细节,但是也可以产生足够的信息使主体得到认识,而且这种信息可以扩散得相当广泛。这与硬币形成对比,硬币起大众媒介的作用,而且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开始,上面就包含有实际人物的图像,但是却缺少使主体变得真实、清晰可见所必须有的细节。正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所指出的:
法国大革命中一件很著名的事件,揭示了压印在硬币上可以重复的老式图像与因印刷的出现所带来的新型结果之间的差异。天子与国王的个人图像被压印在硬币上,他们的个性特征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详述,但是当他们隐姓埋名地游走时,他们的面孔是可以被认出来的。也正是印刷在纸币上的肖像使一位警惕的法国人在瓦雷纳认出了路易十六并阻止其继续前行。[11]84-85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清楚解释的,机械复制对于艺术品、视觉影像以及英雄具有民主化作用。虽然这一技术使得人们能够进行脸部识别,但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它是真实的却并不完全清楚。考虑一下这一事实,为了核实路易十六的身份,法国人必须对路易十六与他的印刷版图像加以比对。在类似的情况下,当生活于今天的美国人遇到乔治·沃克·布什时,到底还有多少人需要做这类比对呢?尼尔·波兹曼在描述18世纪和19世纪美国的书写时这样说道:“人们是通过公众人物的书面语言了解他们……而不是通过他们的相貌甚或他们的演讲技术。当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在大街上从普通公民身边走过时,很有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会被认出。对于那个时代伟大的律师、部长和科学家来说,情况也会是一样的。”[12]第16届总统选举恰逢摄影技术的推广(摄影也被用于记录南北战争),林肯成为第一位由于其相貌而受到批评的总统,因此这并非巧合。无奈的是,他是在留声机的发明之前被暗杀的,结果可以想象,林肯被人们牢记,不是因为他拥有高音调的声音,而是因为人们臆断他拥有匹配其严肃又庄重之肖像的低沉声音。
每一种新型媒介的出现,都伴随着英雄概念的进一步突变。电影伴随着电影明星的出现,他们像传统英雄一样高于生活,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在其他方面则并非如此,比如:他们缺乏内在素质,依赖于报纸上的随笔专栏和影迷杂志。无声电影的英雄因他们的面容、手势和身体动作而出名,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向有声电影的过渡时期就消失了,因为有声电影既强调声音又强调不宜过分夸张而是应多些现实特征的表演。摄影与印刷给我们提供了流行模式,其在外观上占有优势,但是在大多数其他特质方面,却似乎处于劣势地位。录音使音乐表演者成为英雄,最终导致录音艺术家这一新型范畴的出现。扩音器成就了像弗兰克·辛纳屈和平·克劳斯贝之类的低声歌唱者,他们因其放大、加粗了的低声而受到人们的崇拜,同时电子放大器也成就了摇滚乐的吉他英雄。无线电广播使那些能够给我们提供产生亲密情感错觉但仅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人成为英雄,但是用巴格斯(Buggles)那不朽的语言说,则是“视频扼杀了广播明星” 。比其他媒介更具杀伤力的是电视,它渐渐地破坏了印刷英雄,从而支持名人或电子英雄(这促成布尔斯廷在《图像》(TheImage,1962)一书中所进行的批评)。
在最近两个世纪引进的每一种新型媒介,都扩展了在文化内部传播信息的数量,从而允许比以前更多的英雄出现。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英雄膨胀现象,给我们提供甚至比印刷文化的英雄更缺乏厚重感的人物。这些人物是如此地分量不足,以至于布尔斯廷认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英雄。电子通信也支持对信息的迅速颠覆,新的和最近的信息放逐先前的和传统的信息;因此,电子英雄往往是当代的,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又以同样的速度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话说就是:“将来,每一个人都会出名。出名15分钟。”或者正如大卫·鲍伊(David Bowie)和约翰·列侬(John Lennon)所写的:“名望——你今天得到,没有明天。”在过去,传记和自传直到主体去世或至少到主体的事业生涯结束才能写;可现在,只要有广泛出名的迹象,传记或自传就开始出现。到他或她的事业生涯结束时,电子英雄可能早就被遗忘了,传记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迅速翻牌是寻常的事,正如布尔斯廷所解释的,这与传统英雄形成对比,他们是逐渐出名,但却在几代人中享有声望。不过,如果运作得当,电子英雄还可以不止一次地走出名人工厂,卷土重来形成一种新的出名周期。但是,通过认真地避免过度曝光,一些名人也可以长时期地吸引公众意识。
一些电子英雄,凭借自己影像的力量也可以超越这种颠覆,并获得不朽的声名。当然,在我们的文化存储体中,似乎也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永恒地位,例如:像查理·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等电影明星的表演,像法兰克·辛纳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甲壳虫乐队等流行音乐家的面容和声音,像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和杰克·格里森(Jackie Gleason)等电视名人的外貌,像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戴安娜王妃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等之类其他英雄的视听录音,如此等等。也许由于布尔斯廷对名人的批评一直针对的是同时代人,因此是不成熟的。当他第一次在60年代早期书写名人时,电影和录音才仅仅存在一两代人的时间,还不足以估量视听媒介如何会影响我们穿越时间进行交流的能力。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断定某些电子英雄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似乎是合理的。不过其他人也许会周期性地死后复出,继而进入下一代的周期。无论如何,与先前的英雄模式不同,已成为过去的电子英雄,当他们被视听媒介复活时,他们将保持其即时性并继续培养一种亲近感。当过去的电子英雄渐渐控制了我们的历史洞察力时,将进一步威胁印刷文化之历史英雄的合法地位。毕竟,作为一种保存过去的工具,一段书面叙述怎能与活动图像和录音材料一比高低呢?与个体的电磁性娱乐形成对照,历史英雄除了显得不真实外,又能怎么样呢?对过去的文字和印刷英雄来说,要在电子媒介环境中继续做文化英雄,他们需要复活,需要借助演员出现在电视、电影等媒介上,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得到复活。
以视听格式出现的信息,通常比以书写形式编辑的信息更容易接受,因为视听材料不要求任何程度的专业知识及文字能力。于是,这也巩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电子媒介增加了可以进行传播的信息量,由此也增加了有关任何一位特定英雄的信息量,这使得英雄更容易被接受。对英雄的快速颠覆,也有助于搜寻名人信息并迅速传播这些信息之倾向的出现,不管此类信息是否重要。不过一般来说,这些信息是不重要的。电子传播使英雄平凡化。我们了解他们的健康情况和家庭问题、他们吃的食物、他们开的车以及他们与谁发生性关系等。例如:比尔·克林顿就无法对媒介保密他与一位白宫女实习生的婚外恋情,这几乎毁掉他的总统生涯,但是却赋予莫尼卡·莱温斯基很高等级的名人身份。克林顿很久以前就设计自己面对电视摄像机时的形象,他出现在访谈节目上,戴墨镜和演奏萨克斯,回答音乐电视上 “穿平脚裤还是三角裤”的问题,并举行关于性关系问题的“电子公民会议”。他的成功基于以性行为牺牲人性尊严的名人策略。但是,性丑闻透露太多关于克林顿人性弱点的信息,从而破坏了他当总统的业绩,虽然很多美国人明显感觉到这“纯粹是性”与克林顿“像埃尔维斯”(Elvis-like)的明星形象并不一致。
口传文化中厚重的人物从定性上讲比我们伟大;印刷英雄在某一专门领域具有重大成就。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电子文化的那些分量不重的人物,就像我们一样,是平凡的。电子英雄对其自身的生活甚至可能拥有比我们更少的自我约束,使得他们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因而,我们曾经看到把受害人介绍为英雄,但他并不是一位像林肯一样为某一事业献身的烈士,而仅仅是因毫无意义之暴力行为的伤亡人员,诸如肯尼迪;甚或是经得起痛苦折磨而存活下来的人,例如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成功地度过了伊朗的人质危机。此外,充当受害人的角色,承认其具有某种心理或身体问题,可能也是名人的一种复出策略,但至少要保证弄到在日间脱口秀节目上出现的机会。但是,每一个失去自我形象控制的名人,不管是男是女,甚或那些不能正确对待其名誉要求的名人,最终都会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英雄,最极端的事例就是名人自杀。一位新闻发言人对当地听到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因用药过度而身亡的消息时评论道:死亡是一次成功的事业转型。
无论是平凡还是讽刺,电子英雄都不值得我们像对口传英雄那样进行崇拜,也不值得我们像对文字和印刷英雄那样心生羡慕。由此,对电子英雄的崇拜者或羡慕者,都变成了浮躁的粉丝。名人的声名鹊起可能带来歇斯底里,因此,fan(粉丝)的词源是fanatic(狂热入迷者)的缩写形式。Fans追随的是fads(时尚),而且,大批可以选择的英雄和对英雄的迅速颠覆,都有悖于仰慕者对某一个英雄可能赋予的持久性忠诚。电子英雄的平凡,意味着名人与粉丝之间或多或少是平等的,几乎是可以换位的。结果是产生一种权利感,因为我们渐渐相信,自己也应该出名十五分钟,否则就是失去那十五分钟,是名人剥夺了我们这十五分钟,因而他们应该对我们心存感恩,以作为对我们的奉献的报答。粉丝与英雄之间距离感的缺失导致粉丝一方的亲密幻觉,于是我们与名人的关系是亲近的,是朋友或情人。在名人世界,做一名粉丝也有可能出名,当然也有可能从粉丝一跃而成为名人。的确,一些飞黄腾达之名人的出名就是靠持续地像粉丝一样表现,正如罗茜·奥唐内(Rosie O'Donnell)在她的脱口秀节目上所做的那样。有时候,追星族就是靠其活动出名的,或者是作为名人追星族到处跟追,或者是通过与明星建立一种更加稳定的浪漫爱情关系。最极端的是,从名人-粉丝的关系,转而成为病理学上的名人-刺客关系,例如: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和马克·大卫·查普曼(Mark David Chapman),他们就是通过袭击电子英雄而使自己出名。
这一切导致人们对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谓之英雄的困惑,由此,贝克尔认为,我们的英雄体系在60年代曾经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我们自己国家的英雄体系本身在遭受原始部落早些时候所遭受的质疑,逃避现实的年轻人是新一代失去部落化特征的人。伴随着英雄主义一致性模式的被打破,人们看到各种属于子群体的特别英雄行为以及属于个体的私人英雄行为的出现——每一个人都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英雄。”[2]126难怪更近些时候,当让某些人说出他们心中的英雄时,列出的名单包括历史英雄、名人、虚构英雄甚至人际关系英雄。于是,就出现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英雄的困惑,这或许是由于英雄的概念处于变化之中的缘故,也或许是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更加多样化的英雄概念的建立。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仍然保持着我们传统的英雄和英雄主义概念,尽管媒介的内容已经是另一种了,但媒介形式却常常是旧有的。无论怎样,文字英雄的概念已经被渐渐地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被直接取消合法地位,不如慢慢地变得暗淡,以至于被人忽视。例如:在1979年,《学乐杂志》调查了他们的年轻读者,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排在前五位的是:斯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埃里克·埃斯特拉达(Erik Estrada)、伯特·雷诺兹(Burt Reynolds)、约翰·韦恩(John Wayne)和杰里·刘易斯(Jerry Lewis)。我发现特别突出的是来于《学乐活动》(ScholasticAction)在如下评论中所展现出的表达上的智慧:
是的,排在前五名的英雄都是男性。他们都是电影或电视名人。没有政治家,没有宗教领袖,也没有历史人物。
一些人感觉奇怪和悲伤。“为了让年轻人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说:“必须放在电视上。”
但是,14岁的库尔特,一位南山(Southern Hills)的学生,则这样解释道:
“时代已经变了。”他说:“像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林肯之类的人,他们仍然由于自己所做的一切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英雄。”
的确,这是一种不同的英雄。电视上,强调的不是行为或思想,而是外表和个性。思想可能被一个人的一生所拥有;但图像的出现和接受就是几秒钟的事。即便思想出现在电视上也会被图像所遮蔽,从而创造一种思想图像,但却无实质性内容。行为可能是图像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电视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媒介,但是与口传英雄不同,电子英雄的行为不是令人难忘的。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幅行为图像,一幅作为实干家的男人或女人的英雄图像,但是他们的具体行为却被忘记了。把赫拉克勒斯匪夷所思的劳动比作像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和施瓦辛格(Schwarzenegger)之类电影明星的众多的极度暴力,但在其他方面却又普普通通的行为,就是一个例子。简而言之,电子英雄以图像出名,而非以行为或思想出名。在口传文化中,英雄是以刀剑生存和死亡。在印刷文化中,笔比剑更有力。但是,在电子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既不是武器也不是笔,而是外表与个性。然而,文字英雄是传记的主体,因此,他们是因他们的生活而出名,但电子英雄则是随笔专栏,像美国《人物》(People)之类的杂志,还有像《今晚娱乐》(EntertainmentTonight)之类电视节目等的主体,在这里,他们不是因其生活而出名,而是因其生活方式而出名。
此外,正如笔和印刷机创造新型英雄一样,电子媒介也创造新型英雄。典型的是,被称之为名人的新型英雄是演艺人员,例如:电视和电影明星、录音艺术家、电台节目主持人等等。其他的还有媒体从业人员,例如:新闻评论人、体育直播员和时装模特等。这些新型英雄几乎使老式英雄黯然失色,他们甚至充当权威人物。正如约翰·费兰(John Phelan)所指出的:“制作一部电影,成为一位明星。治疗疾病,成为明星。买肥皂,成为明星。拯救灵魂,成为明星。有人听你的,你就是明星。”[13]但是,当名人推销产品时以及当他们做慈善事业时,他们也在推销他们自己。而且当他们为了某些目的寻求宣传时,他们自然也会为自己获得宣传。最利他而又最无私的公共法令,当用名人代言时,就会变得与完全蓄意的和自私的行为难以区分。在海森堡(Heisenberg)或第一名人公理(the First Axiom of Celebrity)之后,把其称为名人不确定性原理(Celebrity Uncertainty Principle),继瓦兹拉威克(Watzlawick)及其同行之后,名人就不可能不自我推销了。
当娱乐圈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构成新型英雄模式时,更传统型的英雄则由于被转型为名人而出名。如此一来,现在政治家通常在谈话节目和系列幽默剧中出现;他们主持《周六夜现场直播》(SaturdayNightLive);他们甚至为一些产品大做广告;当然,演艺人员可以成为政治家这件事也已不再被认为是离奇的,甚至加州之外也是这样。政治与娱乐总是具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即便其他部门也并非不受名人的诱惑。现在,宗教领袖也有他们自己的电视节目,并且成为谈话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有时不经意间还可能成为肥皂剧明星。李·艾科卡(Lee Iacocca)在电视广告上出现,部分是要描述自己经营的一家大公司,但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则论证,在电视节目中担任主要角色是经营中的真正底线。像诸如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泽西·考辛斯基(Jerzy Kosinski)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等之类的作家则变成了电视和电影演员。自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之后,艺术家们开始理解并呼吁名人文化,像约翰·凯奇、马友友、鲁契亚诺·帕瓦罗蒂和伊萨克·帕尔曼等之类的一些古典音乐家,他们也是同样地心向往之。但是,正如雷·古德尔在《可见科学家》(TheVisibleScientists,1977)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科学家也并非不受这种现象的影响。牛顿和爱因斯坦却都是因其思想而出名的专家,然而,在此所说的名人-科学家则是由于紧紧抓住了“热点问题”而出名,这些热点问题因其相关性和容易引起争议之特点而吸引媒体报道,即便这些问题超过了科学家的专业知识领域:“可见科学家(Visible scientists)是媒体时尚的产物……无论是赶潮流,还是不赶潮流,时间的选择都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故意地还是本能地,能够恒久被人记住并产生影响的科学家,随着公众利益的变化,他们都要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14]卡尔·萨根(Carl Sagan)通过他在《今夜脱口秀》(TonightShow)以及他自己的电视系列剧《宇宙》(Cosmos)等节目中的出现,还有他对关于核冬天之辩论的参与,展示出他的名人才能,进而使他成为可见科学家中可见度最高的人物之一,古德尔把这一范畴应用于硬科学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各种类型的专业学者都渴望得到知名度(visibility),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凭借他们在电视上的权威见解,成为公众知识分子。马歇尔·麦克卢汉是第一批通过在电视上频繁出现并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中饰演一个配角而出名的;更近一些,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在电影《黑客帝国》中演了一个角色。在名望的冲击下,象牙塔本身已经倒塌,因为大学也在寻找频繁出镜的专业学者和非学术性名人加入其师资队伍。况且,这种现象也不只限于美国。在法国,知识分子曾经是无与伦比的文化英雄,但是雷吉斯·德布雷认为,他们现在也变成了名人:“高级知识分子成员也要依赖于自身的形象,这种依赖常常成为一种困扰。对于有思想的专业人才来说,‘我的形象好不好?’与‘我的想法是否正确?’相比,(并且常常)成为一个更加紧迫地需要解决的问题。”[15]
最终,这导致所有这些具有印刷文化特征的专业化英雄消失,因为职业已经被转化为就是站在摄像机前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趋于迎合别人,从而变得很容易被废弃。对此,约翰·拉尔简洁地陈述道:“政治家变成了新闻评论员,新闻评论员变成了电影演员,电影演员变成了政治家,名人把每一次严肃的活动都变成了一场表演。而且,在美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聚集在电视访谈节目上。”[16]电子英雄不是精通所有职业的能手,而是展示所有职业的一位演员。但是,这里指的不是人们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表演。人们最常见的情况是:演员扮演角色,明星扮演自己,而名人则把这种特征发挥到极致。要求名人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自我展示,使自己出洋相。这样自然在吸引人的外观上要投入高额的费用,这也就是为何名人文化彻底改革了许多产业,其中包括时尚、化妆品、发型设计、修复学(如鞋跟增高)和整形手术等等。波兹曼论证道:在电视时代,一位没有吸引力的人不可能被选为总统,虽然美貌在任何职业中都是用于获得高知名度的一种工具,但是一般而言,电子英雄还需具有与众不同的外表。例如:杰·雷诺(Jay Leno)的下巴和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门牙间的缝隙,都成了他们的显著标志;同理,肥胖的体重则成了罗茜·奥唐内、罗西妮·巴尔(Roseanne Barr)和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人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裸体像也能增加一个人形象的特殊性,例如:为诸如《花花公子》(Playboy)、《阁楼》(Penthouse)甚至《皮条客》(Hustler)等杂志摆造型,也是女性名人严肃考虑的一种选择,这样做并非仅仅只是为了金钱报酬,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提高知名度;而且,这与自我展示也并不矛盾。因为名人吹嘘的唯一价值就是诚实,但是,这种情况在伦理行为的传统意义上是不诚实的(正如在杜撰出的乔治·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中,或如林肯的绰号“诚实的艾贝”[Honest Abe]所表达的)。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自我展示的诚实,把自我暴露作为名人展演的基础,如在谈话节目上,在影迷杂志的采访中,在脱口秀沙龙的套路中,如此等等。要想出名,你所要做的就是要争取站在摄像机前做你自己,这种感觉增强了我们对电子英雄之平凡性的感受,而且也培育我们要在他们身边占有一席之地的欲望。难怪,近些年真人秀电视节目十分流行。《幸存者》(Survivor)、《老大哥》(BigBrother)、《单身汉》(theBachelor)、《学徒》(TheApprentice),甚至《美国偶像》(AmericanIdol)等等,都是对把我们牵连其中的新型英雄体系的颂扬。
在电视上,表演是唯一的真实,因此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仅仅通过书面语言体验人物,要确定这些人物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就需要有普遍公认的程序。不过,要使一个虚构人物在电视上活起来,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扮演虚构人物的演员必须演得像他们自己演自己一样真实,否则就不真实了。实际上,两者都是表演者,都是在演出,都是自我展示的形式。在许多方面,虚构人物似乎比扮演这个角色的人更加真实。例如:柯克舰长(Captain Kirk)、阿契·邦可(Archie Bunker)、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和托尼·索普拉诺(Tony Soprano),他们都变得比其扮演者威廉·沙特纳(William Shatner)、卡罗尔·欧康纳(Carroll O’Conner)、莎拉·米歇尔·盖拉(Sarah Michelle Gellar和詹姆斯·甘多菲尼(James Ganolfini)更加出名。虚构英雄与非虚构英雄之间的区别,作为文字的产物,在电子文化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痛痒,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群体中也是这样。因此,人们请求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即饰演马库斯·威尔比(Marcus Welby)的演员,向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致辞。此外,为一种非处方药物所作的广告则突出一位演员认可这种产品,他在广告中说道:“我不是医生,但我在电视上演过一位医生。”亚伦·艾达(Alan Alda)曾经在几所医学院发表毕业典礼演讲,雷蒙德·布尔(Raymond Burr)曾经在法学院演讲,电视节目《人民法院》的法官约瑟夫·瓦普纳( Joseph Wapner)也一样做演讲(至少瓦普纳还曾经担任过法官,虽然是一位无名的法官)。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这种区别在节目中进一步被侵蚀,例如:在《宋飞正传》(Seinfeld)这部喜剧片中,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这位喜剧演员演的就是他自己,只是作为一位虚构人物起名叫杰瑞·宋飞,他一度是一部虚构情景喜剧中的一颗星,起名叫杰瑞,在这部喜剧中,他通过把自己扮演成一位虚构人物以便展示他自己。
计算机媒介已经延伸并强化了电子英雄的许多特征。当然,计算机也已引出了一些新型英雄,例如:程序员和各种类型的电脑黑客。互联网也已带来一些提高知名度的新形式,例如:网络存在、可下载图像、网站点击率等等,由此也进一步增加了英雄的数量,然而却同时也减轻了这些英雄的分量。网上英雄具有一种很强的民主成分,因为参与讨论列表和聊天室以及创建网站和安装网路摄像机等,能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名人。数字技术在扩大了电子英雄范围的同时,通过其重新合成和定位音像内容之能力,也进一步模糊了其边界。例如:汤姆·汉克斯(Tom Hanks)被完美地插入到电影《阿甘正传》(ForestGump)的老式新闻镜头中的情况就是这样。电子英雄的图像还可以被用于游戏目的,成为大批玩游戏者突发奇想的傀儡主体。人工智能程序和专家系统,开始记录各种不同领域中著名人物的思维过程;经过进一步研究,他们或许也能够成功地重构与个体性格的某些相似性。随着捕捉并重组声音与图像之能力的进一步开发,人工合成的表演,离取代传统表演的时代已经不远了。这无论是否是一次成功的转型,死亡或许再不会标志着名人事业生涯的终结。再说,对像林肯或柏拉图之类历史人物的模拟,可能会把他们这样的文字英雄变得也具有交互式电子个性。无疑,这将会促进名人-粉丝(celebrity-fan)的关系,因为你可以拥有对你心中英雄的交互式仿真,但是这也进一步模糊了事实与虚构、真实与幻觉之间的界限。还有,数字英雄可能是一种完全彻底的计算机仿真,是计算机程序伊丽莎(Eliza)和拉科特(Racter)的派生物,非常像在电影《西蒙尼》(Simone)中所描述的,计算机制作了一个电影明星。说到此,对于这些数字化英雄立马就有一种十足的讽刺感,就更不用说是人了。但是,正如弗莱所建议的,当被推向极端时,具有讽刺意味的英雄就翻转成了虚构英雄(替身英雄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关于计算机仿真,确实有些东西是虚构的。电子英雄的历程可能牵涉到与充满技术延伸的社会环境的对峙与调和,正如坎贝尔的单一神话那样,其强调积极应对口传文化中的自然环境和文字文化中思想与精神的内在环境。
美国“9·11”之后的英雄
在此,我提出的基本论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概念是基于我们所使用的主要传播模式,这一论点随着2001年9月11日悲剧事件的发生而得到验证。顷刻间,我们似乎要放弃我们对名人的热爱,转而面对那些在事故当天就献出自己生命的消防员、警察和救援人员,同时还有那些经常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的同仁们,继而支持他们所展示出的更加传统的英雄主义。此时,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英雄,他们在阻止第四次恐怖袭击时牺牲了。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当他们在灾难中极力帮助其他人时,他们自己却处于危险之中,甚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总而言之,虽然大部分美国人承认“9·11英雄”的英雄品质,不过他们却很难从这数千名真实的英雄中说出具体的个人或指认出具体的面孔。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多么想相信他们是英雄,他们依然是没有得到歌颂的英雄,因此也不可能被认为是文化英雄。
或许,最出名的“9·11”英雄就是托德·比默(Todd Beamer),他是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上的英雄之一。这架航班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人们认为,比默与其同行的乘客们一起奋起抵抗劫持者,并且阻止了其对白宫或国会大厦将要进行的第四次袭击。我们通过手机这一媒介知道比默的情况,因为他通过手机传递出他阻止恐怖分子的决心、他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他最后传递出来的话语:“让我们上!”(Let's roll!)这句话在电视连续剧《美国:向英雄致敬》(America:ATributetoHeroes)中,被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反复重复;作为关于“9·11”的一首歌曲的合唱词和歌名,尼尔-杨(Neil Young)也反复重复“让我们上!”乔治·布什在“9·11”之后的那个星期对全国演讲时,以及在之后的很多场合都重复了这个句子;还有很多其他人,他们也都一样,这个句子成了号召全国人的一个战斗口号。布什在其演讲中介绍了比默的遗孀丽莎·比默(Lisa Beamer),她在袭击之后借助多次接受采访和电视见面会的机会,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并写了一本书(与肯恩·亚伯拉罕合著),书名是《让我们上:平凡的人,非凡的勇气》。这使得丽莎·比默本人变得有几分像个英雄和名人,导致一些人质疑她的动机(名人不确定性原理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托德·比默,连同一位不太出名的93号航班上的英雄杰里米·格利克(Jeremy Glick),他们的出名是由于他们最后的手机信息几乎就像是他们最后的行动一样。对此,我们也只能推测。
另外,作为“9·11英雄”,并被人们最为熟知的人物是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liani)。当然,这主要是基于他的象征性领导。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他是否真地取得了伟大业绩,充其量,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引人注意的是他站在摄像机前时呈现出的勇敢面孔,以及他面对纽约市民和我们整个国家时所表现出的演讲能力。实际上,在“9·11”事件之前,朱利安尼的形象曾经多少有些消极,如果这次袭击事件不发生,他将会被列入纽约市有争议市长那长长的黑名单之中。但是,“9·11”事件使他的形象焕发了生机,并使他成为事件之前他从来就不曾想过的名人,以至于《时代周刊》把他选为2001年的年度人物。不过这一选择并非是无异议的,因为鉴于《时代周刊》的选择标准——年度人物应该是对新闻造成最大影响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并不考虑此影响是好还是坏——显然,奥萨马·本·拉登应该是明摆着的人选。在1980年,《时代周刊》的编辑们真正坚持了他们的标准,并选择了霍梅尼,其结果是,他们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订阅者。即便很多人批评他们选择朱利安尼是把利润凌驾于新闻诚信之上,但是值得回味的是,《时代周刊》在1935年创立“年度人物”的意图,就是作为增加销售和订阅量的一种手段。因此,这就是名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似乎庆祝传统英雄行为时的情况也是这样(此外,媒介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旧式媒介)。
发生于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由于战地记者的参与,为庆祝士兵的英雄行为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机会。但是,其中引起最多注意的则是那些战地电视记者,尤其是那些24小时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记者们。通过“伊拉克自由行动”(Operation Iraqi Freedom)真正出名的唯一士兵是女兵杰西卡·林奇(Jessica Lynch)。她最初是以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出现的:在中埋伏之后,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她仍然进行反击,在战斗中受伤,并被敌人俘虏。作为一名战俘,同时她还是一名女英雄和处于困境中的一位年轻少女,受到伊拉克一位仁慈律师的帮助,戏剧性地被美国军队在一次袭击中营救,而且这次袭击借助微光摄像电视被录制成了视频。但是,我们后来得知的实际情况是:当时她的武器卡壳了,她从未射出一粒子弹,她的受伤也被夸大了,拯救她的行动也远非让我们相信的那么危险。批评者谴责五角大楼制造厚颜无耻的宣传,但是如果这是一次故意的宣传,就反映出对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的关于宣传之最基本原则的极端无知。但是我认为,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名人逻辑现在已经渗透到军队的勇士文化,而且五角大楼不可能不受这股潮流的影响。这一基本事件是令人激动的,而且她的外表,一位有魅力的、白肤金发碧眼的女性,也为她的感染力增加了砝码。再说,军队也已经熟悉了高级将领中的名人现象,例如:奥利佛·诺斯(Oliver Nort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tzkopf)、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还有很多陆军上尉和将军们,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但却仍然在充当新闻节目中的权威人士。
林奇作为一位普通士兵的出名,由于其被捕情况的模糊不清而得到强化,其中包括对她的囚禁(她有没有被威胁?被强暴?被拷打?如此等等)、对她的营救以及她曾经因政府对其故事的最初描述而对政府进行的批评,另外还有当曾经帮助过她的伊拉克律师来美国逗留时,她竟然忙得没有时间见他一面的事实。一如既往,她出名了,成了一部电视电影《营救杰西卡·林奇》的主角,这一电影名字暗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这种关联是以前媒介中经常使用的,同时也有助于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于2000年11月9日首次公演的电影《伊丽莎白·斯玛特的故事》,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了,进一步强化了对名人过度反应的感觉。与林奇有关联的还有一本书,其书名是《我也是一名士兵:杰西卡·林奇的故事》,还有一些她参战之前拍的裸体照片也已经浮出水面,《皮条客》杂志编辑拉里·弗林特购买了这些照片,不过他说他不会出版这些照片,但是并不否认有公开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许多表现其他士兵(其中包括专家苏珊娜·约翰逊,一位非裔美国妇女,她也是一位战俘)勇敢和英雄主义行为的故事,则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
如果对“9·11”这一创伤性事件对美国人生活中名人之支配地位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存有任何疑问,那么,好好想想2003年麦当娜亲吻布兰妮·斯皮尔斯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的画面,阿诺德·施瓦辛格接任加州州长的画面,丑闻涉及迈克尔·杰克逊和篮球运动员科比·布莱恩特的画面,以及名人女继承人帕丽斯·希尔顿的表演,首先是在一家能够在互联网上流通的性爱家庭视讯中播出,而后又在一部新的电视真实系列剧中出现,片名为《简单生活》(TheSimpleLife)。
正如口传英雄失去其合法性而书面英雄和印刷英雄却得到其支配性地位一样,今天的文字和印刷英雄正在消失,并被电子英雄所取代。此种发展着实令人忧心忡忡。布尔斯廷是正确的,他提醒我们,老式英雄为我们提供的是展现人之伟大而且令人鼓舞的模式,而且此模式不能被名人所取代。即便我们已经获得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英雄概念,但丧失老式英雄模式是否真是一种适当的补偿,仍然是有争议的。而且,我们起码应该懂得,我们已经放弃了什么,好好想想随着传播媒介的创新,当我们的英雄概念继续变化时,我们还有可能失去什么。
[1] Campbell J, Moyers B. The Power of Myth[M]. New York: Doubleday,1988:123.
[2] Becker 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Mean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an[M].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3] Becker E.The Denial of Death[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4-5.
[4] Potok C. Heroes for an Ordinary World: In Great Ideas Today[M].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73:71.
[5] Campbell J.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6] E T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M]. Garden City: Doubleday,1956:97.
[7] Boorstin D J.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M]. New York: Atheneum, 1978.
[8] Parry M.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M].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1:150.
[9] Ong W J.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M]. Binghampton: Global, 1967:204-205.[10] Eliade M. Myth and Reality[M].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5:157.
[11] Eisenstein E L.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 Postman 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M]. New York:Viking, 1985:60.
[13] Phelan J M. Media World: Programming the Public[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7:64.
[14] R Goodell. The Visible Scientists[M]. Boston: Little, Brown,1977:19.
[15] Debray R.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M]. London: NLB, 1981: 146.
[16] Lahr J. AutoMatic Vaudeville: Essays on Star Turn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4: 218.
(责任编辑:魏琼)
Heroes and/as Communication
Lance Strate, HU Ju-lan
(1.DepartmentofCommunicationandMediaStudies,FordhamUniversity,NewYork10458,USA;2.CollegeEnglishDepartment,HenanUniversity,Zhengzhou475001,China)
How to understand and explain hero? To study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aspects, we’ll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 hero can be considered as text which can be read, written,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and a culture form constructed and commemorated, to sum up, hero is a product of communication.The real person is simply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hero, which is processed via narrative, textuality,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human symbol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In this sense, there are no heroes in reality, there is only communication about heroes. And the only real way to study heroes is to study communication about heroes. The form the hero takes is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the type of communication that produces the hero, and so different modes of communication will yield different types of heroes.The shifts from mythical heroes to historical heroes and from historical heroes to celebrity are both dramatic,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modes of communication, the first involving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the second the graphic revolu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cology,the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the changes of the modes of communicationhave l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contents and the culture of communication.The 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have changed the ways we talk about heroes, telling their stories and our feelings about them, and thus their conceptions in our mind are changed. On the whol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hero and the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most dramatic shifts in conceptions of the hero have been closelyrelated with innovations in communication, such as the invention of writing and pr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onic media.
hero, media, communication, oral hero, literate hero, electronic hero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12
2016-08-01
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GDW20164100040)
兰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1957- ),男,美国人。美国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新媒介计划专业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简介: 胡菊兰(1959- ),女,河南周口人。河南大学外语部教授。
G206.2
A
1007-6522(2016)06-01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