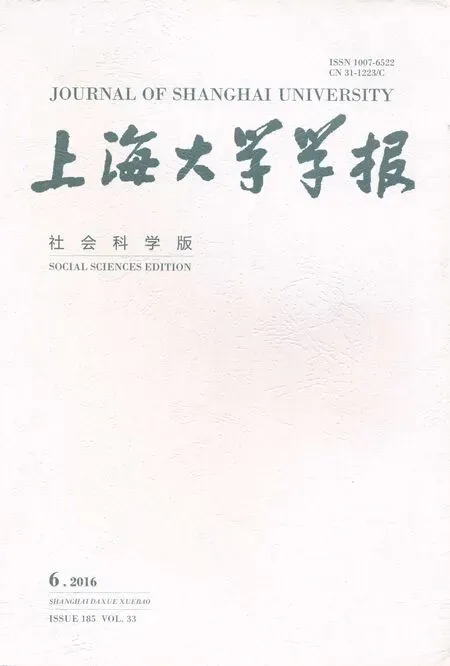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及功能——刑事制裁扩张问题的探讨
岳 平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及功能
——刑事制裁扩张问题的探讨
岳 平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刑事制裁扩张问题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发挥,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热点问题。近年的刑法修正案,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的行为调整和介入,刑法前置化趋势显现。而在社会治理手段功能中,是固守刑法的事后法、保障法的功能和边界,还是追捧刑法前置对社会治理的提前介入的刑事制裁扩张,将引发后置法可能挤占前置法的功能空间而兼具管理法、治理法之嫌的趋势,必将引发对社会治理手段配置的理性思考。常态性的社会治理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因社会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耐心而受到旁置。在这一现实可能性前,更应重视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和功能,从法律和事实层面摆正公共政策、社会管理及刑事政策、制裁手段的地位和层次,建构社会治理的长治目标。犯罪治理中犯罪预防的二元结构战略和策略体系,则应在社会治理中得到重视和应用。
社会治理;刑法前置;刑事制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代化进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此外,国际社会安全局势日趋动荡,街头犯罪、暴恐犯罪、生态安全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形势极为严峻,因此,社会治理也更趋于注重效率和效果。一个最显著的表征就是刑法对社会治理的干预功能明显增加。出于社会治理效率的迫切要求,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中,国家也趋向于频繁运用刑事制裁手段这一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由此,刑事制裁扩张逐渐显现,更是引发了对刑法前置化的讨论。其中,“刑法过度化”“风险刑法”和“治理型刑法”等命题和模式成为刑法前置化争议的议题。这些议题反映了对社会治理手段配置的合理性和长效性的思考与检视。因此,关于“刑法过度化”“治理型刑法”以及“风险刑法”对社会治理干预的讨论,均反映了对社会治理手段的理性配置及功能的追问:是更大限度地倚靠刑事制裁手段,推动刑法突破在社会治理中固守的边界;还是理性分配社会治理的手段及功能,建构社会治理科学、长效的治理结构,从显性和隐性两方面发挥治理功能的作用,这是当今社会治理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刑法前置:刑事制裁扩张理论基础的纷争
刑法前置是指相对于刑法传统属性而言的,在社会治理中,刑法突破了其二次法、事后法的界限,提前介入到社会治理中。其特征是将犯罪行为事后性惩罚的启动提前,并扩展到危险行为的预先判断中并给予制裁。这种突破传统刑法功能的前置理论,将导致刑事制裁手段的扩张,即社会治理中过多地启用刑事手段进行治理。这些变化势必带来对刑法固有属性的突破,而对刑法前置有争议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风险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流行和影响。相对应的,它分为风险刑法和治理型刑法。该分类主要与风险刑法及治理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及功能有关。
(一)关于风险刑法
风险刑法最早始于风险社会理论肇始下的刑法应对问题。自从德国社会学家马尔里希·贝尔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人们逐渐认同他所阐述的“这恰恰是因为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等方面的各种风险——在我们当今的世界里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着”[1]这一风险社会概念,并深受其理论的影响。风险刑法则是相应于风险社会而提出的刑法理念,最早由德国刑法学家乌尔金·德·赫伊泽尔根据风险社会的概念对“刑法与风险”的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至此,“风险刑法”这一概念逐渐流行开来。根据风险刑法的要素,刑法应从传统的相对保障自由视角转变到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的方向上,即将定罪标准前移到实现有效预防犯罪风险行为,实现风险社会下刑法的转型。因此,风险刑法也被称为“敌对刑法”“对立刑法”。正因如此,社会治理中如果确立风险刑法或过多强调刑法的提前介入、 扩大犯罪圈等方式而加大刑事制裁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力度,增强刑事制裁手段介入到对新型危害行为的预测中并赋予犯罪化处理运用的功能,从而引发刑法前置带来刑法边界的变化将可能牺牲刑法本身“最后法”属性的担忧。有学者指出,风险社会要求刑法由传统的罪责刑法向风险社会中的安全刑法转型,注重事先预防,维护社会的安全秩序。但是,我国当前刑法立法坚持结果本位的立场,恪守传统的罪责自负原则,过度追求法典化的做法都与上述理念不相适应,导致刑法难以有效规制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危险犯, 归责的范围过于狭窄,在应对风险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显得被动、滞后。也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诸多技术上的难题,如行为的危险难以认定,危险结果无法预见,传统因果关系的证明无法奏效等,使得立法本身存在局限性。[2]22更有学者指出,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多样性, 要遏制这些风险必须采取综合的防范措施,不能过分倚重刑法。刑罚只是一种相对单一的风险应对方式,且只是一种次要手段, 其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风险社会, 刑法仍然只能担当以保障人权和弘扬法治的价值为基础的 “最后法”的角色,若以刑法为急先锋来遏制风险,非但不能实现社会保护的功能,反而会牺牲社会及其成员的权益、丧失人权保障的功能。因此,刑法乃至作为刑法灵魂与核心的刑事政策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2]23至此,一度风靡的风险刑法理念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其通过对危险犯的提前介入进行的制裁,则可能难以实现刑法作为保障法的本质作用,这一点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二)关于治理型刑法
治理型刑法的提出、发展与治理理论的兴起密切相关。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而管理分为统治型和治理型两类,治理型与统治型的区别在于:统治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本身,而治理的着眼点是整个社会。[3]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叶,当时一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空前的社会危机之中。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统治式行政已不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需要一种新型的行政理论来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在此背景下,治理式的行政理论便应运而生。因此,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在对政府、市民社会与市场进行的反思及西方政府改革的浪潮中产生的。尤其自1989年世界银行就国际社会危机问题第一次提出“治理危机”,并提出“良好治理”的制度框架以来,治理一词在公共行政领域便渐渐流行起来,逐渐形成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界的发展已渐臻完善。 关于治理的定义,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 《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的界定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该报告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或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因此,治理理论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的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不单单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寻求一种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因此,治理理论不仅对我们重新界定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体制转型阶段的社会治理具有很大的理论启示作用。在治理理论基础上,社会治理则是一个没有上下关系,只有平等互动关系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或认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所以,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基于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之上的合作。而这一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我们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基本理念,它进一步强化和支撑了社会综合治理的理论基础。
治理型刑法概念借用了治理理论中治理与统治这一对概念,将刑法的基本理念划分为治理型刑法理念和压制型刑法理念。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压制型刑法完全排斥了民间力量对刑事冲突的解决,容易形成与民间法的对立,国家垄断了刑罚权,压制型刑法下容易滋生重刑主义;治理型刑法则将刑事冲突权分出一部分给社会组织,将治理犯罪扩展到化解社会矛盾、积极预防犯罪中,甚至实现犯罪预测的可能性。[4]依据治理型刑法的理念,刑罚权的唯一性将被突破,部分刑罚轻刑权也可放入到社会组织中。因此,治理型刑法的理念是将刑事法律中法的功能辐射到社会治理的具体事务。在治理型刑法理念下,传统刑法固守的边界将被突破,包括将习惯法引入到刑事冲突的解决中,以及社区矫正和刑事和解制度等纳入到刑事程序中等。这一理念如果盛行,将可能把刑法改造为治理法或管理法,其结果同样会突破传统刑事法律的功能边界,刑事制裁将完全工具化。
由此来看,无论是风险刑法还是治理型刑法,所积聚的是刑法前置的治理决策的理论模式。在该模式下,刑事制裁手段将得到进一步扩张,它将导致社会治理手段的结构和功能面临重新定位和调整,刑法的“最后法”性质和功能将产生新的变化。即便如此,刑法前置理论仍然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否能得以坚守。*所谓谦抑原则,一般是指立法者在范式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得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时,就不必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谦抑原则追求的是在启用刑事制裁手段时,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应。实际上,刑法的谦抑原则体现的是刑法适用的有限性、迫不得已性和宽容性,是“冰冷的刑法为人类捧出的一鞠同情之泪”。如果刑法某项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时,则该项制裁性的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由此可见,刑法谦抑原则的提出进一步维护了刑法的最后法和保障法的边界和功能。从人类社会法律史的发展角度来看,谦抑原则的确立也是刑法从对社会治理的无所不包到退缩为一个突出特殊治理手段的法律部门,最后固守在最后法界定的发展过程中。因此,在社会治理中,是助推刑事制裁手段的扩张,还是坚守刑法应有的谦抑原则,*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即:“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依据。故而,那种将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法并不可取。既关乎刑法自身的定位和突破,更是现代社会治理中对刑事制裁手段理性分配及功能认识的重要问题。
二、社会治理中的刑事制裁扩张与理性配置
刑法前置理论和实践在社会治理中呈现为刑事制裁手段的扩张,即刑法启动前移,也被称为泛刑法化,在犯罪学领域也被称为犯罪圈的扩大化。其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并未遵守与其他法律及社会规范的界限,替代传统前置法如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而先行介入到治理中。刑事制裁因其介入到更多的具体事务或纠纷中,因而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治理手段的角色。具体而言,即从惩罚实然犯向未然犯扩张,从启动结果危害行为介入到危险犯的抽象化介入,并过多地涉入行政和治安处罚圈中,也被称为对行政处罚和治安处罚等非刑事制裁圈的侵入。
刑事制裁扩张化在当今世界也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联邦和州两级刑事司法系统中都有实体刑法的明显扩张和刑法惩罚名称的增加。在1997年至2006年期间,英国刑法就新创建了3 000个罪名。[5]此现象也说明,当今社会在选择社会治理手段上比过去更多地依赖刑事制裁手段。应当说,这一趋势的呈现并非偶然。刑事制裁的扩张与当今世界严峻的犯罪形势尤其是社会安全受到的严峻挑战有关,包括恐怖主义犯罪、生态安全犯罪、食品药品犯罪、公共安全犯罪等现象激增密切相关。这些犯罪都亟待社会投入更多的力量进行整治,并期望得到尽快的遏制。由此,运用刑事制裁手段治理而产生的短期快速效果引起关注。但同时新的问题也在出现,即刑事制裁治理手段的扩张将可能在社会治理上重蹈刑法万能主义、工具主义以及重刑主义之路。刑法万能主义在社会治理中把刑法塑造成消防员的角色,屏蔽掉其他部门本该承担的职责,容易导致一些管理部门的“惰政”。因此有学者担忧,刑法将被动地充当消防员的角色,但凡社会出现险情,人们总是在第一时间想到刑法介入,热切希望并坚信刑法能化解一切。重刑主义和犯罪圈的扩大就会随民意肆意侵入刑事法治实践。[6]实际上,“刑法对外行人来说通常是法的全部,但它绝不是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法的最重要部分”。[7]刑事制裁仅仅是法律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系统本身,是所有其他一切法律背后的制裁措施。在此基础上,刑法的任务本质上是发挥辅助性的法益保护功能,是保护法益的最后一种手段。刑法万能主义的蔓延将导致刑法工具主义的强化,而在工具主义的运行中,重刑主义则是其无可避免的宿命。这一逻辑链接,更提示了对刑事制裁手段和功能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应有清醒的认识,重视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的理性分配。必须承认,刑法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刑事制裁则是重要的治理保障手段,其在社会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刑事制裁的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首先是治理主体,同时它又是整个治理体系实施的最后保障。任何抽离刑法和刑事制裁的社会治理,其治理目标将无法得到保障。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刑法的参与应如何理性地摆正位置,并最终提供正当性支持和功效,是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和功能设计的重要任务。
纵观近些年来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社会治理已开始过多地倚重刑法的介入,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在刑法修正案中。自1997年重新颁布刑法典以来,刑法修正案已达9个。值得关注的是,在修正案中新增罪名多达30余个,且新增罪名多集中在对经济秩序领域和社会管理领域犯罪行为设定上。有些新罪名纳入到刑法处罚的制裁行为甚至早于行政性处罚和治安性处罚规定之前。比如对酒驾、飙车等引发的交通肇事行为的处罚。刑法将这类行为直接入刑,是刑事制裁扩张的最典型表现。又如,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新设罪名,属于扩大犯罪圈,将一些本该可以纳入到经济法规调整的纠纷予以犯罪化,如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行为。在实践中,两类行为划定界限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如果草率地升格为犯罪,既是犯罪圈的扩大,也为社会制造了更多的犯罪人,对社会治理显然不利。又如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其立法宗旨为运用刑法介入治理前些年频发的群体性讨薪事件及矛盾升级导致恶性犯罪。但现实中处理劳动纠纷的程序规定实际上已较为完备,当事人本可以根据劳动法进行处置。当然,可能因等待解决的时间周期较长,纠纷僵持化,当事人一旦失去耐心或解决环节受阻,容易引发劳资对立的群体事件或恶性报复事件的发生。但将该类行为直接升格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给予刑事处置,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负面效果:一方面,罪名的设立似乎是在保护劳动群体而处置资方,认为将资方入罪即可化解纠纷,其实这只是一种急功近利且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一旦资方入刑,讨薪者的讨薪目标也很可能跟着落空。如此一来,第三方介入甚至政府管理部门的斡旋也被排除。一旦讨薪者陷入无薪可讨的困境,便有可能转而求助政府管理部门并形成新的纠纷或事件,如此又何来治理呢?其实,该类矛盾如果先与行政和市场管理及政府干预有序地衔接起来,对欠薪可能引发的纠纷冲突的预防和疏解更为有效,而一味地倚靠刑事制裁扩张的治理手段以扩大犯罪圈了事的方法并非根本的治理方法。
上述案例也反映在近20年的刑法修正案进程中。提前介入社会管理这一刑法前置化趋势正在逐渐形成,刑法正逐渐蜕变成社会管理法的一部分。这一趋势的发展将会为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即在社会事务中出现矛盾或纠纷,人们习惯倚靠刑事制裁手段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矛盾双方彼此对立,何来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呢?因此,对运用刑事制裁的手段承担社会治理任务亟须建立理性分配的设计理念,树立科学的犯罪观、刑罚观,摒弃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追求,而不是一味地依靠启动刑事制裁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当今就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目标而言,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合理的治理手段功能的分配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作为刑事制裁手段的适用范围应界定在犯罪这一行为范畴中。而犯罪是寄生在社会中的一种病理现象。在现代的犯罪观中,犯罪现象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法律现象,尤其是当今身处法定犯时代,犯罪的界定和犯罪圈大小的决定通常与国家决策者的立场、观点密切相关,其代表的是当政者的刑事政策立场。因此,有学者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犯罪现象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贪贿犯罪、税收犯罪、法人犯罪、计算机犯罪、环境犯罪等法定犯和白领犯罪等在犯罪现象中占据多数,于是,自从加罗法洛将人类社会的犯罪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即认定犯罪以来,*犯罪学历史上的犯罪分类是19世纪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提出的。他将人类社会的犯罪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犯罪两大类。自然犯罪指的是传统的对人身或私有财产的犯罪,如暴力犯罪或盗抢类犯罪;法定犯罪则是由统治者制定的在自然犯罪之外的类型犯罪,多与统治者的统治意志与统治秩序及利益密切关联。犯罪史由原来的自然犯时代过渡到了法定犯/行政犯时代。而法定犯时代则是犯罪问题的政治化时代,因为,犯罪对策已成为公共决策中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领域,*参见赵宝成《法定犯时代的犯罪对策——解决犯罪问题的政治之道》,见《2006年第三届犯罪学论坛论文集(上海论坛)》第31-36页。良好的社会政策将起到有效的犯罪预防和治理的效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犯罪对策上是否就意味着频繁启用刑事制裁手段这一问题也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应予纠正。
其次,社会治理涉及各个方面的管理和治理而非仅有犯罪治理内容,而刑法在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和方向是单一的,即运用刑事制裁手段开展对犯罪的治理。在这里我们要辨明的问题是:刑法能否在社会治理中完成预防犯罪这一主要任务或成为主要主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社会其他治理主体的功能又将如何体现?笔者认为,在解答这些问题前,应当先厘清刑法本身的功能。在刑法学术传统及现代刑法定位上,刑法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处罚犯罪并起到事后对犯罪的惩戒作用,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也就是通过刑事制裁手段来制裁犯罪从而达到使犯罪人不能犯、不再犯以及威慑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犯罪预防的目的。其中犯罪人接受制裁而不能犯罪是刑法特殊预防的主要功能。*虽然我国刑罚主要针对行为人设计。除辅助型刑罚以外,以及少数被适用死刑,大部分犯罪人领受的刑法多是监禁性惩罚,刑法通过剥夺犯罪行为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其行动自由,使犯罪人不能犯、不敢犯。这一功效与刑法本身的滞后性密切相关。犯罪发生后,刑事法律才能启动程序通过追缉、起诉、审判、定罪及最终犯罪人领受刑罚而进行治理。这一治理功能及特征并非一般的管理类治理,而是国家设定的运用刑事制裁进行的强制性治理,是最后迫不得已的特殊治理手段。因此,作为刑法最重要的功能之法律保障法,刑事制裁是对前置法即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最后保障。前置法体系是以授权、管理的内在功能来规训人们的行为规范,一旦前置法未能奏效,后置法即最后法的刑法才能启动。这一本质功能凸显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10大类罪中。*《刑法》规定的10大类罪对应的正是前置法体系规训未能奏效时的保障和保证。正因如此,如果刑法作为后置法在社会治理中一旦取代前置法,其功能将发生变化,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的有序性也会受到冲击,其所设定的功能必将受到影响。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和功能及手段应是有序和有层次的,每一个要素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作用,要素之间相互配合、支持并构成有机的整体。因此,手段的设定与分配与该治理体系的结构相互建构。过于强调某一部分手段和功能甚至以此取代或减弱其他手段,将影响整个有机体的运作和功效。社会治理应使各有机体能动协调运转来达到总体目标。尤其是其他机体并未发生重大调整时,“越界和混搭”显然难以达到治理目标,甚至会减损整体治理效果。比如前述的欠薪治理,笔者认为,对该行为的治理可以依据如下治理程序:欠薪权利主体依据劳动法规定的权利由主张调解主体的介入而进入仲裁诉讼。具体而言,在对这类行为引发的纠纷及治理中,各治理体系的功能启动程序为:欠薪发生后,由企业内部或工会启动劳动法规;追讨无果下劳动仲裁或诉讼启动;调解、仲裁或第三方包括并不限于诉讼机关调解并无果;启动行政处罚(剥夺从业资格、破产清算或个人财产连带责任);一旦前面程序未能奏效,纠纷升级引发犯罪——刑事制裁启动——同时国家予以救急性救济(启动企业保证金或专项资金),同时国家鼓励部门追讨。如此一来,既及时平缓了讨薪者的对立情绪并使其获得暂时的救助,同时,对欠薪者给予一定的时间和机会救赎其法律上的过错,各有关管理部门也在其中发挥管理和调解功能,最终达到对欠薪导致的群体纠纷的预先治理。在这一程序设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刑法依然起到了威慑性治理作用,并固守了最后保障法的功能和边界。如果在该治理中刑事制裁过早介入,则挤占了社会调解和行政管理部门的功能空间,排斥了治理体系中本应发挥作用的其他手段的空间和渠道,事件双方对立情绪也难以消除。
由上述案例可看到,具体的社会治理所启动的主体应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功能是理性配置的基础和前提。在配置结构上,首先是社会层面的非诉程序,非诉手段的常态化更会助推社会和谐的建设。其次才是国家层面的司法途径。可以说,刑法前置带来的必将是刑事制裁的扩张,是社会治理缺乏耐心和恒心的表现;同时,也折射了我国在民法、经济法及行政等机制上的缺位及乏力。但在现实中,一旦某项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时,国家通常习惯倚靠刑法治理功效的一蹴而就。因此,理性配置治理手段则是当前社会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布局。
要摆正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位置,必要的前提是在治理理念上要与刑法工具主义、泛刑法化划清界限。刑法的过度化必将造成犯罪圈的扩大。应充分认识刑法对社会治理的工具性功能,它并非是社会治理犯罪的治本之道。当然,理性配置社会治理手段应当重视刑事制裁手段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定位和价值,如风险刑法理念下的刑事制裁扩张,其预设的危险犯的犯罪化,将本该化解为民事纠纷或行政处罚的行为人赶入犯罪圈里使其污名化,一旦污名化被行为人认同,就可能产生更多顽劣的犯罪群体,势必加重犯罪治理和预防的压力。又如治理型刑法一旦越位,将刑事制裁手段扩张到社会日常纠纷的治理中,将纵容刑法万能主义的肆意妄为。当然,也要防止墨守成规和故步自封削减刑法在犯罪预防中的功能和效率。
三、犯罪学的犯罪预防体系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手段
犯罪治理一直是犯罪学在犯罪预防中的核心要务,也是社会治理中犯罪预防的积极主体。虽然在犯罪学的历史中,由于传统犯罪原因理论与犯罪对策的相互限制,犯罪预防仅作为犯罪原因理论的对应性回应,未能建构较为独立的犯罪预防体系和手段。直至20世纪70年代,人们针对传统的犯罪原因理论在犯罪预防上的无能为力,设计出具有使用价值的犯罪预防理论和策略。犯罪预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策略手段上终于实现了突破。使犯罪学对社会治理而言,从单一的犯罪发生源治理和预防发展到复杂犯罪行为发生源的二元解构体系,这一发展丰富了社会治理中的犯罪预防理论和手段。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情境预防理论和方法的创立。该理论与方法所建构的犯罪预防体系和具体措施手段的设计,奠定了犯罪预防策略和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和地位,也促使犯罪预防从隐身于犯罪原因的对应性回应中脱颖而出,成为治理社会更为科学和有功效的战略和策略手段,因此被率先践行在当前制度性的犯罪预防中,成为重要的犯罪治理和预防主体。
当前,随着社会对犯罪预防的应用性理论和模式的重视和接纳,犯罪预防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围绕情境预防的犯罪控制模式的兴起,犯罪预防被赋予了更为实际和迫切的应用价值期望,犯罪预防的基础理论及模式日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运用在犯罪预防的实践中,一些阻断犯罪行为生成机制的治理模式被广泛应用。比如:在当今社会治安的立体措施中,无论是摄像视频的街面治安控制,还是逐渐在各项政策设计中的犯罪预防理念,包括在建筑设计中要求的环境犯罪预防的要求等,都是犯罪学的犯罪预防策略和手段的现实践行。犯罪预防的理念和技术还被企业的合规管理所接纳。这里值得警醒的是,虽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境预防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措施受到追捧,但犯罪学在理念上应坚守初衷,即一个完整的犯罪预防体系和手段才能成为社会治理犯罪的利器并起到总体效应,而非某一部分理论或措施。
犯罪预防应坚守初衷。在社会治理中要实现对犯罪治理的最终目标,应始终围绕犯罪发生的二元结构展开。既要重视犯罪发生源的预防和治理,又要重视对犯罪行为发生环节的破解,两者的结构层次是有序递进的。犯罪发生源与社会运转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而犯罪行为的环节则更多地与个体和环境因素有着较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要达到对犯罪的治理和预防,两者不可或缺。另外,还需要注重对犯罪预防治理体系中手段的合理配置。所以,犯罪治理的根本是从宏观和微观的社会层面对可能促使犯罪发生的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同时需要进行深入的原因研究,用科学的理论破解来自于犯罪发生源的各个因素,给出改善社会管理的良药。在手段上,运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和教育等方法与手段阻断犯罪发生源的生成环节。比如,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保障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失业犯罪的累积源;运用教育政策的制定实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杜绝未成年人失学现象的产生,预防因失学而游荡在社会并成为不良成长环境的受害者,达到治理和预防犯罪后备军的积聚和生成之成效;社会福利政策的科学、合理制定则能更大限度地治理因贫困而产生的困境性犯罪等。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应高度注重廉政制度的设计,消灭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腐败犯罪生成的土壤;在二元犯罪源的行为结构破解上,用更为务实的理念设计具体犯罪预防策略,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各个环节进行破解。尤其是当前,犯罪预防的实务手段因大量运用情境预防中的犯罪热点时间、热点区域及环境预防以及犯罪地理学的具体方法手段,已在对街面犯罪的治理和预防中取得一定成效。
因此,就社会治理中的犯罪预防而言,治理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对犯罪的治理,更多的是展开对犯罪的预防。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提出将对社会的综合治理理念和要求当作一项重要的社会治理战略。根据这一战略,对社会的治理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级组织。所适用的手段囊括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行政等各个方面。在我国社会治理中,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犯罪治理成了整个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因此,我国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分别呈现不同特点。首先,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在社会某个阶段呈现犯罪高峰或某类犯罪高峰时启动的社会治理模式。从“十年动乱”结束时开展的第一次“严打”,到改革开放30余年来进行的各项犯罪治理专项任务,说明运动式治理仍然是我国具有本土化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对短时间遏制犯罪的高发或骤发有立竿见影之功效,是我国在犯罪治理中最常用的应对性犯罪治理手段。其次是常态化的犯罪治理,即建构社会层面的综合力量对犯罪进行预防和治理。尤其在经过30余年的发展后,社会综合治理在近年来更为细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战略目标更是折射了国家对这一社会治理战略的坚持和发展。在治理的结构层次上,更趋向于对治理手段的理性配置。如:我国在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对反恐主体的界定就突破了传统的将反恐限定在司法主体职责唯一性上,该法将反恐的责任主体扩大到了各级政府,使反恐的权利、义务完整地落实到了综合治理的法律关系中,使反恐法兼具了行政法和司法法的综合性法的属性。而反恐法的颁布,实际上对于社会治理过多倚重刑法的犯罪治理工具作用进行了回应。所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如果单一追求刑法前置,彰显刑法万能主义,只能将刑法推到消防员式的尴尬角色中,从而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和投入。同时也应看到,即使以治理为前设,在治理型刑法框架中,刑法兼具治理法、管理法功能的前提下,刑法工具主义也必将带来社会治理手段的机械、刻板以及人为的犯罪圈泛化,社会可能耗费更大的治理成本。而将刑法设立为民生刑法,同样会产生诸多的司法隐患。首先,其他法的退位和旁落会改变刑法的最后法和保障法性质;其次,势必造成刑法大肆侵入民生法体系中并取而代之,而刑法本身的强制性和暴力工具等本质属性,也不会因介入民生法而改变,为此出现高频率地适用刑事制裁的定性和手段的运用,大量本可通过平等权利法关系解决的矛盾,被人为地升格为犯罪法处置,势必对民生民怨的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作为社会治理中最后保障和最强硬法,理顺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及作用,是对社会治理科学理念建构和践行的重要前提。当前,以犯罪预防为目标的现代社会治理,最根本的目标是对犯罪发生源的消减。该目标任务的实现,不能一味地倚靠刑事制裁手段,而应启动和建构立体的社会法治网络。
首先,应重视立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尤其在当今时代,公共政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应给予充分重视,“好的公共政策能够起到刑事政策所不及的化解犯罪问题的功能,即将犯罪问题化解于无形”。因此,要想真正有效地解决犯罪问题并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标,一是政府必须善于运用良好的公共政策。因为,对化解社会矛盾来说,每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密切相关,“良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政府层面,重视公共政策对犯罪治理的功效,尤其在涉及民生、社会福祉的政策制定时,应注重社会公平和利益统筹兼顾,减少社会矛盾易积点;在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政策,应强化、细化政府管理和治理的行政职责,建立严谨的职责追责体系,而非倚重刑法和制裁来化解风险,尤其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安全的公共政策和事务中,严格的工作制度和科学的公共政策能够对法定犯罪时代的犯罪类型起到积极的预防和治理功效。二是密切关注并审视刑事政策走向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在治理策略手段上,避免因刑法泛化而造成的刑事制裁扩张的趋势;在刑事立法上,则应尽量避免制造更多的刑法前置内容,妥善处理刑事制裁的过多介入与社会治理其他结构的冲突;创立新罪名应审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评价。三是要通过立法和执法,更多地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加强民法对社会治理的功能手段,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强化对义务的履行。
其次,在对犯罪治理手段上,重视建构和强化犯罪预防的实务模式以达到犯罪控制和治理的目标。在犯罪预防上,以重视和强化国务院提出的社会综合治理五个“网”的建设为目标,继续发展和建设情境预防的技术措施和手段。尤其是环境犯罪预防理念和设计、犯罪地理学对犯罪热点的聚集模型的应用,以及犯罪情势制图技术的推广,必将使犯罪治理的应用效果得到提升。现实中,犯罪学的犯罪预防手段也得到了警方的高度重视。一些犯罪预测和犯罪热点制图已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重要手段,这些探索和实践必将进一步夯实社会综合治理立体网络的建设和发展。
[1] 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J].社会学研究,2010(5): 208-231,246.
[2] 方芳. “风险社会与刑事政策发展”学术综述[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1(1): 21-25.
[3]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年)[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5-17,159.
[4] 苏永生.治理型刑法理念之提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切入[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4-60.
[5] 何荣功.社会治理“过渡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J].中外法学,2015(2):523-547.
[6] 高铭暄,曹波.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J].法学评论,2015(3):1-9.
[7] 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3):126-139,206.
(责任编辑:魏琼)
Means and Functions of Rational Alloc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On the Expansion of Criminal Sanction
YUE Ping
(SchoolofCriminalJustice,Shanghai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1701,China)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expansion of criminal sanction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 is a hot issue in current social governance. The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in recent years have increasingly reflected behavior regulation and mediation over social economic order and management order, an obvious indicator of advance intervening of criminal law. Among the mean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governance, sticking to penalty after consequences thus guaranteeing the functions and boundaries of laws or pursuing the expansion of criminal sanctions by advance intervening of criminal laws over social governance triggers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the appropriate allocation of the means of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normal principal part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multi-polarized means may be weakened as a result of social eagerness for quick success and instant benefits and lack of patience, it is all the more important to highlight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the means and functions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essential to put in the right places the positions and levels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management and criminal policies and the means of sanctions in order to set a long-term goal for social governance. The dualistic structure of tactic and strategic system of criminal prevention in the criminal governance should be underscored and adopted in social governance.
social governance; advance intervening of criminal laws; criminal sanctions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02
2016-07-02
岳 平(1959- ),女,内蒙古赤峰市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法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D035.29
A
1007-6522(2016)06-0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