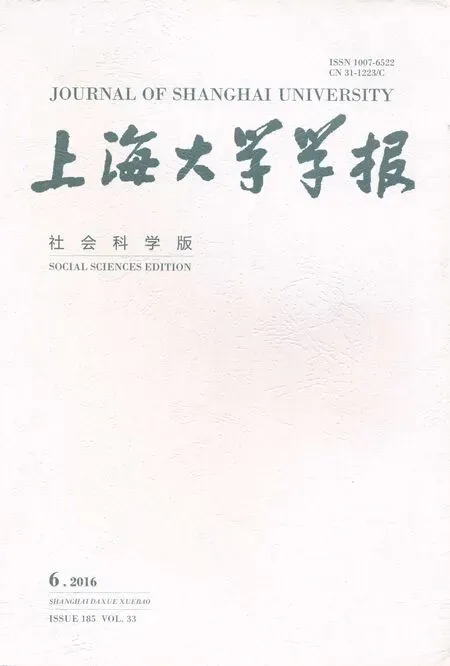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刘 笑 言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062)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刘 笑 言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062)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家庭;家庭政策;现代国家;权力
杜维明曾在其经典著作《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中提到:“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发展的速率,发展的前景及动力;另一个是承受力和对伤害性的防御能力。”[1]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不仅仅要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动力,一种足以抵抗前进“后坐力”的社会防御能力同样是不可回避的政治议题;国家前进得越快,“后坐力”越强,对社会防御力的要求就越高。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在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一系列问题相互磨合中形成了对现代性的认知,政府、宗教团体、社会组织与家庭一起承担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建设同步进行,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被动地接受了作为西方现代化建设成果的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等概念。遗憾的是,尽管它们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意识形态,但在东亚社会却并没有其发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渊源。由此而导致的近百年国家发展事实是:一方面我们接受独立自主和高举人权的现代话语体系,试图在国家建设中妥善处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多数副产品留给不属于公共领域的家庭;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在家庭议题上左右摇摆,或赞成或否定其与政府、社会和市场三个领域间的权力边界,以免家庭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累赘。[2]
然而,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现代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家庭包括经济支持、生育抚育和情感抚慰等传统功能的相应弱化,这几乎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当然,这也是家庭功能不断转换、调试,进而适应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都在发生着变化,两者变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经济与文化发展速度与效率的配合,也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外在“干涉”。然而,由于工业社会将家庭严格界定在私人领域范畴,现代国家所代表的政治权力在家庭问题上始终小心翼翼。与传统政权下国家对家庭关系、家庭道德赋予强制性的政治规范不同,现代国家更倾向于从家庭功能入手,着力于以分离、共担或者转移家庭事务的方式来间接影响或塑造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这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称之为“家庭政策”。家庭政策的产生,是现代国家与家庭不断进行权力博弈的结果。也正是协调家庭内部有效关系的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国家大量干预家庭生活的依据” 。[3]在与家庭的不断碰撞与磨合中,国家权力与家庭权力之间的边界日趋形成,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家庭政策类型,其在各自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为现代国家构建出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关于家庭政策更为详尽的讨论请参考Joan Aldous, W.A.Dumon & Katrina Johnson. The Politics and Programs of Family Policy: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s.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80;Sheila B. Kamerman, Alfred J Kahn. Family Policies: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Fourteen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Shirley L. Zimmerman. Understanding Family Policy. California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Inc.1988;Linda Hantrais, Marie Letablier. Families and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Press. 1996;Gabriel Kiely, Valerie Richardson. Family Policy: European Perspectives. Dublin: Family Studies Centre. 1991.
一、“消失的家庭”: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权力界限
在大多数现代政治学教科书中,家庭通常是无足重轻的,因为它不属于“公共领域”,更不是政治问题,它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小部分” 。[4]通常来说,现代政治常被认为是在一致与冲突之间达成相对平衡的动态过程,这一政治发展的理性中心主义分析路径奠定了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却共同忽略了作为社会系统核心要素的家庭、性别和其他私密关系在政治体系中的价值和意义。而事实上,家庭是社会建设的根基,也是其所有制度性建构的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对家庭的讨论,必须首先将其视作一切政治价值的源头,明确导致“家庭”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消失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原因,是工业时代以生产性劳动为主、非生产性劳动为辅的制度建构。这种制度建构包括普遍性的贬低生育抚育等照顾活动为基础的教育(文化)体系,习惯性逃避承担家庭照顾责任的雇佣工作(经济)环境,以及长期剔除私人领域等自然繁衍现实的政治逻辑。所以,所谓的“家庭消失”,只不过是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在剔除了前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之后的过程性事实,是公民权利、资本利益和国家权力相互博弈的动态结果。
伴随避孕技术的推广和工业时代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女性(早期主要以工人阶级为主)实现了身体与经济上获得独立的可能,这也意味着传统上建立在性别分工模式下的家庭结构日益瓦解。[5]更为严重的是,与其相关的传统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等维持早期工业社会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要素也日趋瓦解并逐渐消失。
首先,家庭关系重构。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首先带来了家庭劳动与工业劳动之间的分离,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陆续转移到城市之后,为了赚取工资并改善家庭生活,城市工人家庭的夫妻与亲子关系遭遇破坏重组。“家庭过去是学习和传授知识与本领的所在,孩子从父亲和祖父那里学习技术,而技术变化在那个时期是很缓慢的。机器出现以后,不需要在家里学习了……用不着去请教长辈了。”[6]549同时,在妻子为了家庭生计走进雇佣工厂的同时,家庭中传统的夫妻关系(至少是女性的经济从属关系)也被打破。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将更多的女性输送到工厂中,工人妻子一方面无暇照顾家庭;另一方面社会所鼓励的资产阶级家庭道德越来越得到工人阶级的认可,虽然家庭事务被天然地视作女性的工作,但不仅资产阶级的妇女尝试将家庭事务交由佣人去做,工人阶级的家庭也将家务事通过花钱转交他人完成,并以此视作其事业成功的表现。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随着子代和女性的独立,传统的亲子和夫妻关系发生了转变,但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对公民家庭事务给予财政和制度上的支撑,长时间社会保障措施的缺位导致家庭内部的亲族网起到了很好的凝合家庭成员关系、相互帮扶支撑的作用。“这说明,虽然夫妻关系处于危机之中,而家庭作为不同代人的组织,仍然是牢固的。”[6]580所以,在家庭关系中,即便横向的夫妻关系面临瓦解,但由于国家对家庭事务支持力度的缺乏反而促进了纵向亲子关系因为得到重构而相对稳定。
其次,道德观念的瓦解。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价值理念,在瓦解传统家庭中父亲权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女性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所以,一方面,多样化的家庭,如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同居家庭等不同形式的家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家庭形式和传统家庭道德;另一方面,女性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独立进一步冲击着过去建立在传统性别观念基础上的伦理规范。相对于传统上以异性恋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多元化的家庭不断充实人们对于家庭概念的理解,家庭关系的重构进一步瓦解并不断冲击着既有的家庭道德观念。
毫无疑问的是,对于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现代政治体制来说,面对家庭遭遇的变化,国家能做的是有限的:它既不能强制性地规定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关系遵循既定轨迹,也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家庭道德进行规范——只要公民行为没有因伤害他人利益而触犯法律,国家权力就必须严格被限定在那个没有“家庭”的公共领域之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家庭事务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迈进,已经成为家庭与现代国家关系发展变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不仅避免了国家权力僭越既有的公私边界,又实现了国家权力影响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的目的。毕竟,家庭事务所遭受的系统性贬低是工业社会迅速发展的结果,在家庭作为社会组织形式越发变得不再稳定的过程中,国家需要保护家庭维持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在对如何干预家庭事务的价值判断上,各国之间仍旧存在差异,这直接导致当前社会上三种不甚相同的家庭政策模式的出现,在这三种政策模式下,作为政策效果的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二、划定边界:家庭政策的三种基本模式
家庭政策是国家对家庭事务进行干预的基本尝试。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利益连带是通过家庭政策建立起来的,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是国家对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的塑造,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则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家庭政策的不同表达形式中,国家与家庭的权力该如何划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对理想家庭的定位,也关系到国家建设的社会空间容量,即国家发展的社会耐受力。
(一)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国家与公民的经济契约
这种模式是工业社会发展初期和当前新自由主义国家主要认同的家庭政策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将家庭事务大范围地推向市场,通过市场配置的方式“由赚取薪酬的雇员来承担” ,[7]54以使私人领域的家庭活动进一步职业化。“这种配置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路径,区别仅仅在于它将传统上属于公共领域的基本原则重新应用于私人领域。”[8]将家庭事务转向市场空间是将家庭照顾活动的商品化过程,这种措施在很多国家的工业发展初期都有不同形式的应用,大体包括家务劳动的市场化以及托老育幼措施的国家货币支持手段。这一政策模式的另一特点是,政府提供基本照顾服务的前提,要求政策受益者必须是具有雇佣身份的公民,其所获福利的多少取决于个人在职业角色中的贡献多少。社会保险计划是这一家庭政策模式最通常采用的措施,它在减轻公民因意外或市场失灵状态下的家庭经济生活质量方面有着关键性保护作用。当然,在这一政策模式下受益者均需具备最低限度的职业角色,这是公民获得国家帮扶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因此,这种家庭政策模式具有典型的经济契约特征,国家与家庭成员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不必要借助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位。
美国是家庭事务分离模式特征最为典型的国家,这一政策模式在美国经济发展早期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将家庭事务市场化,虽然在形式上使家庭事务走向了公共领域,但事实上,其自身的家庭属性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因为国家不需要与家庭建立直接的关系,导致其各项政策措施在巩固家庭关系方面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和持续增加的单亲家庭始终是美国社会的顽疾,“那种为我们所稔熟的家庭形象——有丈夫、妻子和子女只是少数家庭的形式” 。[9]同时,美国文化中对“依赖”状态的深恶痛绝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种以否定“依赖”为主的政策理念“结束了福利是应得的权利、政府有义务为所有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救济的历史,使救济从原来的无限制的终身福利变成有限制的临时福利”。[10]这也促使美国家庭政策与欧亚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倾向于将家庭成员视作彼此独立的个体所达成的共同生活契约人,而任何依赖于国家福利资源的家庭成员都在政策层面难以得到认同。*如“贫困家庭短期援助”( 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TANF) 项目是美国政府现行的主要针对拥有未成年子女或怀孕妇女家庭的短期福利援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美国对自由主义和独立精神等基本价值概念的信仰,尽管经济契约式的家庭政策并没有在事实上促进家庭组织的成员关系和道德凝聚力,但美国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的整体稳定性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在美国国家发展的整个大的脉络中,家庭更准确地说是扮演了一个共同体的角色,其中每一个具有自主权利的美国公民根据自由意愿达成的共同生活协议,国家与家庭之间界限清晰,互不侵犯,且国家权力在走向家庭的过程中早已被市场空间稀释和溶解。
(二)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合作
这一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通过政策手段最大限度地干预并承担家庭事务,国家对家庭成员提供保护并扮演家庭照顾活动的最终责任人。政府通过税收等方式调控家庭成员在家庭事务与职业角色之间的平衡状态,帮助公民在两种角色之间顺利地转换,而无需因为雇佣工作而否认家庭事务的重要价值。弗雷泽曾经强调,这一方法并无意将家庭事务转嫁给市场,而是承认它们的社会价值,并“将大量的这种工作保留在家中,通过公共基金对其提供支持” 。[7]59很明显的是,在能够提供多项优越福利制度的国家体系中,政策的最终受益者无需是雇佣劳动中的职业工作者,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就能够保证获取特定额度的国家支持。而家庭,只是在国家与公民合作的过程中扮演一个载体和媒介的角色。
瑞典是家庭事务共担模式最典型的国家,其家庭政策的制定源于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这也是很多北欧国家的共享价值):每一个公民,无论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如何,也无论其婚姻状况如何,都被赋予基本的获得政府补助的权利。在此基础上,瑞典家庭政策的整体规划均是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直接作用展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婚姻和家庭作为传统社会制度的基础制度形式,逐渐因为其政治功能遭遇“架空”而日趋衰弱。
虽然从政策动机上来讲,瑞典政府尝试通过由国家扮演“保护人”的方式在家庭事务方面开展多项社会福利计划,如政府重点资助的公共育儿系统和双亲离假计划,国家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家庭关系和纯粹的道德模式,例如“母亲在生育之后休18-24个月的双亲假照顾儿童,然后返回工作,并将儿童送到公共儿童照顾机构中” 。[11]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瑞典家庭政策的本意是为支持家庭,而其最终的政策后果却起到了分解公民家庭角色认同的作用。对瑞典公民来说,家庭并不具有基础性的功能性构成地位,国家通过家庭政策成功地将个人从家庭与市场中分离出来,个人既不是家庭的人,也不是市场的人,而是与国家通过社会为载体直接开展合作的公民。国家权力跨越传统的公私界限,取代了除情感抚慰之外的大部分家庭功能,这不仅令家庭的存在感降低,也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三)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国家与家庭的政治联盟
与以上两种家庭政策模式截然不同的是,家庭事务转移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在于:家庭事务被全部留在了家庭。这一模式并不着意于解决照顾责任在家庭、国家和市场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地将家庭事务从国家和市场的发展轨迹中转移出来,并最终将其全部留给家庭,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市场调配和社会支援等手段支持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这种以家庭为照顾责任主体的政策模式在东亚地区有着扎实的社会文化基础,其现实版本来源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开始于“二战”后的家庭建设过程,也内含于东亚文明对家庭责任和传统性别观念的深刻认同语境里。在东亚诸国与家庭相关的所有政策中,一个最根本的定位依然是东方传统的家庭价值取向,即认为照顾活动应当是家庭功能的首要内容,强调“国家不应该取代家庭去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只有在家庭功能无法正常运转的时候,国家、社会或者市场才应当参与进来,帮助家庭及其成员回归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轨道。政策的受益者不是公民个人,而是家庭整体。Aurel Croissant曾经指出,东亚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相对于欧洲福利国家而言是十分“省钱的”,它是建立在其“稳定的传统家庭结构和持续性的青年劳动力供给”[12]基础之上的。
近年来,很多东亚国家开始陆续推行各种支持家庭功能正常运转的社会政策,虽然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张个人奉献精神,个体应当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家庭事务转移模式的家庭政策在东亚社会中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予以呈现:以职业角色为前提对家庭给予援助,公私共担的资金支持以及强化亲缘的政策帮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东亚社会始终坚持着“家庭”对养老和育幼的独立责任,家长(早期通常为男性)对家庭成员的生活和家庭的整体生计往往承担着无法推卸的义务。要维系家庭功能的正常运转,家庭成员必须投入到大范围的雇佣劳动中,这种对职业角色的期待也符合东亚社会自20世纪开始的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与此同时,传统性别分工在东亚社会中的广泛市场也构成家庭(特别是女性)独立承担照顾事务的文化基础。根据日本卫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家庭调查报告》(National Survey on Family),日本20-30岁的已婚女性认为她们应该待在家里专注家务活的比例从2003年的35.7%上升到了2013年的41.6%,同时,将近三分之二的年轻已婚女性认为应该等到孩子三岁以后才能恢复工作,同样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女人在拥有第一胎后放弃了工作。日本、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这种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东亚社会的家庭成员之间所具有的强大的情感凝聚力,再加上长幼有序的亲子关系和男女有别的夫妻关系,家庭事务得以在家庭内部有效运行,国家似乎并不需要过多地涉足家庭。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东亚家庭强大的自我运转能力支持着东亚国家的发展。因为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被动”现代化对经济迅速发展的渴望是一种国家权力主导的变革路径,而国家不愿、也没有能力为家庭事务买单。然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的存在前提也是它的基本困境,国家政治话语以传统文化为价值依据,将家庭事务留在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之中,而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却在践行源自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念,两者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消化。由此而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父亲权威的丧失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共同导致东亚家庭关系处在随时可能失衡的不稳定框架之中;另一方面,传统的家庭道德在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着不断的破碎重组。正如汪晖教授曾经指出的:亚洲的历史认识是被建立欧洲式“现代国家”的目标所牢牢地限定的,与对国家概念的理解相同,人们对于家庭的理解也始终无法摆脱对所谓西方话语体系的“崇拜型”认知。但与此同时,东亚国家在接受西方对家庭议题的理解的同时,既没有稳健成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又缺乏性别平等和个人权利的价值底色。从理论上看来,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而言,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对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的保护是比较完整的,然而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这种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可以良序运行的“家庭”,却时刻扮演着东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盟友”,其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捉襟见肘,日渐式微。
三、家庭式微:一种难以摆脱的界限魔咒
东亚社会的家庭承载了比西方国家更多的职责,家庭不仅仅有义务照顾未成年子女,亦有责任照顾老人,更是长期扮演了社会文化的核心价值追求和制度载体。与此同时,由于家族主义与宗庙意识在东亚社会传统中的核心地位,以世俗主义为价值主导的家庭政策往往将国家发展、社会建设以及经济调整所伴生的一系列问题习惯性地推向家庭,家庭的高效配合进一步帮助并促进了东亚国家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然而,这种建立在传统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家庭政策模式却在21世纪以后逐渐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在面对养老育幼过程中的乏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更多女性走向劳动力市场,繁重的工作压力和现代社会节奏的加快促使传统社会由家庭所承担的生产、消费、生育抚育、性满足、经济和情感支持功能逐渐外移和淡化。东亚各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在调整家庭政策过程中去试图解决这些现实性的问题,但东亚社会所固有的结构性难题却愈发显现出其顽固性,东亚家庭曾经的制度和文化优势愈发转变为无法摆脱的内生困境。
(一)个体的消失与再现
在东亚社会文化中,鼓励个人自强不息、不断奋斗的人格特征已经成为社会的文化底色,公民习惯并且乐于接受关于国家的略显沉重的“创业发展史”,大多数人也愿意为国家或其所在集体的强大做出贡献,这一切可能都主要归功于东亚国家早期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以日本为例,“日本员工对于自己所在的公司有强烈的认同感……即便在日本经济紧缩时期,日本男人依然觉得他们应该效力于公司,时间不能被私人生活所侵占” 。[13]5这种愿意自我奉献的工作价值观点固然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快速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与此相伴而生的则是个体权益在庞大的集体主义面前整体消失,且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越来越弱的耐受力。这在职业女性群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当西方现代思想传入传统的东亚社会,职业女性自我实现的愿望觉醒,这意味着原本建立于女性自我牺牲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难以在新形势下获得合法性存在空间。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自己能够在公共雇佣空间中获得足以安身立命的职业身份,而在诸多不利政策的条件下,东亚青年职业女性们更倾向于选择在完成学业(通常为大学以上)之后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推迟婚姻,推迟甚至拒绝生育。因为在现存东亚家庭政策环境下,职业女性、已婚、有子女,这三个条件相加意味着女性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加大,自身生活水平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降低。“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大学并获得好的工作时,中断职业生涯选择回家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就会不断增加。”[13]5与此同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们不再认同女性天生需要依附于男性,对于传统文化中有关女性美德中的包容、服从和为家庭做出牺牲的观念也难再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女性个体的再现作为资本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引起了东亚各国的高度关注,女性缺乏进入传统婚姻的热情注定了东亚很多国家超低生育率的现实,这使得各国纷纷在近二十年来制定有利于兼顾两性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家庭政策。
与此相应的是男性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变化,遗憾的是这种变化并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人们常常习惯性地认为东亚社会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发展模式,然而在早期国家建设的工业化宏观叙事背景下,作为公民主体身份的男性与女性共同成为集体主义的牺牲品,区别仅仅在于女性是在家庭领域,而男性则是在公共的就业空间。由于国家对家庭承担大量社会、经济和文化责任的高度期待,东亚社会中的男性公民通常被作为家庭生计的主要承担者肩负着全家生计的使命。同时,由于东亚社会普遍认同长时间的雇佣文化,人们对男性的评价也倾向于更为认同其在工作领域中的表现,而其家庭角色却常常被人所忽视。纳加伊曾经指出:“在日本社会,配给给男人从事家庭建设的时间几乎没有。”[14]在ISSP的权威调查中,日本男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是56小时,当然这有着劳动用工制度上的原因,但深入到社会价值体系中鼓励勤奋工作的理念已经在无形中塑造了日本公众的偏好和习惯。与此相应,根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对27 492名20-65岁劳动者进行调查的《韩国劳动环境调查(2011年)》分析结果,韩国男性的工作时间也普遍存在超时、过量的现实,其中以30多岁的高学历人士更为严重。在高强度工作的雇佣文化中,东亚女性虽然面临着十分不利的个人发展局面,但并不意味着男性个体并没有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压抑。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报道,韩国女性在家庭管理上花费的时间是男性的4.7倍,其中虽然强调了女性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双重负担,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韩国男性作为个体与其家庭的疏离,这无论对女性还是对男性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家庭对于两性个体的个人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种“亲家庭”的生活方式可以给家庭成员带来与工作环境不同的轻松舒缓感受。而东亚社会中的男性,虽然在东亚崛起过程中作为群体得以呈现,但无论是工业化迅速崛起的经济发展时代,还是逐步进入后工业化的社会建设时代,男性作为个体而言,却远不如女性一般得以出现在国家建设和家庭发展空间,男性个体的全面发展需求,被一种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所淹没。
总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亚社会传统上崇尚个人服从集体,鼓励个人为国家利益作出牺牲的文化正在一点点淡化,经济能力和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增加了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所有公民群体自我实现的需要。针对这些变化,各国不断调整着适应本国现状的家庭政策举措,但以平衡公民家庭和工作双重困境为出发点的政策形式似乎在改变两性关系的路径上作用十分有限:一方面是女性结合自身发展状况进入公共雇佣空间,凸显了女性以个体身份“出现”的难题;另一方面是处于工作状态中的男性同样难以获得回归家庭空间的正当理由,男性作为群体虽然大范围地出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其作为个体“消失”的权利也同样被国家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需求所绑架,并最终被剥夺。
(二)夹缝中的家庭
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性别分工模式一度保证东亚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数十年长足发展,在无需过多照护老幼病患的国家体制内,政府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快速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国家向第一世界的角色转变。但由于长期承担着国家发展的社会成本,家庭在东亚社会已经十分疲惫,其传统上可以发挥的功能也正在一点点消退。虽然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现实,并辅之以强度越来越大的家庭支持力度,但由于惯性使然,政策措施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落差依旧存在,两者的张力依然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作用于社会机理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当前东亚国家对于家庭政策本身的工具性态度:或者将其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或者将其作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供给单位,或者将其视作政党竞争的政治筹码,或者将其作为世俗社会建设的文化根基。纵然方式方法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家庭政策的制定从未因为家庭本身,家庭与国家之间权力界限不清,使得家庭始终挣扎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角逐之间。
战后东亚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保障之一就是传统而稳定的家庭结构。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纷纷制定了以一种类似于“家族主义模式(familialistic model)”为主体的社会福利制度,即在对作为家计负担者的男性成员给予丰厚职业酬劳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家庭辅助政策肯定女性作为家庭照顾者的主要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不同时期的家庭政策形式是有所不同的,其主要依据则是结合各自国家发展的不同利益需求和政党政治的驱动。尽管东亚各国在战后纷纷制定了有利于公共就业空间的性别平等法令,但其家庭政策却并没有脱离家长制传统,无论政策法令中对于女性基本权益有怎样的论述,婚姻中的女性被作为家庭照顾活动的核心力量而得到来自文化和制度两方面的“保护”。“日本国家政策的独到之处是把女性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即个体的女性和已婚的属于家庭的女性。国家对这两类女性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参政权和劳动权所突出的是作为个体的女性,即已经成年的女儿,不被丈夫抚养的妻子,或者说是成年单身女性;而一旦结婚,进入家庭的女性则是另一种形式、另一种内容的保护。”[15]这种稳定的以传统性别分工为主的家庭结构有利于战后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仅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在这种以亚洲传统性别分工为主体的家庭结构中获得了早期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和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市场中的企业成为职工全家生计的基本来源,更加鼓励了职工的奋斗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亚洲金融危机重创了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模式,企业开始纷纷削减用工成本,大量雇佣无需为其承担额外家计和福利支出且报酬低廉的临时工、计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年报》统计:21世纪以后,日本非正规就业人数逐年上涨,从2002年1 451万人增加到2008年的1 760万人;而正规就业人数则从2002年的3 489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3 399万。“非正规就业者工作极不稳定,收入低,工作时间长,缺少福利保障,生活易陷入困境,工作和生活的冲突问题表现得更为严峻。”[16]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鉴于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职工的薪资水平和家庭负担日益加重,为更好地渡过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公民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家庭政策开始逐渐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与此同时,以“公私共担”为载体的社会保险式家庭政策形式在维护东亚社会一贯“反福利”主张之外,也为社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女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也为本土经济催生出一项刺激内需的服务产业。另一方面,在东亚社会长期快速发展的经济绩效面前,东亚国家执政党政府通常习惯于将经济发展与政府绩效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但经济发展的放缓,公众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得东亚社会公众对自身福利制度和家庭可持续发展更加予以重视,21世纪的东亚国家逐渐关注建立和完善家庭政策体系也体现了政党迎合选民需要的竞争策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伊始就将其对公民家庭的保护和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立国之基,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颁布符合国情的家庭政策举措。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公民家庭的重视,但无论是新加坡,还是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进入21世纪之后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居于国际末位,他们对家庭的“重视”及其颁布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在对改善低生育率现状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中国是东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与其他东亚国家相类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也同时面临着比其他东亚国家更为严峻的文化社会问题。如果说一个完整有效的家庭包括家庭关系、家庭道德和衔接两者的家庭事务三方面内容的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户籍制度的桎梏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已经不断地改变着中国家庭的基本概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的家庭结构变迁、家庭功能弱化、家庭关系松散以及家庭道德的瓦解,已经从根本上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构成持续性的负面影响,其主要特征在于:横向的夫妻关系与纵向的亲子关系同步弱化,家庭关系无法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状态;家庭道德遭遇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严重冲击,不仅无法在公共领域扮演传统的价值支撑角色,甚至在家庭内部也日益丧失了其本应具有的尊严;家庭事务的安排从被政府大包大揽,到不合时宜地抛向市场,再到今天向家庭内部的全面收缩,国家权力与中国家庭之间似乎很难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在国家与家庭之间普遍缺乏界限感的情况下,家庭永远都无法摆脱被国家裹挟的命运。
四、结语
家庭,是一个可以跨越地域限制并超越文化壁垒的人类共同的生存事实。伴随着家庭政策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推上政治舞台,中国各界对家庭政策的探讨和争论也愈发热烈。一部分学者热衷于对欧美家庭政策体系进行讨论,也就是文中的家庭事务分离或共担模式,希望我国的家庭政策可以从市场化或者政府主导的经验中获得借鉴;另外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对东亚地区经济发达国家家庭政策问题的研究,也就是本文中归纳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因为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与东亚诸国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事实上,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数十年来,其所施行的具体家庭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具有家庭事务转移模式的特征,而其对市场化的政策倾向也保留着家庭事务分离模式的痕迹。然而,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在几种政策模式中,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家庭事务转移模式是对家庭关系和家庭道德保护得相对最好的政策类型,但伴随西方现代观念的涌入和东亚本土文化在现代政治语境中的相对“弱势”,家庭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系中日益丧失其本来拥有的核心地位。
家庭,是东方文明之根,它为我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文献,且今天仍是我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本要素。家庭政策已有多种模式,我们尽可取百家所长。但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家庭政策过程中,一个基本理念值得我们共同守护:找回家庭,不能仅是将其作为整合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或推动国家进步的制度和价值基础,它不应再因为自身具有的任何工具性价值而获得存在意义。相反,我们找回家庭,只是因为,这是家。
[1] [美]杜维明. 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6:97.
[2] [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美]加里·贝克尔. 家庭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36.
[4] [美] W·古德. 家庭[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4.
[5] Laslettp.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
[6] [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 家庭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3.
[7] [美]南茜·弗雷泽. 正义的中断: 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8] 刘笑言. 走向关怀: 性别正义视阈下家庭政策的理论模式比较研究[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36.
[9] [美]M·赫特尔. 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75.
[10] 何欢. 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J]. 清华大学学报, 2013(1):147-156.
[11] Central Policy Unit,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Family Policy[R].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8:165.
[12] Aurel Croissant. Changing Welfare Regim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risis, Change and Challenge[J].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04,38(5):504-524.
[13] Boling Patricia. 人口、文化与政策:解读日本的低生育率[J]. 南方人口,2011(3):1-9.
[14] A Nagai. Marriage for Social Recognition and Subsequent Married Life[J]. Social Science Japan, 2005(33):6-8.
[15] 王立波. 日本家庭主妇阶层的形成[J]. 社会, 2004(10):48-51.
[16] 胡澎. 日本在解决工作与生活冲突上的政策与措施[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0(12):100-104.
(责任编辑:周成璐)
Back to Family: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tates
LIU Xiao-yan
(DepartmentofPolitic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Famil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ountry. Accompany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e family affairs originally attached to private areas gradually come to the public space. Family policies are basic means of intervening in family affairs by modern countries. The core issue is the power boundary between families and the State. Nowadays, there are three models of family policies: family-affair separation model, family-affair sharing model and family-affair transfer model. The first two models have weakened family’s own value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 the family-affair transfer model widely adopted by East Asian countries try to blur the power boundary between family and the State, identifying families as the nation’s political allie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ization, family-affair transfer model also faces double predicaments: first, there is a deepening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awakening sense of rights and the collectivistic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nation; second, East Asian families are playing a waning role in the competition for power with the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family; family policy; modern States; power
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6.009
2016-05-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4YJCZH10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4EZZ003)
刘笑言(1984- ),女,吉林蛟河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性别政治学、家庭政策与社会治理等。
C913.11
A
1007-6522(2016)06-008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