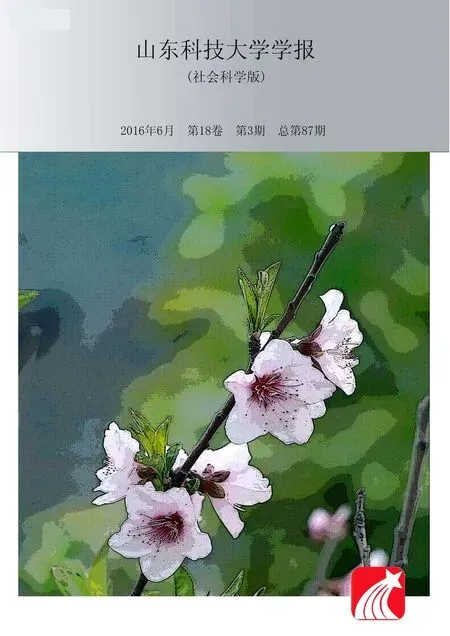王星拱两种比较独特的科学方法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100049)
王星拱两种比较独特的科学方法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北京100049)
摘要:王星拱对科学方法论素有爱好和研究,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科学方法论的专著,其中提出了两种比较独特的科学方法:一是综合和推较,二是权量、分类和例外之应付。
关键词:王星拱;科学方法;综合;推较;权量;分类
王星拱(1888~1949)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化学家和哲学家。他早年留学英伦,主攻化学专业,对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亦甚感兴趣。学成归国后,他受聘北京大学化学系讲授化学,兼开科学方法论课程,并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科学方法论》——这是中国第一部科学方法论专著。此外,他在《科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一些文章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到科学方法。本文拟集中讨论他的科学方法论的两个比较独特的科学方法。
一、论综合和推较方法
王星拱所谓的综合(他也称其为“普遍”)和推较(他也称其为“比论”),今日译之为或称之为“概括”(generalisation)和“类比”(或“类似”)(analogy)。他在论述这两种推论方法时说:“科学之价值,在能用已知推论未知,用少数经验的现象,推论多数未曾经验的现象。这样的推论,有两个方法:从分个推论到共总,叫做综合,从此分个推论到彼分个,叫做推较。这两种推论,都是从观察所得的若干同点,推论其他的同点,不过在综合里边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同点之彼此的因果的关系,在推较里边,我们尚不知道这些同点彼此关系若何。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是自狭而广,自少而多,所以我们推论所得的知识,都可以算得新的。”他紧接着把演绎法和归纳法与综合法和推较法进行比较,得出它们均是或然的结论:“纵然就演绎法而言,自共总推论到分个,似乎是自广而狭,自多而少,换一句话说,演绎中之结论,已包含在大前提之中,不能算得新的了。然而从大前提之构造的时候,到我们用这个大前提来推论的时候,其间中词(Middle term)所代表的对象,谁能保证没有变迁呢?所以我们用普遍的定律去推论分个的事实的时候,必须擅定小前提中之客词,和大前提中之主词,是完全同一的,然后才能得一个一定的结论。试问擅定是怎样讲呢?就是拿不知的当做知的计算。这不知的不能算得新的吗?再拿我们常引的极端的例子来说:由每日太阳必出的定律,而推论明日太阳必出,我们必须擅定明日太阳之情境和从前构造此定律时所观察的太阳之情境,是完全同一的;由凡人皆死的定律,而推论某某必死,我们必须擅定某某之情境,和从前构造此定律时所观察的人之情境,是完全同一的。不过在这样的推论之中,过去的经验如此之多,这擅定之危险极少,所以这推论之假定的性质,也因之而减至最低度。至于综合之推论,虽有因果律为凭,然而我们必须擅定每次的因,是完全同一的,才能构成一个普遍的定律。若后人用这个定律去推论分个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完全保证它,不过这个定律,可以作他们的指导罢了。这样看来,在演绎的推论之中,我们擅定现在所推论的分个,和从前所观察的分个,是完全同一的;在归纳的推论之中,我们擅定将来所推论的分个,和现在所观察的分个,是完全同一的,都不过是或然的。至于推较,不过在两个对象或两个现象之若干同点而推论它点或者也有同的,那更是或然的了;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因果的关系的缘故。”为了厘清综合和推较之异同,他进而利用字母代表性质,加以条分缕析:综合和推较,都是自物或现象之同点而推论其他同点,至于此物或现象仍有异点,并无碍于推论之进行。在综合之中,同之外延大而内包小;在推较之中,同之外延小而内包大。譬如有一物,其性质为A、B、C、D;又有一物,其性质为A、B、E、F;又有一物,其性质为A、B、G、H。若将来发现一物,其性质中有A,则我们可以推论其性质中亦必有B,或另有他项性质xy,并不牵涉到这个问题。这叫做综合。又譬如有一物,其性质为A、B、C、D、E,又有一物,我们已看见其性质为A、B、C、D,则可推论此物亦必有性质E。这叫做推较。康德说:“有一(性质)在多(物)中,则此一(性质)亦在凡(物)(Eines in vielen,also in allen)”,这样的推论,叫做综合;“有多(性质)在一(物)中,则其余(性质)亦在此一(物)中(Vieles in einem,also das übrige in demselben)”,这样的推论,叫做推较。综合之凭借,在同之举例之多(外延大),推较之凭借,在同之切入之深(内包大),但是这二个之区别,也不过是等级的问题。同之外延小的,必有内包来补偿它,同之内包小的,必有外延来补偿它。然而论它俩确切的价值,当以综合为较高。[1]141-144
在这里,王星拱的观点直接继承了马赫的思想(见《认识与谬误》第十三章“作为探究的主导特征的相似和类似”)。马赫“把类似定义为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其中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对应的要素是不同的,而要素之间的对应的关联是相同的”。[2]238他这样描绘类比的内涵:“相似(similarity)是部分的等同:相似的对象的特征是部分等同的和部分不同的。一个对象的单一可观察的标记不需要与另一个的重合,可是一个的诸种标记可以与另一个的诸种标记以严格相同的方式相互联系。杰文斯称类似(analogy)是更为根深蒂固的相似;人们可以说,抽象的相似。类似可能在某些环境中依然完全向直接的感官观察隐蔽着,只是通过比较一个对象的标记与另一个对象中的相应关联之间的概念上的相互关联,才揭示出类似本身。麦克斯韦不仅定义了类似,而且也强调了它的对科学探究来说是最重要的特征,当时他把类似描绘为一个领域中的定律与另一个领域中的定律之间的部分相似,以致每一个都可以阐明另一个。”[2]239他使用字母加以说明,以使人们方便地把握类似的真谛:“如果对象M具有标记a,b,c,d,e,另一个对象N就a,b,c而言与它一致,人们倾向于期望它将在d,e也一致,这一期望在逻辑上未受到辩护。逻辑仅仅保证与被固定的东西一致,只要把它保留下来,这就不能遭到反驳。不过,我们的期望依赖于我们生理的和心理的组织。出自相似和类似的推断严格说来不是逻辑的事情,至少不是形式逻辑的事情,而仅仅是心理学的事情。若上面的a,b,c,d,e是直接可观察的,则我们涉及相似,若它们是标记之间的概念关系,类似则更接近正规的用法。如果对象M是熟悉的,那么对N的考察将通过联想使我们想起与所观察的a,b,c并列的d,e,倘若d,e是无关紧要的,这便终结了该过程。当d,e具有强烈的生物学的利益时,因为它们具有有益的或有害的性质,或者它们对某一应用的或纯粹科学的及理智的意图特别有价值时,情况就不是如此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不得不寻求d,e,以密切的注意力等待结果。这将借助简单的感官观察,或借助复杂的技术的或科学的概念反应而达到。无论结果是什么,我们还将通过得到相对于M的新一致或新差异,扩大我们对于N的知识。两种情况同等重要,都包含着发现,但是就一致而言,我们具有把一贯的概念扩展到较大领域的更加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我们对寻求一致特别热心的原因。”[2]243-244马赫在这段话里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类比不是逻辑证明的工具,而是科学发现的利器,不管类比的两个对象的标记一致还是有差异。
马赫十分看重类比方法在科学探究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相似和类似的考虑在几个方面是扩展知识的富有成果的动机。一个还相当不熟悉的事实范围N,可以显示出与另一个比较熟悉的、直接的直觉较为可以达到的事实范围M的某种类似:我们感到立即被驱使以思想。观察和实验在N中寻求与M的已知特征或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应的东西,通常这将揭示出关于N的迄今未知的事实,从而发现这些事实。即使我们的期望受挫,我们发现了N和M之间的未曾料到的差异,我们也不是劳而无功:我们最终更充分地了解N,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它的概念上的把握。促动我们使用假设的,恰恰是简单性和类似的这种吸引力:假设使我们的直觉和幻想活跃起来,从而激发有形的反应。此外,假设的功能部分地被加强和被砥砺,部分地被消灭,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他对类比方法的巨大认知价值洞若观火:自然的探究者“对类似的注意大大推进了他的工作”;“并不缺乏类似重要性的例子;事实上,在自然科学中怎么高估它都不算过分。”[2]244-245
与马赫相比,王星拱似乎有点小觑了类比的价值或威力——类比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也许高于概括,起码也是旗鼓相当。要知道:类比是扩展知识的富有成果的动机,其有助发现的价值怎么高估都不为过(马赫);类比是从已知通向未知的必由之路(彭加勒);类比是价值无限的事情——智力经济和发现的方法(迪昂);类比是科学认知尤其是科学革命中概念变革的助产士之一(库恩)。尤其是,“科学中的类比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主要关注的不是表观的、质料的相似,而是深邃的、形式的或结构的相似——两个事物或现象的结构是同构的,或者描述它们的方程形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主要关注形式类比而不是实质类比,尤其是科学发展到高级阶段即理论化阶段之时。”[3]因此,尽管类比推论不是证明,而是或然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应低估类比作为科学方法在科学发明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宣明的是,王星拱没有意识到或者忽视了批判学派关于类比方法的精髓——马赫尤其是彭加勒更看重的是深奥的、数学形式的类比,而不是表观的、物理现象或物质性质的类比。例如,彭加勒就这样写道:“原始人仅仅知道粗糙的类比,这是些给感官以印象的类比、颜色或声音的类比。他们从来也不可能梦想到光与热辐射类似。是什么东西教导我们从这些眼睛看不见而理性却能够神悟的、真正的或深奥的类似呢?这就是轻内容而只重纯粹形式的数学心智。”[4]92
王星拱进一步阐述综合的意义和分类:“综合有两个意义:一是自事实之归纳而构成定律,一是自较少普遍的定律而归并于较多普遍的定律。”[1]144对应于前者,是所谓的逼近的综合(Approximate generalisation)。其公式为“多数x皆为y”[2]145-146。在社会生物等学之中,此种逼近的综合甚多。然须得同时研究,去解释那个少数的“不”。这个少数的“不”,叫做负号的举例(Negative instances),或叫做例外(Exception)。若能解释这些例外,则此逼近的综合,变成普遍的定律。由千头万绪的事实之中,构成一个定律,不是便易的事体。若是不能解释这些例外,也须得把它明白表示出来指示后人一个研究之途径。这样方法,对于大公的共同的科学之进步,最有利益。若是能造统计表而计算之,则可用百分数,去代替逼近的综合。关于定律之构造,首先须寻出同点之因果的关系。既寻出确切的因果的关系,即令到了我们观察不能底试验不能及的地方,我们还可以推论它。不过这样的综合,推论到观察试验所不能及的地方,必须保持实证的精神,立两个限制:(一)因果的凭借须确切,(二)推论的阶级不能过多。对应于后者,这就是所谓的分个之综合,是从貌似无涉的定律,看出它的深根的同点来,归并于一个更为普遍的定律之下。综合之价值在于,“每次综合,都在科学进步上加一个头衔。”[1]146-147尽管如此,王星拱还是提醒人们:“我们又不能贪综合之美名而陷入于急促的综合(Hasty generalisation)之弊途。人类原有好作综合之癖性,往往从不多不确的经验之中,未能理解因果的关系,而遽作综合的判断。这样的判断若载在著述之中,最为科学进行之障碍物。……所以培根说:‘我们的智慧,无须再加翅膀,但须有铅锤做个坠子,使他缓慢的进行。’朋加烈(“朋加烈”今译“彭加勒”,作者注)说:‘古人综合,我们现在笑他以不同为同,我们综合,谁能知道我们的子孙不笑我们以不同为同呢?’综合之好处虽多,但是要谨防误入迷途啊。”[1]148稍早他还这样写道:“宇宙之根本的真理,总只有一:各科学,各方面所研究的,原有彼此之处,然我们确切之经验不够,断不能作早期的普遍(hasty generalisation)。”[5]
王星拱接下来阐述了推较的意义:“推较也有两个意义:一是,一种没有充分的证明之推论,二是,暂系观念之贷品。凡我们研究现象,若是不能得其因果的关系,只能拿已知的现象和未知的现象之同点,两相比较而推论其他的同点。但是对于这个推论的结果,我们若是把它当作证明,那是极其不充分的。我们若是把它当作假定,那就当设法再去做试验以证明它,这倒是引导发明之好方法。”他提出估计推较的或然数的三个条件,因为拿推较去推论,其结论的或然数是很低的,就这个很低的或然数之中,若欲定其高下,须用以下三个条件去考察它:(一)同点之数目愈多,同点之重要愈大,则推较之或然数愈高。(二)同点之数目愈少,同点之重要愈小,则推较之或然数愈低。(三)所推论的未知点愈多,则推较之或然数亦愈低。推较另有一个意义即暂系观念之贷品,也就是记号的假定。“大凡我们觉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必须将此现象联合于一个相似的已知的现象,然后用观察或试验去研究他,才能走到发明的地位。……假如有一现象,和已知的现象毫无同点可寻,则欲研究此现象,除乱碰外,别无他法。乱碰既不是正当的方法,则凡欲研究一现象,惟有从推较入手。无论其同点若何的微淡,我们总须利用它作个起点。所以注重‘创造的智慧’的人。对于推较之价值,极力增加。……推较之动作,直是引导发明之无上的工具。不过我们须得把他当做研究之起点,不能把他当做结论之终局才不至于陷入唯心的组造(Mental synthesis)之危险哪。”[1]148-151
王星拱最后总结道:“推较和综合之区别,也不过是等级的问题。二者都是取二以上的现象之已知的同点,去推论未知的同点。不过综合中之同,广须多于深,推较中之同,深须多于广。故从多数现象之中之少数同点而推论它同点,叫做综合。从少数现象之中之多数同点去推论同点,叫做推较。综合之中,有时同点虽少,而可以推论,是因为我们须得寻出同点之因果的关系的缘故。推较的条件较宽,所以推较在证明的方面,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在发明的方面,就当‘名列凌烟’了。”[1]151他在此前还提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复原方法就是推较方法:“历史所记载的事实,往往缺而不完,就此缺而不完的事实,首先须从各方面,考察他们本身真实不真实。至于未曾记载之事实,须用复原(Restoration)之方法求之。复原之方法也不外乎推较——就是用现在的事实,推较古时的事实。”[1]90
二、权量、分类和例外之应付
在其他科学方法上,王星拱也有值得一道的见解,其中包括权量、分类和例外之应付。为此,他在《科学方法论》中针对这三个论题各自专列一章,足见对它们的重视。在本文的最后一节,我们拟简洁地加以评介。
关于权量,王星拱洞察到:“物理的科学愈发达,分量的权量愈精确;分量的权量愈精确,预测的本领愈高,而且发明的机会愈多。因为有许多微细的现象之区别,非精确的分量的权量,不足以表见出来。……要得这样精确的权量,不是我们的器官所能奏效的,必须有仪器来辅助它。所以在科学之中,一个新仪器的发明,往往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因为我们人类工作的进步,原于裸体的智慧的,远不及原于人为的方法的,和原于人为的材料的之多。然而精确的权量,也不能本身独立,必定有算学的理论同时并进,相辅而行。在理论的方面,有这样精确的预测,在实验的方面,就应该有这样精确的权量去证明它。”他进而指明:我们要求确切的权量,有两个必需的情境。一是界线之清晰,若是一事或一物的两端,浑沌不分,则权量甚难确切。二是标准物和所量物之可等。有时我们把标准物的分量不动,而增减所量物的分量,使它俩相等。有时把所量物的分量不动,而增减标准物的分量,使它俩相等。至此,他给权量一个明确的定义:“什么叫做权量?就是设法使标准物的分量和所量物的分量相等,……就是寻觅一个标准物的分量和一个所量物的分量之中间的比例数。要寻觅这个比例数,不能不倚靠仪器来辨别它,因为我们的器官的辨别力有限,并且易生错误的缘故。……仪器的用处,能够叫外界的现象呈具易于辨别的性质,所以我们用器官去判断它,不至易生错误罢了。况且科学中的权量,渐渐趋入‘用空间的权量代替各种的权量’之途径。……因为空间的现象,易接触于知官,而空间的观念,又易成立于精神界的缘故。”[1]50,53,54
具体到操作层面,王星拱罗列出拿标准物和所量物的分量相较可以采用的四种方式:主变式(变标准物的分量使之和所量物的分量相等)、客变式(变所量物的分量使之和标准物的分量相等)、共正变式(既乘标准物的分量又乘所量物的分量,使之低于公倍数时而相等)、共负变式(既除标准物的分量又除所量物的分量,使之低于公分数时而相等)。他还提到间接权量(有时所量的两个分量之间有一定的算学关系,知其一即可知其二)和权量之分序(有时所量物过多最好是先后其中取出几个详细量之以备后来权量他物之参考;有时所量物的分量,和标准物的分量,相差过大,我们可以在二者之中,取出一个承上接下的分量暂作标准以便计算)。王星拱注意到,在实际进行权量操作时,往往夹杂外搀现象,从而引起错误:“我们研究现象,理想的最好的方法,是每次提出一个现象出来而研究之权量之。无奈现象界不能应允我们的要求,每次送一个‘六亲无靠’的现象于我们之前,等我们详细权量它,所以这个目的,(每次提出一个现象而权量之)无论我们如何精巧,是不能完全达到的。从根本上说起,我们为什么要权量呢?是因为要寻出现象之因果的关系,而发明现象界的定律。既是要寻出因果的关系,最好是变换因的情境,而考求果的现象之变换。倘若我们能够每次变换一个情境,(没有他项情境与之俱变)以考求之,则试验并非难事。然而每次变换一个情境的时候,不能撇开少许外搀的情境之同时变换,所以结果的现象,也有少许外搀的现象杂在里边。这些外搀的现象,在另外一个范围之内,每每能供给发明之材料;然而从我们所要权量的现象的方面看来,这些外搀的现象,乃是扰乱的分子,就是错误的根源。科学既是要求真实,自然是要免除错误,纵然不能免除,亦必得把他减少到最低度。”为此,他介绍了杰文斯在物理学里所用的免除和减少错误的六种方法:免除(Removal)、常定(或译微分)(Differentiation)、更正(Correction)、赔偿(Compensation)、反覆(Reversal)、平均(Means)。[1]54-58,58-59,67,69
也许多少受到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第一章对事实分类的重视以及在最后一章对“科学的分类”的探讨之影响,王星拱在《科学方法论》中也专设一章讨论“分类”。他自问自答:“分类是什么呢?乃是依事实或对象之同点,在心理上集合的方法。何以说是心理上的集合呢?因为分类也同综合一样,包已知和未知而言。由综合而得的定律,我们可以推论事实或现象之有一定的同点的,都在此定律范围之下。由分类而得的类,我们可以推论事实或对象之有一定的同点的,都归属于此类。……分类也可以叫做综合之一种。不过依寻常的意义,二者是平列的,综合是从天然界的动的方面分析之,分类是从天然界之静的方面分析之。二者皆能拯救我们于繁复杂乱之中。由综合而知一现象之因,由分类而可置一对象于适宜的地位。这一层分类的功用,是希腊哲学家所最注重的。这样宗谱式的分类之观念,近来虽已打消,然分类之方法,仍为研究之必需品。而且依联想律而言,凡忆起一事物的时候,必有与此事物相同的,为联想之介绍,故分类又有可以提醒忆起之功用。然分类之功用,又能叫我们记忆我们所需要的。至于使我们记忆我们所需要的缘故,是因为当分类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性质,为分类之基础(Fundumentum divisions),可以表出同存的性质(Correlated or co-existent properties)。同是一群事物,因分类者之目的不同,可用不同的方法以分之。然而科学的分类,以能表出同存的性质最多的为最适宜。”[1]152-153在这段议论中,他界定了分类,而且是在与概括的对比中界定分类的,同时还胪举了分类的功能。他得出的结论是:“物之分类,为实在的或理想的排列,集其同者,离其异者,第一为表出彼此血统的关系,第二为表出同存的性质,第三佑助我们的心思,以领会及记忆此等物之性质。”[1]162
在论及分类之方法时,王星拱认为“可以分为演绎的和归纳的二类。自共总分至分个,叫做演绎的分类。自分个汇至共总,叫做归纳的分类。”就其一而言,“演绎的分类,又可以叫做理想的分类,或形式的分类。在一群之中,取一个重要的性质,为分类之基础。其一类为有此性质者,其一类为无此性质者。然后用两枝法(Dichotomy)逐层前进。每次前进,分一大类为二小类。凡被分的大类叫做属(Genus),凡分出的小类叫做种(Species)。然而在演绎的分类之中,属和种不过是对待的名词,属对于其上的大类也是种,种对于其下的小类也是属。以符号记之,在大类A之中,以B为重要的性质而分之,得AB和Ab两小类。再从AB和Ab两小类之中,以C为重要的性质而分之;得ABC和ABc,及AbC和Abc四更小类。”就其二而言,“归纳的分类,又可以叫做实在的分类,研究中所最常用的。当我们研究物之性质而类分之之时,若能尽得物之性质,层层往下分去,固乃是至好的。然而我们所知道的物之性质,是由比较和经验得来,不过是物之性质之一部分。若云以重要的性质,作分类之基础,则重要二字,究作何解,尚难有确定的意见,还是最显著的呢?还是最古的呢?还是最有因力的呢(Causally influential)?还是最能表出同存的性质的呢?即依上节而言,以最能表出同存的性质的为重要,然而彼可以表出此之同存,此亦可表出彼之同存。……科学愈发达,此种二类中间的过渡物之发现者愈多,而分类之界限,渐渐由天然的,而变为强订的。因为天然界中之万物,形如一树,我们所得接触而研究的,不过是它的一个横截面罢了。若是退而求其根,进而求其杪,并无类之可言,乃是一个永远动的变的推广的分衍的联续(Continuum)。”[1]156,160-161
在归纳的分类中,王星拱还列举了两个具体的方法——“列载的方法”和“表式的分类”(现似可译“诊断方法”和“类型分类”)。按照他的观点,天然界既是一个渐变的联续,凡不同的物,都有过渡物介乎其中,各物之性质又多。譬如有一物A,有一班性质与B同,有一班性质与C同,又有一班性质与它物同。所以我们分类之方法,须将被分物之所有的性质,通同记录下来而比较之。这是归纳的分类所必经的途径,又叫做列载的方法(Diagnostic method)。其同点多者置之距离甚近的处所,其异点多者置之距离甚远的处所。多数共有的同点,算作最重要的,例如植物子叶之单双,动物脊椎之有无,因为它能够作分大类的基础。少数共有的同点,重要较轻,例如猫之爪甲能伸缩,狗之爪甲不能伸缩,因为它只能作分小类性质,例如动物之脊椎,与其陆居、水居、肉食、素食种种习惯没有关系,所以较为重要,而可以作分大类的基础。至于齿爪,是和素食肉食有关系的,足鳍、肺、腮,是和陆居水居有关系的,重要较轻,只能作分小类之基础。因为愈与特别习惯无关系的机支,愈不易为环境所变迁,故纵而至于已灭的生物,横而至于遍球的生物,多数都具有这个性质。至于同存的性质,自当通同记录下来,以备将来辨物归类之辅助。归纳的方法,依以上所说的看来,若是欲达精密确切之目的,不是便易的事体,然而我们可以以下三层概括之:将所有的被汇的分个总集于一处,取其有同点者同归一类;同点愈多者集之,愈近异点愈多者离之愈远;有同点者,既归于一类,然后取他类之与此类异少而同多者又归一大类,如此上行,至最初的共总而止。表式的分类科学之中,有时因为类之界线不清,或分个过繁,我们可以取一个性质最简明的以为表式,而以其他分个之与此表式有一定的同点者,皆归一类。这叫做表式的分类(Classification by types)。表式之本身,也是一个分个。它分个之性质,决不能与此分个皆同;但是我们取此表式之若干性质作为标准,凡它分个之性质,有与此标准同者,即与此标准同类。依严格而言,表式的分类,不能算得逻辑的方法。然而为济穷取便起见,表式的分类,可以有简约之功用。表式的分类之价值,对于济穷一方面,是极大的,至少也可以算得有系统的分类之第一步。至于在试验的学习里边,更当利用表式的分类。[1]162-163,165-166
王星拱介绍分类的讨论时,从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分类的意义:“总而言之,综合和分类,都是从异点之间求其同点科学知识所以能够有系统,就是综合和分类的功劳,故有人以求同点于异点之间,为科学之起源。大凡我们察觉一个现象的时候,必觉得现在所察觉的,和刚才所察觉的,有异点,然后才能辨别这个现象(Discrimination)。然而我们若是仅能辨别这个现象,仍不过是得着一个负号的报告,无从推论其他点。所以必觉得现在所察觉的,和从前所察觉的,有同点,然后才能识定此现象(Identification)。既能如此识定,那就可以用已知而推论未知了。但是如此的推论,仍须试验来证实它,才能算得真实啊。辨别和识定,乃是人类智慧之活动之两大关键。异点之间的同点,乃是宇宙变迁中之旗帜,叫我们怎样用旧的去对付新的。”[1]166-167附带说一下,他在另处涉及知识分类或科学分类时,提出可以方法或范围作为划分的标准:“把各种学术下一个确定的界说,往往不是易于做到的事情。要下各种学说之界说,不外以各该学术所研究的范围,或其所使用的方法为标准。然而范围相同的,方法不必同;……方法同,范围也不必同;……概括起来,把大类动作之产品分为大类的时候,可以用方法为标准;凡用信从的方法者为宗教,凡用领会的方法者为文学,凡用实证的方法者为科学。把大类分成小类的时候,可以用范围为标准,凡研究有机者为生物学,凡研究无机物者为矿物学,凡研究物质者为化学,凡研究能力者为物理学。”[6]
“例外之应付”也是王星拱着意论述的论题。他注意到,各科科学之中,都有若干定律为中心。凡该科学范围以内的现象,可以该科的定律去预测它。然而我们与外界相接触,有时发现例外的现象——定律不能预测的现象,应当用什么方法去应付呢?若是定律真有普遍的价值,则不当有例外之发生,但是定律是凭我们过去的经验而构造起来的。过去的经验,无论若何充足,总只能指示我们将来一定的现象,大约和一定的定律相符,并不能保证我们将来一定的现象,永远和一定的定律相符。所以例外是可以随时出现的。但是每个现象,必定有一个因,例外的现象,也必定有个例外的因,我们须得研究这个例外的因罢了。这个例外的因,若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所已知的,我们就可以解释此现象和定律何以不符;若是我们所未知的,我们正当利用它做引导去发明新定律。所以我们遇着例外的时候,应当有希望构造新解释和发明新定律的乐观,不应当有哀悼旧定律破产的悲观。“况且例外之研究之重要,不但是以上所说的两端。若是我们一生所接触的现象,每次都和预测相符,而且每日所观察的,都是寻常习见的现象,则我们研究之兴趣,就便易趋于颓废了。例外之发现,正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而激发我们的兴趣。预测和结果相符,固然是研究者之赏品,预测和结果不相符,也是研究者之兴奋剂。因为例外乃真是知识之新材料,我们可以依惊奇之心理,向前探测,这也是科学进步原因之一端。故有人说‘惊奇乃是不知之女,又是发明之母。’此种发明之机会,随地都有。即在日用寻常之间,若详加考察,常有未曾注意的例外。因为人类之知识有限,天然界之奇异无穷,凡研究家都可以做发明家,不必气馁心灰的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1]168-169在这里,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与定律不符的例外在科学中并非罕见;例外必有因;研究例外之因,或可解释例外现象何以与定律不符,或可发明新定律;尤其是,例外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是研究者的赏品或兴奋剂;因此,面对例外应该持乐观态度,无须悲观失望。
王星拱接着论述例外现象的种类:有不是真正和定律不符的,有可以限制定律之范围的,有可以推翻旧定律而引导发明的。况且一个定律或一个理论成立的时候,虽经过严密的方法,往往不能一时骤增美备,故例外之发现,不但有发明新定律之可能,而且有修补旧定律之功用。所以古语说,例外证验定律(Exception tests rule)。他遵循杰文斯的分类,把例外分为八类:(一)虚伪的例外(False exception),(二)貌似的例外(Apparent exception),(三)独殊的例外(Singular exception),(四)极端的例外(Divergent exception),(五)外搀的例外(Accidental exception),(六)未解的例外(Novel exception),(七)限制的例外(Limiting exception),(八)冲突的例外(Real exception)。前五种,可以叫做整理旧定律的例外,后三种,可以叫做引导新发明的例外。虚伪的例外,本身原不存在,不过是偶因心理的悬想所生的错误。至于观察人的心理上,何以生此错误,自然也有因。但是在客观方面的事实,并不成为例外。貌似的例外,是说一个现象似乎和定律不符,而实在是相符的。当现象发现之时,在一定的情境之中,不但使定律掩蔽而改样,并且似乎和定律相反而矛盾,故粗心的观察家,往往被它蒙蔽而看作例外。独殊的例外,本来遵守定律,不过表现出来一种独殊的性质。极端的例外,和定律也不相悖,但是在特别的情境之中,发现为分量极大或性质最显的现象。外搀的例外,是说一个现象不全是由定律所指定的动因所生,而为外来的动因所搀扰;但是这个外来的动因,也是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们能够解释它。未解的例外,也是说一个现象为外来的动因所搀扰,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动因是什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外来的动因,究竟应归何种定律之范围,尚在须待发明之列。凡我们遇见例外可断为缘于外因的时候,有两条途径可取。若管理此外因之定律为已知的,则可用之以解释此例外。若管理此外因之定律为未知的,则须研究它,发明它。限制的例外,是说由此现象而限制定律之应用或缩小定律之范围。当此定律成立的时候,其所根据的事实,并没有与此定律不符的,不过综合过于快遽,将此定律侵越到它所不能管理的现象罢了。此种例外之反对定律,不是全体的,但是局部的。冲突的例外,是说一个现象和管理这个现象的定律两不相容,可以使我们推翻这个定律的。凡一现象与一定律相冲突,不是观察有错误,就是定律不真实。若是此冲突的例外,已经证明是真实的,则定律自当归于取缔之列,决没有桎梏新发生的事实,去屈就它的范围的道理。科学史中新旧换代,无时无之。今天强有力的定律,明天也许就不中用了。今天时髦的理论,明天也许就变成古董了。[1]168-175
王星拱最后坦陈,例外无穷,事出有因:科学发达,无论在什么阶级,总有例外呈献于我们之前。有人以为科学愈发达,定律愈增加,则例外之发现愈少。其实这是个谬误的见解。科学尽管发达,终不能耗尽天然界之奇异。故例外之发现,可以亘古不穷。英国有一句俗语,每个定律都有例外(To every rule there are exceptions),倒是很不错的。何以随时随处,可以发现例外呢?约有三个原因:(一)试就联合换合之原理而言,由若干原质所发生的现象,可以多至无限。人类知识之范围有限,哪能说天然界所有的现象,都已经我们研究过的呢!(二)定律是由我们构造出来,用以描写外界的动作,而定律也不是现象的本身。现象是繁复的,定律是简约的。现象是具体的,定律是抽象的,总有若干不符。(三)宇宙进化,时时不同。外界既是在那里时时刻刻的变迁,则将来的现象,自然有我们现在所不能察见的。无论推论如何精巧,终不能穷其变化。这样看来,“科学之发达,在综合的方面,以定律为中心,在分析的方面,反以例外为起点。倘若此例外是虚伪的,貌似的,独殊的,极端的,外搀的,则我们可以用各区域中固有的定律,参错贯通,以解释新逢的事实。倘若这个例外,是未解的,限制的,冲突的,则我们可以从此例外而求新定律。在以上两层之中,或是联合固有的定律而成一个新理论,或是寻出新定律之存在,都是于科学进步大有功的。”[1]175-176他和盘托出应对例外之方:“若是遽然因这个例外而抛弃已有的定律,似乎易陷于虚妄:然而天然界中之奇异是无穷的,我们又何能抹煞新发现的例外,而保护老朽的定律呢,科学家最重公平,到了这个时候,也无所谓守旧,也无所谓维新。大概应付例外之应经的进径,首先须考订这个例外是否真正存在。若是真正存在,再审察这个例外是否真正和定律不相符。若是真正不相符,再审察这个例外是否可以在旁的区域之内,找出一个定律来解释他。若是不能,那就不能怪我们要‘舍其旧而新是谋’了。再从此研究,或可推翻旧定律,以新定律取其领土而代之;或可限制旧定律,而给予新定律以相当的割据的土地;或可另外发明新定律,而深入未曾探过的新大陆。在这些新得的区域之中,层层步步,前进如前,永无终了之一日。罗司金(Ruskin)说,‘知之不全,但是知之不止,乃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这一句话,倒可以表现科学进取的精神。”[1]176-177
王星拱关于例外的一些议论,肯定或多或少受到彭加勒的启示。一是与定律不一致的例外事实变得分成重要:“以规则的事实开始是合适的;但是,当规则牢固建立之后,当它变得毫无疑问之后,与它完全一致的事实不久以后就没有意义了,由于它们不能再告诉我们新东西。于是,正是例外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不去寻求相似;我们尤其要全力找出差别,在差别中我们首先应该选择最受强调的东西,这不仅因为它们最为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最富有启发性。”[7]二是人们对被抛弃的假设不应该抱病态情绪,因为它比真实的假设成效更大:“假设应当总是尽可能早地、尽可能经常地受到证实。当然,如果它经不起这种检验,人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抛弃它。这正是我们通常所做的工作,但是有时人们却有点儿病态情绪。好了,甚至这种病态情绪也是不正当的。真正抛弃他的假设之一的物理学家反而应当十分高兴;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发现机会。我想,他的假设并不是毫无考虑地采纳的;这个假设考虑了一切似乎能够参与现象的已知因素。如果检验不支持它,那正是因为存在着某些未预期的、异乎寻常的东西;因为在那里存在着将要去寻找的新颖的东西。可是,被抛弃的假设是毫无成效的吗?远非如此,可以说,它比真实的假设贡献更大。它不仅是决定性实验的诱因,而且若不做这个假设,人们不会看到异常的东西;人们只不过多编入了一个事实,而不能从中演绎出最小的结果。”[8]
参考文献:
[1]王星拱.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马赫.认识与谬误[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李醒民.隐喻:科学概念变革的助产士[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22-28.
[4]彭加勒.科学的价值[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92.
[5]王星拱.科学方法论与近代中国社会[M].吕凌峰,等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29.
[6]王星拱.科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114.
[7]彭加勒.科学与方法[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11.
[8]彭加勒.科学与假设[M].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33.
(责任编辑:黄仕军)
Two Special Scientific Methods of Wang Xinggong
LI Xingmin
(Association for the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Wang Xinggong is always interested in scientific methods and often researched them.He published China’s first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onograph.He put forward two special scientific methods:the first is generalization and analogy;the second is measurement,classification,and solving of exceptions.
Key words:Wang Xinggong;scientific methods;generalization;analogy;measurement;classification
收稿日期:2016-03-01
作者简介:李醒民(1945—),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N03;B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6)03-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