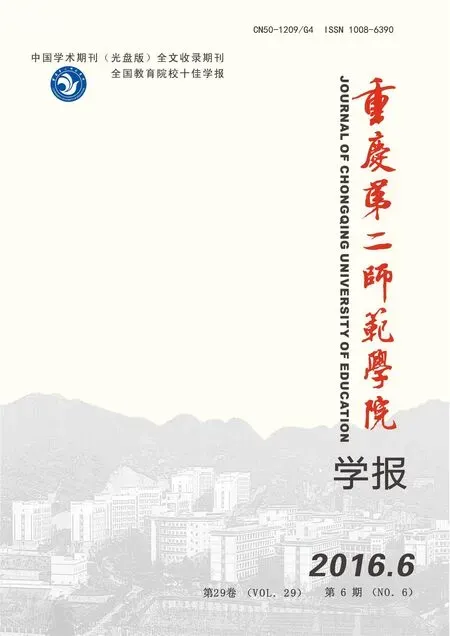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过程的解读
代 红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 401120)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过程的解读
代 红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重庆 401120)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指出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选择活动。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翻译生态环境是主客体共同构成的整体组合,译者的选择和适应贯穿翻译过程,并相互交织,呈现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交替循环状态。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体现出动态、平衡之美。
翻译生态环境;译者;适应;选择
一、引言
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开始追求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全球的生态风潮也刮到学术领域。1978年,美国学者提出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借用生态学的哲学理念来研究、反思文学。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标志着我国学者自主创立生态翻译学的开端。此后,以胡庚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进一步整合生态学途径的系统翻译研究,推动生态翻译学的发展。2010年,“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成立;同年,国际生态翻译学第一届研讨会召开;2011年,《生态翻译学学刊》创刊。这表明中国的生态翻译学研究已具备完整的系统性,并走出国门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隐喻“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基本原理,以“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中国哲学为依归,提出生态翻译伦理,揭示翻译生态理性,是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结合的产物,主要包含九大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和事后追惩。
生态翻译学历经十余年的发展现已自成理论体系,也带动了理论指导下多角度的应用实践研究,如从生态翻译学视角阐释名家译论,用生态翻译学理论指导广告翻译,把生态翻译理念引入翻译教材建设等,生态翻译学显示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同时,伴随生态翻译学发展的是来自学界的质疑,有的学者怀疑“自然选择”是否适用于生态翻译学,有学者提出生态翻译学并没有像生态文学那样为环境发展做出贡献,更多的质疑聚焦在“译者中心”、“事后追惩”、“翻译生态环境”等核心理念。诚然,新的理论有不完善之处,学界提出质疑很自然;新理论不一定完全是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植根于已有理论,对于追随旧理论的人来说有不太适应的异化感,从而发出疑问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质疑都代表对该理论的关注,这些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可以促进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新的理论因为其新,不为众人了解,因而需要做出详细的解读。本文则基于解读的目的,考辨生态翻译学的几个核心术语,以期对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做出准确、明晰的意义建构。
二、翻译生态环境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与发展十周年之际,生态翻译学的领军人物胡庚申出版了《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对生态翻译学做出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他指出,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1]232。换言之,翻译是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的适应、选择活动。进一步分析胡教授的表述,发现潜藏着两个问题:
1.“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是不同的生态环境,即一个翻译活动中存在两个生态环境;
2. 两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典型要件分别为“原文”和“译者”,“原文”是物化概念,“译者”是主体概念,两者不对等。
先看问题1。翻译是一个持续性的活动,为什么要分为两个生态环境?对此,孙迎春提出,间接性的原文生态环境和译者及译文存在的真实的生态环境,译者对原文生态环境的适应具有“间接性”、“预备性”和“虚拟性”。[2]间接、预备、虚拟、真实等概念都是相对译者而言的,因此,以虚拟性和真实性为标准进行生态环境区分,意在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突出译者和译文存在的环境,把翻译活动的重心放在文本转换过程和转换结果上,但忽视了源语文本及原作者。韩巍把翻译生态环境分为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3]。以主客体作为划分标准,明确了生态环境的特性,易于区分环境中的变量因素和常量因素,有助于分析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
翻译是一个过程,一个整体活动,不能以两个生态环境将其割裂开来。为了分析和陈述的方便,将一个复杂、持续性的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或许是科学可行的。翻译过程的三段式划分比较普遍,如张培基将翻译过程界定为理解、表达和校核,韩巍将翻译分为准备阶段、译文形成和译本生存三个阶段[3]。胡庚申在回应针对“译者中心”的质疑时解释说,“译者中心”针对的是“译事中”行为阶段,而翻译行为的另外两个阶段为“译事前”准备和“译事后”效果阶段[1]207。这说明生态翻译学指导下的翻译过程也包含三个阶段。翻译行为的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彼此影响,构成一个完整过程。
既然翻译是分阶段的一个持续过程,从生态学视角来看,译者面对的是一个生态环境,只是在不同阶段,翻译生态环境的构成因素略有不同。
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行为发生的总体环境[4],包含源语、目的语、文化、读者等众多生态环境组成要素。考虑到理论的整体性,可以对生态环境进行概括性描述。韩巍把翻译生态环境分为客体环境和主体环境,指出前者包含原文本、译本、文体功能、翻译策略、翻译规约等元素,后者包含译者、作者、读者、出版商、洽谈商、审稿人等元素。该表述区别环境中的客观因素和能动因素,关照到翻译过程的一体性。以此为基础,可以尝试将翻译过程描述为:翻译是译者对由主体和客体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和适应。译者在主体和客体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选择,也在这个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适应。
问题2的产生,在于表述的混乱和矛盾,“原文”是物化概念,“译者”是主体概念,两者不能等同。胡庚申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解释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他说:“翻译生态环境指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5]就翻译本身而言,不管学界对译者身份如何界定,对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如何评定,原文和译文,源语和译语必然是共存的、相对的概念。但是,在上述表达中,我们只看到原文、源语和译语,意味着文本转换前后的不对应,而且,在实际的翻译活动中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显示出表达的矛盾或者不严谨。再从表达的整体看,前半部分是静态、物化、对象性概念,后半部分是动态、主体性概念[6],用“即”来连接前后两个部分,以进行解释,表明内容的相似和同质,也有欠妥当。原文、源语和译语都是物化的客体概念,等待主体施动而得以具有生命力,如何能自己“呈现”?后半部分的译者、读者、委托者等主体登场,与原文、源语、译语等客体互动关联,才能构成完整的翻译生态环境。关照前后的一致和主客体的互动,笔者尝试将翻译生态环境的表述修改为:翻译生态环境是作者、译者、委托者等主体和语言、文化、社会等客体互联互动而形成的整体组合。
三、译者
从翻译活动出现以来,译者即存在并实际完成翻译工作,但在不同翻译理论中被赋予不同的地位。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主体地位,以诠释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肯定译者的选择,以受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的解构主义等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操纵。译者从“隐身”到主体性显现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是翻译本体论的发展,也是译者重要性得到认可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从原文—译者—译文三元关系视角,读者、译者、译评者等诸者关系视角,译者功能视角,译品差异视角,意义建构视角,适应选择视角和翻译实践视角全面阐释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将译者置于翻译的中心位置,提出“译者中心”,以“彰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和功能”[7]。但是,译者中心说遭到学界质疑。冷育宏认为,译者具有主体性,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普通一员,翻译的生态意识则意味着解构译者中心。[8]陈水平认为,译者中心论有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嫌,过于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会忽略其他主体的权利,否决文本生命权,忽略生态的可持续发展。[4]两种批判均认为“译者中心”不符合真正的生态理念。
胡庚申解释说,“译者中心”是针对“译事中”而言。如果一个理论只适用于事件的某个阶段,而不是整个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理论不具有普适性,或者不够完善。译者作为翻译全过程的直接参与者,“是翻译生态场最积极、活跃的因素”[9],具有主观能动性,与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均发生联系,尤其与主体因素互动互联。由于译者的直接参与和实施,源语文本得以转换为目的语文本,源语信息得以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源语文化得以输入目的语文化,最终完成翻译过程,并对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产生一定影响。反之,如果没有译者,原文永远只是以源语形式存在,不可能主动变成以另一种语言(即目的语)呈现的文本信息,也不可能被不懂源语的非源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因此,译者是翻译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主体。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翻译活动中具有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彰显其创造性,并获得优秀译品。但是,译者不得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操纵或随意发挥,其所要做的就是与生态翻译环境中的各个要素协商对话。
四、选择与适应
翻译是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是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差异被消解、以规范的目的语再现原文本的过程。翻译的操作即译者作为主体,运用创造性思维跨越文化障碍,调节适应环境的过程;由于译者的“时空局限性”和“思维的阶段性”,翻译中的调适过程是“渐进式、无限性”的。[10]再现原作,满足目的语读者需求,是译者的基本职责。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译者履行职责的渐进、无限性调适表现为选择和适应,确切地说,就是译者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由于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交替循环”[1]232的方式做出选择和适应。
选择以适应为目的,适应以选择为手段,两者都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行为表现,且在翻译过程中彼此依存,相互影响。相对而言,适应趋向被动性,选择更体现译者的主动性。
(一)译者选择
1.追求译有所为
译者选择某部作品为翻译对象,或者开始某个翻译行为总是出于一定的目的或需要,如“求生、宏志、适趣、移情、竞赛”[1]247。朱生豪用译作所得稿费维持全家五口的生存,其所译是为“求生”。林纾因发妻过世,愁结郁闷,受邀与友人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他的翻译是为了缓解丧偶之痛,是为“移情”。译者的特定翻译目的促使译者对翻译对象做出选择。如严复为“宏志”,选择翻译《天演论》,意在借用生物进化论阐发救亡图存的观点。
2.主体意识干预
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受译者意识的影响。[11]选择是主体的行为表现,受主体的自我意识驱动,主体意识越强,选择的目的性越强。林纾翻译《黑奴吁天录》(UncleTom’sCabin)有许多改写、增删,或许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强烈的主体意识指导做出特殊选择。林纾古文素养深厚,在文学思想上比较保守,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他在翻译中进行了多处改写,以易于读者接受。被他删减的则主要是原文中有关宗教的描述。林纾本人不懂宗教,中国当时的读者对宗教也未必感兴趣,为读者着想和故事情节的生动、完整和简洁,他删掉了有关宗教的枯燥、晦涩的描写。
主体意识也体现为译者自律。傅雷在修改自己的译稿时,常常是三改四改,工作量大到简直像是在对作品进行重译。这表明译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体现了译者的高度主体意识和自身素质,希望用地道目的语替换地道源语文本和表达,创造高品质的译文。
译者的主体意识除了在宏观层面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外,在微观层面,句型的选择、词语的选用、修辞保留与否等也需要译者主体意识引领,并由译者进行开放性阐释。译者的开放源自文本(包含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信息的开放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是译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体现。
3.适应性选择
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是整体平衡,和谐共生。整体平衡意味着子系统内部平衡,系统之间彼此关联,和谐共处于大的生态环境之中。翻译生态环境遵循相同的生态原则。组成翻译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有多个,现以几个核心系统来予以分析。翻译活动最直接的参与者是译者,而作者、赞助商、读者、译评人等间接参与翻译活动,所有具有主动性的人构成一个子系统,译者要协调彼此关系以维持系统平衡。在译者与源语、目的语构成的子系统中,译者受源语和目的语双重权力话语制约,译者作为主体,需要在制约中寻求平衡。译者本身内在的意识、认知、经验等主观因素与原文、读者接受能力等外在客观因素构成影响译者的重要子系统,且系统内部矛盾重重,需要译者进行调整甚至做出妥协,以维持系统平衡。在各个子系统中,译者当仁不让担当选择者、协调者;而在子系统组成的总系统中,译者仍然是“大总管”,在翻译生态环境中作为一切要素的连接点,积极主动与各方合作,在翻译的实践操作中从语言、文化、交际等多维做出选择并促成子系统的和谐共生,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译者为适应生态要素、适应子系统、适应整体生态环境而选择,译者的选择带有适应性,且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而译者在自主选择的同时还要接受生态环境的选择,并在译境中进行适应,适应的结果则体现在翻译成果即译品上。译品的命运或者生命周期则由译者的选择和适应确定。比如,经典文学作品通常有多个译本,这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包容性,也体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选择。随着岁月的流逝,有的译本得以留存甚至再版,而有的版本则退出历史舞台,这体现的是译者选择与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不同结果。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同样适用于译者与译品,因此译者主体为生存、长存要做出适应性选择。
(二)译者适应
在生态翻译学中,适应是通过优化选择以求生存和长存[7]42的,即选择性适应。名为适应,过程的本质仍为选择,以优化的方式做出选择,追求“整合适应选择度”[1]239高的优秀译文。
在生态翻译语境中,译者作为主体参与各个阶段的具体工作,但生态环境中的主客体因素却无时不在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译者。译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译品的生存甚至长存,必须适应或妥协。由于译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适应又表现为选择性适应。罗新璋所说的“译而作”[12]指的是激发作者主体意识,发挥创造性,突破源语表达的局限,在目的语规约下进行“二次创作”,是所谓“不信”的叛逆性翻译。这种创造性叛逆翻译以源语文本为依托,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属,打上更多的译者印记,而译品常常具有更长生命。傅雷追求翻译的“神似”,在强烈的自我创造驱使下脱离源语表达的局限,以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为己任,其大多数翻译作品在当前仍受推崇。读者是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具有主观能动性,如果译者不能与之和谐相处,联系二者的译文自然处于尴尬境地,生态环境不见平衡之态,而现混乱之状。傅雷追求“神似”的过程正是适应环境的自我主体性发挥的选择过程,追求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译者、译文生存,读者获得良好阅读体验,生态平衡,环境和谐。而同时期的穆木天在翻译时追求对原文和原作者的“信”,甚至为“信”而抹杀自我,抑制自己的灵性,今日已难见其译作。抹去自我是译者的选择,羁勒灵性或许是译者为选择而做出的适应,译作难以长存则是翻译生态环境对译作选择的结果,换言之,译作不为环境所适,从而为现世抛弃。这一对典型的例子说明,译者做出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同时生态环境选择与之适应的译者和译品。两者融合的结果可能是译者适应,做出整合适应选择度高的译文,译者和译文被选择,翻译生态环境一片和谐;也可能是译者和译品进一步调整或者被彻底淘汰。总体说来,译者和译品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译者手中,译者需要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在反复的优化选择中达到与环境的高度适应,即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翻译生态环境的“生态”蕴含的是动态,也就是说,环境中的因素处于变化中,穆木天的译作“不流传于今日”是说其译作不适应当前的翻译生态环境,而其译作在译者当年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曾经是作为适者而生存的。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适应和选择都具有相对性。这就是生态翻译学作为新的视角审视、研究翻译的价值所在。
五、结语
借用“5w”理论分析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过程,会发现译者是“who”,是事件主角,即翻译活动的参与者,是翻译实践的最直接主体,贯穿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并与其他参与要素发生关联。翻译生态环境是翻译活动发生的地点“where”,但不是具体的地点,包含原文本、译本、翻译策略、翻译规约等构成的客体环境和译者、作者、读者、出版商、审稿人等构成的主体环境。翻译活动发生的时间“when”等同于译者参与、完成文本转换的过程所耗费的时间,但不限于此。在翻译生态环境中,还有众多因素跟译品产生关联,如阅读、评价、出版等,这些因素或过程影响译本生命周期,同时改变翻译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译本的生命是翻译活动的延续时间。翻译中的“what”是译者在主体意识支配下做出选择和适应。为了翻译生态的平衡,则是译者做出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why”。概言之,翻译就是译者在主客体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做出选择和适应的过程。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域,因为生态学的引入,翻译活动具有了生态之灵性,翻译过程成为译者主体在主、客观要素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不断做出适应、选择的动态过程,体现出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及动态之美。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孙迎春.张谷若与“适应”、“选择”[J].上海翻译,2009(4):1-6.
[3]韩巍.对“翻译生态环境”、“适者生存”的重新审视[J].外语学刊,2013(1):122-126.
[4]陈水平.生态翻译学的悖论——兼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中国翻译,2014(2):68-73.
[5]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6]王育平,吴志杰.超越“自然选择”、促进“文化多元”——试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外国语文,2009(4):135-138.
[7]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8]冷育宏.生态翻译理论下译者真的是“中心”吗?——与胡庚申教授商榷[J].上海翻译,2011(3):71-73.
[9]方梦之.论翻译生态环境[J].上海翻译,2011(1):1-5.
[10]屠国元,李志奇.论译者的思维结构[J].中国翻译,2007(5);16-21.
[11]宋志平,杨颖.从适应性理论看翻译研究的语用取向[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01-108.
[12]罗新璋.释“译作”[J].中国翻译,1995(2):7-10.
[责任编辑 亦 筱]
2016-06-03
代红(1974— ),女,四川广安人,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H315.9
A
1008-6390(2016)06-00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