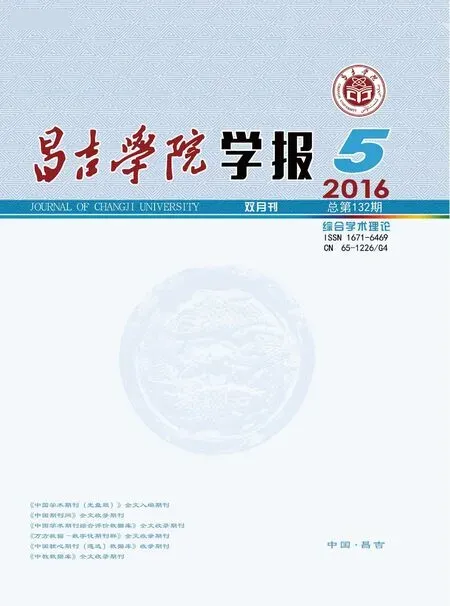《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胡远远 郭立鑫
(1.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9;2.68206部队 甘肃 临夏 731100)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探析
胡远远1郭立鑫2
(1.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河南郑州450009;2.68206部队甘肃临夏731100)
《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据此,《毛诗序》和朱熹《诗集传》以女性为《诗经》的原创主体。基于女性在《国风》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相关问题。《论语·子罕》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表达了孔子对容貌之美的诱惑甚于德性之美的焦虑。《国风》作为女性创作且大多以女性为抒情主人公的作品集,突出体现了女性的“好色”观。具体包括:清晰的“性别”及角色意识、以形貌之外形美和德性之内在美为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精神内核、因礼教约束而形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几个方面。
《国风》;女性“好色”观;“情”;“礼”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一部诗歌总集,后世学者对它的研究可谓既“广”又“深”,产生了传序、点校、译注等以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如毛亨《传》、郑玄《郑氏传笺》、朱熹《诗集传》、陈戍国《诗经校注》、杨任之《诗经今注今译》等。同时,从价值论的角度,《诗经》的文化学、社会学价值也得到充分阐发,如刘玉峨《诗经与古代社会》、樊树云《诗经宗教文化探微》等著作。再次,从文论和美学的角度,《诗经》的比兴传统、抒情性等问题也得到关注,如李子广《〈诗经〉抒情艺术的审美特征》等。以上宏观研究为《诗经》研究在更加细致的层面展开奠定了基础。本文在现有从女性视角研究《诗经》的成果基础上,以《诗经·国风》为主要依据,呈现我国古代女性“好色”观的发生、审美标准以及“色”与“德”、“情”、“礼”的关系范畴和“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审美特征。
一、“性别”意识及角色意识
《诗经·国风》女性“好色”观发生于“性别”意识观念,以“性别”划分两性角色和责任的观念意识在《周易》中有鲜明的体现。《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这里不难见出《周易》对男女、天地、吉凶区分的观念。韩伯康注曰:“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趋则凶。”“性别”决定男女角色和地位的不同,并认为只有顺从这种差别性才能“吉”。再如:“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广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静也闢,是以广生焉。”论者以为这是《周易》“庄严地纯洁地描写两性”,[2]以之为生殖象征,“乾坤各有动静,……静别而动交也。直、专、翕、闢,其德性功用如是。”[3]由此可见,认为“性别”是决定两性角色差异的根本。
“性别”意识在《诗经·国风》中具体形象地表现为两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责任分工不同。总体来说,《国风》中的社会活动大致包括日常生产劳动、祭祀和战争。相比之下,女性则主要以日常生产劳动为主,较少参与祭祀等政治活动,而国事与战争则以男性为主。如以采摘、饲养、手工制作等生产活动,《诗经·国风》多以女性为主。采摘活动如《采蘋》、《卷耳》、《采薇》等篇目。“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纠纠葛縷,可以履霜?掺惨女手,可以缝裳?”都呈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热情清新的劳动场面。对此,姚际恒说:“古称采桑者皆妇人。”[4]《诗经·大雅·瞻》:“妇无公事,休其桑蚕。”可以见出,从社会分工和性别角色来看,女性主要以桑蚕、织造劳动为主。《国风》中还有少量女子以歌舞娱神的形式参与祭祀活动的记载,如《陈风·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坎其击缶,宛丘之道。”《陈风·东门之枌》:“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描写的是巫女径自欢舞娱神的场景。由此可见,日常劳动及祭祀活动中的部分事务属于“德性功用”规定的女性行为、意识的存在之所。
除此之外,以战猎、政事为例,则以男性为主,女性只以他者的身份观察体验此类活动,而本身并不作为此类活动的主体。如《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豵,于嗟乎驺虞!”塑造了男性猎手箭法高强、气概如虹、不可战胜的形象。此外,《君子于役》、《扬之水》、《兔爰》等篇,也都是描写戍卒行役之苦的诗篇,观之,可见男性在战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女性往往在对此类男性活动的观察或体验中产生崇敬、爱慕、担忧、思念等情感,这也从侧面体现出男女“性别”的差异性。
但是,女性在家庭、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有别于男性,并不意味着女性审美意识与男性无关。相反,女性审美意识正是通过个性化的劳动实践活动与两性爱情、社会德性联系起来。以《关雎》为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姑娘在采集荇菜的劳动中,赢得君子的爱情。闻一多《风诗类钞》曰:“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再如《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意思是约定的社会习俗或劳动实践常常是男女婚恋的平台之一,因此女性的情感、爱恋在劳动中酝酿发酵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产活动的作用也直接孕育了女性的德性评判意识。如《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无情地嘲骂不劳而获者。《硕鼠》:“莫我肯顾,是将去汝”,是反抗剥削的最强音。
总之,“性别”意识蕴含在男女自身自然差别和社会角色差别之中,使女性审美活动的范围从闺阁拓展到广阔的社会,也使女性审美意识呈现出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交织的状态,体现了女性审美意识的丰富性。
二、以外在形貌美和内在德性美为审美对象
《国风》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好色”观是外在形貌之美与内在德性之美的统一。薛富兴说:“‘美’在《诗经》里又有其独特内涵,主要形容男女两性外在形式之美,指人的容貌、形体,相当于今天之形体美。”[5]《国风》中有大量描写男女形貌之美的作品,并对这种形貌之美表现出赞赏的态度。《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对集中体现女性特征的手、肤、颈、齿、眉做了形象的描写,比之于柔荑、凝脂等,加之笑靥如花、美目流转,突出了女性形貌柔美靓丽的特征。再如《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劳心悄兮。”描写的是皎洁的月光下,女性轻盈窈窕的体态美。除了直接描写女性形貌美之外,《国风》还常常通过譬喻或男性的视角侧面体现女性形貌美。花、玉、云等美好的事物也成为女性美的象征。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桃花之美艳比喻女性美,同样《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以木槿花和琼琚之美比喻女性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以云之洁白、轻盈、飘逸象征女性美。此外,女性形貌美还通过男性的视角表现出来。如《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表达了青年男子邂逅美女的喜悦心情,女子清新婉丽的外形在男子的欢欣喜悦之中呼之欲出。《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体现了男子对美丽的沤麻姑娘的爱恋。
女性对外在形貌美的审美标准也适用于男性,尤其以男性高大、健壮的形体特征为审美的关键。如《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能够一箭射中五只野猪,男性孔武有力的形象呈现无遗。《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全诗“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的反复咏叹,热情赞颂男子的英武潇洒。《汾且洳》:“彼其之子,美无度。”也是女子对意中人美男子的赞美。由此可见,《国风》女性审美意识把男女形貌美一并作为审美对象,如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古人‘硕’、‘美’二字,为赞美男女之统词,故男子亦称美,女亦称硕。”可见,男女形貌美都是女性审美意识的指涉对象,强调人体外在形貌的“美”和“硕”特征。
《国风》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好色”观还包括内在德性之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描写了一位终生劳苦,抚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德性之美不彰自明。此外,如“淑”、“婉”、“静”、“都”等关乎德性标准的词在《国风》中大量运用,也是对德性美的强调。《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鸬鸠》:“淑人君子,其仪一兮。”《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以晤歌。”《毛传》解:“淑,善也。”“善”是德性价值评判的范畴,在《国风》成为审美标准的一个方面。再如“婉”、“静”,《猗嗟》:“猗嗟娈兮,清扬婉兮。”《甫田》:“婉兮娈兮,总角卯兮。”《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说文》:“婉,顺也。”《毛传》:“婉,顺。”《毛传》:“静,贞静也。”温顺、贞静是古代社会对女子性情和行为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属于德性范畴的评价标准。“都”,《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集传》:“都,闲雅也。”娴雅是对人的气质、人格、性情特征的指涉,有别于单纯的形貌标准。由笺注对这些词语的解释来看,我们可以认定,《国风》审美意识关于“美”的标准,除外在形貌美之外,还关涉内在精神性,这就是德性美标准的体现。
此外,《国风》强调德性美还体现在对失德行为的批判上。如《何彼禯矣》:“何彼襛矣,棠棣之华?何不肃雍?王姬之车。”表达了对貌美却行为不端的贵妇人的讽刺。《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表达了对庄姜美丽外表之下不端行为的谴责。再如《新台》、《墙有茨》、《鹑之奔奔》三篇,均以女性有色无德、宫闱之中淫乱秽行为讽喻对象。以《墙有茨》为例,《毛诗序》评之曰:“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6]《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针对夏姬屡嫁之事,借叔向之母的口吻表达了对有色无德女性的批判:“甚美必有甚恶。……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7]“尤物”指貌美的女性,美色足以迷惑人心。如果没有德义的规范,必然成为祸患。综上可见,《国风》女性“好色”观以“外美”与“内美”为审美对象,强调“色”与“德”的统一的审美准则。
三、“情”:《国风》女性“好色”观的精神内核
“情”,尤其是爱情,是《国风》中几乎所有女性抒情主人公咏唱的主题。从女性“好色”的审美意识看,正是“情”的精神内核使“好色”意识具有了深刻感人的力量。《国风》女性对“情”的诉求突出表现在女性对真挚情感的渴望和对不公平两性关系的谴责上。首先,真挚热烈的情感是《国风》女性群体的一个鲜明倾向。《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一个姑娘看到树上的梅子即将熟透,想到青春易逝以及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表达情感真实、坦率、热烈。最为典型的是《蒹葭》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芦苇、白露、流水、伊人,此情此景,使女子的思恋之情溢于言表,透露出淡淡的幸福和哀伤,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牛羊下山,鸡群上架的暮色中,渗透着女子对服役在外的丈夫的牵挂和期盼。千载之下,女性细腻温暖的情感依然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美感。《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感慨“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因其用情之深,连恋爱中思念之情和嗔怪之意也显得纯真自然。《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幽会中的女子故意打趣意中人的调笑之语,拙朴热烈的真性情扑面而来。再如,《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表达一个女子为追求婚姻自由反抗父母之命、“之死矢靡它”的决心。以上都说明,《国风》女性“好色”意识不仅止于对外在形貌的追求,真挚热烈的情感意识才是其最重要的精神实质。
女性真挚热烈的情感诉求促成了追求平等自由之爱的理想。这一方面体现在《国风》对两情相悦的赞颂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负心背义男子的鞭挞上。前者如《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以女子叫醒睡梦中的男子的闺阁之语开始,继之以烹调、对饮、琴瑟相和,相亲相爱的两性关系使全诗在温情脉脉中展开,意味无穷。《缁衣》:“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女子以男子着缁衣为美,因此亲手缝制修改,殷殷深情款款爱意将和睦的家庭生活中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呈现出来。《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裹。心之忧矣,曷维其已!”一位情深义重的男子悼念亡妻之诗,睹物思人,斯人已逝的悲切感人至深。另一方面,《国风》中女性对自由平等两性关系的渴望还体现在对不合理的婚姻的抗争和对负心男子的谴责上。《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表达了一个女子对已婚男子以刑狱手段粗暴逼婚的反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这首遭到遗弃女子的自慰诗,充满了对男子及其续室的诅咒。再如《遵大路》、《中谷有蓷》也是弃妇的哀怨与谴责。《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则是正面呼吁女性的尊严和独立。
由此可见,《国风》女性在两性审美意识问题上,虽然“好色”但不流于“好色”之肤浅,而以真情、自由平等、两情相悦的两性关系状态为“好色”的精神内核,这也是《国风》女性审美意识之爱情观念的主要内容。“情”与“色”的统一,使《国风》女性两性审美观彰显出深刻的意蕴美。
四、“礼”:《国风》女性“好色”观的约束因素
“礼”是儒教对社会人伦一切秩序的最高规范,《国风》中女性“好色”的审美意识也受到“礼”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以《关雎》为例,足见《国风》对“色”的强调。“窈窕淑女”,如杨雄《方言》所说:“美状曰窈,美色为艳,美心为窕。”[8]即《关雎》所谓“窈窕淑女”就是形貌德性俱佳的理想女性形象,足以引发君子强烈的思念和爱慕之情。但是“色”必须受到“礼”的制约。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孔子诗论》一篇以《关雎》等篇为例,说明“色”与“礼”的关系。其中,第十简:“《关雎》以色喻于礼。”[9]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10]即从竹简《孔子论诗》来看,《关雎》是“喻于礼”、“纳于礼”的,即对“色”的思慕和渴望最终被控制在“礼”的范围内。另外,《论语·为政》:“随心所欲,不逾矩”,“矩”否定了无限放任情感和行为的处事方式,即孔子认可包括两性情感在内的人的自然性情,但是这仅限于“礼”的范围。如《国风》中的《绿衣》、《燕燕》、《东方未明》、《将仲子》等表现的情感类型有两情相悦、有怀人、有追思,这些发于个体内心的自然情感,孔子作为《诗经》的编纂者并不回避反而尽数摘录,表明了他对人的自然性情的尊重。但是孔子同时又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孔子自知“色”对人的诱惑和对礼法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不可忽视,所以主张以“礼”对人的“好色”之情加以节制。彭燕说:“作为《诗经》编纂者的孔子自觉地将诗教和礼教结合起来,……进而建立和维护一个他所心仪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主仆等级有差、内外有别的均衡和谐社会。既然如此,则其对《诗经》女性及有关女性的一切评价仍应是从这个原则出发的。”[11]也认为“礼”是对女性及其评价的标准。总之,“礼”的约束使《国风》中的“情”、“色”女性意识呈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特征,用孔子《为政》中的话说就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即诗乐情感中正平和合于节度。
综上,由《诗经·国风》以女性创作及抒情主人公的实际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其中女性审美意识之“好色”观的产生、审美对象及标准、精神实质以及审美特征等内容。概括地说,《国风》女性审美观念产生于“性别”意识,以“外美”和“内美”并重为其审美对象和审美标准,以真挚的情感为其精神实质,以“礼”为约束而形成中正平和的审美特征。直至今天,这几个方面依然是女性两性审美观念的主要内容。任一鸣说:“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12]《诗经·国风》以女性创作为主,表现了女性生存生活、女性性情命运和女性观念意识,这也是以《国风》考察我国古代女性审美意识的依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27.
[2]周予同,朱维铮.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A].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80.
[3][清]陈梦雷.周易浅述[M].卷7.九州出版社,2004.
[4]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231.
[5]薛富兴.《诗经》审美观念举例[J].阴山学刊,2005,(10):5.
[6][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313.
[7][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118.
[8][汉]杨雄.方言[G].四部丛刊初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9:2.
[9][10]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2,24.
[11]彭燕,黄俊鹏.论《诗经》女性形象的社会角色及意义[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3.
[12]任一鸣.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及其批评之辨析[J].昌吉学院学报,2003,(3):7.
I01
A
1671-6469(2016)-05-0038-05
2016-05-19
胡远远(1981-),女,河南郑州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