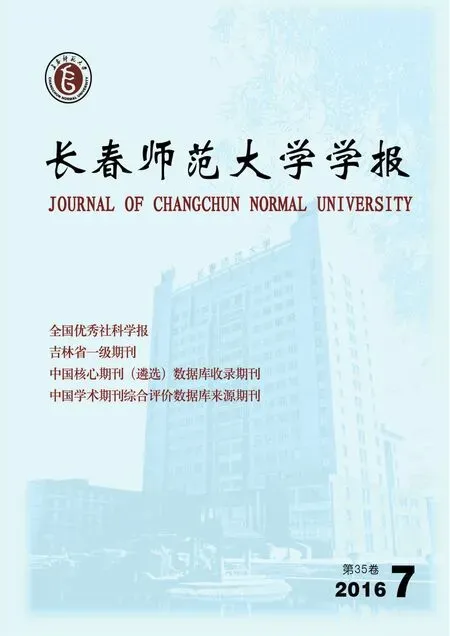论桃花源与龙宫城的文化意象差异
王熙宁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桃花源与龙宫城的文化意象差异
王熙宁
(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日本的浦岛太郎龙宫奇遇与中国的刘晨、阮肇山中遇仙的民间故事在内容及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通过对龙宫城、桃花源等具有文化意向意义的要素分析,寻找这些物象的不同寓象意义,从文化意向视角出发,对中日文化的差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文化意象;物象;寓象;逃脱与超越;民族性格
文化意象是凝聚各民族智慧、体现民族文化特质的语言符号。作为记录文化的语言符号,文化意象是“各民族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结晶”[1],存在于特定的文学系统,表达着特定的民族心理,为共同文化背景的特定群体所接受。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象两个层面构成。前者作为一种感性经验,可以呈现为一种乃至多种感官感知的具体物;后者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感情,可以被理解为“物象在一定文学语境中乃至整个文化环境中的引申”[2]。有学者指出,文化意象“与各民族的传说以及各民族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密切的关系”[3]。
日本的浦岛太郎龙宫奇遇与中国的刘晨、阮肇山中遇仙是中日两国流传范围广、代表性强的两则故事。日本有关浦岛太郎的传说最早记载于室町时代(15-16世纪)短篇说话集《御伽草子》。故事讲述了一个叫浦岛太郎的年轻人,捕鱼时偶然救起一只海龟,后来被海龟带到了海底的龙宫城中,和龙女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因牵挂家中父母,浦岛太郎又回到陆地,发现原来居住的村庄早已不复存在。原来在龙宫城的三年时间里,人间已经度过了300年。浦岛太郎感到绝望,打开龙女交给他的宝盒,一瞬间变成了耄耋老人。中国的刘晨、阮肇山中遇仙并误入桃花源的故事情节与浦岛太郎的故事多有相似之处,记载于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幽明录》中,讲述的是汉朝时刘晨、阮肇两名青年在天台山中迷路,后被两名少女相救,并随少女进入桃花源,结为连理的故事。在这两则故事中,作为文化意象的物象部分的是桃花源和龙宫城,作为文化意象的寓象部分的是理想中的社会、幻想中的天堂。但是,形似不意味着神同,故事相似更不意味着旨趣一样。
一、物象的差异:从桃花源到龙宫城
在上面两则故事中,作为文化意象的物象部分而存在的是桃花源和龙宫城。在浦岛太郎的故事里,物象从山中移到了海上,由桃花源变成了龙宫城。对于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恐怕要从中日两国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中去寻找。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安土重迁、自给自足成为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性格特点。动乱战争、自然灾害、社会压迫、人口增长等原因促使人们移居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开辟新的理想家园。这种理想家园的地点选择在相对封闭的山中,不仅可以消除来自原先生活群体的竞争压力,避开各种关系的烦扰,还能够在清新的新环境中开疆拓土。类似桃花源之类的传说或故事,不仅表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还显示了生产方式方面的连续性以及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相通性。
“中国仙乡故事多半是入山,日本的浦岛传说是下海到了仙乡,这当然是由于日本是海岛国家的实际地理环境而产生的变化。”[4]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在四周的海域中能够捕获到每天赖以充饥的鱼类,有时还能够从贝类中发现隐藏的珍珠。在日本人的眼中,大海既是广阔无边的世界,也是富饶的神秘地方,不仅隐藏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可能还会有奇遇和意想不到的收获。从浦岛太郎的故事中看到的日本人对异界——龙宫城的渴望,是长期栖居岛国的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种海洋崇拜情结,或者说是一种海洋空间意识的反映。在这里,既没有类似中国的安土重迁的土地情结,也没有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历史存在感和时间延续意识,有的只是对当下时间的体验与即时性收获的感恩。这种差异的产生与日本农耕文化发展比较晚有关。公元前3世纪弥生文化的产生,标志着绳文时代中期就存在的农耕技术的成熟,预示着农耕文化的开始[5]。这显然大大晚于中国的农耕文明。在农耕文化开始前的漫长岁月里,日本人一直以采集和渔猎为生,所获生活资料都无法长期保存,加之日本列岛雨水充足,大自然的馈赠丰厚,更强化了生产活动的即时即用性,由此形成了强调功利、重视时效、讲究灵活、追求快捷的民族文化特质。这也是日本文化很难接受类似中国《愚公移山》里愚公的做法和形象的原因[6]。
二、寓象的差异:超越与逃脱
在民间传说中,对异界空间的描述主要可以区分为两个对立面:比现实社会更加黑暗、更令人恐怖和绝望的地狱;没有任何烦恼与忧愁的理想世界即天堂。在对理想世界的认知和感受上,中日两国存在文化意象上的差异。在浦岛太郎的故事中,太郎所探访的龙宫城所处地理位置与周围环境与人类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人公对这种差异有着明晰的认知。对远离现实社会的龙宫城的幻想表现出日本人在潜意识里的逃脱现实生活的愿望以及逃脱后对理想世界(异界)生活的渴望。久松潜一在《神话传说说话文学》指出:“异界观念中分为天上界、地上界和地中,地中多数是指黑暗的黄泉国、根之国,海底虽然同样是底部,但是水底清澈透明这点可以联想到光明的仙境。这样一来,由山中或海底联想而来的仙境观念不占少数。”[7]可见,日本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不仅有玄远的天界,也有仙山和海底仙境,因为这里有光明和美好,可以完全卸掉来自俗世生活中团体的压力与束缚,即使只能享有片刻的欢愉和自由,那也值得尝试与追求。
在中国的古代传说中,也存在着类似日本龙宫城的海底世界——龙宫。但中国人心目中所公认的理想之地并非龙宫,而是桃花源:一个无王法、无国税,远离战乱纷争,摆脱剥削压迫的理想乐土。与浦岛太郎的传说中的异界——龙宫城不同,中国的桃花源被描绘成神奇莫测的仙乡模样,那种和平、宁静的劳动生活给人以平凡朴素、亲切真实的感受,与现实的生活世界相似,即便偶然误入其中,也不会觉得特别神秘或异样。所以说,桃花源与其说是与世隔绝的中国式的乌托邦,不如说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大同”或“小康”社会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日本人的龙宫城情结是对现实的一种逃脱的话,中国人对桃花源的钟爱则是一种乐于改变的超越,表明中国的先民们对理想社会和美好家园的憧憬与渴望。尤其是当人们不满于黑暗现实或人生遭遇挫折打击之时,“桃花源几乎成了人们摆脱烦恼、忘却忧愁、渴望恬静、追求安逸的精神家园”[8]。
三、禁忌的差异:自由与禁制
刘晨、阮肇从桃花源回归故里后,感叹时光匆匆而逝,想返回桃花源,因找不到归途而作罢。后来刘晨结婚生子,与常人一样度过了幸福的一生。阮肇则看破红尘,周游诸国,传说后来羽化成仙。除刘晨、阮肇误入桃花源之外,刘禹锡的“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诗句中所引用的“烂柯人”的典故同样属于游历异界的传说,但也没有像太郎一样遭遇悲惨的结局。为什么情节相似的故事却在结尾出现如此的差异呢?在浦岛太郎的传说中,多出了一个具有文化意象的物象物——龙女交给太郎的玉匣:一种类似禁忌的存在。正如久松潜一认为的那样:禁忌之物是拥有绝对力量的,是约束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宗教,不仅规定着古代人民的现实生活,也为古代人由空想情绪所产生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现实的基础[7]。人类的现实生活充斥着各种痛苦与不幸,无限的生命和绝对的自由在现实社会中又无法实现。于是,这种人类的冲动、欲望便通过诸如浦岛太郎这样的神话传说表现出来。禁忌的存在会让人感受到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神话的世界里获得自由、快乐的同时可能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中国相关的神话传说中没有日本故事中表征文化意象的物象——锦盒。这里提及的锦盒作为一种物象,对于传说中的人物而言是实际存在的物体,可以被感知。而锦盒这一物象蕴含的抽象的寓象,可以被看作一种禁忌。具体到浦岛太郎这一传说中,锦盒寓意的禁忌指的就是从所属团体中逃脱出来这一行为。集团性是日本人性格的重要特征,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罕有美国式的超级英雄,大家所喜闻乐见的情节多数像桃太郎一样组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团体,靠团体的力量去击败敌人。在抗击敌人的时候,内部的个体差异被无限地忽略。加藤周一将这种集团中的个体的行为称为“顺应大势主义”。“大势”是大部分集团成员往特定方向的运动。“问题不在于那个方向的是非曲直,而只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朝那个方向走,所以自己也加入该行列,与别人采取相同的态度,附和雷同”[9]。在浦岛太郎的传说中,太郎作为村落、乃至社会整体的成员之一,抱有逃脱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这样的太郎是极少数的异端,其想法可能与大多数成员相左,或者对集团的行为抱有消极的态度。浦岛太郎的逃脱行为无法令人容忍,因此受到惩罚也就不足为奇了。
强烈的集团意识和顺应大势的想法在中国民间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在中国,儒学替代了宗教的功能,扮演了准宗教的角色。在儒家看来,“天道”即“人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这样也就不需要舍弃现实世间、否定日常生活,而去另外追求灵魂的超度、精神的慰安和理想的世界。”[10]正因为“人道”即“天道”,统治者就应该博施“仁政”、广行“王道”。古代中国存在将皇权与神权相联系的做法,古代知识分子相信天人同构互感,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与其说是对皇权的神化,不如说是“对君主的制约与权力的超越”[11]。经过儒家仁学精神和古代人本主义思想洗礼,中国少有把君主无限神化的文化土壤。如果中国的统治者有违天道、不施仁政,民众是有自由选择权的,推翻其统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顺天应人的合理合法行为。然而,在日本的各个时代,无论政权由贵族掌握还是由武士掌握,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一直被认为是神圣的存在。崇尚天皇的传统决定了日本人在心理上皈依于天皇。在行动上完全听命于天皇,全体日本人在天皇的旨意下结成一个庞大的集团体,从这个既有宗教色彩又包含政治因素的团体中逃脱绝对不会是一件可以被原谅的事情。换言之,在日本社会里反抗权威并没有合法的理据,是被禁制的行为。
四、余论
民间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现代人了解古代人生活实态的重要媒介之一。在浦岛太郎的传说中,对太郎在龙宫城内度过的一段梦幻般的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古代日本人在心理上渴望片刻逃离社会组织的朴素愿望。而在刘晨、阮肇的传说中出现的桃花源可以被称为全体中国人的精神乐园。可以说,我们通过以桃花源的生活为蓝图创造理想社会的形式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通过对造成寓象差异的原因分析,更能看清中国人积极地追求自由、幸福的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变化、更替更具有宽容之心的民族性格,而这恰恰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魅力。
[参考文献]
[1]顾建敏.关联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意象互文性及其翻译[J].外语教学,2011,(5):110.
[2]赵迎菊.语言文化学及语言文化意象[J].外语教学,2006(5):48.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85.
[4]王孝廉.花与花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41.
[5]樋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74.
[6]于长敏.中日民间故事比较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46.
[7]日本文学教養講座:第五巻[M].日本:至文堂.1952:90,100.
[8]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45.
[9]加藤周一.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62.
[1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4.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66.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王熙宁(1992- ),女,硕士研究生,从事日本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7-0192-03
On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Images of the Peach Blossom Yard and the City Palace
WANG Xi-ning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Ji 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many resemblances between the Japanese Urashima Taro’s adventure in the City Palace and the Chinese Peach Blossom Yard’s legend.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images between the Peach Blossom Yard and the City Palace, then elucidated the distinction from these two places’ implied meanings. The author offered th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about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from the cultural implied meanings’ view.
Key words:the cultural image; image; implied image; escape and transcendence; national charac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