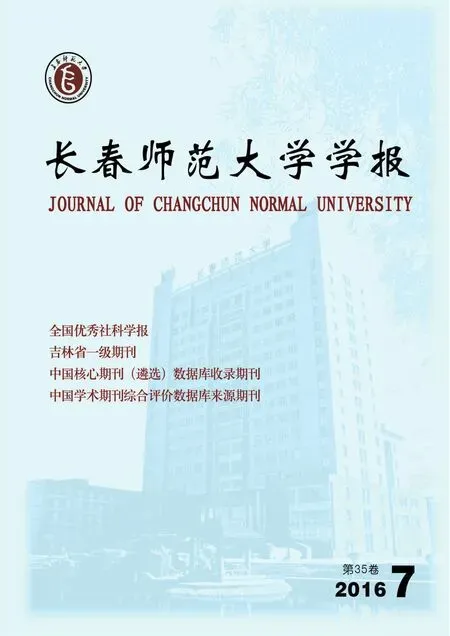《裂缝》与《蝇王》的互文性研究
李楠楠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裂缝》与《蝇王》的互文性研究
李楠楠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互文性理论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依赖、互为表征的关系。以互文方式拓展作品的意义空间是后现代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范式。运用互文性理论对《裂缝》与《蝇王》进行解读,探讨两部小说在场景、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和主题等方面的显性互文,能够更好地了解两部作品的关联与内涵,拓展研究和解读的可能性。
[关键词]互文性;《裂缝》;《蝇王》
《裂缝》是美国非裔女作家谢拉·科勒(Sheila Kohler,1941- )的一部重要作品,1999年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被美国《新闻日报》和《图书馆杂志》评为当年最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并提名了IMPAC都柏林文学奖。《图书馆杂志》评价这部小说:“虽然作品语言简洁,其中却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旧金山纪事报》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未有一部作品像《裂缝》这样对人性的邪恶做出如此深刻的剖析。”
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妹妹的亲身经历,讲述南非一间寄宿学校中青春期女孩儿暴虐的故事。主人公是一群游泳队的女孩儿和老师G小姐。孩子们练习游泳的主要目的不是参加校际间的比赛,而是取悦漂亮、妩媚、有着传奇冒险经历的G小姐。像湖水一般平静的生活被一位“不速之客”费雅玛掀起了波澜。她出身于西班牙贵族,拥有优雅的气质和傲人的外貌以及同龄女孩鲜有的开阔眼界。她的超凡脱俗招来了G小姐的仰慕、同伴的嫉妒,最终招致被追打致死的命运。在小说中,科勒以阴暗的笔触,探讨人与人关系中的暴力因素,大胆地触碰了“儿童的残忍本性”这一禁忌话题。
关于儿童罪恶本性的主题,早在当代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寓言小说《蝇王》中就进行过深入剖析。两部小说都以寓言的形式,追溯暴力产生的根源,演绎人性堕落的历史,在场景、故事情节、主要人物塑造以及主题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互文性对照。
本文重点运用互文性理论,探讨《裂缝》对于《蝇王》的移置与重构,探讨两部作品关联的内在原因,揭示这部“女性版《蝇王》”的深刻内涵。
一、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被称为文本间性,是西方文学理论界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本理论。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使用这个词,她在研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互文性主要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每个文本都具有复杂性和异质性,但都不能脱离其他文本而独立存在,任何文本的意义生成都必须依赖于其他文本的意义,并且与其它本文共同形成相互参照、彼此联系的关系网。文学作品被视为“叛逆性创造”,即作者在创作中实现了继承与创新、过去与现在、传统与个人创造的统一。解构主义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精辟地阐述了互文性的理论价值,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文本,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只有互文本。”[2]互文性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对文本封闭单一的阐释,将其放置于庞大的文本关系中,形成一种开放的、多元性的解读。互文性理论为《裂缝》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角,将其放在与《蝇王》的互文性参考体系中,有助于激活文本的意义、凸显作者的创作意图。
二、《裂缝》与《蝇王》的互文性分析
尽管故事发生的年代和创作背景不同,《裂缝》的字里行间却体现出与《蝇王》的高密度交叉。
(一)场景与故事情节互文
寓言小说《蝇王》的场景特意设置在一座荒芜的孤岛上。岛上有充足的淡水、丰美的食物、湛蓝的海水和绵延的沙滩,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间伊甸园。刚开始,这群天真烂漫的男孩子在这里度过了欢快美好的时光,他们搭建棚屋、燃起篝火,以海螺为号令召开民主会议,岛上一派文明与秩序的景象。但是好景不长,对“野兽”的恐惧和“肉”的需求迅速占据了孩子们的思想。本来井井有条的小团体很快分裂成两派:以杰克为代表的“狩猎派”和以拉尔夫为首的“营救派”。在寻找野兽的过程中,两派的斗争不断升级,“狩猎派”的势力不断巩固加强,最终战胜了代表文明和秩序的“营救派”,孩子们享受着杀野猪吃肉的快感,文明与向善的理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杀戮与残害。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讲到,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即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男孩们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要,寻求一种在周围环境中的安全感,完全摆脱了文明社会的束缚,相互厮杀与毁灭,把伊甸园变成了屠宰场。
与架空了时间和社会的《蝇王》相比,《裂缝》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残酷。故事地点选择了20世纪60年代南非的一间寄宿学校。学校位于人烟稀少的角落,风光秀美,河水清澈,一望无际的田野中开满了白色的鸢尾花,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故事的主人公是以黛为首的游泳队的女孩儿们。在这里,食物和安全已经不是她们的第一需求。群体的认同感和情感上的寄托才是最重要的。跳水队成员在学校中声名显赫,是其他女孩羡慕的对象。在她们心中充满对外面精彩世界的好奇、对异性的幻想。神秘、博学的G小姐能满足她们情感上的诉求,是她们释放思想和超越自我的“精神导师”。“G小姐就是我们的裂缝。当你通过裂缝观察时,事物变得格外清晰。”[3]27“只要我们读懂G小姐,我们就会明白生活的全部奥秘。”[3]38女孩们享受被G小姐赞美、呵护甚至训斥的感觉,把这些视为一种宠爱。“我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保住我们摇摇欲坠的地位。我们一直担心G小姐让我们出局,赶到黑暗的地狱,把我们与那些游泳队外的女孩儿化为一类,甚至与那些基本不存在的人放在一起”[3]51可见,“裂缝”也代表了一种“迷恋”。G小姐沉溺于被围绕和崇拜的女王般的感受。菲雅玛的到来将需求平衡打破。女孩们不再处于金字塔尖,学校里的领导、老师甚至宿管阿姨、打杂的都对菲雅玛态度友善、照顾有加。连与众不同的G小姐也给予这位贵族公主特别关注,深深为她散发的独特气质吸引。这一切让习惯了优待和宠爱的女孩们无法容忍。当归属和爱的需求无法满足,毁灭菲雅玛的念头在心中萌生,人性的丑恶与暴力渐渐显露。终于,在一片幽暗的树林中,女孩们揭下文明的面纱,毁灭了心目中的“敌人”。与《蝇王》中为了食物和安全而刀戎相向的男孩们相比,科勒笔下这群身处文明社会、受良好礼教熏陶、温文尔雅的女孩们在屠杀同伴时表现出的残忍与冷漠更令人难以接受,使人心有余悸。
(二)人物的相互指涉
与《蝇王》一样,谢拉·科勒在《裂缝》中的人物塑造可谓是独具匠心,选择了一群十三四岁的女孩,讲述她们在寄宿学校这样一个封闭空间内的相处与生存之道。两部小说在人物性格刻画及命运安排等方面存在着相互指涉的关系。
1.G小姐与杰克
戈尔丁笔下的杰克是一个天使与魔鬼的统一体。他出场时的外貌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个子又高又细,瘦骨嶙峋,黑帽子底下的头发是红的,脸皱巴巴的,有很多雀斑。他样子虽丑陋,却没有半点傻气,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这时他感到颓丧,正要或准备发怒。”[4]10杰克强悍、精明,具有领袖气质和权威意识,与拉尔夫相比,更富有冒险精神,凭借他的力量和英雄行为帮助解决了岛上饥饿的问题,很快赢得大多数孩子的尊敬,使这些孩子心甘情愿地归顺于他。然而,杰克对力量的崇拜在追捕野猪的过程中不断地膨胀,甚至达到了近似野蛮和残忍的程度。他开始变得嗜血如命,最后竟然将刀子指向了自己的同类。
与杰克类似,《裂缝》中的G小姐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的人物。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传统、保守甚至刻板,一袭黑色风衣包裹下的身体散发着成熟女人的活力,娇艳的嘴唇、妩媚的眼神、手拿着烟轻轻吐着烟圈的样子透露出“优雅”的气质。她经常在女孩们面前谈论自己“漫游世界”的各种传奇经历,用一种低沉富有磁性的噪音;她会在半夜里带学生一起去游泳,和学生一起玩闹,具有冒险精神;她思想开放,鼓励学生努力追求自身的欲望。“无论是游泳还是其它任何事情,如果想做到最好,最重要的就是拥有欲望。”“只要欲望足够强烈,我们可以完成任何事情。”[3]36对于这些远离家庭甚至遭到遗弃的女孩们来说,G小姐不仅是老师、母亲,更是精神导师和效仿对象。孩子们对她顶礼膜拜,希望能够成为像她一样美丽动人、令人艳羡的女性。贵族公主菲雅玛的出现让G小姐的生活起了涟漪。相对于G小姐封闭的生活圈子而言,体验过人生的菲雅玛无疑是一道清泉。如果说G小姐是其他女孩心中的“裂缝”,菲雅玛便是G小姐心中的“裂缝”。笑脸、恭维成了她生活的主题。然而,菲雅玛的冷漠态度让G小姐感到矛盾与困惑。当遭到嫌弃后,一种极端的情感开始在G小姐心中滋生。既然得不到爱与青睐,唯有毁灭心里那个“希冀的模样”。最终,G小姐玷污了菲雅玛的纯洁。在这个过程中,G小姐的欲望不断升级,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从最初尝试对菲雅玛私人物品的占有,发展到对她身体的占有,乃至最后对菲雅玛生命的占有。这种“占有”完全是一种力比多(libido)冲动的集中显现。高雅文明的G小姐在面对自己的“裂缝”时,最终屈服于野性冲动,沦为了欲望的奴隶。
G小姐与杰克皆具有特立独行的性格和非比寻常的领袖气质。也正是这些特质让他们对“野性”的本能冲动无法克制,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斗争中屈服于受欢乐原则支配的“本我”。
2.菲雅玛与西蒙
在《蝇王》众多的男孩当中,西蒙是唯一至善至纯的人物,拥有着明镜般透彻的心灵及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甚至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不善言谈,然而本性善良的他在大家困居小岛后,主动帮其他孩子找野果充饥。他勇敢无畏,常常一个人独自上山探究“野兽”的真相;他具有智慧,在一次次的观察沉思后,道出“大概野兽不过是自己”的真理。可惜的是,西蒙这样一个善良、理智的“圣子”最终掉进了由人性中的邪恶筑就的万丈深渊。一个先知者、预言家就这样成为了捍卫真、善、美的牺牲者、殉道士。
《裂缝》中,菲雅玛一出现便显露出她的超凡脱俗和与众不同。她来自意大利的贵族家庭,拥有牛奶般丝滑的皮肤、清澈的蓝色眼睛、飘逸的金色秀发,一切让菲雅玛看起来像一位童话中的公主。更难得的是,她拥有无与伦比的游泳天赋,她轻盈优雅的划水动作,彻底颠覆了女孩儿们的标准。在众多女孩眼中,她是一个完美的同类。对于同伴的游戏或秘密,菲雅玛显得毫不在意;她少言寡语,经常独来独往,去原野中散步,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菲雅玛的本性是善良的,她能够慷慨大度地面对同伴的排挤和敌对,与这些看上去并不友好的同学分享自己的事物、饰品甚至是G小姐的“加餐”。菲雅玛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女生,有阅历但不显露,有经验但不张扬,她与G小姐是一对南辕北辙的“姐妹”。她丰富的人生阅历注定她是一个体验过人生的“智者”。当女孩儿们都沉浸在G小姐“奇幻世界”时,唯有菲雅玛清醒地意识到“那些都是别人的故事”。她比任何人都了解G小姐强大的控制欲与虚伪的人格,勇敢地在同伴面前揭露出“G小姐一直在欺骗大家。她只不过讲出大家想听,又对她自己有利的话。她根本没有那么强大。这世上没有谁是通过欲望学习游泳或做其他事的。”[3]169在封闭的环境和小群体意识影响下,菲雅玛追求真理和人格独立的勇气令人钦佩。然而,在作者谢拉·科勒的笔下,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完美无缺的。菲雅玛致命的弱点在于她身体的顽疾——哮喘。在同伴们的围追和折磨下,菲雅玛最后因哮喘发作而死去。
几近完美的菲雅玛与西蒙就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担负着向世人揭示真理,启迪灵魂的神圣使命。可是,他们的命运却同样悲惨,同样孤独与苦难,善良的行为不被世人理解,最终被钉上了命运的“十字架”。
3.黛与拉尔夫
拉尔夫是《蝇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头发金黄,又高又瘦,肩宽背阔,体格健壮,将来也许能成为一个拳击家,不过他的嘴巴和眼睛却很温柔,没有半点邪恶的神情。”[4]21良好的家庭背景让拉尔夫身上具有一定的领袖气质。困居荒岛后,他最先想到如何获救。他以海螺为集结号,按照一种文明社会的方式和原则组织孩子们在岛上求生,等待救援。可是,随着杰克“君王”地位的确立,拉尔夫主张的民主式管理方式和制度迅速失去效力,他的地位也随之受到撼动。拉尔夫发现他的提议在强大的杰克面前失败后,转入到对力量的崇拜中来,心中的“兽性”逐渐占据上风。在扮演猎手的游戏中,温柔的拉尔夫竟然高喊“宰了他,宰了他……”挥舞着长矛向罗伯特扮演的野猪刺去。让人吃惊的是,拉尔夫这个崇尚文明的少年最后居然参与到危害西蒙的行动中。事后,他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耻辱和自责。
《裂缝》小说中,黛是G小姐挑选的游泳队队长,也是女孩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她是看上去成熟、理智,虽然不满学校封闭的管教体制,却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性,还鼓励其他女孩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融入寄宿生活。她是众女孩生活和思想上的领导者。在她的领导下,女孩儿们个个安分守己。黛与G小姐的关系颇为微妙,像师生,更像姐妹。G小姐时不时分享的小秘密、偶尔的少许赞扬都让黛兴奋不已。在她心中,G小姐是完美无缺的,她迷恋并时刻模仿G小姐,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G小姐一样“成功”的女人。菲雅玛的到来让黛如坐针毡,这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族女孩抢走了自己的风头,使自己的权威受到极大挑战。更重要的是,G小姐的目光和关注也开始被菲雅玛吸引,这是任何人都没受过的“优待”,令黛等一众女孩无法忍受。恐惧和嫉妒的情绪在这个小团体中蔓延开来。大家坚信G小姐对自己的冷落与忽视是菲雅玛的错。要求菲雅玛对G小姐“好些”,以便G小姐对她们“好些”,甚至还提出要菲雅玛“牺牲自己来换取大家的幸福”。女孩们对菲雅玛的感情已渐渐转变成恨意。这种恨意逐渐演变成一种极其强烈的个人仇视,归根结底是因为她们害怕面对自己心底的真实想法,害怕承认自己对菲雅玛身上那种特质的渴望与惧怕的矛盾心理。因此,她们只好把这样的感情转化为浓浓的恨意,发泄在菲雅玛身上。当发现菲雅玛与G小姐“有染”后,人性中残暴的力量找到了出口。黛带领着同伴疯狂殴打折磨菲雅玛,直到菲雅玛没了气息。最后,黛带着忏悔和歉意离开了这所承载了她太多回忆的地方。
黛与拉尔夫原本都是理性和文明的拥护者,却因为自己在群体中的权威受到质疑和挑战,将人性中的暴力显露出来,犯下难以饶恕的可怕罪行。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并没有沦为“撒旦”一样的魔鬼,思想上仍有文明的痕迹,深深地为自己的行为而负疚。
(三)主题的相互呼应
两部小说中,作者都以现实主义叙事手法,揭示人类生存状况,主题存在显著互文性。
1.人性的恶与善、堕落与救赎
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至今,关于人性善恶的探索从未间断。参加过战争的戈尔丁就是其中一员。在他看来,人类的本性就是邪恶的:“凡是经历了那些烽火岁月的人,如果看不到人类产生邪恶如同蜜蜂酿蜜一样,那么,他们不是瞎子,就是头脑有毛病。”[5]《蝇王》的悲剧故事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女作家科勒虽未经历战争,但妹妹离奇地死在南非一所寄宿学校的事实,让她对人性的善恶有了格外透彻的反思与认识。在《裂缝》中,作者煞费苦心选择了一群青春期少女为主人公,让她们在远离父母和家庭的寄宿学校独自生活。她们本可以凭借自己的纯真与善良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乌托邦”,却抛弃了文明社会的教诲。尽管有学校、宗教和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她们最后还是变成了自相残杀的“暴徒”。作者在展现孩子们内心世界的过程中,突出了潜在她们心中的一股“神秘”力量,这股力量无形地控制着她们的行为,将暴力和攻击倾向展露无遗。这股力量就是蛰伏于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性之“恶”。“恶就像深埋在人的心里的颗种子,如果有合适的环境就会开出毒花,结出恶果。”[6]恶不是偶然的意识外显,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类似一种“种族印记”,也就是著名哲学家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它既不是生育个人的经验,也不是个人后天获得的,而是生来就有的。”[7]它在人的一生中几乎从未被意识到,却会深刻地影响个人乃至社会的各种行为,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法规避的。
当然,无论是戈尔丁还是科勒,在作品中浓墨重彩地表现人性的邪恶与堕落的意图绝不仅限于此。他们更希望人类能直面恶的一面,认识自身的缺失与不足。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两部作品中隐含了向善与救赎的主题。西蒙与菲雅玛两位人物被精心塑造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树立一个邪恶的对立面和散播真、善、美与希望的榜样。拉尔夫和黛为代表的少男少女在最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悲泣自责,恰恰说明了人类只有在直面和认清邪恶后,才能走上向善的道路,经历了灵魂的黑暗是获得救赎的必经过程。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开篇指出:“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完全一样的。”[8]他认为,趋向至善和上帝荣光的“向上的道路”与直面人性的邪恶和经历灵魂的黑暗的“向下的道路”都指向了与上帝之道沟通、获得灵魂拯救的道路。这种人性的邪恶与善良、堕落与救赎转换的思想完全可以从两部作品中找到痕迹。
2.群体的冲动性与轻信性
《蝇王》与《裂缝》两部小说都聚焦处于青春期的少男或少女的群体心理问题。日本社会学家岩原认为,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宿感,存在着互动关系复数个人的集合体。”[9]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有显著的不同。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认为,在一个群体中,个人的后天习惯的特殊性会被抹杀和淹没,因而他们的个性也会消失。这样一来,种族无意识的东西会冒出来,同质的东西则淹没了异质的东西。[10]《蝇王》的第九章描述了在一个电闪鸣、风雨交加的夜晚,孩子们为了摆脱恐惧,在杰克的带领下跳起了捕猎舞,猎手们越来越兴奋,边跳边叫着“杀野猪!割喉咙!放鲜血!”最后竟然把跌撞而来的西蒙当作怪兽活活打死。《裂缝》中女孩们的暴力行径更加惨无人道。当菲雅玛告诉同伴G小姐在说谎时,愤怒和妒火填满了黛的内心,于是她提出“既然菲雅玛能够做G小姐的玛德琳,也可以做我们的。”①集体兴奋被点燃,女孩们追逐虚弱的菲雅玛到了墓地,有节奏地高呼着:“抓住他!抓住他!”“揍她!揍她!”[3]184可怜的菲雅玛被绑住手脚、塞住嘴巴,“躺在那里就像祭台上的祭品”[3]187。女孩们把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用力地向菲雅玛下体塞去,将她折磨至死。群体的影响力就像磁铁一样吸附着每一个人,使个体很容易受到狂热情绪的感染,意志力和判断力彻底丧失,就像被催眠师催眠一样,成为屈从于本能冲动而行事的“野蛮人”。
群体心理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轻信性。“一个群体极易轻信,也极易受外界影响。它没有什么批判的能力,也不存在什么未必确实的事情。”“如果对某种事物存在一丁点儿怀疑,这种疑问就会立即转变成一种无可争辩的确定性。”[11]《蝇王》中当第一个小孩提到野兽,恐惧便开始在大家的心中生根。当负责守夜的两个孩子发现了飞行员的尸体,便立刻把它当成怪兽。拉尔夫和杰克在寻找的过程中,“怪兽”一露头,便仓皇而逃。《裂缝》中在周末的礼拜上,女孩们看到姗姗来迟的菲雅玛因疼痛晕厥后,便有人开始猜测菲雅玛与G小姐在前晚发生了什么。看到G小姐对菲雅玛举止亲昵,大家便更加坚信是菲雅玛勾引了G小姐,任凭菲雅玛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她们宁愿相信是菲雅玛这个“撒旦”,让一直宠爱她们的女神G小姐“抛弃了她们。
从两部小说的可以看出,即使是单纯、天真的青少年处于群体中也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群体心理的控制,产生对权威的崇拜,从而一步步地跌入邪恶和黑暗的地狱。
三、结语
表面上看,《裂缝》与《蝇王》这两部相隔45年之久的作品没有任何渊源。然而,通过仔细的交叉阅读后,会发现两部小说在场景、情节、人物、主题等设置与创造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具有显性互文关系。
互文性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是将两个或多个有联系的文本并列比较。通过对其中共同点的挖掘和阐释,不仅可以加深对本文本身的理解,还能够揭示某些文学现象。在百变的世界文坛中,科勒与戈尔丁两位作家背景不同、经历各异,为何她们的作品却体现出如此显著的互文?仔细推敲后会发现,她们的互文文本绝不仅仅缘于技巧层面的影响和借鉴,而是来自思想上的共鸣。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不断地经历诸如战争、杀戮等生存状况的典型处境,或者称为一种“原型”,经过漫长的演变已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生活中有多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刻进了我们的精神构造中,它们在我们的精神中并不是以充满着意义的形式出现的,而首先是‘没有意义的形式’,仅仅代表着某种类型的知觉和行动的可能性。当符合某种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12]《裂缝》与《蝇王》所体现的高密度互文正是两位作者在“本能驱力”下表露出的对人类生存“原型”的忧虑与思考。可以说,二者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交相辉映,共同谱写出一曲哀悼人性的挽歌。
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指出:“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它文体才可能理解它。”[13]以互文性理论审视《裂缝》与《蝇王》两部作品,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谢拉·科勒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内涵。我们通过比较两部作品不难看出,《裂缝》实则描述了又一个关于“童心泯灭和人性黑暗”的失乐园故事,堪称“女性版”《蝇王》。如果说戈尔丁在《蝇王》中成功塑造了由善向恶的经典儿童形象,在远离文明世界的情况下他们本性中的残酷、兽性渐次爆发,那么在《裂缝》中这些青春美少女则将人性中的“暴力倾向”演绎得更加彻底,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又身处文明社会,仍然无法避免“自相残杀”,人类罪恶本性一览无遗。“在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谢拉·科勒用她一贯优雅的写作风格对声色感观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凭借独特的女性视角、细腻的叙事语言,科勒笔下的《裂缝》仿佛具有无限魔力,深深吸引着读者。我们在为小说所揭示的人性感到震惊、不安与悲伤的同时,也深深领悟到这位非裔女作家对“人类面带微笑”的普世情怀。
[注释]
①玛德琳(Madeline)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819年的长诗《圣·爱格尼斯之夜》(The Eve of St. Agnes)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小说中是女孩子们私底下以这首诗中的故事为原型玩的一个游戏。
[参考文献]
[1]Kristeva, Juli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36.
[2]哈罗德·布鲁姆. 误读图示[A].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970.
[3]Kohler, Sheila. Cracks[M].Cambridge:Zoland Books Inc.,1999.
[4]威廉·戈尔丁. 蝇王[M]. 龚志成,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魏颖超. 英国荒岛文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160.
[6]陈静. 燃烧的方舟——从《蝇王》看戈尔丁的人类生存境况观[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科学版, 2008 (11): 6.
[7]荣格. 荣格性格哲学[M]. 李德荣,编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3:32.
[8]Eliot, T. S.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World[J]. American Prefaces, 1935(11): 20.
[9]田宗介. 社会学事典[M]. 东京: 弘文堂, 1988:439.
[10]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7.
[1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论文明[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157.
[12]荣格. 荣格文集[M].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7:90.
[13]乔纳森·卡勒. 符号的追寻[M]. 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81:77.
[收稿日期]2016-01-15
[作者简介]李楠楠(1981- ),女,讲师,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7-0120-06
A Study of Intertexuality betweenCracksandLordoftheFlies
LI Nan-nan
(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ts,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0, China)
Abstract:Intertextuality criticism theory focuses on mutual dependence and characteriz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exts. As a means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meaning, intertextual relations is a popular paradigm in postmodern writings. An explicit intertextual relation is explored between Cracks and Lord of the F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sett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the depiction of main characters and themes. Through the crisscross reading,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novels is explicated and new meaning is generated.
Key words:intertexuality; Cracks; Lord of the F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