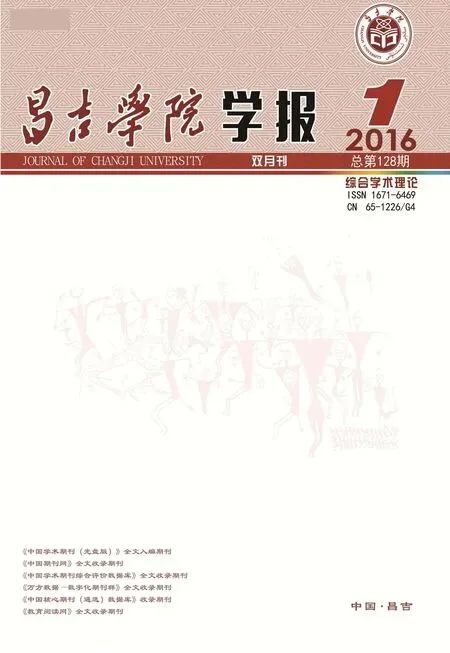雅俗的完美统一
——论陇东革命歌谣的艺术品格
张文诺
(陇东学院文学院 甘肃 庆阳 745000)
雅俗的完美统一
——论陇东革命歌谣的艺术品格
张文诺
(陇东学院文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摘要:陇东革命歌谣是中国革命歌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几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陇东民众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之作。陇东革命歌谣实现了民间形式与革命主题的完美统一,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实现了在革命与传统、主流与民间、雅与俗之间的无缝对接,成为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种成功的文艺形式与革命文化。
关键词:雅俗;艺术品格;陇东革命歌谣
革命歌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根据地,都产生了一批革命歌谣。由于陇东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像其它根据地那样发生断裂,在众多的革命歌谣中,陇东革命歌谣是非常成熟、独特的革命歌谣。陇东革命歌谣是中国革命歌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几年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中,陇东民众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之作,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民间艺术家如孙万福、汪庭有、刘志仁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赋予了陇东歌谣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更加强盛的生命力、战斗力,开辟了陇东歌谣的新境界。”[1]在革命文化的影响下,在陇东民间文化的哺育下,陇东革命歌谣取得了全新的艺术品格。
一、革命现实的反映和革命情感的表达
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2]而歌谣是最原始形态的民间文学,“歌谣从来是人民心声的自然流露,它也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时代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3]因而,陇东革命歌谣是对近现代陇东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和革命情感的表达,陇东革命歌谣实现了由表现礼俗到反映现实生活的转变,由娱神敬神到歌颂革命的转变,这就扩大了歌谣的题材范围与主题思想。陇东民间歌谣有不少内容是与祭祀、娱神、礼俗有关,题材相对来说不够宽泛。陇东革命歌谣逐步摆脱了鬼神文化、巫覡、各种崇拜文化及宗教文化影响,集中反映现实生活。陇东革命歌谣真实地反映了陇东底层民众的生活、情绪、要求、愿望,记录了陇东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传达了陇东底层民众的时代情绪,是陇东革命现实的反映和陇东民众革命情感的表达。
陇东革命歌谣立足于陇东社会现实生活与革命斗争历程,揭示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揭露封建礼教与礼俗的罪恶,反映大生产运动与劳军拥军的热情,歌颂革命根据地与革命领袖,展开了当时陇东的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人情的形象画卷,具有极大的认识价值。比如《豹子川大合唱》唱道:“自从来了刘志丹,咱们的日子不一般。打倒了土豪与地主,推翻了军阀和赃官,没有地的人民有了土地,没有穿的有了穿。自己动手自己享,没有人再来抽税捐。这儿的人民相亲相爱,这儿的人民上了天。”这首歌谣通过对比唱出了陇东的社会现实,阶级对立、贫富分化,陇东人民深受军阀、地主、赃官的欺压,苦不堪言,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必然性。陇东革命歌谣还展现了陇东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情感世界,反映了陇东人民深层次的政治心理与文化心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不满,谋求社会公正合理,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是根据地民众投身革命的直接政治心理动因。”[4]在旧社会,底层民众常把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命不好、自己没有福气。“福/命思想不仅使伦理道德与超自然因素发生分离,而且还派生出一种反道德的‘无限忍耐'的立场。它彻底地悬置了道德判断,泯灭了善恶是非之间的差别。”[5]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陇东民众明白了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他们不再把自己的贫穷归结为命运,他们具有了全新的革命意识。
更为重要的是,陇东革命歌谣还把革命理想与世俗幸福结合起来,他们对世俗幸福的怀想正是他们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动力。如“靠自己,不求神,子子孙孙满堂红,勤苦劳动加油干,谷子糜子堆成山,堆呀堆成山,有吃又有穿。勤劳动,全家乐,余粮满囤有吃喝,人财两旺靠自己,双喜临门享安乐,多呀多安乐,全呀全家乐。”其实,陇东民众的理想很实际、很朴实,他们向往的是有吃有穿、子孙满堂、全家安乐的生活。在旧社会,他们的劳动成果被地主剥削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分给了他们土地、他们过上了温饱的日子,这是他们参加革命的根本动力。陇东革命歌谣中不难看到,陇东民众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向往美好的爱情,他们为了革命的胜利,不但积极劳动缴纳公粮、为八路军战士纺线、做鞋袜,而且支持自己的儿子、丈夫积极上前线。在陇东革命歌谣中,陇东广大女性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她们对自己的丈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支持自己的丈夫、情郎积极参加革命队伍。如《送郎歌》:“送郎送在大门口,一把拉住郎的手,情郎莫难受,咿呀哇得哇,情郎莫难受。送郎送在火车站,看见火车冒青烟,祝郎早凯旋,咿呀哇得哇,祝郎早凯旋。”新婚不久的小两口离别,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看到情郎依依难舍,妻子虽然也舍不得情郎离开,但为了革命的胜利,她非常体贴地劝慰、鼓励自己的情郎放心离开,并表达了自己美好的祝愿。再如《织手巾》:“七织牛郎和织女,八织鸳鸯戏水中,再织上石榴串子莲,哥哥妹妹心连心。织成手巾送情郎,千言万语再叮咛,妹妹后方勤生产,盼郎杀敌多立功。”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意,她们常常亲自制作一些东西来表达自己的深情,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显示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人的心灵的丰饶与美好。陇东革命歌谣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强烈的人民性,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方面达到了非常高的层面。陇东革命歌谣之所以深受陇东民众的喜爱,是因为陇东革命歌谣与陇东民众生活、心灵的接近,是对陇东民众革命情感的真挚表达,很容易引起陇东民众的共鸣。
二、基于赋比兴手法的优美意境
与陇东民间歌谣不同的是,陇东革命歌谣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陇东民众自觉吸取了陇东民间歌谣的多种艺术手法,创作出更成熟的艺术作品。可以说,赋比兴是中国民歌的传统艺术手法,赋比兴的用法与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与思维方式相关,朱自清先生认为起兴在歌谣中的迫切与普遍与两种关系有关:“一是我们常说到的歌谣是以声为用的,所以为集中人的注意起见,有的从韵脚上起下文的现象。二是一般民众,思想境阈很小,即事起兴,从眼前事物指点,引起较远的事物的歌咏,许是较易入手的路子;用顾先生的话,便是他们觉得不突兀,舒舒服服听着唱下去。虽然起兴的事物意义上与下文无关,但音韵上是有关的;只要音韵有关,听的人便不觉中断,还是舒舒服服听下去。”[6]朱自清先生从起源学上论述了民歌运用起兴手法的原因,但是,在赋比兴手法产生以后,由于赋比兴手法在抒情方面的效果,赋比兴手法成为民间歌谣甚至是文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手法。陇东民间歌谣在赋比兴手法的运用上还有不够完美之处,比如说,上句的起兴与下句的内容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显得有点突兀,比喻也有不够恰当之处。虽然只要音韵有关就可以,但是,内容相关更能增加艺术感染力。“比与兴不能单独作为一种完整的艺术思维方式存在,它们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完善的艺术思维方式,共同承担着情意和形象的创造与融合,同时,也呈现了其无与伦比的诗性品格。”[7]陇东革命歌谣借鉴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描写陇东革命的大好形势,烘托出优美的意境,引起读者美好的情思。《咱们的红军到南梁》深情地唱道: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的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红缨子枪,
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红军来了晴了天。
打倒了土豪分牛羊,
分了那个天地又分粮。
千年的枯树还了阳,
受苦人翻身喜洋洋。
山丹丹开花红当当,
红军跟的是共产党。
再如《中央红军到陕甘》:
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甘。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领兵的元帅是朱毛。
一人一马一杆杆枪,
咱们的红军势力壮。
千里的雷声万里闪,
革命的势力大无边。
这两首歌谣在赋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都比较成熟,“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刘志丹的队伍到南梁”这句歌谣兴中有比,写出了刘志丹革命队伍的非凡气势,很有鼓舞人心的作用。第二首歌谣描绘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势力大发展的情景,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起兴,描绘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浓缩了中央红军经过千难万险长征的辉煌胜利,很有画面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含蓄蕴藉,把情感融于物象之中。“‘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和观念(‘情'‘志'),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无论对比、正比、反比,其中都包含一定的理解成分)结合联系在一起,而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智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融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的客观形象。”[8]
陇东革命歌谣的比兴手法常常是比中有兴,兴中有比,使诗歌具有了一种象征意味,增加了诗歌的宽度与厚度,生活的密度。如《军民合作一条心》中的“青天蓝天蓝格莹莹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第一句是对根据地天气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根据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的象征。“蓝格莹莹的天”写出了歌唱者内心的轻松、愉快与明朗。达到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境界,内涵深远悠长,令人心驰神往。赋在陇东革命歌谣中得到了全新应用,赋按朱熹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形式。在陇东民间歌谣中,赋的运用不免有夸饰或者是凑数的印象。在陇东革命歌谣中,民间艺术家创造性的发展了这一手法,虽然和民间艺术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有了革命内容的支撑,夸饰与凑数的成分减少了。比如《五只花》借鉴的是秧歌调“对花”,《送夫参军》借用的是陇东小调社火调“十二月”,比如《五只花》:
(男)什么开花朝太阳?
什么人拥护共产党?
(女)葵花开花朝太阳,
老百姓拥护共产党。
(男)共产党,怎么样?
(女)好像天上的红太阳,
照的边区亮堂堂。
(男)什么开花身上暖?
什么人话儿记心间?
(女)棉花开花身上暖,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间。
(男)毛主席,说什么?
(女)号召咱们大生产,
边区要变米粮川。
(男)什么花开花大路边?
什么人坚决来抗战?
(女)马莲花开花大路边,
八路军坚决来抗战。
(男)八路军,怎么样?
(女)个个都是英雄汉,
英勇抗战美名传。
(男)什么花开花耀眼红?
什么人和咱一家人?
(女)桃花开花耀眼红,
八路军和咱们一家人。
(男)一家人,怎么样?
(女)军民联合一条心,
一心赶走小日本。
(男)什么花开花迎春天?
什么人迎接胜利年?
(女)迎春花开花迎春天,
同盟国迎接胜利年。
(男)迎接胜利怎么办?
(女)加紧准备大反攻,
抗战胜利在眼前。
这首歌谣充分体现了赋这种手法的特点,这首歌谣分为五节,第一节写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第二节写大生产给边区生活带来的美好变化,第三节歌颂了八路军的英勇抗战,第四节表现了军民鱼水情,第五节表现了边区军民迎接胜利的革命豪情。这首歌谣借用对花的调子,句式比较整齐,写出了边区多方面的生活,让人不觉得累赘。
三、浓郁的生活气息
陇东革命歌谣的作者大多为农民、士兵,或者是具有生活体验的民间艺人。他们大多选取自己非常熟悉生活、劳动或者战斗场景,传达自己的情绪。无论是歌颂领袖、歌颂革命,或者是表现拥军劳军,无论是反映大生产运动,还是描写根据地生活,不管是表现个人情怀,还是革命情绪,他们都选取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最动人的细节、画面,表达自己优美的情思。比如孙万福的歌唱领袖系列,毛泽东主席对革命的功绩表现在各个方面,孙万福选取和他自己生活最密切的方面进行描绘。“山川万里气象新,五谷生长绿茵茵,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枯根翻了身。自力更生闹革命,开展了生产大运动,为了革命得胜利,跟着咱领袖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孙万福对毛泽东主席指挥千军万马决战、写下革命著作指导抗战方面的功绩不太了解,他最熟悉的无疑一是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土地改革让他分得了土地,告别了贫苦的生活,二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他从这一角度歌唱领袖,就把领袖的功绩传达得十分自然真挚,没有丝毫的浮夸之意,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陇东革命歌谣的生活气息蕴含了一个特定地域共同体的生存情感和生活体验,形成了一种审美的鲜活性,能够获得一种最真实的感受与体验。艰苦的峥嵘岁月虽然已经过去,陇东革命歌谣仍然被广泛传唱,就是因为它能激活歌唱者、听众对过去的美好记忆。对逝去的艰苦而又可贵生活的回忆能激起歌唱者、听众对自身价值的体味。对于那些没有经过革命岁月的年轻读者来说,陇东革命歌谣的优美旋律与内容可以唤醒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那些外地的听众来说,陇东革命歌谣可以让他们感受到陇东黄土高原的人们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唤起自己对故乡的美好回忆,帮助读者留住乡愁。歌唱陇东革命歌谣,可以达到一种释放的功能,这是“一种心理的解脱,一种心灵的松弛,一种压迫被移除的快感。”[9]
四、鲜明的色彩和乐观的基调
陇东革命歌谣大多选择红色的事物进行书写,形成了以红色为主调的色彩。“显而易见,‘红'作为一种色彩并不是中性的,它的象征作用在中国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审美认同。这种审美认同并不是理性的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强加,而是跟愉悦、快感、希望和美相关联的身体经验。不仅红色本身,还可以与‘红'互文的太阳、桂花、杜鹃、梅花、火、灯笼等意象同样能引发这种积极的身体经验。”[10]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并不是一种吉利的颜色,红色象征危险,所以在“红绿灯”设置中,绿灯意味着安全,红色意味着危险。而在气象、国土等语境中,红色也通常为最高等级。我国在红绿灯的设置中借鉴了西方文化的经验,但在我们民族无意识中,红色还是一种吉利的颜色。红色蕴含着生命的活力和欣欣向荣之意,是健康、热情、温暖、自信、繁荣的象征。过年贴春联,都是用红纸写成。青年男女结婚办喜事,都要用红花、红布,生孩子过满月,鸡蛋都要染成红色的。一般重要的庆典仪式,背景都用红色底子。在陇东革命歌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与“红色”有关的事物或者颜色。比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红旗”、“芦花公鸡”、“大红公鸡”、“红火”、“红豆豆角角”、“红缨子枪”、“赤卫军”、“梅花”、“石榴花”、“鲜花”、“太阳”、“大红被子”、“红枕头”、“热腾腾的油糕”、“红枣”、“红灯”、“牡丹”、“桃花”等,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红色有热烈、红火、热闹、乐观、生机勃勃的意味。工农革命在敌人的包围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在陇东革命歌谣中,没有表现出一丝悲观、彷徨与寂寞、畏惧的情绪,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前仆后继、一往无前的豪迈与乐观。红色渲染光明、胜利的前景,虽然面对千难万险,但一想到未来的美好期许,他们心中就充满了向上的力量与勇气。“由于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人们与各种具有不同色彩的事物打交道,凭着所积累的色彩经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传达信息以至表现情感,在不同的色彩中早已储藏并积淀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意味,因而在审美中,作为自然属性的色彩便能转化为对象审美条件的构成要素,具有了一定的审美特征。”[11]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陇东革命歌谣把象征喜庆、幸福的红色延伸为革命,促进了陇东民众对革命的文化认同。“由于形势所迫,根据地多位于落后偏远地区,在这些人类学家所谓的‘小传统'社会中,歌谣(山歌)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它不仅是地方特有的传统习俗,也是底层民间社会表达情感、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一文化资源,努力把‘大众'改造为‘先锋'或者说‘新兴'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文化基础中植入了‘红色'印记。”[12]“红色歌谣借助了民间社会的审美习俗,使民众对‘红'的新内涵的接受成为一种与身体经验相联的自然过程。”[13]红色象征了革命的红火前景,激励了陇东民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豪情,红色成为陇东革命歌谣的底色与亮色。
五、重章叠句的形式
陇东革命歌谣在句式上非常灵活自然,有四言、五言、七言,更多的是字数不太统一的散文体,在这些不太整齐的句式中,由于衬字、语气词、重叠的使用,唱起来并不拗口,非常流畅。比如说:“正月里来是新春,家家户户来拥军。赶上牛羊出了门,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咳哟咳哟咳哟,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为了抒情的需要,陇东革命歌谣常常采用重章的形式,所谓重章,即重复几章,意义和字面都没有多大改变,只有几个字不同,可以形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可以把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玩花灯》: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救星灯。什么叫个救星灯?毛主席,大救星,领导穷人翻了身。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太阳灯。什么叫个太阳灯?共产党,像太阳,照亮咱们陕甘宁。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英雄灯。什么叫个英雄灯?大生产,当英雄,劳动英雄真光荣。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王八灯。什么叫个王八灯?顽固派,小日本,勾结起来害百姓。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拥军灯。什么叫个拥军灯?军爱民,民拥军,军队人民一条心。
这是一盏什么灯?这是一盏民兵灯。什么叫个民兵灯?八路军,自卫军,组织起来打日本
这首歌谣借用陇东典型的小调“对花”的形式,把对革命的礼赞、祝愿等心理表达出来,充满着对革命良好的情感,这是陇东边区民众最为真实的情感流露,以传统的民间形式容纳了新时期朴素真挚的情感思想。
为了歌唱的需要,陇东革命歌谣常常使用叠字。陇东革命歌谣在叠字的使用方面很有创造性,有各种各样的叠字。AA式,如,隆隆、嗡嗡、线线、娃娃、角角、豆豆、朵朵,在AA式中,既有名词与名词,也有形容词与形容词,还有量词与量词,还有象声词。ABB式,如一面面、一对对、一道道、一杆杆、一把把、一捧捧、红艳艳、绿茵茵、乐哈哈、吱咛咛、金灿灿、喜盈盈、喜洋洋、闷沉沉、红冬冬、格咛咛、绿夹夹、滴溜溜、白生生、红彤彤、香喷喷、亮堂堂、短缨缨、忽闪闪、明灿灿,这类词最多,有数词与量词的组合,也有A格BB式,如蓝格莹莹,AABB式,咯咯咛咛、时时节节、家家户户、AAB式,如朵朵红、花花红、叶叶青,ABA,如,心连心,红又红,肩并肩,白生生不但写出了人的皮肤的白,还写出了皮肤的嫩;红艳艳既写出了花的颜色,也写出了花朵怒放的情态;红冬冬既有颜色也有声响,视觉与听觉交织在一起,令人印象深刻。重叠的使用,突出了词语的意义,增强了形象性,增加了音乐美,给人以字音协调、节奏鲜明、形式匀称的美感。重叠的表现法,是民歌的常用的表现手法,顾颉刚先生说:“对山歌因问作答,非复沓不可。……儿歌注重于说话的练习、事物的记忆与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复沓的需要。”[14]钟敬文先生说:“这种歌每首都有两章以上重叠的,全部几乎没有例外。……这种歌的回环复沓,不是一个人自己的叠唱,而是两人以上的和唱。我又想到对歌合唱,是原人或文化半开的汉民族所必有的风俗,如水上的疍民,山居的客人,现在都盛行着这种风气,而造成了许多章段复叠的歌谣。”[15]“陕北民歌中重叠最主要的作用是‘生动化',即让普通词语附带上小巧可爱、亲切可人、惬意可心等意味,是一种爱昵的使用法。”[16]陇东革命歌谣的重叠不但可以增加形象性,还可以增加音乐美。通过反复咏唱,把那种满足、幸福、兴高采烈、扬眉吐气的心理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很具艺术感染力。
陇东革命歌谣是陇东民间歌谣在革命斗争时期发展的必然,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它必然会反映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陇东革命歌谣实现了民间形式与革命主题的完美统一,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陇东革命歌谣的发展与成熟与革命文化的推动分不开,承载了一定的宣传、政治功能,然而,陇东革命歌谣也没有完全消解自己的艺术形式,它仍是一种民间文艺形式,陇东革命歌谣在承载革命意识的同时,也保存了民间文艺的那种泼辣、自由的特征,陇东革命歌谣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的典范,以旧形式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内容,体现了在革命与传统、主流与民间、雅与俗之间的无缝对接,成为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一种成功的文艺形式与革命文化。
参考文献:
[1]高文,巩世锋主编.陇东红色歌谣前言[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2.
[2]拉法格.拉法格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9.
[3]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中国歌谣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
[4]曹敏华.革命根据地社会变动与民众社会心理嬗变[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6):57.
[5]周福岩.民间故事的伦理思想研究: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6.
[6][14][15]朱自清.中国歌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91.
[7]李健.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01.
[8]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9.
[9]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2.
[10][12][13]曹成竹.关于歌谣的政治美学——文化领导权视域下的红色歌谣[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2):111.
[11]朱立元.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26.
[16]张军,张咏梅,徐彤.语言学方法与陕北民歌研究[J].榆林学院学报,2006,(5):4.
中图分类号:I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69(2016)01-0077-06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甘肃省庆阳市科技局项目“陇东革命歌谣的当代价值研究”(MS2014-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诺(1976—),山东阳谷人,文学博士,陇东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