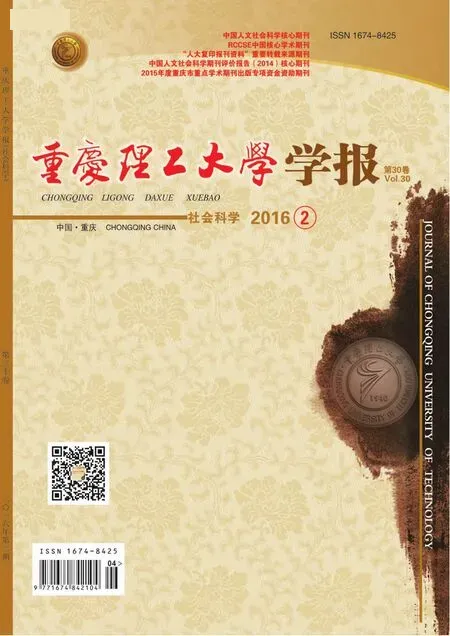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余 萍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1120; 2.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重庆 408000)
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余萍1,2
(1.西南政法大学 法学院,重庆401120; 2.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重庆408000)
摘要: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关键词:社区矫正;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保安处分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2012年1月联合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社区矫正制度为轻微犯罪人回归社会提供了一座“金桥”,减轻了犯罪人对社区的敌视,对于预防再犯罪具有积极意义。据统计,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一度被控制在0.2%左右的超低水平[1]。然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成效却始终不尽人意。首先,实证调研结果反映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远高于成年人*笔者对C市F区司法局下属L街道司法所的调研结果显示,该司法所辖区从2012年至2015年8月止,共接收成年社区矫正对象225名,其中社区矫正期满后再犯罪的有2名,再犯罪率为0.89%;接收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9名,社区矫正期满后再犯罪的有2名,再犯罪率为22.22%。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再犯罪率远高于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学者许晓娟、张京文对南方某市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情况的实证调研也支持上述结论。。其次,我国的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暂于监外执行”的犯罪人,大量具有“不良行为”的罪错未成年人被排除在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之外,得不到相应的社区矫正,处于“脱管”状态。
鉴于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困境,笔者认为有必要跳出传统刑罚体系的藩篱,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进行重新定位,将其适度剥离出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制度框架,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重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一、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矫正制度的运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针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轻微犯罪行为以及再犯罪的可能,提出了监禁刑与非监禁矫正的差别化处遇措施。其中,非监禁矫正制度又分为社区矫正模式、监护人严加管教模式、工读学校模式、收容教养模式、检察机关矫正模式等其他矫正模式[2]。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非监禁矫正制度主要存在如下不足:
(一)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
不良行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前兆。多数未成年人在犯罪前就已经具有夜不归宿、不良交友、逃学、打架斗殴、吸烟等不良行为,并处于家庭、学校无力监管的状态[3]。这既与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不良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矫正制度过分强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忽视惩治手段所内蕴的保护价值紧密相连。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4条的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是未成年人法定教育主体,负有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只有督促父母、其他监护人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一旦上述教育主体处于缺位或不利状态时,相当数量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矫正工作就会出现相应问题。在此意义上来讲,必要的法律干预手段(包括社区矫正)反而是阻止未成年人从不良行为边缘滑向违法犯罪深渊的最有效方式。特别是在父母、学校无法管教时,基于国家亲权理念,作为“替补监护人”的国家应毫不迟疑地运用法律干预手段担负起教育未成年人的责任。
(二)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手段有限
目前,我国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正渠道主要分3种:一是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二是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处罚;三是收容教养。但3种矫正渠道各有弊端,使得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矫正手段大多流于形式。
1.工读学校的标签效应与“交叉感染”
工读学校教育作为矫正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重要方式,曾帮助一大批处在违法犯罪边缘的未成年人改掉了不良行为,顺利重返社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工读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也在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首先,工读学校的封闭式管理隔绝了未成年人与家庭、社会的联系,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的发展;第二,作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集中聚集地,工读学校给“交叉感染”提供了可能;第三,工读学校的“标签效应”使得许多家长宁肯让自己的孩子在社会上闲逛,也不愿将其送到工读学校去接受矫正。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曾有300多名学生的北京门头沟工读学校,到2014年5月只有两名学生上课[4]。 工读学校招生正呈现逐年萎缩的发展趋势,大量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基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管教和矫正,极易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2.治安处罚的短期效应和放任嫌疑
治安处罚作为矫正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第二种渠道,具有比工读学校教育更强的惩罚性和威慑力。但短暂的拘留*我国法律规定,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处罚规定的,将受到不超过15日的行政拘留。根本不会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产生任何有效的矫正效果,反倒让未成年人拘留期满后很快就对法律失去了敬畏感。特别是治安处罚的后续矫正措施几近于无,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速了那些经历短暂羁押的、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迈向违法犯罪的步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治安处罚本身具有放任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之嫌。
3.收容教养缺乏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
收容教养是一种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来规范未成年人行为的矫正手段,它针对的对象是其行为已触犯《刑法》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但收容教养也只是将有犯罪可能性的未成年人暂时隔绝于社会,在一定时期避免其危害社会,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虽然未成年人在收容教养期的行为能够符合监管要求,但缺少亲情关护、交叉感染、标签效应等问题极易导致未成年人的心理出现偏差,若不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当这些未成年人收容教养期满后,将难以避免地再次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对不起诉未成年人的后续矫正不到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视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悔罪表现、监管条件等,对已经构成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微罪不起诉或者附条件不起诉处理,以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让未成年人免受监禁刑之苦。但如何矫正被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却是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
第一,法律上未对微罪不诉的未成年人如何开展后续帮教、矫正进行任何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由构成微罪不起诉的未成人的监护人对其进行日常管教,检察人员间歇性地开展为数不多的回访教育,很难对未成年人进行持续的行为矫正与专业的心理疏导。
第二,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负有监督考察之责,监护人负有管教之责,司法实践中也形成了检察机关牵头联合其他部门共同承担或自行承担更进一步的矫正教育工作两种模式[5]。但两种模式都使检察机关面临着“资源有限、专业不足、勉为其难”的问题,而且这种考察、帮教本身也与检察机关自身的职能定位存在不相称的问题[6]。
(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虽然我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3条特别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与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并实行特别的身份保密制度。但由于该条款只是笼统的宣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采取有益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监督管理措施及相应的教育、心理辅导等方式,而未认真区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首先,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难度远高于成年人,因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以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等重罪行为人居多[7],自控、自律能力远低于成年人;其次,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主体的从业资格,无专业性可言,并且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数量严重缺乏*有数据统计,截止到2014年10月,重庆市辖区内每个司法所平均不到2名工作人员。笔者对C市F区司法局下属L街道司法所的调研结果也显示,该所截至2015年8月,共有矫正工作人员3名。,造成未成年人心理测试与矫正的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其三,设置的惩罚措施相对简单,只规定“违反社区监管纪律,在三次警告无效后,将面临重新收监的严重后果,缺乏中间缓冲地带,对涉世不深、处于青春懵懂期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监督作用。所以,现行社区矫正制度导致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事实上处于监管无力、手段单一、流于形式等状态,不利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破解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实践问题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未成年人矫正制度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缺乏单独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进一步突出国家对未成年人矫正工作的主导地位,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建构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内涵。
(一)突出国家在矫正未成年人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社会价值观念愈来愈多元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离异家庭子女等现象益发普遍[8],由此带来的家庭教育缺失、家庭关系紧张、亲子沟通不畅、心理健康欠佳等问题,使得未成年人极易偏离正常的成长轨迹,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9]。实践已反复证明:现代社会的家庭和父母已难以完全负担未成年人的矫正重任,国家应在矫正未成年人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也是《儿童权利公约》的明文规定,充分体现国家亲权理论在少年司法中的具体运用。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处于家庭残缺、贫穷、父母无力管教等不利条件的未成年人提供国家监护,避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当前,由国家指引社会力量介入未成年人教育,帮助未成年人的父母履行管教职责,不失为一种现实的路径选择。当然,由国家主导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意味着国家就必须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事必躬亲”。毕竟,专业化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队伍不是短期可以打造的,而且国家过于深入地干预家庭生活本身也不一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矫正体系之外的未成年人矫正体系
认知心理学认为,未成年人正处于成长过程中,其行为恶性小,可矫治的潜力大,宜通过专门的少年司法制度来帮助他们[10]。若忽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心理、生理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对二者处以同样的刑罚,势必使得未成年人失去社区矫正的机会,影响其一生的发展。对于未成年人不应只考虑先前犯罪行为,而应更多地关注其后续的矫正可能性与再犯可能性。须知,不同的处遇方式蕴含的是新派刑法与旧派刑法在刑罚目的、处罚责任等方面的争论。成人刑法更多体现的是旧派刑法学观,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张行为主义、道义的责任、报应刑、一般预防[11];少年司法本身就是新派刑法学的创立与发展的产物,强调的是行为人主义、社会责任、教育改善刑、特殊预防。两者对于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位是不同的,体现了有“广狭义”之争的不同的“社区矫正”理论,当然,对矫正对象的选择和措施的设立亦应有所差别。
在成人刑法中,社区矫正应定位为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与其他刑罚措施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将执行场所放在社区里,但本质依然是惩罚性,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会受到必要的限制,行为也要随之限缩。概言之,为维护社区安全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将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限制在经过刑法审判的轻微犯罪人的范围是必要的。与之相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则更多地体现出社会保安处分的性质,而非监禁刑的替代措施,注重的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教育与心理矫正,而不是单纯限制人身自由。申言之,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从具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不起诉的且缺乏家庭管教的未成年人扩展到犯罪少年的范围,并没有违背人权、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而恰恰是国家对儿童的福利。
在少年司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习惯的矫正已经成为共识,如美国少年法院管辖的身份犯罪案件*身份犯罪案件是指未成年人实施的不良行为的犯罪,不良行为主要包括离家出走、逃学、吸烟、饮酒等。。对该类身份犯罪的未成年人的矫正往往在社区矫正机构中进行[12]。而日本对虞犯的行为矫正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行为偏差的不良少年的处理均带有社区矫正的性质。推及而来,在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的矫正可以依托于社区矫正制度,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司法成本。如果在我国逐渐成熟的社区矫正体系外,针对家庭教育缺失的未成年人再探索一套矫正体系,无疑会造成机构重复设置,人员冗杂,势必浪费国家财力与人力,而将因家庭教育缺失而导致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的矫正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定位、对象范围、措施方法有根本性的区别,构建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建立专门机关和招募专业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是破解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实践问题的现实出路。
三、独立建构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设想
独立建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是对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重大改革,必须紧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和成年人社区矫正在法律理念、职能定位上的差异性,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适度剥离出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进一步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和专业的保安处分制度,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矫正体系。
(一)制定专门的《少年处遇法》
当前,我国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处遇与矫正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之中,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专门以未成年人为立法对象外,其余法律法规均以成年人为立法对象,仅在专门章节或条款对未成年人加以特殊规定,未能突出未成年人矫正的特殊性与处遇的轻缓化;而且,监禁刑矫正、工读学校、收容教育、治安处罚、社区矫正等矫正措施分布在多部法律与实施办法中,体系化不足,矫正措施之间缺乏相应的衔接,无法形成制度合力。因此,构建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第一步就是尽快制定专门的《少年处遇法》,建立有别于成年人刑法的少年司法体系,将未成年人的处分措施由单一的监禁刑转变成监禁刑与保护处分并存,并以保护处分为主的二元矫正体系。同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贯穿于各类保安和处分措施之中,实现对未成年人轻微违法行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全程矫正。
(二)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
专业的矫正人员和管护机构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独立化的组织保障。要真正实现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中脱离出来的目标,必须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如设立儿童福利局,负责社会志愿者招募、人员培训、社会调查评估、矫正方案制定与实施、心理矫治与疏导等各项工作。同时,为确保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效性,针对缓刑、假释、附条件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轻微违法行为、不良行为以及严重不良行为等不同类型的未成年矫正对象,应组织具有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员对其进行分类指导。对于那些具有严重不良行为或一般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在其家庭管教不力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应当主动介入,给予其系统的行为矫正和心理辅导。概言之,政府应主导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并鼓励社会志愿者积极参与、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和人民法院居中裁判,以此形成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积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再犯罪。
(三)构建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
在扩大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以满足不同类型未成年人的矫正需要,避免社区矫正流于形式。比如,通过组织假日辅导机构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矫治辅导;组织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对相对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人进行社区矫正;建立具有福利性质的社区教养机构对那些具有严重不良行为且家长无力监管的未成年人以及附条件不起诉且在本地无固定居住地的未成年人进行行为矫正与心理疏导;开设家长培训学校,帮助家长树立现代的教育理念,学习正确的教育方法,建立与未成年人积极沟通的渠道,重塑良好的亲情关系;引入社区恢复性司法制度,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工读学校的投入,保障工读学校正常的教育经费开支,并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社区矫正体系中,让那些尚在义务教育年龄的、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能够在工读学校学有所成,为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奠定职业基础。当然,工读学校自身也应转变教育观念,开门办学,大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工作,定期安排学生进入社区参加公益活动,消除与社会的隔阂,破除社区居民对工读学生的偏见,避免“标签效应”。即使是那些触犯刑法但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应尽量让他们通过社区矫正回归社会。收容教养应改变其行政矫正的性质,而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收容教养所应成为与社区紧密相连、充满关爱的感化教育所。被矫正对象在收容教养所中应得到专业人士的心理辅导及行为矫正,避免再次犯罪。
当然,在多元化社区矫正模式的基础上,不同类别的矫正模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既有助于督促被矫正对象遵守既定规则与义务,也有利于激励被矫正对象自觉改正,提升社区矫正实效。
参考文献:
[1]姜爱东.狠抓落实、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J].中国司法,2015(3):17-20.
[2]吴宗宪.论未成年犯罪人矫正的主要模式[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1):32-42.
[3]路琦,董泽史,姚东,等.2013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下)[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4):28-42.
[4]林艳.北京工读学校现状:“门头沟工读学校只剩两名学生”[N].北京青年报,2014-05-26.
[5]张寒玉,吕卫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13(9):29-34.
[6]彭玉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析[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5):54-59.
[7]廖新兰,罗倩.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其预防——渝东南地区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6):62-68.
[8]常宇刚.新时期重庆市青少年犯罪研判与对策[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7):82-86.
[9]操学诚,刘桂明,路崎,等.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J].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4):4-15.
[10]张文娟.中美少年司法制度探索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1]张明楷.刑法学[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2]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何培育)
Study on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YU Ping1,2
(1.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2.Fuling District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ongqing City, Chongqing 408000, China)
Abstract:This essay explored the reasonable pa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of China on the theoretically basis of parens patriae and by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firmation of juveniles and that of adults on penalty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s of the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and set up independent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institutions by complying with the relevant specialized legislation to construct a juvenile community system with government-led, community involvement, diversified supervision assisted by the judiciary, and step arrangement according to many existing issues in our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such as the absence of correcting the bad behaviors, the limits on correcting the serious misconducts, the defects in the subsequent correction of juveniles with the decision of not to prosecute, the issue that the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becomes a mere formality and so on.
Key words:community correction; the principle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security measure
文章编号:1674-8425(2016)02-0098-06
中图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425(s).2016.02.016
作者简介:余萍(1974—),女,四川邻水人,检察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重点课题“跨区域社区矫正实务问题研究”(CQJCY2015B12)
收稿日期:2015-09-11
引用格式:余萍.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2):98-103.
Citation format:YU Ping.Study on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of Juvenil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2):9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