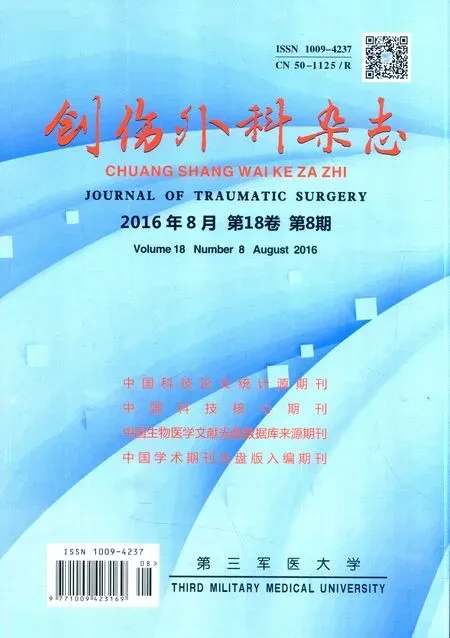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的发展历史与诊断标准的进展
贾梦潇,王 翰,张岫竹
·综述·
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的发展历史与诊断标准的进展
贾梦潇,王翰,张岫竹
创伤后应对各种实际与潜在损失的能力以及对机体功能障碍的适应性,不仅是决定躯体功能康复与再适应的关键,也将是决定创伤患者创伤后生存质量的关键。是否能够适应“创伤”这一应激性事件对人体整体包括躯体与精神的影响,决定创伤后的社会功能。创伤后引起生存质量降低的最常见疾病即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本文从这一疾病的认识历史、诊断标准进展的角度进行综述,为创伤医护工作者认识并积极筛查该疾病、早期正确有效干预奠定基础。
创伤; 创伤应激障碍综合征; 诊断
创伤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主要威胁青壮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人为(interpersonal)或者意外(accidental)导致的各种伤害已经成为24~44岁青壮年人群首要死亡原因。2009年,WHO在巴西召开的全球创伤救治论坛大会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因伤害(injury)死亡的人数高达580万,其中>90%都发生在低-中等收入国家,而相应的伤残与经济损失也相当巨大。因此,如何适应创伤导致的各种生活变化,如后遗症、截肢、以及潜在的经济、社会功能的损失,并仍可保持良好的行为能力是提高创伤后生存质量、降低各种疾病负担的关键,成为了现代社会健康定义的基本需求。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长期影响创伤后生存质量以及增加创伤后疾病负担的重要原因,不仅出现一系列心理病理症状,进一步还将反过来影响躯体健康,导致伤口愈合减缓、并发症发生风险增加等。因此,早期筛查并及时有效干预可促进创伤早期愈合,提高伤员生存质量。
显然,PTSD常见起病原因不仅仅只是躯体实质性的创伤,自认可能威胁生命安全或导致严重损伤的事件均是PTSD的诱发因素,但往往这类高危人群同时也兼具创伤发生的高危因素,如儿童期负性成长经历、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学历以及其他高危犯罪行为相关的活动,如药物滥用、驾驶超速等。因此,PTSD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是创伤的后果,两者间危险因素的重叠使得创伤-PTSD之间更可能互为因果、交互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从创伤救治的角度,对于创伤救治的预后、降低创伤患者再次因伤入院率,防控创伤发生等而言,重视PTSD将对提高创伤医学的整体救治水平,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与地位。
1PTSD的历史
1.1西方PTSD的发展与认识历史在西方近代史中,拿破仑战争时期,瑞士军医借用1688年Johannes Hofer提出的“Nostalgia”作为术语描述的一类战争后,士兵不明原因地出现一系列躯体症状,包括发热、心动过速、眩晕、消化不良、胃痛等综合征,现被普遍公认为最早关于PTSD的现代疾病描述[1]。1865年,美国军医Da Costa医生更加详细地报道了一组300名美国内战时期的士兵在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类似症状,即心动过速、焦虑、易激惹、疲劳、呼吸短促、出汗、胸痛等,但体检未见器质性/躯体异常,并定义为“Soldier’s heart”,也即“Da Costa综合征”。1905年,俄军军医用“战争休克(battle shock)”定义了在俄军中被认为是正常的一类士兵的医学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7年),Charles Myers在《柳叶刀》发表文章,使用了“炮弹休克(shell shock)”定义了一类症候群,表现为爆炸后,士兵和军官出现耳鸣、头痛、记忆力减退甚至失忆、眩晕以及震颤等一系列症状,从而导致战斗力下降。1918年,Smith与Pear开始提倡采用术语“战争压力(war strain)”,并建议对士兵进行治疗与干预。1922年,英国国防部提供的一份报告将其称为“战争神经症(war neurosis)”。此后,这类疾病一直广受西方战伤救治的关注,但直到1980年美国精神病医师协会颁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3版(DSM-Ⅲ)才正式将这一症状群,纳入了诊断标准体系,建立在“焦虑疾病(anxiety disorder)”这一大类之下,并命名为PTSD,这一名词也即替代了所有之前关于这类疾病的所有术语,也标志着PTSD正式作为一种疾病出现在心理-精神体系框架中。2013年5月,美国精神病医师协会颁布了最新的DSM-5,在这一版本中,PTSD与相类似疾病从“焦虑疾病”这一大类中独立出来,列为了一类新的精神异常疾病即:创伤与应激相关性精神障碍(trauma- and stressor- related disorder)。
战争是认识、了解并定义PTSD的重要背景。从美军两次伊拉克和13年阿富汗战争的经历来看,PTSD更被视为“看不见的战伤(invisible wounds)”,并被称为“标志性战伤(signature wounds)”。与躯体战伤不同,PTSD往往不能被所谓“肉眼”直接看到,因此经常被忽视而漏诊[2]。因此,美国国防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协会、美国国会以及总统都从不同层面推动了大量与损伤如何处置、如何定量以及如何形成干预方案等相关研究。出于对填补美军官兵在军事行动中的认知能力、精神健康状态认识的知识空白需要,美国国防部重点强调了发生机制、早期筛查与诊断以及有效干预等研究的紧迫性。
1.2我国PTSD的认识与发展历史在我国,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PTSD越来越受到临床工作者、研究人员以及社会民众的重视与关注。以“PTSD或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China或Chinese”为搜索词,对PUBMED数据库进行检索,截止2013年,大约有400余篇文献,而2008年之前的文献数仅为50余篇。但是,PTSD在我国并非一类“现代”疾病。其历史同样在我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西汉·刘向所编著的《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中记载了成语“惊弓之鸟”故事原型,其中描述的大雁基本可能符合DSM-5中PTSD的诊断标准: 标准A:经历过对生命有威胁的创伤性事件——被箭射落;标准B:事件过程的再现与再体验——对意味着弓箭的弓弦声出现明显的心理行为学反应即奋力往上飞;标准C:持续的回避症状以及标准D:认知感情麻木——远离雁群、叫声悲伤;标准E:高激惹——听到弦响,其他雁群无反应,而它自己猛然上飞导致用力过猛反而坠地;标准F:超过1个月。
但长期以来,PTSD并未在我国受到与西方社会相当的重视。其中可能存在多方面原因:比如西方科学心理学(或新心理学)在我国的学科体系中归属于“教育学”,这可能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从清末时期政府制定的学校章程中就被列入师范学院有关,而在医学教学体系中的地位与传统的“内、外、妇、儿”等临床学科大相径庭,从医学教育的角度就已经形成对心理学的低估,造成医护工作者对“心理”与“躯体”疾病的认识与感知受到心理学的影响尚浅,加之中国社会与民众容易对心理类疾病长期偏见与抵触,导致PTSD在日常医务工作中被忽视与漏诊;而另一种更为乐观的假设是,在我国的社会-家庭-个人环境与传统文化、社会习俗中,对PTSD的保护因素强于风险因素,因此“创伤”对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影响与西方社会相比,并非如同想象中的严重,因此导致对PTSD的出现重视或认识和筛查不足。
2PTSD诊断标准的进展
自从1980年PTSD被列入DSM以来,PTSD的诊断标准随着临床研究与分类的进展进行了相应的更新。
对于标准A,即“经历创伤性事件”的定义越来越明确和特异。主要区别是对主观感受是否列入判断“创伤性事件”的标准,从“不包括——强调——不强调”的一系列变化。在DSM-Ⅲ的诊断标准中,创伤性事件(诊断标准A)仅被局限于曾经经历过的事件,没有包括自觉体验或感受。之后1994年颁布的DSM-Ⅳ将创伤性事件的诊断标准进行了扩展:任何威胁生命或身体完整性的事件,目睹这类事件或致命性事件、或者听闻过任何与死亡相关的暴力性事件。可被列为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有:战争、性侵害、身体伤害、绑架或入狱(限制人身自由)、恐怖袭击、人为或自然灾害、事故、以及被诊断为患有威胁生命的疾病。2000年颁布的DSM-Ⅳ-TR中,创伤性事件的判断标准为经历过创伤事件且伴随害怕、恐惧、无助等情绪反应。DSM-5中,重新整合了对应激性事件(原)的表述,不再强调主观感受,将标准A简化为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和(或)感受到的威胁。
从症状簇的角度,从DSM-Ⅲ到DSM-Ⅳ-TR,症状簇主要分为3类:再体验(re-experience)、回避与麻木(avoidance)、高激惹(hyperarousal)。2013年5月最新公布的DSM-5最大的变化就是将之前诊断标准中的3大症状簇分为4大症状簇:回避症状簇被分为两类独立的症状簇,即将回避与负性情感分别独立,同时新增加了诊断标准H:排除了因医学干预或药物使用造成的相关症状;并新增了儿童PTSD亚分类与以脱离感为主要表现的亚分类诊断列出了单独的诊断标准[3-5]。突出“激进性”与“分离感(disassociation)”是DSM-5版PTSD诊断标准最突出的变化[6]。
“症状持续一个月或没有减轻”这一标准是各版诊断标准中没有发生变化的一项。创伤性事件发生后,如同生理应激反应一样,心理上也会出现类似的反应,而这些表现与PTSD(样)症状并无太大差异或者就是症状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诊断为PTSD。创伤后心理变化本身就既可能是PTSD的症状又可能是正常心理反应,而决定正常心理反应是否发展成为异常症状则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与之相反的变化,则称为“心理抵抗(resistance)”。前者被视为良性的心理过程,后者通常认为与不良预后明显相关。因此,PTSD的诊断中,“持续一个月”的时限要求是基本标准。
排除其他因素导致的心理/躯体应激状态持续存在,也是DSM-5版中明确提出鉴别诊断PTSD的标准之一。创伤性事件,往往或轻或重造成躯体不同程度的损害,近年来,主导创伤紧急救治的“损害控制”理论,使得分期多次手术的实施成为创伤后“救命、保肢”的关键,但也相应使得某些过渡性外科处理策略,如暂时性腹腔关闭、暂时性肠道腹壁造口、骨折外固定支架,又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应激症状产生,而这些医疗干预措施,往往很难在短期内去除,对后续医疗行为还是创伤性事件本身造成的心理/精神症状进行鉴别,是避免误诊PTSD诊断的关键之一。
3PTSD的主要诊断方式
3.1临床医师专用PTSD量表根据美国国家PTSD研究中心公布的诊断要求, 结构化临床面谈是现行诊断PTSD的“金标准”,如临床医师专用PTSD量表(Clinician-administered PTSD scale, CAPS)等。CAPS包含9个部分: (1) 标准A:经历过创伤性事件:包括亲身经历、目睹或者遇到实际存在的威胁生命或涉及严重伤害的事件或威胁自身或他人身体完整性的客观事件;以及发生过强烈害怕、无助或恐怖的反应; (2) 标准B:持续存在的创伤性事件的再体验; (3) 标准C:对创伤事件相关刺激持续的回避行为; (4) 标准D:创伤相关的认知行为与情绪的负面改变; (5) 标准E: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警觉性及其反应的明显改变; (6) 标准F:标准B/C/D/E的症状出现持续1个月以上; (7) 标准G:临床症状显著影响或破坏了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方面的功能; (8) 整体评估:判断当时患者回答的可靠性、整体PTSD症状的严重性、以及经过干预后的整体改善情况; (9) 区别是否存在分离症状:包括自己对其他人的疏离感以及非现实存在感。
3.2PTSD检查量表(PTSD checklist,PCL)PCL在平常临床工作中,是更常见的诊断筛查工具。适用于DSM-5的PCL5,主要由20个问题所构成,主要目的是对治疗中和治疗后症状的改善进行监测,对PTSD患者进行筛查,暂定PTSD的诊断等。在现行的PCL-5中,有3种形式: (1) 创伤暴露已经利用其它方式进行过评估,因此不需要诊断标准A; (2) 简要的标准A的评估; (3) 利用修订版的DSM-5相关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checklist for DSM-5,LEC-5)与其他扩展的标准A的评估。
相对于之前PCL版本,PCL5没有民用与军用之分。这一量表共计80分,每个项目分为0~4分,从“一点也不”到“非常明显”,>38分为目前推荐的诊断界限值,并要求至少满足1项B簇、1项C簇,2项D簇,2项E簇评分≥2(中度)。问题1~5体现标准B,问题6~7体现标准C,问题8~14体现标准D,问题15~20体现标准E。毫无疑问的是,随着进一步对PTSD临床研究的数据积累,这一诊断临界分值可能会修订。尽管PCL-5是以“自我回答”的问卷,但其解读必须由临床医生来进行,完成整个量表的时间为5~10min。Blanchard等[7]报道,之前基于DSM-Ⅳ的PCL诊断效能研究,总的PCL与CAPS的相关性为0.929,相对于CAPS的诊断效能为0.90,每个单项的相关性为0.386~0.788,对症状的诊断效能约为0.700或更好,因此推荐PCL可以作为PTSD的迅速筛查、诊断手段。
3.3功能影像学脑功能成像(brain mapping)是近年来研究PTSD生物客观诊断标志物的热门领域。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itude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已定位了一些与PTSD相关的脑功能区,比如杏仁核、内侧前额叶皮质、海马、岛叶、丘脑以及扣带回皮质等。总的说来[8-9],杏仁核与PTSD相关的情绪反应有关;海马与情绪记忆有关,杏仁核基底外侧核与腹内侧核之间神经回路活动的改变与PTSD分离症亚型有关[10-11];内侧前额叶皮质则与恐惧记忆的消除有关[12]。但这类研究大多数采用了任务相关功能磁共振研究,而任务模式本身则涉及了多种大脑的信息处理过程,因此为了明确PTSD相关的内在脑区活动,对脑部自发性活动进行研究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可能提供更有效的研究PTSD病理生理变化的证据。静息态功能磁共振表明,在上述相关脑区的自发性脑部活动明显增加,且与某些再体验量表的得分成负相关[13]。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fMRI研究结果都只能提供与PTSD相关的脑区,且很多文献报道都未能提供统一的证据,进一步对于脑区之间的连接关系,与PTSD相关的脑区功能泛化如何实现,以及脑区活动异常对PTSD的风险预测、诊断与干预疗效等诸多方面尚未见相关文献报道。同时,近几年来,随着纳米科技的进步,fMRI已经开始利用具有释放sncRNA其中一个亚类——miRNA的纳米载体,研究细胞内miRNA的功能[14],从而对细胞活动进行跟踪。但如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用于诊断PTSD的fMRI相关sncRNA分子探针,阐明sncRNA、脑区功能及其与PTSD相关症状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也是其根本基础。
4展望
对高水平的创伤救治的定义已经从基础的“救命、保肢”逐渐提升至尽量提高创伤后生存质量。创伤早期救治能力的增强,意味着严重创伤患者获得“救命”的概率不断增加,随之而来更高的挑战将是如何促进严重创伤患者重新回到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重新开始工作并获得相应的收入。PTSD作为创伤后最常见、最重要的影响伤患社会功能恢复的疾病,如能获得广大临床医师正确认识,实现早期筛查以及及时有效、正确的干预,阐明PTSD的发病机制将成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根本。
[1] Fuentenebro de Diego F,Valiente Ots CNostalgia: a conceptual history[J].Hist Psychiatry,2014,25(4):404-411.
[2] Tanielian T,Jaycox LH.Invisible wounds of war[M].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08:2.
[3] Dell’Osso L,Carmassi C.PTSD 30 years after DSM-III: current controversies and future challenges[J].Giorn Ital Psicopat,2011,(17):1-4.
[4] Dorahy MJ,van der Hart O.DSM-5’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ith dissociative symptom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J Trauma Dissociation,2015,16(1):7-28.
[5] Levin AP,Kleinman SB,Adler JS.DSM-5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J Am Acad Psychiatry Law,2014,42(2):146-158.
[6] Tye S,Van Voorhees E,Hu C.et al.Preclinical perspectives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riteria in DSM-5[J].Harv Rev Psychiatry,2015,23(1):51-58.
[7] Blanchard EB, Hickling EJ,Taylor AE,et al. Who develops PTSD from motor vehicle accidents? Behav Res Ther,1996,34(1):1-10.
[8] Hayes JP,Vanelzakker MB,Shin LM.Emotion and cognition interactions in PTSD: a review of neurocognitive and neuroimaging studies[J].Front Integr Neurosci,2012,(6):89.
[9] O’Doherty DC,Chitty KM,Saddiqui S,et al.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easurement of structural volum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J].Psychiatry Res,2015,232(1):1-33.
[10] Spielberg JM,McGlinchey RE,Milberg WP.Brain network disturbance related to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 veterans[J].Biol Psychiatry,2015,232(1):1-33.
[11] Nicholson AA,Densmore M,Frewen PA,et al.The dissociative subtyp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unique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basolateral and centromedial amygdala complexes[J].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15,40(10):2317-2326.
[12] Hayes JP,LaBar KS,McCarthy G,et al.Reduced hippocampal and amygdala activity predicts memory distortions for trauma reminders in combat-related PTSD[J].J Psychiatr Res,2011,45(5):660-669.
[13] Yan X,Brown AD,Lazar M,et al.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combat related PTSD[J].Neurosci Lett,2013,(547):1-5.
[14] Gomes RS,das Neves RP,Cochlin L,et al.Efficient pro-survival/angiogenic miRNA delivery by an MRI-detectable anomaterial[J].ACS Nano,2013,7(4):3362-3372.
(本文编辑: 黄小英)
Develop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rogress in its diagnosis
JIAMeng-xiao1,WANGHan1,ZHANGXiu-zhu2
(1.Battalion 11th,Student Brigade,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38,China; 2.Department 4th,Institute of Surgery Research,Daping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400042,China)
Corresponding response and adaption to various exact and potential loss and dysfunction is not only the key that determines the rehabilitation and re-adaption,but also the key that determines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after trauma. Whether one is able to be adapted to the influence of trauma to his/her mind and body determines his/her following social function. In the aftermath of trauma,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is a potent concern to the overall outcome of trauma. This review focused on the history,and the diagnostic development of PTSD to facilitate the enhancement of the early screening and diagnosis,as well a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rauma;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diagosis
1009-4237(2016)08-0507-04
全军医学科技青年培育项目(14QNP092)
400038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学员旅11营(贾梦潇,王翰); 400042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第四研究室(张岫竹)
张岫竹,E-mail:xiuzhu.zhang@hotmail.com
R749.5
A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8.021
2015-01-24;
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