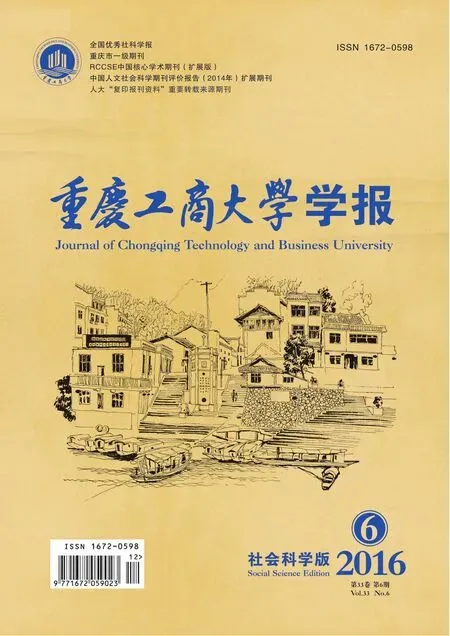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
——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陈梦熊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
——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陈梦熊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失语症;得语;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现代性体验
“失语症”的提出是与中国社会在20世纪所面临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它折射出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难以抉择的精神焦灼。深入探求“失语症”的本质,以及它对当下的文论研究和文化建设带来的影响,以及疗治“失语症”的药剂是什么?将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一、“失语”还是“得语”
“失语症”是曹顺庆先生针对古代文论研究和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存在的“以西释中”现象,有针对性的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1]50这一观点的提出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热议,赞成者不乏其人,反对者亦不在少数。无论学者们对于“失语症”的态度如何?我们首先要厘清的问题就是“失语症”的本质,只有把握了其根本属性,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的‘哑巴’。”[2]51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丧失了言说能力,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不妨以王国维为例来考察中西文论的交汇是否真的让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
20世纪初,王国维充分借鉴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创造性地完成了《〈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两部巨作。前者的价值在于首次引入西方文论思想评介中国古典名著,既是中国文论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中西思想融汇的产物;后者回归中国古典诗学的言说方式,以感悟式批评和朦胧化语言延续了“诗文评”的传统。代迅先生曾撰文指出:“整个《人间词话》的成功之处在于,王国维巧妙地不露痕迹地使西方文论的理论观念被涵盖于中国文论话语的传统表达方式之中,这不仅在《人间词话》的思维样态和逻辑架构上是如此,在概念范畴术语的使用上亦然,王国维在此文中是不露痕迹地化用了西方文论中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放弃了把中国文论当作西方文论的理论注脚的理论思维范式。”[3]66正是由于《人间词话》以传统“诗文评”的表述方式拓展了古代文论的言说空间,并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才能创造出具有鲜活生命力话语资源。近年来,罗钢先生完成的“《人间词话》学案研究”通过审慎的分析、翔实的资料再次为我们验证了——构建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基石是叔本华哲学思想。他指出:“王国维所说的‘能感之能写之’是根据中国古代诗歌‘兴发感动’的传统来加以解释的,它另有所本,出自一种与中国古代诗学判然有别的诗学传统。具体地说,它出自19世纪德国美学家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美学体系。王国维所谓‘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就来源于叔本华对天才与常人的区分。”[4]6
但是在长期的文论实践中,无论是朱光潜、宗白华、叶嘉莹等研究者,亦或普通古典文学爱好者,从未认为将《人间词话》视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延续有任何的不适应感。于是经过王国维的努力,我们的确在《人间词话》中感受到了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诗学融合的痕迹。
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镇,王国维将李煜后期词作视为“伶工之词”与“士大夫词”的分水岭,并不符合宋词的历史原貌。非但宋人并不视李煜为士大夫,其词作也多为抒发“故国不堪重回首”的伤感。虽然少了花间词的浮艳,依旧没有士大夫之词的雄豪之气。可见,王国维对于“士大夫之词”的理解是不同于前人的。他视李煜之词为“士大夫之词”的关键是“以血书者”——即融合个体生命的短暂和宇宙人生的苍茫于一体。因此,他才会将宋徽宗《燕山亭》视为“略似”,二人均为亡国之君,词作的差别正在是否将个体生命的体验上升到宇宙意识的层面。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王国维用以言说此种情感的概念则是借自西方的“释迦、嫉妒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并不是直接从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中寻求解释。他不仅没有让西方文论话语主宰自己的思维,并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当时的文学理论建设中。王氏所掌握的文论话语是兼具中西文论色彩,是中国文论在中心汇流的历史时刻造就的,符合中国学人所理解的“学术规则”。 可见,王国维并不是“失语”,而是“得语”。
什么是“得语”呢?我们不妨以“意境”作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这一概念是《人间词话》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最终生成以更为全面的姿态为我们展现了王国维从西方文论中“得语”的过程。一方面,王国维用以印证、阐发“意境说”的例证都是古典诗词,这从客观上塑造了很多人理解《人间词话》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意境说”的建构是在20世纪兴起、发展并完成的,它不是中国传统诗学的自主发明,而是经由一代学人的辛苦爬梳之后形成的理论体系。*此处参考了李春青先生发表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略论“意境说”的理论归属问题》。“‘意境说’是对中国传统审美经验的理论升华。”[5]36-37“境界”是王国维在融合了传统诗学话语资源的基础上,从西方文论和西方哲学中获得灵感,对“兴趣说”“神韵说”的再造,也是他对古代文学的个性化阐发。虽然构建“意境说”的理论基石是西方的,但我们并未产生任何的不适应感,是因为王国维做到了两种思想的巧妙融合。王国维拈出的“境界”是他站在西方哲人的肩上,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重新审视的理论成果。他开启了将“西来意”和“东土法”融合的历史进程,使古代文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言说的能力,我们称之为“得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得语”之“得”在于从西方文论中获得新的启示。这种启示可能是思维模式层面的,也有可能是价值观层面,关键是它使得我们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有新的提升或拓展。
二、中国文论“得语”的内在逻辑
中国文论“得语”最早的成果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但这一历史性转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中西方文化和文论思想经过漫长的浸润、交流才最终诞生的,其中不乏产生某些失败的范例。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中国文论“得语”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提炼“得语”的内涵。
中国文论“得语”并不局限于“意境”说,而是一场涉及中国文论全方位的重大变革。仅以“文学”一词为例,最早出处是《论语·先进》,与现今通行的涵义有较大差别。“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三种涵义:“一是指学识渊博。如桓宽的《盐铁论》中的‘文学’,就是指博学之士;二是指官名。汉代州、郡和王国皆设置文学官职,类似于后世的教官。这种官职位一直延续到唐代;三是指文章,包括诗、文等。”[6]167其后,“文学”的概念融入了“纯文学”*“纯文学”是与“杂文学”相对的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学观是以“杂文学”为主。的成分,并在唐代时有了较“文笔说”更进一步的发展。古风先生指出:“汉语‘文学’一词的现代化是通过两条线进行的,一条是传统‘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化,即由《诗》→诗→诗文等转化;另一条是通过翻译英语‘Literature’来进行内涵的转换。”[7]169自五四以来,我们逐渐忘却了传统的“杂文学观”,转而以西方的纯文学观来看待文学。但二者并非完全隔膜的存在,正是由于“杂文学观”中隐含着纯文学的基因,才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就厘清了中国文论“得语”现象第一层面的内涵——中国现代文论“得语”的逻辑前提是传统诗学和西方文论存在着精神契合的基因。
《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而判断境界有无、高下的标准是“隔”与“不隔”。他将叔本华的“直观说”转化为“话语可以直观,便是不隔”,又在正式发表之际将其调整为“话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罗钢先生认为王国维的改动暴露了《人间词话》的理论本质,我们却从中发现王国维利用“目前”与“直观”的精神契合性,使中国语境孕育的“目前”被赋予了叔本华“直观说”的理论内涵,这是中国现代文论“得语”的例证之一。“得语”绝非随意的拼凑,它必须符合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属性,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规范。在中西文论汇流的历史进程中,汲取西方的经验固然重要,本国文论的民族特性也不可忽视。这种认识很早就得到了中国文论建设者的重视,郭绍虞先生就曾明确指出:“我国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特色,古代文学理论中许多用语,都是前人从创作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也是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的”。[8]6因此,我们认为“得语”之“得”不仅要善于发现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之间的精神互通性,进而谋求建构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古代文论的民族特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得语”,否则就成为了西方文论的附庸。
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忽略中国文论的民族性特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语”,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完全依据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去解读《红楼梦》,固然是证明了《红楼梦》具备浓烈悲剧属性的审美特征,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最为后人诟病的就是王氏以贾宝玉之“玉”为“欲望”之“欲”的影射,进而构建起评价《红楼梦》的逻辑架构。从思维模式的层面看,王国维将“欲”与“玉”联系在一起颇有汉儒以谶纬解经的意味,似乎符合中国文论的民族特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古典诗学的主体是儒家文论,存在着否定个体欲望、凸显集体意志的价值倾向,而佛道两家也不涉及个体生命最为原始的“欲”。而王国维奉为圭臬的叔本华正是将“欲”作为导致生命走向悲剧的根源,他认为“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人类的‘生活意志’支配着人的一切思想和一切行动。意志有着永不知足的欲求,是不能遏止的盲目冲动,它在现实世界中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有限的满足与无限的欲求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中间的沟壑无法填平,因而人不能脱离痛苦”。[9]61-62王国维完全接受了“可爱而不可信”的叔氏哲学,并以其作为理论支撑解读《红楼梦》。
王国维是将《红楼梦》作为解答人生与艺术之关系的范本来解读的,他站在叔氏哲学的理论基点上,完全脱离了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这就使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成为了他“解剖”《红楼梦》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工具,我们当然要承认《〈红楼梦〉评论》在否定索隐派、建构中国文学批评新模式和引入西方文论以逻辑思辨为特征的文学评论架构中取得的成绩,却也不能否认《〈红楼梦〉评论》忽视中国文论民族特性方面的缺憾。
中国文论“德语”重视“民族性”的逻辑延伸就是强调中国文论的“传统”。在通常意义上,中西文论的交汇直接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决,其结局往往是传统的失利。中国传统文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逐渐退缩到社会的边缘,其中心地位被以欧美文论和马列文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所取代。传统失利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是传统的彻底消亡,成为被观赏的精神遗存;其二是传统的文化资源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延续,通过一定方式的转换,参与到新阶段的文化建设中来。前者往往发生在极端激烈的文化冲突中,直接后果是传统文化资源的彻底“失语”;后者则以较为隐性的方式渗透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需要我们通过学理分析甄别传统与现代的差别。“得语”正是后者带来的积极成果,当我们将外来文化资源融入到本民族的传统中,创造出新的成果后,它俨然就成为了我们的传统。正如黑格尔所说:“构成我们现在的……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9]7-8
三、中国文论“得语”举偶
我们要挖掘古代文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化语境中仍然具有言说能力的话语资源,在借鉴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使其焕发出新的光芒,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批评中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中,“失语”毕竟是极少的,更多的情况是“得语”。以20世纪的杜诗研究为例,我们将会发现中国文论“得语”所取得巨大成绩,以及“失语”对于我们理解文学文本、作家本人带来的负面影响。
杜诗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镇,宋代即形成了“千家注杜”的盛况,以杜甫研究作为考察对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论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刘明华先生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一文中将20世纪的杜甫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学术思想在杜甫研究领域的建立”……第二个阶段则是杜甫研究的过渡期,“世界观、人民性、爱国主义”等话题被重点讨论;同时还出现了“文革”时期“评法批儒”和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第三阶段是“杜甫研究的活跃期”,“现代学术意识,在这一批学者身上表现相当明显”。[11]158-15920世纪的杜甫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杜甫研究领域的个别现象,也在中国文论研究中有所显现。因此,以杜甫研究作为我们考察中国文论发展中出现的“得语”“失语”现象就兼具学术史价值和文学实践的针对性。
杜甫及杜诗研究的转变历程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基本范式的变化,早期的学者延续了注释、校勘的古典文献学模式。在西方学术方法传入之后,杜甫研究开始出现新的元素。
“梁启超1922年诗学研究会的演讲《情圣杜甫》,首开以西方‘真善美’为标准评杜诗的风气,针对传统道德标准第一的‘诗圣’提法,称杜为‘情圣’”[12]5梁启超的观点颇具新意,被一部分人所接受。以西方学术研究方式实现古典文学研究的更新,绝非梁启超一人。正是在这一原则引导和促进之下,“得语”的原则得到了体现。对于20世纪的文学阅读者而言,忠君的思想已被抛却,而杜甫的忠君品质仍需要得到继承,这就需要研究者以创造性转换的思维来重新阐释杜甫及杜诗的意义。由于杜甫对民生疾苦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不会将“致君饶舜上,再使风俗淳”视为士大夫高高在上的训诫,而是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者最真实的情感表达。梁启超以“情圣”作赞,无疑是极大地提升了杜诗的审美内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浪潮中,胡适是较早采用“科学方法”研究杜甫的先驱。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胡适曾就杜甫作专章讨论。首先,胡适赠给杜甫“写实派”的冠冕,这成为后来研究者从“现实主义”考察杜诗的理论渊薮。在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杜诗中“流离陇蜀,毕陈于诗”的价值被极大地提炼了,成为新时代语境下“诗史互证”的典范。胡适研究杜诗最大贡献是将“问题诗”作为杜甫的贡献,认为“其乱离中诗歌的艺术风格是:观察细密,艺术愈真实,见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13]6其次,我们也必须承认胡适的研究存在着“失语”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胡适将杜甫作为论证白话文兴起的重要标志。他将杜诗中俗语、俗词视为白话文发展的产物,进而将其界定为杜诗的审美特征。很显然,从第一个层面来说,胡适针对杜甫的研究是成功的。但若就后一个层面的研究而言,由于主题先行、观念先行的干扰,胡适没有把握到杜诗的精髓,故可视为“失语”。
新时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成果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美学热,在推动思想解放的同时,也促进了学术研究自由度的提升。本师刘明华先生在《社会良心——杜甫魅力新探》中就以西方知识分子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揭示出一个全新的杜甫。而杜甫所具备的忧患、批评和重建不仅让杜甫在宋代得到了认可,也是今日我们认识杜甫的最佳切入点。特别需要强调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建立在政府与民众的二元对立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文化背景下,与杜甫的士大夫身份有较大区别。在这一点上,明华师并没有陷入到以理论图解杜甫的泥沼中,而杜诗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正好与宋明理学中“民胞物与”的思想保持了精神内涵的同构特征。“杜甫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固然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亲切的一面,但杜甫那些同情不幸者,关心弱小者,帮助受难者的诗篇更显示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独具风采的原因。”[14]54唯有从此理解,才能体会杜甫能够挺身营救房琯。这当中既有私人友情的成分,也是杜甫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发挥作用。
从梁启超提出的“情圣”到萧涤非先生提出的“人民性”,早期的杜甫研究中所取得那些能够传诸后世的成果,无一例外都是中西文化汇流的成果。而胡适的“现实主义”虽然开启后世杜甫研究的新法门,却陷入到主题先行的泥沼中,成为“失语”的典范。将前人的成果与刘明华先生拈出的“民胞物与”相结合,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在尊重文化传统、突出民族本位文化当下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激发出中国文论的话语言说能力。将这些成果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国文论“得语”的最佳证据。
四、疗治“失语症”的药剂
我们认识到单纯坚守中国传统文论的“学术规则”是无法真正融入到当下的文论建设中来的,更遑论发挥文学理论的现实干预性。“失语症”的本质是由于担心传统文论失去了既有的中心地位,直接原因是古代文论在面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时所表现的“乏力感”。这不是因为中国文论患上了“失语症”,而是中国文学的实际发生了转换。在诗文已不居于主流地位,以及西方的小说、戏剧、散文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的现代语境中,传统文论的苍白感是无法避免的。
蒋寅先生曾为“失语症”开出过这样的药剂:
病状:失语症。此症多发作于国际文化交流的场合,经常伴有严重的文化自卑感与精神焦虑。
病因:脱离文学研究活动,缺乏艺术感受力与文学批评经验,于文本本身殊无知解,故随波逐流,略无定见。
处方:配以古今并举、中西双修之操,多看作品,多做研究,留意创作,留意批评。[15]34-35
孕育“失语症”的话语背景是国际文化交流,即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汇,具体表现为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现代性体验”。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三个特征分别是“时空分离”“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上述三者对传统文论的影响分别表现为西方文论的强制介入,使得“实行数千年的原生性古典时空观传统被迫突然中断,转而实行来自西方的现代时空观”;“抽离化机制在中国也是意味着中国古典知识型的断裂和外来西方现代知识型的置入”;现代性反思则体现为“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反思和对被置入进来的西方现代知识型的反思,以及对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反思。”[16]37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层的价值秩序”发生了位移和重构,“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在转化过程中,这种隶属的程度日增,随工业精神和商业精神战胜军事和神学——形而上学精神日益深入到最具体的价值观中。”[17]142他们最终凝聚成为“现代性体验”的“怨羡情结”,并直接投射到20世纪的中国文论发展和建设中,成为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理解文学的外在因素。
所谓“怨羡情结”是王一川先生针对中国社会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性体验并非单纯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天灾人祸,还应落实到十分具体的“器物”层面,这就囊括了古典文学和古代文论。当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之际,中国人的确是逐渐开始摆脱传统的束缚。而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则意味着传统文人开始走出“华夏中心论”的思维。但我们仍旧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到时隐时现的“怨羡情节”——“怨恨具体地表现为对中国自身状况的怨贫恨弱心态和对西方的怨强恨霸心态。……人们在怨贫恨弱时也会更加急切地渴望实现现代性目标,即羡慕西方现在的富强,并以此为目标而渴望自身尽快实现甚至超过西方的富强。”[18]75
受到如此文化氛围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我们形成了这样几种认识:其一,古代文论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类似于西方文论的逻辑思辨体系;其二,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丧失了言说能力,不能帮助当代人构建中国现代文论做出贡献;其三,中国文论曾在特定历史阶段被视为“封建糟粕”,认为应批判地继承,并且是以“批判”为主。正是这些因素对我们正确、全面、系统地认识古代文论形成了遮蔽,才最终导致了“失语症”学说的提出。事实上,在中国社会被卷入到“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进程伊始,偶尔出现、零星发生的“失语”现象的确存在,但它绝不是古代文论在20世纪的主流,而应被视为前进道路中短暂出现的“回波逆流”。
总结上述讨论的成果,我们认为疗治“失语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现在社会架构中的文论思想退出了社会中心地位,士大夫阶层的消亡使得古代文论更多地成为了精神资源,而非“言志”的工具。“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境遇的确令人感到遗憾,但这或许也是文学之幸,它获得了相对僻静的生存空间,能够以更为冷静、客观、审慎的态度去整理百年走过的道路。其次,理性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现代性过程中的选汰,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西方文论所提供的话语资源已经改造了我们理解文学的思维模式,试图回到传统文化语境更多的是研究者的愿景,而非现实生活中可以实现的目标。因此,谨守古代文论的“学术规则”是无法正视当下的现实诉求的。再次,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在适当借鉴西方文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中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的前提下多多创造“得语”个例,为构建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奠定基础。现代文学的主流不是诗文,而是小说、戏剧、散文。它们或是古典文学中根本不存在、或是被视为末流的,希冀古代文论对其展现言说能力是很难做到。
[1] [2]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50,51.
[3] [9] 代迅.成功与失误:王国维融汇中西文论的最初尝试[J].文艺理论研究.1999(2):66,61-62.
[4] 罗钢.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J].文史哲.2009(1):6.
[5] 李春青.略论“意境说”的理论归属问题[J].文学评论,2013(5):36-37.
[6] [7] 古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67,169.
[8]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
[10]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8.
[11] 刘明华.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J].文学评论.2004(5):158-159.
[12] [13] 林继中.百年杜甫研究回眸[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5,6.
[14] 吴中胜.学术怪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J].粤海风.2010(3):47.
[15] 蒋寅.学术的年轮[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34-35.
[16] [17]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7,75.
[18]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M].刘小枫编校.北京:三联书店,1997:142.
(责任编校:朱德东)
Whether It Is Having Nothing to Say or Having Something to Say—On the Solution to Having Nothing to Say
CHEN Meng-xiong
(Schoolof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 discussion of China, there is frequently having nothing to say, but it is not the main body. More mainstreaming is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based on compatibility, nationality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discussion. In the Du Fu research in the 20thcentury, the advance of the concept of people’s character, realism and people being my brothers and I sharing the life of all creatures demonstrates the strong vital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cussion, which is the verification of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The treatment of having nothing to say should be under the premi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scussion, should clarify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discuss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its social attribute in the process of one hundred years modernization experience history, should seldom adulterate nationalism feelings, should use the learning rationality analysis and should reevaluate the creating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aving nothing to say;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compatibility; nationality; tradition; modern experience
10.3969/j.issn.1672- 0598.2016.06.018
2016-02-17
陈梦熊(1984—),男,湖北恩施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I206
A
1672- 0598(2016)06- 0119-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