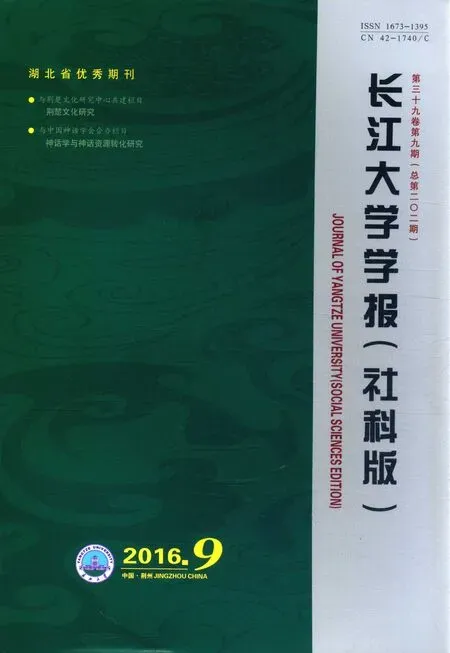向死而生:论《土生子》主人公别格的心理成长模式
邓芬 赵晓光
(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向死而生:论《土生子》主人公别格的心理成长模式
邓芬赵晓光
(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理查德·赖特是20世纪美国黑人抗议小说的先驱。在《土生子》中,别格触犯法律和道德准则的主要原因是白人世界对黑人群体的压迫。这种压迫使得原本就迷失在白人价值观当中的黑人别格发生心理扭曲。从麻木不仁地杀害两名女子转变为自我觉醒和人性复苏,别格在心理意识上获得了成长。尽管最后未能逃脱死刑的惩罚,然而在与社会的冲突和融合中,别格不断地寻找自我定位,建构自我身份。追溯别格的心理成长轨迹,有助于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呈现别格乃至整个黑人民族的成长历程。
成长模式;心理成长;认知;种族主义
在整个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尤以黑人文学的发展最为瞩目。理查德·赖特作为美国黑人文学的代表作家,在其经典著作《土生子》中,精心刻画了一位歇斯底里地反抗白人主流社会的黑人青年形象——别格,在黑人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土生子》因为主人公别格对白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的疯狂反抗而被归入抗议小说之列,成为控诉种族歧视摧残黑人从而导致悲剧发生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欧文·豪所言:“自《土生子》诞生的那一天起,美国文化被永远地改变了。”[1]
别格的故事是有“原型”根据的,1938年芝加哥黑人罗伯特·尼克松谋杀白种女人,赖特被该案件所触动,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别格这一经典文学形象。别格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来自白人文化至上的美国主流社会对黑人的压迫。另一方面,造成别格悲剧的原因并不仅限于白人社会的压迫,也包括别格本身的心理状态。站在别格的角度衡量,这部作品可以被视为其个人的心理成长记录。赖特并没有简单地将别格作为种族歧视制度下的牺牲品来进行叙述,反而深入地挖掘了其看似如野兽般凶残,实则另有他因的杀人心理,以及其在犯罪后所经历的心理逃避、心理折磨和心理再构。在赖特创作的时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文学领域也颇为流行。赖特本人也承认别格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在生活中也同样受到了别格曾遭受的歧视和自卑的折磨。换言之,在黑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他们都在承受这种歧视和自卑。
赖特在小说叙述中用了颇多笔墨描画了别格杀人前后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描写符合成长小说的内在逻辑。《土生子》中的别格对自我和世界的心理认知过程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更多地呈现出动态的特性。别格的心理成长践行了美国成长小说的叙述模式: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悟—认识人生和自我。[2](P8)美国的成长小说和英国、德国的成长小说有很大区别。在传统的英国、德国成长小说中,主人公经历种种遭遇,最后都能通过战胜精神危机而长大成人,因此结局圆满。譬如,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以及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主人公对个人成长都持有较积极的态度,在故事的结尾,能够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并成功融入现实社会。然而,美国的成长小说“似乎更加相信个体的力量和完整,且在是否要融入社会这一点上更加犹豫。因此,美国的成长小说鲜有传统成长小说的喜剧或者大团圆结局”[3](P37)。
别格的最终归宿证实了这一论断,因为别格的命运和传统成长小说的结局有极大的区别。白人主流社会对别格的歧视导致了他的心理失衡,进而引导其走向不归路。艾力克·范·胡塞指出,“仅仅密切关注外在环境对别格的影响,并不足以全面理解别格及其人生经历。”[4]为此,我们还应该更加重视别格内在的心路坎坷和心理扭转过程。Helen White Childers在《美国小说中的青少年,1920~1960》中指出,研究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一种主要方法就是“心理研究,展现出因为心理疾病而成长失败的青少年”[5](P20)。故而,本文从别格的心理成长模式来考究其人生悲剧的另一成因。从心理学上看,人的成长有其阶段性。本文旨在揭示别格的心理成长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即成长的困顿:人格结构濒临崩溃;成长的考验:人格结构失衡;成长的顿悟:人格的升华。
一、成长的困顿:人格结构濒临崩溃
这部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分为“恐惧”、“逃跑”和“命运”三部分。每一部分都以别格在睡梦中被唤醒进入嘈杂、可怕的真实世界开场,这也暗示着他对现实世界的抗拒。无论是别格,还是其家人,他们对于别格的教育和职业成长都没有明确的规划。别格自出场的那一刻起,其一举一动都是为了满足他的本我。他的成长处于停滞阶段。本我按照享乐原则行事,毫不顾忌外在世界的束缚,因此自我承担了控制本我的任务。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以安全感和舒适感为行事目标。超我的运作原理则刚好与本我相反。超我负责帮助个体按照外界所能接受的方式行动,遵循良心、道德感和禁忌等的控制。自我负责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实现平衡,同时还要满足现实世界的要求。当自我无法同时满足这三者的需求,个体就会产生焦虑感和挫败感。别格的本我主要表现在以自己为中心,且倾向于用暴力发泄情绪和解决问题。别格平日游手好闲,并不在乎家人的生活处境。只有在自我告诫他温饱将受到威胁之时,他才会勉强愿意通过劳动换取报酬。
别格成长于生存条件恶劣的黑人家庭,依靠救济金生活。一家四口挤在八平米大小的屋里,两张床占据了房间的大半部分。当母亲与妹妹换衣服时,别格和弟弟得把头扭过去。恶劣的环境让他心生怨恨,他甚至怨恨母亲为何要生下他。别格与朋友聊天时说:“他们有机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白人什么也不让我们干,每次一想起来,好像有人拿烧红的铁塞进我喉咙。”[6](P21)别格对家庭环境和周遭环境都深感不满,因为这两种环境让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别格对食物、性和模糊的未来都有着强烈的欲望,当强烈的欲望无处发泄时,他就用暴力来掩饰自己的恐惧。不论是对待亲人,还是朋友,别格都倾向于使用暴力来发泄不满。别格采取残忍地杀死老鼠的手段来寻欢作乐。用老鼠的尸体吓唬妹妹,其实是他对内心抑郁情绪的发泄,他“哈哈笑着,拎了死鼠像钟摆似的摆动着,向床走去,拿他妹妹的恐惧开心”[6](P6)。对于女友,别格也是将其当作发泄欲望和敲诈道尔顿先生的工具。别格不敢实施抢劫白人商店的计划,所以选择通过殴打同伙来拖延时间,最终使抢劫计划无法进行。
可以说,一方面,贫寒的家庭环境让母亲忙于谋生而无暇照顾别格,也让他根本无处接受正规教育,因此也就无法获得通过教育带来的心理成长。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成长,别格没有任何概念,他甚至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困惑。在别格的本我中,欲望犹如一口沸腾的大锅,随时可能喷薄而出。在这一阶段,别格还能受制于外在现实世界的控制。别格原本对去白人雇主道尔顿先生家里当司机毫无兴趣,直到救济署用切断食物救助威胁他,他才不得已而为之。他的本我不受制约,只想满足自己游手好闲的欲望,直到对食物的原始欲望受到威胁,他才对现实世界妥协。
别格在潜意识中明白,一旦意识到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要么自杀,要么杀人,所以他尽量克制自己,让自己装得强横。尽管他面对成长的困惑:基本的温饱难以维持,毫无尊严可言;家人、朋友和女友,他哪个都不爱;当飞行员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被白人社会遏制——但在这一阶段,自我能够束缚强大的本我,因为他知道“越过禁区,白人世界会开火”[6](P15)。然而,他其实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所以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用粗暴的语言甚至暴力行为来掩饰内心沸腾的愤怒和恐惧,强压住自己的本我,压制潜意识里的疯狂反抗和愤懑,对现实世界暂时妥协。
种族歧视使别格对白人社会感到恐惧,对黑人社会也是如此,但在表面的逆来顺受之下,难以掩盖的却是他蠢蠢欲动的反抗情绪。他远离白人社会,也与黑人社会疏离。此时的别格在精神上处于流浪状态,困惑不安,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亦无成长规划,有的只是认知的焦虑和蓄势待发的暴力倾向。
二、成长的考验:人格结构失衡
别格在接受道尔顿先生安排的工作之前拒绝成长,他故意搞砸救济署提供的工作机会,把自己的生活范围局限在家庭和与朋友鬼混。他并不愿意真正踏入社会,宁愿躲在冷漠暴力之后,拒绝成长。别格表现出其不愿成长的特征,“……或是不愿意面对成长所必须承担的责任,或是对成长的前景感到茫然,甚至对成长的意义产生怀疑。”[2](P114)家庭不幸、种族歧视以及内心的困顿,导致了别格的扭曲心理。他不愿意承担成长的责任,拒绝通过工作来养活家人。同时,他对于自己的前景也感到茫然,白人世界并未给他平等生活或者工作的权利。他不愿意经历成长的磨难,他的自我抗拒关注外在世界,包括玛丽和简对他的善意。
正如白人社会普遍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黑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也渗透着对白人的敌意,别格本我中对白人的敌意显而易见。自我和本我此时在人格结构中的影响力很小,只是担心惹恼了白人小姐会让自己工作不保,别格才勉强敷衍白人雇主。他根本不相信玛丽和简会成为自己的朋友或者帮助黑人。在潜意识中,他早已习惯白人的厌恶,以至于不知如何回应现实世界的善意。外在环境导致别格的人格结构失去平衡,本我中对白人的厌恶和恐惧占据主导地位。
在工作的第一天,他开车送玛丽回家。因为醉酒,玛丽无法独立行走,别格只好扶着她回到床上。此时,别格的自我能够将本我协调在一定范围内,因为自我意识到黑人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玛丽喝醉酒以后,别格并不愿意和她发生肢体接触,他几经挣扎,才下定决心扶住站不稳的玛丽。尽管因为触碰玛丽而感到兴奋,但他更希望尽快离开她,因为他的自我清醒地明白如果被白人看见,他将无法解释。然而,强大的本我战胜了自我,“他内心中有个声音催促他,叫他马上离开,但他俯在她身上,异常兴奋,在暗淡的微光中望着她的脸,舍不得让他的两只手离开她的胸脯”[6](P100)。
和玛丽的身体接触激发了别格本我中的性欲,尽管现实原则要求他立即离开白人小姐玛丽的房间,他却无法抗拒本我中的性冲动。失明的道尔顿太太的突然出现让他更加惊慌失措,因为他知道一个黑人晚上九点以后还呆在白人小姐的房间里,肯定会被人认定为强奸。存在于集体无意识当中的恐惧本能被无限放大,自我和超我再也不能将其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因此,他杀害并且焚烧了玛丽。“他知道那姑娘的死并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已起过多次杀心……他的犯罪看起来很自然,他觉得他这辈子的生活必然导致这样的结局。”[6](P122)
杀害了白人小姐玛丽之后,长期压制在别格本我中对白人的厌恶和仇视瞬间爆发。随后,因为担心女友蓓西会告发自己是杀害玛丽的凶手,他杀害了蓓西。别格对于自己的杀戮行为毫不后悔,甚至还有一种可怕的骄傲在心底泛起。本我完全控制了他的心理结构,自我和超我毫无地位。超我的形成长期受制于基于白人利益而形成的不平等社会规则,因此他判断事物的准则习惯性地遵循这种不平等的社会规则。与白人相处时,他会不自觉地按照白人的意愿行事。这种环境下形成的超我无法抗衡,更无法制约强大的本我。除了白人社会的歧视,别格的悲剧也来自于其心理结构的失衡。
别格的焦虑和痛苦的经验本可以由自我运用防御机制包括压抑、投射、反向形成、升华和隔离等来化解矛盾,缓解或者消除焦虑,恢复人格结构的平衡,然而,别格用杀害行为发泄了本我中的恐惧和厌恶,走向极端,造成了心理的失常。
三、成长的顿悟:人格的升华
倘若理查德·赖特以别格进入监狱作为《土生子》的最终结局,那么这部作品也许就不会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对别格悲剧心理的深入考究,以及别格最后对理性的回归和人生观的升华,使《土生子》具有区别于其他反抗种族歧视的作品的魅力。
关于成长小说,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作了明确阐述:“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含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7]
别格在残忍地肢解白人小姐玛丽之前,就曾明言自己的冷漠、愤怒和欲望“好像水流,由于远处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拽,时涨时退”[6](P32)。这股水流里流动着的欲望和沉默就是他的本我。为了掩饰内心对抢劫白人商店的恐惧,他通过殴打朋友盖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随后,他又杀害白人小姐玛丽和女友蓓西。对别格而言,所有的暴力和杀害都是为了自我满足,发泄愤怒和欲望。别格的本我中找不到任何正面的情绪,只有恐惧、愤怒和厌恶。
别格在监狱中对良心和自尊的思考代表着其人格结构的回归。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在杀害玛丽和蓓西,被抓入监狱之后,别格看到玛丽的母亲道尔顿太太时完全没有内疚感。在与主动帮助自己的共产党白人律师麦克斯谈话时,他曾坦言自己对于杀死玛丽一事毫不愧疚,他甚至在杀人之后还感到一种暂时的解脱。变态心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他极其厌恶见到家人,更讨厌他们为自己求情。白人只看到了别格体内的兽性,他也已经习惯了白人的歧视,以至于他觉得白人的认知没错:有着黑色皮肤的就是坏人。然而,妹妹维拉因为他的罪行而无法上学的事实却提醒他:他并不孤单,且家人永远是他血液和精神中的一部分。别格第一次发觉“他的所作所为也给别人带来痛苦……他的家庭是他的一部分,不仅在血统上,而且在精神上”[6](P345)。
其次,共产党白人麦克斯和简对别格的帮助以及宽容,进一步唤醒了他的良知和人性。起初,别格告诉麦克斯他并不惧怕死亡,不需要白人的帮助。后来,他慢慢了解到麦克斯是想让他的死对黑人民族的真正解放更有意义。在别格的人生中,麦克斯是第一个将其看作有尊严的生命个体的人,麦克斯的劝导激发了他对杀人的内疚感和对正义的渴望。他的超我慢慢觉醒,本我逐渐回归理性。被别格陷害的简不顾偏见和敌意,多次来监狱看望他,并且到处为他寻求帮助。别格开始体会并且享受到人间温暖,而这种温暖是以前的家庭和社会都无法给予他的,他终于为杀害玛丽小姐和蓓西而道歉。
最后,理查德·赖特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法庭上的场景,其目的是让读者明白尽管死刑无法避免,然而法庭上的言论至少可以给别格带来积极的启示,别格的真正思想也在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得以展现出来。白人将蓓西的尸体毫无遮蔽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以此作为别格杀人的证据,其实是希望激起更多人对别格的厌恶。在这种情况下,别格愤怒了,因为他认为白人是在利用一个黑人女性的身体,公开侮辱蓓西。对蓓西的道德感和内疚感是别格理性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监狱中,他进行了自我反思,承认自己过去完全是无意识地按照欲望和恐惧来行事的。在此之前,他从未进行过类似的思考。最终,他的超我和自我得以回归。临刑前,他对麦克斯说:“可事实上我从来不想伤害什么人……他们挤得我太厉害了;他们不肯给我一点空隙。”[6](P485)他一再安慰麦克斯,自己对于死亡已经不感到恐惧了,最终,他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四、结语
个体的冲动和欲望是本我的一部分,按照快乐原则行事。不顾后果地满足欲望是本我的行事方式。自我的任务就是将本我调控在合理的范围内。别格杀害白人小姐玛丽和黑人女友蓓西,与其人格结构失衡不无关系。在对黑人存在歧视的社会环境中,言语和心理上对黑人的设防,其残忍性并不亚于身体上的暴力殴打,这于别格而言更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土生子》并非一部简单的反抗种族歧视的小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多面性,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有助于阐发其独特的审美魅力。白人社会对别格的精神压迫导致了他的自我心理失衡,进而促发其悲剧命运。赖特深入挖掘了别格的人格结构,这也极大地深化了《土生子》的主题意义和人文关怀。赖特将别格的个体成长经历寓于整个黑人种族获得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并以此隐喻整个黑人民族的身份构建,具有种族性和民族性,也使得小说的主题更加深刻,更具内涵,更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1]Irving Howe.Black Boys and Native Sons[J].Dissent,1963(Autumn).
[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孙胜忠.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4]Eric Van Hoose.Native Sun:Lightness and Darkness in Native Son[J].The Black Scholar,2011(41).
[5]Witham W.Tasker.The Adolescent in the American Novel:1920-1960 [M].New York:Frederick UngarPublioshing Company,1964.
[6](美)理查德·赖特.土生子[M].施咸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7](前苏联)巴赫金.小说理论[M] .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叶利荣E-mail:yelirong@126.com
2016-06-10
2014年度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课题
邓芬(1988-),女,江西抚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美小说心理美学研究。
I562.074
A
1673-1395 (2016)09-008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