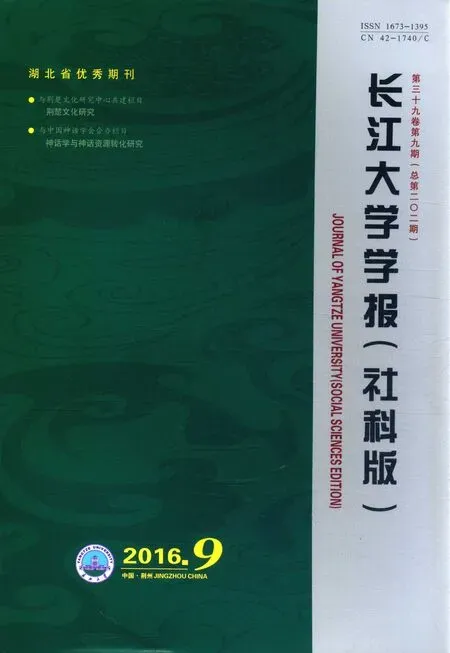青年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历史必然与逻辑错位
陆寓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青年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历史必然与逻辑错位
陆寓丰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210093)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借助物化概念,开启了对马克思主义主体向度解读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路径。然而,在黑格尔的逻辑张力与马克思·韦伯的隐性支援背景下,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物化概念的解读,无法使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解放路径,反而使其试图重新唤起无产阶级意识的努力,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镜花水月。
卢卡奇;物化;马克思;历史与阶级意识
物化概念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核心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侵袭,是导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丧失的重要原因。正是基于这一判断,重塑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阶级意识,就成为青年卢卡奇思想的内在逻辑发展路径;而这种偏向主体性的逻辑走向,也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本文拟从青年卢卡奇物化概念的起源出发,探寻这一概念的理论支援背景及其深层逻辑内涵,并试图揭示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及其逻辑悖结。
一、物化概念提出的历史必然
卢卡奇及其所开辟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非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其怀抱憧憬,但其拒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即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化解释:因为在他们眼中,这种机械化的解释,使得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最重要的革命性。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实践与理论上,重燃了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其所倡导的主体能动性,不仅是青年卢卡奇,也是之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在青年卢卡奇的视域中,无产阶级只有把握这一力量,才能实现革命目的;只有把握这一点,才能恢复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才能真正回复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而物化现象却是导致这一切无法实现的原因。因此,卢卡奇重新提出物化概念,是想重新激活被第二国际遮蔽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批判精神。虽然青年卢卡奇所说的物化实际上并非马克思所说的物化,但其能十分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在对人的奴役的意义上所讲的物化,并借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想重新激活历史辩证法与主体能动性,就此而言,其不愧同时代的领路人。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历史发展基于主客体相互运动的总体性,而总体性是主客体辩证法的革命动力。为什么工人阶级作为掌握总体性的主体,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了革命性呢?这就是卢卡奇提出物化的意义。在他看来,正是物化现象蒙蔽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过,由于主客体辩证法是区别于传统的客观规律的辩证法,不是客观对主观粗暴的纯粹支配,而是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只要无产阶级重拾阶级意识,发挥主体作用,就可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写作顺序得到验证——先说明物化现象,再说明资产阶级意识的二律背反即无法担任历史主体的根源,最后说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立场。在青年卢卡奇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物化现象愈发普遍而奴役了一切,其结果是人的主体性逐渐丧失,主体与客体不再同一,主客体辩证法的革命性也渐渐被遮蔽,而资产阶级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地位的制约,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发展,不能实现主体-客体的同一,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承载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力量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无产阶级的作为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本质才能发挥出来”[1](P232)。这不仅是青年卢卡奇为恢复主体革命性所给出的方案,也是其想重新恢复主客体同一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的思维路径。
二、物化概念的理论支援背景与深层逻辑内涵
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大杂烩。我们既能在其中看到黑格尔的辩证同一性、主体异化的影响,也能看到其对韦伯可计算的合理化的颠倒,还能看到其在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上,对马克思物化概念无意识挪用并重新解释的痕迹;而最有趣的是,青年卢卡奇本人似乎并没有觉察到这其中的逻辑和概念的错位。
第一,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是对马克思的误读。正如青年卢卡奇自身指认的那样:“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非偶然。”[1](P143)但青年卢卡奇关注的是商品关系的结构,而不是商品关系的矛盾。这也注定了其对物化的探讨只能停留在商品拜物教层次,而看不到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之间层层递进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卢卡奇没有区分物化、异化和对象化。在其看来,这三者是一个意思;然而,其在马克思那里却并非如此:“马克思没有把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他认为物化有两种:一种是对象化的物化,一种是异化的物化。”[2](P7)必须说明一点,即使在人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也区分了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只不过那时其所谓的异化,是黑格尔式三段论的价值悬设,体现出一种复归应有的意味;随着唯物史观的成熟,马克思抛弃了异化史观,将物化区分为两种。对于第一种物化,马克思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作为对象化的人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和能力的确认和肯定。对象化是人的劳动的本质特征,正是对象化劳动的结果即生产力,才形成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对于第二种物化,马克思将其区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之后,成为与人的意识异在却又支配人的意识的社会力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就是如此;第二层次也是更深刻层次的物化,是事物丧失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实现了与自然物质形态合一的物化。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风作怪。”[3](P940)而青年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比较接近于马克思物化的第一个层次,强调物化的奴役性,即物役性。[4]他认为,物化使得“人的活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P147);但卢卡奇所批判的重点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强调的是物化对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自由意志的丧失的作用,是商品形式普遍化发展后,主体的人变成了客体的物。这与马克思在关系意义上所言的物,及其在更深层次的历史客观内在矛盾运动关系意义上所言的物,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青年卢卡奇虽然从马克思理论出发,但其物化是主客体颠倒的物化,而不是主体间社会关系的物化。这就把物真的理解为物了。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卢卡奇没有区分对象化和物化,所以他不可能看到,即使作为物役性的物化,其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历史必然性),是可以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扬弃自身的;并且,扬弃异化的必要客观物质基础,其实就是作为对象化的物化自身。由于对马克思物化概念不作区分的误读,在嫁接韦伯合理性理论之后,青年卢卡奇就自然地转向了对生产力本身的批判。
第二,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底色与韦伯的嫁接。青年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及物化意识导致了主客体的分裂,而消除物化就是重塑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1](P149)也就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已经不是自主创造历史活动的主体,而异化为自己所创造的客体世界的商品;而在青年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意识的恢复和历史总体性的恢复是同一的。于是,当我们重新审视青年卢卡奇给出的分析路径时,就不难发现其遮蔽的黑格尔底色: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外化就是异化的过程。主体性的恢复和扬弃异化,是在绝对精神不断实现自身的思辨运动中实现的。卢卡奇将绝对精神外化的阶段替换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将绝对精神替换成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因而,扬弃物化所造成的主客体分裂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扬弃外化而重建主体性,以实现主客体的再次同一。但是这样的改造方案,显然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了,因为青年卢卡奇并不是从物化产生的历史根源着手,去追问人类历史发展中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异于人的本质、意识之外的现象,而是停留在历史根源的外部去寻找替代方案。这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乌托邦。青年卢卡奇之所以会误读马克思的物化概念,除去黑格尔底色的逻辑困境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物化直接来源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严格地说,他通过颠倒韦伯合理化思想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之拜物教思想做出解释。”[5](P154)这样的做法,契合了青年卢卡奇既想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目标,又想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泰罗制的普遍应用,使得抽象成为统治不断加深,而马克思·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则是对当时资本主义新发展现象的精准分析。青年卢卡奇虽然认可韦伯的分析机制,却又想站在马克思的批判立场上,因此,这使他陷入了逻辑的混乱。于是,他便将韦伯的论述颠倒,再在其中融入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目标。这就自然地将一切引向了意识形态。在嫁接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后,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存在着这样的双重逻辑:其一,其表面逻辑是马克思的物化概念,但正如前文所述,卢卡奇“没有弄清马克思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地颠倒的,却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物化观点”[5](P153);其二,其深层逻辑则是对韦伯的可计算的量化的合理化颠倒。韦伯只关注生产过程中的形式合理性(只关注生产的客观进程)。对韦伯而言,人的主体性的东西在社会的客观运转面前是无意义的,“所以人(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6](P49)。这对站在资本主义批判立场上的卢卡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由于卢卡奇将韦伯的物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混同,所以其不知不觉地背离了他“只打算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的理论支撑,将马克思的物化替换成颠倒的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他说:“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1](P149)之所以说是颠倒的韦伯的合理化思想,是因为卢卡奇注入了人本主义的因素,强调物化/合理化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这是使得主客体不再同一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于是,卢卡奇所面对的,已经不是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而是加入了伦理价值的颠倒了的韦伯的量化。逻辑的颠倒并没有导致冲突,是因为卢卡奇逻辑错位的背后,是同一性的黑格尔底色。
三、物化概念的逻辑悖结
青年卢卡奇通过《资本论》及部分已出版的马克思著作中零星的物化、异化概念,来发挥其对马克思的创造性解读,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抓住了某些关键问题;但由于其理论依据是颠倒了的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因此,其对马克思社会关系意义上物化的理解并不准确。由于其将物化的物,理解为实体的物,故其将扬弃的对象,从关系转向了生产力。这也影响了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所以,青年卢卡奇虽然认可历史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历史理解成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故其无法理解马克思所要扬弃的是关系,而不是物本身。这是青年卢卡奇物化概念脱离马克思的地方,也是其与马克思革命路径的差异之所在。马克思抛弃人本主义的伦理立场,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步步完成的。正是因为发现了商品使用价值-机制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才能“跃出商品本身来研究商品”。因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象化的物化,是物化的社会历史内容本身,所以马克思不是没有看到物化对人的奴役,只不过他是先承认物化的客观存在,再从主观性的角度进行批判。而青年卢卡奇将物化简单地理解为物对人的奴役而导致的人的主体性丧失,并且错误地分析了物化的原因,从而走向了游离在历史之外的主体性解放路径。可以说,在青年卢卡奇那里,只有价值判断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而没有客观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
[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1卷)[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2016-05-22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15JJD710004)
陆寓丰(1989-),女,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5
A
1673-1395 (2016)09-0060-03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