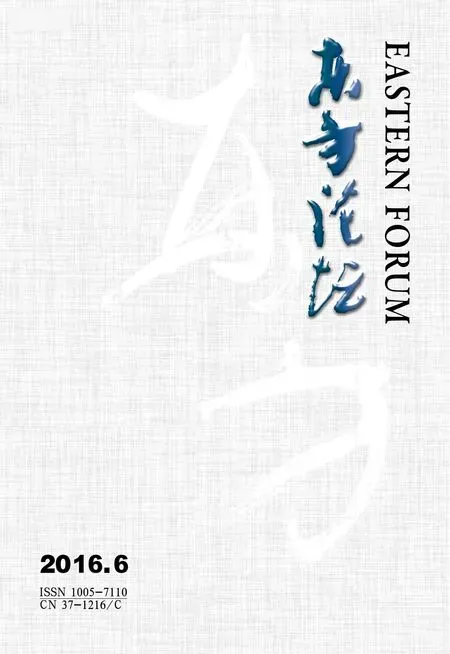中国文化探源与发展研究的新途径
——评《海陆一体化维度上的东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程 玉 海
中国文化探源与发展研究的新途径
——评《海陆一体化维度上的东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程 玉 海
在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中,关于东夷部族的聚居、生活与演变,文明与文化的研究,不仅当属其中,而且其田野考古,史料发掘和整理,理论研究和探索的成果,填补了一系列历史空白,冲击和改变着一些传统的观点和认识。同时,也将我国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研究,推向了新高峰,并且同文化自觉、探寻精神家园的各项目标密切相联。巩升起先生的《海陆一体化维度上的东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1](以下简称本书)一书,既属于上述文化探源和发展研究的范畴,又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为青岛地区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历史文化发展等方面,探索了一条创新之路,取得了优秀的成果和宝贵的经验。
一
就近代意义上的青岛市而言,其开埠建市,也仅有百余年的时间。但就现青岛地区的历史文化而言,其悠久性和丰富多彩,并不亚于我国其它历史文化名城或地区。北阡遗址、三里河遗址、城子遗址等,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如本书所言:青岛地区历史文明的曙光,至少不会晚于距今70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距今46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由“城子遗址”等反映的“古城子人”,即远古意义上的东夷“不其人”,已达到了“新的繁荣的高峰期”。因此,早在公元前692年齐国灭莱子国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这里始终是东夷人的故土,正是东夷人点燃了青岛地区历史文明的火焰。这既是本书充分论证,并有着可靠依据的重要结论,也是对东部沿海地区东夷部族和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与贡献。本书的意义首先表现在这里。
在20世纪前的两千多年间,我国关于东夷部族和文明的研究极为薄弱,其主要原因是儒家“尊夏卑夷”思想影响的结果,并由此造成了“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把“发祥地完全不同的氏族都强隶属于黄帝名下”的观点和做法。[2](P6-9)因此,在春秋后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它成为我国历史典籍中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关于东夷人的研究被边缘化,甚至成为“历史空白”。直到20世纪,由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的相继发现,这种状况方得以扭转,东夷部族及其文化的意义,逐渐得到承认。
本书坚持和深化了上述观点,并充分考证认为:“不其”两字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产物。“不”字来自东夷原始骨刻文中的“文字符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其”字也指向东夷部族的名称和图腾。正如本书所说:“自新石器晚期开始,‘其’字作为专有名称而存在于历史记忆之中”,它“首先是东方一个古老部族的名称”[1](P70)。
在夏、商东夷人的莱夷族群中,存在着一个被称为“其”的部族,它是“由若干胞族组合的总体”,是莱夷中“最强大的一个部族”,“它所居住的区域相当辽阔”[2](P45)。本书认为:“不其人”,应为莱夷“其族”的一部分。并指出:“上古时代在东方曾有其族和其国的历史存在,其立族和立国之地就在山东半岛”[1](P86),“尔后在中原王朝不断东扩的背景下,其族和其国的领地不断压缩并向东迁徙,从而到了今不其地”[1](P86)。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其”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概念,“这是一个古老的东夷部族”,“一个古文化体系”,其“内在于东夷文化大体系中”。[1](P60-88)
本书不仅确定了“不其”与东夷“其族”和文化的关系,还厘清了它的历史延续和承继,那就是“不其”由图腾、族名,而被直接承继为地名和山名,即“不其地”和“不其山”。此后又出现了“不其县”“不其城”“不其侯爵”“不其侯国”等六重承继。这一文化现象极为独特,它本身已经证明,“不其”直接源自东夷文化,不仅是“直系”,而且没有间断。这种文化现象在国内极为罕见,同时,它也从另一方向提供了东夷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证据。
一个严肃科学结论的确立,往往仅需几句话就能表述清楚,但求证与探索过程的艰辛和痛苦,却并不为人所知。确立“不其文化”源于东夷文化同样如此,由于时代久远,除了“不其山”仍屹立在崂山西北麓,几乎没有多少可供直接使用的现成资料。这也是过去无人触动这一课题的原因之一。由此,本书所以把“不其文化”喻为不亚于“迷津或阿特兰蒂斯沉没”般的迷题[1](P9),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巩升起先生很早就认识了这一课题的意义,多年持续不断的对它进行探索和研究。史海荡舟,艰辛探索,方拨开迷雾,披沙见金,从而把散落于东夷骨刻文、陶文、甲骨文和金文,大量典籍中的只鳞片爪般的点点资料,发掘整理出来,并在本书中加以全面考证和论述,终解开了不其谜题,为青岛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文化探源作出了贡献。
当然“不其文化”源头的确立,对全面、准确地认识青岛地区和城阳的历史文化极为重要, 它作为与“琅琊文化”“即墨文化”等基本相同的古文化渊源,共同支撑起了青岛地区历史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平台,展现了以“不其”为标志的“不其人”“不其部族”“不其文化”,以及包括“古城子人”在内的青岛地区古先民,在这块广阔的东夷故土上聚居、渔猎、航海、生活,以及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过程,从而揭开了青岛地区古历史文明的神秘面纱。当然,青岛地区和城阳,在全国、齐鲁和山东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也就在其中了。
二
“海陆一体化”和“东方中的东方”,是本书提出的两大命题,也是本书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它与“不其文化”东夷起源说,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它说明“不其文化”的意义,还深深植根于海洋文明与文化之中,无论是不其地东夷故人的航海活动,还是我国古代发生在这里的海战,春秋至北魏年间与这里相关的大航海,以及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等,都充分证明了它的产生与发展,同我国海洋文化紧密相联,它属于古代中国海洋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说,它也证明了青岛地区历史文明和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属性。
新石器时期,也就是龙山文化时期,古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的同时已经有了交换,因此就有了交通和古道,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4](P695)。我国历史学界和考古界,依据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点分布图认为:在新石器时期,我国西部已形成了从中原沿黄河和渭水的古道。同时,我国东部也存在着由“古济水直到东海之滨的古水道”,并且还是“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4](P398)。
莫言创作以其独特的风格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莫言小说创作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一直以来,不少学者认为莫言作品具有狂欢化的叙事特点。从狂欢化理论的形成及其特质来看,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叙事并不是对狂欢化理论的简单模仿,而是体现了高密东北乡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欧洲狂欢文化的渊源不同,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叙事没有狂欢节庆仪式的喜庆气氛和广场效应,而更多地表现了民间底层社会的人生苦难和悲情诉说。
就水运和海运而言,“5000-7000年前已有舟楫的发明”,即原始“桴与舟”,“桴即竹筏,或木筏”,“舟就是独木舟”,这就是古语中的“刳木为舟,剡木为辑”[4](P398)。
由上可见,至少到龙山文化时期,滨海沿岸居民,已经有了“桴舟”和航海活动。由于东方滨海的原始居民为东夷人,所以,本书认为“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民族已创辟大航海史诗而传播文明于太平洋两岸”。
不其地的“古城子人”,作为东夷部族的一部分,无疑应属于具有航海活动的古人类。“古城子遗址”发现的“蚌锯”等原始工具,说明他们已具备建造“桴舟”的条件和能力。当时,古胶州湾的海岸线,可直接到达今城子遗址附近。拥有如此理想的海湾航海条件和能力的“古城子人”,为了生存与发展,也必然会有航海活动。为此,本书认为,“古城子人”不仅开始了航海活动,而且在胶州湾东北岸不其地海域,还会“存在着古港”,“至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关于东夷人、“古城子人”航海和古港的更直接证据,虽然还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现,但本书提出的观点,已具备了一定的事实依据,仍应为可靠的结论。
商、周时期,这里的航海活动不仅已很频繁,而且开始了远洋航行,周初的箕子东渡,就已到达朝鲜。有一种观点认为,箕子由胶州湾出航进入远洋。如果这一事实成立,那么它对“不其文化”海洋属性的意义不可估量。本书也非常慎重的记述了这一点。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南北海上航线已经通畅,如《左转·哀公七年》中的“吴之舟师自海入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范蠡“浮海出齐”等。当时,吴、齐等沿海诸侯国,各自的海上战船已达到数百艘,吴、齐两国还在琅琊海域打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战。这就证明,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海船已适应远程航海,已积累了海运和航海经验。史料记载:此时我国商船已能由福建一带,到达今越南和印尼,这应为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
秦汉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海运确已相当发达”[5](P686),虽然汉武帝时期已打通了出使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但由于陆路交通不断被阻断,“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线”,首要的还是“海上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到汉末三国前,人们甚至一度忘记了陆上通道,“只知道有通往大秦的水道”[5](P686)。
以上充分说明了两点,一是包括不其地海域和女姑口在内的胶州湾两岸,早在春秋时期已是由海上出入齐国的必经之地,已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运输和海路交汇之地。公元468年,为争胶州湾和不其地的控制权,建都南京的刘宋政权,同北方的北魏,曾在女姑口海域,爆发了一次大海战,这也是我国少有的几次大海战之一。可见,至少从春秋战国起,胶州湾和不其地,在海运和航海方面已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今天对这方面意义的估价,可能仍然不足。二是由于我国南北海上航行和贸易的通畅,北方的黄海和渤海,不可能不参与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之中。为此,胶州湾和不其地海域,在古代北方丝绸之路中,也必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秦汉到东晋年间,曾有过三次大的航海活动涉及不其地海域,并对“不其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包括:公元前219-前210年,徐福两次东渡,到达日本和朝鲜;公元前182年不其人王仲,因“诸吕之乱”而避祸海外,由不其东渡朝鲜;公元413年,东晋高僧法显,在历经14年的印度取经后,由海上返回,在崂山登陆,入住不其城。这三次航海或经不其海域,或直接从不其出海,或在不其地沿岸登陆。
特别是法显的这次航海,不仅对不其文化影响巨大,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公元399年,即佛教传入中国300余年后,高僧法显为解决佛经中的难题,毅然走上了徒步西域取经之路,直接到达印度,携经而归。他的西域取经,不仅早于唐玄奘230余年,而且开创了佛教史上的“法显时代”。按汤用彤先生的说法,“故海陆并尊,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返者,恐法显为第一人”[6](P380)。法显由印度到达斯里兰卡,转海路返回,经孟加拉湾、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又经广州,到东海、黄海,在崂山登陆。
法显的这次航海说明,早在郑和七次下西洋(1405-1433年),达伽马(1498年)绕过好望角,从西欧到达印度1000余年前,法显的船队已经完成了由印度洋到达黄海、渤海的航程。这同时也证明,由不其地海域、胶州湾,可直接到达印度洋。这就为古代北方海上丝绸之路,为不其地沿海口岸、女姑口等,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和地位,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据。
同时,它对“不其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显登陆后,郡守李嶷躬自迎劳,法显“持经像随还”,进入不其城。法显驻不其城期间的谈话和活动,必然涉及佛经、佛事等内容,所以他到达不其城,以及他对此地佛教兴盛的影响绝不可低估。正如本书所说“在不其地,高僧法显必有讲经之为”。同时,他到达本身,也“提示了佛教海上传播路线的相关问题”,“法显登陆对不其文化的意义不可估量,在佛教中国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时空中打下深深的不其烙印”[1](P173)。
上述事实已经揭示了汉武帝把不其作为走向海洋东方的大门与桥头堡,设立明堂、太一祠、交门宫的真实原因,同时也证明了本书提出的“海陆一体化”和“东方中的东方”命题的正确性。当然,这两大命题还如点睛之笔,使人们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它不仅是解开“不其文化”谜团的钥匙,而且在本书提出的构建我国海洋历史文化体系任务中也具有重大意义。
三
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形态,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所以,汉以后在不其县名下发展的“不其文化”,既是“存在于中国东方的一种地域文化形态”,又是传统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部分。本书认为:“不其文化”包括了“帝王巡狩史、海上求仙史、明堂渊源史、太一崇拜史、道教史前史、经学流变史、佛教传播史、海上交通史、中外关系史”[1]等九重内涵。它在汉后800余年发展过程中,不仅内容不断丰富,而且高峰迭起,包括汉初的明堂文化和太一文化;王吉、房风等不其儒学家、经学家群体,伏湛、郑玄等集结于不其的知名硕儒,在这里创造了几度辉煌的两汉经学;佛教在这里的兴盛,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我国佛教传播路径的思考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发生于这里的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现象,虽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烙印,但它实际已完全超出了地域的范畴,已属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
正确把握“不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双重性,既是完成课题的基本要求,也是构成它文化特色的基本要素,同时,由此也决定了这一课题的艰巨性,并考验着作者的意志和水平。当然,课题的完成、成果的优秀,其成功的奥秘在这里,给人们的启示也在这里。
盛世修史,当今县域、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本书把地域、区域文化研究,放到了中国历史和文化,齐鲁和山东历史和文化的大格局中加以探索,比较和研究,把“不其文化”,放在东夷文化,中国历史文化起源,历史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大趋势中,探其源流、观其发展、述其意义、升华理论。正如本书所说:“阐述不其的历史基脉和文化精神……完全可以将其结合到我们对古代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中去,结合到我们对大历史的对话中去,结合到我们对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的体系的反省中去。在宏阔的历史景深和文化背景上,同样具有适应力,而且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多元对话中同样具有适用力。这也是参透中国传统意识,并完善天人合一关系思维的一个合理的渠道”[1](P104)。这段近乎哲学意义的论述,实际在指明一种方法论的思想,那就是既要登高望远,使“不其文化”与中国、齐鲁和山东历史文化的起源、发展,多元比较浑然一体。由此把握“不其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展现其历史意义和光辉。同时又要俯视不其,扎扎实实的收集、整理、探索、研究各种资料,再现历史轨迹和真貌。把握基本特色和特点,从而既避免就事论事,就县论县,先天不足,落入俗套,同时也能以小见大,在“小史”研究中,展现博古通今的“大学问”。这种方法和结果,无疑为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闯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历史文化研究并非总是古语、古董、古事与古板,重要的在于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本书实现了这一基本要求。作为“史书”,它清晰的展现了基本历史线索,使读者较容易的把握历史顺序和历史过程。作为总结经验和反思,作为文化研究,它又处处闪烁出仰望星空、说古论今、升华理论和哲学反思的光芒。当然,文化浪漫和畅想,也使本书文字活泼、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如本书提出的“一地之兴,必有一地之史”。“海洋是大地的载体,大地是海洋的归宿”。“中国思维是圆的,起点和终点合一”。“今天看到的是自然,上古看到的则是神奇”等观点。再如“今天是历史和未来的联结者、沟通者,今天的精神世界有历史和未来同时贯注的光辉”。“大自然构成的文化基因,在自然与文化的融合中形成地脉、文化之脉”。“中国文化精神统一而多元、南北分殊、东西异禀”。“一瞬与亘古之间,如星辰般稀有,而丰富的语言可以参透自然、参透世界”。等等。这些极富哲学意义和哲理的语言,在文学浪漫的表达方式下,显示出它的优美、通透和理性。这是本书的又一成功之处,也启示着人们如何作好历史课题。
一部优秀的著作,虽然包含了艰苦的文字和写作功夫,但它也决非仅仅是“写出来的”,它首先是作者长期探索和研究的结果,渊博学识,扎实的功底,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厚积薄发的结果,说到底还是“面壁十年图破壁”,“十年磨一剑”和“甘做冷板凳”等学术精神的结晶。这既是完成课题的基本条件,成功的基本奥密,也是学人应有的本色和科学精神。
在《海陆一体化维度上的东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出版之际,我们看到了它为新一轮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所提供的这一范本,探索的新途径和经验,它对青岛历史文化研究等多方面的意义和启示。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以极为严肃、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已经开启了新的研究与探索的航程,即直面由于史料、时机、个人认识等因素所导致的某些缺憾,继续深入探讨在胶州湾沿岸,以及日照、泰山一线,古东夷各部族的关系、文明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古不其人航海,以及古港口发展的研究;古不其文化、琅琊文化、即墨文化、胶州文化、崂山文化等关系,它们对青岛历史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整体意义,及一体化研究;关于佛教在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胶东和青岛地区的传播路径、发展状态、独特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关于重构我国海洋文化体系方面的研究等等。
生命不息,研究未终,学人归宿,可贵可泣。
[1] 巩升起.海陆一体化维度上的东方秘境——不其文化研究 [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2] 李白凤.东夷杂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1.
[3]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4]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为山东省政协常委,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