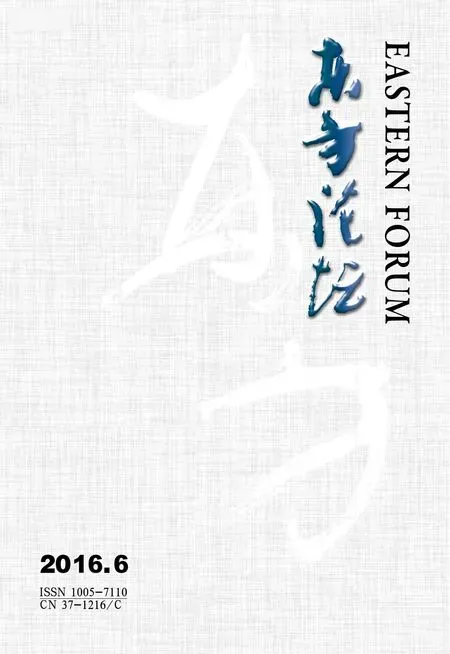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刘 志 平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刘 志 平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焦氏易林》;兼并;六国;扶苏;商鞅;昏暴之政
《焦氏易林》是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易学典籍,①关于《焦氏易林》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笔者已进行过相关阐述,详见拙文《〈焦氏易林〉所见西汉农业自然灾害及牛耕和粮食亩产量》,载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是“象数易留传后世的少数著作之一”[1](P88)②王子今教授还指出:“我们讨论《焦氏易林》,则更为重视其中体现在汉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交接的特质。人们都注意到,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提升之后,有逐渐教条化、法典化的倾向。……《焦氏易林》则体现出另一种文化走向,可以看作是将经学中最为精深的《易》学与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数术信仰相结合,并且应用于日常普通的民俗生活的绝好的文化标本。”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55页。,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生动展现了汉代人的秦史观,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政治文化启示。
一、对秦兼六国的肯定
《焦氏易林》对秦兼六国有如下记载:
《大畜·离》:“车辚白颠,知秦兴起。卒兼其国,一统为主。”(《焦氏易林》卷二)③关于《焦氏易林》的版本及笔者所引《焦氏易林》林辞的来源,笔者亦已进行过相关阐述,亦见拙文《〈焦氏易林〉所见西汉农业自然灾害及牛耕和粮食亩产量》,载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坎·剥》:“车邻白颠,知秦兴起。卒兼其国,一统为主。”(《焦氏易林》卷二)
《否·否》:“秦为虎狼,与晋争强。并吞
其国,号曰始皇。”(《焦氏易林》卷一)
《焦氏易林》所谓“车辚白颠”和“车邻白颠”,④《经典释文》卷五《毛诗音义上》:“‘车邻’,本亦作‘隣’,又作‘辚’。”〔唐〕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7页。是对《诗经·秦风·车邻》“有车邻邻,有马白颠”的化用。《毛诗正义·秦风·车邻》序云:“《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孔颖达《疏》:“正义曰:作《车邻》诗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国始大,又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来,世为附庸,其国仍小。至今秦仲而国土大矣。由国始大,而得有此车马礼乐,故言‘始大’以冠之。”[2](P368)细观《焦氏易林》林辞,亦言“秦之兴”,义同《毛诗》。⑤另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齐》《韩》于此与《毛》义同。〔清〕王先谦撰,吴格点校:《诗三家义集疏》(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35页。而紧接着“卒兼其国,一统为主”的表述,无疑是对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的肯定。对秦兼六国的这种肯定态度也可从《震·困》“六明并照,政纪无统。秦楚战国,民受其咎”(《焦氏易林》卷四)的表述中看出。不过,《否·否》所言“秦为虎狼”,又似乎表现出对“秦”及“秦始皇”的贬斥。①先秦秦汉时人在贬斥“秦”及“秦最高统治者”时,常以“虎狼”为喻。尉缭就曾批评秦王嬴政“少恩而虎狼心”(《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0页);楚昭雎在劝阻楚怀王赴秦时也说“秦虎狼,不可信”(《史记》卷四○《楚世家》,第1728页);屈原在劝阻楚怀王赴秦时也说秦为“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84页);魏信陵君无忌也认为“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57页);苏秦也说秦是“虎狼之国”(《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第2261页);樊哙在鸿门宴上也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313页);仲长统也说“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49页)。而《焦氏易林》对“秦”及“秦始皇”的这种贬斥,似可理解为对秦只以诈力统一六国的批评。
在“过秦”思潮盛行的汉代,对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似乎多持肯定态度。汉初辩士陆贾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3](P2699)陆贾在此并未否定“秦并天下”本身,只是批评其在并天下之后不行仁义,不法先圣。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批评统一六国之后的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以及秦二世“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的同时[4](P14-15),也对“秦统一”结束了“诸侯力正,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4](P14)的局面表示了肯定。对此,司马迁也是赞同的,所谓“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3](P276)晁错在对文帝之诏策时有言:“臣闻秦始并天下之时,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迟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财用足,民利战。其所与并者六国,六国者,臣主皆不肖,谋不辑,民不用,故当此之时,秦最富强。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帝王之资也,故秦能兼六国,立为天子。当此之时,三王之功不能进焉。及其末涂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5](P2296)晁错虽批评秦兼六国后的“暴酷”之政,但对秦兼六国有“三王之功不能进焉”的赞扬。主父偃在向汉武帝“谏伐匈奴”时说道:“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踰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饟,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3](P2954)主父偃在此虽对秦始皇用兵匈奴进行了批评,②主父偃后在汉武帝出兵进击匈奴的情势下,又改变了看法,“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页。但对其“并吞战国,海内为一”,作了“功齐三代”的赞扬。严安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说道:“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岁,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愬。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輓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3](P2957-2958)严安也是虽对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急刑罚,厚赋敛,重繇役,贱仁义,贵权利,下笃厚,上智巧”和“北构于胡,南挂于越”之举表示批评,但对秦兼六国本身有使“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的肯定。
而汉文帝时的贾山对“兼六国”之“秦”是这样评价的:“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5](P2328)虽以“虎狼”为喻,表示对“秦”及“秦始皇”的贬斥,①这种贬斥,可理解为对秦只以诈力统一六国的批评,同《焦氏易林》。又对其“并吞海内”后“不笃礼义”提出批评,但未明确否定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班固也说:“若秦因四世之胜,据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奋其爪牙,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猋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也。…… 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5](P1089-1091)又说:“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5](P1096)可见班固和贾山一样,也未明确否定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只是以“豺狼”为喻,表示对秦将的贬斥,②这种贬斥,也一样可理解为对秦只以诈力统一六国的批评,同《焦氏易林》。并对秦统一天下后“穷武极诈”“专任刑罚”而不以“文武相配”提出批评。这与张耳、陈余所言“秦为无道,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3](P2573)是截然不同的, 张耳、陈余于此彻底否定了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
汉代人对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多持肯定态度,是与汉承秦之统一帝国形式分不开的。如果批评“秦统一”本身,就会削弱“汉统一”的合理性。司马迁不仅对“天下一统”有“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感慨,且对刘邦承继“秦统一”而建“汉统一”之帝业有“岂非天哉”的感慨,[3](P759-760)③而关于司马迁对“秦统一”的认识,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曾指出:“司马迁并未对战国时代秦国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秦之所以一统天下,既是因为地势坚固,亦是因为得到天助。……《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各战国世家,两者配合协调,通过叙述地上的天下统一行动,来说明秦统一之天命。”(〔日〕藤田胜久著,曹峰、〔日〕广濑薰雄译:《〈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58页)可见,司马迁认为“秦统一”和“汉统一”皆为“天意”。足见“天下一统”乃战国秦汉之大势,且来之不易。
而具有民间文化色彩的《焦氏易林》对秦兼六国的客观积极意义的肯定,可看作是儒家“大一统”理念在汉代民间得到普及的一个体现。
二、关于扶苏
《焦氏易林》中有同情扶苏的林辞:
《大畜·夬》:“太子扶苏,走出远郊。佞幸成邪,改命生忧。慈母之恩,无路致之。”(《焦氏易林》卷二)
扶苏的事迹,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及《史记·蒙恬列传》。扶苏的政治风格和文化取向似乎不同于其父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坑儒”一事上,扶苏曾对秦始皇有这样的建议:“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3](P258)可见,扶苏很重视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且将其提高到能影响“天下安否”的政治高度。亦可见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在秦代有广泛的影响。而对于扶苏的建议,秦始皇的反应是:“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3](P258)这或许是秦始皇在“大怒”之下而做出的情绪化举动,因为后来秦始皇在死前还是清醒地想到了长子扶苏,有让扶苏以太子继承帝位的意思。但因赵高、胡亥、李斯的阴谋而使嬴政的遗愿未能实现。④详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4页;《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548—2551页。不过,据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赵正书》,胡亥被立为皇帝继承人是秦始皇听从了李斯、冯去疾的建议而做出的决定,相关简文为:“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夫(扶)胥(苏)、中尉恬。”(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能否据此就断然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我们认为对此应持谨慎态度。退一步讲,就算《赵正书》所载更接近历史真实,我们还是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迄今为止,更多的史料表明,汉代官方和民间关于扶苏事迹的认识是不同于《赵正书》的,这种认识本身已经成为真实的历史现象。而扶苏的仁义忠孝又从其接到“赐其死”的假诏书后的言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3](P2551)当然,扶苏是在不知其父秦始皇已死和赐死诏是假诏的情况下自杀的,若知其父已死,并知赐死诏是假诏,想必不会有自杀之举,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种走向。可见,赵高等人对秦始皇去世这一消息的封锁是成功的。
扶苏的事迹不久就在社会上传播开来,不过关于扶苏之死,当时民间似多未知晓,又加上扶苏的政治口碑很好,故陈胜起事时利用了这点,他说:“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3](P1950)
赵高谋害扶苏之事多次被汉代人提及,如樊哙在刘邦因病“恶见人,卧禁中”的情势下,曾带领群臣直入禁中并对刘邦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5](P2072-2073)终使“高帝笑而起”。[5](P2073)又如叔孙通在刘邦“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时向刘邦进谏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汙地。”[5](P2129)加上“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刘邦“遂无易太子志”。[5](P2129)看来刘邦对扶苏之事是心知肚明的。其实,刘邦多方面吸取秦亡教训,其中很早就注意到立太子这一问题。其在彭城之战惨败后的高帝二年(前205)六月,就立刘盈为太子,“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3](P372)
扶苏的悲剧后又警醒着戾太子刘据,最终促使刘据斩杀江充及其同党。《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据》有详细记载:“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廏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5](P2742-2743)不过最后戾太子刘据还是被追逼自杀,这同扶苏的结局一样,但汉高层并未因戾太子自杀而产生乱局,这无疑是因为戾太子死时汉武帝仍活着,能有机会掌控残局,最终做出如司马光所说的“晚而改过,顾讬得人”等“免亡秦之祸”之举。[6](P747-748)而秦高层之乱首先源于秦始皇暴崩,而后扶苏之死又加深了混乱的程度。
西汉末期的扬雄在《尚书箴》中写道:“昔秦尚权诈,官非其人。符玺窃发,而扶苏陨身。一奸愆命,七庙为墟。”[7](P418-419)透露出对扶苏的政治同情和对赵高的斥责。
东汉时人也有言及扶苏之事的,如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广陵思王刘荆,在写给东海王刘强的书信中,愿刘强“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8](P1447)使“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8](P1447)而明帝刘庄因刘荆为其同母弟,故“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8](P1448)又如汉冲帝刘炳崩后,梁太后“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李固表示反对,言及“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终使“太后从之,即暮发丧”。[8](P2082-2083)王充在《论衡·变动》中亦有言:“李斯、赵高谗杀太子扶苏,并及蒙恬……其时皆吐痛苦之言。”[9](P657)
可见,汉代人在将扶苏之事作为政治警示的同时,对扶苏表现出广泛的政治同情。扶苏因其秉持儒家文化立场和具有仁孝忠义的品质而受到汉代人的肯定和同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文化在汉代处于主导地位。《焦氏易林》所谓“太子扶苏,走出远郊。佞幸成邪,改命生忧。慈母之恩,无路致之”,正表达了对扶苏浓厚的怜悯之情,而这更可看作是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得到普及的一个体现。
以汉代人对扶苏的肯定与同情为基调,汉以后之人明确提出一种强烈肯定扶苏的历史假设,所谓“使扶苏嗣位,则秦祚尚可延”;[10]“若扶苏嗣位,三五载即世,而子婴承之,秦社岂墟乎哉”;[11]“使扶苏嗣位,即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何所不可”。[12]
三、对商鞅的态度
《焦氏易林》中有批评商鞅的林辞:
《升·需》:“商子无良,相怨一方。引斗交争,咎以自当。”(《焦氏易林》卷三)
《丰·遁》:“商子酷刑,鞅丧厥身。”(《焦氏易林》卷四)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3](P2236-2237)《升·需》林辞言此事,而所谓“咎以自当”,则透露了对商鞅的批判态度。《丰·遁》林辞乃“言商鞅用酷刑,终自害也”,[13](P544)①《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灭商君之家。”《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2237页。可见对商鞅的重刑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
王子今教授曾从秦汉时期法家命运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汉代人对商鞅的批判。[14](P202-208)不过,汉代人对商鞅似既有批评,也有赞扬,如司马迁对商鞅就是这种态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3](P3313)赞扬商鞅强秦之法。而在《商君列传》中对商鞅有这样的评价:“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3](P2237)又对商鞅的“刻薄少恩”提出批评。又如《盐铁论·非鞅》集中反映了汉代人对商鞅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桑弘羊极力肯定商鞅,而文学儒生对商鞅进行了尖锐批评。[15](P93-97)对此,王子今教授指出:“由于文化基点不同,有关商鞅评价的见解几乎完全是针锋相对的。”[14](P207)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做进一步的分析:盐铁会议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国家高层会议,从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我们可知当时汉代人的重大关切。故对商鞅的评价能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足以说明此问题关涉重大。大概是因秦兴于商鞅之霸道政治,又亡于商鞅之霸道政治,故汉代人对商鞅产生了极端矛盾的看法。对商鞅这种极端矛盾的看法,我们认为给中国古代执政者提供了一种理论警示,以使其在政治实践层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状况动态性地保持“王道”与“霸道”的合理搭配。②《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卷九《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王子今教授指出:“正统的儒学学者的法家观,以为其理想的地位,是辅助儒学政治以求成功,这就是所谓‘以辅礼制’。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其深意。”同时指出,商鞅的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受到重视,“也可能由于社会再次沦入‘战国横鹜’,‘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的境况,使得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重新得以上升了。”(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第211—213页)金春峰指出,盐铁会议的“辩论表明,法家思想是武帝时期政策的实际指导思想”,而这是由于战争的开始,然而,随着“武帝时期的战争及战时体制的结束,新的和平和休养稳定时期的到来,也必然使一度居于支配地位的法家思想重新跌落下来,由无权的儒生和儒学取而代之。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桑弘羊的进攻,是这种历史变化的先声和征兆,标志着新的转折时代的到来”。(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255、259页)看来,法家霸道政治在非和平时期确实受到重视,而在和平稳定时期儒家王道政治则受到更多重视。不过,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蜿蜒曲折的,总有诸多强力的偶然因素促成了历史规律之外的特异历史阶段面相的出现。“王霸问题”(“儒法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话题。[15](前言,P19-22)“王霸问题”(“儒法问题”)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也曾受到关注,这令人印象深刻。
《焦氏易林》对商鞅的批判反映了商鞅的反面政治形象在汉代民间的牢固树立,也可看作是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得到普及的一个体现。
四、对秦昏暴之政的批判
《焦氏易林》中多有批判秦昏暴之政的林辞:
《乾·大壮》:“隙大墙坏,蠹众木折。狼虎为政,天降罪罚。高弑望夷,胡亥以毙。”(《焦氏易林》卷一)
《坤·大壮》:“岁饥无年,虐政害民。乾溪骊山,秦楚结冤。”(《焦氏易林》卷一)
《蛊·贲》:“转作骊山,大失人心。刘季发怒,禽灭子婴。”(《焦氏易林》卷二)
《大壮·需》:“君不明德,臣乱为惑。丞相命马,胡亥失所。”(《焦氏易林》卷三)
《睽·井》:“井堙木刊,国多暴残。秦王失戍,坏其太坛。” (《焦氏易林》卷三)
《夬·噬嗑》:“长城骊山,生民大残。涉叔发难,唐叔为患。”(《焦氏易林》卷三)
《中孚·姤》:“老慵多郤,弊政为贼。阿房骊山,子婴失国。”(《焦氏易林》卷四)
对秦昏暴之政的批判,是汉代人一致的态度,如前述陆贾、贾谊、晁错、主父偃、严安、贾山和班固等人皆持此态度。而汉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治举措正是基于对秦昏暴之政的批判而推行的,这可说是对秦亡诸多教训①从汉代人的理论总结及政治实践可知,汉代人除了对“昏暴之政失民心”这一根本性教训的吸取,还有对“不早定太子而灭祀”“不封子弟功臣而无以承卫天子”等教训的吸取。中最具根本性的教训的吸取,此即《蛊·贲》 所谓“人心”问题,《夬·噬嗑》所谓“生民”问题,亦即“民心”问题。
汉代人对“民心”②“民心”一词在先秦文献里已频繁出现,如《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页) 《孟子·尽心上》:“善教得民心。”(〔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97页)《吕氏春秋·顺民》:“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99—200页)多有重视。贾谊曾说:“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贤者而贤者归之。”[4](P392)又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呜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4](P338-339)强调“民”是“国’“君”“吏”之“本”“命”“功”与“力”。贾谊还认为对“民”不善,必受“天殃”,“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故强调对“民”的态度应为“至贱而不可简”“至愚而不可欺”。[4](P339)《淮南子·氾论训》也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16](P921)而对贾谊所言“民欲”和“民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淮南子·兵略训》也有详细阐述:“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得道之兵……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故明王之用兵也,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民之为用,犹子之为父,弟之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决塘,敌孰敢当!故善用兵者,用其自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为己用也。用其自为用,则天下莫不可用也 ;用其为己用,所得者鲜矣。……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民胜其政,下畔其上,则兵弱矣。故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知强弱之势,此必胜之本也。……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积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兵之所以强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行者,威也。……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于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偿其二责,而上失其三望,国虽大,人虽众,兵犹且弱也。”[16](P1043-1090)其实,刘邦在灭秦的军事行动中早已很好地实践了这一兵学思想,刘邦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后,“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3](P362)
汉代皇帝的诏书对“民心”也多有言及,如《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诏书有“祈进民心”[5](P166)一语;《汉书·元帝纪》所载永光二年(前42)三月诏书有“至今有司执政,未得其中,施与禁切,未合民心”[5](P289)之语;《汉书·元帝纪》所载永光四年六月诏书又有“政令多还,民心未得”[5](P291)之语。可见,“民心”确实受到汉代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焦氏易林》在批判秦昏暴之政时说到“骊山”“长城”“阿房”,这是秦汉时人批评秦昏暴之政时所使用的标志性语词。
贾山曾有言:“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5](P2328)刘向在建议汉成帝实行薄葬时也说:“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5](P1954)谷永在批评汉成帝“改作昌陵”之举时言其“役百乾谿,费疑骊山”。颜师古注:“言劳役之功百倍于楚灵王,费财之广比于秦始皇。”[5](P3462)①这与《坤·大壮》所言“乾溪骊山,秦楚结冤”一样。
秦末大乱时,武臣在作反秦动员时说道:“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3](P2573)司马迁对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之举有“轻百姓力”[3](P2570)的批评。伍被曾批评秦“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3](P3086)严尤在批评秦始皇对匈奴的政策时也言及“长城”,他说:“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5](P3824)班固也曾批评秦“奢淫暴虐,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填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5](P1472)东汉时人杨终也曾向汉章帝上书说:“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8](P1598)贾谊曾孙贾捐之在批评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时,说到“《长城之歌》至今未绝”。[5](P2831)②关于《长城之歌》的内容,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河水注》引扬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65页)汉末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引用到《长城之歌》,其诗曰:“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间。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页)秦汉时人以歌谣的形式表达对“秦修长城”的批判,足见批判“秦修长城”的观念深入时人之心。
而对于“阿房宫”的修建,秦末大乱时,秦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就已经表示反对,主张“止阿房宫作者”。[3](P271)秦二世胡亥不但不采纳这一建议,反而要治冯去疾、李斯和冯劫的罪,最终冯去疾和冯劫自杀,李斯被抓进监狱,最后也被杀。[3](P271-273)汉代人多有对秦修阿房宫的批评。贾山曾有言:“(秦)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骛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讬处焉。”[5](P2328)伍被在批评“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时,也说到秦“作阿房之宫”。[3](P3090)东方朔也曾说“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5](P2851)班固也说秦“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5](P1447)
《大壮·需》所谓“君不明德,臣乱为惑。丞相命马,胡亥失所”,是对赵高专权、胡亥昏聩的斥责。《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3](P273)而《史记·李斯列传》有不完全一样的记载:“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3](P2562)陆贾《新语·辨惑》又有这样的记载:“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邪,以鹿为马也。’高曰:‘乃马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于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其直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于闇昧之事乎?”[17](P75-76)虽然以上材料所言具体情景有不同之处,但在斥责赵高专权、胡亥昏聩方面是一致的。
《焦氏易林》对秦昏暴之政的批判,无疑也是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得到普及的一个体现。
综上所述,《焦氏易林》对“秦兼六国”之“大一统”的肯定、对扶苏的同情、对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批判,都可看作是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得到普及的体现。而这和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学在政治上统治地位的确立是密切相关的,正如金春峰所言:“宣帝时期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确实已经确立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国家政权的组成人员上,首次得到了体现。从此以后,至东汉末年,儒学一直享有政权文官组成上的优势和独尊的地位。”[18](P272)王子今教授对此也有非常精当的论断:“《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是儒学地位空前上升,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也是儒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实现‘更化’,逐步走上神学化道路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儒学影响的推广,并不仅仅限于其学术原理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尊重,其政策建议为帝王所采纳,而更突出地表现为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同以及通过这一媒介向民间的文化渍染和精神控制。儒学向社会基层的空前规模的渗透,也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研习人士的增多和传布范围的扩大,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对民俗生活的全面影响,包括对下层社会思想和言行的逐步规范。”[14](P262)
通过细致考察汉代人的秦史观,我们还可知汉代人对秦的反思是理性的,对秦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汉代人对秦的这种理性反思无疑是为了使汉帝国的存在更具合理性、更能持久。汉代人对秦的这种理性反思掀起了中国帝制时代“以史为鉴”这一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的第一个波峰。当然,从长时段的角度看,历史上的中国执政者最终似未做到“以史为鉴”,王朝周期循环就是很好的说明。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否定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于一朝一代之现世中,由于执政者注重“以史为鉴”,在一定历史时期确实收到了值得肯定的积极效果。
[1] 高怀民.两汉易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贾谊撰, 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7]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8] 范晔.后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卷一)[M].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1] 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一)[M].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2] 李贽.史纲评要(卷四)[M].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中国基本古籍库》本.
[13] 尚秉和注,尚秉义点校.焦氏易林注(修订版)[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14] 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侯德彤
Han Dynasty People's Outlook on the History of Qin Dynasty from Jiao Shi Yi Lin
LIU Zhi-ping
( College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
As a special cultural classic written roughly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Jiao Shi Yi Lin (literally: "Forest of Changes of the Jiao Clan")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which have many record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By investigating carefully Jiao Shi Yi Lin's attitude to the unifi c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Fu Su, Shang Yang and the tyranny of the Qin Dynasty, we can know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people's outlook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Dynasty and the popularity of Confucianism among the folks of Han Dynasty and the Han Dynasty people's rational introspection of the Qin Dynasty.
Jiao Shi Yi Lin; unifi cation of the Qin Dynasty; Fu Su;S hang Yang; tyranny of the Qin Dynasty
K234
A
1005-7110(2016)06-0015-08
2016-10-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 (14ZDB028);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6JK1713)
刘志平(1981-),男,湖南沅陵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