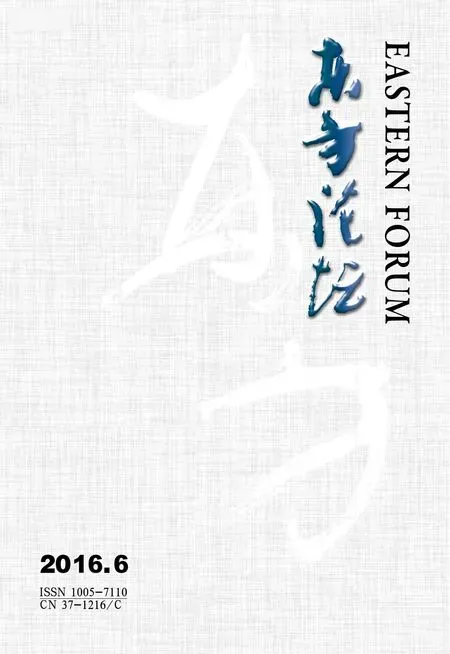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分期问题
韩 晗
(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00)
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分期问题
韩 晗
(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00)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也是第一个时期,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此为萌芽期;第二个阶段为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从1901年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此为发育期,期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多门类逐渐完善;第三个阶段为第四个时期至第六个时期,从1917年至1949年,此为成熟期,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完备。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晚清;历史分期
学界公认,文化产业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概念,封建社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并无文化产业,前者只能说存在着具备文化产业特征的文化形态,但不具备产业化的生产、消费方式与社会化的规模;而后者只有文化事业,而无文化产业(譬如前苏联与今天的朝鲜)。西方学界对于文化产业、文化工业相关问题的反思与研究,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资本主义问题研究升华之后的结果,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①“文化工业”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人所提出,用以批判现代西方文化的工业化生产,认为文化成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商品,丧失了其人文主义的启蒙意义,后世一般以“文化工业”指称工业化生产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产业是资本主义时代所蕴育出的文化形态。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起源于晚清,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同时。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文化产业从无到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繁荣中国现代文化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我们必须要厘清一个史实,有学者认为,晚清至1949年之前,中国并非是资本主义时期,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1](P2)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明显是有冲突的。但本文所言之“资本主义”是指的经济特征,而“半殖民半封建”则是政治特征,两者属于不同概念范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萌芽于晚明的苏州,真正出现于晚清的口岸、租界地区。化产业本身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一种文化方式与产业形态,故而中国文化产业亦最早出现在晚清的口岸、租界地区,这是历史、经济双重原因所决定的。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开始为海内外学界所共同重视,学界同行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受制于全球史观及其研究方式的影响,就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分期这一问题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而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历史分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方向。藉此,笔者愿不揣浅陋,就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分期问题的粗陋孔见,抛砖引玉,请学界诸方家不吝赐教。
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称之为“萌芽期”,即第一个时期,时间跨度为是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二个阶段则称之为“发育期”,即第二个时期与第三个时期,时间跨度为1900年义和团运动至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第三个阶段则称之为“成熟期”,即第四个时期、第五个时期与第六个时期,时间跨度为新文化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萌芽期”即第一个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预备期,我们知道,这一历史时期是十九世纪最后六十年,也是清王朝从闭关锁国走向内外交困的一个时期。其间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所谓的“同治中兴”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与八国联军战争。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当时中国处于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生死关头,也应该看到它也处于“被迫”的现代化进程当中。一方面,清王朝不得不应全球化的大势,通过一系列强加在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设立租界,一方面,清王朝亦要“师夷长技以自强”,通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现代化手段来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进而在与西方列强谈判时,可以多一点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民族工业、外来资本工业与官办工业也由是应运而生。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中国有了自己的早期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市场。
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出现。在晚清之前,中国也有一些可以称之为“文化产业”的文化现象,譬如唐代的歌舞教坊、宋代的勾栏瓦肆与明清的江南出版业等等。但是要衡量一种文化现象是否属于文化产业,首要标准就是要看是否属于“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的英语是“industry”,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工业”,即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首先“文化产业”必须是规模性的,其次它存在于都市文化、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消费、分配等流通诸环节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根本不能算是文化产业。
因此第一个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萌芽期。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则不得不谈中国现代文化,它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主体。十九世纪下半叶,时值诸口岸通商开埠、租界林立,一批以传教士、工程师、士兵、外交官、记者、探险家、商人与学者为主体的外国侨民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许多地方形成“华洋杂居”之状况。侨民来华,自然也将新的外国文化形态及其表现方式带入中国。
这当中既有他们生活必不可少的《圣经》及各类与基督教有关的文化生活,也有他们平日里所喜欢的歌剧、赛马,以及在欧美早已习以为常的报刊、杂志。他们既需要在文化上自我满足,也希望可以用他们的文化来影响周围的中国人,这是当时大多数殖民者的普遍想法——不管是欧西诸国在中国租界,还是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即今日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等地)、英国人在英属印度皆如此,而且当时中国人本身对于源自欧西的舶来文化也怀有一种“异邦想象”的喜爱。这一切使得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客体既有外国侨民,也有受西方教育、影响并“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2](P16)
在这重语境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应运而生。早在1815年,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香港中国办了最早的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33年,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Gutzlaff)在广州创办另一份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60年,上海出现一个由旅沪英美侨民创办的 A.D.C剧团(又称大英剧社、爱美剧社,Amateur Drama club of Shanghai);1874年,改良派先驱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宣传变法维新;1894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支持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创办《京津泰晤士报》(亦称《天津时报》);1897年,严复等人创办的《国闻报》在北京创刊。
从形态上看,在第一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主要以两种形态存在,一是报纸,二是戏剧。但有两点不得不提,上述只是“新文化”产业,而传统文化产业,也在新的生产关系下绽放出了新的光彩,那就是全国各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广州地区)日渐成熟的戏曲市场与书画市场。
书画、戏曲原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两大文化市场亦非新鲜物种,白居易的《琵琶行》便是讲的歌女上船卖艺,《清明上河图》里的勾栏瓦肆则将其市场化,而书画“润格”早在晋代就有,王羲之为一位道士抄了《道德经》,道士将自己养的一群鹅“举群相赠”,这便是书画交易之雏形。及至唐代,诗人王勃字、诗皆冠盖文坛,求字者甚多,王勃未及而立,便“金帛盈及”。而另一位书法家皇甫湜曾向求字的宰相裴度开出“一个字三匹绢”的“高润格”,这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书法交易最高纪录。宋明以降,戏曲、书画的早期市场都是存在的。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依旧不能算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仍是一种自由、不规范的封建市场。形成市场固然是产业的前提,但是这个市场必须是健全、规范并明确法权关系的,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所说,“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律,但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3](P20)唐宋以来的戏曲、书画市场明显不具备这个基本因素。因此,中国戏曲、书画现代市场则发轫于晚清,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这样的市场下,才可能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书画市场、戏曲市场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而逐渐现代化,其交易亦开始逐步走向规范,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之雏形。譬如同治六年(1867年)在广州成立的戏曲市场中介组织“吉庆公所”与上海出现的“京班戏园”、1878年在上海出现的书画中介交易机构“笺扇庄”等等,这与十八世纪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出现的艺术品中介机构、拍卖行与剧院经纪人(Theatre broker)有着功能上的相似之处,不难看出,这显然是“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一言以蔽之,第一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处于萌芽期,只有零星的一些文化产业现象出现,尚不够成气候。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是报纸、戏曲还是书画市场,它都已经展现出了现代文化产业的特征,这是和传统的文化市场很不一样的文化产业形态,这一时期理应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起始性的萌芽期。
二
第二个阶段则是“发育期”,即二十世纪前十七年(1901-1917)。这一时期之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意义非常。首先是电影、话剧等新兴艺术形态的出现,这是形式上的创新,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制的发育;其次是时代的变迁,在这短短十七年里面,帝制宣告终结,新文化运动兴起,封建专制法统与道统相继走向崩溃。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而言,无疑是促进其发育的重要土壤。在发育期中,第二个时期与第三个时期可谓先承后续,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意义上有着共通之处。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第二个时期是从义和团运动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清王朝的最后11年。此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意义非凡。在这一时期里,三个重要的现代文化形态依次在中国出现,一是1904年出现的唱片,二是1905年出现的电影,三是1907年出现的现代话剧(萌芽时称文明新戏)。这三个新生事物,构成了日后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当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有两个因素不能忽略,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就是西方现代科技,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形成至关重要,但时常被人忽视。前面我们讲到的报纸,它和之前中国的“活字印刷”就很不一样,因为它是现代机器印刷出来的,不是人手工雕版、排版的。现代机器的能源不是人力,而是电力,这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人力雕版印刷的印刷品,数量有限,难以成为“产业”,但电力就不同了,这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可以在短期内印刷大量的报纸、书籍,为传播新闻、昌明新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保障。报纸如是,唱片、电影与话剧则更不用说,这是西方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福利。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依赖于录音技术的唱片播放载体留声机一经发明便由西方侨民带入中国广州、上海等地,因为其功能奇特,当时颇受中国达官显贵们的青睐。但当时只是以销售留声机为主,未有唱片制作。及至1904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试制了《铁莲花》《捉放曹》等唱片,1908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是为中国唱片业之起始。毕竟唱片的生产、灌制以及留声机的生产、维护必须要依赖于现代技术,中国唱片。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发展,同时中国的唱片技术也有了从无到有的进步。
与唱片一样,电影在中国的出现也与传统戏曲关系紧密。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为京剧大师谭鑫培拍摄了京剧《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黑白无声电影。在此之后,中国电影业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而电影业的发展,又与摄影、录音技术密不可分。
和电影、唱片不同,中国最早的话剧是留日学生“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演出的《茶花女》与《黑奴吁天录》,但要说最早的现代戏剧,则应属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编演的新戏《官场丑史》。但后者演出之后,并未形成应有的反响,既未加演,也未推而广之。前者在演出之后,主创团队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却认为此应是中国戏剧一大创新。于是,回国之后,他们继续进行文明新戏的创作、演出活动,成为了中国话剧的奠基人。
话剧与传统戏曲不同,它因为是写实而非写意的艺术,因此更多受西方歌剧影响,需要借助舞台灯光、音响技术与升降设备等等。所以,话剧、电影与唱片都是与新技术息息相关的新兴文化技术。此外,印刷技术的繁盛也带动了画报业的兴旺,如北京的《启蒙画报》(1902)与《开通画报》(1906)、广州的《时事画报》(1905)、上海的《东方杂志》(1904)、《世界日报》(1908)和《图画日报》(1909)等等都在这一阶段相继创刊。新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前11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4]
必须值得说明的一点还在于,就在这一阶段,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被取消。读书人的“中举”之梦被迫断碎。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为求生存从江浙一带“转战沪上”,成为了“自轻自贱”的“补白文人”,靠卖文而求生。当中以周桂笙、李伯元、包天笑为代表的近代小说家由是崛起,成为了晚清通俗文学、大众文艺与都市文化的重要主体,是当时报刊、画报、话剧、电影等新兴文化产业最重要的生力军。
因此,我们势必要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来反思这一问题。这11年是清王朝最后的11年,一方面,戊戌变法已经宣告失败;另一方面,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考试,宣统年间宣布“预备立宪”。但在朝野上下,大家对于清王朝的改革态度以及是否能够成功并不抱太大期望。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同年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事败;1907年,女权运动先驱秋瑾被清廷杀害于绍兴;1910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与此同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1907-1909年两年间发动了8次起义,虽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却在国内掀起一阵狂飙突进的推翻帝制的革命浪潮。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藉此武昌城一声枪响,两千年的帝制在中国终结了。
国运如此,文运岂能僭越?中国古代早有“文以载道”之风。在经历了“西学东渐”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形态借助新技术、新观念横空出世,它显然就不可能是遗世而独立之物,在特殊年代,文化当然要有所作为。因此,话剧、电影与唱片的出现,显然与大革命之前这暴风骤雨将至的历史大时局密不可分。事实上也证明了,在此阶段出现的新兴文化形式,尽管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了革命家改造社会、唤醒民众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特征重在一个“新”字——新形态、新技术、新观念与新的时代需求——即对于革命的追求。
第三个时期则是从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爆发的1917年,虽然只是6年时间,但这短短6年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相当重要的6年。一是中国电影业的登场。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这标志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出现;二是出版业的兴盛。与辛亥革命爆发的同年,中华书局成立,国内出版界形成“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争雄”的局面,意味着中国的出版市场开始进入竞争时代;三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大量清廷遗老、寓公显贵的出现,使京沪两地书画、文物交易相当火爆,大大超过了以往。[5]
归根结底, 这是由于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封建时代,也瓦解了传统伦理所致。长期以来,受孔孟礼教影响的中国人奉行“重农抑商”的观念,而辛亥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观念进入中国,不但科举早已废除,且官方自上而下推行“实业救国”之政策,使得商业行为不再被全社会所轻视。传统的文人墨客唯有卖字鬻文以求生存。晚清遗老、书法家李桂清如是哀叹自己迫不得已做“职业书法家”的境遇:
(我)不得已,仍鬻书作业,然不能追时好以取世资,又不欲贱贾以趋利,世有真爱瑞清书者,将不爱其金,清如其值以偿。[6](P53)
在旧王朝已倒,新文化未立的6年间,中国现代文化处于黎明前的探索期,但现代文化产业却蓬勃发展,为日后现代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得益于文化产业的主体——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可能是落第书生,也可能是留洋学生,还可能是被西化的晚清遗老、洋行买办,也可能是新政府里的职员等等。他们既是现代文化产业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支持者与推动者。
在这6年间,租界未废,民国已立,借着“实业救国”的浪潮,中国的都市文化迅速崛起,这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正逢其时的温床。在1910年代的上海,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此同时,陆续建立了由华侨投资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与大新公司。而且就在1910年代,传统的茶楼、戏园开始让位于拥有镜框式舞台、新式灯光技术、编号座位与展演新剧目、新影片的现代戏院、电影院。“游乐场”这个新生事物也随之出现,并在1910年代在沪上大行其道——如经润三在1912年创办的“楼外楼”、1915年创办的“新世界”与1917年落成的“大世界”等等,皆为当时新兴文化产业形式之代表。[7](P78)此外,工艺美术大师郑曼陀在1914年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首创“擦笔水彩画法”为商家绘制月份牌;另一位美术家周柏生在1917年开始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计广告牌、月份牌,此为中国现代广告业之滥觞。[8]
上述种种皆深刻地反映了新文化未兴,现代文化产业先行,这一切皆拜都市文明所赐。6年时间虽短,但现代文化产业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历史地看,这6年的时间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定下了一个基调:以都市文化为基础。这与欧洲、美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是一致的,只有市民社会的勃兴,才能为文化产业带来广阔的市场,无论中西,皆不例外。
三
第三个阶段则为“成熟期”。所谓“成熟期”,就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制逐渐完备的时期(1918-1949)。在此期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多门类体系发育齐全,并且开始有了文化产业类的法律法规,部分门类的市场化程度亦较为深厚,并且参与到了二十世纪文化全球化的大势当中。纵观“成熟期”的三十二年,是现代中国战乱频仍的乱世,但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此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先后经历了第四、第五、第六这三个时期。可以这样说,虽然历经战火淬炼,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却一直在艰辛中努力开拓,在挫折中扬帆起航,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均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经济史、城市史乃至社会史的重要内涵。
第四个时期则是从新文化运动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在这20年里,中国的现代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形成蔚为壮观的“摩登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初步形成了自身的格局:以图书、报刊出版业为主体,以民营电台、电影业为两翼,唱片娱乐业、戏剧戏曲业、工艺美术业与艺术品市场齐头并进的壮观局面。
现在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乃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黄金时期”,因为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文学作家、电影导演乃至建筑师的经典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但实际上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乱世。在短短20年时间里,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两广战争、两次蒋桂战争、第一次国共内战、“一二·八”事变、济南惨案与“九·一八”事变,战火从东三省烧到两广,从上海蔓延到川藏,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当中还不算家常便饭的匪患、天灾、瘟疫等等。如果说这段时间里还有不错的文化成果诞生,这只能说明中国的文艺家、文化人确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逆境中不但求生存,而且还得到了发展,这自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最好写照。
因此,我们要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既要对当时的文化史有所了解,也要把握大的历史背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局面的确“壮观”,乃是因为文化产业各体系均有较大发展,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譬如1935年成为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杂志年”,杂志发行量与品种堪称翘楚;1922年,张石川的明星电影公司成立,1925年,邵醉翁(邵氏兄弟之兄长)的天一影片公司成立,1928年,大光明电影院开业,1932年,卢石的联合电影公司成立,1934年,张善琨的联华电影公司成立——几乎与此同时,好莱坞八大公司在上海、北京分别设有分号,并大规模占领中国市场;在出版界,1920-30年代形成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四足鼎立”之势,而以《玲珑》《万象》为代表的沪上文化、时尚类杂志则争奇斗艳,现代文化产业一派繁荣之景象。
如此乱世,这般文章,初看确实匪夷所思,但细想却非毫无理由。一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此20年内,除了日寇入侵的战争之外,其余战争军阀、党派夺取地盘的内战为主,多半集中在乡村而非城市,因此乡村虽生灵涂炭,但城市仍歌舞升平,文化产业的发展未受到太多影响;二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内战特别是军阀混战不但催生出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群体,而且可以提高重工业、纺织工业、面粉与制药行业的效益,使得产业工人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提升,这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所决定的。美国总统杰弗逊(Jeffson)曾有“一场战争制造一批富人”的论断,中国也有“发国难财”一说。史实证明,在这20年里,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920年,国内民族工业资本产值不过2.51亿元,到了1936年,竟然达到了16.32亿元,每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41%,这个增长率是相当惊人的。
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实际上为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重要的主体与客体。笔者曾就印刷工人与左翼文艺运动的互动关系为例,解析了产业工人之于现代文艺的重要意义。①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详见拙文《论现代印刷业与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载于《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实际上,产业工人的构成是复杂的,除了体力的底层工人之外,也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与工厂管理者等“准中产阶层”。他们在上海、南京、北京、汉口、重庆与广州等口岸城市广泛存在,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与市民观念,这是现代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基础。
但是,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则彻底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拉至谷底。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五个时期——抗战八年(1937-1945)期间,中国一大半国土沦至敌手。军阀混战意在问鼎中原,因此多是抢夺乡村地盘,但日寇入侵却是为其本国工业殖民化需要,因而专挑城市下手。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广州、福州等大都市在铁蹄下纷纷沦陷,即使剩下的重庆、桂林、成都与昆明等被称之为“大后方”的城市,曾经以消费文化为主的文化产业也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事业”。纵然在上海“孤岛”时期有一些古装戏、传统戏曲的演出,也是借古讽今、宣扬抗战之作。而汪伪文人们所鼓吹的“和平主义文艺”则几乎毫无市场,受到了沦陷区群众的大力抵制。几年前兴旺的杂志出版业,在抗战时期却无比惨淡:
最近我们常听人谈起,上海的出版界几乎可说是停顿。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近年学术研究空气完全等于零的时期。[9]
但在这一时期,仍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产业的人物不得不提,一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都市作家,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出版业难得出现的亮点;二是以费穆为代表的电影人,他们在抗战时期为中国电影业所做出的历史性尝试,对于中国电影业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重心当然是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上海文化人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上海最大的特点在于“华洋分治”,它的租界区曾在战时长期未被日军占领,直至1941年12月上海彻底沦陷,1943年汪伪南京政府宣布“接管”租界地区。因此,上海的租界地区在1937-1941年间曾涌入大量资本家、外商与各种难民,当中不乏有产者。藉此,上海租界地区在抗战时曾一度呈现出了“畸形的繁荣”,百货商场、酒店、舞厅、跑马场生意好过战前,“今朝有酒今朝醉”“时尚摩登”的娱乐消费主义成为了当时沪上文化产业的主旋律,“张爱玲现象”“费穆现象”便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出现的。
但从大局上看,抗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总体上仍是凋敝、萧条的状态。上海局部的泡沫式繁荣并不具备普遍性。而且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其核心是中国现代文化,其核心是晚清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与“五四”启蒙思想。但抗战时上海的“摩登文化”,虽然形成了“看上去很美”的高产值,但除了少数呼吁抗战的古装戏、古装电影之外,真正有意义、可留诸后世的作品并不多。
因此,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可以用“一家泡沫,百家凋零”来形容。上海租界地区文化产业的泡沫化,至今仍是学界、文学创作界热衷关注的一个话题。但作为对中国近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既应关注上海地区抗战时这种不正常、泡沫式的“兴”,更应放眼全国,去研究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因战争而导致的文化产业之“衰”,只有这样,才能对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有一个准确、客观的把握与了解。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第六个时期,就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化可谓是枯木逢春,从日寇严酷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中走出,开始寻求“五四”精神中人道主义的价值,而文化产业亦是如此。电影业告别了光怪陆离、搔首弄姿的“都市摩登”,一批现实主义、反映人性之温暖的“文人电影”开始出现,如黄佐临的《假风虚凰》(1947)和《夜店》(1948)、桑弧的《太太万岁》(1947)和《哀乐中年》(1948)以及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等等,皆为当时代表之作。与此同时,中国的出版业亦走向了复苏,上海地区在该期间创办文学刊物198种,年均54种,与“孤岛”时期(年均60种)、“杂志年”前后(1928-1936,年均59种)差异并不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地缘格局处于“分裂”状态,一是国统区的文化产业,一是解放区的文化产业。前者不言自明,而后者是否属于“文化产业”,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注重文化宣传,并认为其是政治、革命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解放区的文化活动虽然繁盛,但一无民营资本进入,二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严格地说不能算作是文化产业,而被大陆主流史家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宣传事业”。但事实上,解放区出版、电影、戏剧活动并不逊色于国统区,其杂志、书籍的出版当然也有盈利。延安、东北与华北等解放区书店、出版社何止百千,而且还成立了“新华书店”托拉斯发行机构。其出版业是显而易见的高额利润,只是解放区的整个文化产业的投资方、获利方都是中国共产党而已。这种近似于“官办文化产业”的文化行为,应属于广义上的文化产业,因此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应探讨、研究的对象,而且应与国统区的文化产业进行对比研究。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前后一共三个阶段,六个时期,历时109年,横跨晚清、民国时期。这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中的各自不同的历史事件、社会思潮共同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跌宕起伏与波澜壮阔。平心而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中国现代文化史一样,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意义非凡,对于后世影响尤其影响深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承接中西之学、昌明科学民主的历史意义,因而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2] 熊月之.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复旦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历史教研组.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
[4] 韩晗.摩登图像:论传媒技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J].现代传播,2014,(8).
[5] 韩晗.想象的空间:都市文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基于科学思潮的视角[J].东方论坛,2014,(6).
[6] 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7] 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8] 韩晗.日常生活、都市文明与现代科学的传播——以1900年代的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为中心[J].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J].2015,(6).
[9] 漱六.七年来的上海杂志事业(上)[J].文友, 1944,3(2).
责任编辑:冯济平
Analysis of the Period Divis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SUNNY H. HAN
(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ies into three periods ( including 6 stages ) in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fi rst period, also the fi rst stage, is the late 60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named the embryo period. The second period, which includes the second stage and the third stage, is the fi rst 17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named the puberty perio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ategories of the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were perfected gradually. The fourth stage to the sixth stage is from 1917 to 1949, also is the third period named the mature period, when the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ed fully.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ndustry; late Qing Dynasty; period division
G129
A
1005-7110(2016)06-0064-07
2016-09-16
韩晗(1985-),男,北京人,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研究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抗日文艺期刊研究(1931-1938)”(15FZW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