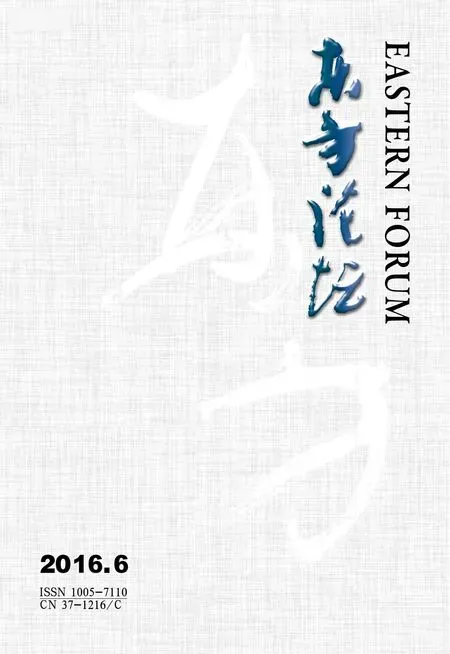与谢野晶子的《君莫死》是反战诗吗?
于 华 王光红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与谢野晶子的《君莫死》是反战诗吗?
于 华 王光红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与谢野晶子的长诗《君莫死》长久以来被当作“反战诗”受到世人关注。但从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诗歌之道”“尊皇之道”以及政治立场分析,她的《君莫死》只是一首真情流露的“心声”诗作,甚至算不上厌战诗。对与谢野晶子的这首诗,应该放到她的整个创作当中加以判断和定位。
与谢野晶子; 《君莫死》;反战诗;天皇制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是著名的和歌诗人、作家、评论家,这是今天对与谢野晶子文学地位和身份的一般认定。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它的评价和定位,比如“教育家、和平主义者、社会改革家”①详见360百科(http://baike.so.com/doc/3013392-3177664.html)等等。对于“作家”“教育家”“评论家”等认定大概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对于“和平主义者”“社会改革家”的说法似乎尚有探讨的余地。问题就是,与谢野晶子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吗?
与谢野晶子出生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她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是在民权运动被镇压后重新得到复活并继续受到强化的儒教式教育。1879年(明治十二年),即晶子出生的第二年,文部省颁布《教育令》(也称“第一次教育令”),规定男女分别授课,在修身课上专门要求和教育女生要温顺、要保持贞操,进行彻底的“良妻贤母”②中文的惯用说法是“贤妻良母”,而日语的“良妻贤母”更在强调作为母亲的聪明才智和作为母亲肩负教育下一代的职责。主义教育。至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以《高等女学校令施行规则》为标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制度整顿完备。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全程接受了“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的晶子,同在1901年,即此年的8月刊发了她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时年24岁。《乱发》热情歌颂与儒家礼教相违逆的自由恋爱、女性的肌肤之美,大胆讴歌人性的自由解放。当时在儒教道德观依然根深蒂固的社会中,《乱发》非但没有使大逆不道甚至激情疯狂的女诗人身败名裂、遭世人唾弃,反而给她带来了无上的赞誉,一举摘得短歌歌坛女王的桂冠。这种意外的结果只能理解为,是其卓越的诗歌才能为她带来了无比的幸运。
然而,晶子的离经叛道之举并非只体现在《乱发》中的一首首叛逆的青春赞歌之中,就在《乱发》刊发的两个月前,即1901年6月,晶子离家出走,投奔到身为其师的与谢野铁干(与谢野宽,1873-1935)的怀抱,且铁干实为有家室、有妻女之人。在铁干抛妻舍女离婚一个月后,两人仅在少数朋友的祝福和帮助下结为连理,而晶子的兄长却与之断绝了亲缘关系,甚至在父亲去世之际也不允许她跨进家门。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决定女性婚姻和终身幸福的时代,晶子毅然冲破重重障碍,公开地自由恋爱,决定自己的婚姻对象。在这个“私奔”问题上,她的大胆妄为令人瞠目,但同样极其幸运地躲过了世道的惩处,享用着她歌坛女王的盛誉。可以说,晶子完全是得救于她的聪明才智。
1904年9月正值日俄战争最激烈之时,与谢野晶子在新诗社①于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结社,与谢野宽为社主,提倡浪漫主义与诗歌、和歌的革新。第二年其机关杂志《明星》创刊并发行,打造了一批和歌诗坛的新人,如与谢野晶子、山川登美子等。的机关杂志《明星》上刊发了她的长诗《君莫死》②这首诗的日文标题为「君死にたまふこと勿れ」,国内有诸多译名,如“你不要死去”“你千万不要死去”“弟弟你不能死”“你可千万不能死去”等等,“君莫死”为笔者所译,本文皆使用此译名。,并加有副标题:“为身陷旅顺口战事的弟弟悲泣”。此诗一发表随即遭到国家主义者御用文人大町桂月(1869-1925)的猛烈攻击,斥之为“乱臣”“贼子”,公然非议以天皇之名发布的《教育勅语》③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以天皇之名颁布,是推进天皇制教育的主要根基,确定国民道德的根源和国民教育的基本理念,在国家庆典之日国民有义务进行朗诵。1948年,国会通过决议撤销并确认其失效。和《对俄宣战诏勅》④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2月10日发诏,日俄战争爆发。,对天皇大有不敬。大町桂月对晶子在《君莫死》中“反天皇”“反战争”的言论大加鞭挞。
那么,与谢野晶子果真是“反天皇”“反战争”的吗?《君莫死》是一首反战诗吗?作为诗作者的晶子是一名真正的“反战的和平女神”吗?
一、关于《君莫死》
《君莫死》刊出之际也是日俄战争激战之时。在日俄战争爆发前,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即“主战派”与“非战、反战派”。后者主要为持社会主义立场和人道主义立场的少数人,在文坛有创办《平民新闻》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诗歌领域有木下尚江(1869-1937)、小塚空谷(1877-1959)、樋口配天(1869-1969)、小杉未醒(1881-1964)、内海泡沫(1884-1968)、石上露子(1882-1959)等人都创作了优秀的非战、反战诗歌。但“主战派”誓要讨伐俄国的喧嚣声笼罩了全国,人们反战、厌战的情绪成为不可表露的“私情”。
与谢野晶子的《君莫死》发表之时,奔赴战场的战死者、受伤者已经开始不断增加,然而新闻媒体却在不断鼓吹国威、鼓舞士气。反战活动只能成为潜流在暗中悄悄涌动。
《君莫死》在二战结束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和赞美,并作为反战诗的代表广为宣传,晶子也被罩上了一层“反战的和平女神”的光环。文学评论家小田切秀雄(1916-2000)曾在《文学史》(东洋经济新报社,1964年)中评论说,“与谢野晶子在日俄战争中将《乱发》的激情展现为一首反战诗《君莫死》”。日本近代文学研究家山田博光(1928-)在红叶敏郎、三好行雄、竹盛天雄、平冈敏夫编写的《明治的文学》(有斐阁,1972年)中,也是将《君莫死》定位为“反战诗”[1](P91)。这一评价,在一段时期内似乎成为定论。然而,政治学家、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中川八洋(1945-)在其著作《向与谢野晶子学习》(图表社,2005年)中明确表示,“晶子是与‘反战’毫无关涉的和歌诗人。……将其宣传为‘反战’文学家是某政党在战后所编造的弥天大谎,如此行径极其恶劣。”[2](P32)并且论述道,“日俄战争从1904年2月至1905年8月持续了一年有半,如果说晶子是反战诗人,那么其间应该作有其它反战诗,但事实上并没有。例如,她与铁干共著的《毒草》出版于1904年5月,与山川登美子共著的《恋衣》出版于1905年1月,其中可理解为反战用意的和歌一首也没有,《明星》诗刊上也无一首。将晶子拥立为反战诗人的作为可谓荒唐无稽。”[2](P36-37)中川八洋坚定地认为《君莫死》并非反战诗。
在国内对《君莫死》的评价大概有三种情况,即“反战诗”“厌战诗”和“具有反战倾向”这三种观点。张晓宁在1995年《与谢野晶子及其反战诗》一文中评论说,“这首诗不但是一支骨肉手足至亲至爱的抒情乐曲, 更是一首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时代之歌。”[3](P17)这篇文章的标题本身也表明了作者对这首诗的认识。十年后,张晓宁在《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一文中重复了同样的观点:“诗歌中洋溢着‘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思想;洋溢着一种超越个人命运的广义上的人类爱……”[4](P15)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中,不但有这首诗(标题译为《你可千万不能死去》)的全文翻译,而且在诗后附有对作者以及这首诗的背景介绍,其中表明:“本诗发表于一九〇四年《明星》九月号,是一首鲜明的反战诗歌。一发表即受到超国家主义者的猛烈攻击。”[5](P251)王玲于2005年发文《与谢野晶子和她的反战诗〈你不要死去〉》,也表明了“反战诗”的观点:“与谢野晶子的《你不要死去》是反战文学的代表作,它表达了尊重和平的愿望,启示人们反思历史……”[6](P176)。主张“厌战诗”的有张蕾写于2009年的《用爱和热情去点亮一生——「与谢野晶子」》,其中评论道:“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战争的狂热,但这首诗却流露出强烈的厌战情绪和对天皇的谴责。”[7](P15)另有申素芳于2011年发表《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诗歌情感解析》一文,同样表达了“厌战诗”的观点:“这首诗流露出对战场上的弟弟的思念之情。作品的表现手法真切动人,讴歌了人性,表现了诗人憎恶战争,爱好和平的强烈愿望。”[8](P149)认为这首诗“具有反战倾向”的是李芒在1983年对与谢野晶子这首诗进行译注时所作的评论中持有的观点:“当时正处于日俄战争中间, 其反战倾向比较明显, 因而作者曾被污骂为‘乱臣贼子’……”[9](P48)
显然,以上三种观点都与中川八洋的观点相偏离,国内对这首诗的相关评论中,“非反战诗”的观点目前还未见一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渡边澄子(1930-)在《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一书中表示,有必要摈弃先入之见,重新审视似乎已成定论的“反战诗”的观点[1](P92)。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看待这首诗呢?怎样评价才能给予它较为客观的定位呢?要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看清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在其整体的战争观之下,再来判断这首诗是否为“反战诗”,问题就会比较容易解决了。
二、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
在与谢野晶子的一生中,发生过的重要战争或重大事件有甲午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一·二八”事变(1932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八·一三”事变(1937年)、太平洋战争(1941-1945),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或战事,必定会进入到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的视野,也必定会对她的战争观形成影响,《君莫死》就是在日俄战争的背景下吟诵出来的“心声”。
“九·一八”事变后,晶子并没有撰文揭露日本关东军的侵略野心,却反过来替造事者说话,她在1931年9月27日的《横滨贸易新报》上发表《东四省的问题》一文,认为“事变”是中国军阀政府因排日言行积累而“自己招来的灾祸”,“决不是突发事件,而是日本忍辱负重的结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
“一·二八”事变后以及日本在导演建立“满洲国”的欺世荒诞剧时,与谢野晶子又在《日支国民的亲和》(1932年10月)一文中发表与战争相关的言论,她说:“军人要拿起武器争取胜利,胜利并非最终的目的,而是通过胜利,在天皇陛下面前献出作为军人的忠诚和武力,同时贡献于我们的国民和世界人民的福利。日本军人的强大在当今属世界第一。……全体国民也一样……必须以军人般的勇敢去奋斗。尤其是国民中精锐的青年男女,我期望他们像爆破三勇士那样大胆地实现他们各自内心里潜在的传自于父祖之辈的旺盛的生活意志力。”[10](P280)在日本侵略者无端挑起“九·一八”事变和阴谋扶植“满洲国”的历史进程中,与谢野晶子的这番发言显然是竭力为侵略者摇旗呐喊,这种向全体国民、尤其是要求青年男女拿起武器投奔战场,向天皇献忠的呼吁,实在难以与“反战的和平女神”的称号相关联。
张晓宁在《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一文中将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早年持有“反战观”,经过中年时期的“忠君爱国”思想,滑向晚年的支持和赞美战争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并且文中,对其晚年的“转变”使用了“变节”“蜕变”“晚节不保”[4](P14)等字眼进行表述。当然,“变节”也好,“蜕变”也罢,抑或是“晚节不保”,都是建立在认定《君莫死》为“反战诗”的前提下来使用的。那么,早年的与谢野晶子与晚年的与谢野晶子之间,确实存在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吗?她的“忠君爱国”思想是在中年时期才持有的吗?如果晶子的“忠君爱国”的思想观念贯穿终身,始终是一致的,那么将《君莫死》认定为“反战诗”就是值得怀疑的问题了。
首先,我们看看她的“忠君爱国”思想从何而来,何时成为坚定信念的?
在《君莫死》旋即遭到大町桂月的攻击、诋毁的情况下,与谢野晶子于当年11月在《明星》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回应。她说:“在堺市商家的掌柜们敬仰天子如先考,无人不对皇家之事而忘我,更何况我这样一个少女,自打九岁始就一心捧读《荣华物语》①编年体历史故事,共40卷。记述了平安中期贵族藤原道长(966-1027)一生的荣华,正篇30卷,从宇多、醍醐天皇时期叙述至道长离世后的第二年。续篇从堀河天皇时期记述至1092年(宽治六年)2月,前后经历十五代天皇计200年。《源氏物语》,长大后更加倾心于王朝圣代。如今的读物只撰写下层小官,我认为这很浅薄,至于《平民新闻》②由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组建的“平民社”创刊于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的周报,在日俄战争之际,主张反战,1905年废刊。1907年复刊为日报,发行有三个月,在政府的压制下废刊。上一些人等的言论,我听上一句都感到浑身颤栗。……”[11](P17-18)文中作为商家出身的晶子毫不掩饰她内心从少女时期通过古典文学所形成的对贵族精神的向往和对天皇及皇室的崇敬之情。而对《平民新闻》上的言论,表明她对社会主义思想所感到的恐惧以及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
1890年以天皇之名颁布的《教育敕语》首先确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巩固了束缚妇女的“家制度”,对此晶子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坚信,纲常伦理之大本在于皇祖皇宗的遗训中,集其圣训的框架与核心,句句朱玉的皇家圣典,现今陛下的教育敕语的伟大、庄严、及光辉照耀之处,正如圣言“施之于内外而不悖”,正因如此它才不仅为日本人所依凭、当遵守之伦理,且更在于它是世上全体文明之人跨越永恒、必将到达的理想之事。君主若守之,则为王道,施之于民则为民道;用于个人则为人道,行之于社会则为公道。我坚信在教育敕语之上无需附加任何东西,教育和宗教都是教育敕语之下的存在。即作为教育敕语的详解、注脚和奖励,这些才是必要的。……
近来政府在整顿和彻底清除社会上那些破坏纲常伦理的言行,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往这一类的查处都过于手软。……现已出现的思想破坏,进行十二分的禁压为好,禁售等处置也是不得已之事。[12](P277-278)
这段文字收录于1911年的评论集《心中一隅》(『一隅より』),晶子时年33岁。在此晶子对天皇及皇室的尊崇已成为坚定的信念,对《教育敕语》的心醉程度也表露无遗,甚至认其为文明人类之理想,值得夸耀于全世界,是无可替代的“纲常伦理之大本”。其“句句朱玉”之表述的内里是她坚定不移的“忠君爱国”思想。并且主张对“破坏纲常伦理的言行”和“思想”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压和取缔。
接着,她无不带着自恋情结地表示自己的贵族式的思想感情是与尊崇皇室的感情不可分割的。
本人喜嗜记录贵族的历史和文学,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也是贵族式的,从而伦理也好兴趣也罢,其中心都是与之相连接的。本人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去除掉尊崇皇室的感情,这也是自然传承了祖祖辈辈居于畿内的父祖们的感情之故。本人并不喜好武家思想和平民文学这类东西,也是出于此故。而且本人在举例说明文明妇女之典范时,并不以松下禅尼、明智光秀之妻等人为例,而总是引持统、光明那般贤明高雅之女帝圣上为榜样,这也是为了从皇室中选出圆满实践纲常伦理之大本的模范。[12](P278)
可见,其“尊崇皇室的感情”不仅是祖辈的“传承”,而且早已浸入其骨髓不可剔除。就在收录此文的评论集出版(1911年7月)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5月晶子赴欧访游,在法期间传来了明治天皇的讣告,其时画家梅原龙三郎(1888-1986)曽邀其观剧,被晶子回绝了。她说:“如在国内当停止一切歌舞娱乐,即便我们身在国外也要服丧致哀。”[1](P108)晶子对天皇的尊崇和热爱可谓是一片赤诚,无论身在何处毫不动摇、矢志不渝。
1928年5月,晶子夫妇受邀于南满铁,开始在满洲、内蒙古为期近40天的访游,晶子时年50岁。期间与谢野夫妇两次参观了旅顺战场遗迹,参拜了白玉山的纳骨堂,遍访203高地、东鸡冠山炮台、旅顺港口封港军舰遗迹。两年后(1930年)出版的夫妇合著的《满蒙游记》中,晶子写道:
在此阵亡的四万个年轻的日本人,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念头将生命交与炮火之下的呢?其后日本人在满蒙打造的那些设施,是否让那些悲惨的牺牲者的志愿得到了实现呢?死者最后的慰藉就是让自己的兄弟们离开本国狭小的土地而在这一片新的领土上开拓出自由快乐的劳动生活吧。他们是否抱有这一希望呢?
在我想来,从一个国民的立场来看,也从筹划支那人的幸福这一邻居的立场来看,我希望采取将日本农民中没有失去劳动精神的踏实稳健的青年男女移居满蒙的办法,正如山东的支那农民、朝鲜的农民那样一百万、二百万地涌入满蒙。[1](P105)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再经过“卢沟桥事变”到伪满洲国的建立,与谢野晶子都在积极响应时局,对日本侵略亚洲近邻的行径表示肯定与支持,她的爱国激情也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呈上升状态,激进式的喷发,使得她看不清战争的性质,而一味地勇往直前地讴歌日本军国主义。
1932年(昭和七年)元旦之际,54岁的晶子在报刊上发表《作为日本国民的幸福》一文,表达对皇室的感恩之情:“我时常怀有一些感激之事,其中第一件不胜感激的事就是生于日本而生活于皇室统治下的幸福。……”“我在此于昭和七年元旦之际,谨祝皇室万万岁,同时作为一国民对生活于圣代恩宠之下的幸福表示感谢。我认为,只要皇室之繁荣与天壤共恒久,无论遭遇怎样的、比今日更大的物质上的国难,国民都将围绕着皇室更加拧紧纽带之结,在正确的统治下,不粗野、不过激,继续乐观地发展下去。无论遇到何事,只要想到皇室就会肃然起敬,恢复正常;无论怎样的公私争斗都会消散而去,这是三千年的历史培养起来的特殊的国民精神。”[13](P269)
1940年,与谢野晶子已是生涯的晚期,时年62岁,她以虔诚之心在诗歌中表达了对当今圣上(昭和天皇)及初代皇祖神武天皇的感谢之情:
思日本今日之繁荣,必源自圣祖之神武
昔日先祖身匍匐,膜拜亘古大和祖。
今日吾愿如此伏,身向圣君足下伏。
(《白樱集》)
其实,这样的诗句在晶子的诗集中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在此就不一一引述了。纵观与谢野晶子一生中与战争和天皇相关的言论,其中并不存在明显的“断层”和“转变”,可以说,晶子晚年的所谓“变节”“蜕变”根本就无从论起,判断她是反天皇的这一点也毫无依据。她非但毫无反天皇之意,其“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和热度是随着年岁的增加不断加深和提升的,正如渡边澄子和中川八洋在文中反复论述的那样:“皇室崇拜随其终生不变”[1](P100);“赞美和尊崇天皇之念贯穿其生涯,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1](P108);“晶子的尊皇思想持之终身。”[2](P48)如此一个“忠君爱国”的与谢野晶子何以只在《君莫死》这一首诗中发出“反天皇”的言论呢?显然大町桂月的攻击是无稽之谈。
通过以上的引述,我们还可以看到,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与她的天皇观又是连为一体的。那么,一个狂热的尊皇者,“忠君爱国”是晶子贯穿终身的坚定信念,她在《君莫死》中,就会是反战的吗?
三、再论《君莫死》
《君莫死》何以会遭到大町桂月的攻击呢?诗中哪些语句成为攻击的把柄呢?这首诗的全文由五节构成,第一节从弟弟的身上说起,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最受父母宠爱,但父母养育了24年的孩子,不是让其去厮杀战场的;第二节从家业的角度来说,弟弟不仅要继承拥有老字号的家名,还要继承具有传承的家业,战争的胜负不是商家要承担的义务,而作为商家的继承人,弟弟必须活着回来;第三节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天皇是无比慈悲的,绝不会无端地驱使国民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把陈尸战场说成“至高荣誉”是臣下们的鼓吹和煽动;第四节着眼于老母亲的立场,丧夫不久又送子上战场,偌大的家业仅靠她一人打理,因此,不使老母更添白发,弟弟也要全身而回;第五节述说了新婚燕尔的妻子与夫君离别的痛苦,如果体贴到妻子的哀伤,也不能牺牲在战场。这首长诗在每一节中都重复着一句“君莫死”的祈求和祈愿。本文限于篇幅,在此只将引起异议的第三节译文列出:
……
你可千万不能死去!
天皇又不会参加旅顺战役。
有道是圣上慈悲无比,
怎么会颁下这样的旨意:
让自己的臣民大开杀机,
再像禽兽一样变作肉泥;
还把这种离奇事体,
说成是什么至高荣誉。①本文中除了此诗的译文外,其它引用的译文皆由笔者翻译。
……[5](P250)
可以说,大町桂月的攻击是断章取义的,仅仅因为一句“天皇又不会参加旅顺战役”就断定晶子在“反天皇”“反战争”,是“乱臣”、是“贼子”,似乎太急于下结论了。我们只要再往下读几行,就可以读出原诗的旨意并非在指责天皇不亲自领军参战,而是指责那些主导了战争的臣下,他们驱使民众如禽兽般持枪荷弹战死疆场。诗中说“圣上慈悲无比”,且老母“躬逢盛世可享安逸”(第四节),如此看来,晶子非但毫无反天皇之意,实则是乱世之中的颂词了。大町桂月作为当时的诗人、评论家未必看不懂晶子的诗句,但同时作为御用文人的大町桂月,当前方将士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时,他在阵地后方大概也要有所作为吧。为了“业绩”和“求功”的需要,对晶子的诗句进行故意的曲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君莫死》在遭到大町桂月的大肆攻击后,当局采取了与大町桂月相同的立场,对刊载此诗的《明星》作出禁止发行的处分。大町桂月的炮轰之举的确达成了一种“作为”。对于大町桂月的“故意曲解”,渡边澄子认为,“晶子作为女性在《乱发》出版后,成为《明星》的女王,进而又成为短歌歌坛的女王,全身笼罩着光环,在诗歌界获得稳固地位,这使桂月感到不快。‘一个女人神气什么?别那么得意忘形吧’这种无法公开说出口的不快,盘踞在其心头。”[1](P96)在渡边澄子看来,桂月的“不快”中显然包含着对女性取得成功的妒意和不屑。
针对大町桂月的曲意攻击,与谢野晶子及其丈夫铁干并没有采取漠视的态度,而是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诗歌之道”,表明自己的“非政治立场”。
首先,与谢野晶子在《明星》当年的第11期上发表《公开信》一文,阐明自己的作诗意图:
弟弟应召勇往战地,万一之时不顾身后之事,勇往直前。……无疑我那可爱的弟弟也是一名勇士。尽管如此,已故的父亲也不会教导家中最小的儿子成为无情的、如禽兽般的人,叫他去杀人,情愿奔赴丧命之地。……
诗歌就是诗歌,不咏唱心声的诗歌有何价值?即使你没有弟弟,你且去新桥、涩谷的车站看看,当火车启动之时、军队出发之日,只需站在那里一小时,你的眼里必定能看见送行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握着行将离去的孩子的手;你的耳中必定能听见他们一声声的嘱咐:“你要平安无事地回来啊!一定小心啊!”然后大声地喊着:“万岁!”……
说到拙诗《君莫死》,这也是发自真情的心声。他们那也是发自真情的心声,用真心真意发出真情之声,除此之外,我无法理解诗歌之道。[11](P18-19)
“诗歌之道”在于“咏唱心声”,而不是表达政治立场,《君莫死》也无非是咏唱自己担心弟弟战死沙场的“真情之声”,与“反天皇”“反战”毫无关联。若说英勇杀敌,弟弟也堪称一名“勇士”了。然而,弟弟作为商家的继承人,父母所传授的并非杀人之道,而是希望他顺利地继承家业,不能使家业后继无人。在此能够窥见到晶子的“家”观念,中川八洋认为,“生于明治十一年的晶子,她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其父母还依然是江户时期生活过来的人所传授的。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乡间,依然浓厚地残留着‘奔赴战场行军打仗只是武士阶级及其子弟的任务’这一观念”[2](P39)。因而战事与商家子弟无涉,无须商家子弟参与。“晶子在此摆出的是‘士农工商’的阶级身份规范”[2](P39),中川得出结论说,“这首诗所诉诸的无非是担心家里的老店失去了唯一的继承人——她的弟弟而为其祈祷,希望他能从战场上平安归来。这就是《君莫死》的全部了。”[2](P36)它与反战、反天皇全然无涉。
其后,铁干也认为这首诗在战争期间被读解为“反战诗”、攻击为“批判天皇的诗”,受到“乱臣”“贼子”和“罪人”的攻击,不能对此置之不理、视若罔闻。于是他与《明星》的同仁平出修(1878-1914)一起代表新诗社,会同社外投稿人翻译家生田星郊(生田长江,1882-1936)一路前往大町桂月所在的居蜀红园,进行对决论争,并撰文《何谓“诗歌的骨髓”》发表于《明星》(1905年第2期)。针对桂月的故意曲解,铁干评论道:“在诗歌的评论中,引用宣战敕令的词句,说什么有非常情况之时等等,实在可笑。”[1](P102)
晶子与铁干都是立于“诗歌之道”与桂月进行辩论,与战事、与政治立场毫无关联,桂月的“胡拉乱扯”在他们的眼里是荒唐可笑的,是“非诗歌之道”。
铁干的“诗歌之道”一直主张的是无涉于政治。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秋,铁干曾对创作了反战诗的内海泡沫进行训诫,他说:“诗歌不能直接取材于与政治社会时事相关的问题,不能对其表现出关心。土井晚翠、儿玉花外等人都走了偏道。决不能向他们学习。”[1](P102)并且对泡沫发表在《新声》上的反战诗予以否定和强烈的指责。由此铁干的诗歌观可见一斑。
晶子作为铁干的弟子,其诗歌观与铁干是一致不二的,《乱发》中许多字眼的使用就受到了铁干的诗集《紫》的影响。不仅如此,对于政治事件,晶子同样也是抱着避而远之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前文中晶子的自述提及那些持有反战主张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平民新闻》上的言论,“我听上一句都感到浑身颤栗。”[11](P18)
“大逆事件”①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以一些社会主义者计划暗杀天皇为由,政府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全面镇压,逮捕了很多社会主义者,其中26人以“大逆罪”被起诉,24人被判死刑,于1911年1月,包括幸德秋水、宫下太吉等12人被处死,也称“幸德事件”。《平民新闻》就是由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社会主义者组建的“平民社”发行的机关报,日俄战争之时,主张反战。是一起很不光彩的政治事件,一些社会主义者被诬陷谋划暗杀天皇,借此社会主义者遭到镇压,几乎被一网打尽,这在日本政治史以及法制史上留下一大污点。在“事件”中获得冤罪而被处刑的还有铁干的好友,也是《明星》的同仁大石诚之助(1867-1911)以及唯一一名女性菅野须贺(1881-1911)。1911年2月22日,即大约在被判“大逆罪”的犯人被处死的一个月之后,晶子产下一对双胞胎,其中一女为死胎。产后的伤痛有所减缓后,晶子在《产褥之记》中,叙述了一个令她心生“不快幻觉”的梦境:“产后的疼痛渐渐平息了,闭上眼睛正在迷迷糊糊中,种种令人不快的幻觉侵袭而来,就在正月时由于大逆罪而被处死的、我不曾见过的大石诚之助等人的灵柩就摆放在床前。当我睁开眼睛时,幻觉立刻消失了。”[12](P97-98)
菅野须贺曾经说,在日本的女性中比起紫式部和樋口一叶来说,她更喜欢与谢野晶子。[1](P89)当菅野须贺已经被判死罪时,还向晶子表示想要读她的诗集,用今天的话说,菅野可谓是晶子的“忠实粉丝”了,生命不知还剩几何,竟然还存着念想要去拜读偶像的诗作。可是,晶子是如何对待这位“有罪”的粉丝呢?她在1914年3月20日写给小说家小林政治(1877-1956)的书信中提及此事,她说自己当时因为胆怯,没有送诗集到狱中。[1](P103-104)与谢野晶子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担心和忌讳,她并不想与政治犯之间有所牵连。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谢野夫妇对于“诗歌之道”和政治事件、社会时事都有着一致的认识和态度。诗歌作为铁干所倡导的“自我之诗”要远离政治。其实,无论“诗歌之道”还是“商家之道”,晶子所持守的是一条始终如一的“尊皇之道”,在“尊皇之道”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割裂、裂变或断层,她始终都是一个忠诚于天皇制的“好国民”。《君莫死》之所以被认为是“反战诗”纯粹出于大町桂月的故意曲解以及战后某政治团体为了宣传的需要进行蓄意引导的结果。对这首诗的创作者与谢野晶子来说,诗中仅仅表达了对手足至亲的担心而发自真情吟诵出的“心声”而已,因为这个弟弟与把她赶出家门的长兄不同,既是她在诗歌上的同道人,也是她生活与理想的支持者,如此的姐弟关系,彼此之间的手足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再从晶子一生不曾产生过动摇的尊皇思想来看,不可能突然唱出“反调”来;从她远离政治的立场来看,她不可能主动地“引火上身”,为自己招来祸端。彼时当局之所以采信了大町桂月的“读解”,是因为于官方而言,大敌当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区区“私情”不可扰乱民心。而国内的一些读者和论者长期以来一直僵化地持有“反战诗”的观点,大概是受到我们自身传统上的“文以载道”以及“诗言志”的观念影响,似乎唯有“高大上”才堪称为名诗,也忽视了这首诗的背后所残留的日本文化中的“家”观念。抑或是“人云亦云”的思维惰性所致。
最后,就其战争言论而言,从日俄战争到日本对亚洲诸多国家的侵略以致挑起太平洋战争,晶子非但没有反对的态度,甚至是侵略战争的赞美者,甘愿成为战争的宣传者和鼓动者,这一切从她“远离政治”的立场来看,似乎是矛盾的,但其实都是统一在她作为一个天皇制下的“好国民”的表现,只要是为了皇国(日本帝国)之大业,她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和赞颂。针对短歌女王的这种“短板”,渡边澄子认为其原因是“……由于孩子每年都在增多,庞大的家庭开支并非铁干而是由晶子来承担,精力充沛的晶子承受住了生活的重担,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继续磨砺内在世界的学习时间已被剥夺殆尽。”[1](P107-108);“晶子的生活过于繁忙,没有时间好好地读一些‘有份量’的书籍来形成自己的思想。由于年轻之时早早地就站到了顶峰,没能拥有发现“自己缺点”的视角,固定地将天皇制作为‘绝对唯一’的‘价值’。……这种僵化的意识观念使她失去了‘判别思想书籍等的能力’而招致了令人感到奇怪的结果。”[1](P110-111)晶子的“短板”就在于她优异的感受性能够使她看透和说破一些事物的本质所在,然而,由于思想性的缺乏而使她仅仅固守一种观念和价值,那就是对天皇制的绝对化、对作为“好国民”的终身追求。因此,不加分辨地、轻率地就将与谢野晶子作为“反战的和平女神”来认识和定位,完全是一场误解和误读,忽略了其思想上的薄弱性,抑或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吧。对待《君莫死》这首诗,将其作为“反战诗”毫无依据,进一步将其作为“反战文学的代表作”更是无稽之谈。根据晶子在《公开信》中的陈述,“对每一个少女来说都是厌弃战争的”[11](P18),《君莫死》至多也只能算“厌战诗”而已。而写作《公开信》时的晶子早已不是“少女”了,是“尊皇思想”早已浸入骨髓的诗人了。所以,即便是“厌战诗”的判断也要画上问号的。我们不应将《君莫死》仅仅作为“一枝独秀”来看,而要将其放到作者的整个创作当中去作判断和定位,至少应该将其放到她所有的诗作当中去作判断才会具有客观性和体现出一定的说服力。
[1] 渡邉澄子. 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論――闇を拓く[M]. 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
[2] 中川八洋. 與謝野晶子に学ぶ[M]. 東京:グラフ社,2005.
[3] 张晓宁. 与谢野晶子及其反战诗[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2).
[4] 张晓宁. 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J].外国问题研究,2005,(3).
[5] 水田宗子主编.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C]. 陈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6] 王玲. 与谢野晶子和她的反战诗《你不要死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0).
[7] 张蕾.用爱和热情去点亮一生——「与谢野晶子」[J].日语知识,2009,(1).
[8] 申素芳.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诗歌情感解析 [J].咸宁学院学报, 2011,(12).
[9] 李芒.与谢野晶子诗一首(译注) [J].日语学习与研究,1983,(4).
[10] 與謝野晶子.與謝野晶子全集:第二十巻 [M].東京:文泉堂,1972.
[11] 鹿野政直·香内信子編.謝野晶子評論集[C].東京:岩波書店,1985.
[12] 與謝野晶子.定本 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四巻[M].評論感想集一,東京:講談社,1980.
[13] 與謝野晶子.與謝野晶子全集:第十九巻[M].東京:文泉堂,1972.
责任编辑:冯济平
Is Kimi Shinitamou Koto Nakare by Akiko Yosano an Anti-War Poem?
YU Hua WANG Guang-h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
Akiko Yosano was a famous Japanese waka poet, writer and critic. Her long poem Kimi Shinitamou Koto Nakare had long been regarded as an "anti-war poem", and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After the war, it continued to be trumpeted as an "anti-war poem". And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lso gave it high praise. However, from the poet's point of view, it just expresses her innermost feelings instead of anti-war ideas.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text or poems.
Akiko Yosano; Kimi Shinitamou Koto Nakare; anti-war poem; system of the Japanese emperor
I106
A
1005-7110(2016)06-0077-08
2016-07-26
青岛大学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项目“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QDYK C14006)
于华(1964-),女,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王光红(1991-),女,山东潍坊人,青岛大学外语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