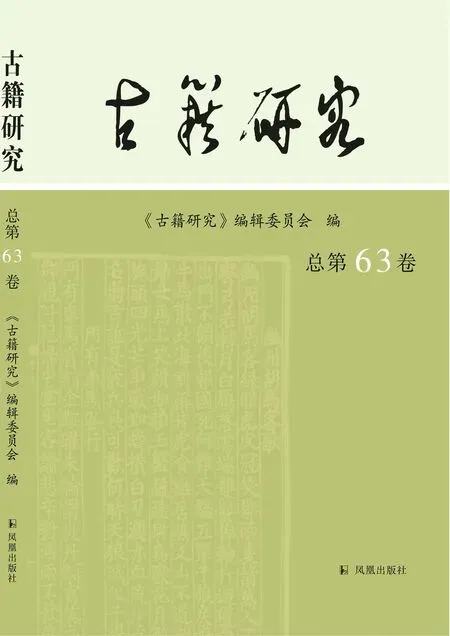旧文体中的新世界
——潘飞声《海山词》的价值与特色
林传滨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
旧文体中的新世界
——潘飞声《海山词》的价值与特色
林传滨
上世纪末,学界对近代文学改革运动中词体的缺席与否展开讨论,陈铭、袁进认为近代词人没有提出革命的口号,词逐渐走向衰微*陈铭:《晚清词论转变的核心:以诗衡词》,《浙江学刊》,1993年第3期,第78页;袁进:《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85页。,张宏生、巨传友、沙先一和倪春军则指出近代词有新语句和新意境的表现,在内容和精神上与诗界革命有所呼应,而民国以后胡适、曾今可、卢前等人也相继对词体创作提出改革的意见*张宏生:《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3-372页;巨传友:《临桂词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5-197页;沙先一、张晖:《清词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8-344;倪春军:《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31-40页。。上述学者探讨的是词(旧文体)在近代社会及文学革命(新时代)中的发展(或衰微),论述其创作内容是否反映新时代的事物和社会变化,不过,他们的讨论多聚焦在国内词人,较少关注直接面对新世界的海外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船舰日益频繁来华的同时,愈来愈多的国人也因各种机缘远赴海外,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对晚清郭嵩焘、王韬、黄遵宪等人的海外日记和诗文著作早已有所关注,然而除了民国时期的吕碧城之外,对海外词的讨论研究却不多。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文人潘飞声(1858—1934)*潘飞声,字兰史,号剑士,广东番禺人,曾担任《香港华字日报》和《实报》主笔,与黄遵宪、丘逢甲、邱炜萲等人往来,晚年寓居上海,与朱祖谋、周庆云、胡寄尘、柳亚子等相过从,有《说剑堂集》《在山泉诗话》《粤词雅》等著作。就已应德国驻华公使邀请*张德彝:《五述奇》卷1,见《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1996年,第65页。,担任柏林大学东语学堂教席,旅居期间除了《柏林竹枝词》《游萨克逊日记》之外,更著有《海山词》一卷,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编著于海外的词集。虽然自晚清以来不少人已注意到《海山词》描写海外风光的特色,然而它对于审视近代词体创作发展变化的价值意义却尚未被关注。相较于国内词人,《海山词》是潘飞声在柏林直接面对新世界的创作,如何将生活周遭的新事物纳入旧文体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以潘飞声的《海山词》为例,首先介绍其中的海外因素和特色,其次探讨潘氏对旧文体表现新材料的创作思考,由此说明海外词对审视近代文学改革运动中词学发展的价值意义。
一、 新材料与新意境
《海山词》以主题划分大体可以分为友朋交游、冶游爱情、羁旅思乡、纪游怀古四类。由于生活环境的异域色彩,潘飞声在相关作品的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呈现了一些特别的趣味特色,亦即“新材料”和“新意境”。
“新材料”是指海外生活经验中的各种新奇事物。潘飞声旅居德国,在创作时无可避免要触及生活环境中有别于国内的新事物,然而在表述时,若直接采用中国对应的文字,则失去了新事物本身的新奇性,况且也未必能轻易找到完全对应、又符合词谱声韵要求的现有词汇,于是如何将海外新事物融入词体就成为他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
《海山词》对于“新材料”入词有两种取向。第一种是为了体现事物本身的新奇或异域特色,直接音译或自创新词,如《临江仙·记情》:
第二红楼听雨夜,琴边偷问年华。书房刚掩绿窗纱。停弦春意懒,侬代脱莲靴。 也许胡床同靠坐,低教蛮语些些。起来亲酌架菲茶。却防憨婢笑,呼去看唐花。*潘飞声:《海山词》,载《说剑堂集》,香港:龙门书店,1977年版,第24页。
这首词可能是潘飞声在柏林“访妓香闺”*方宽烈编:《二十世纪香港词钞》,香港: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第59页。所作。词中“架菲茶”的“架菲”是咖啡的音译,加“茶”字以表明其性质,而“胡床”是指“沙发”,“蛮语”指“德语”,以“胡”“蛮”点明其西方特性,借用已有的传统字词来表达新的意思。这样的词语搭配既是作者为描述新的生活环境而音译自创,同时也为传统的词作带来新的时代气息,即使掩去潘飞声赴德国的背景资料,“架菲茶”“胡床”“蛮语”仍能提醒读者当时作者身处异域的创作背景,也要求读者由此想象海外的生活情境。
第二种情况是为了迁就词的文体特色及审美需求,不直接用音译新词,而是用中国的传统词语、典故来表达新事物,以求融入词境当中,如《金缕曲·德兵合操日,姚子梁都转命车往观,柏林画工照影成图,传诵城市,都转征诗海外,属余为之先声》:
图画人争买。是边城、晶球摄出,陆离冠盖。绝域观兵夸汉使,赢得单于下拜。想谈笑、昂头天外。渡海当年曾击楫,斩鲸鲵、誓扫狼烟塞。凭轼处,壮怀在。 列河禊饮壶觞载。有佳人、买丝绣我,临风狂态余在安德定陵河边酒肆,与诸女史修禊,亦有人写入图画。请缨上策平生愿,换了看花西海。只小杜、豪情未改。自笑封侯无骨相,望云台、像绘君应待。敲短剑,吐光彩。*《海山词》,第20-21页。

除了意译或借用现有词汇表达海外新事物之外,《海山词》的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如《菩萨蛮·宿威陵》:
飞车穿过层云湿。长河渡口烟波黑。今夜宿山村。水风寒到门。 蒲桃供浅醉。短烛酣清睡。梦里见烟鬟。吹愁上碧山。*《海山词》,第39页。
潘飞声在这首词中描写了坐火车的经验,以“飞车”描写火车的快速,更以“飞”字为启发,将火车的快速夸大为好像在天上飞一样,可以感受到天上云层中的湿气。“烟波黑”乍见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可以解释为河面上的夜幕或乌云,但是也可能是指轮船喷出来的黑烟,这样的解释是源于潘飞声《游萨克逊日记》的记录。他在光绪十六年四月初六(1890年5月24日)从柏林搭乘火车到威陵,途中经过萨克逊首都得来斯登(Dresden),此时是“戌刻”(约为晚上7点到9点),潘氏“登郭外望,迤连碧河,楼阁云连,灯火潮拥,河水为沸”*潘飞声:《游萨克逊日记》,见李德龙、愈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7-8页。,“长河”“碧河”即指贯穿得来斯登城的易北河(Elbe),河面宽广,两岸有供货船客轮停泊之处。由于5月的得来斯登一般日落时间约为晚上九点,如果潘氏抵达时间是在晚上七、八点之际,则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黑”字则未必是指夜幕,而可能是指当时在易北河上往来的轮船释放出来的黑色烟雾。另外,古人诗词中描写烟波多写“白”或“碧”,很少用“黑”字,如白居易《南湖晩秋》“烟波白浩浩”*(唐)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4页。,司马光《送章伯镇知湖州》“烟波碧四围”*(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第2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50页。,即使谢章铤《酬林二子鱼直》有“此时南望烟波黑”*(清)谢章铤:《赌棋山庄全集·诗集十四卷》诗一,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773页。一句,也有它特定的语境,是指当时南方的战事。因此,“烟波黑”很可能是潘飞声在途经易北河见到轮船的特定情境下产生的语句,是描写轮船的黑烟,乍看是普通的旧词语,实际上表达了新的生活体验,也为作品带来不一样的情境。
《海山词》除了描写海外新事物,予读者新的生活感受之外,还有“新意境”的特色,在此,新意境不只是指新的思想或审美情趣,还是新的世界观。古人诗词中的世界视野往往局限于中国或毗邻的国家地区,时至晚清,西方各国的东来使国人重新认识这个广阔的世界。潘飞声由广州至柏林的旅途中,东南亚、非洲、欧洲各国各地的名字不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活现在眼前的建筑文明,在柏林期间,他又与日本人井上哲、金井飞卿,印度人杜鲁华那沙尔,暹罗人永远臣等不同国籍人士往来,意图联合东亚各国组建兴亚会,共谋自强之道。随着对欧亚各国认识增加,对世界形势的发展有更为确切的掌握,潘飞声已经不再是当年僻处岭南一隅的普通文人,在新的世界观下,他在反视己身或国家的过去未来时有了不同以往的比对资源,在他的创作中也呈现超越本国意识、反映时代的广大叙述视野。颜清华《老剑文稿序》曰:
兰史远游欧洲,旅居德国四年,威廉第一之伟绩,毕士马克之大猷,如何而转弱为强,如何而以小敌大,如何而内治,如何而外交,皆一一身履其地而目覩之,提纲絜领,掇其国之大政,与耳食途说者迥不侔。……兰史负经济才,十年前尝上书于当道矣,广铁路以通地利,联南洋以固藩篱,筹边隅以防俄,练海军以慑倭。秉国钧者,苟将其说而行之,于边功外交已得过半。*见潘飞声:《老剑文稿》卷首,载《说剑堂集》(25种本),光绪刻本。
潘氏赴柏林任教时,正值德国最强盛的时期。1871年,普鲁士先后击败奥匈帝国和法国两大欧洲强国,统一德意志地区建立德国,由德意志邦联的小国一举跃升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清朝对外战事是屡战屡败,内部又有太平天国和捻军之乱,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国家。潘氏在柏林亲身体会到德国的文明富强,相较于国内的内忧外患、积弱不振,更加感受到两者之间的强弱悬殊,德国从弱到强的历史经验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是他反思和改革清朝政治的范例,其《欧洲各国论》《德意志学校说略》《德意志兵制兵法译略》《兴亚会序》等文章*以上诸篇皆见于潘飞声《老剑文稿》。或劝谏为政者借鉴德国政制对中国进行改革,或审时度势描绘出欧洲各国的政治形势和未来发展,更提出联合东亚各国自保的策略,这些都是海外生活对他的刺激和帮助。
除了上述政论文章之外,潘飞声《海山词》中的部分作品同样因为新的世界观及对德国历史的认知呈现出新的意境,如《满江红·博子墪译言橡树林也,有布王富得利第二离宫,风亭雪阁,数十里相望。大河湾环,明湖迤逦,山光水色,苍翠万重,为布鲁斯第一佳山水》:
如此江山,问天外、何年开辟。凭吊古、飞桥百里,粉楼千尺。邻国终输瓯脱地,名王不射单于镝。看离宫、百二冷斜阳,苍苍碧。 葡萄酒,氍毹席。挠饮器,悬光璧。话银槎通使,大秦陈迹。左纛可能除帝制,轺车那许遮安息。待甚时、朝汉筑高台,来吹笛。*《海山词》,第33-34页。
博子墪即波茨坦(Potsdam),在柏林西南;布王富得利第二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在位时加强军事力量,出兵夺取奥地利西里西亚,瓜分波兰获得西普鲁士*陈永正选注:《岭南历代词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7页。,是普鲁士历史上甚有作为的皇帝;而离宫即指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
虽然这只是一首纪游怀古词,然而词中所游的是普鲁士皇帝的离宫,怀想的是德国、中国的古今。词上片写潘飞声前往博子墪游赏,亲见普鲁士离宫的繁华,有“飞桥百里,粉楼千尺”,进而联想到当年腓特烈二世强政励治、扩充版图的风光历史。下片由西欧器皿联想到汉代出使西域时中国的强盛,“葡萄酒,氍毹席”曾经是汉代珍视的西域进贡之物,此时则是潘氏柏林日常生活中的用品,然而词人由此所发想的却是千多年前的大汉盛世,今昔对照之下,生出不知何时清朝再次富强,使西方诸国“朝汉筑高台”的感慨。这首词不单是潘飞声的纪游见闻,其情感思绪更在中、德历史之间来回往返,作为一名拥有悠久历史文明、但现在却沦为半殖民国家的国民,潘氏面对眼前德国离宫的金碧辉煌,古今、中外的强弱对照,词人羁旅异地的哀伤,国事日艰的叹息,这些繁杂的情感思绪不仅加深了作品的内涵,更呈现了新的意境,在以往的词中少见。
又如另一首纪游怀古词《浪淘沙·登石门》:
匹马破蛮烟。倚剑峰峦。雨晴天外好看山。想见夸娥来裂石,划此孱颜。 壮志任投闲。射虎空还。元帅曾出铁门关。谁续西游编手录,醉墨斓斑。自注:元史,太祖收印度兵至铁门关,耶律楚材劝还。*《海山词》,第40页。
当时,潘飞声游览萨克逊的石门天险,见到眼前山势的巍峨险峻,不禁心生感慨,继而联想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丰功伟业,引发一番思古豪情,却也对自己现在羁旅海外心生怅惘。这首词的现实空间虽然只是萨克逊,然而时空跨越于古今和欧亚大陆之间,思绪神游于成吉思汗西征的时代,将古今中外都挽合在一起。
以上两首词的时空背景都是空前的辽阔,其世界观也不再限于中国或东亚一地,而是包括欧亚两大洲。在古今对比方面,以汉朝、元朝时中国武功的强盛,对照现在清廷对外战事的连连失利;在中外对比方面,又以普鲁士的崛起,对比清廷的日趋腐朽。这两首词不但有豪放之气,而且是针对时事兴发感慨,虽然身处海外远离家国,然而德国之行却给予潘飞声更开阔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在叙述当前时局、抒发个人感慨时,自然地营造出更大的时空背景作为衬托,不仅体现了一个晚清中国文人在欧洲强国的生活感受,更将欧亚大陆的时空、历史连接在一起,在古人视为小道、诗余的词中呈现出具时代意义和广阔深厚的新意境。
二、 《海山词》与近代文学革新运动
《海山词》描述了潘飞声身处德国的生活情感,在论述其海外词特色时,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其对旧文体表现新材料的思考与中国近代文学改革运动是否存在某种联系。
早在明清之际,已有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来华传教经商,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更成为朝廷官员,一些新奇的西方事物也随之传入中国,如康熙皇帝十分喜爱的自鸣钟等,也有一些文人尝试将这些新材料写入诗词当中,如纳兰性德的《自鸣钟赋》写自鸣钟的种种功用特色,陈维崧《满江红·赠大西洋人鲁君,仍用前韵》写外国人讲话“怪怪奇奇,咄咄甚、砈砈出出”,但是医术十分高明,“能医却笑神农苳”*(清)陈维崧著,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06-1207页。。虽然西方传教士在清初已经来到中国,然而他们在华的活动受到限制,大多集中在澳门、广州和北京,西方新事物也不是国人日常可以接触到的,当时文人也只是以一种尝新的想法将新材料写入诗词当中。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开放门户,外国船舰由沿海港口逐渐深入到内陆地区,与此同时,大量西方新事物、思想涌入并且逐渐遍及整个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都造成重大的冲击,文学创作亦未能例外,文人无法再用偶一为之或尝新的心态去面对西方新事物,而是必须思考如何使用旧文体书写新材料、新时代:是要避用新词汇,保留旧文体的语言风格?还是突破文体的传统框架,寻求新的叙述方式?
在十九世纪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提出政治维新变法的同时,对诗、文、小说和戏曲提出改革的口号,这些改革口号固然有政治上的考虑,但也响应了晚清文学界面对的如何用旧文体表达新材料的问题,从而拉开了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序幕。
在1896—1897年间,夏曾佑(穗卿)、谭嗣同(复生)的新诗体创作尝试可以视为晚清文人对于新材料入旧文体的第一种取态,梁启超对他们当时的创作有这样的描述: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又赠余诗四章中,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苛非当时同学者,断无从索解,盖所用者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也。*梁启超著,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饮冰室文集》第6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16页。以下引用一律简称为《饮冰室文集》。
以夏曾佑和谭嗣同为代表的新诗体创作标榜以新名词入诗,对于西方的新材料是全面接受的,不避忌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欧洲语句和思想,直接以音译新词和圣经典故入诗,如“巴力门”是Parliament(英国议院)的音译,“三言不识乃鸡鸣”则是用《圣经》中彼得在鸡鸣天亮前三次否认认识耶稣的典故。虽然他们的创作将新材料直接化生成新词汇带入旧文体当中,表达了新的内容思想,然而梁启超认为这并不是成功的方法,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说:
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③④ 《饮冰室文集》第3集,第1826页。
几年后,又在《饮冰室诗话》批评二人诗作“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饮冰室文集》第6集,第3816页。梁氏认为夏、谭二人新诗体尝试以新语句表达新内容思想值得肯定,但他们在解决书写新材料的问题时也使旧文体失去了原本的风格特色,新诗体不像是古典诗歌,更像是容纳新语句的文字工具。
1899年,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提出“诗界革命”时指出了第二种取向:“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③梁氏认为在内容方面不必避忌新词汇,要追求新意境,以求反映新事物和新时代精神,而要求古风格则是一种尊体意识,是对夏、谭二人新诗体创作的改进,强调在用旧文体表现新材料的同时,需要关注文体本身的古典特色。“古人之风格”是“诗界革命”口号中接合新材料和旧文体的重要桥梁,然而,梁启超在提出以“古人之风格”补救新材料入旧文体的同时已经意识到新语句和古风格之间的冲突:“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④在梁氏看来,旧文体中如果包含太多的新语句,难免会出现像夏、谭的新体诗失去旧文体特色的问题,新语句和古风格实际上未必能完全融合,即使是黄遵宪,也只能勉避新名词以求保存古典诗歌的风格特色。因此,在后来写作《饮冰室诗话》时,梁启超已经放弃了对于新语句的要求,更加重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念:
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虽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饮冰室文集》第6集,第3817页。
梁氏认为“诗界革命”的实质并不是一味堆积新名词,而是要有新意境,同时保存诗歌的风格特质,新名词至此已经可有可无。
简而言之,近代文学改革运动对新材料入旧文体产生了一些尝试和讨论。第一种取态是夏曾佑、谭嗣同的新诗体创作,在旧文体中直接引用新名词和西方典故,在表达新内容的同时,难免出现失去古风格的缺陷。第二种是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梁氏最后选择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方式,对新名词虽不避用,但强调保存旧文体本身的风格。在了解近代文学改革运动对新材料入旧文体的思考和尝试后,我们可以发现,早在他们之前,远在德国的潘飞声已经在词的创作上面对相同的问题,而他和梁启超不约而同、并且更早地采取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方法。
比起生活在国内面对新材料逐渐涌现的文人而言,旅居德国的潘飞声更切身地体验着西方的新文化、新事物,也更难以避免旧文体描写新材料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海山词》中不乏描述新材料的作品,其中虽有直接音译入词之作,但是更多的还是借用或变化旧有词汇、典故来表达新的意思,使新事物自然地融入词中而不会破坏文体本身的风格。如《洞仙歌》(电灯妒月)以“檀槽声”借代歌剧的音乐*《海山词》,第20页。;《寿楼春》(向琼楼开筵)以“晶球”指电灯,“湘弦”指洋琴,又以“东瀛旧侣,西海群仙”写日本友人和欧洲美女*《海山词》,第23页。;《罗敷艳歌》(玻璃亭子明如水)中的“玻璃亭子”实指“温室”,潘氏于词后更有详细解说:“此园所得数茎为玻璃圆屋以护风露,又以铜管注热水其中,使温暖如中土地气。”*《海山词》,第32页。以词为媒介向读者介绍温室这种西方新事物。这些词作既表达潘氏身处海外的生活体验及新事物,同时又顾全了词体本身的语言风格。
潘飞声对新材料的叙述方式除了可能是出自对中国读者认知接受上的同化需要,或是词体音韵上的限制选择,同时也与他对词体表现方式的思考有关。潘飞声的文学思想论述多是在返国后所作,1905年,他开始在香港《华字日报》上刊载《在山泉诗话》,其中曾经转载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刊登的狄葆贤(字楚青)的一首七律,并作出以下的评价:
其所作有七律一章云:“又见东风拂耳过,任他飞絮自蹉跎。金轮转转牵情出,帝网重重酿梦多。珠影量愁分碧月,镜波掠眼接银河。为谁竟着人天界,便出人天也奈何。”全用新理想,却有意味可寻,与谭壮飞之满纸硬铜怪铁,不成一器者,正自不同也。*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3,第1628页。
不知道是趣味相投,还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潘氏也对谭嗣同大量引用新名词的新诗体创作提出批评。他认为狄葆贤的诗歌虽然借用佛经词语,如“金轮”、“帝网”和“人天界”,在体现新意境的同时仍有古典诗歌的意味可以咀嚼,而谭嗣同的新体诗则截然相反,谭氏在以新名词表现新事物时未能兼顾旧文体的风格特色,只留下生造硬砌的弊病。
此外,潘飞声又认为以新材料入旧文体,最好还是采用传统的表现方式。潘氏《在山泉诗话》对梁启超评价狄葆贤《泊长崎有感二绝》“以美人喻中日两国,不着一字,感怆甚深”深表赞同*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3,第1628页。,称许狄氏写新材料时,善用比兴手法,既有新意境,又有古风格,感慨愈深。而这种重视新意境和传统表现方式的思考同样反映在潘飞声的创作实践上,《海山词》的大部分作品正是用现有词句或典故表达新材料、新意思,音译新词只是偶一为之,更多作品都能兼顾词体本身的语言风格。
然而,使用传统表现手法也可能导致词作真实情境难以明白的问题,一旦掩去作者的前序、自注和写作背景,读者恐怕难以从传统词句、典故中读出当时作者身处的海外情境。这样的问题确实出现在《海山词》的部分词作当中,如《高阳台·芜亚陂女子越梨思所居第五楼,镜屏琴几,位置如画。槛外绿鹦鹉,能学语唤人。余两宿其中,绣榻明灯,曾照客梦。而梦中思梦,转难为怀,题此词,疥其壁,亦足见回肠荡魄时矣》:
帘卷花痕,屏开雪影,有人楼外偷凭。密语些些,等闲忘了深更。娉婷心似纤纤月,照闲愁、又照闲情。慰飘零,细酌银瓶,细拢银筝。 年来孤阁听秋雨,问绮怀谁诉,冷枕寒灯。一夕温存,消他暖熨吴绫。鹦哥解唤伤春客,护梨魂、晓梦休惊。记香盟,如此分明,如此凄清。*《海山词》,第17-18页。
这首词是潘飞声记与欧洲女子的艳情之作,词中从女子房间中的装饰写到二人之间的情感。然而,女子和房间的西方特色在这首词中消失了,剩下的是被潘飞声中国化了或者说是考虑词体风格后经过选择的语言,德国房间、欧洲女性以及作者和异国女子的情事完全以古典诗词的语言风格呈现,如果将词的序和写作背景抹去,将之置于秦观、柳永等人的作品中,几可混人耳目。
不过,这样的表现方式选择或许与作者想要表达的主要情感相关。潘飞声学词是由纳兰性德和郭麐入手,其《粤东词钞三编序》云:
飞声少时稍学为诗,于词则未解声律也。尝读先大父《灯影词》,拟作数首,携谒陈朗山先生,先生以为可学,授以成容若、郭频伽两家词,由此渐窥唐宋门径,心焉乐之。*潘飞声:《老剑文稿》,第82页。
纳兰和郭氏的词作皆以抒发性灵为主,潘氏在学习过程当中自然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对他而言,词作最重要的就是表达个人性情。因此,他对当时词人模仿梦窗词风、大量使用生僻典故以致词意难明的现象有所批评:
词者,诗之余,盖长短句之变格耳。大凡清辞丽句,慷慨高歌,必有意思以运之,性灵以出之,雅而不俚,真而不伪,方成一己之诗,即词又何独不然。迩日词学大兴,代有作者,然以描摹草窗、梦窗二家最多,晦涩生强,至不可读。*潘飞声:《刘廉生词集序》,《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2号,第193页。
他认为诗词创作必须要有自己的意思,抒发个人性灵,追求词风典雅和情感真挚,批评时人一味模仿吴文英词,不以抒情达意为主,刻意使用生僻典故,造成词意“晦涩生强,至不可读”的问题。了解这一点之后,在解读《高阳台》(帘卷花痕)时就可以明白作者在词中实际想要表达的未必是海外的艳福奇遇,而是个人的私密情感,既然已有序作为背景说明,那在正文中就不用再刻意突出异域女性及闺房的特殊不同之处,更重要的还是当时欧洲女子对他心灵的抚慰,以及二人分离后,自己对这段情感的追忆:“记香盟,如此分明,如此凄清。”
综合而言,潘飞声对词体创作方式有以下的思考:第一,旧文体不必避用新语句,但在表述新事物时,不能生砌硬造欧化新名词,而是应该兼顾文体本身的特色,善用比兴等表现手法,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第二,文学创作以抒发个人性情为主,运用典故时不宜用生僻涩典,使本意难明。
在了解潘飞声和近代文学改革运动对旧文体书写新材料的思考和创作实践后,我们可以知道潘氏和梁启超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在海外的生活环境和国内大量新材料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他们都抱持开放的态度,实践或提倡“旧风格含新意境”的理念,在创作上追求不避用也不堆砌新名词,重视旧文体的风格特质。虽然,潘飞声《海山词》的出现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提出前,对于新材料入旧文体的问题有自己的创作实践,也呈现出具有“新意境”“新材料”和古风格特色的词作,但应该认清他更多的思想论述是在“诗界革命”之后才提出,因此,在近代文学改革运动探讨“新材料入旧文体”的问题上,潘飞声是早期的创作实践者及后期理念上的认同呼应者,而不能认为他比梁启超等人更早提出了具体的文学理论。
三、 结 语
在潘飞声赴德国四十余年后,他的这种旧文体书写新材料的创作取向仍然在另一位海外词作者吕碧城的作品中得到回响。虽然吕碧城经过了白话文运动的洗礼,然而在运用词(旧文体)表现海外情景时,她和潘飞声一样,不约而同地采取传统的叙述方式,用旧有的意象典故描述西方新事物,使其融入于词体当中又不觉突兀。在《念奴娇·游白琅克Mont Blanc冰山》(灵娲游戏)中*吕碧城著、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她以“晶屏”“巫峡”写瑞士雪山之美,以“飞车”指高空缆车,自注云:“电线悬车,掠空而行。”*《吕碧城词笺注》,第164页。以“飞”字表达缆车悬空而行的特点。在《玲珑四犯》(一片斜阳)中*《吕碧城词笺注》,第168页。,她写自己游览意大利佛罗罗曼Fororomano的市场遗址,由眼前的残垣败壁联想到过去的罗马帝国(大秦),进而想到周穆王访西王母的典故,由此将中国和意大利的历史连接起来,同时又抒发了对时移势易的感慨。吕碧城与潘飞声一样,在采用现有词汇和典故叙述新的海外经验时,经常会使用小序和自注为读者提供解读的写作背景,从而弥补了新材料融入旧文体后实际情境不明的问题。
也许从整体上而言,潘飞声和吕碧城的海外词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框架,但在内容意境上,他们以旧文体描写海外新事物和生活体验,表现新的世界观和广阔的书写语境,展示了词在描述海外事物的可能性及创造力。近代海外词以及其他海外文学值得研究的不只是当中书写了什么样的风景或新事物,而是新的生活环境、新的世界视野对他们的心灵及思想造成怎么样的冲击,就像德国之行赋予了潘飞声新的世界观,让他从另一个广阔的叙述视野反思国内形势,创作出突破国内文人及反映时代的作品。另外,就时间点而言,潘氏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文学改革运动之前,已经于创作上实践了梁氏所提倡的“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改革思想。无论潘氏在当时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词学思想,无可否认的是他并没有革新词体的意向,即使在“新材料”和“旧文体”的问题上,比梁启超等人更早的有所思考和实践,但晚清词界并没有因此产生大范围和有影响的改革。如果对比潘飞声和吕碧城的词作,会发现在晚清民国社会、政治和文学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间,词即使在内容意境上有很大的扩充,然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却几乎没有丝毫的改变。在新文学运动以后,旧文体的创作地位逐渐被新文体取代,即使还有一些文人学者探讨词体创作的改革问题,然而更多的新一代作者似乎已不再关注旧文体如何反映新材料、新时代的问题。词体创作的衰微也许不是因为它没有提出革命的口号,也不是因为它无法反映新时代的变化,而是它与所有古典文学样式一样,在新文学运动的驱逐下,成为边缘的书写文体,再也难以回到创作主流的中心地位了。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俪人文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