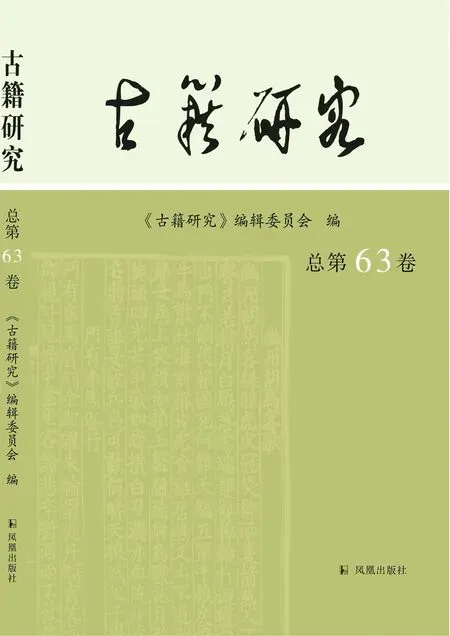“挽歌”源流考论
顾春军
(作者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挽歌”源流考论
顾春军
从文体学角度考察挽歌,有学者认为,“挽歌便是一种哀祭文体,它通常是用于为死者送葬之歌曲,大致是生者表达对于死者的怀念和哀悼之情”*吴承学:《汉魏六朝挽歌》,《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但若从起源角度考察,挽歌“就是送葬歌”*[日]一海知义:《〈文选〉挽歌诗考》,俞士玲译,《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2011年,第248页。。作为哀祭文体的挽歌,是丧歌演化流变的结果。
一、 西汉——丧乐开始出现
关于挽歌的起源,一种谓其起源于春秋时期,哀公十一年,齐国和吴国交战,《春秋左传》记载曰:
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杜注:《虞殡》即送葬之挽歌,唱之以示必死。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62页。
“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含玉以明将帅有必死之志:“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玑;士以贝;庶人以谷实。”*(汉)刘向撰:《说苑校正》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第493页。战争最需要砥砺士气,故公孙夏命其徒所歌之《虞殡》,必是激励鼓舞士气之歌,其歌词大约不外慷慨任气罢了。我们可从类似的故事揭橥其主题: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汉)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58页。
《礼记·郊特性》:“素服,以送终也。”《周礼·春官·司服》:“大札、大荒、大灾,素服。”故“皆白衣冠”,与“具含玉”之意同,均暗含必死之意。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可以推断:《虞殡》必是慷慨与激昂的励志之歌。将《虞殡》视为挽歌,最早来自于杜预对《春秋》的笺注。首先,从《春秋》成书到杜预生活的西晋,已有七个世纪之久,期间没有其他材料认为《虞殡》为挽歌之始;其次,晋代是挽歌大盛的时代,杜预或“以己度人”,以为《虞殡》为挽歌之始;其三,挽歌哀叹生命易失,其曲调必然主悲,这与《虞殡》的慷慨激昂是不同的。
另有挽歌起源于战国之说,例证是《庄子》一书的佚句,这见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所作的笺注:
按《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绋所以有讴歌者,为人有用力不齐,故促急之也。”*(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92页。
司马彪是西晋宗室,他将“绋讴所生”解释为引柩索,实武断:任何苦力都可引绳而歌,这种论证方式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我们还可看到,附会先秦史料为挽歌起源之证据,基本为晋代学者,这因为挽歌在晋代大盛,为将如此“越礼”行为纳入仪轨,故不能不敷衍故事。
从礼学角度分析,丧葬之礼乃先秦《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中的重要内容,如果先秦有挽歌,怎么不见片言只语提及?《荀子》一书亦有“礼论”章,但其荦荦大端者,亦毫不提及挽歌。所以,挽歌起源于先秦说,是靠不住的。另有一种说法,见于三国时期蜀国学者谯周,他以为挽歌起源于西汉的田横:
谯子曰:“周闻之:‘盖高帝召齐田横至于户乡亭,自刎奉首,从者挽至于宫,不敢哭而不胜哀,故为歌以寄哀音。彼则一时之为也。’”*《世说新语笺疏》,第892页。
关于田横之死,《史记》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司马迁尤其喜好奇谈异闻,故《史记》一书“作意好奇”处极多,倘田横自刎身死,其门客以“挽歌送葬”,又为何不见于司马迁笔下?再退一步,如司马迁忽略此事,为何班固一仍其旧?那四百年后的谯周又如何得知?之后,晋代的崔豹更多添加枝叶:
《薤露》《蒿里》,并哀歌也,出自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其二曰:“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晋)崔豹:《古今注》,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页。挽歌出于田横门客一说,另见于《新辑搜神记》卷二十三,《北堂书钞》卷九十二,《文选》卷二十八,《初学记》卷十四,《太平御览》卷五百五十二,其他类书史书也多有记录,不一一罗列。
李延年是见于史籍的西汉著名音乐家: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3853页。
制礼作乐是历代王朝的大事,汉武帝时期更是如此: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51页。
如果李延年为汉武帝改作挽歌,史籍没有理由不实录:然而在《史记》《汉书》中,找不到任何关于挽歌的记录。由此观之,挽歌起源于田横之徒一说,符合古史辩派所主张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台北:蓝灯文化事业公司,1992年,第60页。
无论是挽歌起源于田横之徒,还是李延年制作挽歌,都是后世的传说。但在西汉时期民间,丧乐开始大量出现:“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散不足第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4页。演奏丧乐亦成为职业:“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汉书》卷四十《周勃列传》,第1586页。丧乐的产生,就为挽歌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尤可注意者,“吹箫给丧事”的周勃是楚人,东周以来,楚国巫风大畅,民间素有祭祀鬼神的风俗,祭祀仪式上会唱祭歌,屈原所作《九歌》,即为祭歌中的代表,汉代学者王逸云: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二《九歌章句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
祭礼属于吉礼,有别于属于凶礼的丧葬之礼,祭礼上所演唱的祭歌,从内容上看,与挽歌迥然不同;再从丧葬礼仪角度看,丧葬仪式后的庙祭(虞祭),已属于吉礼。毫无疑问,早期的祭歌会影响到挽歌的形成,显然,周勃的“吹箫给丧事”,盛行于楚国故地,就可以为此提供一个例证。
二、 东汉到魏晋——挽歌的产生与盛行
人死化为“魂”和“魄”,此种观念源于商周并在汉代成型:“尽管儒家和道家对于魂和魄的各自功能的看法有别,但其基本结构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相似性充分证明了魂魄相异,即魂是‘精神的’灵魂,魄是‘肉体性’灵魂,在汉代已具普遍性”*余英时:《东汉生死观》附录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76-177页。。儒家以为魂魄是可以分离的:“魂气归于天,形魂归于地。”(《礼记·郊特牲》)魄附于身体入地,而魂则四处飘散:“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礼记·檀弓下》)秦汉之后,又有“泰山治鬼”之说:
尝考泰山之故,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左氏》《国语》未有封禅之文,是三代以上无仙论也。《史记》《汉书》未有考鬼之说,是元成以上无鬼论矣……然则鬼论之兴,其在东京之世乎?*(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18-1719页。
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相结合,当代学者研究认为:
汉人不仅相信泰山为鬼魂群聚之处,而且还把和泰山相连的高里山也看作是和幽冥有关的地方。《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十二月,禅高里。”颜注引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高里和泰山相连,所以在民间迷信中,它和泰山一样地被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汉代人以为人死后到篙里,篙里即是从山名的高里演化来的。*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03期,第60页。
也就是说,直到汉代,蒿里才成为亡魂的归宿地,故所谓的起源最早的《蒿里歌》:“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就不可能早于汉代,这又为挽歌不起源于汉代之前增添一个例证。
西汉晚期,在皇室的大丧及大臣丧礼上,开始有挽郎出现。西汉哀帝的时候,大臣孔光死后,礼仪甚为隆重: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张,谏大夫持节与谒者二人使护丧事,博士护行礼。太后亦遣中谒者持节视丧。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辒辌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余辆,道路皆举音以过丧。*《汉书》卷八十一《孔光列传》,第2505页。
由上述可见,按照当时礼制,羽林孤儿之挽送类似于仪仗队性质;由“道路皆举音以过丧”可以看出,丧礼用乐已被纳为朝廷礼制。挽歌被朝廷采纳并成为礼制,是在东汉明帝刘庄母亲阴太后的葬礼上:
永平七年,阴太后崩,晏驾诏曰:“柩将发于殿,群臣百官陪位,黄门鼓吹三通,鸣钟鼓,天子举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参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车,黄门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魂车,鸾路,青羽盖,驷马,龙旗九旒,前有方相,凤皇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卤簿仪。”后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51页。
尤可注意者,“后和熹邓后葬,案以为仪,自此皆降损于前事也”。也就是说,在阴太后之丧礼上,挽歌正式成为礼制。在皇室贵族的丧礼上,挽歌的演唱者基本由贵族子弟担任:“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五《礼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06页。成为一名挽郎显然是荣耀之事:“任育长年少时,甚有令名。武帝崩,选百二十挽郎,一时之秀彦,育长亦在其中。王安丰选女婿,从挽郎搜其胜者,且择取四人,任犹在其中。”*《世说新语笺疏》,第1069页。
挽歌本来是主悲的丧歌,但在东汉末期,达官显贵将演唱挽歌视为娱乐,后来的史学家将其收入“五行志”,以为是不祥之兆:
《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国家当急殄悴,诸贵乐皆死亡也。”自灵帝崩后,京师坏灭,户有兼尸,虫而相食,“魁櫑”“挽歌”,斯之效乎?*《后汉书》志第十三,第3273页。
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列传》,第2028页。
挽歌登上“大雅之堂”,这与汉魏晋社会思想潮流极有关系:一、 东汉后期,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清议盛行,甚至“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纪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650页。;二、 魏晋以来,玄学兴起,人们更以“齐生死”的态度去面试死亡,所以就不忌惮在宾婚嘉会上演唱挽歌。
魏晋政治上黑暗,杀戮盛行,士人难有保全,谈玄说异成为一种风流,在意识形态上,儒家的礼制被颠覆了,为显示特立独行,唱挽歌成为风雅之举:
海西公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宴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36页。
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世说新语笺疏》,第890页。。

流风余韵所及,在魏晋时期,很多达官显贵也喜欢演唱挽歌:
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皆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唐)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颜延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9页。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弟广渊,时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晔与司徒左西属王深宿广渊许,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义康大怒,左迁晔宣城太守。*《宋书》卷六十九《范晔列传》,第1819-1820页。
或单骑出游,逢人婚姻葬送,辄就挽歌,与小儿同聚饮酒为乐。*(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9页。
居白杨石井宅,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客恒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南史》卷十九《谢几卿列传》,第545页。
平秦王诉之于文宣,系于京畿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唐)李百药:《北齐书》卷四十八《尔朱文略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67页。
所以发展到西晋,虽然舆论认为丧礼与挽歌相悖,但囿于习俗的力量,统治者做出了妥协的决策:
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设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不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倡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亦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诏从之。*《晋书》卷二十《礼中》,第626页。
魏晋时期人性得以解放,其代表人物嵇康阮籍之流“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用阮籍的话来说:“礼岂为我辈设也?”嵇康更是认为:
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阙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47页。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传统礼制被颠覆的同时,乐文化也出现了新提法,那就是“声无哀乐”论的提出:
夫天地合德,万物贵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不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哭〕非(悲哀)〔哀乐〕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感)慼,然而哀乐之情均也。*《嵇康集校注》,第346页。
既然声无哀乐,那么,宾婚嘉会演唱挽歌也就不算违礼了——在传统儒家看来,魏晋之际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挽歌大行其道的时期。
三、 由兴盛而消歇——皇权制度下的挽歌
隋唐统治者有恢弘的心胸与包容的气魄,在文化上承袭魏晋南北朝之遗风,依然将挽歌列入朝廷丧葬礼仪:
三品已上四引,四披,六铎,六翣;挽歌六行三十六人;有挽歌者,铎依歌人数,已下准此。五品已上二引,二披,四铎,四翣,挽歌四行十有六人。九品已上二铎,二翣。其执引、披者皆布帻、布深衣;挽歌者白练帻、白褠衣,皆执铎、披。*(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08页。
一旦遇到帝王的大丧,当朝文士还要撰写挽歌诗,以供朝廷选用:“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唐)魏征等撰:《隋书》卷五十七《卢思道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97页。浸染久远,挽歌就成为葬礼等级的一种标志:
武德六年二月十二日,平阳公主葬,诏加前后鼓吹。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谓曰:“鼓吹,是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军,既常为将,执金鼓,有克定功。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匹也,何得无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绩。”至景龙三年十二月,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请自今婚葬之日,特给鼓吹。宫官准此。”*(宋)王溥撰,牛继清校正:《唐会要校正》卷三十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594页。
挽歌不单单兴盛于朝廷,在民间亦成习俗:“丁会字道隐,寿州寿春人也。少工挽丧之歌,尤能凄怆其声以自喜。后去为盗,与梁太祖俱从黄巢。”*(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四十四《丁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81页。但是,民间的挽郎地位卑贱,在唐传奇《李娃传》中,因为儿子流落民间做了挽郎,所以太守大怒:“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89页。
到了宋代,一旦遇到遇到皇家丧礼,大臣依然要献上挽歌:“改卜陵寝,宣祖合用哀册及文班官各撰歌辞二首。”*(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二十二《礼二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第2848页。对于大丧及大臣之丧礼所使用挽歌,做了更细致的规定:


蒙元之丧葬习俗迥异于汉族:“北俗丧礼极简,无衰麻哭踊之节,葬则刳木为棺,不封不树。”*(元)黄溍撰:《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蒙古贵族采取“不封不树”的密葬方式,于挽歌不相宜,故蒙元统治者的丧葬礼仪中没有挽歌。到了明代,挽歌已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在明代的正史及稗史中,再也见不到对丧礼中挽歌的描述;另一方面,士大夫父母之丧,花重金求挽歌诗为册,依然成为一种风气:
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为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既有诗序,则不能无诗,于是而遍求诗章以成之。亦有仕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对这种陋俗,明代学者如程敏政、章懋、湛若水、丘濬等多有批判,参看徐乾学《五礼通考》卷六十五“挽歌”条。
然在所留存的明代史料中,亦有两条关于挽歌的记载,不少论者以之为证据:
灵车动、从者如常。灵车后方相车、次志石车、次冥器舆、次下帐舆、次米舆、次酒脯舆、次食舆、次铭旌、次纛、次铎、次挽歌、次柩车。*(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4页。
铎者,以铜为之,所以节挽歌者。*(清)张廷玉:《明史》卷六十《礼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5页。
虽然在制度中有规定,但史料中见不到丧礼中关于挽歌的记载;清代满族统治者继承了汉文化,但是丧礼中使用挽歌却是没有了,明清两代是挽歌消歇的时期。
四、 民间“挽歌”——由“丧乐”到“丧戏”
《吕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远古时期,诗乐舞本为一体。前已述及,丧乐产生时间不会晚于挽歌。汉代《风俗通》曰:“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櫑,丧家之乐。”也就是说,在东汉的送殡仪式上,丧乐和挽歌同时并举:
孝昌元年,太后还总万机,追赠怿太子太师、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辒辌车、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挽歌二部,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谥曰文献。*(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3页。
晋代礼部在制礼作乐的时候,大臣挚虞以为,挽歌与哭泣之声相通,虽然并不是古礼,但依然可以保留;而丧乐则与儒家主张相悖,故只得剔除丧乐:
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以鼓吹。新礼以礼无吉驾导从之文,臣子不宜释其衰麻以服玄黄,除吉驾卤簿。又,凶事无乐,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晋书》卷二十《礼中》,第626页。
作为文化小传统的民俗,并不完全受制于儒家礼制,往往更能体现人性一面,所以也有“礼不下达庶人”一说:
郑氏曰: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孔氏曰:张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礼,但以其遽务不能备之,故不著于经文三百,威仪三千耳。其有事,则假士礼行之。”*(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1页。
礼不下庶人。非谓庶人不当行,势有所不可也。且如娶妇三月,然后庙见,及见舅姑。此礼必是诸侯大夫家才可行。若民庶之家,大率为养而娶。况室庐不广,家人父子朝暮近在目前,安能待三月哉!又如内外不共井,不共湢浴。不共湢浴,犹为可行,若凿井一事,在北方最为不易。今山东北畿大家,亦不能家自凿井,民家甚至令妇女沿河担水。山西少河渠,有力之家以小车载井绠,出数里汲井。无力者,以器积雨雪水为食耳,亦何常得赢余水以浴?此类推之,意者,古人大抵言其礼当如此,未必一一能行之也。*(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所以,丧礼用乐,不独民间如此,就连士大夫都不能禁止:
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晋书》卷七十九《谢安列传》,第2075页。

凶肆之间也必然会有竞争,故须不断改进业务,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从唐代开始,戏曲开始萌芽:“至唐而所谓歌舞戏者,始多概见。有本于前代者,有出新撰者。”*王国维撰,马美信疏证:《宋元戏曲史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页。戏曲婉约多姿,生动活泼,必然会吸引更多观众:
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见闻记校注》卷六《纸钱》,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1页。
蒙元贵族采用密葬方式,丧礼无挽歌,不奏乐;但汉族百姓依旧保持了传统乐丧习俗:
晋宁路总管府契勘本路:一父母兄长初亡,殡葬之际,彩结丧车,翠排坛面,鼓乐前导,号泣后随,无问亲疏,皆验赙礼多寡,支破布帛,少不如意,临丧争竞兢。*黄时镢辑:《大德典章遗文》,《元代法律资料辑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0页。
从恪守古礼之士大夫的反对声中,可知丧葬用乐在元朝已成流俗:“丧礼之废久矣,今流俗之弊有二,而废礼尤甚。其一,铺张祭仪,务为观美,甚者破家荡产。以侈声乐器玩之盛,视其亲之棺椁衣衾,反若余事也。其二,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以极斋羞布施之盛,顾其身之哀麻哭踊,反若虚文也。”*(元)谢应芳:《辩惑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页。随着戏曲表演艺术的成熟,在明清葬礼上的丧乐就演变为戏曲演出:
近年京城军民之家丧事甚违礼制,初丧扮戏唱词,名为伴丧及出殡,剪制纱罗、人物、幡幢之类排列塞途,兼用鼓乐、戏舞导送,及墓陈设荤酒饮啖至醉,又有扬幡设坛,修斋追荐,糜费钱物,不可胜记,宜并禁革。*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1104页。
京师丧家出葬,浮费最多。一丧车或至百人舁之。铭旌有高五丈者,缠之以帛,费百余匹。其余香亭幡盖仪从之属,往往越分。又纸糊方相,长亦数丈,纸房累数十间。集送者张筵待之,优童歌舞于丧者之侧,跳竿走马,陈百戏于途,尤属悖礼。*(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六,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37页。
在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就体现了乐丧这种民俗:如李瓶儿死后大殓,“晚夕,亲朋伙计来伴宿,叫了一起海盐子弟搬演戏文”。“下边戏子打动锣鼓,搬演的是韦皋、玉箫女两世姻缘《玉环记》。不一时吊场,生扮韦皋,唱了一回下去。贴旦扮玉箫,又唱了一回下去”。西门庆吩咐:“拣着热闹处唱罢。”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清代的风俗画,在秦可卿之死章回中写道:“只听得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对于这样的“越礼”行为,儒学之士依然要猛烈抨击:
鼓吹,古之军容。汉、唐之世,非功臣之丧不给,给或不当,史必讥之。近来豪富子弟,悉使奴仆习其声韵,每出入则笳鼓喧天,虽田舍翁有事,亦往往倩人吹击,何其僭也。*(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1页。
军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即大臣非恩赐不敢用。旧时吾乡凡有婚丧,自宗勋缙绅外,人家虽富厚,无有用鼓吹与教坊大乐者,所用惟市间鼓手与教坊细乐而已。近日则不论贵贱,一概混用,浸淫之久,体统荡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兢也。*(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90页。
对恪守古礼的人,文人在笔下则予以歌颂:“后与胡端敏嗣君纯交,悉其行事谨身节用,敦笃姻族,训诫家人,修治坟墓,皆若父训。迨举父丧,一遵《家礼》。所列惟方相、香亭、神亭、旌亭、包筲、银瓶、把花、雪柳而已。鼓乐陈而不作,尽削杭城繁缛之习。”*(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页。
民间凶肆素来被视为“贱业”,西汉的周勃,唐代的荥阳公子郑生,他们的职业无一不被人轻视,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清依然如此:
民间吉凶事,率夫妇服役,鼓吹歌唱,以至舁轿、篦头、修足,一切下贱之事,皆丐户为之。*(明)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2页。
然性纡缓,多为人所愚,任湖南学政归,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薄,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8页。
只有生活没有着落,或身残之破落户,才从事凶肆这个职业,反之,比如上引材料中的官员褚筠心,以官宦之身开办凶肆,就受到他人耻笑;与之相反的是皇家大丧的挽郎,却令人艳羡不已,因为筛选挽郎不公,唐代的诗人贺知章甚至因此被贬官:
俄属惠文太子薨,有诏礼部选挽郎,知章取舍非允,为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以梯登墙,首出决事,时人咸嗤之,由是改授工部侍郎,兼秘书监同正员,依旧充集贤院学士。*(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贺知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除了道德上的谴责,对于丧礼用乐,明清均明确规定了处罚措施:“凡闻父母及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丧制未终,释服从吉,忘哀作乐及参预筵宴者,杖八十。”*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卷十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95-96页。至于朝廷,则有诏书要求严格处理如此事件:
今各处愚民有遭父母、兄弟之丧,殓葬之期,宰牲筵款吊祭姻朋,甚至歌唱以恣欢,乘丧以嫁娶者,伤风败俗,莫此之甚,乞敕该部严禁约之,上命该部议行。*李国祥,杨昶主编:《明实录类纂》,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1100页。
乾隆十年,陕西巡抚陈宏谋上《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云:
丧中宴饮,已属非礼;而陕省更有丧中演戏之事,或亲友送戏,或本家自演,名为敬死,其实忘亲,哀戚之时,恒舞酣歌,男女聚观,悖理伤化,莫此为甚。从前屡经禁止,至今恶习未除,风化攸系,未便因循。嗣后应先从绅士为始,遇有丧事,禁止演戏,违者无论乡保地邻,许其首告。并令教官严切训诫,不时稽查,倘有违犯,即为详究。然后及于齐民,一体禁止。*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陕西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4页。
清代朝廷也屡颁发诏书,要求对丧中用乐给予处罚:
十三年,诏曰:“朕闻外省百姓丧葬侈靡,甚至招集亲邻,开筵剧饮,名曰闹丧,且于丧所殡时杂陈百戏。匪唯背理,抑亦忍情。”敕督抚严禁陋习,违者治罪。*赵尔巽等著:《清史稿》卷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25页。
从周代直到晚清,一方面是统治者的三令五申,希冀通过道德倡导和法律制裁回复儒家的丧葬礼制,然而丧乐和丧戏在民间却禁而不止,这除了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矛盾外,还应该看到:一方面是皇权社会对民间控制的松弛有关系,另一方面是王朝的法律更多约束文人士大夫,而对民间自然生成的礼俗,往往会网开一面:
守丧之制虽在唐以后的历代法律中加以规定,甚至入于“十恶”大罪,但从实际司法效果来看,其主要的禁约对象仍然是贵族官僚,极少见有惩治平民百姓之不遵守丧法律者。因为守丧之制虽属礼教精粹,但毕竟不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直接利益所在,而且民间习俗之演变,也非法律力量所能禁止得住的。*丁凌华:《中国古代守丧之制述论》,《史林》,1990年01期,第5页。
五、 挽歌——习俗与礼制的冲突

丧礼用乐,有悖于儒家礼制,被历代统治者所不容。汉景帝之孙刘勃,父丧期间奏乐击筑,因此被贬谪到房陵:
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囚……有司请废勿王,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汉书》卷五十三《常山宪王传》,第1855页。
公元前74年,昌邑王刘贺被立为皇帝,在位27天后被赶下王位,其罪状之一就是在先王丧期奏乐: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磬,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汉书》卷六十八《霍光列传》,第2215页。
以礼入法的晋代,将丧中禁乐时间更为延长:
唐宋以来,统治者开始用刑罚规范礼仪,丧中禁乐,相关惩处就更为严厉:
诸闻父母若夫之丧,匿不举哀者,流二千里;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即遇乐而听及参预吉席者,各杖一百。*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宋刑统》一仍其旧,基本就是照搬前者。《宋刑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83-184页)
元代虽然是蒙古人主政,但在对于汉族的管理上,还是秉持了儒家的丧葬制度,对丧中用乐做出了严格规定:
至大三年,皇太子令旨,禁教坊司乐人送殡。延祐元年,江南行台御史王奉训言:“近年以来,江甫尤甚。父母之丧,小敛未毕,茹荤饮酒,略无顾忌。至于送殡,管弦歌舞,导引灵柩,焚葬之际,张筵排晏,不醉不已。泣血未干,享乐如此。昊天之报,其安在哉!兴言及此,诚可哀悯。请今后除蒙古、色目合从本俗,其余人等居丧送殡,不得饮食动乐。违者诸人首告得实,示众断罪,所在官司申禁不禁者,罪亦如之。不惟人子有所惩劝,抑亦风俗少复淳古。”*何绍忞撰:《新元史》卷九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58页。
前已述及,明清两代基本就是唐宋法制的沿袭,对于丧中禁乐,一直都有严格规定。这种禁忌更多表现在道德层面的约束,如明代的官员黄佐撰乡约定:“凡丧事不得用乐,及送殡用鼓吹、杂剧、纸幡、纸鬼等物,违者罪之。”*(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一百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53页。历代王朝从维护正统意识形态出发,都对丧中用乐加以禁止,但却禁而不止:
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息利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丧葬祭,并不许以金银锦绣为饰及陈设音乐。其葬物涉于僭越者。勒禁。”*《唐会要校正》卷三十八,第599页。
九年,诏曰:“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盖闻邻里之内,丧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尝饱,此圣王教化之道,治世不刊之言。何乃匪人,亲罹衅酷,或则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所在官吏,常加觉察,如不用心,并当连坐。”*《宋史》卷一百二十五《礼二十八》,第2918页。

康熙二十二年,左都御史徐元文言:又律文:凡居丧、释服、作乐、筵宴、嫁娶,悉有明禁。而比者士大夫鲜克由礼,或衰绖婚娶、或丧中听乐、或迟讣恋职、或吉服游谒。此皆薄俗伤化,不可容于圣世者,宜并严行申饬。*《读礼通考》卷一百八,第528页。
儒家以为,礼以维护秩序,乐以教化人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莫善于乐。”(《荀子·乐论》)儒家的乐论有着极强的社会功利性:“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礼记·乐记》)那么,对于违礼制行为,就必须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无论丧礼用乐,还是使用挽歌,不但与儒家礼制相悖,更与传统乐论相离。
但人是万物之灵,内秉七情六欲,易受外物激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礼记·乐记》)复杂的情感需要多样表达方式,故歌唱可以表达愉悦,亦可以抒发痛苦:“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之,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礼记·乐记》)《诗经·四月》说:“君子作歌,唯以告哀。”那么,在亲人去世之后,由哭而泣,由泣而歌,由声音到乐音,就属于情理之中了。
儒家重视乐教,但从来都是把音乐视为手段,维护礼制才是真正的目的,比如隋炀帝杨广还在藩邸之时,就装作一副远离声乐的姿态:“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隋书》卷三《炀帝上》,第59页。所以,无论挽歌还是丧乐,必然会凸显儒家礼制与音乐之间内在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是说,无论是反对丧乐,还是认可挽歌,儒家礼法的制定者只是在人性与制度之间首鼠两端,历经三千年,终皇权社会,都没有基于人性与礼法之和谐而建立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
此外,儒家还以为,音乐与朝政紧密相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淫邪”的音乐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前奏:“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荀子·乐论》)违反礼制的音乐必然被儒家所排斥:“故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此三者,君子慎之。”(《荀子·乐论》)基于这种包含有道德基因的乐论,所以在《汉书·五行志》中,梁商等人非礼非时而唱挽歌,就被视为覆灭或者末世之前兆了。
挽歌与丧乐在民间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亦受道家主张影响,道家以为以“齐物我、齐生死”的态度看待死亡,故面对死亡必然会有超脱一面:
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杨柳乔:《庄子译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1页。
在道家看来,死亡并不可怕,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与死是没有差别的。故《庄子·至乐》记载说,庄子的老婆死了,惠子去吊丧,“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另一方面,儒家虽然隆死重生,却也有达观于生死一面,孔子在死亡来临之际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礼记·擅弓上》)所以,好生乐死就成为一种民间的“隐形”信仰。人们通常认为,“寿终正寝”就是最好的结局,老而不死则为“贼”。所以,从民间的生死观来看,挽歌和丧乐以有其生存的土壤。此外,任何社会底层,都会存在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差距较大的底层礼俗,这也是挽歌与丧乐存在的社会基础:
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5页。
挽歌与儒家的礼制相冲突,但因其与世俗人情相契合,所以就能够在儒家礼制的空隙中存在、生长;虽然历代统治者不能接受丧乐,但是丧乐、丧戏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所以往往就是禁而不止,以倔强的生命力存在于世俗社会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六、 挽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挽歌本是丧礼上演唱的丧歌,主题往往是演绎人生之悲苦,生离死别之惨痛。魏晋以来,挽歌创作在体现实用性的同时,作为文人案头的挽歌诗创作则早早兴盛起来。
挽歌诗之所以兴盛,一方面和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如一些帝王甚至为亲近大臣作挽歌诗,以示恩宠:“帝又亲为作碑文及挽歌词,皆穷美尽哀,事过其厚。”*(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外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80页。另一方面,挽歌甚至成为诗人竞展才华邀宠的手段:“及文宣崩,文士并作挽歌,杨遵彦择之,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余人多者不过三四。”*《北史》卷四十二《刘逖列传》,第1551页。
挽歌诗的抒情性,丧礼上的实用性,创作的功利性,成为后世挽歌诗创作的动力所在。以挽歌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历久不衰,最别具一格的是咏史诗、自挽诗、悼亡诗。
一、 咏史诗
史诗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中,东汉班固的《咏史》则是最早以咏史为名的咏史诗,而以挽歌题材创作咏史诗,曹操当为第一人。
东汉末年,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曹操继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写实主义的传统,创作了以挽歌为主题的咏史诗,一首为《薤露行》。另一首则是《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47页。
名为挽歌,实为咏史。故明代钟惺评价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诸葛亮做《梁甫吟》以咏史,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5-606页。
魏晋之际,以古题创作挽歌咏史者甚众,比如前凉君主张骏的《薤露行》,西晋傅玄的《惟汉行》。王粲的《七哀诗》则最为出色: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二,第365页
以挽歌咏史,概因其旋律凄切,更能表达文人的悲悯。而从东汉到东晋四百年间,一方面社会动荡不安,另一面就是瘟疫频发:“大的瘟疫一共有36次,每次瘟疫,死者泰半,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7页。很多的文人士大夫不能永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曹植集校注》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丕感叹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梁)萧统:《文选》卷四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91页。所以,魏晋以来:“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汉魏六朝,风尚如斯。”*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506页。
从文学创作角度考察,这与曹魏政权下形成的文人集团是极有关系的:“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梁)钟嵘:《诗品序》,《中国历代文论》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
以挽歌为主题创作咏史诗,这种风尚的形成,源于挽歌曲调主悲,内容上书写死亡,在变现精神上二者是一致的。前代学者以为:“要之,以内容而论,魏乐府实远不逮汉,盖写作多以个人为主,题材单调,局面狭小,且不足以‘观风俗,知厚薄’也。”*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7页。如果我们考察曹魏时期的咏史诗,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起码是有失偏颇的。
二、 自挽诗
死亡令人恐惧,讳言死亡是普遍的世俗观念,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出现了一种比较奇特的文学现象,那就是自挽之作的出现,其中最著名就是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七,第1012-1013页。
在萧统编著的《文选》一书中,按创作时间顺序,选有缪袭、陆机、陶渊明三人的挽歌,从这三者的挽歌中,可以看出自挽诗的发展过程,如曹魏之际缪袭的《挽歌》:
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文选》卷二八,第406页。

到了陶渊明,则用大开大合的手法,完全以全知视角描绘自己的“出殡”,所以他的诗歌多了悲情,少了板滞之感。不少研究者认为,陶渊明之自挽诗是学习陆机的结果,从二者生存时间上是有可能的,但考察诗歌史,也未必尽然。比如南朝鲍照作自挽诗《松柏篇》,如果按照上述逻辑,那应该就近学习陶渊明,但其在自序曰:“余患脚上气四十余日,知旧先借《傅玄集》,以余疡剧,遂见还。开袠,适见乐府诗《龟鹤篇》,于危病中见长逝词。恻然酸怀。抱如此重病,弥时不差,呼吸乏喘,举目悲矣,火药间缺而拟之。”*《乐府诗集》卷六十四,第931页。

在魏晋时期,自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叔集弟道玙,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临死,作诗及挽歌词,寄之亲朋,以见怨痛。”*(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0-1691页。这种风尚就是魏晋风流的表现方式,其源头就在于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他们崇老谈玄,乐生轻死,就像晋人所作《列子》杨朱篇所言:“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页。
在晋人的眼中,生是暂住,死是长往,他们重生:“死生亦大矣”;但却并不畏死,如王羲之慨叹说:“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兰亭集序》)嵇康的告别演出竟然是一曲《广陵散》,这是何等的潇洒!所以,自挽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魏晋风流土壤上结出的果实。
三、 悼亡诗
挽歌产生、使用于丧礼上,悼亡诗则是作于殡葬之后,一些文人创作的挽歌诗,也是创作于殡葬之后的悼亡诗;故可以说,挽歌诗和悼亡诗的关系紧密,在很多时候是混同的。
一般认为,最早的悼亡诗是《诗经·绿衣》,汉武帝亦有悼亡之作:“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2910页。但是,这些诗歌对后代悼亡诗的创作基本没有影响,而真正成为后世使悼亡诗创作源头的,则是晋代潘岳悼念亡妻的“悼亡诗”,如其第一首:

这首诗歌没有生僻的典故,词句明白如话,他善于使用譬喻,文笔流畅,对妻子的思念娓娓道来,不矫揉造作,故清代的学者评议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潘岳的诗歌创作,无疑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就是人的觉醒。*《美的历程》,第88-90页。
魏晋士大夫不屑物议,故多我行我素之态,于夫妻之情的表达,更能于礼教之外,体现其真情的一面:“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世说新语笺疏》,第1075页。另一则故事是:“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世说新语笺疏》,第1080页。这在阮籍身上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晋书》卷四十九《阮籍列传》,第1361页。
也就是说,潘岳的悼亡诗断然不会产生于经学一统的两汉时期,只有在个人情感淋漓展现之晋代,悼亡诗才能成为诗歌创作的一种选择。在具体写作上,潘岳的悼亡诗明显借鉴了东汉以来的挽歌诗,但清代的赵翼却认为,悼亡诗比挽歌诗起源更早:
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寿诗挽诗悼亡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83页。
赵翼是清代的重要学者,但就挽歌和悼亡诗起源关系的论断,逻辑混乱,结论武断,错漏百出:既然已明确悼亡诗出自晋代的潘岳,为何又武断说源于齐梁?再者,不提挽歌诗的起源,没有比较,就骤下结论说,悼亡诗早于挽歌诗,没有道理么。
悼亡诗远绍《诗经》,汲取了但其重情感的一面,但对悼亡诗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则是挽歌。晋代之后,悼亡便成为悼念亡妻诗歌的特称。自此以后,悼亡之作源源不断,其作品显赫者,有唐代元稹,宋代苏轼,以及清代纳兰性德等诗人。
(作者单位: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