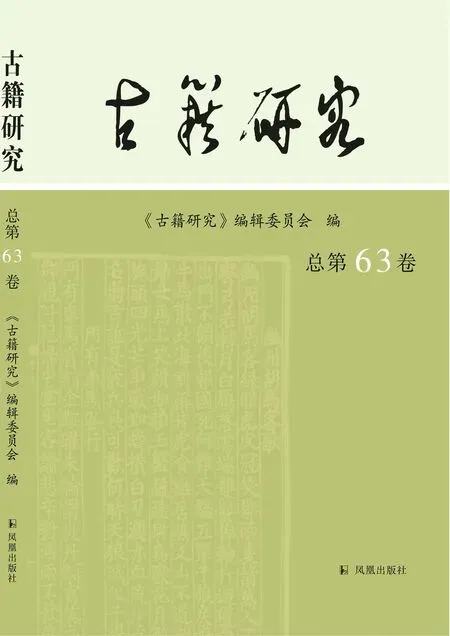遗山集诸本详考*
颜庆余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遗山集诸本详考*
颜庆余
遗山集的流传情况,与陶集、杜集、韩集、白集等相比,并不算复杂,然而,遗山集诸多传本的具体特征、沿承关系和完整谱系,尚未得到详实的考察。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2004年增订本),广泛搜罗众本及其异文,却未能理清诸本的关系和异同,并且忽视现存最古的刊本。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2011年),简明地将传本分成全集系统和诗集系统,对于各传本只是提及,未作具体的描述。著者所撰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以及后来修改发表的论文(2012年),比较完整地描述遗山集诸传本的源流关系,但仍然失之简略。
基于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遗山集诸本(尚存和已佚)逐一考察,撰写翔实的版本叙录,描述各本的具体特征、相互之间的传承和变化,并构建完整而准确的版本谱系。这一考察的目标,不仅是为遗山集的校勘提供版本方面的参考,也是从文献方面呈现遗山诗文在元明清时期的接受史。
(一) 元刊本
1. 中统本
《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交城张德辉类次,蒙古中统四年(1263)东平严忠杰刊本。卷首封龙山人李冶中统三年(1262)十月序、陈郡徐世隆序,卷末济南杜仁杰后序、曹南王鹗中统四年癸亥(1263)七月后引。
此本已佚。诸家序引,具载明刊本。版式特征,据学者推测,保留在翻刻的明刊本中。
刊刻者,李、徐、王三家序引所称“东平严侯弟忠杰”,是元东平行台严实第五子,“严侯”指的是袭职的次子严忠济。遗山与严侯父子交往颇多,集中有《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有序》《约严侯泛舟》诗,其他诗文如《东平府新学记》等,也多次提及。
此本付刻的底本是严忠杰所得元好问家藏稿本全集。李冶序称:“求得其全编,将锓之梓。”徐世隆序称:“求其完集,刊之以大其传云。”王鹗引亦称:“即其家购求遗稿,捐金鸠匠,刻梓以寿其传。”从文献来源上说,此本是完全符合作者之意的权威刊本。
中统本刊行于遗山殁后五六年,此前遗山集的流传情况,李冶序提到:“其遗文数百千篇藏于家,虽有副墨,而雒诵者率不过得什一二,其所谓大全者曾莫见焉。”可知除家藏稿本外,世间已有传抄本。至于这些无名的传抄本对遗山集的流传有无影响,是完全无法确定的。
严忠杰所刻文集包含诗十四卷和文二十六卷,一向并无异议。然而清人施国祁提出:“考徐序有评乐府语,则新乐府五卷,当并入刻,或别自为卷,至明刻乃削去。”(《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例言》)徐世隆序确实提及“乐府”,不过并未明确说明中统本包含词集,只是在论述造物之文时泛泛谈到:“故为诗为歌为赋为颂为传记为志铭为杂言为乐府,兼诸家之长,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断。”并且徐序中的“乐府”,未必指词,也可以是古乐府诗。明清以来著录中统本的书目、翻刻的明刊本序跋,也从未提及词集。因此,施国祁的推论不能成立。
2. 至元本

此本已佚。段引载明刊本。版式特征,据学者推测,保留在翻刻的明刊本中。


至元本所收诗多于中统本,乃曹之谦“续采所遗落八十二首”搜集之力。二者间的具体差别,晚清莫友芝已有考述:“遗山全集,凡四十卷,交城张德辉所类次,中统壬戌严忠杰刻之,在曹刻前六年。其诗居十四卷,凡千二百七十八篇。曹本次叙悉同,唯卷析十四为二十,又增多五言古诗十二篇,七言古诗四篇,杂言三篇,乐府二篇,五言长律一篇,五言律七篇,七言律三十四篇,凡增八十四篇,分续各体之末,合千三百六十篇,为不同耳。”*(清)莫友芝:《郘亭遗文》卷三《遗山诗集跋》,清咸丰至光绪间刻《影山草堂六种》本。
遗山诗的总数,据这两种出于家藏稿本的权威刊本,应是1280首(或莫友芝所计1278首),再加上曹之谦所辑82首(或莫友芝所计84首),凡1362首。传世也有一些集外的佚诗,数量不多,大抵保存在方志等载籍中,因此总数应当相差不远。然而,遗山门人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却记载:“以五言雅为正,出奇于长句杂言,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恩者,又百余篇。”*墓铭石本的文字如此,而《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五收此墓铭,无“五”字。墓铭末尾记大德四年(1300)立石,可见郝经当日撰写墓铭时,遗山集的中统本、至元本皆已行世。清人赵翼由此指出:“郝经作《遗山墓志》,谓其诗共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以写新意者,又百余篇,以今题为乐府者,又数十百篇,是遗山诗共五千七百余篇。今所存者,惟康熙中无锡华希闵刻本。魏学诚作序,谓其购得善本而锓之。卷首载元初徐世隆、李冶二序,于元世祖,仍抬起顶格,是必仿元初刻本。然诗仅一千三百四十首,则所存者,只五分之一而已。岂元初严忠杰等初刻时,即为删节耶,抑华氏翻刻时删去耶?……不知世间尚有全集否?当更求之。”(《瓯北诗话》卷八《元遗山诗》)
郝经的记载和赵翼的统计,从中统本和至元本的来源和数量看,显然不可采信。这里补充莫友芝的相关考辨:“郝经志遗山墓,谓其诗至五千五百余篇,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者,又百余篇,用今题为乐府揄扬新声者,又数十百篇。校此本篇数,乃溢出四之三。而忠杰刻全集,有李冶、徐世隆、杜仁杰、王鹗四序,并谓忠杰就其家求得完帙,而遗山《自题绝句》云‘千首新诗百首文’,盖即晚年定集所作,特举成数,与今传者未为悬殊。然则郝志两‘五’字,盖一二字之伪,曹本即是元诗足本,不必援郝志误文见疑也。”*《郘亭遗文》卷三《遗山诗集跋》。
3. 至顺本
《遗山诗集》二十卷,元至顺二年(1331)余谦校刊本。卷首余谦至顺二年三月十一日序。
此本已佚。未见书志著录或学者提及,可见其流传湮晦。清中叶尚有传本,道光初,施国祁笺注遗山诗集,曾从归安杨凤苞(1754—1816)假读一旧钞至顺本,所谓“架阁本”。道光三十年,张穆校刊遗山全集,自序已称:“而元黄公绍选本,穆又未之见也。”有关此本的有限情况,仅见于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例言》的介绍以及所附余谦序。余谦序亦仅见于施注本附录,今人所编《全元文》亦不及收录。
此本卷数虽与至元本相同,而据施国祁所见,收诗仅七百余首,并非一本。余谦序称此本出于邵武黄公绍手抄,而黄抄本出于何本则不可确知,大抵是出于中统本或至元本的选本。施国祁《例言》曰:“盖选本也。”选录情况已不可考,而施国祁《例言》引杨凤苞语曰:“此集七律不载《岐阳》,七绝不载《论诗》,弃取已失当,他何论耶。”
余谦序曰:“予为补其残阙,正其谬误,凡阅月而告成。”可见黄抄本付梓前经过余谦校订,并留下若干校语,如施国祁《例言》所引:“其《移居八首》注云:元本止七首,今仍之。”校订质量并不让人满意。这条校语后,施国祁指出余谦将八首误作七首的错误:“乃以‘故书堆满床’句,上接‘尚有百本书’句,为一首。岂知八首各用一韵,无转韵者,误也。”
余谦序又曰:“至篇什次第,悉依原本。汇付剞劂,俾海内骚雅共珍之。”明确声明校刊本不改变黄抄本的次序。而施国祁《例言》指出:“乐府次首卷,余略同。”乐府置于首卷,与中统本、至元本置于古体之后、近体之前不同,这大概只能归诸黄公绍的改动。
以上元刊本,凡三种。
(二) 明刊本
1. 汝州本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明弘治十一年(1498)沁水李瀚序刊本。卷首李瀚弘治十一年四月序、段成己引。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如国家图书馆藏周叔弢旧藏本、上海图书馆藏华亭封氏篑进斋旧藏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清王士禛批本(残)、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徐康跋本、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唐翰题跋本等。
此本是旧本重刊。据李瀚《重刊元遗山先生诗集序》:“近奉命巡按河南,复取家藏诗集,属汝州知州高士达刻行之。”虽然没有明言家藏何本,从版本流传情况看,重刊的应该是至元本。后世藏家的误认或考辨,也证实这一点。
晚清唐翰题藏本有手跋曰:“元椠元印本,纸墨与予所藏《战国策》吴氏校注至正十五年第一刻本同,若黄氏士礼居所称之本序有舛错者,则校注之第二刻也。世人不察,以黄氏所称为元刻,不知已落第二义矣。此等元刻最易交臂失之,故特书于册首。丁卯重九又记。”此本后经吴重熹、长尾甲递藏,现藏于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藏书志指出此本实是明刊汝州本:“今李序已为黠估抽去,唐翰题遂定为元刻,函外书签有日本长尾甲手题‘元椠元遗山集,雨山草堂珍藏’,则沿唐氏之误也。”*《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86页。
唐翰题误将抽去重刊序言的汝州本当成元椠元印本,这说明汝州本在重刊时尽可能保留至元本的版式特征。莫友芝《影山草堂六种》之《郘亭遗文》卷三著录耕钓草堂影抄汝州本,也提出:“此之细行密字,盖犹元式也。”恰好唐翰题手跋也提及这一影抄本:“《遗山集》有密行小字本,不分诗体。曾见独山莫偲老案头影抄本,惜未及一借校耳。鹪安记。”所谓“元式”,叶景葵(1874—1949)有更明确的描述:“己巳冬日,有故友以弘治本《遗山诗集》求售,为二十卷本,前有稷亭段成已引,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遇‘恩纶’等字,或抬头,或空格,当遵元刻款式。疑即郘亭所见之沁水李瀚汝州刊本,惜无重刻人序跋。”*叶景葵:《卷盦书跋》,顾廷龙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3-134页。另外,潘景郑(1907—2003)著砚楼藏有汪氏古香楼旧藏汝州本,称:“字体犹不失元椠意味,为可宝也。”*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2. 开封本
《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明弘治十二年(1499)李瀚序刊本。《附录》一卷,海陵储巏辑。卷首李冶、徐世隆二旧序,储巏弘治十一年冬十月序、李瀚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序,又附《储太仆先生手简》(弘治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与李瀚书),卷末杜仁杰、王鹗二引、丹徒靳贵弘治十二年后序。卷端题“颐斋张德辉类次”。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大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卷首序跋之后,既有《遗山先生文集总目》,只列出各类文体,又有《遗山先生文集目录》,列出分体编次的详细篇目*按,《总目》应有串行的讹误,第九行“七言绝句 宏词”应在第五行“七言律诗 五言六言绝句”后。。

卷末靳贵弘治十二年序,《四部丛刊》影印本已脱去,诸家藏本大抵如此,故皆著录为弘治十一年李瀚刊本。惟傅增湘所见尚存靳序,故《藏园群书题记》著录为“明弘治十二年戊午刻本”,又由靳序所载,提出此本的实际刊刻者并非李瀚:“卷末又有弘治己未翰林院编修靳贵后序,言‘太仆爱其文,尝手为讐校,故视他本为善。侍御李君叔渊出按河南,始命太康杨令溥录之,而属方伯徐公用和、仰公进卿刻梓以传云’。据此始知刻书者实为徐、仰二君,叔渊不过为之倡率,今则人只知为李瀚本矣。”*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五《明弘治李瀚刊本遗山先生文集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65页。案靳贵序,学界罕见称引,孔凡礼辑《元好问资料汇编》、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增订本)皆未收此序。藏园所见之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三著录马寒中旧藏明抄弘治本,有靳贵跋其后。靳贵序,亦载其《戒庵文集》卷六,题作《元遗山文集后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45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靖十九年靳懋仁刻本),文字略有不同。集本不署姓氏、官职及时间,关于刊刻者,也只提及徐氏,而删去仰氏。刻书者徐恪和仰昇,皆见《河南通志》卷三十一《职官二》,二人皆于弘治间任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升右布政使,即靳贵所称“方伯”,李瀚序所称“藩臬诸公”。徐恪字公肃,一字用和,江南常熟人。仰昇字进卿,江南无为人。河南布政使司驻开封府,刊刻之事想必就在驻地,因此这里称此本为开封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著录一汝州本,有何焯跋语称:“汝州所刊遗山诗视归德所刊全集为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80-1081页)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亦著录此何焯跋汝州本。何焯所谓“归德所刊全集”,大概是认为刊刻的地点是河南归德,或别有所据。不过,明前期归德降府为州,属开封府,即使此本刊于归德,也可称为开封本。。
此本同样是旧本重刊,是出于储巏传抄的新安程敏政所藏善本。程敏政藏本是否即是中统原刊本,储、李二序未透露,但由此本保存的元人序引和卷端所题,即使不是原刊,至少也是出于原刊的传抄本*傅增湘称:“据储太仆手简,言得秘本于礼部程公,录而藏之,李氏即据以墨板。是所得亦钞本,仍未见中统本也。”(《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五,同上,第766-767页)。
汝州本与开封本,素来都称李瀚刊本,且都有弘治戊午李瀚序,不免令学者混淆。潘景郑还为此作出考辨:“因疑瀚先刊二十卷本,继得储本,再刊河南;而提要所据,则是后来一本耳。今藏家于此本混淆莫明,故不得不详为辨正之。”*《著砚楼书跋》,第249页。实际上二本的版式特征,除每行字数外,也是相同的。唐翰题等藏家都认为汝州本保留元刊特征,由此推论,开封本同样如此。
3. 潘是仁本
《元遗山诗集》十卷,明潘世仁编《宋元名家诗集》本,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本,又有天启二年(1622)重修本。前有李维祯、焦竑二序。卷端题“明潘是仁讱叔甫辑校”。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
此本今存。国家图书馆等藏。
此本的来源、编次、数量等情况,俟考。潘是仁《宋元名家诗集》的编纂情况,可参《郑振铎书话》。
遗山诗集十卷本,除此本外,尚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浙江图书馆藏清抄本。又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一种旧抄本,每半叶九行十九字,版心题“竹北亭手钞”五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81页。,从行格看,或是潘是仁本的传抄本。
4. 汲古阁本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如上海图书馆藏沈钦韩校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周半樵跋本等。通行有民国涵芬楼影印《元人十种诗》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本。翻印本有清光绪六年(1880)南海黎维枞刊本,卷末附考异一卷;清宣统二年(1910)成都茹古书局刊本,卷末山阴周肇祥跋;民国九年(1920)曹氏刊本。

至元本既已失传,这里比较汲古阁本与汝州本的差异。版式上,从汝州本的细行密字,汲古阁本改成疏行大书,版心、鱼尾、框栏也都不同。文字上,叶景葵已经指出汲古阁本擅自删改卷首段引,实际上,汲古阁本误改的例子还有很多。狄宝心《元好问诗编年校注》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却经常要依据汝州本、开封本校改,这就说明底本存在大量讹误。
以上明刊本,翻印者不计,凡四种。
(三) 清刊本
1. 剑光阁本
《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无锡华希闵剑光阁写刻本。卷首蔚州魏学诚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上浣序。卷首《遗山先生文集目录》,卷端题:“无锡后学华希闵重校订。”每半叶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翻印本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定襄李镕经京都贵文堂刊本。卷端题“定襄后学李镕经重刊”。
遗山诗文全集,元刻有严忠杰中统本,明刻有李瀚开封本,此本为第三刻。中统本久已不传,此本附有储巏附录一卷,付刻底本应是开封本。附录资料,华希闵略有增补。
此本在清代流传颇广,清道光初施国祁指出:“此刻盛行,传是楼所藏,查初白所评,赵蓉江所易,赵云松所说,皆是。”*(清)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卷首《例言》,《续修四库全书》1322册影印清道光二年南浔瑞松堂蒋氏刊本,第105页。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集部号字二格)所著录,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所评校,赵翼《瓯北诗话》卷八所论说,都是剑光阁本。赵蓉江,俟考。
2. 南昌本
《元遗山诗集》八卷,清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南昌万廷兰刊本。卷首《金史》本传,传后有万廷兰刻书题识。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尚无影印本。
此本的来源,应该是剑光阁本或开封本。万廷兰题识称:“遗山诗久无专刻,兹于全集中录出,校订而付之梓。”可见他并不知道汝州本、汲古阁本等单诗本传世,只能从四十卷全集本中录出十四卷诗,并重订成为八卷。清人张穆已指出:“南昌万廷兰本,系从全集摘出,故于曹益甫所增之八十余首,概从缺佚。”*《元遗山先生集》卷首张穆序,清道光三十年刊本。
这本是毫无疑义的问题,然而,沈钦韩(1775—1831)却提出:“汲古阁本《遗山集》二十卷,兹本合为八卷,既不合旧时卷目,而于阁本每卷后,或缺数首,有多至二三十首者。不知何故。盖抄掇合卷时,或任意删削,或抄胥偷刊,未可知也。既从阁本对勘一过,因识之。嘉庆庚辰七月,沈钦韩记。”*国家图书馆藏万廷兰刊本沈钦韩手书题记。此引自孔凡礼辑《元好问资料汇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偶阅《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著录此本,对沈钦韩所谓“删削”情况作出详细的描述:“此本与汲古阁刻二十卷本各篇排列顺序略同,然如《读书山月夕》一首后,汲古本有《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及《寄题沁州韩君锡耕读轩》数首;《王学士熊岳图》一首后,汲古本有《赠史子桓寻亲之行》一首;《付阿耽诵》一首后,汲古本有《挽赵参谋》二首、《嗣侯大总管哀挽》二首、《答弋唐佐》《不寐》《送杨叔能东之相下》等篇;《张村杏花》一首后,汲古本有《送仲希兼简大方》等二十九篇,此本皆已删去。是此本非但擅改卷次,且任意删落篇章,而致编次歧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第287页。
这种疏谬是不明白遗山集流传谱系的表现。以至元本为祖本的单诗本,由于曹之谦的续采,所收诗多于以中统本为祖本的全集本。从全集本中摘录而成的南昌本,收诗数量自然要少于单诗本系统的汲古阁本。实际上,南昌本卷首目录标出各卷数量,如卷一“五言古诗一百二十九首”,卷二“七言古诗七十八首”,卷三“杂言三十六首”“乐府四十八首”等,正是全集本收诗的数量。万廷兰所作的改变,只是卷数的合并。前引《书志》所举某某篇后,汲古本有某某首,实际上是曹之谦续采的篇目,这算是徒增淆乱的认真考证吧。
3. 瑞松堂本
《元遗山诗集笺注》十四卷,施国祁笺注,清道光二年(1822)南浔瑞松堂蒋氏刊本。卷首依次是原序、例言、本传、墓铭、世系、年谱。原序包括诸传本所载序引。例言,考订旧本、校勘、佚作等,凡十五则。本传、墓铭,皆附有考辨。世系、年谱,均出施氏所撰。卷末有附录(储巏辑、华希闵增)、补载(施国祁辑)各一卷。卷端题“元张德辉颐斋类次”“后学乌程施国祁北研笺”“蒋炳枕山校”。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行三十三字,黑口,无鱼尾,左右双边。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翻印本有清道光七年(1827)苕溪吴氏醉六堂刊本、苏州交通益记书馆刊本。又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清宣统三年、民国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影印本有《续修四库全书》1322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又有凌朝枢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1989年修订版)。
此本所用底本,据卷首《例言》,是清代前期盛行的剑光阁刊本。《笺注》十四卷的卷数,也是沿续全集本所收诗的编次。又据所谓的眠琴山馆藏至元本,补入曹之谦续采诗*施国祁从眠琴山馆借读的所谓“元刻曹益甫至元庚午本”,因为《南浔刘氏眠琴山馆藏书目》失传,已无从考定其真假。从至元本流传湮晦的状况看,眠琴山馆所藏极有可能与唐翰题藏本一样,是抽去李瀚序而冒充元刊的明刊汝州本。傅增湘指出:“惟李瀚同时别刻有《诗集》二十卷,写刻视《文集》为工,余曾藏有一帙,不知者咸以为元刊。余颇疑施国祁所言暝琴山馆藏元至元本即是刻也。”(《藏园群书题记》,同上,第768页)另外,施国祁《例言》提及清中叶以前所有遗山集刊本,唯独不及汝州本,这也是可疑之处。。参校的本子,包括至元本、至顺本和开封本,又参考《初白庵诗评》的校语。此本只收诗,却不属于单诗本的系统,而是全集本的后裔,并杂有单诗本的血统。
施国祁没有交待底本选择的理由,为何是晚出的华希闵本,而不是元明旧本,为何是收诗较少的全集本,而不是收诗更全的单诗本。由《例言》所述推测,大概华希闵本是归安夙好斋主人杨知新(号拙园)所赠,便于用作工作底本,而开封本、至元本是从刘桐眠琴山馆借读,至顺本既非足本又是从杨凤苞(号秋室)假读,只能用以参校。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施国祁原定笺注诗文全集,所以选用全集本,而最终完成的只有诗笺。稍晚的张穆提到:“近乌程施北研氏,熟于金源掌故,有《遗山诗文笺》,极精博。《诗笺》初梓,吾友沈子惇即以相赠,近亦印行。《文笺》仍郁未出也。”*《元遗山先生集》卷首张穆序。
瑞松堂本是最后一种单诗本,也是古代仅有的经过全面考订笺注的遗山诗集。清末灵石耿文光(1830—1908)准确地指出:“此本只录其诗,详为之注,订讹补阙,其功不少。前有总目、本传、墓志、世系、年谱。读遗山诗者,以此本为最佳。”*(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十九,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影印《山右丛书初编》本,第3954页。
4. 阳泉山庄本
《元遗山先生集》四十卷,《续夷坚志》四卷,《新乐府》四卷,附凌廷堪撰年谱二卷、施国祁撰年谱一卷、翁方纲撰年谱一卷、附录一卷、补载一卷。清道光三十年(1850)平定灵石杨氏阳泉山庄刊本。卷首张穆序。卷端题“元张德辉颐斋类次、平定后学张穆廉友校梓”。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下题“阳泉山庄”四字。
此本今存。公藏书目著录多本。翻印本有清光绪三年(1877)京都同立堂刊本、清光绪八年(1882)京都翰文斋刊本等。又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卷前宣统元年吴重憙序,卷末有缪荃孙光绪乙巳九月刻书跋。前有牌记:“灵石杨氏原刻本光绪八年京都翰文斋书坊印行。”内封又题:“遗山集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补于江宁。”《新乐府》卷五版心下题:“石莲庵补刻。”可见石莲盦本是据翰文斋本重印,又补刻缺佚的《遗山新乐府》第五卷。
此本所收遗山著述各种的底本,叶德辉(1864—1927)《郋园读书志》著录时指出:“平定张石舟穆刻《元遗山集》,为遗山集大全之本。其诗文四十卷,从明弘治李叔渊本、康熙华希闵本、毛晋汲古阁本、南昌万廷兰本、乌程施国祁注本,勘定伪误,别白是非,各类之后增补续编,凡遗山诗文佚见他书者,此本悉详载之,可谓留心文献者矣。《续夷坚志》四卷,从余秋室刊本重刻,旧传只写本。《新乐府》五卷,《四库》未收,阮氏元《揅经室外集》着录,此亦从华本再刻。《年谱》三卷,施本从《诗注》本,翁本从《苏斋丛书》本,凌本从汉阳叶氏钞本,皆善本也。”*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九,杨洪升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18-419页。除词集所本并非华本外,叶德辉的描述是准确的*关于词集底本,张穆序只说:“乐府五卷,阮太傅《揅经室外集》载有提要,而《文选楼书目》初无其名。闻汉阳叶氏有写本,数从相假检,未获也。”既未获汉阳叶氏写本,又不再交待另外的来源。而叶德辉所说的华本,实际上不收词集。。
张穆校本收录遗山诗、文、词与小说,是遗山自著的首次汇集刊行。张穆序自称:“遗山一家之业,其存于今者,约略备矣。”傅增湘也指出:“盖遗山遗著五百年来至此乃蔚然萃为钜观,其致力可谓勤且卓矣。”*《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五,第767页。
5. 读书山房本
《元遗山先生集》四十卷,卷首一卷,《续夷坚志》四卷,《新乐府》四卷,附凌廷堪撰年谱二卷、施国祁撰年谱一卷、翁方纲撰年谱一卷、附录一卷、补载一卷,赵培因考证三卷。清光绪七年(1881)忻州读书山房刊本。卷端题“照平定张穆阳泉山庄本校梓”。卷首方戊昌《重刻元遗山先生集序》,卷末赵培因《重刻遗山先生集书后》。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无鱼尾,四周单边。
此本出于张穆校辑的阳泉山庄刊本。方戊昌序称:“平定张硕洲苦心搜集,萃其诗文、乐府、年谱及《续夷坚志》,都为一集,刊行于时。今甫三十年,访之平定,询之京都,版已无存。”又称:“检郡中所存张硕洲所裒全集,加以校正,重付手民。”*阳泉山庄本,光绪八年尚有京都翰文斋重印本,可见板片尚存北京,而方戊昌光绪七年却称:“访之平定,询之京都,版已无存。”是未见而径称无存。重刻的表现,一是版式的变化,二是重加校订,并增补若干佚作,即赵培因《书后》所说:“爰取郡人士所校硕洲原本,与司孝廉冀北、年友李计部希白、张明府坪、胡文学警三及王君覆加商订,脱者补之,讹者更之,疑者阙之,其有各书互异与文有可商者,别为考证三卷,以俟博雅君子辨正焉。至编辑次第,一依硕洲之旧。惟补载中收录稍滥及与本书重复者,酌删三则。其增入集内者,有五律四首、七律一首、词四首,则郝孝廉曼修、子才两君暨家用九兄新从诸书所采得也。”
6. 汗青簃本
《遗山诗钞》三卷,樊宗源辑。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内封牌记:“光绪癸未季秋叙州汗青簃刊。”附清光绪十年庆符樊宗源序、《金史》本传及郝经所撰遗山墓铭。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有藏本。
据樊宗源序,此本系摘自阳泉山庄本,虽仅三卷,遗山诗悉数收录。卷上,五古、七古、杂言;卷中,乐府,五律、七律;卷下,五绝、七绝。
以上清刊本,翻印者不计,凡六种。
以上元明清三代刊本,翻印者不计,凡十三种。
(四) 旧抄本
在遗山集传本中,诸刊本流传有绪,收录完整,又迭经学者校订,显然构成权威的流传谱系。然而,无论刊本如何盛行于世,载籍可稽的抄本始终不绝如缕。在中统本之前,除家藏稿本外,已有作为副墨的抄本行世。在中统本、至元本、至顺本三种元刊本问世后,明代中期李瀚仍然感到刊本不易获见,书在人间,多是抄本。在李瀚倡率的汝州本、开封本先后付梓后,文徵明后人仍然世代收藏楷体精写的玉兰堂抄本,其他明人旧抄本甚至流传至今。而在有清一代,遗山集从康熙至光绪间先后刊行五次,并产生更多的翻印本,清抄本仍有数种幸存至今,并得到学者的批校和珍藏。
这些抄本,无论已佚或尚存,无论出于名家所书或佚名所写,都表明手抄本文化及其相应的阅读方式在印本时代的持续存在和影响。在遗山集诸传本中,抄本的校勘价值也许不应高估,然而诸多抄本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此。一方面,在遗山集近八百年的流传中,抄本与刊本并存互补,共同作为知识阶层可以获取的书籍资源;另一方面,在刊本的流传链条中,抄本有时成为其中的一环,已佚的旧刊本通过其传抄本而得到重刊。
这些经常来源不明的抄本,除名家抄校批跋外,一般不见诸著录,也不会得到珍存,幸存于世的十数种远远并不能反映实际的数量。这里只依据相关资料介绍其中五种。
1. 玉兰堂旧钞本
《遗山诗集》二十卷,明长洲文氏玉兰堂旧钞本,楷书字体,四册。
此本未见书志著录,仅见于嘉兴钱仪吉(1783—1850)《衎石斋记事续稿》卷七《跋遗山诗集玉兰堂旧钞本》:
“《遗山诗集》,写本四册,前后有文嘉、休承、文彭、文掞、宾日诸印文。又有玉兰堂图书记印。第四册前页,有十二砚斋及东吴文献衡山世家印,知为文氏故物。楷法劲秀,不必定是衡山,要出善书人手。史婿叔平得之山阴,喜以示予。遗山诗单行本,以至元庚午刻曹益甫本为最古。昔予里居,尝从友人借观,凡二十卷,前有段氏序。诗凡千二百余篇,又续增八十余篇。今此本亦二十卷,篇数略相当,知从至元本钞录者。”*(清)钱仪吉:《衎石斋记事续稿》卷七,《续修四库全书》1509册影印清道光刻咸丰四年蒋光焴增修光绪六年钱彝甫印本,第187页。
钱仪吉跋称,文氏玉兰堂旧钞本出于至元本。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不过,从文徵明(1470—1559)的生活年代看,他所抄录的也可能是重刊至元本的汝州本。另外,与施国祁年代相近的钱仪吉,他所经眼的所谓至元本,可能也是汝州本。
钱仪吉跋记述卷中钤印,可见文氏世代珍藏此旧钞本,从明代嘉靖、万历初的文彭、文嘉(字休承),至清初的文掞(宾日、十二砚斋)。此本后归史叔平,今未见。
另外,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一种玉兰堂旧藏开封本遗山集,称:“卷首有玉兰堂、辛夷馆暨季振宜印记,盖文氏旧藏后归沧苇者。”*(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二,冯惠民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99页。
2. 汲古阁藏旧抄本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元遗山诗集八本。旧抄 三两二钱。”(清嘉庆士礼居刊本)在这部鬻书目录中,毛扆没有提供这部旧抄本的更多特征,或许是汲古阁所刊遗山诗集的底本。今未见。
3. 士礼居藏明钞本
《元遗山集》三十卷,明钞本,何焯校,汤燕生、黄丕烈递藏。
此本今未见,仅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著录:“遗山集元刻仅见五砚楼曾藏十余卷,昔年借校家传钞本,知近本校明刻录出居多。是本为明汤燕生严夫氏所旧藏,亦出自明本。其朱笔字的系何义门手迹。较他本多是正,视元刻亦在伯仲间矣。嘉庆乙亥午月得此因识,荛圃。”*(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六,清光绪间潘祖荫刻本。
此本卷数与诸刊本皆不合,来源无考,下落不明。黄丕烈跋声称此本出自明本,想必是开封本,而脱去十卷;又提出此本经何焯校订后,文字接近他曾借校的五砚楼旧藏元刊本十余卷。概言之,黄丕烈跋提供的信息比较混乱,与可考的遗山集都不相吻合。
4. 耕钓草堂旧钞本
《遗山先生诗集》二十卷,吕留良南阳耕钓草堂抄本。前有莫友芝跋。三册。每半叶十二行,行三十字,无栏格。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
莫友芝同治七年戊辰(1868)在苏州书肆购得此本,手跋略曰:“此影钞明弘治戊午汝州重刻曹益甫所编二十卷本……此之细行密字,盖犹元式也。”又曰:“此耕钓草堂影抄旧本,旧有段稷亭氏至元庚午为益之二子刻书引,亦载叔渊此书序,而云附,则其据汝州本或至元本,未可知也。……此影手虽未致佳,然殊不草草,细行密字,矧大资我舟车耶。”(《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附录卷一)
此本后归南浔刘氏嘉业堂。《嘉业堂藏书志》卷四著录,缪荃孙、董康所撰提要,记述此本相关特征:“此本密行小字,书口书‘南阳讲习堂钞书’,或作‘南阳耕钓草堂’,或作‘南阳村庄’,吕晚村藏书。有莫子偲手跋并其父子印记。”(缪稿)“此本密行小字,为南阳讲习堂抄书。……有‘莫友芝图书印’‘子偲’‘莫印彝孙’‘莫印绳孙’诸记。”(董稿)而刘承幹所撰提要对莫友芝的判断提出异议:“按元遗山诗无小字,此本亦非影钞,跋语过夸,不足据。”(刘稿)*缪荃孙、吴昌绶、董康撰:《嘉业堂藏书志》,吴格整理点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98-599页。从行格上看,此本确非汝州本的影抄,抄录的来源也未必就是汝州本,也可能是汲古阁本。
5. 静乐故家藏旧抄《遗山诗集》
清乾隆五十九(1794),忻州知州汪本直修葺元遗山墓,重建野史亭,并访求遗文。据山西学政戈源记载:“刺史汪公既修遗山先生墓,复博求遗文,于静乐故家,得旧抄先生诗,并此《世系略》一则,今摘出,附刊于此。督学使者河间戈源识。”*(清)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附佚名《遗山先生世系略》后戈源按语,清咸丰三年(1853)南海伍氏刊《粤雅堂丛书》本。
汪本直于静乐故家访得的旧抄遗山诗,同时静乐人氏李銮宣在其题墓诗自注中同样提及:“旧钞《遗山诗集》,每首下注作诗岁月,较世行本为详,先大父中宪公所藏书,余家故物也。余索米长安,离里门几及二十年,未曾目睹此本。今为守愚先生(汪本直号守愚)购去,缘是重其葺遗山墓。表兄冯仲匢学博来京师,为余详言之。余闻是举,既叹祖研之不能守,而又深喜官兹土者表章先贤之功不朽云。”*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附《忻州刺史守愚汪君重修元遗山先生墓诗》所收李銮宣三首其三自注,同上。
李銮宣提及,此旧钞《遗山诗集》的特点,是“每首下注作诗岁月,较世行本为详”。如果所言属实,这应该是具有很高价值的旧抄本。遗山集自张德辉编次(甚至是家藏稿本)以来,都如翁方纲所讲的“粗分各体而时地则未尝一一细考也”,所收诗也大多不注年月。翁方纲显然应该知道此旧钞本,李銮宣的题墓诗就附录于翁方纲所撰年谱之后,并且翁方纲在年谱附录中也提到“静乐旧抄遗山诗后世系略”*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附录,同上。。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访得旧抄的汪本直、旧藏的主人李銮宣,还是撰写年谱的翁方纲,都没有提供有关此旧抄本的更多信息。近读忻州人氏张俊赟《李銮宣野史亭歌咏元好问》一文,称:“(汪本直)从静乐县五家庄李銮宣的老家购得渤海戴明说手抄《遗山诗》《遗山先生世系略》和《元遗山墓图》。”(文载忻州传媒网)所谓“渤海戴明说手抄《遗山诗》”,不知所本,姑记于此,俟考*戴明说,字道默,沧州人,工书画,生活于明末清初(详参张玲:《戴明说生平及作品创作年代考证》,载《美苑》2010年2期)。所谓戴明说手抄本,年代应定于明清之际。。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宋以后师古诗学研究”[12YJC751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