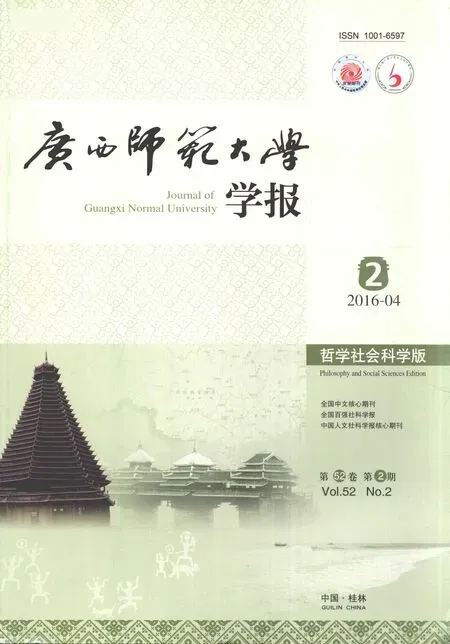《孤独者》新论
——中西文化之“个”的艺术熔铸
蒋永国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孤独者》新论
——中西文化之“个”的艺术熔铸
蒋永国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摘要]魏连殳和“我”都有欧洲近代个人主义的痕迹,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个”(叛逆者)的因素。但已有的研究大都分别从中西或古今这两个维度进行,缺少把中西文化之“个”并置的视野,这肢解了作为艺术有机体的《孤独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现实因素促使鲁迅在精神深处与他所认可的中西文化之“个”发生深度关联。在此基础上,鲁迅通过现实和历史细节的植入,把中西文化之“个”并置在《孤独者》中,并实现了中西文化之“个”的交汇和相互改编,最终以一个有机的艺术体表征了他真诚的生命律动和复杂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孤独者》;中西文化;“个”;艺术合成;鲁迅
一、《孤独者》与中西文化之“个”发生联系的现实因素
《孤独者》写于1925年10月17日,相隔4天后鲁迅又创作《伤逝》,这段时间也正好是《野草》创作停笔的时间。《野草》中的《死后》写于1925年7月12日,紧接着下一篇文章是《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中间这5个月时间鲁迅没有延续《野草》的写作。《野草》停笔这段时期,鲁迅创作了《彷徨》中的4篇小说,即《孤独者》、《伤逝》、《兄弟》(1925年11月3日)和《离婚》(1925年11月6日)。紧接着《孤独者》前面那篇小说是《高老夫子》,写于1925年5月1日,相隔5个月。也就是说,从7月到10月份,鲁迅没有写《野草》中的散文诗和《彷徨》中的小说,只写了一些杂感(从《华盖集》中可以看到)。那么,1925年10月17日前三个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是《孤独者》产生的具体背景。第一个要提的事情是女师大学潮。从7月到10月这三个月,女师大学潮到了白热化阶段。鲁迅在这场斗争中一直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和杨荫榆及北洋政府展开斗争。由于斗争激烈,鲁迅和学生们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鲁迅日记这段时间多有赴女师大或女师大维持会的记录,其中8、9月份的日记最多这样的记录[5]575-584,所以客观上没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受女师大学潮的影响,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职位被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8月12日解聘。鲁迅不平,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章士钊打官司。1926 年2月23日平政院作出裁决,鲁迅胜诉,他在教育部的职位得到恢复。从这个事件我们能够感到北洋政府对进步知识分子的压力,从鲁迅的作品中也能充分感到他对此深有体会。第二个要注意的是鲁迅的婚姻爱情问题。许广平和鲁迅于1925年3月开始通信,到10月份就不仅仅是师生情谊了。这表面上看对鲁迅是好事,其实却加重了鲁迅的精神负担。他家里有妻子朱安,和许广平的关系如果公布,他将遭受到道德攻击,让他在道德上陷入困境。直到许广平给鲁迅明确的鼓励,他才最终接受了这段师生恋,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放下心理的重负。第三个要提到的是鲁迅的病。1925年9月,鲁迅肺病复发,鲁迅日记从本月到12月共有17次“往山本医院诊”的记载,平均一个月4次去医院,最多的是10月份,共6次[5]581-597,说明10月鲁迅病情最严重。一般来说,人生病容易产生孤独感,况且鲁迅这病在当时是顽疾,这对鲁迅心情的影响可以预料。他在此时写《孤独者》这样的文章也就比较合理了。
上述这些现实背景是《孤独者》感性细节的直接来源,比如魏连殳患肺病和咯血就直接与鲁迅自己的病有关。同时,孤独的情感基调也是源于此时鲁迅的真实感受:政府的反动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爱情给他带来了道德压力;病魔给他带来了生命压力。它们合起来围剿鲁迅,使他产生深刻的孤独感,进而想把自己包裹起来,独自舔舐伤口。鲁迅觉得《孤独者》是写给自己的小说,不便公开,所以在《彷徨》出版之前没有发表这篇小说,有人从鲁迅当时所处的现实对这个问题作过详细分析。[6]这种现实带来的孤独感表面上看是鲁迅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但是何以鲁迅有这样的觉察?这只能从鲁迅的文化精神偏好上找原因。我们知道,鲁迅对中西文化中的异端性元素非常关注,无论是绍兴生活阶段还是外出求学,都表现了这一点。鲁迅1887年入私塾后,不大喜欢传统的授课内容,对神话、绣像小说和稗官野史比较关注。同时,大禹、墨子、王充、勾践和徐文长这些极具个性的先贤也植入鲁迅的内心世界。在南京求学时期鲁迅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沿着进化论的思路又认可了施蒂纳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此后又高度肯定了具有极强个人主义特点的摩罗诗人。1909年回国后他又沉入古代,在整理乡邦文献和小说史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异端文化的体验,其中对魏晋名士和一直受到排挤的传统小说特别关注,而在关注魏晋名士的时候又对孔融、嵇康和阮籍等人投入了更深厚的情感。《孤独者》产生的时候是鲁迅在北京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现实所赋予他的孤独感及人生体验很容易把鲁迅与他所接受的这些中西文化之“个”连接起来,因为孤独、孤傲是中西文化之“个”的基本特征。这些现实因素的注入加深了鲁迅对中西文化之“个”的认同、修正和反思,从而它们便共时地以矛盾激越的状态深刻表征着他的精神世界。通过小说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到中西文化之“个”的并置、交汇及它们的相互改编。
二、《孤独者》中的西方文化之“个”
“狂人”作为“个”的文学化表现在《狂人日记》中还有凌厉之气,他和超人、摩罗诗人、精神界战士之间的相似度还很大。可是在《孤独者》中,他们已经逐渐退隐到文本的精神深处了,但这并不是说鲁迅从西方文化中所获得的“个”消失了。只要作细心的文本考察,依然能够理出西方之“个”的文学化痕迹。
小说中无论是魏连殳还是“我”都有西方之“个”的影子。先来看魏连殳。这位主人公一出场,就很异样,他悖论地存在着:学的是生物却教历史,平素不理人却爱管别人的闲事,破坏家庭又极爱他的祖母。学生物学表明魏连殳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但去教历史,这就是在事业上与传统形成的对抗;平素不理人是违背儒家之礼的,但他却是真正关心别人,这是与传统虚伪的礼节相对抗;破坏家庭明显是反抗传统家庭对人的束缚,可是他又依恋自己的祖母,极尽孝道,这是他在家庭观念上的矛盾。所以,魏连殳在寒石山就被别人看成一个外国人。出场的这个交代,就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人。从思想内蕴上看,他反传统;从小说技巧上看,这为读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形成了认识魏连殳的期待视野。在他祖母死后,族人认为他是“新党”,不讲道理,也不会同意他们的丧葬仪式,所以之间会有一场争斗。虽然最终没有争斗,但却透露了魏连殳对待传统的战斗姿态。在S城教书,大家也认为他是“新党”,他写文章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于是小报上就有人匿名攻击他,他不久就被校长辞退了。这是反对传统而被传统势力清算,结果是没了工作,和吕纬甫一样将要遭受生存的困境。从这些外部表现看,魏连殳继承了狂人的“个”性,即超人、摩罗诗人和精神界战士的基本品格——反传统。同时,魏连殳具有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所塑造的人格特征,他爱帮助别人。后来我们知道他对他祖母的爱并非因为血缘关系。他祖母死后他像狼一样地嗥哭,他自己的解释是: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的,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苦,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7]100
这个解释是对他祖母作茧自缚的哀伤。在魏连殳看来,他祖母是一个自己让自己陷入孤独的人,她的整个生命都是自己酿造的苦酒,而且像他祖母这样的人还那样多,他不是仅仅为他祖母哭泣,而是为所有像他祖母一样的人哭泣,包括他自己。由此可知,魏连殳的爱类似基督教式的博爱,他祖母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他的爱不是像大家看到的那种传统家庭孝道。在“五四”时期,鲁迅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讲到:“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需一面清算旧账,一面开辟新路。”[8]145随顺长者,就是尽孝道,解放幼者就是再不能像长辈那样对子女有绝对的权威。与此相对应,清算旧账就是打破父辈对子女绝对权威的做法,只是对子女尽义务,同时子女也不要因为孝道而做无谓的牺牲。这样的父子关系奉行个人人格独立,不再是宗法伦理关系。魏连殳对祖母的关系从实质上看不是过去的宗法伦理关系,他很憎恨这样的关系,他讨厌族人在他祖母死后对他老家房屋的觊觎。魏连殳践行的人格精神是西方近代个人主义的,挣脱家庭束缚,具有基督教式的博爱。如拜伦支持并参加希腊的独立战争,莱蒙托夫声援异民族的反专制,都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放大。他们所透露的人格精神正是鲁迅早年在日本所认可的,魏连殳在这一点上延续了鲁迅在日本获得的这种思想。反抗传统的“个”和爱别人在摩罗诗人身上也统一在一起。小说中把上面这些细节通过“狼”这样一个意象又集中起来,用象征性的手法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涵。薛毅、钱理群认为:“狼,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物,与驯化了的狗形成二元对立。狼喻指着反叛的精神,但在一种重秩序、教化,将温顺的狗作为仁义象征的中国社会中,反叛的狼是受到敌视的。所谓‘受伤的狼’便喻指着一种反叛的精神在中国社会中被视为异类、被攻击、被驱逐而伤痕累累的必然命运。魏连殳便是这样一只狼,一头闯入了一个只需要驯服的狗而视狼为异类的环境中,孤独、挣扎、嗥叫、绝望,直至死亡。”[9]这个解说把握到《孤独者》的深层思想,也从侧面证明了魏连殳和鲁迅早年从西方获得“个”精神之间的血缘关系。
小说中的“我”也是一个具有“个”性的人,他在山阳教书,也写文章,结果和魏连殳的遭遇一样,被传统势力所攻击,连推荐魏连殳就职的事也成了他呼朋引类的证据,于是不得不躲进屋里,只是上课出门。虽有躲避,但当他看到魏连殳在做了杜师长顾问后写给他的信,还是很不舒服。这段描写就反映了他的基本态度:
这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但草草一看之后,又细看了一遍,却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又想,他的生计总算已经不成问题,我的担子也可以放下了,虽然在我这一面始终不过是无法可想。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7]104-105
“我”矛盾的心态并不表明“我”对魏连殳行为的认可,“有些不舒服”还是不舒服,最终没有回信的关键原因不是没话说,而是心里不认同魏连殳的做法而又同情他的现实处境,所以就不能说。这表明“我”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的。后面“我”又看到《学理七日报》上关于魏连殳的诗文,虽然使“我”记起魏连殳,但觉得他的面貌渐渐变得模糊。之所以这样,其实是“我”觉得魏连殳已经和自己不同路了,也就是“我”将要继续坚守自己的反传统立场。“我”便收不到这份报纸了,《学理周报》有流言对“我”进行攻击;到第二年暑假,“我”不得不离开山阳。通过这些描绘,“我”绝对是一个反抗传统、坚持自己道路的人,这是西来的“个”在“我”身上的表现。不同的是,魏连殳在传统的逼拶下无可奈何地臣服于传统,而“我”却坚守了“个”性。这是鲁迅通过分身术使问题在对话中得到更深刻的展现。小说结尾魏连殳通过与世沉浮来表达他的不满,这是从精神上向社会复仇。而“我”在送敛完毕,走在清冷的石板路上,表明“我”将孤傲地坚守自己的路,前方是什么似乎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需要焕发勇气。这就是由尼采“超人”演化而来的“强者的孤独”,也是易卜生所说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孤独的人。[8]349读到此,我们发现鲁迅在表达具有“个”性的反抗精神时,比以前的小说更加文学化了。之所以有这样的跃进,与鲁迅从西方文学作品中获得养料有极大关系。
高旭东在一篇文章中讲到魏连殳反抗传统的“强力”受到拜伦《海盗》的影响。[1]魏连殳起先为人处事都具有反抗传统的特征,不与传统调和的态度很坚决,但他最后因生存不得不消极反抗,从内在思想上看,他还是反抗的,可形式前后有别。这样看来,魏连殳并不像“我”那样具有“强力”的美学特点。所以,康拉德倒和“我”更像一些,也与此前鲁迅塑造的“狂人”更加相似。魏连殳从积极反抗到消极复仇,有学者指出是受到《工人绥惠略夫》的影响。[3]鲁迅1920年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这篇小说,他就是把工人绥惠略夫作为一个尼采式强者来看的,可以说这是他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魏连殳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已经不是“超人”式的个人主义者,他和吕纬甫一样要面临存在的炼狱,他单纯的反抗本身就否定了人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这一历史规律。但是社会的进步又不能没有这样的改革者,因而魏连殳作出了属于人悖论存在的反抗,就是精神性复仇。这在实质上与绥惠略夫所走的道路相似,不过,鲁迅并不赞同绥惠略夫开枪胡乱射击,因而魏连殳的反抗仅仅是通过与世沉浮的方式作出的反抗。
三、《孤独者》中的中国文化之“个”
小说首先给我们提供了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地理信息,即是“我”所教书的地点——山阳。一提到这个地名,凡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就会想到“竹林七贤”的聚集地也是山阳。山阳即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市东南),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主要的活动空间。这个地名至少承载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竹林七贤”,二是“竹林七贤”生存的社会背景。“竹林七贤”据陈寅恪认为是后人的杜撰[10]161,[11]181,后学王晓毅又在《“竹林七贤”考》中驳斥了陈的观点[12]90-99。不管“竹林七贤”称谓是否真实,但作为魏晋时期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士人群体是无可争议的。“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是阮籍、嵇康和山涛,他们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人格精神。据史料透露的信息,“竹林七贤”内部成员的思想倾向并不统一,阮籍和嵇康思想接近,都反传统礼教,对仕途冷淡;而山涛和王戎则热衷于仕途,他们聚集山阳也主要是为了避祸保身。“竹林七贤”何以常聚山阳清谈,表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据王晓毅考辩,“竹林之游”以嵇康赴河东三年(256-259)学道为界,分前期(247-256)和后期(259-262)。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山涛,特点是避开洛阳的政治旋涡;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吕安、向秀,特点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这个划分在学界还有争议,比如高晨阳在《阮籍评传》中就认为“竹林之游”到甘露三年(258)嵇康离开洛阳到河东就结束了[13],但无论怎样,“竹林之游”发生在正始末年是没有争议的。魏明帝死后(239),第二年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正始,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辅8岁少帝曹芳。前几年曹芳对司马懿基本还是尊重的,政治局势也相对稳定。正始五年曹爽不听司马懿之劝发动骆谷之役,结果惨败,此后,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矛盾开始全面激化。正始八年(247),司马懿称疾避爽,标志着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公开破裂。249年“典午之变”,司马懿乘曹爽随少帝曹芳出洛阳祭扫高平陵明帝之机,一举控制京都,迅速勒兵占据要地,曹爽得知后慌了手脚,结果曹爽及其重要党羽被司马懿全部诛灭,司马氏集团在这场争斗中取得了初步胜利。据研究,“典午之变”中司马懿诛灭曹爽、何晏等八族,前后共杀人计三千多,以致造成“名士减半”、天下震动的恐怖局面。[13]这给当时的名士、特别是和曹氏集团有关的名士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所以247年前后很多人为避政治之祸,采取退隐山林的办法,这就是“竹林七贤”常聚山阳的政治背景。此外,司马氏集团对一些不是曹氏集团核心的名士也采取了拉拢的政策,比如阮籍、山涛和王戎都先后出仕司马氏集团。以此来看,山阳是和动乱的政治局势相对应的一个地理空间。
鲁迅对魏晋文章及人事的关注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在《孤独者》中设计地名山阳,恐怕不是无意为之,而是为魏连殳和“我”设置一个具有隐喻意义的地理空间,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地理空间把读者引入到一个动乱的时代,同时又把这个地名与山阴对应起来。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局势非常动荡,“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之间战争连绵不断,这样的政治局势和魏晋正始末年难道不像吗?鲁迅也有这样的暗示,1927年7月在广州以《魏晋风度及文章和药及酒之关系》为题发表演讲,他说过是有感慨而发的。[14]1431923年国民党联俄联共,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更换的转折点,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比如胡适就肯定了其联俄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部分有汇合的迹象。1925年孙中山逝世和广州国民政府两次东征的胜利又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新陈代谢,结果在广州就出现了一个由孙中山的文武幕僚及亲戚组成的领导核心,也就是以国民党和黄埔军为核心的新型“客籍”势力击溃相对偏旧的“客军”和“本土军”,于是“土客”矛盾激化,比如“蒋李交恶”。同时,新的领导核心内部因权力和利益的不平衡而相互争斗,比如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的争斗。共产国际也作为支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一股势力进入广州。因而,广州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中心,各派都想寻找政治上的合作者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蒋介石为提高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不得不拉拢反共的国民党右派,这就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4月15日大屠杀的主要背景。[15]507-546广州的政治形势与正始末年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斗争也很相似。鲁迅这个演讲大有把现实的中国和魏晋那个时代相对应的感觉,而中国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也在鲁迅的潜意识里被比成竹林名士。早在1924年到1925年,鲁迅参与女师大学潮,章士钊免了他在教育部的职位,和北洋政府关系闹得比较僵,1926年南下也主要是因为“三·一八”惨案和政府关系紧张而致。《孤独者》创作时间虽然比广州演讲要早,但1925年的10月却是鲁迅内外交困的一个重要时期,从历史实质上看,南北之争及军阀混战与国共争斗并无很大差异。鲁迅对魏晋历史很熟悉,这就极可能把魏晋时期名士的生存背景移居到小说中,来表现中国这段时间进步知识分子的现实状况。
《孤独者》不仅仅是通过山阳来展露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通过塑造与竹林名士相似的人物形象来表现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从相似程度来看,魏连殳更接近阮籍,而“我”则像嵇康。魏连殳首先是一个反抗传统的战士,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王瑶早就指出魏连殳像狼嗥一样的哭与《晋书》中记载的阮籍在他母亲死后的哭很相似,他通过援引《晋书·阮籍传》中阮籍哭母来说明这个问题[4]22,此处就不赘引了。魏连殳不拘礼法,大家都哭的时候,他没落一滴眼泪,当哭的人走散后,就落下眼泪像狼嗥样地恸哭。这一段记述更像阮籍的做派: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7]91
阮籍在他母亲死后多有这样怪异的举动,除前王瑶说的“哭”外,还有青眼和白眼的典故。《晋书·阮籍传》说:“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16]1361阮籍是一个十足的怪人,不拘礼法到被人仇视的地步。魏连殳也不拘礼法,有阮籍的影子。魏连殳一生的事迹和阮籍也有诸多重合之处。魏连殳反传统而被传统反,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屈尊杜师长门下做顾问;而阮籍先被曹氏集团征辟,在正始末年为避祸保身,称病不仕曹爽集团,后来又出仕司马氏集团,作从事郎中,在司马昭手下请求外调做东平相,十余日回来又作从事郎中,觉得和核心政治集团靠得太近,就主动请求做步兵校尉,主要原因是那里酒多,可以和好友一起酣畅淋漓。阮籍的确通过买醉,逃脱了司马昭的求婚和钟会的谋害(见《晋书·阮籍传》)。阮籍采取的策略是敷衍和游戏政治,就是表面上的与世浮沉。魏连殳后来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花钱似流水,喝酒度日,通过与俗浮沉的办法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怨愤,这也和阮籍相似。王瑶讲“在我国历史上对现实抱有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本来是很多的,但他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不是‘与俗浮沉’就是‘悲愤以殁’,这种情况一直到魏连殳的时代仍然是存在的”[4]23,这也正是王瑶所认为的鲁迅在塑造魏连殳的性格时受到古代叛逆者事迹的影响。王瑶没有深入论证魏连殳和阮籍思想的相似,其实他们二人确实有内在精神的近似点。阮籍虽“与俗浮沉”,但并不表示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追求独立的人格精神,只不过在生存的压力下用一种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他“口不臧否人物”,借酒装糊涂,不是是非不分,善恶不辨,而恰恰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决策。他身在官场,心在“竹林”(理想的象征),处于精神悖论之中。《晋书》说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是政治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使他无缘实现理想,最后不得不采取矛盾的方式来苟且偷生,其思想斗争和内心纠葛可见一斑。郭熹微指出:“他的世俗人格与理论人格、批评人格被封建专制主义割裂了,这成为他不可解脱的矛盾与痛苦,这正是他令人感觉隐晦难解的咏怀诗的写作背景,而他种种沉默任诞的行为,也正是他社会批判与独立人格意识的表露与挣扎,是他对现实的变态反抗。”[17]而魏连殳的精神状态也是如此,他与俗浮沉了,但并不是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他只是通过这样一种变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如同阮籍的消极抗议。按常理看,魏连殳如果真的喜欢做顾问的话,那他应该很珍惜,但实际上他既不珍惜官职也不珍惜通过做官挣来的钱,更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只希望在这浮沉中活几天。最后在死前通过轻蔑的笑来向这个覆灭他肉体的社会复仇。魏连殳是忧愤而死,阮籍是抑郁而终。
嵇康青年时代大约一直闲居在家,潜心读书或与友人相互来往,抚琴咏诗,清谈高论,大概在二十五六岁结婚[18]71,娶了曹魏宗室女为妻,大概也在这个时候迁郎中,拜中散大夫,随即迁居洛阳,“竹林之游”当是迁居洛阳以后的事情。中散大夫是个闲职,嵇康也不热心政治,山涛曾经举荐他为官,他便与之绝交了。《晋书·嵇康传》说钟会拜访嵇康,嵇康与向秀在大树下打铁,并没有像样地礼会他,钟会回后即向皇帝进谗言[16][17],又因吕安事件最终在钟会的谗言下被司马昭杀害。这个事情的具体时间及情节在学界还有争议,但是嵇康不仕,以名士的做派反抗当权者是事实。由此可知嵇康在做官上和阮籍有区别,他明确告诉世人,他不想做官。这是司马氏集团杀他的根本原因。《孤独者》中的“我”反传统,和阮籍、嵇康一样追求独立的人格精神,这是没有问题的。在细节上也能找出一些相似处,“我”在山阳也因写文章遭到流言的攻击,最后被迫离职,但是“我”却没有像魏连殳一样做杜师长的顾问。“我”收到魏连殳告知做了杜师长顾问的信后,有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反对的基本立场没有变。结尾“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又坦然地走在月光底下,也是进一步对自己立场的坚守,不过这个坚守是经历感情和理智淘洗后的坚守。如此来看,“我”有嵇康的影子。还有一个证据在于“我”教书的地点。从王晓毅《“竹林七贤”考》中所引文献可知,山阳是嵇康的居住地应该没有什么问题。[12]“我”在山阳教书,正好和嵇康在山阳居住过形成对应关系,而阮籍是否到过山阳还是有争议的事情,史籍大概也没有他在山阳寓居的明确记录,学界只是推测他在洛阳时可能因“竹林之游”去过山阳。《晋书·嵇康传》记载王戎曾在山阳居住二十年,但王戎热心仕途,和嵇康有本质的区别。综合以上各点,《孤独者》中的“我”和嵇康相似度较高。
上面讨论了魏连殳和“我”与阮籍和嵇康的相似性,不是要完全坐实这两个人物与阮籍和嵇康的关系,而是想说明这两个人物在《孤独者》中从细节设置到精神内蕴都有阮籍和嵇康的影子。阮籍、嵇康的精神内核就是反传统的叛逆者,是中国文化中最具“个”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们已经具有了个体独立的精神追求,对传统能够作出自己的是非判断,这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咏怀诗》和嵇康的《太师箴》、《声无哀乐论》、《答难养生论》及诗歌中都可以看到。李泽厚曾经指出:“儒家并不否认个体,但它认为群体、社会是无限地高于个体的;玄学也并不否认群体、社会,但它认为群体、社会不应成为个体人格自由的障碍、束缚,更不应当成其为个体人格自由的否定、取消。极大地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这是玄学区别于儒学的一个根本之点。相对于东汉日趋神秘化、烦琐化、虚伪化的儒学统治来说,这种强调带有‘人的觉醒’的重要意义。”[19]7阮籍和嵇康就是魏晋玄学中这种人格自由和独立精神的代表之一,他们体现了“人的觉醒”。鲁迅关注魏晋人事,对嵇康和阮籍的偏爱,是对他们这种反传统的独立自由人格精神的肯定,这也是鲁迅把这种精神通过形象的小说人物表现在《孤独者》中的重要依据。
四、《孤独者》中中西之“个”的交汇和相互改编
《孤独者》中所涵养的中西文化之“个”,并没有先后的顺序,其实中西文化之“个”在小说中是并置的,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分开论证。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文本,它是各种因素织就的有机体。那么,仅就鲁迅所看重的中西之“个”而言,他是怎样把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个”熔铸在一起的?这个熔铸是不是仅仅限于移植?
《孤独者》中的西方之“个”的原型是“超人”和摩罗诗人以及他们的文学变异体,而中国传统之“个”的原型则是阮籍、嵇康及他们的变异体。他们通过鲁迅这个桥梁,在《孤独者》中走到一起,然后有机交织起来,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魏连殳和“我”的形象。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跨越古今中外的共同性。源于西方文化的“超人”和摩罗诗人,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共同性就是反抗传统、专制、奴役,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精神。尼采所建构的“超人”要重估一切价值,对整个西方传统文化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拜伦在他的一系列诗歌中为我们塑造了反抗传统、崇尚强力、孤傲绝世而独立自由的“拜伦式英雄”;雪莱提倡无神论,反抗世俗,猛烈反抗专制统治;普希金、莱蒙托夫继承拜伦的叛逆精神,对沙皇的专制统治猛烈揭露和攻击;密克威支和斯洛伐支奇是反抗专制统治、向帝王复仇的歌者。鲁迅认为这些人都“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就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8]101,其思路是从“立人”到达“立国”,“立人”是基础和前提,因而什么样的国民就很重要。为完成这个造人的任务,他提出了“立人”的标准,就是摩罗诗人那种真诚、独立自主、不同流俗的人。而中国现在的国民已堕入“秋萧”,因此需要摩罗诗力来拯救,进而才能强国保种即“立国”。竹林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处在一个个性觉醒的时代,他们在政治动荡中也坚守自己的信仰,“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传统礼法,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这在精神实质上与“超人”和“摩罗诗人”是相似的,尤其是在反抗传统上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具体来看,阮籍反传统不拘礼法,可是又和当局者消极合作,其生命轨迹和精神内核与普希金近似;而嵇康自幼不受约束,成年后就更加任性不羁,孤傲,坚守信仰,誓死不与统治者合作,近似拜伦式英雄。因而,在生命呈现方式和精神内核上,都能找到阮籍、嵇康与“超人”和摩罗诗人之间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正是他们能够交织起来的基础。鲁迅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自觉地把这个共同性熔铸在魏连殳和“我”身上,从而搭建了中西之“个”的对话平台。伊藤认为鲁迅的“个”来自西方,是与中国异质的东西,这可能是伊藤对中国文化体味不是特别深的缘故,也过分夸大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从“立人”到“立国”是鲁迅的思维路径,他在日本时期写的论文明确体现了这一构建理路,这其实也是他从摩罗诗人身上看到的。他推举的八位摩罗诗人几乎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反抗专制,呼吁国家、民族独立与自由。摩罗诗人爱国思想的内容不同,但是关注国家命运是共同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是太丰富了,几乎所有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都感时忧国,这是儒家文化中“修身、治国、平天下”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阮籍和嵇康虽“越名教”,但并不是彻底地反名教,在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时,他们根本上还是关注国家社稷的,也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来批判曹魏政权,比如嵇康在他的《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中都有关于理想的政治建构。阮籍也一样,本有济世之志,无奈理想破灭,才与俗浮沉,但在他的文章中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追求。由阮籍和嵇康来看鲁迅,他们对独立自由的追求和国家是相联系的。在思维方式上,阮籍和嵇康与摩罗诗人也相像。前面还谈到,鲁迅在写作《孤独者》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政府专制的时代,这个时代和魏晋之间形成对应关系,那么存在于这样社会中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然也面临着相似的处境。19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出现就是这个时代背景的反映。于是魏晋、西方19世纪初期与尼采、鲁迅生活的20世纪初期就具有了相似性,处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人相应也具有共通的东西。鲁迅在此发现了阮籍、嵇康和摩罗诗人、尼采与魏连殳和“我”的古今一体性,并创造性地实现了古今中西的并置。
《孤独者》对中西文化之“个”还进行了创造性的双向改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西之“个”的变异。下面从三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用人间温情来软化“超人”的冷漠。《孤独者》是通过以下细节完成的。魏连殳对祖母非常爱戴,发工资了首先给她寄钱,他祖母死了,他不是像很多人那样虚伪地哭泣,而是真诚地感受到祖母人生的不幸,并由这个不幸推及很多这样的人,因而才像狼嗥一样恸哭;同时,他对孩子也非常关心,给他们买吃买穿,可是有一次孩子不要他买的东西,他感到很伤感,这也可看出魏连殳的善良。通过这两个细节可看出魏连殳身上充满了人间的温情,这种温情和爱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的社会伦理;二是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中国传统社会很讲究人际温情,人与人和谐相处,每个人要融入集体中,朋友之间也讲究谦恭礼让,即使是嵇康这样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为人也性情温和,阮籍和朋友之间相处同样很融洽。而西来的“超人”却是很高傲的,他耸立云端,视人民群众为庸众,俯视尘寰;拜伦的孤傲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有“超人”和拜伦这样的特点。“我”在《孤独者》中是很有人情味的,几次去看魏连殳,提酒去和魏连殳聊天,关心魏连殳的生计问题并给他推荐工作,这是朋友之间的关怀,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人性温情。总之,经过很长时间的探索,到创作《孤独者》时鲁迅已基本摈弃了“超人”的人性冷漠,他把中国传统中人性温情的一面附着在“超人”身上,其实就是用中国的东西改编西来的东西。当然,魏连殳的爱实质上不是传统型的爱,他突破了血缘关系而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人道的爱,是基督教博爱精神在中国小说人物形象中的再现,这又是从西方来的,更具体地来说可能是鲁迅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中吸取的养料。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其实,我的意思原也不容易一时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20]81人间温情对应人道主义,“个”则对应个人主义,鲁迅袒露自己在这两种思想中斗争。《孤独者》用人间温情来软化“超人”的冷漠,就是消长起伏的表现吧。由是可知,在外在形式上,魏连殳和“我”透露出中国式的人性温情,但在爱的伦理关系上却不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爱,而是带有基督教痕迹的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第二,用进化论的个人存在改造复古论的个人存在。阮籍和嵇康在政治理想上是复古的,所对应的人格理想也具有复古的特点。魏晋时期,玄学兴盛,而玄学主要和道家思想有关,也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新变,知识界主要关注的经典文献是《庄子》。竹林名士大都热衷于玄学的清谈,阮籍和嵇康当然不能例外。从他们的文章中可看出这一点,这里以嵇康《答难养生论》中的言论为例说明:
至人不得以而临天下,以万物为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与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无事为业,坦尔以天下为公。虽居君位,飨万国,恬若素士接宾客也。虽建龙旗,服华衮,忽若布衣在身也。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岂劝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贵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显,色不加悦;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义之贵;三黜之贱,不伤冲粹之美。二人尝得富贵于其身,中不以人爵婴心也。故视荣辱如一。由此言之,岂云欲富贵之情哉?[2]54-55
这段文章讲理想人格和理想政治的构建问题。嵇康认为的“至人”是理想人格的化身,他心怀天下,居高位处之泰然,居低位而不悲哀,正所谓宠辱不惊。他所看重的不是“令尹之尊”,而是“德义之贵”,并且明确反对私欲膨胀,把物质之有视为不存在。嵇康建构这个理想人格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政治,“至人”这样的品德必然导致“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足于下”的政治局面。我们知道先秦道家就倡导“无为”的思想,他们所崇尚的人格理想也是“无己、无功、无名”,在政治理想上则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嵇康这段论证的思想核心源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无论是人格理想还是政治理想都是道家思想一次新的阐发;在嵇康其他的文章中也能找到这样的证据,这说明嵇康的主体思想是回归道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复古论者。阮籍在晚年所撰写的《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一个隐士孙登的形象,这是他的理想人格,表明了他强烈的道家立场,因此有人指出:“阮籍晚年的言论,表现为强烈的道家立场。他对名教的荒谬、虚伪、奸诈的抨击和揭露十分无情,其态度之激烈可以说近乎偏激。”[13]132
通过阮籍和嵇康核心思想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他们追求个体人格独立的精神,但是他们却是指向过去的,带有很强的回归倾向。这和孔子复周礼是一样的思维,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总体特征。魏连殳开始写进步文章,投靠杜师长之后就写传统的诗文,他也是一种回归的趋势,他写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本意,他是想混一口饭吃,大有逢场作戏的意味。他的复古倾向是上世纪20年代复古逆流在小说创作中的表现,也是阮籍、嵇康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文化的一个宿命。《孤独者》通过“我”对这个宿命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基本思想渊源是西方指向未来的进化论。鲁迅从南京求学开始就接触进化论,他对尼采和摩罗诗人的接受都带有进化论痕迹。要完成“立人”任务,也要经过一个进化的过程,鲁迅的设想是把中国的奴隶人性首先改造成素朴之人,然后再使他们成为主体性的人。这个人要像“超人”和摩罗诗人一样有永远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说革命没有止境,进步没有止境。
除了对魏连殳具有人道主义关怀外,“我”更加关心他死后的问题。小说的结构以送殓开始,又以送殓终结。通过环形结构把魏连殳的一生作了形象的再现,这个环形结构隐喻生命的重复和无意义,如同《在酒楼上》所说的苍蝇一样,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其实,复古也是循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复古几乎出现于历朝历代。魏连殳的复古就是他生命的一次轮回,这个轮回引起了“我”反思,进而做出了逃离循环结构的举动。当“我”在最后看了魏连殳的遗容后,举步出了灵堂,对此作者写道:
敲钉的声音一响,哭声也同时迸出来。这哭声使我不能听完,只好退到院子里;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7]110
“我”不能听到哭声,是这个哭声里有太多的世俗与虚伪;顺脚出了大门,是他要与这个虚伪的世界和循环的生命作别。告别这个循环、寂静、不发展的环境,“我”要到哪里去呢?没有明确的方向,而且道路是潮湿的,但是月光很明亮,乌云已经散去,太空是那样广阔,“我”在月亮冷静的光辉中坚定了要走下去的信念。这个信念在未来,魏连殳也曾经有过,可是他无法逃脱生的炼狱,最终展开了与世浮沉的变态反抗,当然这也是人的存在悖论,而“我”所要明确的是:只要指向未来,革新传统,就一定会遭受传统的反作用力。先行者于是经历阵痛就成为必然的事情,在此经过了一次情感和理性的再锻造,所见的月光就露出清冷的光辉。“我”在小说中是终极意义的追求者,如同“过客”“过滤掉了魏连殳身上不能不带有的阴气和毒气,同时保留了他的追求和理想”[22]171。 “我”与魏连殳形成对话关系,“我”像一条直线切破中国文化的圆圈。这就是鲁迅用西方进化论的存在个体改造中国复古论的存在个体。
第三,用“与俗浮沉”的反抗批判血淋淋的仇杀。魏连殳在生计无着落的情况下投靠杜师长,过着“与俗浮沉”的生活,这是他反抗社会、对社会不满的变态表现。从鲁迅获得西方之“个”来看,摩罗诗人、尼采都具有强力性的复仇思想;后来鲁迅又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主人公在反动势力威逼下最后举枪射向群众,使复仇变得盲目,主人公的这种“无治的个人主义”遭到鲁迅的批判。魏连殳形象受到了绥惠略夫的影响,但是鲁迅却用“与俗浮沉”的反抗改编对群众疯狂射击的“无治的个人主义”。这个“与俗浮沉”正是阮籍所用的反抗手段,他做官,在表面上认同曹魏政权;他喝酒,酩酊大醉,借此麻醉自己。魏连殳的变态表现和阮籍极其相似,这就是说鲁迅把阮籍的与俗浮沉嫁接到魏连殳身上,来批判性改造一个外来的绥惠略夫。
中西文化之“个”在《孤独者》中的相互改编,其实是中西之“个”经过鲁迅的过滤而实现的一次变异。这是鲁迅在文化上的自觉创新,它浸透着鲁迅的内心挣扎和深刻的精神危机。所以,魏连殳和“我”不仅艺术形象鲜明,而且精神内蕴丰富复杂。魏连殳属于传统文化中类似阮籍这样的人,他原来是很激进的,也有改革社会的志向,但是因为生存的诸种问题,就放弃了原来的理想,和生活妥协了。鲁迅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显然浸透他思想的血液,“我”从鲁迅中分裂出来,不是仅仅为了否定魏连殳,而是为了深刻地思考魏连殳的存在。从人存在的角度看,魏连殳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人的正常之举,他本身就表明了人类存在的通常方式——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像嵇康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所以不能完全否定阮籍和魏连殳的存在价值。鲁迅在此对西方那种具有冲创意义的个人主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孤独者》已经表明先前的魏连殳和实际生活相脱节,因此后来的魏连殳身上就有了阮籍那种表面上与世沉浮的性格特征。这样,鲁迅就通过魏连殳和“我”之间的对质,把中西文化之“个”并置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从而把人在这种现实下存在的悖论尖锐地提出来了。由是,鲁迅在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艰难挣扎就得到了艺术的呈现,而这一矛盾体现出来的精神危机也鲜明地表现在《孤独者》中。
五、结语
《孤独者》是鲁迅血肉的结晶。鲁迅通过这样一篇小说,不仅把自己生活的一个最艰难时期进行了艺术再现,也向我们表征了他生命的真诚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用心体味并消化中西文化的养料,所以我们就能看到《孤独者》这样的中西文化之“个”所熔铸成的艺术有机体。单单从中西或者古今的角度研究《孤独者》都可能造成对这个小说文本复杂性和深刻性的遮蔽,同样,研究鲁迅的其他小说也不能这样,因为鲁迅的文化接受视野是世界性的,这一点学界已成共识。但是,结合文本具体解析鲁迅在小说中是如何把中西文化元素艺术地并置在一起,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造成这个研究现状的原因很多,仅就方法论而言,可能是缺少真正比较文学视域的引入。因此,这篇文章通过这样的尝试性探索,试图为鲁迅小说的研究提供新的进入通道,希望它能够为深入解读鲁迅小说提供一些启示。
[参考文献]
[1]高旭东.拜伦的《海盗》与鲁迅的《孤独者》《铸剑》[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6):94-95.
[2]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程致中.《孤独者》与《工人绥惠略夫》比较论[J].中国文学研究,1989(3).
[4]王瑶.鲁迅作品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余放成.鲁迅为何不发表《孤独者》和《伤逝》[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6):45-49.
[7]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7):23.
[10]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王晓毅.“竹林七贤”考[J].历史研究,2001(5):90-99.
[13]高晨阳.阮籍评[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9.
[14]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李新:中华民国史: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郭熹微.从竹林七贤看魏晋之际名士的政治心态[J].文史哲,1992(1):29.
[18]童强.嵇康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李泽厚,刘刚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 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20]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1]鲁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2]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阳欣]
New Discussion onTheMisanthrope—The Artistic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JIANG Yong-guo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Both Wei Lian-shu and the title ‘I’ leave some traces of western modern individualism, which also contain the factor of ‘individual’ (rebel) in Chinese culture. Whil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Misanthrope were mainly conduct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Western to Chinese an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few of them focused on the term ‘individual’ from the angle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hich damaged the artistic integrated article into pieces. In the mid-1920s, social reality in China urged Lu Xun to closely link the term ‘individual’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On this basis, by implanting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details, Lu Xun placed the ‘individual’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together into The Lonely and made them integrated and adapted with each other. Finally, an organic artistic unity came into being, which showed his sincere life rhyme and complicated spiritual world.
Key words:The Misanthrope,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synthesis of art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2.014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6)02-0093-09
[收稿日期]从“个”的角度解读鲁迅的小说人物形象是伊藤虎丸的首创①* 2014-10-20
[作者简介]蒋永国(1974-),男,陕西紫阳人,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①“个”在内涵上与真正的个人主义对应,它是是一个信仰体系。不同类型的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信仰体系,具有一般性意义。这种信仰体系相信人的尊严、自主和自由发展,确保每个人具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个人是真理的最终裁判者。我们应该在多元文化中来界定“个”。,他认为“个”和鲁迅小说中的“积极人物形象”相对应,是欧洲近代个人主义的神髓,但是他在解读鲁迅小说的主要著作《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并没有运用这一思想分析《孤独者》。是不是《孤独者》中没有伊藤所说的“积极人物形象”?事实上魏连殳和“我”身上都有欧洲近代个人主义的影子。不仅魏连殳和“我”有欧洲近代个人主义的痕迹,而且还有中国文化中 “个”之因素。学界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关注。高旭东在1985年撰文认为魏连殳受到拜伦《海盗》中康拉德形象的影响[1],冯光廉在《鲁迅的小说研究》中谈到魏连殳与尼采的亲缘关系[2]328,程致中也指出魏连殳与工人绥惠略夫的关系。[3]鲁迅在求学过程中先接受西方的进化论和自然科学思想,然后又推崇施蒂纳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接着又非常关注欧洲近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些研究者所论述的正好是伊藤虎丸说的鲁迅所接受的欧洲近代个人主义及其文学变形。*鲁迅在翻译完《工人绥惠略夫》后写文章认为绥惠略夫像尼采式的强者(见《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绥惠略夫在鲁迅看来应该是“超人”的文学化变异。较早谈论魏连殳和中国文化中“个”之关联的学者应该是王瑶,他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分析了魏连殳和嵇康、阮籍的相似[4]21-23,此后的学者基本认同王瑶的观点。但是这些研究的问题也很明显,即分别从中西或古今的角度研究《孤独者》与中西文化中之“个”的关系,没有把中西文化之“个”并置在一起来透析《孤独者》怎样把中西这方面的文化元素进行艺术的熔铸。《孤独者》是一个有机的艺术体,中西和古今关系的单方面研究显然会磨损《孤独者》的艺术成就。因此,在中西文化之“个”并置的视野下来研究《孤独者》对中西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融合就显得非常必要,这样不仅可为认识《孤独者》及鲁迅小说形象提供新的启示,还将为探索鲁迅其他小说的丰富内涵提供新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