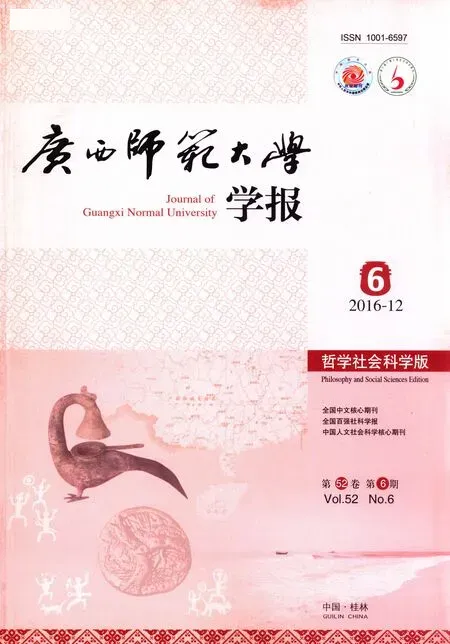从出土佛教题材汉画看东汉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
刘 克
(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南阳473061)
从出土佛教题材汉画看东汉宗教生态格局的变迁
刘 克
(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南阳473061)
传统宗教生态在东汉年间发生了巨大改变,形成了一个以佛教为特征的新型宗教生态。出土佛教题材汉画(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铜镜、碑刻等的合称)几乎同步记录了这一变迁过程。从佛教汉画来看,东汉宗教生态的这种改变是当时宗教系统的总体态势、层次结构、表现形式和内外关系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在东汉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虽然传统宗教生态的构成基础、条件及其性质跟佛教文化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构成了佛教入华拓展空间的严重障碍,但讲求慈悲为怀的佛教在本质上跟儒教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虚静之理又有共通之处。东汉末年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摧毁了传统宗教生态中主体信仰的制度支持和祖先、自然崇拜的社会基础,政治统治和农民造反严重打击了宗族势力和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不期然地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消除了屏障、扫平了道路,并为东汉政主教从、兼容互补、多元通和、相依相扶这一宗教生态的形成夯实了台基。佛教汉画视野宏阔,立意高远,其吐纳驰辩为我们考察东汉宗教生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东汉;佛教汉画;宗教生态;宗教关系;社会结构;生态格局
任何宗教的产生与发展都难以离开它所在的那个宗教生态系统。不仅宗教与人文环境关系的好坏关乎其进退兴衰,而且文化共同体的总体态势和走向还可能给所处时代锻造新的信仰传统。东汉佛教信仰的形成与东汉的宗教生态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虽然有关东汉佛教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也要看到目前关于东汉佛教分布的识别方法,无论是社会学分类、现象学分类、语言学分类还是地理学分类,都未能从佛教历史、佛教理论和佛教情状相综合的立场来进行,相关研究无法恰如其分地揭示东汉佛教那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而停留在概念的抽象述说和佛教事象的简单描述上。一些像佛教进入中土而导致东汉传统宗教格局发生变迁这样重要的宗教现象,很难通过其阐释逻辑得到科学而充分的说明。这里既有历史资料上的困难,也有理论方法上的障碍。如果宗教生态理论从文化生态圈角度对东汉佛教汉画资料进行识别,系统考察汉画中那些表现佛教核心教义的文献、表现佛教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文献和表现佛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关系的文献,并在东汉宗教那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中阐释佛教在东汉新型宗教生态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不仅可以弥补现有分类方法的不足,实现理论突破,促进相关研究发展,而且还能呈现东汉文化圈里各种宗教的动态分布情状和宗教间那脉息呼应的斑斓色彩,更有利于人们正确把握和评估东汉佛教的类属与走向。笔者认为,从东汉佛教生成的视角对东汉那些表现宗教系统总体态势、层次结构、内外关系的已出土汉画进行勾稽整理,并在佛教与所处文化圈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中谫探上述问题,想必不失为国内外同仁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一、东汉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宗教共同体的总体态势
从目前文献的记载来看,佛像出现在明帝永平年间,但从考古发掘来看,汉画中的佛像却晚到安帝延光年间才出现。可能由于当时佛教影响力相对弱小,尚不足以对中土已有宗教生态构成挑战的缘故,出土汉画显示东汉中期以前的宗教生态,体现的仍是一种原始宗教为主、黄老方仙为辅,祭祀斋醮频繁及本土各种信仰交相融汇特征。
原始宗教是产生于国家宗教和人为宗教之前的自发型宗教,它由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内容构成,是组成早期宗教生态的核心因素。虽然原始宗教演变为宗法性国家传统宗教之后其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原始宗教中那敬天法祖的基本内容和多神崇拜的信仰特点却得到了保留。汉画告诉我们,这种为世界各地原始宗教所共有、在统一的最高神产生之后已逐渐消失的信仰现象,一直到东汉仍然是传统宗教的重要内容。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月风雨山川土地和祖先均成了需要按时祭祀的神灵。面对自然,世人认为一切自然现象不仅有意志,而且还都具有神力。《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从汉画中一再刻绘的情形来看,人们总是以无比虔诚的心情在祭祀和膜拜这些具有无穷神力的自然神。如武氏祠前石室的画像石上,从上至下分别刻绘着风伯、雷公、雨师、电母及主宰刑杀的太一神。[1]24又如在南阳市王庄汉墓出土的风雨图中,上部三神在曳一车,另一神坐于车中。下部刻四神怀抱大罐向下行雨,风神风伯张口做吹嘘状。[2]古人认为自然神都是至善,乐意把大爱普施给天下所有的人。若在墓室里供奉这些神祇的图像,便能对自己所在的土地和人畜实施护佑。传统儒教认可自然神的这种存在价值。《荀子·礼论》认为天地是生存的根源,所以要求人们把“上事天,下事地”作为礼的根本。汉代儒宗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也承认自然神的存在,其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哲学体系中包含对传统神道文化的充分肯定。祖先崇拜成熟于周代,被看作是“国之大事”。《礼记·中庸》云:“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周人尚左,因祖先高于社稷,故在神位的排列上,往往“右社稷左宗庙”,祖先崇拜在宗教信仰中居于支配地位。周礼要求,不仅在葬礼上要给祖先上供,而且按照《四民月令》的规定,族人一年要在正月、二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分六次祭祀祖先。施祀之时要虔敬如仪。儒教讲求孝道,把祭祀祖先看作是恪尽孝道的表现。汉代以孝治国,因此画像石中表现子孙祭祀先人的内容甚多。如南阳英庄出土的祭祀图上,上层为祠堂,左放五盘,右置六杯。中层两侧各置提梁壶,中间置一樽。下层左置叠案,右置三碗供品。[3]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祭祀图上,也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祭祖时那毕恭毕敬、情真意切的场景。[1]60除此之外,还有嘉祥武氏祠的前石室[1]17和左石室所刻的祭祀图[1]28,山东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后壁刻绘的祖先受祭图[4]31等。这种被儒教视为孝道的祭祀,表达的是慎终追远、时刻不忘先人的思想感情。人们相信魂灵有知,在冥冥之中会发出一种支配人类命运的力量。祭奉它们,就会招福纳祥、庇荫后代。东汉人刻绘此类画像的用意除彰明自己是孝子、由宗族见证自己遵守并执行了祖先崇拜的仪轨之外,还希望通过供养这些画像,使“死者的灵魂安息”,“不要来扰乱生人的生活”,并“长利子孙”,“保佑生人”。[5]山东元嘉元年汉画上就有“柃(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的铭文。[6]这些画像和铭文说明,作为东汉时期宗教生态的主导势力,虽然儒教的制度性不强,其教义和科仪也不够系统,但其对敬天法祖精神的积极张扬,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于天地祖先的崇敬态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毫无疑问,这种要人不忘本根的祭祀精义和众神相容共存的信仰特点,为东汉兼容互补、“多元通和”[7]这一宗教生态的生成夯实了台基。
儒教的侧重点在治国,旨趣是修齐治平和“选贤与能”以建立圣贤社会,属于哲人宗教范畴。作为国教,东汉时期的儒教是跟先知预言的亚伯拉罕一神教系统和神秘主义的印度宗教系统有本质区别。虽然它以伦理意识居于宗教位置,自身也未能拥有一套成熟的宗教体系,但却不能因此而说它无视自身的宗教性建设。儒教在东汉时期增强自身宗教性的作法,从汉画来看,除祖先自然神崇拜外,还有以下两种:一是遵循民俗宗教原理,对死去的人封神。儒家典籍《礼记·祭法》中规定,活人在世间若做到“法施于民”、“能捍大患”、“以劳定国”和“以死勤事”,就可以得到儒教的认可而受到祭祀。如季扎以品高多闻著称,能联系时政说明诸侯的盛衰大势,是当时的知名人物,被儒家封神。东汉画像石墓中多处都刻绘有季扎的画像,在嘉祥宋山[8]和嘉祥武氏祠[1]27都有出土。又如刘邦,大汉的真龙天子,特别符合相关规定,在东汉的画像石中也有刻绘,如唐河针织厂汉画墓中就出土有高祖题材的画像。[9]13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典范,忠孝诚信且仁义超凡。儒教将此类人物纳入祭典并赐额封爵,相信其能够垂灵万世而护佑一方。同时,这种从民俗宗教一脉传承而来的血统也使儒教带上了崇拜对象多和功利性强的特点。二是吸纳民间公开举行的祭祀活动。民众虽然没有资格参加和举办祭祀日月天地的大典,但在国家祭祀体系之外,官府通过将一些常年举行的民俗祭祀活动纳入祀典并亲历亲为,昭明主流文化对神明信仰的肯定和恪守。在这些民俗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宗族是人力物力的提供者,地方官员则是活动的批准者和领导者。如周代为劝人在节令到来之时及时农耕,民间有祭春之俗。所谓祭春,就是于阴阳分气、时序和顺的立春之日举办出土牛活动。后来该活动被周天子纳入祭典,《周礼·月令》有“出土牛以送寒气”之语。此礼仪在东汉依然受到遵守。《后汉书·礼仪上》载,“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汉画掇拈香草,审慎地模山范水,将这一宏通的儒教意旨刻绘进了墓室之中。这种气格妩媚、形神兼备的祭春画像除洛阳汉代壁画墓有出土之外[10]14,南阳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还以文字的形式记述了郡守丞于延熹二年同意张景以家钱包揽这一祭祀活动以免除其劳役的决定。[11]888面对民俗中的此类祭祀活动,儒家总是含英咀华、不忍遗珠。汉画中广泛存在的祭祀风伯雨师仪式,其进入儒教的情形跟这种出土牛具有相同之处。这些神秘的远想幽思为东汉儒教信仰填充了逼人省思和正视的内容,透射出一种纵横两仪、联袂缀彩的气调与才情。这些民俗宗教因为与儒教国家政治力量和宗族组织的紧密结合而在当时的宗教生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顺势具有了民众利益与官府利益的共谋结构。这种结构使此类民俗宗教逐渐演化成一种强制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弥散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习俗,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道教是东汉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宗教,从东汉墓室出土大批道符、丹鼎、仙丹、道士、解除文等沉厚精致的汉画资料来看,道教养炼内丹、塑铸金身的宗教追求对当时人们“通灵天地”的理想有极深的影响。作为原始宗教之外一种新的心理安慰,道德真言、柱下旨归以及道教所提供的服务,在维系社会秩序和慰藉时人心灵方面是祖先崇拜和自然神灵信仰的有效补充。
但这种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文献和汉画考古发掘显示,东汉这种宗教生态平衡在明帝永平年间被植入了佛教这一新的种芽。佛教在西域广泛流传之后,于永平十年随着天竺、安息等国的僧侣来到了中土。佛教也叫像教,具有用佛像或佛教故事画表现教义的传统。由于供奉佛像之后生生世世都能得到福祥,深受朝廷和民间的青睐,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如现存最早的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一书,在写明帝梦见佛教神人后,“欣然悦之”,不仅“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而且“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甚至还“予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浮图像”。去汉不远的魏国也有如此记载,《魏书·释老志》云:“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追求实用是古人宗教观念的基本要素,由于供养佛像能得大果报,荣显始终,亡故之人也能托生于西方妙乐之土,所以据《大正藏》卷49载,自永平以来,臣民从佛者甚众。“中国始传其法,图其像”。2001年在重庆丰都的一座砖室墓中出土了东汉延光四年的摇钱树佛像[12],证明了东汉中期崇奉佛教的史实。虽然现今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对丰都出土佛像关注不多,但这一佛像的出现,却标志东汉宗教一个老式生态的终结和一个新式生态的诞生。
即便如此,但据此仍不能说传统宗教生态格局在东汉中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现在掌握的佛教汉画来看,佛教生存空间获得真正的扩展、东汉宗教生态发生实质性的变迁,是东汉末年的事情。
光武帝借谶纬神学起家,一俟登基,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便“宣布图谶于天下”,致使整个东汉笼罩着一层浓郁的宗教气氛。当历史进入到政风日下的东汉末年,面对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府企望神祇保佑挽救统治危局,贫民则希望神灵拯救脱离苦海。在这种失衡失序的社会中,佛心慧语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和满足人们宗教诉求的作用,所以这期间佛教不仅渗进了汉廷的皇宫大内,而且还深入乡鄙的灶间床头。从东汉佛教汉画的出土情况来看,佛教的这种蓬勃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影响大。在影响区域上,跨越东汉中期以前的京畿和西南两地,向晋陕、齐鲁、江浙、岭南发展,近年来上述地区接连不断地出土过佛教汉画。除此之外,前来传译佛经的僧人和翻译经卷的数量也都远远超过了中期以前各朝。据《高僧传》记载,桓灵二朝,前来译经的有月支国支娄迦谶、支曜,安息国安世高、安玄,天竺国竺佛朔、竺大力,康居国康孟祥等,可谓是高僧如林、大德济济。共译出以《安般守意经》、《道行般若经》、《阿含口解》等为代表的佛经290部395卷,以令人目动心眩、激赏不已的实绩托起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第二,出土佛教汉画数量多、种类全。据笔者统计,截止2015年秋,全国已出土东汉末年佛教汉画118幅,不仅数量远远超过东汉中期以前佛教汉画的总和,而且还初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像系统。其中佛像53幅,表现佛教教义的佛塔、莲花(仅指具有佛教属性或要素的莲花,传统装饰类莲花图案不在统计之列)、力士、白象等画像38幅,反映佛教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的画像27幅。这些汉画作为古人的精神图像和心灵轨迹,没有一幅不是精美手笔。东汉民众虽然没有用文字写下外来佛教跟东汉文化融合之后时代宗教诉求新变的专论,但是用饱含激情的刻绘抒写了没有明言的情结。第三,信徒多。这一点其实跟第一点相辅相成,影响范围大,信众自然就多。另外,这方面的人数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从文献对东汉末年佛事活动的记载中也可以间接地了解信徒和清信士规模宏大的史实。据《三国志·吴书四·刘繇》记载,汉末灵献之际,丹阳人笮融承接楚王刘英余绪,在“百姓殷盛,谷实甚丰”的彭城,大起浮图祠,“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当浴佛日,四乡咸集,络绎如市。“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以上这些烂漫景象高度浓缩了佛教在东汉末年的骄人成绩与迷人风光,虽然看似具体而微观,但它背后却显示了一个佛教在东汉末年法缘日盛、道业渐隆、新型宗教生态迅速生成的宏观格局。
与佛教的繁盛格局相比,儒教和道教在东汉末年呈现一种每况愈下的衰落态势。儒教虽然作为主流信仰,其纲常教化业已成为一种习俗而漫布于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东汉末年所出现的名教危机,严重影响了它在淳化民俗和敦励世风过程中的作用。道教跟汉廷关系一向密切,章、和、安、桓、灵诸帝均喜欢跟道教接触。特别是灵帝,不仅与道教信仰者交往并接受其思想,而且还企图征用他们来朝廷为官。河南偃师出土灵帝建宁二年的高道肥致碑,其碑文中有“诏闻梁枣树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礼娉君”的文句。[13]《后汉书·襄楷列传》亦载:“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举方正,不就。”爱屋及乌,后来当灵帝知道中常侍张让跟黄巾交通,“竞不能罪之”。可以认为,灵帝及其以前各朝是道教跟汉廷的密月期。在政治与宗教的热恋期间,如果不积极地建构统治秩序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公共规则,而只是利用皇权试图让某个宗教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工具存在时,那么就不仅容易麻醉统治者的思想并进而扰乱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行政规则,而且也往往容易使那些受到宠信的宗教变得妄自尊大。当灵帝不能接受道教的“应天改元”要求时,认知理念的交锋和碰撞最后竟演变成了宗教与政治的生死对决——道教徒在灵帝中平元年勇毅地踏上了推翻汉政、取而代之的征程,后在官府的镇压下,才逐渐趋于泯绝。五斗米道虽然在张鲁手里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但最终也没能逃脱为曹操所降的命运。跟儒道两教的这种式微趋势相比,佛教由于没有受到伤害,所以它能够在道教活动被严厉禁止的形势下迅速浮出水面并进行公开活动。
为什么中华民族维系了数千年的宗教生态会在东汉年间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并形成一个以佛教为特征的新型宗教生态?本文的着力点在于考察佛教传入中土后所导致的东汉各种宗教之间力量的相对消长并对汉代宗教生态由此而发生的变化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跟现在学界只强调文化交流或商业往来导致佛教传入,不太关心东汉各种宗教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差异性的研究具有本质区别。出土汉画使我们认识到,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并能在中土获得立足,文化和经济因素固然产生过莫大作用,但巨大的政治力量不仅对佛教的塑形和传播产生决定作用,而且还通过佛教对东汉的宗教生态的变迁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趋严重、各种势力都纷纷利用宗教来宣泄情绪、表达愿望的形势下,佛教不跟传统宗教及民间信仰发生激烈冲突,而通过宗教间的论辩和对话等温和的形式来扩展生存空间。这一生存智慧与东汉社会生态健康化诉求之间有强烈的通合性与呼应性。心阅目想相关汉画的琳琅风色,深知这仅是佛教初入中土时的内部因素。在外部,东汉政治统治对于宗族势力和社会深层结构的深刻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佛教在民间的日益兴盛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信仰思维上看,东汉宗教生态的改变更像是宗教运营结构的重建和信仰心理倾斜的矫正。
东汉吸取王莽“因绝”西域诸国之失当举措所引发匈奴怨叛的教训,文武两手交互使用,以一系列的军事扩张行动和独特灵活的贸易方式来加强跟西域的联系。现从丝绸之路新疆段和田拉瓦克遗址出土的圆塔、立佛和丹丹乌里克方形木骨灰泥墙佛寺墙壁所绘千佛图以及若羌县米兰三号寺院佛陀与六弟子图、相师占梦图和五号寺院花绳供养图、须大拏本生图等可以看出,佛教在东汉的发展始终跟《后汉书·窦融列传》所谓的这种“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策略脉息呼应、紧密相随。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有效控制,东汉军事威慑所到之处,及时恢复西汉业已设立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等行政机构以代表中央管理西域的各项事务,并以武力为后盾,用各种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中土跟西域的深入交流。毫无疑问,虽然佛教信徒不是这些东来西往使者的全部,但是,现有的汉画文物和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其中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佛教信徒,他们在中国也应当有所活动”[14]。作为东西交往活动中的产物,如果没有汉廷出于显示汉威、镇抚西夷目的所建立的交通条件、为商旅使臣所提供的安全保障,佛教也不可能会在东汉一朝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东汉雄浑豪迈、开放活跃的精神特质,也极大地强化古人对于佛教的兼容性心理,从而为佛教进入中土、并使东汉宗教生态的多样化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另外,跟社会交换关系建立之后的不同收益决定了佛道二教在官民心目中的不同定位。东汉末年,特别是道教惨遭镇压之后,人们或官府与佛教进行互动和整合,可能会带来精神和利益上的好处;而跟道教交往,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可能因此而致祸。总之,在佛教改变东汉固有宗教生态的活动中,东汉的政治文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些因素的存在,既给佛教进入中土带来了机遇,也为东汉宗教生态的变迁提供了可能。
二、传统宗教生态的社会基础与佛教在东汉中期以前的发展模式
要深入解析佛教给东汉传统宗教生态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孕育和支撑传统宗教生态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和宏观政治性因素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从对相关汉画的考察可以看出,传统宗教生态的构成基础、条件及其性质跟佛教文化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构成了佛教入华拓展空间的严重障碍。
儒教既是华夏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底色,也是东汉传统宗教生态的基础,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是佛教发展道路上无法规避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教作为帝王之师和文章之祖,在两汉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儒教是为官的主要标准和衡量个人品操及社会风气的基本依据,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匹夫幼童,无不热衷于诵读儒经、研习章句。在这种浓郁的儒教氛围中,不仅出现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喜人景象,而且从层出不穷的拜谒读经汉画,蔺相如、伍子胥忠臣汉画,荆轲、聂政勇士汉画,董永、邢渠、闵损孝子汉画和秋胡戏妻、鲁义姑姊烈女贞妇汉画等宣传汉代意识形态画像的出土来看,儒教在思想领域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在精英人士的感召下,儒教走进了全民的心灵深处,构成了道德伦理的基石。由于佛教剃除头发、弃婚绝嗣、身披袈裟等大悖儒教,所以其传教行为更容易引起反佛民众的仇视。面对佛教这一“夷狄异端”,他们在感到其价值观念跟崇尚忠孝仁义、敬宗法祖的儒教格格不入的同时,还担心一旦为该术所惑,必将影响诵读孔孟之经而招致诗书礼乐典则发生奇变。因此,在世人的心目中,佛乃“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对于佛教进入中土之初,与维护传统宗教信仰的势力所展开的这场激烈的碰撞和论争,《牟子理惑论》里有忠实记载。其云:“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云其辞说廊落难用,虚无难信。”《高僧传·晋邺中竺佛图澄》在记述东汉时期官民仇佛、传统力量依旧强大的情况时,对当时“汉人皆不得出家”[15]352的规定也有翔实记录。这些用儒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起来的民众,无疑成为一道阻挡佛教传播的铜墙铁壁。
宗族是汉画表现的重要题材。相关汉画显示,作为一个忠实贯彻落实儒教理念的社会组织,它也是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强大阻力。宗族是同宗同族的人们以父系家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宗法共同体,在乡里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发掘的汉画墓中的西王母、嫦娥、飞廉、天吴和祠堂画像可以看出,有汉一朝,强宗大姓的祭祀体系已逐渐从郡国县乡的宗庙和社稷祭祀中抽绎出来,形成了像墓祭这种祭祀在内的祭祀样式,并吸引了其他宗族和一般民众纷纷效仿。宗族组织除调解矛盾纠纷、荫庇户口和赈赡族内穷人之外,还成为乡里执行儒教准则的基层社会组织。其依据传统伦理道德所制定的宗族条规不仅对族人的婚丧嫁娶、言行举止、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有明确要求,而且对族人应该信奉的宗教有详尽的规定。由于宗族是依赖人伦和亲情组建起来的基层自治性社会组织,代表着民间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所以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便借助这一组织能够轻松地进入基层社会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族在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所发挥的这种作用,常常能够博得族人的拥戴,宗族给予族人的家族归属感也能够使他们形成积极维持宗族秩序的社会心理,并自觉维护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在主体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情况下,一族之长都由通经明法、殷实富有、威加乡里,具有较高威信的人士充任。此人既跟族人血脉相连,又跟官府交往密切,在生活中扮演着民众之首和一乡之望的角色,在思想观念上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从全国各地那盈千累百的庄园汉画、收租汉画及其精细雕刻上可以看出,民众对宗族组织是敬仰的,对富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向往的。如徐州茅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刻绘的庄园共有五进院落。第一进为双阙、门厅和执钺卫士,第二进为主宾相见场面,第三进为宴饮情景,第四进为庖厨之地,最后一进为三间廊庑,每间房里都立着一个仆人,气派到了极点。[16]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的东汉顺桓年间汉画像石,上面刻着三进院落。第一进为迎客场面,第二进为洒水扫地和河中行船情景,第三进为高大宽敞的庑殿顶主房,逼真地呈现了庄园的整体情况。[1]92河南密县打虎亭汉画像石墓[17]和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1]204出土的收租图,也生动地表现了豪族右姓收租的场景。这类汉画通过通透之手眼和纵横的匠心,形象地反映出人们仰慕豪右庄园甲第连云、金玉满堂和生活富贵的思想情感。另外,汉画显示,当时人们的交往范围较小,一般局限在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熟人圈子里。这种熟人社会传统促使人们易于认同和接受那些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家族式信仰,对熟人圈子以外的信仰则往往心存戒忌。东汉这种社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的封闭性、排外性,无法容忍散布于族人中的那些有违圣训的思想行为。宗族势力对民众思想行为的束缚性,成为儒教地位的制度性保证,从根本上阻断了浮屠教泽在民众思想意识中的深入之径。
从出土汉画来看,汉廷对宗教的态度和西北边境的战事对佛教的传教活动产生了巨大冲击。由于儒家的伦理思想经过一代儒宗董仲舒的神化之后已经演化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生活习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支配地位,所以汉廷、宗族和儒生阶层不能容许其他宗教违犯儒教的伦理纲常,也不能容许各种违背礼仪规则的行为发生。同时,统治阶级深刻了解宗教与叛乱的关系,刘汉皇朝对流布于民间的宗教信仰的包容度极低,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就会果断地进行严厉打击。佛教由于在东汉早期楚王英谋逆案中跟官府发生过龃龉,其传教活动曾被官府断然禁绝。
另外,和帝之后,在“三绝三通”的过程中,匈奴势力屡屡侵入西北边境,东汉跟匈奴之间连年的战争也成为阻碍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强大外力。出土的东汉碑刻中有很多记载。如《封燕然山铭》记录了大将军窦宪于和帝永元元年奉旨北伐匈奴单于军队大获全胜的威德。又如敦煌太守裴岑于顺帝永和二年率军出击北匈奴、威斩呼衍王一事,虽汉传史典未予著录,但裴岑之纪功碑却记述甚详。碑文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诛呼衍王等,斩首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万世。”[11]434对大汉威德的彰表,除这种刻石勒功的形式之外,在出土东汉画像镜中也有表现。如东汉银壳画像镜铭文中写道:“永元五年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歼灭天下复。”[18]21战争的结果导致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西迁。北匈奴在败逃途中,十余万众落入鲜卑,致使鲜卑势力大增,成为继匈奴之后的又一边患。匈奴在侵犯西北地区的过程中往往因侵损了当地民众的利益而引起后者的敌视,从而加剧当地社会的排外情绪,非佛教信徒的矛头直接指向佛教,造成胡汉矛盾激化。胡汉交战汉画目前出土较多,尤以齐鲁、南阳为多。据笔者统计,已达22幅,好多画像上还刻有“胡王”、“胡将军”的榜题。如山东微山出土的“胡将军”画像石上,战争场面相当惨烈。[4]41南阳出土的胡汉战争画像砖上,战马奔驰,箭矢如雨。[19]图144匈奴与东汉皇朝的对斗及东汉西部边境长期动荡而不能绥宁,导致胡人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受阻。因为佛教汉画中的胡人,“他们与佛的关系非常密切,大多为在家信徒”[20]244。而此时期的佛像,“主要为西域胡人所侍。作为宗教的佛像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21]。而胡人就是匈奴人。[22]同时,这个时期在夏夷之辩、礼仪之争的影响下,本土宗教人士致力于对佛教的批判和否定,佛教信徒不敢公开活动,不得不处于蛰伏状态,形成了佛事“遂寝”的局面。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章帝以后佛教汉画寥若晨星,一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层见叠出这一热闹景观的原因。
虽然东汉社会这种敌视而不愿涵容的态度使佛教在中土的传播举步维艰,但也不能就因此而认为讲求慈悲为怀的佛教跟儒教的仁和之道和道家的虚静之理没有共通之处,更不能认为中国的多神信仰传统与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不适宜佛教在中土扎根、开花和结果。诚然,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儒教那套襟袍严谨成熟、学识峻直完整的宗教理性,始终把现实人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反对对彼岸虚幻之事产生迷狂。《论语·先进》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同时,有别于同期佛教,儒教又是一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它不把人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来世,把做好日常事务当作真正懂得人生、真正享受人生并使生命走向永恒的方式和表现。但是,儒教又是一个具有早熟宗教理性的宗教。它在教导人们关注此岸世界的同时,为寄托和表达人生理想,也不反对人们对彼岸来世投以应有的关切。因此儒教并不完全排斥鬼神。一方面,儒教既强调政教分离,不能纯粹用神道来主政。《论语·庸也》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另一方面,又要求政教兼通,不能机械地排斥宗教。《礼记·中庸》又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要引导万民走向正义,不应忽视鬼神的作用,要“敬鬼神”。由于敬鬼神是帮助民众走上仁爱之道的有效途径,因此要从忠恕之道出发,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神道,使鬼神信仰跟世俗文化相依互补和共存并行,不能随便以自己的信仰作标准而横加干涉和排挤其他信仰。《论语·乡党》载,孔子虽然不谈论怪力乱神之事,但在“乡人傩”时,仍“朝服而立于阼阶”,对乡人驱逐疫鬼的迎神赛会表现出由衷的理解与支持。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东汉画像墓在图像的排列设置上,总是把地面人的宴饮拜谒、乐舞百戏、车骑出行、生产劳动等反映社会生活的画像跟上天神的伏羲女娲、天汉螺女、天女旱魃、麒麟送子等表现神鬼故事的画像放在一起来进行陈列,基本没出现过顾此失彼或抑此扬彼现象。如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是目前我国出土汉画最多的东汉墓葬,在150多幅画像中,既有羽人、飞廉、仙人、方相、宗布神、日月神等神画,也有拜谒、侍者、执金吾、乐舞百戏等生活图案。[23]99又如,在孔孟之道首善之区的邹城卧虎山M2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既有雷公、雨师、风婆、仙人、西王母画像,也有伯乐相马、车骑出行、孔子问师、豫让刺赵襄子画像。[24]1-18嘉祥宋山出土的汉画题记是对同墓画像内容的介绍,明确写道:“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贤仁。”[25]此岸与彼岸的圆融,不仅重构了一部新的礼仪春秋,而且也展呈了一套新的哲学模本,可谓是顾盼含章、意深笔长。汉画承接先秦儒学的人文遗产,有文有质,意足神完,努力在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上贡献自己独到的识力和智慧。作为社会情志沟通的中介,汉画将表现生死两界内容的画像同列,表明在东汉公共精神领域,虽然强调不可过分迷信鬼神而不觉悟,但又不拒绝人们以来世承载人生希望;虽然提醒对神道不可过于执着而害生,但又承认人道和神道一体。这是儒教一份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生活在东汉的古人在汉画的刻绘中感会最深切、揭示最深刻的亮点。这里面不仅折射出东汉特殊国情背景下文化选择的政治涵义,而且这种公心直言中也包孕有人文贯通、学理化臻的人文内核。在东汉,儒教鼓励神道设教、支持神灵崇拜并以此来满足世人对消灾免祸的期盼和渴求。
儒教和民间信仰并没有专设的神职人员,也不提供天堂地狱、超脱生死的服务和轮回投胎、祈福禳灾的承诺,所以从出土汉画来看,除儒教的礼制内容之外,反映佛教和道教教理教义的内容及为民众所提供的斋醮服务内容也在东汉谶纬神学泛滥、宗教活动昌盛的背景之下进入汉画之中,形成了政主教从、各有侧重、相依相扶、格局互补的宗教生态。在这种宗教生态下生活的民众,他们对自然、祖先以外信仰的歧视和排斥意识注定不是很强,其行为也常常偏于温和而说不上激烈。
为了应对来自中土的冲击,也为了改变自身多舛的命运,佛教没有刻意谋求跟中土原有宗教的统一或同一,而是在承认差异和保持仪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尊重中国悠久的传统和瑰丽的文化,以求同而存差异、会通而不混淆的变通与创新策略悄悄地接近中国同期的其他信仰,用且因且革、诚恳模仿中国传统宗教的方式来调适与传统信仰的关系,并以形义串通的意趣从意识形态的羁縻中寻求突围。这种不同于流俗的借鉴模仿实践,不仅能够得到以中和之道为处事原则、坚持和而不同为文明目标的传统文化的认可,而且对于佛教相续出新、有效预防唯我独尊和原教旨主义意识的滋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出土的汉画中,佛教这种因跟同期传统信仰冥契暗合、蹈迹承响所造成的形迹近似、性理有异之混杂情形,早已引起了汉画学者的注意,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提出了十分精辟的见解。如罗二虎在研究了东汉时期那些向道教靠拢以获得民众青目的摇钱树佛像后,指出:“看不出这些佛像与佛教教义、寺院和僧侣之间有何直接联系,相反却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26]李淞也在阐述佛像与西王母像渊源关系的过程中,对东汉这种繁简殊型隐现异术、虚以遵道实为敬佛的构图方式给予这样的评论:“中国佛像之所以与同期的西王母像相似,是因为前者迁就了后者,即外来图像力求以一种中国观者熟悉的形式进入中国。”[27]300东汉佛像对传统信仰的依附折射出其背后信仰文化阐释层面的深刻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在经历转型、重构等传教实践调适之后颇具创意的话语圆融。研究者深切的历史体悟和绵密的理论分析,使这一时期的佛教汉画的流变衍化显得厚重而新颖。一般而言,当一个时代对传统信仰失去了自信,那么当有信仰要进入这个时代的信仰生态圈,特别是当这种外来信仰宣称与传统信仰有亲缘关系的时候,潜在于内心深处的信仰需求就会促使人们去接受这种新的信仰,并把这种新信仰当作传统信仰的自然延续。正是这个原因,佛和神虽然性质完全不同,但把佛奉为神却成了此时汉画中的一个随处可见的信仰风习。佛教初传时期这种勇于创新、昂然立世的品格和作法,为佛教在东汉时期的传播打开了一大法门。这既是东汉把神仙佛陀等同、把金丹舍利齐观并安然信之奉之的重要原因,也是《后汉书》诸传世文献中“尚黄老之微言”的楚王英也“尚浮屠之仁祠”、桓帝视黄老佛陀为同类并于宫中黄老浮屠并祠的重要原因。佛教跟民间信仰在汉画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亲密关系,构成了东汉宗教信仰的鲜明特色,巧妙地减少了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化解了佛教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诋毁和蔑视,维持了东汉宗教生态的稳定和和谐,为后来儒释道合流和共同铸造以人为本、仁爱通和的宗教精神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民俗宗教是多神宗教,毫无疑问,当儒教的祭典吸纳了民俗宗教的因素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肌体内注入了多神崇拜的基因。儒教的仁和之道跟道教的济世利人、佛教的慈悲普渡在本质上都是爱与和的学说,三者功德相埒,学理敏感区和精神兴奋点中有较多的心理攸同也是必然的。这就为佛教的立足提供了可能,也为三教相互融摄并以温和的方式构建多元通和生态模式奠定了基础。汉画以沉厚深邃的功力和流畅贯通的逻辑阐发了儒释道相互融贯的内在机理,在儒释道之间凿开了一条循环融合的通道。在山东嘉祥纸坊汉画墓里,出土了一块儒释道共居一处的汉画像石,画面由四层组成:第一层水人弄蛇,第二层为厅堂,屋顶有羽人,第三层周公辅成王故事,第四层为反映大乘教义的僧人诵经、拜忏、替死者超度。[28]儒释道三教在构图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亲和性,不光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教领域引入了鬼神灵物崇拜、多神多教兼容和神道人事一体的元素,弥补了儒教神灵慰藉发育不良的缺憾,而且这种神学与人学互动、人文性跟宗教性融通的作法,也受到了凭借民间祭祀和巫术活动而生存的道释二教的支持,有利于东汉宗教生态中各类宗教信仰的循环与交换。《易经·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个文化经典与时代其他宗教的关系因为人为的着意捆绑而相得益彰,更因为它们的血肉沾溉和水乳交融而继武庚续。汉画披沙拣金、显幽烛微,目光虽然落在鬼神与人生的层面,但意气早已跨越了立人立己的界限,其学理的醇度和学术的厚度给人以文化心态的抚慰和宗教信仰的餍足,那具象的表意之下潜藏甄选纠偏的深沉意蕴。
三、东汉末年宗教生态的变化不期然地为佛教的发展清除了障碍
东汉是在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因此刘秀登基伊始,举国上下便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土地兼并之风。失去土地的农民或中小地主在豪强的巧取豪夺之下,被迫沦为流民或依附民,生如草芥,饥寒切身。和帝之后,因历代皇帝践祚时年龄大多幼小,致使外戚和宦竖交相专权。政治黑暗,横征暴敛,君臣宣淫,上下同恶,朝阁内外被闹得雾烟瘴气。再加之水旱虫蝗和地震霜雹绳绳不绝,大河南北显现出一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兵燹战乱连年不断,民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力自拔。同时,儒学跟东汉谶纬神学结合后导致其思想深度大打折扣,官府所推行的名教政策也因其虚伪和欺诈,不具备动乱无序形势下作为信仰所理应具有的强大感召力、吸引力而遭遇严重的危机。传统宗教地位丧失,人们的精神支柱已达到崩溃的边缘。这些变故对东汉的宗教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宗族势力受到了冲击。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就是他带领南阳豪族集团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东汉王朝建立后,对豪族右姓始终采用“柔道”的优容政策,导致“社会上到处是豪族强宗”[29]330。这些豪族除了荫庇户口、兼并土地、包揽词讼、相互倾轧之外,还干预和控制乡里政权,扰乱和破坏地方政策的正常运行,俨然是一个不受约束的独立王国。针对这种豪族干政顽疾,官府都给予了严厉的打击,对那些仗势“侵枉”“并兼”、为害一方的豪族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剪除。如《后汉书·酷吏列传》载李章治阳平时,清河大姓赵纲不仅缮甲兵,而且起坞壁,为害所在。章“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同传又载任延拜武威太守时,田绀为武威大姓,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 一旦被满门抄斩,家族势力便立马朝盛夕衰。另外,汉画是汉代生活情境和思想意识的写真,从出土的大量执铖武士、持棒门吏和放置弩矛戟盾的武库汉画中可以看出*参见周到、李家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第26-33页;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第101-105页。,地方豪族虽然为使他者不能与争而各竞招募扩充私人军队,但在东汉末年农民接连不断的造反大潮中,也不能仗势阻挡反民打家劫舍的狂飙铁流。在武氏祠前石室第六石和后石室第七石刻绘有两幅战争画像,据叶又新、蒋英炬考证,是东汉“兵长”跟农民之间的战争。[30]在山东嘉祥宋山出土的汉画题记中,有“泰山有剧贼”的铭文,记述了公孙举在桓帝永寿二年领导农民起义的文献。[25]除此之外,出土的汉碑上也记载了一些反民打击豪强地主的史料,有些还是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过的。如灵帝建宁四年博陵太守孔彪碑上有“□以饥馑,斯多草窃”、“白日攻剽,坐家不命”[11]1379等字。三老掾赵宽碑则记载了汉族豪强在羌民的反击下,“郡县残破,吏民流散,乃徙家冯翊”[11]1645,不得不逃亡别处的史实。《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云:“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浸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亦云:“京师劫质,不避豪贵。”通过官府的抑豪举措和反民的反复扫荡,那些郡中大姓和所谓“兵长”等豪宗强族的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汉的社会结构。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行为没有将矛头直接对准宗教,但从实际效果上看,东汉的宗教生态却在这些斗争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当一门朱紫的强宗豪族遭此劫难后,常常是家破人亡、家势速衰,维系宗族组织正常运转的经济来源受到致命的重创。宗族势力的衰落直接导致宗族的凝聚力下降,举行祭祀祖先、自然神仪式时强制族人参加和分担费用的力量就会骤然减弱,阻挠和约束族人信教行为的宗族条规也会失去效用。另外,只有生活稳定、经济富裕了,人们才能把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自然神之类的宗教活动排上日程,也才有能力开展相关的信仰活动。在兵戈四起的形势下,人们都在忙于躲避祸乱,实在无暇顾及自己的祖先、自然神信仰。即使有人勉强做了,香火也难以兴旺。这导致支撑民间宗教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石和源自熟人社会的排外观念土崩瓦解,为佛教的传播消除了羁绊,创造了条件。
其次,名教受怀疑,礼法遭贬抑。当儒教在退却斑驳华彩、不能弥纶群言,变成价值荒芜的濯濯童山之后,民间信仰虽然仍在官府乡里延续,但官吏民众已在很大程度上对它流露出了敷衍塞责的态度。在东汉社会,由于传统信仰既敬重人祖天神,更倡导行善爱人,把爱当作信仰的根本属性,把激发人的善心当作重要任务,所以祭祀和信仰一直都是各个阶层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深受儒教国家的护佑。从汉画来看,东汉中期以前,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在举办各种祭祀活动时,基本上都能办得庄严肃穆、风光体面。这个时候,儒教危机尚未完全爆发,时政也未曾出现大面积动荡,宗族的势力依然稳固地把持着乡里的信仰市场,民间信仰还能够得到崇仰。例如父母将子女抚养成人,恩德重于泰山,自然会受到子女的爱戴。对于这种纯真的情感,东汉民间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在墓地用立祠和举行墓祭的行动来加以体现。王充《论衡·四讳篇》云:“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从汉画来看,墓上祠堂大多为前不设门的敞开式形制,为方便拜谒,墓主画像一般都刻绘在祠堂后壁的中心位置。围绕祠主,则衬以祠主死后所需的庖厨、乐舞、神仙等,以此来宽慰死者和表达儿女那仁爱萦怀、至诚至敬的孝心。如山东平阴县实验中学东汉墓出土的祠堂后壁画像石,西王母、东王公、电母、雨师、雷公、河伯、狩猎、乐舞和鹿车出行等陪衬于祠主的四周。[31]这种立祠以祭及缜密的画像构图勾摄出了孝子的恭谨态度。当东汉末年政治窳败、时局动荡来临时,传统信仰饱受戗害。这种戗害,其一表现为官府对国家祭祀系统的信仰活动兴趣不高,时置时废。出土《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记述鲁相乙瑛于元嘉三年上书朝廷准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以掌领孔庙礼器,诏准事的情形。[11]677《史晨前碑》记述鲁相史晨于建宁二年奏请春秋祀孔庙的相关情况。[11]1228从元嘉三年到建宁二年,两通碑相距仅十余年,孔庙祭祀就至少被废驰了两次。孔庙祭祀的废格,充分反映了东汉末年官府对待孔子那种崇奉不虔、诚心不固的态度。在名为尊儒的东汉时代,孔庙的祭祀尚且祠无常费、祭无礼器,最后败落到守庙乏人、旋举旋废的境地,其他传统祭祀所遭受的亵渎轻慢便可想而知了。刻于桓帝延熹八年的《西岳华山庙碑》记述的是弘农太守袁逢重建庙宇祭祀华山之事,其碑文有“然其所立碑石,刻记时事,文字磨灭,莫能存识”等文句[11]1103,刻于灵帝光和元年的《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亦有华山“斋衣祭器,率皆久远有垢”的表述。[32]28华山祭祀在东汉本属于国家祭祀,通过上述碑文,东汉末年官府不重视华山祭祀,致使其祭祀活动荒疏的情形可见一斑。其二表现为民众在面对先人的义海恩山时,少了真情实意,多了虚应故事。甚至为了附庸风雅,不惜东拼西凑、告朔饩羊。东汉末年动荡无序的生活使人们断了安乡重家、敬上从教之念,儒教的行为准则在民众的心间遭到解构,丧失了对民众生活行为的约束力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力,神圣的祖先崇拜在人们的心中也变得祭而无虔、信而不诚。这种在丧葬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和游戏心态,使东汉末年的汉画葬俗越发显得假模假式、光怪陆离。汉代修筑画像墓原本是孝道的表现,但发展到东汉末年的时候,这种建立在儒家伦理和礼仪基础上的丧葬习俗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出现了画像石、画像墓再用和再葬的奇怪现象。所谓再用,就是用原墓部分或全部画像砖石异地重建墓室;所谓再葬,就是在先前的汉画墓中再葬入后死之人。目前,经过科学认定的此类墓葬已经发现了近20座。如《文物》2003年第4期报道的徐州大庙汉画像石墓,《文物》1994年第6期报道的山东邹城高李村汉画像石墓,《文物》1990年第9期报道的徐州铜山汉王纪年汉画像石墓,《考古》1975年第2期报道的山东苍山元嘉元年汉画像石墓等,都很具有代表性。再用再葬汉画墓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不仅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且形成了社会风气,与儒教的“报本返始”、敬重先人的要求已相去甚远。祠无常费的社会现实和牵萝补屋的丧葬态度,显然跟儒教在东汉末年社会生活中已疏离主流、局促文化边缘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它严重破坏甚至解构了民间宗教的生存条件,妨碍了传统信仰的延续,促使遏制佛教发展的重要传统力量——祖先崇拜衰落,为佛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再次,时政黑暗,民心苦闷。虽然宦官外戚交替掌权导致了“政化陵迟,汉祚衰微”的动荡局面,但这种“宦官权重,椒房宠盛”的执政格局在东汉末年却给宗教信仰的自由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个时期,在接二连三发生的“外戚之祸”“宦官之祸”与“党锢之祸”中,许多豪族甚至付出了身死族灭的惨重代价,生存空间几乎被挤压得荡然无存。这种窘状在汉画中也有反映。如在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出土的“党锢之祸”画像石上,手持麾的官吏正在指挥抓捕手捧竹简的文人。[33]这种近似白色恐怖的严酷现实改变着人们对于时事的看法,政治参与的忧惧体验也让他们心灰意冷。好多人在困迫遁走、望门投止的同时,内心跟道教的清虚理念相共鸣,把神仙逍遥自在、隐形遁迹当作增进福祉的源泉和自己生命的归宿,修仙访道成了东汉末年达官贵人和黔首百姓灵魂鹜趋的幸福热土。现在从四川长宁七个洞熹平元年纪年崖墓、四川泸州大驿坝1号汉墓、四川荥经陶家拐汉墓等出土很多的胜纹符号、玄武符号、双结龙符号、复文道符、炼丹图、金丹图、房中图的细腻刻绘中仍能看见当时那种升蹑仙迹、继续仙志的情志闪光。人们通过这些刊绘于石的图像,做足了性命双修和跟至道通情的功夫。由于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做支撑,所以这个阶段的道教发展很快。在此情况下,跟道教东鸣西应、依门傍户的佛教注重开展社会服务和在民间传教收徒,影响得到扩大,出土汉画和传世文献中开始密集地出现佛教信息,明帝永平至桓帝建和年间佛音百年罕见的现象得到改观,其传播开始走出低谷。与此同时,从大批应龙、射日、虎食女魃等图像的出土来看,此时的巫术也相当活跃,发展势头异常迅猛。各色信仰纷至沓来,蔚然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把东汉末年的宗教百花园装扮得姹紫嫣红、气象万千。这些信仰间虽然有竞争、碰撞,但总体上能和谐相处、理性互动。这种和谐融洽的宗教关系使桓帝统治的二十余年间,至少有十年实现了“四方安静”,未曾发生过大的政教冲突和宗教冲突。如果维持这种和谐局面的各种条件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在东汉末年尽管祖先崇拜和自然神信仰的根基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仍有理由相信,各种信仰还是能够迸发出很强的活力,并在相互依存的发展格局中而各得其所的。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生机盎然、和谐共存的宗教生态,随着一批被末世论武装头脑、有着强烈救世使命的道教徒发动了旨在推翻东汉统治的黄巾起义,不复存在。
黄巾起义后焚烧衙门,捕杀官吏,进攻坞壁,一时造成政教关系极度紧张。在东汉官府和地主豪右的严酷镇压下,道教的传播大受影响,使得东汉末年的宗教生态急剧恶化。
由于乱世更需要有新的价值标准来抚顺人心和维持安定,在东汉末年,与对道教不信不扶的政策不同,官府对佛徒相当宽容仁厚,少有类似道教的严苛要求和制约。不仅有“其有奉佛五戒勿坐”的规定,而且从《吴志·刘繇传》可知,东汉末年在“亩税十钱”、“征役无度”,赋税徭役奇重的情况下,僧尼竟不负担兵徭赋税。在经费上,佛教也有独到的优势。东汉时期的佛寺没有自立经济,其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供养。这在政治高于宗教、权贵身份高于教徒身份的年代,政治上这种优礼与笼络并施的宗教措施,能给佛教的扩张带来很多便利。因为这种支持不光表现了官府的宗教立场,使佛教具有了合法的属性,而且也让传教之人能够在生计无忧的条件下安心译经讲习和弘教宣法。佛教兴盛与道教衰败所构成的这种反相关性关系,现在从佛教汉画的出土情况中仍能看得很清楚——凡是佛教汉画出土较多的地区,必定是东汉末年道教汉画最丰富、道教势力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例如齐鲁和汉中地区,均是道教题材汉画出土最多的地区,也是在东汉末年道教所受打击最剧、宗教生态失衡最严重的地区。然而正是这样的地区,佛教发展却异常迅速,相关汉画也出土最多。由于受政权的支持,所以佛教就能快速发展。而同样具有信众和市场的道教,则在东汉末年迅速凋零、节节败退。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曾精辟指出:“道教的命运不济,错过了大发展的机会,让佛教占先了一步。”在东汉末年信仰真空和信仰危机的背景下,佛教影响渐大,社会不同人群所释放的信仰需求为佛教提供了一个旺盛的市场。佛教依附道教的色彩日趋浅淡,争胜的调子逐渐响亮,从此结束了边缘化的生存方式而开始进行独立公开的活动。这一时期的佛教汉画显示,政教关系和信仰结构的双双改变共同成就了东汉末年宗教生态的新版图。
汉画提示我们:信仰行为本身是复杂的。一方面,信仰什么宗教从表面上看似乎取决于个体的需求,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但从相关汉画来看,一种宗教要做到“本土化”和能否为人们顺利接受、奉行,并不仅仅是信仰者意志的自由表达,其背后总是有来自国家权力逻辑和传统文化知识谱系的支配。自从道教跟官府交恶以后,道风日散,妙法真谛浸淫人心之力渐衰。这种宗教生态结构的重大调整在客观上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消除了竞争;另一方面,人们接受某种宗教主要是看它自身的积储逻辑和运作程式能否符合他们的需要。如果提供的精神产品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么制度的强制力即使再大,也很难从根本上阻挡人们皈依它的步伐。面对苦难的现实,正是出于这样的功利性原因,象征超越生死的舍利、莲花、佛塔图像和表示六道轮回、地狱救赎观念的佛像等便在这一时期墓穴门楣和摇钱树上频繁出现了。前者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中“仙人骑白象”、“猞猁”画像和什邡东汉画像砖上佛塔、莲花图案,后者如陕西城固东汉砖石墓中摇钱树顶端手执六道轮回之轮佛像和安县摇钱树顶端手持六道轮回之轮的佛像。佛教不仅把自己跟儒道二教共有的本质、经验和目的等疑难问题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紧迫议题作出振聋发聩的阐发,使人们认识到佛教跟儒道同脉所系,在儒道的信仰之外还有一种叫作佛的神可以帮助他们;而且针对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难题,特别是黑暗社会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佛教以拯济众生的胸怀积极承当,把引导人们实现精神救赎、解脱、觉悟的实践当作中心任务,来迎合当时社会的宗教消费需求。这种实践主张,在讲求祈福许愿、治病驱邪信仰功利性且宗教生态发生深刻变革的东汉末年,为佛教实现与其他宗教形成互补关系、顺利融入素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华社会奠定了基础。由于佛教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学说启人之处甚多,能给那些走投无路、精神迷茫的人们提供心灵慰藉和自我救赎的药方,所以人们乐意将自己的宗教情感投向佛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光攻击诋毁失去了效用,而且佛教外来身份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在宗教服务与民众需求的交换过程中得到了遮掩。佛教适应时代特点和结合传教要求进行的实践创新,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它这种救心解难的宗教。东汉墓葬中刻绘反映佛教教理教义图像的广泛出土,说明佛教这份令人心动血热的精神遗产,确实是在波谲云诡、风雨如晦的东汉末年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弦。此类汉画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佛教的迎拒态度和应变策略,展现了佛教与社会大众、政治文化之间复杂而精巧的互动关系。
另外,与跟道教具有密切关系的曹操宗族墓出土的“苍天乃死”字砖不同,东汉末年佛教画像和铭文中至今也未发现有违逆朝廷旨意的内容。遵守政主教从规则,在与其他信仰和平共处、互尊互学中,探索自己的本土化和本色化,未与东汉的乡里社会、各级官府和其他信仰间发生过激烈冲突。佛教坚守这种温和主义生存策略,自然就不会引起官府的警觉而受到严苛的管束。从这个意义上说,信仰需求扩大、官府及民众的认可共同孕育了东汉末年佛教的辉煌。
综上所述,宗教文化是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宗教生态也是一个内部不断循环、更新,外部不断交换、调节的互动系统。东汉宗教生态格局所发生的变迁是其文化共同体内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宗教与非宗教因素在出土的东汉宗教题材画像中蕴涵十分丰富,展示的东汉宗教生态鲜活直观。佛教汉画视野宏阔、立意高远,其吐纳驰辩为我们考察东汉宗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出土佛教题材汉画入手披阅、检核东汉宗教生态变迁的路径与步履,发现它跟东汉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具有密切关系。宗教生态的平衡与否固然与外来宗教能否与本土传统信仰和谐相处有关,但出土佛教汉画表明,宗教跟外部条件的良性互动也是重要条件,特别是在宗教管理方面倾向于封闭和专断的东汉王朝,政治的力量更是维持宗教生态平衡的关键。在封建专制、政治强权的背景下,政主教从关系并不影响宗教的独立性。如果哪一种宗教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面临被铲除的命运。反之,就会得到认可而受到优待,获得相对宽松的生长环境。面对历史提供的发展机会,佛教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它虽然把花开在了天国,但却将根深植在了尘世。佛教在跟东汉的社群共同体及社会文化系统相依互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与民众、官府的关系,造成了东汉宗教生态的明显变化,为异质文化成功融入中国传统社会树立了典范。
[1]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1)[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
[2]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市王庄汉画像石墓[J].中原文物,1985(3):26—35.
[3]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河南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J].文物,1984(3):25—37.
[4] 马汉国.微山汉画像石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5] 杨爱国.汉代画像石榜题略论[J].考古,2005,(5):59—72.
[6] 万鹏均,张勋燎.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题记的时代和有关问题的讨论[J].考古,1980(3):271—278.
[7] 牟钟鉴.宗教生态论[J].世界宗教文化,2012(1):1—10.
[8] 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J].考古,1979(9):1—6.
[9] 韩玉祥,曹新洲.南阳汉画石精粹[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5.
[10] 苏健.洛阳汉代彩绘[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6.
[11] 徐玉立.汉碑全集[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
[12] 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N].中国文物报,2002-7-5.
[13] 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肥致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2(9):37—42.
[14] 郗文倩. 张衡《西京赋》“鱼龙曼延”发覆[J].文学遗产,2012(6):15—27.
[15] 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 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
[17] 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象石墓和壁画墓[J].文物,1972(10):49—55.
[18] 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9] 赵成甫.南阳汉代画像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20]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1] 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J].文物,2004(10):61—71.
[22] 朱浒.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87-92.
[23] 黄亚峰.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24] 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25] 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J].文物,1982(5):60—70.
[26] 罗二虎.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J].考古,2005(6):66-73.
[27] 李淞.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8] 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纸坊画像石墓[J].文物,1986(5):31—41.
[29]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0] 叶又新,蒋英炬.武氏祠“水陆攻战”图新释[J].文史哲,1986(3):64—69.
[31] 平阴县博物馆.山东平阴县实验中学出土汉画像石[J].华夏考古,2008(3):32-36.
[32] 洪适.隶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 管恩洁,霍启明,尹世娟.山东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J].东南文化,1999(6):45—55.
[责任编辑 阳 欣]
On the Change of Religious Ecological Pattern Based on Unearthed Buddhist Paintings of Eastern Han Dynasty
LIU K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473061, China)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ecology changed greatl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new religious ecology formed thereafter had obvious Buddhist characteristics. Unearthed Han paintings with Buddhist themes (which includes stone reliefs, brick reliefs, tomb murals, bronze mirrors, inscriptions, etc) almost recorded simultaneously this process. According to Buddhism paintings of the Han Dynasty, this change resulted from conflict and blending of plenty factors at that time: the overall situ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form of express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religious system. Under spe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 sharp contradiction existed between Buddhist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religious constitution foundation, which formed a serious obstacle for the spread of Buddhism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commonality between the leniency doctrine of Buddhism and the Renhe (benevolence and harmony)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the Xujing (emptiness and quiescence) principle of Taoism.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social crisis destroyed the system support of traditional religion an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ancestor, nature worship. Political reign and peasant revolt stroke the clan force and changed profoundly the social structure. All these conditions eliminated the barriers for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lso, this helped the formation of a compatible, complementary and multi-variant religious ecology where politics centers with religion as a supplement. Buddhist paintings of the Han Dynasty are set on a high vision, and provide rare and valuable materials for studying Han religious ecology, which is of high academic value.
Buddhist paintings of the Han Dynasty; religious ecology; religious relations; social structure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16
2016-03-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宗教题材汉画整理与汉代宗教生态研究”(14BZJ003)
刘克(1964-),男,河南南阳人,南阳师范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宗教研究。
J196.2; K234.2
A
1001-6597(2016)05-009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