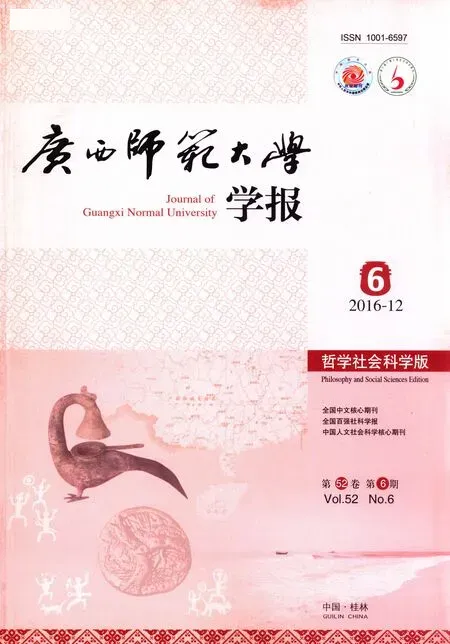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思考
张 坚
(桂林旅游学院教务处,广西桂林541006)
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思考
张 坚
(桂林旅游学院教务处,广西桂林541006)
海外华侨属于和平的经济移民。一战后,随着东南亚华侨当地化趋势的日益加强,他们渐渐成为相对独立于中国的经济实体,他们的行动除了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更多地受到当地社会的左右。近代以来,东南亚华侨在政治上属于被歧视、虐待的少数民族,抗战前后,他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属于双向互动行为,抵制日货运动反映了他们希望得到中国政府有效保护、抗击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侵吞、维护生存发展权利的诉求。
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与世界其他地区华侨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广大华侨积极捐资捐物、购买国债、回国参战等运动一道,构成了海外华侨支持中国反抗外侮的另一道血肉长城,彪炳史册。
一、抵制日货运动是学界关注东南亚华侨与中国交往关系的焦点之一
长期以来,对于海外华侨支持祖国的抗战行为(包括抵制日货运动),国内外学界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国内,早在抗战前后,黄竞初、刘士木、何汉文、丘守愚、姚楠、丘汉平、李长傅、陈达等学界前辈先后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①*[收稿日期] 2016-07-20[作者简介] 张坚(1972-),男,广西宾阳人,桂林旅游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① 参见:黄竞初著:《南洋华侨》,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刘士木著:《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1年版;何汉文著:《华侨概况》,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丘守愚著:《二十世纪之南洋》,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姚楠著:《中南半岛华侨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5年重庆初版;丘汉平、庄祖同编撰:《华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李长傅著:《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他们的研究成果,给后人全面了解中国抗战前后东南亚地区华侨在当地生存发展状况、客观评价华侨对中国抗战的贡献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新中国成立后,在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过程中,海外华侨抵制日货运动也成为学者们颂扬华侨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观测点。例如:黄慰慈、许肖生在其文章《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载《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中,用科学的数据、鲜活的例子,概括了1937年至1941年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的突出贡献。抵制日货运动是文章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分析了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与美国)华侨抵制的措施及其成效。 以林金枝、吴凤斌、郭梁(李国梁)、蔡仁龙、任贵祥、庄国土等为代表的侨史研究专家,都对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抵制日货运动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参见: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凤斌主编:《东南亚华侨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庄国土著:《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郭梁著:《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任贵祥著:《华夏向心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1987年,郭梁、蔡仁龙等人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大量翻阅了民国时期东南亚华文报刊、中国国内报刊以及政府档案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一书,该资料集共有750多页,收集了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人、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海外华侨抗战运动的重要讲话、电文,东南亚各地区侨领、普通华侨民众支持祖国、回国参战、抵制日货、毁家纾难等具体史实。筚路蓝缕,开启山林,郭梁、蔡仁龙等人在基础研究工作方面的辛勤付出,为后人客观评价华侨与中国抗战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在上述资料整理的基础上,郭梁与林金枝等人还共同完成了《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书,作者在书中用翔实的数据,介绍了抵制日货运动给日本在东南亚市场带来的重大经济损失,以及我国国货因此在当地销量大增的事实。作者认为:海外华侨华人抵制日货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有成效的运动之一,“它给日本经济以重大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本的军事侵略力量”。[1]197庄国土在其著作中,特别提醒学界注意:日本人的经济侵吞是促使广大东南亚华侨华人抵制日货、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重要推动力。[2]216-219
2015年,由香港文化生活基金会与香港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手编纂的大型图书《东南亚华侨抗日史料丛书》正式出版,丛书包括16分册(包括图书和音像资料),汇集了日本侵华(尤其是1942年日本入侵东南亚)之后,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等地华侨华人抗日运动的史料。大量亲历者(亲自参加抗战、被日本侵略者迫害的侨领及普通华侨)的回忆录、图片资料,是该丛书的一大亮点。丛书对于世人了解东南亚华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尤其是日本入侵东南亚后对当地华侨华人疯狂报复、屠杀的暴行)提供了难得的一手史料。丛书也从海外华侨的角度,使世人了解了东南亚华侨支持中国抗战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除了我国政府与社会各界外,日本政府也对海外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行动给予了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日俄战争以后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和国策会社调查机构对南洋华侨展开调查,整理出版的资料多达400余种。[3]其中,长篇调查报告书100多种,短篇调查报告书300多种。1968年以来,日本陆续公开这批调查报告资料,分别收录在《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出版)、《现代史资料》(三岭书房出版)、《南方史料丛书》(青史社出版)、《南方军政关系史料》和《20世纪日本关于亚洲研究重要资料(3)》(龙溪书舍出版)等大型历史文献集中,总计达200余种。中国台湾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注意到台湾总督府、台湾银行关于南洋华侨调查报告书的学术研究价值,选编选译了这批文献资料。杨建成主编的《南洋研究史料丛刊》(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 -1986年印行)中收录了13种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和满铁调查部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共出版三辑。龙溪书舍2003年整理出版的48种关于南洋华侨的调查报告书,暨南大学崔丕等人将其翻译成《日本对南洋华侨调查资料选编(1925-1945)》第1-3辑,2011年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如:1925-1944年,日本政府以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等“国策会社”组成的调查团,对南洋华侨作了专门调查,即“南洋华侨调查”。该项调查是日本军国主义实施“南进”政策的产物,该调查结果对日本政府的“南进”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南洋华侨调查”活动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战时中国经济与南洋侨汇关系调查、南洋华侨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调查、南洋华侨侨领及社团调查、南洋华侨与其他种族关系调查等课题。1941年10月5日,日本东亚研究所第三调查委员会出版了《南洋华侨调查结果概要》,该书全面概括分析了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各个阶段及其特点。在评价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程度时,调查者的结论是:“我国对南洋出口贸易的下降,主要受南洋各国的不景气、我国向战时经济体制的转换而来的出口统制、因国内原因引起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南洋各国的进口统制等因素的影响,受华侨抵制日货影响的因素并不明显。从南洋各国进口贸易的下降,主要受南洋各国的输出统制政策的影响。”[3]可见,全面抗战爆发后,对于日本经济力量在东南亚市场上地位下降的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并不是主要受到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
1968年,新加坡南洋学会主办的《南洋学报》第23卷第l-2期合订本上,刊登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比弗福尔斯市杰尼瓦大学美籍日本学者明石阳至的文章《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作者根据日本政府“南洋华侨调查”的资料,以及日本外务省留存的二战期间日本驻东南亚各地领事向日本外务大臣所作报告的档案,西方学者有关南洋华侨的英文著作、资料,深入分析了1908-1928年东南亚华侨历次抵制日货运动的经过、特点及其背后的原因。明石阳至逐一分析了东南亚地区华侨配合中国国内形势先后开展的7次抵制日货运动。作者强调:每一次抵制日货运动激烈程度、效果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次抵制,东南亚不同地区华侨抵制的效果也相去甚远。[4]
可见,中日两国学界有关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其中,抵制的目的、抵制的成效构成了两国学界突出的差异,这意味着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还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 鉴此,笔者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影印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辅之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与中国政府交往的电文、档案以及当时中国报刊、华侨社会华文报刊相关报道,重新审视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
二、牢记华侨华人属于和平经济移民的基本属性,是研究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的基调
马克思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每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每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5]9也就是说,生存发展权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包括国家、民族、阶层等)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在研究华侨与中国交往关系时值得特别强调。
近代以来,自发移居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他们在本质上属于和平的经济移民,他们移民海外的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在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无政治目的;并且,华侨从走出国门到扎根当地,并无政府的扶持,全都依靠自身力量。华侨属于和平经济移民的基本属性,使他们与近代西方殖民者存在本质的差别。后者在政府的扶持或军事保护下,在移居地从事大量殖民侵略活动。
事实上,一战爆发后,受东南亚当地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华侨在当地支柱产业,如橡胶、大米、蔗糖生产加工等领域中,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华侨金融业、航运业等也取得长足进步,出现了能够在生产、加工、流通等领域同时拥有产业的华侨企业集团,如新加坡的陈嘉庚橡胶加工企业、林秉祥和丰公司,暹罗的陈守明“黉利企业集团”、蚁光炎“光兴利企业集团”,荷印地区以黄仲涵为首的建源公司等。[6]102-108[7]117-125上述经济进步意味着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发展逐渐立体化、当地化,他们构成了当地民族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最紧密、最活跃的部分。另外,一战之后,华侨移居东南亚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华侨新客人数剧增,与近代以来广大华侨男性只身下南洋、把家眷留在家乡不同,越来越多的华侨新客把家眷一起带到了东南亚谋生。[8]641-644上述情形表明:华侨生产、生活的当地化趋势已经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他们与祖籍国(中国)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扎根于当地,成为他们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所在。
因此,在经济当地化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大多数华侨更多地考虑如何维护自己在当地的经济利益,谋求在当地的长远发展,而决不像部分学者所说的那样,华侨的行为举止,主要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而不是当地社会发展环境对他们的决定作用。
这是我们研究东南亚华侨与中国关系(包括华侨抵制日货运动)必须把握的基调。
三、全面把握东南亚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环境,是客观评价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行动的关键
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积极响应国内的号召,多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从该运动的动力源来看,国内是东南亚地区抵制运动的主要源头;从表现形式来看,抵制跟国内一样,都是以拒卖、拒买日货为武器,对日本经济予以打击。亦因此,不少学者习惯于把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视为国内抵制运动在海外的延伸。
事实上,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与国内商人抵制日货存在本质区别。突出表现在:国内商人的抵制运动属于国家行为,抵制不仅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从商人到消费者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人们同仇敌忾,共同抵制日货,日本商品便很快在中国市场无法立足,从而受到巨大损失。相比之下,华侨在东南亚地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受到当地大环境(包括当地政府的华侨政策、当地土著民族与华侨的关系、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的直接制约,因此,华商在东南亚地区的抵制行为不能与国内的抵制划等号。
(一)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缺乏中国政府强有力的保护
在近代,虽然在东南亚地区居住的华侨华人多达六七百万人,虽然这支力量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在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国家与地区中,少有南洋地区如此重要的”[9]90,但直到抗战胜利前,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把东南亚地区放在与欧美日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这充分体现在政府外交部门的政策设置当中,“在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处理菲律宾外交事宜的主管机关是美洲司,处理缅甸、安南、马来半岛与所谓荷属印度的外交事宜的主管机关是欧洲司,只有暹罗是属于亚洲司”[9]90。由于当时中暹两国尚未建交,因此,整个亚洲司实际上在保护华侨方面形同虚设。上述外交机构的设置情形,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地区既缺乏战略眼光,也缺乏密切交往的渠道。
由于对东南亚地区战略地位估计不足,因此,中国在当地派驻的领事屈指可数,20世纪30年代一份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的领事馆仅有十个,主要集中在荷属东印度地区、英属马来亚和菲律宾地区,在华侨总人口达到300万的暹罗和越南,竟然没有设立领事馆。[10]253-254
对于中国政府在南洋地区设领情况,当地华侨甚为不满,他们认为:“我国民居留海外,达七百万,南洋占十之八,多于日本万倍有余,他国勿论矣,而领事之多,不如日本。”[11]由于中国领事数量太少,因此,当地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排华。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即便是在派驻了领事的地区,领事馆也难以发挥太大作用。例如在荷属东印度地区,由于腐败的晚清政府与荷兰及其他西方国家签订外交条约时,允许荷兰政府享受片面最惠国待遇,换言之,荷兰国民在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我国臣民在荷兰及其属国则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上述不平等条约给荷兰殖民政府在东印度地区歧视、虐待华侨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
一战后,在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包括东南亚在内的西方殖民地人民先后吹响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受西方殖民政府长期以来“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以及一战后西方殖民者的挑拨,东南亚当地民族主义者将矛头指向了华侨华人。暹罗(泰国)、菲律宾、越南、荷属东印度等地区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排华事件包括:暹罗政府以颁布实施新的国籍法、征兵制为抓手的同化政策,菲律宾针对华侨的“经济独立运动”,越南海防的排华案以及英属新马地区打击国民党势力和华文教育的行为等。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919年,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荷属东印度地区华侨积极奔走,要求中国政府藉此机会改变他们在当地受歧视、虐待的现状。暹罗、越南等地华侨也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借机与当地政府建交、派遣领事,对当地华侨华人实施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斗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7]200-220广大华侨在当地面对各种不平等待遇,仍然“呼吁无门,含辛莫诉也”[11]。
(二)华侨中介商经济地位十分被动,其发展根基极其脆弱
国内学界之所以对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运动长期缺乏客观评价,原因之一在于对华侨中介商地位的认识存在偏差。 华侨中介商亦称仲介商、居间商、中间阶级,英文称Supplant、Supplement等[12]430,包括东南亚各地区的华侨批发零售商,分布在当地矿山、种植园和农村的杂货店店主以及穿行于城乡的华侨货郎等。中介商主要负责沟通东南亚各地区之间、各地区城乡之间、东南亚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经济交往。具体而言,华侨中介商作为中间人,一方面将当地土著居民生产的原料产品收购后卖给西方殖民者在当地开设的大公司,另一方面又将西方大公司制造的生产、生活消费品销售给当地居民。
由于华侨中介商在当地经济交往体系中扮演上述角色,部分学者由此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华侨中介商控制着西方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华侨已经掌握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命脉。
笔者曾在《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华侨中介商经济地位新探》一文中指出:东南亚华侨中介商作为一支介于西方殖民统治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中间力量,受到上、下两方面的制约。具体而言,从其上方来看,由于当地工业极其落后,中介商所销售的商品以及其收购的原料产品在数量与价格上受制于西方资本;从其下方来看,在商品销售环节,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与消费喜好,直接决定华侨中介商生意的好坏。因此,华侨中介商的地位十分被动,其发展之路十分艰难。[13]
一战后,为了对付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商人,日本政府组织了大批学者和官员前往东南亚开展调查。[14]结果发现:当地华侨经济过分集中于中介商层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强大。当时日本人竹井天海在其所著《南洋》一书中,认为东南亚华侨在经济实力方面,“有‘量’的势力,而无‘质’的势力,有平面的势力,而无立体的势力也”。[15]竹井天海上述评价道出了东南亚华侨经济的硬伤,消除了日本人对华商所怀有的畏惧心理,刺激了他们进军东南亚,侵吞华侨经济地盘的野心。
一战爆发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营建由日本人操纵的东南亚经济网络,以此彻底击垮华侨经济力量。为此,日本政府在资金、商品、运输、销售等方面大力扶持日本商人在当地的发展。长期关注日本侵吞东南亚华侨经济行为的学者刘士木在其著作《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一书中,特别记录了当时日本政府的上述举措。日本先后在南洋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三井银行等银行,这些银行“带有政治性质,借资日侨,维持日侨商业”[16]410。与此同时,日本设立了邮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和南洋邮船会社等四家航运公司,上述航运公司共有汽船约70艘,专门负责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商品运输,“日政府凡遇航业界不稳年度,必予以相当之津贴”[16]411。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日本商品在运费方面占据绝对优势。20年代初,日本航运公司所运输货物的运费,由上海至爪哇每吨12元,由爪哇至香港每吨11元,由日本至爪哇仅每吨8元而已。从距离来看,日本到爪哇,远长于上海到爪哇、香港到爪哇的距离,但运费却最低。日本政府在运输方面给予本国商品的扶持力度让人吃惊。
正是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日本中介商的力量在东南亚市场上迅速膨胀,“凡彼处自(行)车通达之处,(日商)遍设售卖日货商店,极受土人欢迎,势力逐渐发展”[17]289。在新加坡的日本商店,大战前只有28间,到大战结束时,已增至78间,而且日本商人的数目亦由原来的数百人增至5 000人左右。[18]164“在马来半岛,日本为欲推销日货,日商入乡与土人结拜,领导土人组织合作社等等,全部销售日货,日方予以种种利便。”[19]135在荷印地区,许多日本人经营糖厂、茶厂、农园等,规模大、资本足,经营手段灵活,逐渐占据了广大的销售市场,华人华侨的经营越来越困难,产品销路受到日货冲击。
一战后,面对日本商人的疯狂扩张,东南亚华侨社会有识之士深感忧虑。陈嘉庚曾痛心疾首地说:以前华商经营各项日用品,多自日本运来,“其后日本训练组织知识分子,散布各处,自行推销与华侨竞争”,华商受此打击甚为惨重。[20]3
四、抵制日货运动使东南亚华侨遭受巨大损失
近代以来,由于华侨在东南亚大都属于被歧视、被虐待的少数民族,他们在经济上也只拥有平面、而非立体的经济优势,因此,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召唤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时,他们在当地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此事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反日怒潮。
在东南亚,当地华侨响应祖国号召,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但由于一战爆发,原来垄断了东南亚市场的欧洲商品数量锐减,日货取代欧货,成为华侨中介商经营的主要商品,抵制日货无异于自断财路。当时爪哇地区一个商会派人向当地华商宣传抵制日货,倡用国货。当地一位闽籍华侨瓷器商向商会提出抗议,他曾响应商会的号召,停止销售日货,从国内购进了几十箱瓷盘,但销售时却碰上了种种困难。因为国产瓷盘与日产瓷盘相比,虽然工艺比日货精细,但式样远不如日货多,并且日货价格低廉,甚受当地居民欢迎,而国货价格昂贵,即使按原价销售,当地居民也不理会。更可气的是,他从国内购进的几十箱瓷器中,因装运而受损坏的极多,运费也不菲,而日货在装运过程中十分小心,受损极少,即使部分受损,厂家也立即照赔,并且运费也很低廉。在上述情况下,抵制日货、销售国货明摆着是把赚钱的机会让给别人,而自己却去做亏本生意。该商人诘问当地商会:“今欲推销华货,恐我妻子老少均将冻馁耳,贵会能补助我养家费乎?则我实甘心专销华货。”[21]商会无言以对,当地的抵制运动遂不了了之。
上述情况在当时东南亚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从整体上看,1915年东南亚华侨抵制行动不甚坚决,抵制的实际效果也不甚理想。日本在东南亚各地区贸易中,除了荷属东印度与暹罗两地区所受打击较为严重外,在海峡殖民地与菲律宾的贸易并无太大变化。整个东南亚地区,抵制日货运动从6月份开始后曾一度打击了日本商品的销售,但到7月份,日本与东南亚各地(荷印地区除外)的贸易额已经开始大幅度增长,到8月份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抵制前的水平。对此,明石阳至认为:“1915年南洋华侨的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并不属于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22]
1919年东南亚华侨在中国爱国人士的号召下,发起支持五四运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其规模与效果远远超过了1915年。之所以取得上述成果,这一时期东南亚经济景气、当地华侨工商业的长足进步、国货运抵东南亚市场数量的充足,使华侨商人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日货的垄断地位,成为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主义浪潮推动下,广大华侨认同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积极抵制日货、捐资捐物或亲自回国抗战,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爱国行动在给中国抗战以极大的支持的同时,由于他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依赖日货的被动地位,抵制运动使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面临严重的危机。
对于华侨商人严重依赖日货的情形,明石阳至指出,20世纪30年代之前,华侨商人以经营日货为生。廉价的日本商品是日本政府一战后专门针对东南亚地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当地土著居民量身定制的,几乎占据了当地全部市场。而华侨商人作为销售日货的中间商,他们如果不经营日货,那么不可避免地面临无货可售或无利可图的危险。也正是出于上述顾虑,东南亚一部分华侨并不很情愿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当地华侨的激进分子(锄奸团、铁血队等)在抵制当中频频采取强制性手段,则从侧面表明了华侨商人的不情愿。[4]
明石阳至的上述观点,在有识之士的言论当中得到印证。抗战时期,我国著名东南亚研究专家、《南洋研究》创办者刘士木在翻译日本《时事新报》记者松村之助所著《日本之南生命线》时,特别在译序中强调:日人提倡日人自卖日货于南洋,不假手于华侨,而华侨抵制日货之威胁,已为之打销,而且曩昔华侨惟恃代销日货,以谋余利者,至此亦失其根据,而反惟恐不能仰日人鼻息。即此一端,日本人在南洋,已足以致华侨死命而有余。[23]刘士木长期关注海外华侨问题,他根据华侨对廉价日货的严重依赖而推导出日本人操控华侨在当地的生存发展的观点,可谓鞭辟入里。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春夏日本入侵东南亚,对长期支持中国抗战的华侨华人疯狂报复。日本侵略者在新加坡实施了与南京大屠杀、菲律宾大屠杀并称二战期间日本滥杀无辜的三大惨案之一——新加坡“大检证”,数以万计的华侨华人丧失了生命。据统计,在日本占领期间,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被屠杀人数达到了50万以上,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此外,日本侵略者专门针对华侨征收“奉纳金”的政策,使东南亚华侨经济面临灭顶之灾。[7]735-738为了避免日本人的打击报复,数以万计的华侨被迫逃离他们生活了多年的东南亚地区,回到中国。余下的华侨华人在日本的统治下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太平洋战争成为了东南亚华侨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五、结语
综上所述,抗战前后,东南亚华侨在政治上缺乏中国政府有效的保护,在当地长期遭受歧视与虐待,在经济上只在中介商的层面拥有平面、而非立体优势的不利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响应国内的号召,开展抵制运动,这足以反映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2015年9月5日,厦门大学李国梁教授在福建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上强调:中华民族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除了大家所熟知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之外,还应该包括一个由世界各地华侨开辟、范围更为广大的“海外战场”。该战场是广大华侨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侨居地政府的干涉、限制甚至镇压的背景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加以维持与推进的。李教授认为:历史工作者只有充分认识到“海外战场”中广大华侨支持中国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才能深刻理解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赤诚,了解他们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所建立的特殊功勋,了解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
事实上,由于一战后东南亚华侨经济当地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他们与中国属于相对独立经济实体的属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华侨与中国的交往属于双向互动的过程。双方的交往,既有中国政府利用华侨为自身政策服务的一面,也有海外华侨需要中国政府支持帮助的一面。在20世纪初直到抗战胜利前,东南亚华侨除了多次开展抵制日货、支持祖国反抗日本侵略,还多次呼吁我国政府利用一战结束、我国作为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的机会,通过与荷兰修订不平等条约、在暹罗建交遣使、在越南派驻领事等措施,改变自身在当地受歧视、受虐待的地位,为自己在当地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机会。对于海外华侨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在修约运动中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各种请求,中国政府在受到外来侵略、国力羸弱的情况下,无暇顾及,因此,东南亚华侨要求中国政府给予保护的呼声被长期淹没在历史大潮当中。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明显的狭隘性与自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实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局部利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全民族各个阶层人民局部利益的总和。大多数情况下,民族主义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整体利益,往往牺牲本民族部分阶层的局部利益。[24]14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是每一个民族成员获得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民族主义大旗的指引下,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愿意抛弃自己的个体利益,为实现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必须指出的是,在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过程中,各阶层民众个体利益的实现程度关系到他们此后对民族国家的效忠程度。因此,从维护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顾全大局,舍弃局部利益。但这种做法必须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它会伤害民族当中部分群体的利益,继而削弱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最终损害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20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生存发展的地位,不断吹响民族主义的战斗号角,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抗争。在此过程中,海外华侨以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斗争史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斗争任务艰巨,因此,中国历届政府常利用华侨力量为祖国服务,而很少利用祖国的力量为华侨服务。如何根据华侨经济当地化、华侨与中国在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客观事实,从长远发展出发帮助华侨更好地立足于当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中国政府足够的重视。受此影响,在20世纪初,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国家兴起的关键时刻,东南亚华侨没有及时顺应经济当地化的潮流,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积极谋求当地化,没有及时把自己在当地的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上的优势,导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处于劣势。
可以说,上述结果正是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给东南亚华侨带来的负面影响,亦因此,时至今日,部分学者仍然否认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属于相对独立的实体,看不到二者之间的交往属于双向互动的关系,仍然从单向的角度、以单线的方式来研究东南亚华侨与中国的交往。这也正是今天我们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并引以为训的原因所在。
[1] 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2] 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 纪宗安,崔丕.日本对南洋的调查及其影响(1925—1945)[J].中国社会科学,2009(1):190-203.
[4] 明石阳至(Yoji Akashi).1908-1928年南洋华侨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关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的研究(下)[G]//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资料译丛:第4辑.2000.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郭梁.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7] 张坚.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发展研究(1912-1928)[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吴凤斌.东南亚华侨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9] 陈序经.南洋与中国[M].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
[10] (日)长野朗.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M].黄朝琴,译.广州: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
[11] 南洋荷属婆罗洲山口洋华侨代表邓克辛呈文(1917年9月8日)[B].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1001,案卷号1410.
[12] V.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3] 张坚.二十世纪初东南亚华侨中介商经济地位新探[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1):42-51.
[14] 郭梁.近代以来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1914-1996年)[J].华侨华人研究,1997(2):58-65.
[15] 荷印华侨之势力[J].外交部公报,1929,2(6):69.
[16] 刘士木.日本海外侵略与华侨[M].广州: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1.
[17] 季啸风.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87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8] 古鸿廷.东南亚华侨之认同问题(马来亚篇)[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19] 季啸风.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91册[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0] 陈嘉庚.我国行的问题[M].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6.
[21] 爪哇通讯(六)续[N].申报,1919-06-24(6).
[22] 明石阳至(Yoji Akashi).1908-1928年南洋华人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上)[G]//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资料译丛:第3辑.2000.
[23] 刘士木.日本之南生命线·译者序[M].中南文化协会,1935.
[24]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C]//李世涛.知识分子的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时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刘文俊]
Some Thoughts on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by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ZHANG Jian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 China)
Overseas Chinese are seen as peaceful economic settlers and since World War I,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gradually become a sort of economic entity which is comparatively independent from Chinese economy as they gradually become localized. Their actions are affected by China as well as their local social status. And since modern China,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re minority that are politically discriminated and maltreated. Thus, before and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ir local development suffered greatly direct loss as their movements of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is mutual as their movements of boycotting Japanese goods resemble the movements of amending unequal treaties which reflects that they expect to receive effective protection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economic plunder in Southeast Asia and to safeguard their equal local righ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ti-Japanese War;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10.16088/j.issn.1001-6597.2016.06.021
K333.8
A
1001-6597(2016)06-01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