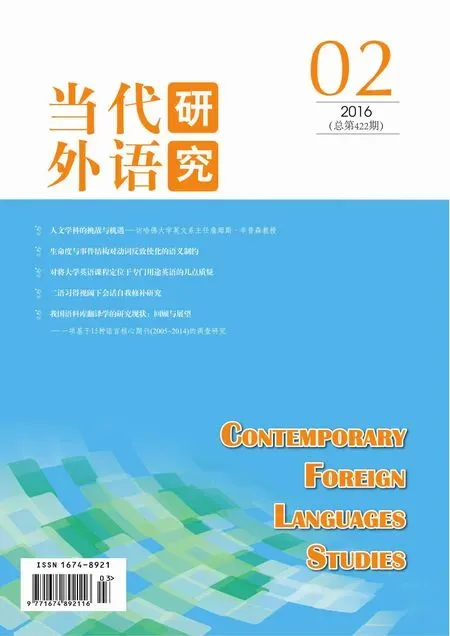翻译、改编与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
——《鲁滨逊漂流记》的个案考察
周红民
(南京晓庄学院,南京,211100)
翻译、改编与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
——《鲁滨逊漂流记》的个案考察
周红民
(南京晓庄学院,南京,211100)
摘要:在译学研究中,“改编”与“翻译”的界限一直十分模糊,如果将“翻译”与“改编”搁置在文学经典的传播空间加以考察,改编完全可以游离于翻译行为之外,作用于文学经典的传播。翻译将外国经典引入一种文化,然而它远远没有宣布一部经典的终结。翻译行为一旦完成,它就开始构建自己的体系,广义地说,这一体系由重译者、改写者、作家、批评家、教师、书商、图书馆和读者共同完成。据此,以《鲁滨逊漂流记》为考察对象,厘清翻译与改写的关系,理性地认识翻译在经典传播中的尺度,改写在外国经典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翻译,改编,关系,经典传播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6.02.014
1.
在译学研究中,“改编”与“翻译”的界限十分模糊,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们常常将改编当做翻译过程中的一种手段,放在语言转换层面来理解和定义。在这一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是温瑞和达贝内特,他们把“改编”列为翻译中的第七种步骤,如果原文的语境在目标语不存在,就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创造。这一广为接受的带有定义性质的观点把改编看做为一种局部的而非整体的策略,当文化出现不对应时,采用这一策略来取得语境对等。就改编方式而言,改编者可以采取以下步骤:(1)翻译原文:逐字复制原文某些部分,通常直译;(2)省略:省略或者隐含原文某些部分;(3)扩展:添加或者显化文本某些部分,可添加在正文中,或以脚注、尾注形式;(4)异国情调处理:将原文成串的俚语、方言、赘言用目标语大体对应的语言形式替代(有时用斜体或下划线标明);(5)更新:用对等的现代语言替代过时的、含糊的语言;(6)情景和文化对应:以现代读者更熟悉的情节代替古老的、现代人淡漠的情节;(7)创造:在保持原文基本信息、思想和功能的基础上,用目标文本全局性地替换源语文本(Bastin 2004)。显然,这种定义在翻译过程中的“改编”必然与翻译技巧有很多类同之处,只是为了生产流畅易懂、信息完整、功能对等、没有文化隔膜的译本而渗入一些非正常翻译方式罢了。
不可否认的是,改编的确可以寄生在翻译之中,翻译中的改编现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普遍存在,但充满变数,很难量化,给出清楚明晰的定义。正因为如此,译学家对改编归入翻译门类持否定态度,并时常与歪曲、盗用、伪造、占有等坏名声联系在一起。在西方,17世纪和18世纪是“不真实的美人”的时代,改编非常流行,它发端于法国,接着在各地流传开来。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的兴趣和阅读习惯,改编就显得顺理成章了(Bastin 2004)。 清末民初也是改编盛行的年代,虽然很多文本我们今天很难辨识是翻译之中的改编,还是先有翻译过的底本,后有写手就译本加以改编的“伪译”,但是,几位大师的翻译手法及主张有力地证明了改编的确是翻译中的常态。严复的“夹议夹译、取便发挥、附按语、颠倒附益”正是出现在翻译过程中;梁启超提倡的“归而记忆其所得,从而笔之”、“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 (陈福康2000:100) 的“舍文取义”法也属于此道;鲁迅从事翻译之初,其作品存在大量的改写痕迹。他承认,《地底旅行》“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又说《斯巴达之魂》是“抄译”和“偷来”的,“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所以“内容也就可疑的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缺乏知识产权概念的时代,译家对原作的处理极端自由,常常借取原著中某些章节、某一主题,由此地此景、社情民意出发,兴发所至,断章取义,渗入自己的想象,突出原著的某一方面,导致以译代作、译中有作、译作合流现象非常流行,正如西方翻译理论家佐哈认为的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原创与翻译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复存在”(周红民2013:21)。
20世纪后半叶,随着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的体制化、正规化和文本类型的增多,“改编”针对的文类发生了变化,而改编手段未曾改变。如果之前的改编出现在文学翻译中,可以随意改变作品的内容和面貌的话,那么现代翻译中的改编主要发生在应用文体和交际类文体中,表现在语言层面和信息整合上。在保证内容不失真的前提下,可以对原文的内容加以选择与舍弃,可以对全文进行适当的压缩、摘编、摘译或译述等,可以在全面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著内容进行高度概括,用准确简练的语言重述原著内容。如新闻翻译以“编”和“述”为主,“译”是“编”的基础和前提,“述” 是“编”的结果,“述”就是改变原新闻稿的叙述风格和口吻,将语言形式归化为目的语的新闻风格,确保稿件简明扼要,通顺流畅。某种新闻事件往往十分复杂,有多种新闻来源,仅靠一则报道就会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因此,报刊、电视新闻对国外的报道会综合各种新闻来源,加工整理,形成一个连贯的、自然的、无任何翻译痕迹的语篇;搞学问的人经常需要参照国外同行的观点,我们总不能把别人整篇论文照样翻译吧,怎么办呢,这时摘取对自己观点有用的进行翻译,这种称作“摘译”的翻译手段有时还不管用,因为原著者的观点很散,需要总结、浓缩,这时又得采取“编译”和“缩译”的办法。如果对他的观点赞同或者不赞同,还得说出个道道来,还得采取评述的方式(周红民2013:219)。我们可以发现,当今的“编译、浓缩、改写、删除、修正、缩译”等与严复时代“夹议夹译、取便发挥、附按语、颠倒附益”等并无二致,仍是改编的前世今生。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将改编定义在翻译内部来讨论,就很难适应其他文本的分析,我们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中很多文本现象。如在“读秀学术搜索”随便输入一部外国文学的书名,就会出现上百个,甚至几百个版本。有全译本、双语对照本、译注本、改编本(编著本、译写本、简写本、缩写本、编译本、节选本、梗概本、连环画本、改编加绘画本、插图彩绘本、导读本、 双语连环画本、美绘本、简易英汉对照本、影视剧本、影视剧英汉对照本、搞笑的演绎本)、原著注释本、影视阐释本、文学评论本、文论本、作者传记本、文学选集本,而“全译本”所占的数量非常有限。难道这么多的改编本都是在原著基础上再行改编而成吗?如果不是,我们怎样定义和看待改编,以及它与翻译的联系呢?这些显然在翻译内部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要认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脱离翻译内部这一封闭的系统,重新设置一个视角,将视线投向更为广阔的视域。本文拟将“翻译”和“改编”搁置在经典传播的空间加以考察,以期理性地认识翻译在经典传播中的尺度,以及改编在外国经典传播中的作用。
2.
毫无疑义,一部外国作品要在接受文化传播和流转,翻译是源头和起始。通过翻译,一部经典才具有超越时空而后生的生命,外国文学经典生存在翻译之中。但是仅有翻译并不能保证它在接受文化中的生命力,翻译所做的是让一部文学经典进入另一个文化时空,“经典文本通过翻译来到一种主流文化的边缘,然而翻译行为远远没有宣布一部经典传播的终结,接下来的问题:是谁在翻译经典?翻译过程得到了什么?又失掉了什么?与翻译相关的群体是怎样成就翻译经典的” (Lianeri & Zajko 2008)。翻译行为一旦完成,“它就开始构建自己的体系,广义地说,这一体系由重译者、改写者、作家、批评家、教师、书商、图书馆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Armstrong 2008)。
《鲁滨逊漂流记》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历久而弥新的接受过程说明了它是一个围绕翻译、多方参与的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1902年沈祖芬翻译RobinsonCrusoe以《绝岛漂流记》之名首度面世时,是一个节译本。从翻译角度,它是一次不正规、不完美、不理想的翻译,但它并没有因此失去其翻译的“正统性”,也不因为它带来的“异质性”而遭到排斥,因为它应和了当时的社会语境。20世纪之交,是西学东渐正酣,有识之士在积极寻求救国之道,思想开始出现裂变的时代。两千多年来,封建意识、儒家伦理根深蒂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义悌、中庸之道致使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国家积弱贫困、落后挨打。在这种语境之下,故事主人公的开拓进取精神无疑带来新意,具有“开启民智”的作用,给译著的接受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意义正如高凤谦在此译的“序”中所言,“不恤呻楚,勤译此书,以觉吾四万万之众”(韩洪举2011:122),宋教仁在1906年读了这部小说后也说:“(鲁滨逊的)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可为顽懦者之药石。” (韩洪举2011:122)
首度翻译可以影响接受语境的价值体系,反之,接受语境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学传统也可以影响一部外来经典的存在形式,“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翻译改变了文本和接受语境,这一转变支撑了一整套的意义和价值观,它们与源语文本所支持的价值观几乎没有或者毫无关系。译者阐释中的语言选择、文学传统和效果,和文化价值可以强化或者修改流行在接受语境中的对外国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翻译巩固了原有的读者群,或者形成新的读者群体”(Venuti 2008) 。《鲁滨逊漂流记》不断重译和重写的过程为这一论点做了注脚。其后该书译本又有1906年林纾和曾宗巩合译的《鲁滨孙漂流记》及《续记》,从这时至20世纪40年代末,先后有李嫘、高希圣、彭兆良、顾均正、唐锡光、杨锦森、张保庠、徐霞村、范泉等做了节译和缩写工作,并先后被编入《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小本小说本》、《学生文学丛书》、《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初中学生文库》、《新中学文库》。1921年,上海崇文书局推出了严叔平翻译的《鲁滨逊漂流记》简写本。1931年到1948年间,该小说就出现了11种译本,翻译者有以后成为翻译大家的顾均正、汪原放、徐霞村等人,也有彭兆亮、李嫘、张葆庠、殷熊、范泉等一般译者。此时的《鲁滨逊漂流记》不但受到翻译者的青睐,还受到出版界和读者的宠爱,出版频率之高,发行数量之大都非其他外国文学作品所能比肩。新中国成立后名气较大的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徐霞村译《鲁滨逊漂流记》,1996年译林出版社的郭建中译《鲁滨逊漂流记 》,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杲忻译《鲁滨逊历险记》, 以及当代数百种出自众多名不经传的译手和写手的重译本和编写本。这一现象说明,RobinsonCrusoe一旦超度了自身的历史节点和空间,就会在接受语境中产生很多剩余意义,支撑了诸如独立、进取、探索、冒险、励志、拼搏、生存智慧等多重解释,成为汉语文化中不断弘扬的品质和能量,具有不断利用的价值和开发潜力。
对于这些重译现象,译界内部曾试图提出各种假设,然而放在经典传播空间来讨论,它们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第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假设是“不完美”论。伯曼(Antoine Berman)认为:“对于文学翻译,严格地说,单次翻译属于一次未竟的行为,只能通过重译才能完成,任何翻译都会带来一种与生俱来的失败,首次翻译尤其如此。” (EHNAZ TAHIR GǔÇALAR 2009:233) 这一假设明显蕴含了“阐释学”色彩。意即,一部译著,只能是对原著的一种理解,一种阐释。一部译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传达,也就是说可以出现不同的翻译(许钧1998),因此任何翻译都是一次不完美的行为。重译完全可能改变原著的表现手法、语言意蕴和意趣,但是要说“一部译著是一种阐释”就意味着改变原著的主题和意义,如此,就显得非常勉强了。如《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在出海之前,父亲叫到床前开导了一番,想劝阻其外出闯荡。父亲历数了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各种生活和心理状态,认为中层人是最好的一类。任何译本,就连改编本都很少篡改这一情节。事实上,据作者观察,任何译本都保留了这一情节。
重译的第二种假设是“语言老化”。鲁迅就说:“因语言跟着时代变化,将来还可能有新的复译本,七八次何足为奇。”(陈福康2000:303)伯曼也认为,原著通过翻译可以永远保持年轻状态,但是其译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因此需要重译(EHNAZ TAHIR GǔÇALAR 2009:234)。语言过时引起重译也并非无懈可击。语言老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感悟到语言系统的变化。文言和白话的分野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如果说林译小说需要重译是因为语言过时倒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五四以后同一部作品不断用现代汉语重译,甚至同一文本在几近相同的时间内出现重译,就很难用“过时”解释了,重译和出版重译不能单单归结于前译的语言老化。
我们通过三个名家译本的对比,可以证明这两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徐霞村的翻译出现在上世纪30年代,时间之久本应显示与当代译本的语言差异,恰恰相反,由于它较少拘泥于原文反而比其他两个当代译本显得更加流畅。另外,三个译本虽然语言表述存在差异,但是都没有改变文本的情节和主旨。
(1) 徐霞村译本:
他叫我注意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同样会碰到生活中的苦恼和不幸;而处于中间地位的人就很少有这些灾难,同时也不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那样在生活上忽起忽落,变化无常。不仅这样,中等阶级既不像那些阔人一样,由于过着骄奢淫逸弄得身心交瘁;也不像那些穷人一样,由于过着终日劳苦,少吃少穿的生活而搞得憔悴不堪。(丹尼尔·笛福1959:4)
(2) 郭建中译本:
他提醒我,只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多灾多难,唯中间阶层灾祸最少。中间阶层的生活,不会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盛衰荣辱,瞬息万变。而且,中间地位不会像阔佬那样因挥霍无度、腐化堕落而弄得身心俱病;也不会像穷人那样因终日操劳、缺吃少穿而搞得憔悴不堪。(丹尼尔·笛福1996:3)
(3) 唐荫荪译本:
他嘱咐我说,只要我留心观察,我就会发现,不论上等人和下等人,他们在生活中都有灾难和不幸,而中间阶层的人却很少有这种不幸,也不会经受他们那种枯荣盛衰的无常变化;不但如此,中间阶层的人还不会遭受到像那些阔佬因耽于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的不道德生活而遭受到的许许多多精神上的忧虑和不安,也不会遭受到像那些劳苦大众因终年劳累、缺衣少食而自然造成的疲劳和困乏。(丹尼尔·笛福2010:6)
这一个案向我们表明:从翻译内部来看,重译与前译存在着一个既相互依赖又互为竞争的关系。一方面,重译者以前译为参照、为坐标,省却全新理解之苦,再取前译之长;另一方面重译者总带着苛责的眼光,总有自己的理由(纠正误译、错译、更新语言等)、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认识,如同翻译家郭建中所说:“重译者的任务除了使语言现代化之外,就是要利用前辈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改善前译本。这也就是为什么文学名著在不同时代均要不断重译,才能日趋完美。” (丹尼尔·笛福1996:6)重译者总想通过重译行为超越前译,“打着与先前翻译和文学规范相‘异’的旗号重新占有权威经典,以此证明这一行为既是一种敬畏,也是一种差异,获取新的文学资本,使传统为我所用” (Armstrong 2008)。但是,在这一不断接力的过程中,重译者尽管试图压制先前的译本,而他自身却只是一位匆匆的过客,他的名字和译著不断被后来者覆盖和刷新,最终在普通读者那里只有“永远的笛福”,“永远的《漂流记》”,而不是“某某翻译的《漂流记》”,换言之,只有永远的外国文学经典,没有永远的、经典的翻译,“只有不朽的创作,没有不朽的译作。任何翻译作品无论出自谁的手笔,哪怕是名家,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而绝不会万世不朽,无可替代” (林一安1998),经典的翻译只留在精英读者那里、后译者那里、翻译学者那里、译评家那里、双语读者那里。
这一“差异性”重译并不能控制和改变读者群的运动方向和层级,无意中重译就让渡了它的控制权,交给了出版商和写手。特别是在电读、闪读、浅阅读、碎片化阅读、读图的时代,原味的翻译和其他经典一样,只能“无可奈何独憔悴”,成了“死活也读不下去”的经典,由此重写就有了巨大的运作空间,而面对如此丰富多样的译本,写手们还会有谁对着原著重新来过呢?其实在历史上,写手一直活跃在文化的前台,但主要针对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重写译著的比重相当有限,如同勒弗维尔(Lefevere 2007:2)所说:“改写者一直与我们相伴相随:从希腊仆人编选的希腊经典用于教授罗马主人的孩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校对整理零散的手稿来出版较有可信度的希腊或罗马经典;从17世纪编撰者编撰第一部先前没有书面记录的希腊语或者拉丁语文学史,到19世纪的批评家给越来越多对文学毫无兴趣的读者阐释蕴含在经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甜美与轻松的品性;从20世纪的译者如同先前无数译者那样,试图将原著跨越不同的文化,到20世纪‘读者指南’的编撰者为那些非专业读者提供快速浏览,这些作品阅读本应成为非专业读者通识教育的精读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并没有读过。” 这些都是通过重写完成的,凡是经典作品都会受到后世的反复解读、注疏、改编与重塑,西方的荷马史诗、莎翁名著,我国的经史子集、四大名著等等莫不如此。
译著重写与自身经典重写的运作方式如出一辙,但是前者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译著重写虽然以译本为根基,但是外人很难看出重写的源头,读者认为读到了原译本或者原著的改编,而不是经由译本后的改编,改编本的封面上也赫然写着原著者的名字。改编者对译本的选择与译本在接受文化的认知度有关,认知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改编的对象,而认知度的获得与翻译的流传有关,如出版次数、教科书采用、文学评论、名人翻译等。改编者对译本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挑剔,他们并不在乎译本的质量,真实完整等等已没有实质意义,译本只是一个底稿而已,因为他们还要大动干戈、施行大手术,他们关注的是读者,译作的尊严可以漠视。
任何重写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市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译本重写有着不同的口味和要求。重写本主要针对四类人群:(1)青少年读者:历险、科幻、探案类是他们的最爱。针对这类读者,译著风格的多样性荡然无存,复调式的多重阐释简化为单一的主题。《鲁宾逊漂流记》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开拓进取,也获得了挑战自然的信心,读者已无法联想起资产阶级在其年轻、革命、上升时期的旺盛而自信的精神。《汤姆·索亚历险记》让我们见证了一个男孩子的成长历程。《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则教会我们要懂得珍惜生命、懂得自强不息。“《哈利贝克·芬恩》中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评价不见了,而只是个儿童冒险故事。《莫比·狄克》中所有的神秘性的成分没有了,仅剩下船长哈伯与鲸鱼搏斗的故事 。”(约翰·弥尔顿2000)(2)外语学习者:以外汉对照、左右对排的方式,方便语言学习。这种编写往往不是某个原本和译本的完整本,而是节选本,或者萃取几种作品合集,其翻译一般不会跳脱原文的范围,语句顺序的变化不大,词义不能过度引申、发挥,少用汉语句式和习惯法。(3)专业读者:针对外国文学研习者和教学者,及以升学、升职为目的会考人。这类读者本应提供完整的译本,而事实恰恰相反,它往往是写家的串讲本,有名段赏析、写家分析、作家生平、作品背景、相关链接,提供一系列保姆式服务。(4)休闲类读者:主要指参与阅读的芸芸众生、社会大众,他们没有专业背景、专业目的,其阅读行为是随意而发,无针对性,只要引发兴趣和好奇,任何读物都能纳入其阅读。对此类读者,重写本以最大的包容心,尽量取悦讨好他们的口味。重写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制造噱头”,强调先声夺人的效果。它有三种表现形式:(1)吆喝式、广告式语言:出现在封面或者封底。(2)编辑或者重写者絮语:出现在序言部分,具有耳边夜话,“润物细无声”的性质。(3)名人客串:名人作序或者留言。虽然三种形式之目的是推广宣传促销,但它们让经典走向了大众,让大众亲近了经典;二是强调“眼球效应”。表现在以图片阐释作品的内涵:有的利用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照,有的用动漫,有的整篇连环画加题图文字,以创造一种轻松、新颖的阅读方式。由于图片稀释了语言,将复杂的情节转化为直接的感官形象,读者注意更多的是图片,而不是语言及思想内涵。
重写的关键部分在语言。浅易化、时尚化、明朗化是这类重写本的主要特点。其表现在:主题修改得符合读者口味,剔除不规范的语言和方言,添加时尚元素,离奇曲折的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简化为明白单一的叙述。为了取得这一效果,常将段落删减(删除与现代人无关的情节)、串并(将上下段落或相隔甚远段落整合)、添加(添加写手的想象、目标语言元素和时尚语言元素,以目标文化或现代眼光阐释外国人伦价值,如“好男儿志在四方,留在家里有什么意思,”或过度渲染某一情节)。如《漂流记》开篇介绍了主人公的家世和Crusoe之名的来历,交代较为详细,但到了重写本那里都简易化了、明朗化了,全译本那种翘舌费力的阅读效果消失了。
全译本:
我于1632年出生在约克市的一个上等家庭。我原本不是英国人,我父亲本来住在德国的不来梅市,迁居到英国后,开初住在赫尔市,在那里经商赚了一大笔钱,后来便放弃商业,在约克市安了家。住到约克市之后,他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姓鲁宾逊,是英国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这样,我的名字也就叫鲁宾逊·克鲁兹纳。但由于英国话通常产生的传讹,现在人家都叫我们“克罗索”,而且就是我们自己称呼自己或是书写姓名时,也都将“克鲁兹纳”改成了“克罗索”。这样,我的同伴们也就经常这样称呼我了。(丹尼尔·笛福:2006:1)
重写本:
(1)我的父亲是德国人,他年轻的时候来到英国胡尔城赚下了一份家产,后来就搬到约克城,娶了我母亲。一六三二年母亲生下了我,因为母亲的娘家姓鲁滨逊,父亲就给我起了鲁滨逊·克鲁索这个名字。(丹尼尔·笛福:2009:1)
(2)我的名字就叫鲁滨逊·克鲁索,1632年出生在英国约克市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我父亲原本是德国布莱梅人,后来,他到英国来经商,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挣了一份不错的家产并在约克市定居下来。我的母亲美丽而又善良,是当地一户富裕人家的女儿。(丹尼尔·笛福:2006:1)
(3) 我叫鲁宾逊,1632年出生在英国的约克城,我是家里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就十分调皮任性,我行我素的,所以我也是家里最令父母亲头痛的一个。(丹尼尔·笛福:2010:1)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一个普通读者对着一本外国文学经典可以“孤灯挑尽未成眠”的话,那么今天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过往,那种持着耐性深入阅读、陶醉于小说情节、随主人公的情绪起伏不定或喜或悲的读者已经大大减少,如果还有人愿意阅读外国文学的话,他们大多转向“低度阅读”、“浅阅读”、“强制性阅读”、“碎片化阅读”、“浏览式阅读”、“功利性阅读”,为应考、写评论、消遣而阅读部分章节、故事梗概、作家生平、评论、妙笔生花式的简写本。“伟大的小说传统,尤其是19世纪的小说,很多著名的作家,如斯威夫特、狄更斯、简·奥斯汀、司各特、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巴尔扎克、麦尔维尔、司蒂文森的作品,大众就以这种方式算是已经读过了。”(约翰·弥尔顿2000:150)
3.
虽然翻译中的改编非常普遍,但是放在经典传播的空间,翻译和改编有着另一层关系,它是以翻译为缘起的,尔后由出版商和写手共同完成的一系列文本运作。这些行为虽然游离于翻译过程,与翻译行为毫无关联,但对翻译成品十分依赖。它与翻译中的改编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时间上,先有翻译,后有改编;在行为主体上,先有译者,后有改写者,两个主体互不交集。总之,没有翻译就没有后续的简写、缩写、编写、节选等行为。只因为后续改编与翻译中的改编生产文本的目的相同、效果相同——让源语文本适应目标语文化,产生流畅易于接受的文本,同时又代表了源语文本,因此后续改编常被读者当作翻译接受,但我们不应当做翻译看待,否则会贴上“劣质翻译”、“投机取巧”、“赝品”等道德标签。我们必须当作另类文本看待,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它对传播经典的积极作用。虽然出版商在争先恐后、花样翻新地运作这些以翻译为缘起的外国经典,适应不同的阅读群体,以期转化为经济资本,但不可置疑的是,这种运作不但证明了某一外国文学经典在接受文化中具有价值,而且还因为它不断被重释、重写,具有增值的潜力,进而巩固了一部经典在接受文化中的地位,延续了它的生命。我们通常认为重译可以延长外国文学经典在接受文化中的生命,但是经典生命的延续不单依赖重译,更需要重写(改编)这种运作方式,需要评论、阐释、出版保持它的地位,需要通过被教科书采用、碎片化重写与阅读来保持它的活力。特别是在信息时代,重写还会衍生更多的形式,文本可以完全被肢解、被掏空,外化为视觉意象和听觉冲击,重写完全可以脱离文本,“图像、动画、声音等多维文本超链接的网络世界,可以实现瞬息间的跨时空,并可以让逝去的一切重新以现代的方式活动起来”(谭军武2003)。
参考文献
Armstrong, R.H. 2008. Classical translations of the classics: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tradition in translation epic poetry [A]. In A. Lianeri & V. Zajko (ed.)Translation&ClassicIdentityChangeintheHistoryofCultur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0-71.
Bastin, G.L. 2004. Adaptation [A]. In M. Baker (ed.)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5-7.
Lefevere, A. 2007.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Lianeri, A & V. Zajko. 2008. Still being read after so many years, rethink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translation
[A]. In A. Lianeri & V. Zajko (ed.) .Translation&ClassicIdentityChangeintheHistoryofCultur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4.
Venuti, L. 2008. 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canon formation [A]. In A. Lianeri & V. Zajko (eds.) .Translation&ClassicIdentityChangeintheHistoryofCulture[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陈福康.2000.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丹尼尔·笛福.1959.鲁滨孙飘流记(徐霞村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丹尼尔·笛福.1996.鲁滨孙飘流记(郭建中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丹尼尔·笛福.2006.鲁滨逊漂流记(郑建、张波编写)[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丹尼尔·笛福.2009.鲁滨逊漂流记(左如科改写)[M].南京:译林出版社.
丹尼尔·笛福.2010.鲁宾逊漂流记(唐荫荪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丹尼尔·笛福.2010.鲁滨逊漂流记(世界名著编委会编)[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韩洪举.2011.浙江近现代小说史[M].杭州:杭州出版社.
林一安.1998.大势所趋话复译[A].翻译思考录(许钧编)[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56.
谭军武.2003.当文学经典遭遇时尚网络[J] . 文艺理论与批评(3):80-83.
许钧.1998.翻译不可能有定本[A].翻译思考录(许钧编)[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34.
约翰·弥尔顿.2000.大众小说的翻译(查明建译)[A].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谢天振编)[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45-50.
周红民.2013.翻译的功能视角——从翻译功能到功能翻译[M].北京: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管新潮)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921-(2016)02-0080-05
作者简介:周红民,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电子邮箱:hmz1213@126.com